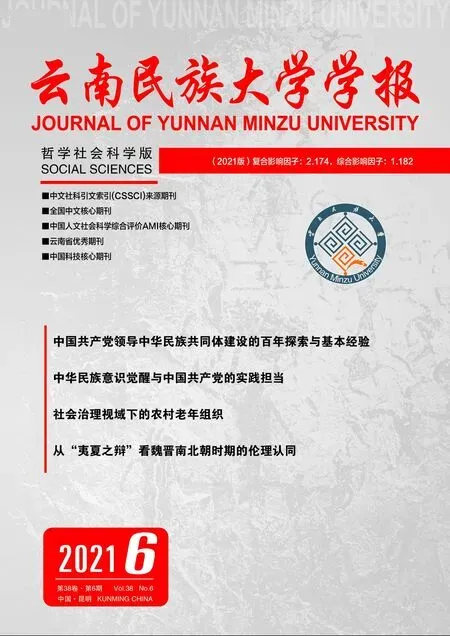云计算服务商著作权间接侵权研究
董京波,唐 磊
(1.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北京 100088;2.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作品的数字化,盗版作品在网站上随处可见,网络用户可以轻易接触并下载作品,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就成了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现如今,云计算的出现使得这样的问题更加严峻,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为用户之间提供数据共享,用户只需使用账户和密码即可登录获取存储云中的大量软件,图片,音乐与电影等作品,而在此过程中云服务商并不掌握用户拥有的数据情况。云计算的秘密性、复杂性和信息检测困难等特点使对既有间接侵权理论形成挑战,如何界定云服务商的注意义务,从而认定其主观过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本文结合国内外立法和司法实践,提出技术中立原则应与侵权标准相结合、运用利益平衡原则界定云服务商的注意义务,并结合云计算技术的发展阶段动态判定云服务商是否存在主观过错。
一、间接侵权理论及其最新发展
(一)间接侵权简介
侵权行为分为两种: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未经权利人许可,在无法定免责事由的情况下擅自利用作品的行为,并且构成直接侵权行为并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间接侵权行为可细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教唆、引诱以及故意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的预备行为、扩大侵权后果的行为。(1)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241页。
云计算实际上为用户提供的是一种服务,其所提供的云服务具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即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以及SaaS(软件即服务)。若将这三种服务模式对应到目前市场上已有的云服务,则可以有以下三种具体表现形式:第一种是云服务商直接为用户提供其所需的数字资源,如音乐、图片、影视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等;第二种是云计算服务商主要作为一个“中介”,提供一个互通平台,使得不同云服务用户之间的资源共享成为可能;最后一种是云服务商仅仅为云服务用户提供接入云的服务,此时这些用户通常是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软件运营商。在第一种云服务的情况下,当云服务商所直接提供的资源没有获得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或超越了其授权范围,那么其行为直接侵犯了相关著作权,属于直接侵权行为的范畴。然而在后两种类型的云服务中,由于云服务商所提供的“桥梁”共享服务或者接入服务而造成了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侵犯,则落入了间接侵权行为的范畴。鉴于对云计算中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与对一般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无异,故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少;相反,对于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更为复杂且难度较大,所以有关间接侵权的争议与讨论一直存在。
著作权侵权中的间接侵权理论最初来源于英美法系,指的是行为人虽没有直接实施损害权利人合法著作权的违法行为,但行为人故意教唆、引诱他人实施直接侵害权利人著作权的违法行为,或者行为人为他人即将实施或正在实施的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提供帮助。(2)See Melvile B. Nimmer & David 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 13. 05[2],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 (2003).由该定义可以看出,认定间接侵权行为需要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同时具备。主观因素具体表现为明知或应当知道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客观因素则是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帮助、引诱与教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如前文所述,可能落入间接侵权范畴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为用户提供的是一种平台或接入服务,以实现用户之间的数据共享,如果用户将该云服务用于侵犯著作权,而云服务提供商明知或应当知道该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则云服务提供商实际上为侵权人的间接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
然而,相较于更为容易认定的客观行为,对于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构成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认定难度较大。例如云服务提供者都会提供的接入和传输服务、信息存储服务、信息定位服务等(3)张耕,黄细江:《略论云计算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期。客观存在、有迹可循的行为,当其造成实际侵权时,对于其侵权的认定是较为简单的。但是,当云服务提供商对其用户的数据以及利用云计算客户端实施的私密行为负有保密义务时,特别是在“私有云”(4)戴哲:《云计算技术下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载《青海社会科学》2014 年第5期。“私有云是一种架设在本地服务器端,供政府或企业的内部人员使用的云服务。私有云也被称为内部云。”的环境下,法律规定云服务提供商不能对用户的数据和行为进行监控或干涉。在这种情况下,若云计算用户利用云计算客户端实施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如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授权上传其作品等,则很难认定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具有主观过错,即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因此,在涉及云计算技术的案件中,过去得以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应知用户侵权的主观过错的认定方法放在当下往往难以适用。只有当云服务提供者积极地推动某项侵权行为发生,或者明确告知外界其会提供侵权帮助时,法院才能够认定该云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由其行为产生的引诱侵权责任。(5)戴哲:《云计算技术下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载《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纵观国际条约与各国法律规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在其第45条规定(6)《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45条的内容为:(1)对于故意或有充分理由应当知道自己从事侵权活动的侵权人,司法机关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足以补偿其因知识产权侵权所受损害的赔偿;(2)司法机关还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有关费用,其中可包括有关的律师费用。在适当的情况下,各成员国可授权司法机关责令其退还利润或支付法定的赔偿,即使侵权人故意或有充分理由知道自己从事侵权活动。中确立了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无过错责任原则为补充的侵权责任认定规则。而德国日本美国主要采取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在我国,目前法学界在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上基本形成共识,即在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案件中,侵权责任认定应当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没有过错就无须承担责任,这种认定规则也符合我国民法立法与其理论体系。(7)王娟娟:《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责任思考》,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30期。总体而言,云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也包括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其中间接侵权与侵权责任法上的第三方责任有着紧密联系。关于第三方责任,美国和欧盟分别在《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和《电子商务指令》(Electronic Commerce Directive)中规定了相关内容,我国也先后建立了相关侵权认定与责任制度,使得著作权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免于受到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帮助侵权行为的侵害。此外,在《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中我国还确立了“通知-删除”规则,(8)“通知-删除”规则具体体现为网络著作权人在其著作权受到侵害时,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对由该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扩大部分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主观过错,即知道其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但该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与侵权人就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该部分内容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得到继承并进一步完善。
(二)间接侵权理论的发展:从技术中立原则到引诱侵权原则
技术中立原则,又称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是指如果一项侵权行为兼具合法目的与非法目的,则该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可以被免除。在1984年“索尼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侵权认定中首次引用了“实质非侵权”理论,认为当技术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兼具合法用途与非法用途时,由此产生的侵权责任可以被免除。(9)梁志文:《云计算、技术中立和版权责任》,载《法学》2011年第3期。而在信息网络传播领域中,技术中立原则具体体现为“网络技术中立”,其内涵在于,即使技术服务提供者知道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可能会被用于侵权,但也不能仅因确有用户使用该产品实施侵权而由此推定该技术服务提供者具有主观过错,并进而推定其构成间接侵权。网络的创造者使用了一种终端对终端的模式,使得网络处于桥梁作用,而不对两端的用户行为进行审查和干扰,这即是网络技术中立体现。(10)Michael P. Murtagh, The FCC, the DMCA, and Why Takedown Notices Are not Enough, 61 Hasting L. J 233, 240 (2009).这一原则也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11)Tomes A. Lipinski: The myth of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in Copyright and The Rights of Institutional Users: Recent Legal Challenges to the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as Mediator and the Impact of the DMCA, WIPO, and TEA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3, pp.824-831.技术中立旨在寻求促进作品传播与保护作品著作权之间,著作权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
单从技术中立原则本身出发,技术提供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免责。然而,随着著作权网络市场的逐渐繁荣,技术中立原则所确立的认定标准已然面临挑战,仅靠技术中立原则难以提供足够的保护。此时法律在建立责任认定标准时,侧重点已从如何坚守技术中立原则转变到如何平衡网络著作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商间的利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实质非侵权”规则会遭受多方置疑,以及为什么各国学术界和司法实践对新的侵权责任认定规则会如此渴望。
“索尼案”的强烈争议说明了仅依靠技术中立原则来平衡权利人与服务提供者之间利益的路已经走不通了。在这种前提下,寻求多种解决方式则成为必要,引诱侵权责任的引入便是其中之一。在美国Grokster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引诱侵权责任进行了具体解释,其是指技术服务提供者通过广告等方式来宣传商品或服务的侵权用途,或者釆取其他积极措施引诱和鼓励他人实施直接侵权行为,技术服务提供者的这种暗示行为可以表明该商品或服务将被用于侵权的确定性意图,且将被认定为构成引诱侵权。此时技术中立原则被排除,即使该项商品或服务兼具其他合法用途,技术服务提供者仍然要为用户使用该商品或服务所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由该案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许多新兴的侵权责任认定规则的出现,技术中立原则的地位已然受到挑战。引诱侵权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技术中立原则,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排除了后者的适用。事实上,技术因素并不应当阻碍知识产权保护的顺利开展。如果已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他人实施侵权行为提供帮助,却由于技术中立原则的庇护而使其能够逍遥法外,这实属与法之正义相悖。因此仅仅适用“实质非侵权”理论的处理方式是不恰当的。但这并非完全否定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其仍具有存在的价值。技术中立原则仍将是维系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与网络发展的利益平衡器,只不过还需要如引诱侵权责任规则这样的其他规则来进行微调,以保障整个制度的正常运作。
在美国Grokster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过滤措施或其他等效机制来减少或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否则,其没有采取任何必要措施的消极不作为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为其网络用户提供侵权帮助的主观意图的证据。在云计算环境下,网络服务提供者虽无义务去阻止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发生,但仍应负有努力减少此类侵权行为发生的注意义务。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是要求云计算服务提供者对每一个云服务进行审核,而是主张云计算服务提供者应从一个服务管理人的角度出发,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尽到自己的必要注意义务。如何维持云计算产业发展与网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网络著作权法“利益平衡”原则一直在探索的,最终是为了在著作权财产权属性和人身权属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多方利益平衡的核心在于如何界定云计算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保护义务。传统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最主要的保护义务来源于著作权所确立的专有权利,作为一种绝对权,其要求除权利人以外的所有人负有未经许可或无法定情形下不得行使作品著作权的义务。然而在当今社会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传统著作权立法的滞后性已经愈来愈明显,仅依赖著作权人所拥有的专有权利来划分云计算服务提供者的保护义务已经出现明显的局限性,难以满足网络著作权人权利保护和互联网产业发展之间“利益平衡”的要求。
(三)间接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从无过错责任到过错责任
以《数字千年版权法》为代表,规定过错责任作为著作权间接侵权的归责原则,即网络服务商主观过错的认定标准是预先已经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以及其收到著作权人的通知知道有侵权行为的发生两种。《数字千年版权法》对网络服务商著作权间接侵权归责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其通过立法平衡了著作权人和网络服务商双方的利益。
在我国,《民法典》和《著作权法》中均没有明确规定间接侵权这一侵权类型。目前我国在司法上主要适用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该条司法解释规定了帮助侵权和教唆侵权两种类型,(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教唆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但是其并未对帮助或教唆的行为是否属于间接侵权行为作出判定。根据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97条规定,我国法律对于著作权间接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具体标准体现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事实的主观状态为知道或应当知道。(13)《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我国《网络侵权司法解释》第8条进一步设定了明知和应知的具体判定标准。(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确定其是否承担教唆、帮助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包括对于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过错。在电影《金陵十三钗》著作权侵权一案中,百度公司虽未直接上传作品,但其向其他用户推荐了相关侵权内容,客观上扩大了涉案作品的侵权范围与损害后果,故认定其具有主观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15)王巍:《“乐视诉“百度云”侵犯电影传播权百度败诉”》,载《新京报》2016年8月30日。
(四)间接侵权免责要素的认定:避风港原则及其限制适用条件
过度加重网络服务商的责任不利于技术创新,故美国法中的“避风港原则”应时而生。避风港原则为网络服务商创设了一定的免责条件,除非网络服务商明知侵权行为,否则其对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侵权后果可以免于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确定网络服务商是否最终承担侵权责任,还应考量其是否符合免责条件,即是否符合避风港原则适用条件。避风港原则是针对间接侵权行为的一种免责规定。根据避风港原则,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既不明知又没有理由知道用户利用该技术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那么服务提供商可以对其服务行为造成的侵权后果免责。该规则来源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16)避风港规则来源于美国《千年数字版权法案》(DMCA法案)第512条的规定,该条(a)该条(a)款是关于临时数字网络传输的避风港条款,(b)款是关于系统缓存的避风港条款,(c)款是关于根据用户指令进行存储的信息存储系统的避风港条款,(d)款是关于信息定位服务商的避风港条款,其中(c)款是网络侵权案件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援引最多的条款。此条款被简述为“通知—删除”规则(notice-take down procedure)。(17)美国《千年数字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第512条(c)款的具体内容为:服务提供者因为根据用户的指令将存放在由服务提供者控制或经营的系统或网络中材料加以存储而侵犯版权的,服务提供者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或除第(j)款规定的情形以外,也不承担禁令或其他衡平性救济的责任,如果该服务提供者:(A)(i)实际上不知晓系统或网络上的材料或者使用材料的行为是侵权的;(ii)在实际上不知道的情况下,没有意识到能明显推出侵权行为的事实或情况;(iii)在知道或者意识到侵权行为之后,迅速移除材料或屏蔽对它的访问。(B)在服务提供者具有控制侵权行为的权利和能力的情况下,没有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以及(C)在收到版权人声明的侵权通知后,立即移除被指称侵权材料或屏蔽对其访问。(18)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public law 105-304-OCT. 28,1998具体而言,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网络服务为他人的直接侵权提供了便利时,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直接侵权行为不知悉或者在收到权利人通知后及时删除相关链接,则可以适用避风港原则而免于承担间接侵权责任。
但避风港原则并非绝对原则,红旗原则便是一个典型例外,其在一定程度上对避风港原则予以限制,避免避风港原则被滥用。当侵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十分显而易见,就像红旗飘扬一样显眼,那么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就不能假装看不见,或者以不知道该行为是侵权行为为由来推卸责任。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权利人未发出通知,也应当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相关行为是属于侵权行为的。红旗原则进一步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条件,即只有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明知或不应知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时,才得以免除其间接侵权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避风港原则适用的限制条件。
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当然也适用于有关云计算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之中。2011年8月,历经四年的百代诉Mp3tunes一案终于落下帷幕,结束了“云音乐”第一案。该案涉及的云服务提供方式——“软件即服务”(SaaS)(19)何怀文:《百代诉Mp3tunes案:“云音乐的避风港”——兼评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载《中国版权》2012年第3期。,使用户能够更加便捷的获取音乐,提高了用户播放和享受音乐的体验,但同时也威胁到了其他音乐公司,鉴此以百代公司为代表的15家音乐公司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判定MP3tunes的行为构成版权侵权。但法院支持了Mp3tunes援引避风港原则的辩护主张,认为其只是为用户的音乐文件提供存储服务而并未直接编辑,所以不可能构成直接侵犯,由此便落入到避风港原则的保护范围。同时,法院还适用了红旗原则,认为涉案的侵权行为应当是清晰且显而易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无需通过进一步调查就可以发现该侵权行为,甚至不需要基于一般人的最低理性的调查,很明显按照此种解释红旗原则的适用范围也将变得极其狭窄。不过尽管MP3tunes无须承担侵权责任,但仍应当删除侵权作品的相关链接,并对已经加入云音乐盒中的侵权音乐进行删除以免除其间接侵权责任。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也引入了避风港原则。比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分别体现于第14条和第23条。(20)《条例》第14条规定:“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被删除、改变了自己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一)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二)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三)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第23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的避风港原则体现在该法第1194条、第1195条以及第1197条。(21)《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94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1195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1197条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我国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将相关立法中的“知道”细分为明知或者应知。该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了两种可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情形以及一条兜底条款。这种对“应知”的认定规则即是“红旗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具体体现。
与美国给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以极大便利相比,我国的红旗规则显然适用范围更为广泛。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的规定和最高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对热播组拼进行编辑、整理和推荐的或其他可以明显感知作为为未经许可提供的,则可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知道”侵权活动。一般情况下,是否明知应以民法原则规定的基于一般人的善良注意义务的标准进行判断。然而,当用户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大规模影响时,例如被传播的作品属于正处于档期或热播、热映期间的影视作品,依照一般人的善良注意即可知其是在投入大量成本后创作而成的,著作权人不可能会让这些作品在网络中免费传播,故对于此类作品,应当要求云服务提供者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而不问该云服务提供者是实行平台即服务模式还是软件即服务模式。这些云服务提供者从存储、传播文件名称可以知晓侵权可能,对于内容也具有审查的可能性,在相关侵权作品时长较长的情况下,还需要云服务提供者采取屏蔽或删除等必要措施(短时间的片花、宣传片不在此列)。(22)张耕,黄细江:《略论云计算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期。此时如果云服务提供商明知或应当知道该侵权行为而未采取任何措施,如没有删除相关链接和数据或纵容该侵权内容的传播,则不能够使用避风港原则免责。
关于避风港原则,值得一提的是涉及百度文库的一系列案件。近年来百度文库多次陷入著作权争议诉讼和作家们的集体声讨。然而实际上百度文库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其并不参与文档的上传、下载等交互过程,信息资源的共享完全是由网络用户自己完成。以历时一年多的盛大文学诉百度文库侵权案为例,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百度文库侵犯了盛大文学网站上的部分作品的著作权,百度文库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原告享有对该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侵权链接的存在,却未及时删除信息或断开链接,构成间接侵权(23)《盛大文学状告百度文案侵权一审胜诉,百度将上诉》,中国财经网,http://www.chinanews.com/it/2011/05-12/3036681.shtml。在这个案件中,百度文库以避风港原则抗辩,但是由于其并未采取及时删除信息或断开链接的必要措施,不符合避风港原则的适用条件,故百度的主张未得到法院支持。无独有偶,在北京中青文化诉百度文库一案中,法院认为针对浏览量与下载量较高的文档,百度公司以一般人的认知标准,只要施以普通的注意义务即可发现在其百度文库内的作品取得合法授权的几率极低,即其构成著作权侵权的可能性相当大。然而百度公司对于这些文档审查缺乏合理注意义务,存在“应知”的主观过错,构成帮助侵权行为,法院同样不支持百度公司以避风港原则为由来规避责任。这便是红旗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由百度公司相关的一系列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过错问题,其核心在于如何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如果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已采取必要措施并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仍无法阻止侵权发生,此时应当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存在主观过错,亦不构成著作权间接侵权。
由前文可知,避风港原则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著作权权利人和网络技术发展之间的利益平衡,故司法实践也在不断地调整避风港原则以及“通知-删除”规则的具体适用。在乐动卓越公司诉阿里云公司一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提供云服务的阿里云公司并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在该案中,二审法院认定阿里云公司提供的云服务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且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制范畴。涉案的《MT畅爽版》是侵权人非法复制由乐动卓越公司制作的《我叫MTonline》的游戏数据包,侵权人将涉案游戏数据存储于阿里云的服务器中,并以http://callmt.com网站为平台运营并获取非法利益的侵权游戏。乐动公司曾先后两次通知阿里云公司,但均无果。一审法院认为,阿里云公司作为云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合理必要措施防止损害后果持续扩大。然而,阿里云公司表示数据隐私保护是阿里云的生命线,作为云服务器提供商,无权审查任何用户数据。一审裁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二审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对于要求阿里云在接到乐动卓越通知即“关停服务器”或“强行删除全部数据”,可能会严重影响云计算行业甚至整个互联网行业,不符合审慎合理的原则。同时,云计算服务不同于普通的网络服务,其在技术层面、主要架构层面以及法律监管层面均有其特殊性,故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提出可以将“转通知”作为独立的一项义务,用以证明云服务提供者确实采取了必要措施,而非机械地适用已有的“通知-删除”规则。此外,二审法院还审查了通知的有效性,认定由乐动卓越公司发出的通知中存在瑕疵,不足以引起阿里云足够的注意。故二审法院改判阿里云公司胜诉。(24)参见(2017)京73民终1194号民事判决书。
从乐动卓越公司诉阿里云公司一案中,我们能够察觉到我国司法机关对于涉及云计算技术的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新趋向。事实上,将“转通知”作为一种“必要措施”的观点最初出现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83号指导案例。在该案中,法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不应当局限于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的手段。这一观点在杭州刀豆“小程序”一案中也得到了支持。乐动卓越公司诉阿里云一案将第83号指导案例中的观点进行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在当今网络环境下,“转通知”本身具有成为独立必要措施的价值。云计算服务的体量虽大,但实际上云计算服务提供者对于其用户的数据的控制力却十分微小。如果云计算服务提供者要实现删除侵权内容的目的,其只能将整个服务器关停,而这显然是一种不恰当的解决措施,关停整个云服务器将影响其他用户的数据及使用,亦会产生巨大的运营成本,不符合利益平衡的根本目的。所以,在不适合直接采取删除、屏蔽或断开链接的措施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转权利人通知于侵权用户的行为一方面起到了对侵权人的告知和警示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云服务提供者并非消极的规避责任,放任著作权侵权行为,而是在积极的应对问题,避免损害后果持续扩大。而当“通知-删除”规则进一步完善成“通知-转通知”规则时,“转通知”作为一项独立的义务,其也被赋予了能够成为认定云服务提供者能否免责的标准之一的正当性。除此之外,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在二审判决中补充了关于如何认定有效通知的相关标准,其认为权利人的通知应当能够使云服务提供者直接定位到侵权内容。两个案例均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云计算网络环境下比例原则的理解。对云服务提供者科以过高的“必要措施”义务显然不是法律公正所追求的。在不抑制网络技术发展的前提下,为网络著作权人构建合理的维权体系,“通知-转通知”规则就是一次可期的尝试。
二、云计算服务对既有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的挑战
云计算为用户提供的是一种服务。该服务以提供音乐、图片、影视作品及文学作品等为内容,或者,为云服务用户提供一个平台,使得用户之间共享作品与资源。该服务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种是云计算服务商直接为用户提供其所需的数字资源,另一种是云计算服务上仅仅作为一个“中介”,提供一个”桥梁”,使得多个用户之间的资源进行共享成为可能。如果第一种服务行为没有获得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或超越了其授权范围,那么云计算服务商的行为直接侵犯了相关著作权,属于直接侵权行为的范畴;同时,如果云计算服务商提供的“桥梁”共享服务造成了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侵犯,则属于间接侵权行为的范畴,本文重点论述云服务商的间接侵权行为。一般来讲,间接侵权要件中的客观因素认定较为容易,即审查云服务商是否实施了帮助、引诱与教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而主观要件认定则相对复杂,因为云计算具有保密性、复杂性、信息检测的技术困难等特点,这些特点对认定云服务商是否“明知”和“应知”用户的侵权行为形成挑战。
(一)云计算的保密性导致云服务商间接侵权主观要件“明知”的认定难度较大
在云计算服务提供商间接侵犯著作权案件中,相较于更为容易认定的客观行为,对于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构成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认定难度较大。例如接入和传输服务、信息存储服务等(25)张耕,黄细江:《略论云计算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期。客观存在、有迹可循的行为,当其造成实际侵权时,对于其侵权的认定是较为简单的。但是,由于云服务提供商对其用户的数据以及利用云计算客户端实施的私密行为有保密的义务,特别是在“私有云”(26)戴哲:《云计算技术下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载《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私有云是一种架设在本地服务器端,供政府或企业的内部人员使用的云服务。私有云也被称为内部云。”的环境下,云服务提供商不能对用户的数据和行为提供监控和干涉,如果云计算用户利用云计算客户端进行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例如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授权上传其作品等,很难对此下结论认为云计算服务提供商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用户的行为而具有主观过错。因此,过去用以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的认定方法在云计算的大环境下则显得局限。只有当云服务提供者积极推动侵权发生,或明确告知外界其会提供帮助时,法院才能够认定其构成引诱侵权。(27)戴哲:《云计算技术下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载《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二)云计算的大数据、复杂性特点导致云服务商间接侵权主观要件“应知”的认定难度大,产生适用避风港原则抑或红旗原则的困境
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作为著作权侵权问题中的重要认定规则,当然也适用于有关云计算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之中。但是云计算的大数据、复杂性特点导致较难认定是否明知或者应知有侵权行为。
关于云计算中如何使用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比较有名的案件就是前文所提到的百代诉Mp3tunes案。在该案中,法院认为Mp3tunes只是为用户的音乐文件提供存储服务而并未直接编辑,能够落入到避风港原则的保护范围。同时,法院还审查了避风港原则的红旗标准,认为侵权行为应当是清分清晰且显而易见的,无须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进一步调查即可发现。据此可得,该案法院认为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仅仅是一般性的知道其所提供的网络服务被普遍用于此类侵权行为时,其是不足以满足红旗标准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是实际知道对特定作品存在特定侵权行为,才能够认定其适用避风港原则并构成间接侵权。
但与美国给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以极大便利相比,我国的红旗规则显然适用范围更为广泛,我国的司法实践也体现出这一倾向。以韩寒诉百度文库侵权案为例,百度以避风港原则为自己免责进行辩护,指出其对用户上传的数据并无管理,关键问题就是百度是否应知涉案作品存在于其文库数据库内,从而适用红旗原则。法院认为,基于韩寒的知名度及其曾就该作品侵权与百度进行协商而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力,百度应当对其文库中的内容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并且及时采取在能力范围内的必要措施。然而百度并未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也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法院继而判定百度公司具有主观过错。(28)参见(2012)海民初字第5558号民事判决书。可见,我国判定是否符合“应知”标准从而适用红旗原则时,条件较为宽泛。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中青文传媒公司诉百度”案件中,法院提出“阅读量/下载量最低阀值触发审查”理论,判决对该理论解释道,当某文档的阅读量或者下载量达到一定规模因而具备一定影响力时,可触发警报系统提醒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审查。本案中,该涉案文档的阅读量高达245045次,远超多数推荐文档的阅读量。故法院据此推知,涉案文档属于热门文档,百度公司应当基于必要且合理的注意义务并掌握该文档的相关信息。(29)参见(2018)最高法民再386号民事判决书。从法院相关案件的判决可以发现,我国法院对于直接提供用户所需资料的云服务提供者赋予了较高的注意义务,即当云服务用户上传资料之后,云服务提供者需要实时对热门文档进行监控,若这些浏览量与下载量巨大的文档明显不具备被合法授权的可能性时,云服务提供者就需要即刻采取必要措施,如删除、屏蔽的措施,否则会被认定为具备“应知”的主观过错,从而落入红旗原则的制约范围,成为避风港原则的例外,无法免责。
(三)云计算中信息检测的技术困难加大了对云服务商的过错认定的难度
云计算带来了极其庞大的数据和十分复杂的程序,这增加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信息进行必要审查和检测的技术困难。网络服务者并没有预先审查信息的义务,但其应有相应的检测义务。(30)参见(2012)海民初字第5558号民事判决书。在韩寒诉百度案中,百度公司专门强调,百度公司上线了反盗版DNA比对识别系统,减少了权利人因网络用户侵权行为而造成的损失,百度无过错。但是法官认为,单凭技术措施来制止侵权会存在限制性因素。(31)参见(2012)海民初字第5558号民事判决书。而对于显而易见的侵权文档,百度公司除了应负的对一般侵权文档的普通注意义务以外,还需要主动去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32)参见(2018)最高法民再386号民事判决书。当然,法院也承认技术措施本身存在的缺陷,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难以及时发现并制止部分侵权行为发生。哪怕网络服务提供者在采取措施后仍未能够制止侵权行为发生而存在主观过错,这并不意味着能够要求其承担在其能力范围以外的更高更重的义务。(33)参见(2012)海民初字第5558号民事判决书。从该案判决中,可以发现,单纯技术因素并不会直接决定云服务商是否有过错,比如韩寒案中百度强调的反盗版系统,法院要综合考虑案件相关因素,如是否是热门文档等因素,来判断百度公司是否应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但是如果百度已采取了相应措施,但由于技术因素,比如报警机制和反盗版机制中的技术缺陷导致其准确率等有问题,法院并不会因此认定百度有过错。
三、云计算服务间接侵权的应对思路: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合理界定云服务商的注意义务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云计算的保密性、检测困难等特点导致对云计算服务“明知”侵权主观要件较难认定,因此,确定其是否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则取决于其是否有“应知”义务,即其到底承担多大的注意义务。本文指出,技术中立原则应与侵权标准相结合、应运用利益平衡原则界定云服务商的注意义务,并结合云计算技术的发展阶段动态判定云服务商是否存在主观过错。
(一)云服务商由于技术困难而对用户失控时,技术中立原则应结合侵权法的责任认定标准,共同界定云服务商是否构成侵权行为
每当一个新技术出现,法律的标准都随之发生。正如Ginsburg教授所言:“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会使著作权体系发生变化。实践证明,当版权人欲排除一项新的传播技术,而法院认为该传播技术并非有害于版权人之时,法院则判决该技术的传播不存在侵权。但这并不是说法院每次都拒绝保护新技术威胁下的著作权。事实上,在新技术的出现之时,法院往往更关注‘控制潜在的新市场’,而忽略‘失去控制的原市场’。”(34)Ginsburg: Copyright and Control over New Technologies of Dissemination, Column Law Review, 2001, pp.1612-1617.Tomes A. Lipinski则认为版权侵权问题与技术之间并无显著关联,当新技术的传播带来著作权侵权问题时,应该适用已有原则,因为技术的发展不应当以阻碍知识产权保护的为前提。(35)Tomes A. Lipinski:The myth of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in Copyright and The Rights of Institutional Users: Recent Legal Challenges to the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as Mediator and the Impact of the DMCA, WIPO, and TEA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3, pp.824-831.同时,对于技术本身的设计而言,它并不考虑服务提供商、用户和著作权人的利益,唯一值得考虑的是该技术是否达到了本来的设计理念,这也是技术中立原则的内核所在。(36)Michael P. Murtagh, The FCC, the DMCA, and Why Takedown Notices are Not Enough, Hasting Law Journal,2009, pp.233-240.在网络环境中,虽然技术中立原则为实施了侵权行为的云计算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免责条件,但就美国相关的判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技术中立原则并不能代替侵权行为的认定程序。在涉及新技术的著作权案件中,“技术中立”原则不是决定存在侵权与否的充分条件, 也不能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离开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孤立地以“技术中立”推卸责任既不合法理又缺乏逻辑。(37)张今:《版权法上“技术中立”的反思与评析》,载《知识产权》2008年第1期。在这方面,澳大利亚iiNet案件具有典型意义。在该案件中,法院审查发现,iiNet接入服务商没有停止重复实施侵权行为的用户的账号,因而符合了传统意义上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且因为没有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而不能根据“避风港”来免责。但是法院并没有立即判定iiNet承担责任,而是进一步审查了iiNet的行为是否符合技术中立原则。法院认为,接入服务提供者难以控制网络用户如何使用该网络服务,故由此认定其不构成间接侵权。(38)关于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澳大利亚版权法》有两款相关规定:第一款是许可侵权的规定。许可侵权是澳大利亚版权法规定的一种间接侵权,它以被告控制他人侵权行为的能力为前提;第二款规定类似于美国DMCA以及我国《条例》规定的“避风港”,也就是免责条件。转王迁:“避风港”原则的适用问题,http://www.mysipo.com/article-2860-1.html在我国韩寒诉百度案件中,法院也认为如果百度采取了适当的技术保护措施,那么即使该措施在某阶段存在不足之处,也可认定百度公司已尽到注意义务,无主观过错,不构成间接侵权。因此,在涉及云计算的案件中,如因技术问题产生侵权,也需结合技术中立原则个案分析云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从而界定其是否构成间接侵权。
(二)针对云计算间接侵权中主观过错的认定难问题,应适用利益平衡原则界定云服务商的注意义务,合理判定云服务商是否存在主观过错
在新技术的挑战下,应努力实现著作权利人利益与云计算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鼓励更多的网络用户加入进来。贯彻利益平衡原则的核心在于云计算服务商的著作权保护义务的界定。过去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承担的最主要的保护义务来源于著作权法确立的专有权。然而,在云计算的环境之下,侵权行为变得更加容易和复杂,过度加重网络服务商的责任会阻碍新技术的发展,平衡著作权人专有权利与云计算服务商应承担的著作权保护义务需要具体制度设计。
在利益平衡这一原则指导下,对于云计算间接侵权中主观过错的认定难问题,应从公平公正的法理出发,以一个善良人的合理注意义务来要求云服务提供商,从而去认定其是否在其行为过程中具有过错。以美国Grokster案为例,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未采取必要前置措施来减少侵权行为的话,那么这种消极不作为可以被作为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为其用户提供侵权帮助的主观意图。我们鼓励云计算服务提供者以一个合理管理人身份在合理范围内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而并非主张其应审查每一个云服务。如果用户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大规模影响,比如当被传播的影视作品正处于档期或热播、热映期间,依靠一般人的注意即可知其是投入大量成本创作而成的,著作权人不可能会放任这些作品在网络中免费传播,故对此类作品,云服务提供者应当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39)张耕,黄细江:《略论云计算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云服务提供者放任侵权行为持续而不采取合理的必要措施,如对侵权内容进行删除、屏蔽或断开链接,又或者在不适合采取上述措施的情况下也未采取“转通知”等合理的必要措施以防止损害结果持续扩大,此时云服务提供者将被认定为具备“应知”的主观过错,构成间接侵权行为且无法适用避风港原则。
(三)结合技术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科学配置归责原则,平衡云服务商和著作权人利益
选择避风港原则给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以极大便利,抑或适用红旗规则更好保护相对处于劣势的著作权人,是科学立法面临的重要问题。考虑到在云计算的环境之下,侵权行为变得更加容易和复杂,网络服务提供者和著作权人的关系更为紧张,著作权人明显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因此倾向红旗规则有其应有之义。但同时,适当合理设置网络服务商责任往往相对更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下一阶段,我国应结合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进一步科学配置归责原则,在促进新技术发展的同时,充分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结 论
在涉及云计算服务商间接侵权案件中,侵权的客观因素认定较为容易,即审查云服务商是否实施了帮助、引诱与教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而主观要件认定则相对复杂,因为云计算具有私密性、复杂性、信息检测的技术困难等特点,这些特点对认定云服务商是否“明知”和“应知”用户的侵权行为形成挑战。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应将技术中立原则与侵权标准相结合、运用利益平衡原则界定云服务商的注意义务,并结合云计算技术的发展阶段科学配置相关归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