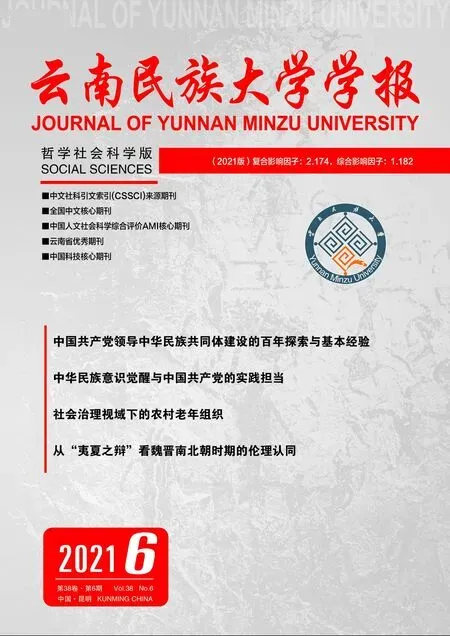外援帮扶与内生激励:“直过民族”整体脱贫的布朗族(莽人)模式
方 明, 徐伟兵
(1. 温州大学 华侨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2.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7)
一、问题的提出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版,第21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进帮助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的工作,尤其是自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更是高度重视扶贫脱贫工作,号召并集中全社会力量和智慧投入到打赢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中。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习近平:《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11-28/7646206.shtml,2019-3-9.作为“直过民族”,由于地处边疆,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是我国扶贫脱贫攻坚的重点与难点,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事关边疆稳定与民族团结进步。从某种程度来说,直过民族的整体脱贫是衡量我国同步小康社会的标尺,具有政治与经济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的布朗族(莽人)为个案,总结整体脱贫的布朗族(莽人)模式,以期能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解决类似的扶贫脱贫问题提供可资参考的样本,也能丰富始终致力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
学界有关直过民族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研究有三个方面的启发。一是关于直过民族的发展丰富了我国民族理论的观点:王磊认为,直过民族的发展经历了生产关系、生产力到全面发展的三重跨越;(3)王磊:《我国“直过民族”的三重跨越》,载《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崔晨涛指出,直过民族的跨越式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实践,丰富和创新了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内涵。(4)崔晨涛:《新中国70年“直过民族”跨越式发展与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创新》,载《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二是从精准扶贫的维度讨论直过民族的发展路径或模式:包路芳剖析了墨脱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指出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牧业,培育其市场的主体性与参与扶贫项目的主动性,才能实现门巴族和珞巴族的精准脱贫发展目标;(5)包路芳:《西藏墨脱“直过民族”与精准扶贫》,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董学荣总结了整族整体脱贫的基诺族模式,认为这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6)董学荣:《“直过民族”跨越发展的基诺族模式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前述成果分别侧重直过民族的理论与实践,但部分内容重叠,均涉及如何从内外两方面帮助直过民族加速发展。三是聚焦布朗族(莽人)的扶贫发展:方明不仅较为全面地呈现莽人的社会文化变迁,(7)方明:《莽人的社会文化变迁——基于仪式的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还具体从民生视角评估布朗族(莽人)扶贫工程的绩效,(8)方明:《从民生视角评估莽人扶贫工程的绩效》,载《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认为应做到政府主导与布朗族(莽人)参与、文化教育与科技培训、扶贫和开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革新等四个方面相结合,(9)方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贫与发展——以布朗族(莽人)为个案》,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2期。而方明与刘晓程认为文化扶贫对布朗族(莽人)的发展尤为重要。(10)方明,刘晓程:《文化扶贫与大众媒介——莽人媒介接触的人类学思考》,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1年第9辑刊。该方面成果为布朗族(莽人)的后续研究夯实了基础,但也发现它们重视“果”的表现而缺乏对“因”的讨论。鉴于前述思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本文以果寻因,即聚焦布朗族(莽人)整体脱贫之“果”,探讨其整体脱贫之“因”,将其归纳为布朗族(莽人)模式。
本研究的主要田野点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下文简称红河州、金平县)(11)金平县是集“边疆、山区、多民族、贫困”于一体的深度贫困县,扶贫攻坚任务艰巨。金水河镇乌丫坪村委会的牛场坪村和南科村委会的龙凤村与平和村,其中龙凤村为布朗族(莽人)、苗族以及彝族混居村,另外两村为布朗族(莽人)聚居村。2019年底,这3个村的布朗族(莽人)共165户,760人。2009年5月至今,笔者共19次进入上述村寨进行了共计400余天的田野调查。除注明外,文中资料均来自前述田野调查,以及后期通过电话与微信对报道人进行的远程访谈。
二、布朗族(莽人)三次跨越的发展概况
布朗族(莽人)在20世纪初从越南迁入中国,(12)方明:《莽人的社会文化变迁——基于仪式的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49页.过着半游耕半定居的生活。1957年,布朗族(莽人)被动员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拉开了布朗族(莽人)现代化征程的序幕,开启了整体脱贫的发展道路。借鉴前述王磊的划分,(13)第二、三次跨越的标志节点不同。以三次跨越为主,简述布朗族(莽人)的发展经历。
(一)第一次跨越(1957—1980)
1957年,金平县委以边防驻军为主的民族工作队成立布朗族(莽人)工作组,动员处在初民社会(14)诸多文献使用的术语为“原始社会末期”,因具有单线进化论之嫌,不予采用。的布朗族(莽人)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第一次跨越。1958年,布朗族(莽人)由12个聚落合并为6个村落,并与邻近的瑶族、苗族、拉祜族(苦聪人(15)1985年归属拉祜族。)组成互助组与合作社,走上集体化道路。之后,经过数次重组,到1973年形成南科新寨、坪和中寨、坪和下寨和雷公打牛四个全为布朗族(莽人)聚居的村落。(16)1997年,金平县营盘乡苗族和铜厂乡彝族共20余户迁入南科新寨,迁到现址并改名龙凤村。2008年实施莽人扶贫工程,龙凤村就地改造,平和村由坪和中寨与坪和下寨合并迁址而成,牛场坪由雷公打牛村异地迁址改名。关于这三个莽村的历史请参阅方明:《莽人的社会文化变迁——基于仪式的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4页.这些村落位于边境一线,海拔在千米左右,与外界交往极其不便。在民族工作队与合作社的帮助下,布朗族(莽人)开始定居定耕,学习开垦水田、种植水稻,由园艺农业向精耕农业发展,但生产力水平不高。1960年,莽人共有64户,312人。(17)宋恩常:《插满人社会经济调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苦聪人社会经济调查》,昆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印刷,1963年版,第47页。经过20年的缓慢发展,到1980年时增加到75户407人,(18)方明:《莽人的社会文化变迁——基于仪式的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年均增长率6.5%。水田面积由1960年的67亩增加到1980年的192亩,(19)杨六金:《莽人的过去与现在——十六年跟踪实察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人均水田面积相应地由0.21亩上升为0.47亩,年均增长率11.2%。稻米逐渐成为莽人的主食,采集物在食物中的比重逐渐下降,1960年占65%, 1980年降至35%。(20)杨六金:《莽人的过去与现在——十六年跟踪实察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布朗族(莽人)最早于1958年开始接受学校教育,但迟至1969年10月、1971年10月、1978年10月分别在三个布朗族(莽人)居住的村开设初级校点。到1980年,只有数人小学毕业,而坪和下寨全村村民皆为文盲。总之,在完成了第一次跨越后,布朗族(莽人)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与其他民族建立起平等互助的关系,学习到先进的生产技术,稻米取代玉米成为主食,适龄儿童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整个布朗族(莽人)的社会面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由于社会发育程度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经济生产能力相对不足,从经济收入看,布朗族(莽人)整体处于绝对贫困状况。
(二)第二次跨越(1981—2007)
1981年8月,金平县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布朗族(莽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助推布朗族(莽人)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第二次跨越。该制度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激发了布朗族(莽人)开垦田地、发展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生产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高,生活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但是绝对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明显改变。
经过5年相对较快发展,1986年,布朗族(莽人)共有86户,467人;有固定耕地713亩,人均耕地面积1.52亩;种植草果1033亩,人均2.21亩;大型牲畜有牛178头、骡马27匹、生猪242头,人均0.96头(匹);粮食产量人均187千克,经济收入人均138.7元。有18户115人基本解决温饱,占总人数的23.65%,绝大多数家庭比较贫困。(21)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编写办公室:《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275页。此后,由于交通不便、人口增长、素养不高、经济意识薄弱、帮扶力度有限等主客观原因,布朗族(莽人)社会发展非常缓慢,贫困状况并未明显改善。到2007年,布朗族(莽人)共有126户681人,其中劳动力245人;耕地986亩,人均1.45亩,其中水田434亩,人均0.64亩,人均粮食仅244千克;牛马共有196(头、匹),猪60头,山羊7只,人均0.39(匹、头、只);鸡鸭共376只,人均0.55只。适龄儿童入学率34.5%,初中及以上入学率仅占适龄人数的7%,16-60岁文盲率为75.6%;有92户397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为58.3%。(22)资料由金平县民宗局与金平县莽人扶贫办(因莽人扶贫工程设立该机构,在工程完工后不久解散)提供,特此致谢!2007年,布朗族(莽人)人均纯收入仅489元,为红河州平均水平的19.3%,按当年国家绝对贫困线计算,他们有62%处于贫困线以下。到21世纪初期,布朗族(莽人)整体仍然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必须采取全方位、立体式整体帮扶,才能实现整体脱贫,力争到2020年迈入小康社会。
(三)布朗族(莽人)的第三次跨越(2008—2020)
布朗族(莽人)的整体贫困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8年1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总理温家宝先后批示:“请云南省委、省政府研究提出扶助措施,帮助其尽快摆脱贫困”“请扶贫办商同云南省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政策措施,下决心解决莽人、克木人(23)主要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2009年归属布朗族,时有3000余人。的生产生活问题。”(24)感谢布朗族(莽人)扶贫办提供。云南省迅速贯彻落实批示的重要精神,出台《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莽人克木人发展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08]111号),2008年4月由金平县负责组织实施《红河州金平县莽人2008—2010年12项工程扶持发展规划》(简称《莽人规划》)。(25)相关讨论参阅方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贫与发展——以布朗族(莽人)为个案》,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2期》;《从民生视角评估莽人扶贫工程的绩效》,载《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此后,布朗族(莽人)迈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这是他们社会发展的第三次跨越。2016年,云南省启动实施《全面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行动计划(2016—2020年)》(简称《脱贫攻坚计划》),金平县立即贯彻落实。通过实施这些规划,再加上自身的努力,布朗族(莽人)于2015年脱离绝对贫困,到2019年实现整体脱贫。
由于实施《莽人规划》,到2010年底,布朗族(莽人)就实现了“四通五有”,即硬化布朗族(莽人)村村内道路并修通连接外界的弹石路、架设高压电、接通广播电视,每户发放一台彩色电视机和卫星接收器、通电话;在平和村修建1所初级校点,另扩建2所布朗族(莽人)儿童就读的小学、培养4名布朗族(莽人)医生,设置1间卫生室,并将布朗族(莽人)全部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大病救助,保证有安全人畜饮水设施,每户一幢2层共122.4平方米的安居房,并根据家庭人数配给木床与被褥等物品,有稳定解决温饱的基本农田,人均耕地面积2.53亩,人均粮食347千克。与2009年相比,人均有粮由296千克增加到347千克,增长了17.2%,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人均纯收入1822元(含低保840元),较2009年1413元(含低保600元)增长了28.9%,(26)方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贫与发展——以布朗族(莽人)为个案》,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2期。为当年国家贫困线2300元的79.3%。《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贫困户脱贫达到“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以此衡量,布朗族(莽人)整体实现了上述目标,但尚未完全实现脱贫摘帽。
2010年后,虽然布朗族(莽人)自我发展意识逐渐苏醒、自我管理能力逐渐提升,但因外援帮扶的大量抽离,其经济社会发展略有迟缓。但是,由于推广良种良法有力、2009年新植的814亩草果挂果等原因,2015年风调雨顺,布朗族(莽人)喜迎丰收年,人均有粮食598千克,人均纯收入3849元,实现了衣食无忧,部分家庭尚有结余存款。以2015年国家贫困线人均2800元来衡量,布朗族(莽人)人均超出1049元,已脱离绝对贫困。2015年,布朗族(莽人)在校生116名,其中,中专生4名、高中生3名、初中生43名、小学生66名,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入学率达100%,巩固率达99%,(27)数据由金水河镇提供,但存疑。据笔者调查,小学高年级与初中学生辍学现象较为严重。为提高布朗族(莽人)的综合素质打下坚实的基础。
布朗族(莽人)的整体脱贫还受益于《脱贫攻坚计划》,成效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提升能力素质。金平县多次组织布朗族(莽人)进行甘蔗与药材种植培训,累计上千人次。2019年6月,2名莽人村组干部参加由红河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组织的“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脱贫攻坚技能培训,时间为期1周。二是组织劳务输出。2016年,金平县对47名布朗族(莽人)进行技能培训后,将他们输出到广东务工,跟踪管理,月薪3000-6000元,加班另算。(28)数据由金水河镇政府提供,特此致谢!此后每年均协助布朗族(莽人)省外务工,对贫困家庭成员还补贴往返车费。三是培育特色产业。2016年,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布朗族(莽人)种植甘蔗约2000亩,公司上门收购,每亩纯利润2000~4000元,至今依旧种植。2017年,种植油茶1600亩,数年后将有收益。四是保护生态环境。布朗族(莽人)在国家生态公益林中不再套种经济作物,国家按每亩10元补贴其部分损失,每户获得360~2400元。而龙凤村莽人因又补量数百亩,每户增加140元。根据“支持边民稳边安边兴边”(29)《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EB/OL].云南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yn.gov.cn/yn_zwlanmu/qy/wj/yzf/201610/t20161028_27364.html,2019—4—21.与“建立动态边民补助机制”(30)《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脱贫攻坚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EB/OL].云南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yn.gov.cn/yn_zwlanmu/qy/wj/yzf/201708/t20170814_30233.html,2019—4—21.,莽人享受沿边补贴由2017年每户1000元在2019年又有大幅度提高,即牛场坪村因地处边境一线,每人1500元,贫困户每人另加500元(脱贫后不再增加),另两村处于边境二线,每人500元。(31)2020年,布朗族(莽人)的延边补贴又每人增加1000元。正是由于这些举措,布朗族(莽人)社会经济保持较快发展。2016-2019年,平和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556元、5283元、6129元、7109元;牛场坪为4934元、5723元、6639元、7701元;龙凤村为 5300元、6147元、7131元、8271元(含受灾生活补贴2400元)。(32)数据由金水河镇政府提供,特此致谢!各村增长幅度一致,其统计数据客观性存疑。布朗族(莽人)经济发展保持16%的增速,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2018年人均纯收入比2010年增长约264%,超过一番。2019年,布朗族(莽人)约60%家庭存款过万,已具备抵御一般风险的经济能力;人均纯收入超过1.2万的家庭约占15%,达到0.8~1.2万的家庭约有47%。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2016年布朗族(莽人)有贫困户42户164人,2018年仅有3户7人,到2019年底已无贫困户。
布朗族(莽人)所经历的三次跨越发展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他们因切身体会加强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建立起明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布朗族(莽人)从初民社会的刀耕火种发展到新时代的整体脱贫,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脱贫攻坚的优秀成果。因此,布朗族(莽人)整体脱贫的成功经验与模式值得总结与推广。
三、直过民族整体脱贫的布朗族(莽人)模式
奥斯卡·刘易斯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贫困文化”,即贫困者维持贫困状态的生活方式。(33)Oscar Lewis. La 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San Juan and New York.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65.贫困者摆脱贫困,需要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对于改变的方式,学界有两种主流的观点:一种是秉持文化相对主义,任凭贫困者自我发展;另一种是以干预哲学为理念的“指导性变迁”,助推贫困者的快速发展。就前者而言,正是因为贫困者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所以难以自我激发革新的力量,改变贫困状态;就后者来说,常因枉顾贫困者的主体地位,那些干预的项目事与愿违,甚至无效失败。(34)[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变人类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有鉴于此,根据贫困者的现实境遇,助力贫困者脱贫致富须结合上述两种学术观点中的合理要素。具体而言,长期目标应该是以激发贫困者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确立贫困者的主体地位;短期目标则是以多快好省地解决贫困者的物质贫困为主。为此,必须确立帮扶者的主导地位,因地、因时、因人的不同而科学地引导变迁。
基于前述思考,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纵观布朗族(莽人)从初民社会到新时代的三次跨越发展,这一成功范例堪称直过民族整体脱贫的典范,可以提炼为“布朗族(莽人)模式”。具体而言,对于往昔整体处于绝对贫困状况的布朗族(莽人)来说,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外援帮扶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他们的绝对贫困问题,增强他们依靠扶助彻底改变发展滞后状况的决心和信心,为实现未来的良性发展夯实基础;而内生激励就是帮助其冲破以往长期贫困状态影响下造成的对发展极度缺乏自信和手段的惯性束缚、从发展愿望、发展能力等方面建立起内在的观念和外在的技术有机结合的体系。简而言之,外援帮扶就是输血式扶贫,主要借助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帮扶与从全面的、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到精准扶贫,即外界直接向扶贫对象提供财物帮助、减免税负等扶贫方式,以满足被帮扶对象所缺乏的生存必需物质。而内生激励则是造血式扶贫,是立足长远考虑,以帮助被帮扶对象建立起具有可持续性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扶贫方式。造血式扶贫具有见效慢、周期长的特点,需要综合考虑个人自身发展素质、素养及其所处发展环境、条件等因素,建立一整套发展规划,培养、培育其自我发展能力和方式。正是在两种扶贫方式的综合作用下,历经数十年的努力,造就了今天布朗族(莽人)新的发展模式。
1.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布朗族(莽人)实现整体脱贫的制度保障。从特殊政策措施到制度保障,布朗族(莽人)充分共享了全社会的发展成果,在此过程中,布朗族(莽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不断增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不搞计划生育,免税和免征、免购公余粮食,大力扶持生产和帮助提高文化科学水平的特殊政策措施”(35)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编写办公室:《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如1985-1987年,国家平均每年给布朗族(莽人)发放救济粮3450千克、现金1800元、返销粮3150千克。(36)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编写办公室:《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2009年,金平县在红河州率先出台了《金平县农村低保实施细则》《金平县农村医疗救助实施细则》《金平县农村五保供养实施细则》《金平县农村困难居民临时救助实施细则》,惠及莽村所有布朗族(莽人)。鉴于布朗族(莽人)的整体绝对贫困问题,金平县从2009年将布朗族(莽人)纳入农村低保救助对象,使他们全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37)从越南嫁到中国莽村的妇女现有21人(莽族20人,拉祜族1人),没有获得中国国籍,不享受低保等待遇,但从2019年开始可以自己缴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由政府财政补贴部分缴纳的费用,所有布朗族(莽人)都被纳入大病救助的保障体系;由政府支付布朗族(莽人)孕妇在医院的生育费用,还补贴往返医院的路费。从2016年起,对布朗族(莽人)贫困户建档立卡,建立退出机制。总之,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与时俱进地采用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布朗族(莽人)的生活负担,帮助他们消除贫困、杜绝贫困的代际传递。
2.从全面帮扶到精准扶贫是布朗族(莽人)实现整体脱贫的策略选择。由于布朗族(莽人)整体贫困,而且贫困程度深,因此当地政府制定了全面帮扶的《莽人规划》。该规划以帮助布朗族(莽人)改善并发展居住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培植、社会事业发展、科技培训等作为工作目标,力求全面助力,通过交通道路通达、水利、通电、安居、基本农田建设、教育、卫生、文化广电、科技产业扶贫、整村推进、生态建设、民生保障等十二项工程实现布朗族(莽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改善的目的。这不仅确保了布朗族(莽人)拥有“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条件,也为最终实现整体脱贫夯实了基础。经过内外一致努力,现在,布朗族(莽人)的人均纯收入由2010年的1822元增长为2015年的3849元,达到当地中等水平,收入水平为当年国家颁布的年人均收入贫困线的1.37倍。
刚刚脱离绝对贫困状态的布朗族(莽人)依然面临着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致富门路不多、抵御社会风险能力较弱等问题,存在因各种主客观原因而导致返贫的可能,对此,必须针对布朗族(莽人)现实发展具体问题进行差别化分类,实行针对性更强的策略进行进一步精准帮助。一是继续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与生态保护补贴相结合的办法,消除可能导致返贫的各种隐患。除了前述提高普惠性的边民补助与国家生态公益林补贴外,加强精准帮扶力度。2019年,针对2户布朗族(莽人)五保户,当地政府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实现其享受兜底脱贫。2019年6月,龙凤村遭受洪涝灾害,很多田地被冲毁,作物收成锐减,县财政为此按每人每月400元发放生活补贴。二是通过产业扶持与帮助就业解决经济贫困的布朗族(莽人)。2019年,针对1户3人的特殊家庭,(38)户主刚成年,母亲因病过世,上要供养年近八旬的奶奶,下要抚养就读高一的妹妹。优先安排户主就业,劳动报酬为每天130~160元,该户成功实现脱贫。其他的帮扶情况详见后文“优化产业结构”。三是通过技能培训与文化教育帮助解决处于文化贫困状况的布朗族(莽人)。2016—2019年,金平县安排农业局、科技局、畜牧局等专业人员对布朗族(莽人)进行技能培训共计数百期,接受培训数万人次,培训包括集中授课和现场教学两个环节,主要内容有水稻、玉米、甘蔗、茶叶、油茶、草果等的种植技术,鸡猪的饲养,每个村还培训乐一名兽医员,建立疾疫信息机制,加强疾疫防控能力。同时,还进行了外出务工如何保障自身权益、家政技巧等方面的培训。四是开展资产收益脱贫。龙凤村将与联防村共有的1200亩荒山租给某公司,租金每年5万元,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和村用数百亩集体土地种植瑶药,村集体在2018年获利12万多元。(39)但后续因管理不善,到2020年已经没有多少收益了。正是由于多种举措的合力作用,布朗族(莽人)得以实现整体摆脱贫困的发展目标,但是,如何壮大并促进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仍是今后必须抓紧抓好的问题。
3.优化产业结构是布朗族(莽人)实现整体脱贫的经济基础。对发展条件较差的布朗族(莽人)而言,使其实现脱贫致富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显然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发展经济生产。在政府和社会的帮扶下,布朗族(莽人)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主要是采用了优化产业结构、增产创收、实现绿色和内生导向型发展四种途径:
一是根据自然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种植合适的经济作物,有效快速地增加经济收入。金平县在县域范围内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大力发展蔗糖、油茶与药材种植等特色产业。2016年和2017年,布朗族(莽人)村分别引进甘蔗、油茶与药材种植,经济收益较以往种植水稻、玉米、木薯等获得的收入增长约30~70%。如2019年,平和村陈忠明家仅种植甘蔗的收入就达9万元。二是大力发展经济林木产业和林下经济,形成增长的长效机制,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目标。2008-2010年,布朗族(莽人)村集体共种植杉木2017亩,待数年成材后变卖即可获益。发挥林下经济优势,每家均种植若干亩草果与香草,其中有几家种植大户,如平和村陈玉光近5年共投资近30万元在荒山上种植了5万多棵杉木,有老板出资80万元购买,被他婉拒;平和村陈忠明与牛场坪陈金亮也各种植杉木约2万棵,他们还种植数量较多的草果与香草等经济作物,每年均获利不菲。三是布朗族(莽人)采取劳务输出方式,以此增加经营性收入。2007年,布朗族(莽人)仅有数人外出务工,如今,外出务工已成为布朗族(莽人)青壮年增加收入的首选项与常态。2018年和2019年,先后分别有85人、87人前往广东省、浙江省等地务工,人均月薪约4500~7000元。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当地仅有20余人前往外省务工,较往年明显减少。四是积极发展畜禽养殖业。以往政府向群众发放仔猪与鸡苗,积极引导群众发展畜禽养殖,现已形成“自觉购买种苗—自行饲养—出售”的良性循环。目前,基本达到了户均养猪2头及以上、养鸡10只及以上。除自家消费,还能出售补贴家用,如牛场坪年近八旬的陈小大,近年来依靠养羊,每年都能获利数千元。
4.提升自身素质是布朗族(莽人)实现整体脱贫的关键所在。布朗族(莽人)一度秉持“消遣经济”的态度,即以减少消费为目的而减少劳作,并将因此结余的时间用于消遣的传统经济态度。(40)费孝通,张丰毅:《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通过大量的宣传、教育和培训,他们逐渐认识到“没本事,赚不来吃的”,因而加强自身对技能的学习,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抓生产、谋发展的意识明显增强。随着布朗族(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不断提高自身素养,拥有高度的文化自觉,逐渐发展成为脱贫致富的主体、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实践主体,内生了脱贫攻坚的动力。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不断加强学校教育,使自己成长为更好的自己。这一方面得益于在布朗族(莽人)村开设学校校点,更受惠于2007年出台的《关于加快莽人教育事业发展的决定》(41)县财政给予莽人小学生每生每年补助1000元、中学生每生每年补助1800元的生活费;小学毕业后免考到县直属八一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考取县内高中或职业学校,每生每年给予2000元助学金,考取县外高中或职业学校,每生每年给予3000元助学金;高中毕业后考取大学,每生每年给予5000元助学金。在莽人村寨学校任教的教师,工资每月增发艰苦生活补贴150元/人。该校点于2015年停办。与《莽人规划》。如今,布朗族(莽人)切实巩固了“普九”教育,在保量的同时,学习质量得到了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布朗族(莽人)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布朗族(莽人)的文化水平逐年提高,文盲率由1987年的86.8%下降为2013年的50.7%,(42)方明:《莽人的社会文化变迁——基于仪式的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到2019年进一步降至36.4%;初中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在1987年的时候为零,到2013年增长为5.1%,(43)方明:《莽人的社会文化变迁——基于仪式的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到2020年4月升至10.6%,增强了他们的社会竞争力。二是通过集中学习与现场培训,布朗族(莽人)的生产生活技能都得到了明显增强。生产方面,布朗族(莽人)劳动力均已掌握不同的种养业基本技能,青壮年能够到厂矿企业从事低端劳动与服务工作。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他们可以通过外出务工挣钱自救。如牛场坪陈海林家的部分田地在2019年6月被泥石流冲毁,夫妻俩在是年7月23日去深圳务工,2020年1月18日返回家中,俩人的工资收入4万余元,盈余2.6万元。生活方面,布朗族(莽人)的个人及家庭卫生状况大为改善,因此而有效降低了致病风险;各家种植的绿色蔬菜可以自给自足,减少了生活开支。此外,布朗族(莽人)的当家理财意识和能力也有显著提高,他们养成了勤俭持家的良好风习,知道存钱以备不时之需,而不再像往昔那样吃光用光。三是扩大了就业途径,在工作中学习成长。一方面是在本地就业,通过向他人学习,参加本地工程施工;另一方面是外出务工,接受新工作的挑战,增长见识,学习新的技能,提高自我素养。现在,布朗族(莽人)劳动力中形成的共识是:“小娃要好好读书,以后到城市教书、当干部、做老板”。就读学生普遍认为:“努力读书,学好本领,走出大山。”
正是由于外援帮扶与内生激励的共同作用,布朗族(莽人)才得以从整体贫困到实现整体脱贫的彻底转变。在新时代,布朗族(莽人)要不断开发自身的人力资源,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激发自主发展意识,改造传统产业、开辟新兴产业,实现更大发展,力争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同步迈入小康社会。与前述门巴族、珞巴族、独龙族以及基诺族的扶贫脱贫模式相比,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于均重视外在帮扶,不同在于布朗族(莽人)的内生激励更加坚强有力。
四、结语
本文研究布朗族(莽人)的整体脱贫问题,简要描述了布朗族(莽人)从初民社会到新时代所历经的三次跨越式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情况。与往昔相比,如今布朗族(莽人)居住地区的基础设施逐步改进、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人口素养日趋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人均纯收入逐年增长,已经达到了丰衣足食的水平,行走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上,逐渐形成了革新的发展文化。直过民族整体脱贫的“布朗族(莽人)模式”,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脱贫攻坚的优秀成果。这为世界其他地区解决类似的扶贫脱贫问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样本,也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虽然布朗族(莽人)整体已经实现了完全脱贫,但仍须思考在后小康社会布朗族(莽人)的可持续自主发展问题,尤其是要加大“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路径”的探索和研究。目前,应该清楚地看到,除了国家的各种补贴外,布朗族(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处于产业链底端的种植业和服务业。种植业受自然与市场影响巨大,如烤干的草果在2013年为72元/千克,2019年则降至38元/千克,而且他们种植的甘蔗、草果、香草等均属于为企业提供原材料,产业附加值较低。他们从事的服务业基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承担苦活、累活、脏活,工资收入也不高。一旦减少或停止国家补贴,布朗族(莽人)将如何自力更生?在今后的发展路上,还有很多问题等待着布朗族(莽人)应对。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还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精神,努力做到外援帮扶与内生激励的和谐统一,牢固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