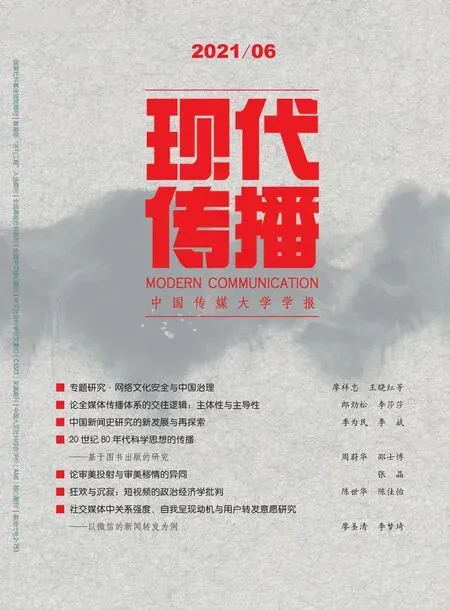文本·时空·人物:论互动剧的交互叙事模式
■ 武 瑶 王晓璐
一、问题的提出
(一)概念的厘定
互动剧无疑是传媒艺术家族中的最新艺术形态。互动剧既有数字化复制的科技性、非实物化的媒介性,更具有传媒艺术参与者去中心化的大众参与性。①从媒介发展的角度而言,艺术在媒介技术的推动下,类型边界模糊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戏剧兼容文学、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类型,而电视剧博采了戏剧、电影、文学等不同艺术类型元素,互动剧则具有电视剧、游戏、数字媒体艺术的元素,其类型归属恰好体现了媒介边界的消融和不同艺术类型兼容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认为互动剧属于数字媒体艺术、影视艺术和游戏艺术的交叉范畴,一方面既是艺术形式,另一方面也是消费产品。互动剧的概念外延是具有交互设计的叙事类影视作品,内涵是运用交互设计规则、影视制作方式创作的动态影像艺术形式,核心特征是交互(技术)、连续(叙事)、影像(符号),以镜头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用演员动作、话语来表达一定故事情节的视听艺术,具备艺术属性和消费属性,是一种新的艺术品类。
(二)研究的视角
通过对互动剧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互动剧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互动是人生来存在的本能需求,互动剧植根于技术发展,形塑于后现代的审美文化,和媒介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媒体理论家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传统的叙事逻辑,他们认为我们所了解以及熟悉的叙事本身就是历史上一种特定的依赖技术的储存信息、组织直接感觉与象征数据的方式。新技术和新媒介会在适当的时候产生新的叙事形式,“交互叙事”在数字媒介时代应运而生,使得互动剧能够在话语层面上重新配置叙事。
互动剧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品类,其独特的叙事模式是什么?互动剧的文本架构、时空建构、人物塑造有何独特性?体现了怎样的美学意蕴?文本试图借鉴叙事学的叙事模式,从叙事的三个重要面向入手,在分析互动剧交互叙事模式的同时试图探讨其独特的美学意蕴。
二、互动剧的文本架构:分岔的小径花园
(一)四种文本架构
互动剧适合非线性(non-linear)的结构,这些结构能够生产不同的故事类型,具有生成性和开放性。笔者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把互动剧的文本架构分为四大类。②
第一种是“等差—分支型”架构。该类型是最基础和最理想的结构,以树的形式组织情节,每个节点后接两个选项。如果剧本有n个节点,理论上会有2n个结局。“等差—分支型”结构有效地模拟了人类生活的决策性走向,缺点在于分支的指数增长容易导致叙事混乱。该结构的代表作是《忘忧镇》,《忘忧镇》共有三个互动节点,形成了八种故事支线,不存在交叉的结局。
第二种是“聚拢—分散型”架构。开始有一条固定的主线介绍故事背景、主题和人物关系,后续有多个分支剧情。该类型给予观众③足够的时间了解人物情感和人物关系的变化,每个章节最终都会回归主线,可以降低内容的损耗率④。这一结构适合恋爱题材的内容,代表作品是《拳拳四重奏》。《拳拳四重奏》开篇设计七个互动节点以便观众熟悉交互操作,在序章结束时引导到一个共同的结尾作为整部剧的起点。
第三种是“分支—交叉型”架构。该结构在主线发展中会出现多个独立可交叉的节点和次要线索。该结构的叙事管理更为高效,允许情节链合并,从而限制了分支的扩散。这一类型紧密围绕一个叙事核心,但是每个分支都有较为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这个结构适合故事世界丰富的内容,如《指环王》《复仇者联盟》等自带宇宙体系的内容。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是《黑镜:潘达斯奈基》(Black Mirror:Bandersnatch),该作品共有一百五十多个分支,每个分支是不同的故事线,不同的分支内容最后都在斯蒂芬询问“这个世界是哪里”这一文本单元交汇。
第四种是网状架构,这一结构在“等差—分支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演变。不同之处在于故事线之间存在交叉,文本单元之间呈现更为错杂的关系。网状结构的故事有统一的起点,没有统一的终点,人物有着共同的故事背景,文本单元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非毫无规律,每条路径代表人物不同的“生活”。网状结构的代表作品是Detroit:Become Human(《底特律:变人》),该作品设计了卡拉、康纳、马库斯三条故事线,每条故事线有2—3种剧情走向,每个走向有5—8种结局。
叙事结构是千变万化的,宏观层面的模式可以嵌入不同的微观类型,比如在总体上使用“聚拢—分散型”,在某个章节使用“分支—交叉型”,以制作出具有可看性的复合性叙事结构。
(二)文本特性
1.超文本性
互动剧是由无数个文本单元构成的超文本,文本单元通过链接相互交叉联系,即泰德·纳尔逊(Theodor Nelson)的“非序列性”(non-sequential),其基本特质为超链接,观众可以从一个文本单元切换至另一个文本单元,所以互动剧存在诸多路径。当观众选择其中某条路径时,其他路径也就从“在场”转为“不在场”。这样的独特形式使互动剧成为了罗兰·巴特的“理想文本”,观众成为了接受美学期待的“理想读者”。
互动剧的超文本结构和叙事逻辑具有根茎(rhizome)特点⑤,这个特点非常符合互联网的多元性特质。根茎意味着“复杂的文化隐喻和游牧的思维模式”⑥,是一种“思想挑战和诗学实践”⑦。根茎的特征是开放性、无中心和多元化。互动剧的叙事结构很好地实现了这样的根茎系统。互动剧的文本单元可以比作根茎的枝,文本单元之间的链接比作根茎的芽。互动剧就是通过链接聚合起来的文本,它依赖四通八达的根状系统实现文本单元的链接,呈现出了近乎无限的分支,观众可以在各个文本间随意跳跃。
互动剧的超文本挑战了文本中只有一个序列和一个情节的观念,超文本就像一个生成工具,它把文本单元抛给观众,观众既可纵向叙述,也可横向链接,能轻松自然地游于广度概述与深度细节之间。
2.非线性
埃尔瑟塞将非线性的叙事方式视为一个“思想实验”⑧。数字媒介时代的互动剧与非线性叙事存在着天然的契合。非线性不按时序展开,具有不固定序列、多条线索并存的叙事结构,主要人物有着不清晰的目的(或目的缺失),叙事事件强有力在场而非人物角色在场。叙事可能是完全非线性的,但可以用线性的文本来表示。
移动的终端带来了碎片化的信息,架构在数字空间两点间彼此联结(超链接)的数字媒介代表着一种在本质上新颖的非线性表达方式。人类每天在计算机、手机、游戏机、平板电脑等媒介中形塑了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可以说,互动剧满足了观众对于信息的多元化渴求和非线性诉求,也正是在非线性诉求的影响下,互动剧才发展出更为多元的播放媒介和观看空间。互动剧将交互性和叙事性结合起来,产生从线性叙事到非线性交互叙事的焦点转移。
非线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最简单的方法是文本朝着两个不同的路径发展。互动剧可设计多分支内容,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可成为其中的“主角”并介入剧中故事世界,通过交互选项决定剧情的走向,提升观看过程中的视听体验。在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下,互动剧的意义是由各文本单元相连接的关系形成的。观众可以控制观看的时间,观看的结果形成具有非线性特征的“脚本单元”,非线性赋予了互动剧多种观看顺序的可能。
三、互动剧的时空建构:阿莱夫的宇宙世界
(一)时间诗学:时间的漫游
“时间是一个叙事问题,涉及故事与话语;而时态则是语言中的语法问题。时间的点与段都在故事当中,又通过话语表现出来。而话语又由某种媒介表现。”⑨传统电视剧属于线性文本,对时空的建构以因果关系为基础,因而在时间上要求有先后性、空间上有固定性。互动剧则改变了这样的时间理解,建立了属于互动剧的时间诗学。
首先,互动剧的时间诗学体现为话语的时态指向“现在”,即“现在进行时”。查特曼把时间的时态系统分为“先前时间”“过去时间”“现在时间”“将来时间”“无时间”⑩。互动剧的时间指向“当下”,带来了“实时”叙事的可能性。时间性源于影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互动剧的实时性并不是指内容在此时恰好发生,而是在观众与互动中进行实时交互,这实时交互的行为将“过去完成时”的体验变成“现在进行时”的体验。
其次,从时间的长短来看,互动剧的时间诗学体现为时间的不确定性。影视剧内容的长度是有规定的,一集为45分钟。而互动剧的时间尺度是不确定的。互动剧每次演进的路线不一,因此每次的单线时长也无法确认,短至几分钟,长达几个小时。观众每增加一次选择,互动剧的情节就会改变,时长也会随之改变。《他的微笑》最短路径的时间仅有17分钟。观众若想要看完所有的结局,需要200分钟以上。
最后,互动剧的时间具有多维性。热奈特认为,在故事中多个事件可以同时在不同的时空里发生,故事时间可以是多维的,但是叙事需要叙事者按照一种组合事件的方式,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因果逻辑讲述出来,这样叙事者需要在同时发生的众多事件中择取重要的来讲述。正如博尔赫斯在《阿莱夫》中描绘的小圆球,这个小圆球看到包罗万象的多重宇宙。时间在节点会产生分岔,这些分岔充满了偶然性、多维性,在不断的分岔中出现了交错又平行的宇宙。
(二)空间场域:空间的探索
1.赛博空间:“全息甲板”的体验
珍妮特·默里(Janet Murray)在《全息甲板上的哈姆雷特:赛博空间中的叙事未来》(Hamlet on the Holodeck:The Future of Narrative in Cyberspace)中认为,“数字环境中的空间可以像现实世界被探索,空间环境的概念可以在想象的故事世界中描绘出来,数字环境实际上可以呈现出导航空间。书籍和电影等线性媒体可以通过文字或图像来描绘空间,但只有数字环境才能呈现我们可以穿越的空间。”
导航是体验赛博空间的重要方式之一。互动剧为观众提供了发散式架构的导航空间,观众在这里将完成一段迷宫式的游历,在空间中导航既是一种探索过程,同时也构成了叙事。互动剧构建了一个虚拟的赛博空间。互动剧的出现推倒了“第四堵墙”,让赛博空间与现实空间进行了行为以及思想上的交互,现实空间里的观众参与到故事的进程中来,加入到虚拟空间的创作里,并将自己的思想带入,两个空间通过多种交互手段进行了密切交流。
在互动剧《明星大侦探之头号嫌疑人》中,观众通过人物进入了赛博空间,观众可以点击嫌疑人的手机,查看通话记录、社交账号的状态,从而实现赛博空间中虚拟现实的在场,使空间意义向多维度扩展。赛博空间超链接的特质使空间呈现开放性,观众类似于游牧者,在这个充满着不确定和可能性的空间探索,形成了默里所谓“全息甲板”的体验。
2.屏幕空间:交互界面的隐喻
媒介决定了故事的叙事形式,技术的发展限定了叙事的技巧。交互界面构成了观众和互动剧之间的信息中介,观众必须通过交互界面(屏幕和窗口)采取行动。交互界面的功能和诗歌一样,都是将陌生的新世界与熟悉的世界联系起来发挥其修辞功能。
互动剧的界面由两个文本选项和可视计时器组成,如果观众没有在时限内做出选择,就会按照系统既定的方式进行叙事。互动剧的交互性倾向于使观众参与琐碎的点击行为,这意味着界面在内容和意义上的提升。随着手指的移动,手指与界面的交互形成了一种可感知的知觉形式。
在符号学的意义上,交互界面相当于一个符码,符码在各式各样的媒体中承载着文化信息。观众使用屏幕观看的一切内容(包括文本、音乐、视频、可导航空间)都呈现在屏幕的交互界面上。交互界面向观众展示互动剧的内容,将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构建观众独特的经验,塑造了观众对于互动剧的想象,决定了观众对互动剧的看法。
在互动剧中,交互叙事消解了传统的时空理念,线性的时间观念被解构,统一的空间观念被消解,随机性与偶然性成为观看的新乐趣。
四、互动剧的人物塑造:“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塑造
(一)人物角色:多重动机
人物是故事的载体,动机是一切行动的因由和力量源泉,动机必须符合人物的逻辑和情境的规定,人物动机导致了事件发生的走向。因此设计人物之初就需要了解人物的欲望和诉求,人物行动才能有明确的方向。
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认为,结构即人物,人物即结构。“如果你改变了一个,就便改变了另一个。如果你改变了事件设计,那么你也改变了人物;如果你改变了人物的深层性格,你就必须重新发明结构来表达人物被改变了的本性。”交互的出现在人物的性格层面上增加了新的因果关系,通过交互行为,观众的意图就成为了人物行为的推动力。交互行为既受到已有文本结构的制约,又受到创作者在情节层面因果关系的制约。
互动剧的角色有多重动机(或者没有清晰的目标)。多重动机才能形成不同的人物性格,才能出现结构的分岔。如果让人物的目标保持一致,这样很难让人物弧光产生转变,因此可以让人物在不同支线拥有不同目标,成长为不同性格的人,从而走向不同的结尾。
互动剧把人物的想法外化为行动,行动正是人物在一定的情境下对于事件的反应,情境与事件会因人物的行动而异,一个选择可能会让人家道中落,也可能让人绝处逢生。《隐形守护者》中,“扶桑安魂曲”故事线中肖途的目标是过上平淡的生活,“红色芳华”故事线中肖途的目标是成为一个“隐形守护者”。观众的交互行为会影响人物的性格特质,当行为偏向于“善”,角色将会遇到更加友善的对待,反之亦然。交互叙事产生了“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效果。当观众在人物关系中发现叙事信息和叙事联系时,交互体验得到了增强。
(二)人物设定:后设叙事性
互动剧的人物角色在本质上是元叙事性的,剧情的发展不能决定人物角色,而是角色的性质优先于剧情。这与后现代文化的特征——角色的脱故事性或后设叙事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物角色被赋予不同的设定或人际关系。
互动剧中的人物不再是原来的人物,变成了人物设定。人物一般是对现实人物的模仿,而人物设定遵循的是数据库的逻辑。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人物角色,一个是人物设定。互动剧的人物角色可以有不同的人物设定,将人物抽离故事文本再进入不同的设定中,以不同的人物形象出现。
互动剧的所有人物设定形成了人物角色的“属性资料库”(database)集合,人物角色存在于超越各个故事本文之外的属性资料库之中。人物角色不是存在于单一故事中,而是存在于各种各样故事或情境中。换言之,人物角色是所有人物设定行为模式的聚合体,为各式各样的故事文本或情境的展开提供可能。互动剧的创作并非按照传统的故事形态创作,而是依据脱故事性或后设叙事性的人物角色的属性资料库来创作的。
人物可以在互动剧中反复“死亡”,角色在一条路径中死亡后可以在另一条路径中重生,实现“生”的复数化与“死”的重置。观众对死亡并不觉得突兀,“反而将其作为理所当然的现实加以接受”。原因在于观众是在元叙事层操控故事,观众本能地明白角色的死亡是叙事层面的死亡,元叙事层面人物并没有真正的终结。互动剧人物的本质不是存在于故事上,而是存在于被称为角色的属性资料库这种后设叙事性的环境中。创作者不依赖于故事的写实性,而是依赖于后设叙事性的属性资料库作为参照,互动剧体现了后现代故事创作的趋势。
(三)角色视角:角色与观众的同一
叙事角度是叙事中的一个关键枢纽,不同的角度可以创造不同美学风格的叙事。视角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面文化棱镜,可以展现出不同的人生境遇、审美品味和历史哲学。
在互动剧中,观众可以用两种方式来体验人物的旅程。第一种方式是陪伴着英雄的旅程,观众创造了共享的经验,产生了同理心,这是全知的视角。第二种方式是观众是英雄,旅程是观众的,这是第一人称的内视角。全知视角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了解故事世界的因果原委和来龙去脉。以第一人称的内视角讲故事时,叙事就变成“个人化”的形式。
第一人称的内视角使叙事深入人物心理世界,观众获得的是一种情感代入的体验,观众与人物在情感上相融获得了“心流”(flow)体验。观众产生的情感代入和心流体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我扮演”带来的控制感与自由度,观众设身处地讲述故事,从人物内部来体验情感,从而降低了人物形象与观众之间的审美距离。
在交互的过程中,观众把角色的情感灌注于“我”之中,使我和角色达到同一。观众与角色共同经历了故事世界,通过交往、对话达到真正的理解。互动剧呈现的世界是客体与主体融合在一起的主体间性世界。观众的现实自我转换成了互动剧中的虚拟身份,观众必然深刻体会角色内心状态和情绪波动,这个过程更像是探索人性的过程。在这种移情作用中,既确定了自我的存在,同时也确定了角色的存在。从艺术的角度看,移情以强烈的形式描述了主体与对象的投射和融合,从美学角度看,移情本身涉及到感觉、思考、记忆、经验。
《当我醒来时》就是典型的第一人称的内视角,分别展示了三个人物的不同身份,并借人物的角色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准备好了吗?”此时叙事就变成个人化的方式,观众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其中,通过人物的表情或语调来感受人物的境遇,用心灵体验人物。
五、互动剧的交互叙事美学:生成性与参与性
(一)生成性审美
互动剧作为影视艺术的新发展,需要新的美学观念对其进行说明。互动剧的特征显示出一个超出传统限制的概念性构架,这个构架提供的可能性不是被抽象演绎得无法辨认的审美体验,而是一个面向全部感知领域开放的世界。
影视艺术的发展不仅是由技术推动的,更是美学原则驱动的结果。数字媒介时代之前的艺术作品,无论是教堂里面的宗教画,还是贝多芬的交响曲,亦或昆汀的电影和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都是已经完成的状态。在数字媒介时代,艺术作品不断打开自己,表现为一种生成美学的特质。媒体理论家彼得·卢兰斐德(Peter Lunenfeld)使用“未完成”(unfinished)定义了数字媒介的美学,正是这种“未完成”特性使得影视的本体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特性来自不同的和不受控制的因素的相互作用。
互动剧的美学特质是一种多面向的、且从未完成的。借用德勒兹的美学思想去形容这种特质,那么互动剧的美学是一种“生成”美学。互动剧本质上是一个动态世界,因内部组合方式不同呈现不同的样态从而产生不同的意义,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未完成状态。交互叙事伴随着动态的叙事情节和人物的变动,因此互动剧的意义是生成的、延展的、暂时的、随机的。
首先,互动剧的故事是“生成的”。互动剧是一个开放的叙事,不断有新的链接加入现有的路径,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断地重构和完善故事以形成新的意义,因此互动剧的发展都是未完成的,因此脚本单元变得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文本单元的整体结构。
其次,互动剧的时间是“生成的”。当叙事从“been”转向“being”,“生成的”美学出现了。互动剧的叙事不断处于现在时,叙事不断向前行进和扩展,时间彷佛没有尽头。此时,观众进入了一个永生的世界里,“未完成”同时意味着“生成”。
(二)参与性审美
媒介的发展历程表明观众在不断增强自己的“参与性”程度,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的参与性文化更强调了当代受众的参与性,受众往往不再把自己视为产品的被动消费者,而是越来越希望自己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提出了一种新的审美方式——审美参与。审美参与追求一种包容性,基本指向是要把审美经验研究的理论重心从心灵经验转向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强调审美的积极参与性和主动性。
“参与”是一种有效和普遍的经验方式,参与的方式取决于时代、风格和艺术形式。20世纪的互动艺术、新媒体艺术的美学诉求都超越了传统无利害的静观美学观,需要一种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美学理论,需要审美主体全身心并且积极地参与到审美活动中。
与静观模式不同,互动剧的参与主要体现为观众在感知、意识、行为上的介入,它体现的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积极的参与性要素。审美经验的获得不仅是一种态度转变,它更是对生活经验的强调。互动剧的多元维度带来了多元感性体验,观众的参与作为一种动态的力量发挥作用,并与其他的因素相关联构成一个整体的审美体验,努力消除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分离,从而尽可能地消解观众与作品之间的距离。
观众交互行为是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参与使得观众和故事在互动剧里结合。观众将经验、知识、背景、审美趣味以及感知和理解带入其中,激活故事的“不定点”。观众不再是被动接受现成的、完整的、封闭的世界,而是主动参与创造作品和世界。观众的参与使得不确定的文本从一种潜在的可能状态转向一个现实的状态,把一个超文本形态变成一个具体的文本。需要注意的是,观众的参与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交互行为不仅受到选择的预先设置,更受到故事情节给予的暗示以及文本结构的制约。
互动剧作为桥梁实现了观众和创作者的心灵沟通与对话,它是一个潜在的引导,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惯性中解放出来,引向新的生命形式,使人们看到未来的可能性,为人们打开未来经验之途。
交互叙事认为世界从多元出发,事物的表现形式并非其所是,遵循的是“偶然性”。在今天,相比单一的因果链,偶然性更容易被人接受。偶然性强调宇宙万物的随意碰撞,打破因果关系的链条。生命是偶然还是必然?偶然性是否能改变人生轨迹从而打破必然性?还是不管有诸多的偶然,生命最终只有一个无情的必然?这些生命思考或许才是互动剧应该超越形式的表达。
注释:
① 胡智锋、刘俊:《何谓传媒艺术》,《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73页。
② 武瑶、庞雪芮、宋凯:《互动剧叙事的桎梏与创新》,《中国电视》,2020年第10期,第58-59页。
③ 在这里,笔者称互动剧的受众为观众而不是玩家,因为互动剧的受众更注重剧情的体验、代入感以及沉浸感,而不是更注重游戏的操作感。
④ 损耗率指的是观众观看的文本时长除以完整剧情的时长。损耗率越高,文本支线的内容越相似,剧情差异越小,互动体验越差。
⑤ [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年版,第 6页。
⑥⑦ 麦永雄:《光滑空间与块茎思维:德勒兹的数字媒介诗学》,《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第78页。
⑨⑩ [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