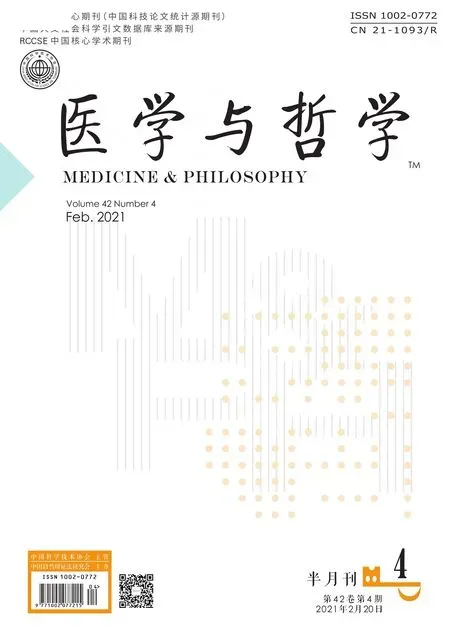镜与像:免疫学与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评《大规模疫苗接种:现代中国的居民身体与国家力量》
潘龙飞 王一方
免疫学是高度社会化的科学,基础研究的发达并不意味着实践层面的成功,常见病的大规模免疫实践高度仰赖政府的作为。也正因为免疫学与政府公共卫生治理之间存在这种密切联系,两者存在着鲜明的镜像关系。当代科学史界对于免疫学的研究以国家主导下的人口控制视角为主。探讨后发国家免疫学实践问题时,也以后殖民视角为主。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今时代,总结中国免疫学实践经验,理解中国民众关于免疫应用不同于西方的价值判断显得愈加重要和及时。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大规模疫苗接种:现代中国的居民身体与国家力量》(MassVaccination:Citizens'BodiesandStatePowerinModernChina)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免疫学实践的全新视角。该书重点讨论了作为实验室科学的免疫学如何在政府能力提升的过程中走向实践而最终大幅提升中国人均健康水平。该书作者白玛丽(Mary Augusta Brazelton)是剑桥大学露西·卡文迪许学院和圣凯瑟琳学院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本书是她的第一本专著。白玛丽主要关注中国医学与社会的互构问题,善于从全球史视角解读和分析中国医学问题。她认为,中国在20世纪初的免疫学科研水平较高,但天花等传染病泛滥仍是导致中国人均寿命低的重要原因,相对先进的免疫学科研水平却并没有在此时发挥很大作用。而在医学科研与发达国家相对隔绝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科学界一度认为此时中国的医学科研水平较低,中国却在该阶段消灭了天花这一恶性传染病,并大幅提高了居民的期望寿命。她认为,医学前沿研究一般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能够大幅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的恰恰是疫苗接种等成熟现代免疫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促成这些现代医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的是国家能力的提升。她在书中开篇做了这样的对比:“1942年,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西南边陲云南省的一个村庄,传教士声称可以通过注射保护当地妇女免受霍乱的侵袭,但她们拒绝了。1952年,一群中国东北的小学生排着队,卷起袖子,伸出胳膊,让穿着护士制服拿着针的年轻妇女为他们打针。”[1]1
1 国家免疫力量的形成
国家免疫力量本质上是其免疫学研究水平与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综合发力,作者为了解释中国如何成功地激发这一力量,回溯了中国自20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免疫学的发展史和相关的社会史,强调了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免疫学成功实践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天花、疟疾、鼠疫、霍乱等传染病曾经在中国肆虐。虽然传染病是当时影响中国人预期寿命的主要祸首,但中国的免疫学研究并不落后,基本可以做到与世界前沿同步。此时中国人极低的预期寿命,并非源于科研水平的落后,而是源于组织水平的落后。与典型的西欧或北美中心主义的叙述相反,档案材料、出版材料和个人记录都清晰表明,二战前中国医生和生物学家是全球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研究领域的活跃分子。然而,当时的免疫学研究机构大多集中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非精英社区”还缺乏基本的现代医学机构,这使得先进的生物医学研究难以惠及大部分居民,也使得大部分中国居民直观地认为中国当时的医学研究比较落后[1]1-33。
白玛丽发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间接促发了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和广泛应用。虽然中国科研人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已经掌握了疫苗研发和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但战前疫苗基本只在大城市接种。抗战导致了大量大城市或东南沿海地区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向内地迁移,这种大规模的人员流动进一步引发了传染病的传播,也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为部队和内迁人员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这使得疫苗开始走向大众。同时,医学科研工作者此时转移到了云南这一当时的欠发达地区,也使得他们开始关注农村地区的传染病免疫问题。在当时,医学科研人员大部分家境优渥,并无基层生活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云南第一次体验了农村的卫生条件,许多人也第一次因为卫生条件差感染了沙眼、伤寒、猩红热和疟疾等当地的流行病,这使得医学科研人员积累了大量关于农村流行病防疫的经验,为之后的农村大规模防疫奠定了基础[1]55-78。
在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已经有了大规模免疫的科研人才储备和技术储备,疫苗也开始了大规模生产,医学科研人员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卫生情况也有了基本了解。然而,截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作为大后方的云南疫苗接种率也未达到总人口的5%,疫苗仍然只在内迁人员和军队中大规模接种。新中国成立后,免疫接种技术才开始在全民层面被推广开。1953年,云南仅天花疫苗的接种率就达到了90%,居民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大规模改善。然而此时中国的免疫学科研水平并没有较大提升,内战时期有大量医学科研人员离开了中国大陆,这对于免疫学科研本身是重大的打击。虽然科研水平没有显著提升,社会组织水平却有了巨大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疫苗接种真正成为了高度组织化的公共卫生事业,国家治理能力与四分五裂的民国时期相比有了质的提升。在过去,疫苗接种一般由医护人员完成,但中国当时的医护人员相当有限,因此新中国政府通过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广泛招募志愿者进行为期两周左右的短期培训,学习免疫原理和技术,课程结束后立即分发疫苗组织接种。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公众当时普遍对于科学的理解程度不高,不愿意接种疫苗。新中国政府便通过海报、歌曲和电台广播等方式对于接种疫苗的好处进行了广泛宣传。同时,新中国政府也建立了基于户籍的责任制度。户籍是中国自先秦以来的社会管理方式,但新中国政府第一次将其应用于卫生防疫。1950年颁布的《全国天花疫苗接种条例》规定,天花疫苗接种必须记录在户口簿上,由基层干部进行挨家挨户的调查并进行登记。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新中国政府利用社会组织优势迅速解决了疫苗接种问题,这样的高效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促使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消灭了天花[1]78-101。
2 非西方视角下的生物政治学
绝大多数生物政治学学者集中在欧洲和美国,他们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免疫学技术应用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认为技术可以实现身体的征服和人口的控制,而技术本身的实施则意味着纪律和规训的存在。在近代早期,免疫学只是微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阵地。而到了20世纪,免疫学则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迅猛发展。原因在于,免疫学自身的应用决定了它可以成为政府重要的政治砝码,也可以作为政府保持国力的工具。为保持对抗能力,在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期间,欧美的政府力量都在不断扩张。欧美免疫学的发展和繁荣本质上是源于政府力量(规训与治理)不断扩张,并将政府需求反映到了科学界。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3]认为,正因为免疫学的应用对于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影响比较大,政府才高度重视免疫学的发展和应用。
作为后发国家,讨论免疫学技术对于个人健康自由的剥夺是奢侈的。健康自由的前提是有可以选择的技术实体,而对于后发国家的民众而言,很多技术本身根本不存在,也就不存在选择的机会。新中国对于免疫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于人类消灭天花病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力量提升的前提下,民众的健康水平大幅进步。此时进行讨论,就要引入一个非传统的生物政治学视角——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王绍光[4]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提供了普惠的全民医疗的直接原因在于新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并非传统生物政治学的讨论范畴,因为利用技术进行社会控制的前提是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传统生物政治学仍然是在发达国家的社会视角下探索技术的价值问题,归根结底是反对国家治理能力过于强大而剥夺居民对于技术的价值判断。
中国免疫学的学术发展最初并不是被实践需求带动的,在没有形成强大国家治理能力时难以普惠全民。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免疫学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而免疫学的应用却与学术研究的水平不相符,这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地科学现象。在乔治· 巴斯拉(George Basalla)[5]看来,由于后发国家缺乏原生的科学研究,其科学事业发展早期呈现出明显的殖民地特征,即复制先发国家的研究,即使这些研究与本国实践关联不大。免疫学在20世纪初成为生物医学界的显学,而中国当时作为发展学意义上的外围国家,其科学研究趋势必然与发展学意义上的中心国家保持一致[6]。中国当时的医学科研骨干以欧美留学生为主,重点科研领域也必然受到欧美的影响。而这些科研需求却不是社会内生的,这使得这些研究并未广泛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并没有广泛的免疫学应用计划。战争中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传染病大流行,使得国民政府为保持军人和内迁人员的健康必须大规模应用免疫技术,这之后免疫学研究才逐渐走向本土化。与欧美国家相似的是,此时的中国遭遇了比较强烈的外部冲击,为了保持国力必须加强社会控制,而人口控制则是社会控制的核心要素之一。实际上,正是20世纪国与国热战冷战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政府才有动力进行严格的社会控制以保持国力,免疫学的科研与应用才因此得以迅猛发展。在缺乏外部威胁的情况下,纪律和规训会逐渐消解,国家治理能力也会逐渐降低。迪姆西·比斯利(Timothy Besley)等[7]认为,在遭遇外部威胁时,国家治理能力会显著提升,在外部威胁减小时,国家治理能力会被削减。传统生物政治学的价值诉求本质是削减国家治理能力,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诉求,对于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显然是奢侈的。
新中国政府在推动免疫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下沉到最基层的国家治理能力是中国过去不曾出现过的,这使得成熟的技术得以大规模应用。大规模免疫接种是新中国早期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项目之一,它也为国家奠定了施展卫生公共政策的能力。
3 非西方视角下的全球公共卫生
免疫学的历史一直是全球性的,相关研究也一直与社会史紧密结合。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始研究身体免疫、抗体形成和过敏过程,殖民制度为他们提供了实验场所和实验对象,许多传染病研究的新发现都来源于殖民地[8]。微生物学、细菌学和免疫学的前沿进展基本都来源于殖民地或者后发国家。更广泛地说,科学史和医学史倾向于通过殖民主义的棱镜来看待非西方地区的知识生产。目前的全球科学史研究,大部分仍然难以摆脱中心-边缘的传统视角,目前比较流行的不列颠-印度体系、美国-菲律宾体系和法国-北非体系,本质上还是没有摆脱传统殖民史的框架。传统殖民史对于后发地区自主的科学发展和应用对于世界的贡献认识不足,容易形成一种观念层面的傲慢,即认为后发国家的一切都来源于先发国家的输入,否定或者看低后发国家对于科技发展的贡献。
白玛丽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她的全球科学史视角不再是宗主国与殖民地关于科学的互动,而是考察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如何自主发展和应用免疫技术。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虽然大量西方国家曾在中国拥有特殊权益,但中国却从未完全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国家。虽然中国早期的主要免疫学科研人员大多来自欧美等国,但大规模免疫技术应用却是本国自行组织,这与传统殖民地区在国家独立之后仍然依赖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提供外界科技援助有根本不同。与传统殖民地地区不同的是,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华夏中心观,留学归国科学家普遍有科学救国的情怀。中国留学归国科学家积极参与了全球免疫学的知识网络建设,他们通过日语翻译德语、法语和英语的免疫文本,并与哥本哈根、伦敦和孟买的同行通信。学生们长途跋涉,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研究人员一起学习,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正是这些研究人员指导了生物制品生产研究所,开发了针对中国地方病的新疫苗和血清,并与卫生管理人员合作在国内分发疫苗,这些事实是与传统全球史观相左的。自19世纪后期,国际卫生会议都将中国定为可怕的病毒传播地[9]。从20世纪初叶直到40年代,中国的传教士和慈善组织的惯用手法就是对中国受传染病困扰的农民的悲惨遭遇进行描述,以便为在中国的医疗资助项目筹措资金。在二战期间,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加强了对于中国的慈善医疗援助。从现象上看,中国当时的整体卫生状况确实与传统殖民地地区区别不大。但传统全球科学史忽略了中国科学家当时的科研水平实际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的事实,也没有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免疫技术应用有限并非因为科研水平低,而是由于国家治理能力低下。
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与国际免疫学界基本处于隔离状态。正因如此,中国免疫学发展相对于全球的贡献被高度低估了。当时的中国仍被视为后发国家,而不是一个不接受外部援助的、可以进行疫苗全民接种的国家。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时,世界卫生组织甚至不相信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消灭了天花[10]。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不结盟运动中,中国的免疫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顾方舟等领衔研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效果好、易于保存,还制成了糖丸以方便儿童服用。冷战期间,中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曾经援助匈牙利,帮助匈牙利消灭脊髓灰质炎,在两国的外交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朵拉·瓦尔加(Dora Vargha)[11]认为,中国当时的免疫学科研和实践都是较为先进的,但在当时的评价体系之下这些贡献并未被西方世界认可。中国也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不结盟国家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免疫学医疗援助,对于天花等流行病的绝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确立了“人人享有健康”的新战略目标,这一新方向是中国倡导初级卫生保健模式的成果。中国的成功免疫学实践向世界证明,后发国家同样可以进行成功的免疫学实践。
4 结语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该书毫无疑问成为了国际医学史界具有前沿性的应景之作。拥有更加强大科研队伍和更加丰富医疗资源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面对疫情时并没有表现得比中国更加抢眼,而中国果断迅速的隔离措施和防疫组织也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免疫学作为高度社会化的科学注定了其实践过程离不开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疫苗的研发需要周期,此时只有利用已有的免疫学知识进行合理的社会化组织才能拯救更多生命。
该书在生物政治学层面的探讨也具有极高的创新性。免疫学这一学科发源于19世纪末,当时欧洲正处于“甜蜜时代”,各个民族国家治理能力强盛,免疫学最初的大规模实践就是由警察局等国家权力机构推动的,因而从社会层面看免疫学从大规模实践开始在欧洲就需要面对国家限制个人健康自由的论题。显然,既往的相关科学史研究忽略了免疫学在后发国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忽略了后发国家居民关于免疫学的普遍价值判断。该书的非西方视角对于解释中国居民对于技术应用的价值判断问题有很大帮助,后发国家更加倾向于认可免疫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公共健康的正面效应。这也侧面解释了为何在西方科学界所认可的封锁措施会遭遇来自社会的极大反弹。发达国家完成现代化的时间比较早,其民众对于技术问题与后发国家民众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并不偶然。该书也为中西方社会对于技术价值问题的认识搭建了沟通桥梁。同时,该书的全球视角也更好地诠释了中国免疫学发展与实践对于人类健康的巨大贡献,澄清了传统全球卫生研究框架下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免疫学的片面理解,对于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拓界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