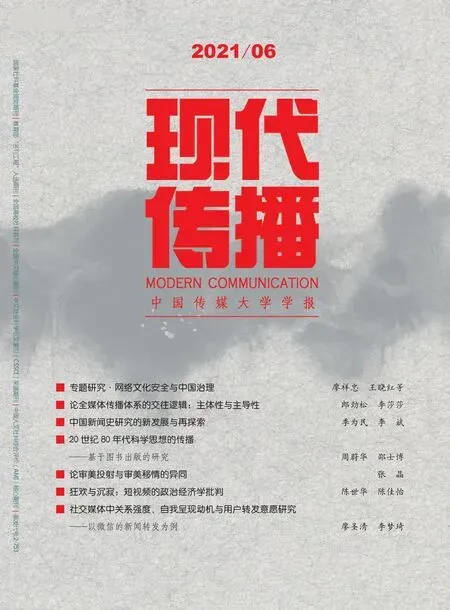数字时代中国国际传播领域面临的五个挑战
■ 徐培喜
大众媒介时代,国际传播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是国际关系和新闻传播研究的焦点问题。芬兰坦佩雷大学教授诺顿斯登和瓦瑞斯(Kaarle Nordenstreng与Tapio Varis)研究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节目的国际流动,得出结论认为国际信息流动是个单行道,主要从发达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①不结盟运动国家以此作为证据,在联合国提出了“国际信息新秩序”,希望提升自身传播实力,改变国际信息流动不平衡,抵制西方通讯社扭曲报道,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失败。②数字时代,谷歌等搜索引擎、YouTube等音视频网站、Facebook等社交媒介平台冲到国际传播最前线,充当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内容传播平台,汇聚数以亿计的用户,释放出巨大的影响力,在为底层和草根赋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沦为大国博弈的工具和场所,给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重大挑战。③
中国经济硬实力实现了极大赶超,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蓬勃发展、自成体系,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华为公司作为5G电信设备商引领全球,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等国家主流媒体走出国门,扎根西方社交媒介平台,抖音国际版TikTok信息服务平台具备了与美国谷歌、脸书、推特等超级平台相比肩的国际竞争力。
私营企业主体的崛起和民间草根力量的壮大,补齐了国际传播的短板,以世界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了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具体效果。这些新兴力量代表着国际传播领域的先进生产力,为克服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奠定了新的经济基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走出了“无米下锅”的尴尬局面,拥有了新平台、新维度。
然而,尽管中国在硬实力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成就,这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恰恰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成就,导致中国被西方敌视,在涉及领土、民族、宗教、历史等诸多重大主题上,西方仍然拒绝从真相、事实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仍然存在尖锐且艰巨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渠道、技术、内容、利益及思想五个方面。
一、渠道挑战
西方以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为借口遏制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封锁中国的对外传播渠道。美国领导的西方保守政治力量对中国做出收紧记者签证、撤销官方媒介播出执照、官方媒介社交媒体账号加注标签、限制海底光缆投资、撤销电信运营商运营执照、封杀或限制中国私营明星企业等一系列激进措施。
中国电信设备和信息服务等高科技企业占据全球科技创新、对外贸易、国际传播制高点,成为美西方安全利益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美国率领西方各国从欧洲和亚洲两个方向对中国发动数字冷战、围堵中国崛起。美国利用“点—线—面”步步为营的方式来围剿华为公司和抖音国际版TikTok等中国明星高科技企业。在欧洲,美国利用爱沙尼亚、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小国作为战略支点和突破口,签署联合声明共同抵制中国5G企业,最终动摇了英国、法国等欧洲大国在5G领域的政策立场。④在亚洲,美国利用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突破口,在印太战略的支撑下将印度拉入了美日澳同盟圈,怂恿印度首先封禁59款中国App。美国以中国单个明星企业作为点,将更多中国企业拉入进来连成线,然后在更广泛的领域形成围堵中国的面,试图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打压中国的最终目标。⑤
美国一方面广泛利用战略、政策、法律、外交工具封杀或限制中国企业,另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对其进行污名化、妖魔化。中国媒介制度、互联网治理模式、网信政策本身构成了美西方政客、强硬派智库、媒介以及社交平台抹黑的核心领域。美西方将中国的国有、私营明星企业和中国网信政策、政治制度捆绑起来对待,将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试图实现“一箭双雕”的污名化效果。
二、技术挑战
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挑战比传统时代更加错综复杂。除了渠道和平台之外,智能技术是其另外一个主要特征。智能技术可以用来批量生产、传播假新闻、假评论。一些国家通过分析大规模的数据库来定位受众,使用机器人水军和算法散布假信息。这些技术手段在影响舆论、左右时局中所起的作用已经不容小觑。
虚假信息代理人建立数以万计的社交媒体假账户、群组、页面,遍及脸书、推特、YouTube、微信、新浪微博等平台。虚假信息代理人利用付费广告、机器人水军等工具,散布假新闻或其他分化民众的信息,干扰正常舆论秩序。各种代理人联合作战,形成点赞、推送、分享等行为,将虚假信息输入到主流舆论,甚至主导舆论。
互联网在速度、广度上完全超越了传统媒介,给数字时代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挑战。涉及种族、宗教等敏感事件的信息内容之所以能够造成巨大的影响,背景因素是互联网对这些事件的无限扩散与扩大。网站是否应该删除争议内容?搜索引擎应否用同样的方式处理搜索结果?都是当下的辩论主题。
2017年6月,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计算宣传研究项目小组发布报告,分析了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加拿大、巴西、波兰、乌克兰等国家的社交媒体中与政治相关的文章,指出机器人水军的舆论影响力,将这些信息操控行为定义为“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⑥西方干涉中国内政也已经落实到代码、算法等技术领域。在涉及到新疆、香港、台湾等主权问题上,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介平台一方面在代码层面较大规模地封禁中国用户,阻挠事实真相的传播;另一方面任由散布假消息的其他账户存在并壮大,且利用自身算法机制加以推动。
三、内容挑战
数字时代,较为典型的跨境内容争议集中在民族(“新疆棉花”事件)、宗教(穆罕默德漫画风波)、领土(美职篮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涉港不当言论)、政治稳定(美俄社交媒介争议)等多个方面。
虽然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禁止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但是这些国际法条款从来没有被落实,网络空间信息内容治理仍然主要依赖社交媒介平台的平台守则。苏联是否曾经为抗击德国法西斯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和日本谁是二战的受害者?香港人民在英殖民者统治期间是否真正享有民主?南京大屠杀是否真正存在?新疆是否存在强迫劳动?对于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在西方舆论操盘者的手中,真相已经变得支离破碎,甚至完全颠倒。中国、俄罗斯、韩国领导人共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媒介直播将这些仪式与舆论有效连接,巩固了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忆。同样的时刻,欧美所代表的西方在共同纪念柏林墙的倒塌,强化冷战思维。中国媒介直播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告知世界中国作为二战受害者的真相。日本媒介逆向操作,纪念广岛长崎核轰炸周年仪式,将日本这个事实上的侵略者塑造成受害者,这些行为已经分裂了两国对于二战的集体记忆。
在另外一些典型争议问题上,数字时代的新旧媒介仍然过于强调直接暴力,故意忽略结构性暴力。因为多次刊登侮辱伊斯兰先知的漫画,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受到极端分子的攻击,这种暴力行为固然可恨。但许多西方媒介从“铅笔和AK47”这个主要视角来报道此类事件,表示铅笔象征着西方文明的言论自由,而AK47象征着伊斯兰文明的暴力邪恶。西方拒绝超越这个事件本身,去批评西方的炮舰、导弹、无人机对中东和北非地区造成的巨大破坏,从而选择性地忽视这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暴力行为。
四、利益挑战
西方行动的背后既有植根于殖民时代的思想根源,也有一条与传统及新兴军工利益集团密切相关的利益动员路径。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和新兴的网络军工复合体需要不断夸大乃至制造威胁,作为自己存在和扩张的理由。在这个复合体的辐射范围内,军火商、国会、五角大楼、保守派智库以及媒介均受益于冲突和高额的国防开支,它们各司其职,巧妙互动,构成利益集团运转的元规则。
中国极其不幸地继承了苏联的负面遗产,成为美国在物理及网络空间树立的现成假想敌。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是这个利益集团生存的理论基础。在军工复合体的眼中,战争及冲突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事情,而成为美国的国家需要。依赖于战争及冲突的盈利模式已然成为美国就业岗位的重要保障,经常凌驾于两党政治和左右意识形态之上。发展至今,这台巨型机器早已背离了形成时的初衷,从“应对威胁”转为“寻找威胁”,又发展到“制造威胁”。原先的“被动防卫”变成了现在的“主动攻击”,原先的“捍卫民主”变成了现在的“唯利是图”。
美国媒介是鼓吹战争的“拉拉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五角大楼雇用了75名退役军官,给美国NBC、CBS、ABC、CNN、Fox、MSNBC等主流广播电视网担任“独立分析人士”。五角大楼在公关和宣传领域的用人规模高达几万人,相当于美国国务院的雇员总人数,这是美国主流媒体积极炒作各种威胁论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制造和挑起冲突是美国军事利益集团构建的帝国生存法则。在这个框架下,美国一方面标榜自己是所有美德的化身,将言论自由等所谓民主社会核心价值观当作地缘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武器,在本可以相安无事的世界上挑起族群冲突,在民主-非民主、自由-不自由的元叙事规则下,污蔑其他文明、文化及国家所代表的文明体系、政治制度、媒介制度。数字时代的到来则为这种行为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场景和动员方式。
五、思想挑战
大众媒介时代,美苏意识形态对抗语境下诞生的典型学术著作是1956年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作者施拉姆等人(Wilbur Schramm)将所有非西方的媒介制度污蔑为“极权主义体系”“威权主义体系”,将西方模式美化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⑦作为欧美畅销教科书,该书影响学生接近30年之久,直到1984年阿特休尔(Herbert Altschull)做出较为客观中立的分类。
阿特休尔在《权力的代言人》一书中表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并非独立的行为主体”以及“所有报业体系中的新闻媒介都是政治、经济权力的代言人”,媒介制度在其本质上没有差异,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发达与发展中之分,以此较为客观地描述了媒介的职能。⑧1995年出版的《最后的权利: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与2009年出版的《媒介规范理论》更为系统地道出了《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谬误。
尽管如此,《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主张仍然代表西方的主流意见。西方在言论自由的掩护下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由来已久。其基本方法是制造主流民意,将别国的媒介制度说成坏制度,将自己的制度说成好制度,形成道义制高点。同样的套路也沿用到互联网模式上,西方认为自己的模式是好模式,别国的模式是坏模式。
东欧剧变之后,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模式,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本来源不再主要基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主要基于文化和文明。“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要隔阂和冲突的主要来源。”“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⑨
文明冲突论为嗜血而生的军工集团撰写了新政治纲领,两者恰属西式世界观在思想和军事阵线上的典型代表,并在东欧剧变这个关键的背景时刻走到了一起。文明之间是否真正存在内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是美国领导的西方首先制造了这些矛盾,然后利用自己的舆论机器宣称这些矛盾真正存在?是世界上所有文明都存在问题,还是西方所代表的文明存在问题?事实的真相恐怕是文明冲突论提供了西方世界观的新剧本,美国按照这个新剧本来制造冲突、改造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表示,正是因为这种分裂的、对立的思维模式,导致西方不可能制定出对世界负责任的规则。他写道:
一定要有‘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这种深刻的‘分裂的政治’意识可以从许多现象看出来,从异教徒意识到种族主义,从热战到冷战,从殖民主义到人权干涉,从经济和军事霸权到文化霸权,甚至在星球大战之类的幻想中也可以看出那种莫名其妙的寻找敌人的冲动。把自己和他人对立起来,把信徒与异教徒对立起来,把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把‘自由世界’和专制社会对立起来,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这就是西方的基本政治意识。这样的政治意识没有世界,尤其不能对世界负责任。⑩
与此相比,中国提倡文明尊重论。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讲话,阐述了自身对文明、文化、以及宗教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指出:“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中国认为网络空间是各个文明、文化、国家交流最为广泛的通道,认为在新的空间应该避免重复各国在传统空间中所走的弯路,不应复制传统空间中的武装化倾向和格格不入的敌我势力划分,从世界观上秉持一种和解主义的思想,做到各文明、文化、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注释:
① Kaarle Nordenstreng,Tapio Varis.TelevisionTraffic-AOne-WayStreet.UNESCO.1974.
② 徐培喜:《全球传播政策:从传统媒介到互联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③ 徐培喜:《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规则的起源、分歧及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页。
④⑤ 徐培喜:《2020数字冷战元年: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两种路线之争》,《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21年第3期,第16页。
⑥ Samuel C.Woolley,Philip N.Howard.ComputationalPropagand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3-5.
⑦ Fred S.Siebert,Theodore Peterson,Wilbur Schramm.FourTheoriesofthePress.Bloomington-Notma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6.p.1.
⑧ Herbert Altschull.AgentsofPower.Londoni:Longman.1984.p.279.
⑨ Samuel 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
⑩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