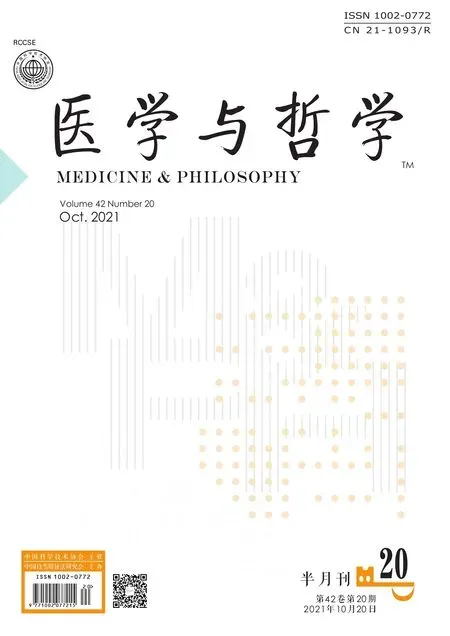明清医家对纵欲与疾病关系的思考
周伟义
在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中,纵欲与健康之间存在着张力。然而,这一课题却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有学者通过民国时期治疗纵欲疾病的药物探讨了当时社会身体观和中西文化汇通与转化的问题[1]。但是,这种汇通更像是中国传统医学借用西方医学理论对既有认识所进行的单方面阐释。那么,中国传统医学自身对纵欲与疾病的认识逻辑又是怎样的呢?明清时期社会所盛行的纵欲风气,显然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绝佳样本。但是,现有研究多为描述性的成果,主要是对医籍中的记载和治疗方法进行梳理[2-4]。毋庸讳言,明清医家对疾病的认识难免存在时代局限性,有学者便提出这类疾病是“医家们用道德观念来推断病因”[5],并且,中医自滥觞之始便与哲学的关系密切,因此,在当今背景下,对明清医家对于疾病的认识进行思想逻辑维度的分析无疑更具现实意义。
1 纵欲关联的疾病
在明清医家的论述中,纵欲是诸多疾病的产生因素。性的基本功能应为生殖,但明清医家认为,纵欲所带来的疾病将会导致性的异化,成为这种基本功能的障碍。《景岳全书》道:“疾病之关于胎孕者,男子则在精,女子则在血,无非不足而然。凡男子之不足……或好色以致阴虚,阴虚则腰肾痛惫,或好男风以致阳极。”[6]462纵欲的不同对象指向了疾病的不同证候,根据性别而分阴阳。在疾病面前,性别又殊途同归于“色”。因此有人总结道:“今人之无子者,往往勤于色欲。”[7]将纵欲作为不育的主要原因。
不育只是身体非健康状态的表征之一,纵欲在异化性的功能的同时,还异化了自己本身。纵欲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感官上的享乐,但其可能造成的结果却是疾病的苦楚。所谓“盖昧者徇情纵欲,因致积热之证”[8]9。性欲的放纵将会带来“热毒”,其几乎可以作用于人体所有经脉,在不同的经脉则呈现出不同的症状,这些症状则以“积热”统而论之。《霉疮秘录》道:“一犯有毒之妓,淫火交炽,真元弱者,毒气乘虚而袭,初不知觉……壮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为患。”[9]王肯堂[10]也道:梅毒“或色欲太过,肾经虚损,感邪秽之气而成”。所谓“酒色劳郁,耗损真元”[11],明清医家认为,纵欲会带来人体“真元”损伤,使“毒”或“邪”更容易趁虚而入,在机体内发生为疾病。
在明清医家的论述中,即便不依靠某种中介,纵欲仍具有使几乎全身器官病变的力量。《普济方》道:“白浊者,肾虚有寒也,过于嗜欲而得之。”[12]《针灸大成》道:“小便淋沥……皆为酒色嗜欲不节,勉强为之。”[13]并且,纵欲的致病性并非仅是行为结果。陈实功[14]言:“下疳者,邪淫欲火郁滞而成。”认为即便未付诸实践,单纯的纵欲思想同样能够致病。
《审视瑶函》载:“乌风内障……风痰之人嗜欲太多,及败血伤精,肾络损而胆汁枯,精气耗而神光坠。”[15]《识病捷法》云:“劳瘵之证非一端,嗜欲不节,起居无时,七情六欲之火时动于中。”[8]142“欲不可纵,嗜欲则脚气发”[16]。无论是眼疾、肺疾还是脚疾,都被医家进行了指向于纵欲的病因推定。
当然,在明清医家的论述中,纵欲所能导致的疾病并不仅限以上几例,如果真的对医籍进行大规模梳理,其实不难发现,在医家的认知中,几乎社会中所存在的每种疾病都能与纵欲建立联系——无论这种行为是否在实践上发生。
2 纵欲的致病逻辑
尽管医家们都相信纵欲与疾病之间联系的存在,但对于其内在机理的解释却不尽相同。以不育为例,众多医家都将男色行为作为其病因之一,对男色影响生育功能的机理,如上引张介宾之语,将其解释为“阳极”,而《宜麟策》却说:“盖男为阳,两阳相亢,必竭其精,精竭则寒,寒则不能生育。”[17]将其解释为“寒”。胡卣臣说:“艰嗣之故有五。一曰性偏刻,好发人阴私;一曰好洁,遇物多不适意处;一曰悭吝,持金钱不使漏一线;一曰喜娈童,非其所用,肝筋急伤;一曰多服热药,铄真阴而尽之。”[18]将其解释为肝筋的损伤。我们并无意讨论哪种解释才是正确的,但我们应当意识到,“作为医学最初始概念的‘疾病’是人们进行价值判断的结果”[19]。当对于疾病的同一病因出现了不同作用机理的解释,这些致病理论便难免是“医学唯心主义”,是从某种包含了价值判断的逻辑起点不断演绎的结果。这些不同的演绎之所以殊途同归,是因为医家们对于“纵欲导致疾病”这一逻辑起点的共同笃信。也正是因此,纵欲与诸多疾病都建立了联系,且其思想与行为具备了同样的致病性。有学者认为,这种“医学唯心主义”的出发点是道德观念[5]。但其实未必,这样的逻辑起点其实渊源有自,继承于先代医家。正如孙一奎[20]182所言:“古人所谓纵欲伤生也。”早在先辈医家的认识中,纵欲即与疾病存在直接的联系,其基于对性与生命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
中国古代医家认为,性与生命之间存在联系,联系的纽带则被称为“精”。“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21]87性的生殖功能所带来的“精”是先天而来的生命起源。《黄帝内经》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21]209医家们相信,上古社会的人因为顺应自然,合于天道,都是长寿健旺的理想健康状态。而当今之人之所以“半百而衰”,其实是因为纵欲的生活方式自戕了原有寿数。所谓“凡精少则病,精尽则死”[22]477。纵欲缩短生命的力量,即源于对“精”的消耗。可见,“精”不仅是生命起源,同时还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23],更是决定寿命长短的关键要素。因此,健康长寿的关键之计便是保“精”,故有“无摇尔精,乃可长生”[24]之说。
中国古代医家对“精”之一物的诠释近乎哲学,在他们的诠释中,“精”并非一个具体事物,它遍布于五脏,不可捉摸。认识源于实践,中国古代医家对于“精”所阐发的理论其实“是由对生殖之精的认识发展而来”[25]。所谓的“生殖之精”,在人体内属于“肾精”[26],其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具有生殖功能的“精液”。当“精”的抽象概念以“精液”的直观体现被认识,纵欲与“精”二者间的张力便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纵欲与“精”间的张力被明清医家们通过形象的比喻表述出来。由于“肾”作为生殖之精的归藏之所,以及“精液”与“精”间的联系,加之肾作为五脏器官的具象性,纵欲对“精”的消耗也多通过其对“肾”的损害为医家们表现出来。《勿药元诠》中便描写道:“人身之血,百骸贯通。及欲事作,撮一身之血,至于命门,化精以泄。夫精者,神倚之,如鱼得水;气依之,如雾覆渊。不知节啬,则百脉枯槁;交接无度,必损肾元。外虽不泄,精已离宫,定有真精数点,随阳之痿而溢出,如火之有烟焰,岂能复返於薪哉!”[27]这里强调的是“淫欲”具有一种调动多种器官的动能,尽管其过程可简化为“血”通过“肾(命门)”,转化为精液流失。“精”转化于血,而血流转于脉;“精”藏于肾,又从中泻出,因此,这一过程的不知节制所带来的是参与了整个过程的经脉与“肾元”的损伤。
然而,即使纵欲行为并未实现,“精”并未以“精液”的直观形象溢出,纵欲思想依旧会带来“真精”无可逆转地流失。因为“淫欲邪思又与忧思不同,而损惟在肾。盖心耽欲念,肾必应之,……凡五劳之中,莫此为甚,苟知重命,慎毋蹈之”[6]177。纵欲思想上的致病力量,来源于其依靠于心所产生的与肾的直接联系,思想的动能使心与肾通过这种联系运行而带来了肾的损伤。这也恰巧是对上引“邪淫欲火郁滞”致病的理论解释。肾不仅与心联系,所谓“肺主气、心主血脉、肾主精”[28],“肾为精血之海……所以肾为五脏之本”[6]7,“肾为禀受之地,诸脏为分布之所”[29],在明清医家的认知中,“肾”不仅是“肾精”的保藏之地,也是五脏之中“精”最主要的归藏之所。因此,“肾”在五脏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所谓“肾为人身之根,本宜闭藏,五脏受精,皆归藏于肾。人能戒淫欲,而不使有伤,病安从来?”[30]尽管在直观上,纵欲行为只是致使“肾精”流失,但“肾损,则五脏皆衰”[31],由于理论上五脏之间的联系以及肾的中心地位,“肾精”的流失自然成为一种关联五脏的连锁反应,意味着更广意义上“精”的流失。“肾精”因此成为了健康的关键要素,而具有动能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引起“肾精”流失的纵欲——无论行为还是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健康的对立面。而这一点,也正是纵欲足以使全身致病的根由。
纵欲之所以致病,是因为其所带来的“精”的损耗。但问题是,“精”的损耗需要通过性行为来实现。但明清医家们显然并不认为单纯的性行为具有致病性。这也便意味着“精”的损耗不一定致病,但这显然与纵欲的致病原理相互矛盾。为了对此进行理论上的调和,医家们则提出了节欲的概念。
孙志宏[32]云:“则寿命修短,全系精气神之盈亏……其害以淫欲为最。少壮宜节,老年宜绝,男女皆同。”在医家的解释中,纵欲所指的是不加节制的性行为。若是节制,则于健康无碍。但问题是,性行为如何才能算得上节制?这一点,恐怕医家们自己也无法说清楚。《医学源流论》中说道:“夫精,即肾中之脂膏也。有长存者,有日生者。肾中有藏精之处,充满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长存者也。其欲动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脱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施去施生,不去亦不生……有肾气盛者,多欲无伤;肾气衰者,自当节养。”[33]“精液”作为“精”的直观体现,医家们当然能观察到它的消耗与再生。由于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因人而异,使节制成了一种无法量化的概念,更不存在一个普适的标准或原则。由于缺乏标准,也由于精深医学素养的缺乏,普通民众通常无法准确地判定自己肾气的盈亏,更无从了解自己的房事是否称得上节制。由于症状的滞后性,往往在身体已因贪欢而亏虚致病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不节制。故有人叹:“人若未死,惟病可以寡欲。”[34]我们并不怀疑传统时代中国医学所具有的科学性,但客观来看,由于缺乏可量化的标准,医家们所谓的“节制”,其标准其实是由疾病来推定的,而这便意味着,是疾病定义了纵欲。因此,纵欲也许并非疾病的原因,而是疾病必须给出的解释。
3 医家的理论反思
医家的任务便是消除疾病对人体的负面影响,因此,面对纵欲,补肾成为了历代医家绕不开的课题。明清时期众多医案则证明了这些或是先代所传,或是本朝新创的补肾方剂的有效性。这便意味着,纵欲对肾的损伤并非是不可逆的,“精”的流失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补回,这无疑客观上为方士提供了理论空间。
医生和方士都起源于巫。不同于医家所提出的节欲,在纵欲与疾病之间,方士们提出的修身延命方法则是房中术。房中术在中国古代历史悠久。这些房中秘术多以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为基础,企图以性行为作为延年益寿的工具。这显然与纵欲导致疾病的医学逻辑相悖。但在医学理论层面,明清之前的医家们对于房中术却并不全盘否定,而是表现出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态度。
《汉书·艺文志》对房中术评价道:“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35]一方面承认纵欲的危害,另一方面又肯定了房中术“至道之际”的理论地位。这种对于房中术的矛盾态度一度为医家们所继承。唐代名医孙思邈[22]476所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就编有《房中补益》一目,既认为人“年至四十,须识房中之术”,又明确指出:“夫房中术者,其道甚近,而人莫能行。”在肯定房中术理论上的有效性的同时,又否定了其在实践上的有效性。元代的朱丹溪对此解释道:“窃详《千金》之意,彼壮年贪纵者,此水之体,非向日之静也。故著房中之法,为补益之助……苟无圣贤之心,神仙之骨,未易为也。女法水,男法火,水能制火,一乐于与,一乐于取,此自然之理也。若以房中为补,杀人多矣。况中古以下,风俗日偷,资禀日薄,说梦向痴,难矣哉!”[36]尽管朱丹溪明确承认了房中术在实践上对人体健康的戕害,但也并未在理论上否定房中术,并借用了理学的逻辑,以圣贤与凡人的对立,来为实践与理论的矛盾提供合理的解释。尽管他们对房中术表示实践上的反对,但显然并非反对房中术作为理论的本身。
明中后期的社会风气则使房中术之风再一次刮起[37]。这表现为诸多房中术著作的流行。“有张三丰的《无根树词》《三丰丹诀》、孙汝忠的《金丹真传》等,提倡阴阳双修,闭精不泄,返精还脑。流传在民间的房中术著作有朱全的《房中炼己捷要》、洪基的《摄生总要·房术奇书》、邓希贤的《既济真经》《修真演义》、浣香主人的《紫闺秘书》及集辑前人著作而成的《素女妙论》等。”[38]在众多房中术著作中,洪基的《摄生总要》中所载的“三峰采战房中妙术秘诀”便为人所熟知。然而,就医案来看,“三峰采战”在实践中并没有达到其所谓的补益功效。
孙一奎[20]712曾接诊过这样一个病例:“秔芝岗文学,酒后近内,每行三峰采战、对景忘情之法,致成血淋。”所谓的“妙术”在实践上不仅没有做到补益,反而带来了血淋之症。血淋的表征为尿中带血。这显然并非个例,吴谦[39]的《医宗金鉴》也言道:“溺血一证,乃精窍为病。每因忍精不泄、提气采战,或因老年竭欲而成。”可见,在明清医家的理论体系中,房中术已经与一些具体的疾病产生了联系。当然,这种联系并非是明清时才开始建立的,先代医家们对于房中术实践层面的反对,显然来源于房中术在个体实践层面所导致的疾病。但是,由于仍承认房中术在理论上有效性,这种反对,在实质上其实是对房中术的失效做出理论上的合理解释,是对房中术的实践主体的质疑。这表示,房中术仍被认为是属于医学理论的范畴。
明清时的医家们则显示出了与前辈医家不同的态度。他们面对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如此直观的、血淋淋的矛盾,不再试着对这种矛盾寻求理论上的和解之道,而是直接对房中术提出了理论上的质疑,试图厘清房中术与医学理论的界限。
因此,万全[40]在《养生四要》中提出:“今人好事者,以御女为长生之术。如九一采战之法,谓之夺气归元、还精补脑。不知浑浊之气、渣滓之精,其机已发,如蹶张之弩,孰能御之耶?已之精目不能制,岂能采彼之精气邪?”直接从理论上否定三峰采战之术的有效性。《医灯续焰》中则说道:“吴山里人日记云:太上曰:‘真人在己,莫问邻。’老子曰:‘事天治人,莫如啬。’是为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则彼家采战之说决非真道可知矣!其原始于富贵人既欲长生,又耽情欲,方术之士因进其说,以逢其欲……误信而误用之,弱者必夭、强者必衰,大都不得终其天年。”[41]从其理论基础——道家理论,对三峰采战之术进行了反驳,并指出房中术得以出现的心理基础是向往纵欲享乐与惧怕疾病间的矛盾,这其实是对房中术的出现动机和道德合理性的质疑。陆以湉[42]则在《冷庐医话》中提出:“采战之术,乃邪说也。孙真人《千金方房中补益篇》详房中之术,且谓能御十二女而不施色必动心,况交合之际,火随欲煽,虽不施泻,真精必因之而耗,安能延年?”直接将三峰采战之术斥为邪说,并进一步对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对房中术所做的描述进行了理论反思,直接对房中术做了理论上的怀疑与反对。这些理论上的反对,其实质是医家们不再承认房中术具有医学理论上的合理性。章楠[43]则更进一步,在《医门棒喝》中说:“无论其术验否,当知天地间未有行悖理丧良之事,而反能益寿长生者。其为害道邪说,显而易见!”跳脱实践成效之外,对房中术做了道德上的批判。谢星焕[44]将方士所谓的房中术与春药称为:“种种妖诞,实堪发指!”更有医家直接将其斥为“房中邪术”[45],这些批判则意味着医家们已是“攻乎异端”,不再承认房中术的医学身份。
这些批判不再受限于前辈医家对房中术的合理性解释,不再试图在道家方术与医学间寻求理论上的和解,这则意味着明清医家已经开始理论自觉,房中术在此时医家的认知中已经失去其医学理论层面的意义。换言之,通过理论反思及道德定性,房中术已经成为了一种无需进行理论探讨的“伪医学”,医学从而也在理论上进一步与同源而生的方术划清了界限。
4 结语
在明清医家的理论中,纵欲实则是一种“享乐的痛楚”。他们认为,纵欲既可以直接为机体带来疾病,也可以通过损耗“真元”使“毒”或“邪”更易在机体内发生为疾病。纵欲本身——无论思想或行为,都拥有致使全身器官病变的力量。
明清医家们都承认纵欲与疾病存在直接联系,但对其作用机理的解释却不尽相同,这意味着,医家们的理论演绎基于对“纵欲导致疾病”的共同笃信。这种笃信继承前辈而来,前辈医家们将生命起源抽象为“精”,并相信其是生命质量与长度的关键因素。因此,“精”先天便带有与纵欲的张力。医家们认为,纵欲能够使血化为“肾精”流泻,故能带来经脉与肾的损伤,由于肾是五脏中心,又可造成五脏的失其补养。纵欲因而有了致病全身的力量。偶发性行为与纵欲皆可致“肾精”流泻,医家们因此提出“节欲”,但由于没有普适的标准与原则,节制的标准实则是由疾病来定义,就此而言,纵欲也许并非疾病的原因,但一定是必须给以疾病的解释。
尽管前代医家们并不认为房中术具有实践上的有效性,但是仍旧承认其理论地位,仍旧在医学理论范畴对房中术进行实践失效的合理解释。明清医家们从实践出发,对前辈医家对房中术所发的阐释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以医学及道家理论破坏其理论基础,在道德层面对其批判。这意味着,房中术已被剔除出医学领域,不再具有医学理论上的讨论意义。这表示明清医家们已经开始理论自觉,进一步明确了医学与方术应划清界限,明确了医学的内涵与外延。这也表明,明清医学在与道家方术进一步划清界限的同时,与儒释两家渐趋渐近。
毋庸讳言,明清医家对纵欲致病机理不尽相同的解释未必能在现代得到有效的验证。因此,我们并没有讨论明清社会具体出现了哪些被认为是纵欲导致的疾病以及相应的应对。但是,医学似乎是一个探查古代社会文化绝佳的切入口。因为,“纵欲导致疾病”逻辑的背后实则反映了对欲望的抵制,而这正是传统时代的普遍共识。因此,医家与疾病的对话,正是社会文化通过医学语言的呈现,其背后所反映的,正是历史的传承与社会的图景。
——杨朱学说的异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