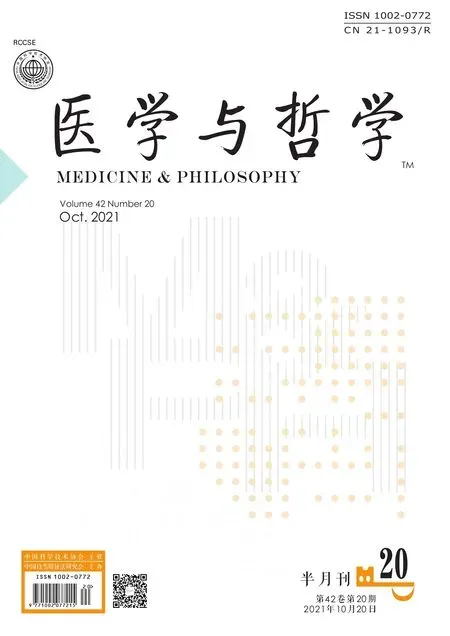“绝地天通”与中国医学“巫医分立”的完成*
孟宪泽 刘 振
如今通常将人类历史上的医学模式分为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1]。中医学代表着中国医学史中的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最早流传下来的《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四部医书构建了其较为完善和系统的学术体系[2]。它们成书的年代跨越甚广,其中最早的《黄帝内经》是多地、多个时代的多个学派在较长的一个时间内不断汇编而成的,其主体部分则大致于战国时期完成[3]。但中医学作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二个医学模式的代表体系,不可能也不会是凭空产生的。现今认为,中国最早的医学是“巫医同源”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巫是中国医学的起源之一。
然而,一旦涉及“巫术”,整个神灵主义医学时期就被视为混沌一片的蒙昧状态,因而中国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内部的演进被忽视了。正如陈邦贤[4]在《中国医学史》中所述:“中国医学早期的演进是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神灵主义医学模式的演变受到了上古时期中国古代思想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绝地天通”事件的巨大影响,“绝地天通”所带来的与“巫医同源”不同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最终促使了中国医学在战国时期完成了巫医分立,为中医学学术体系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1 神灵主义医学的“巫医同源”模式
中国的神灵主义医学时期的“巫医同源”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巫师与医师同源,即最早的时候,是由巫师来行使诊疗职能的;二是巫术与医术同源,即诊疗技术是由巫术实现的。而从当时疾病的诊疗状况来看,这种医疗模式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具有医学的性质。“巫医同源”模式下,一切都在“巫”的意识形态统摄之下,采取超自然的解释,医疗内容也是如此。
商代甲骨文中,各种超自然力量是疾病产生的原因:“……降疾”[5]18756,“贞不隹下上戎王疾”[5]14222正甲,“……帝戎王疾”[5]14222正乙。

疾病的诊断,通常由巫师占卜来确定,并记录在龟甲上。治疗方法是巫师进行巫术式的驱邪或者祭祀,如“御”就是一种御除疾病的仪式:“丙申卜,巫御”[5]5651,“贞巫妆不御”[5]5652。
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也往往投身巫医活动中。夏商周三代的王者行为,均带有巫术和超自然色彩,商王作为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其实也是群巫之长[7]。最高统治者以巫师的身份从事医疗活动,以巫术作为诊疗手段的风尚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
《尚书》载西周初年:“王有疾弗豫……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乃卜三龟,一习吉。”[8]523为病重的周武王占卜、祷告的周公俨然是一个巫师的形象。
“巫医同源”的模式一直持续了整个西周时期,并延续到春秋年间。周代活跃于诊疗疾病领域中的,并不是《周礼》中所记载的各类医生,而是卜、尹、史一类负责占卜的、具有巫的性质的官员[9]10-12。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神灵主义的“巫医同源”模式中,巫师用占卜的技术来诊断疾病,所得出的病因也自然都是超自然的因素。对于超自然力量“导致”的疾病,巫师们则以祷告、仪式等巫术寻求治疗。这种巫术治疗的目的,并不是治愈疾病本身,而是通过与鬼神等超自然力量的沟通,等待疾病消退。即使疾病并没能缓解或者痊愈,巫师和巫术也不会受到质疑。既然如鬼神之类人格化的超自然因素是招致疾病的原因,想要使疾病得到诊治也就只有通过巫师沟通鬼神的中介作用来求治。祈祷后疾病是否能够痊愈,则取决于“鬼神”是否允许疾病的痊愈。巫师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轻易地逃避医疗失败的问责,而且会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地位[10]。
在这种模式之下,虽说巫师运用巫术是在诊治疾病,但诊疗疾病的巫师和巫术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医疗的独特性质,社会生活中其他的礼俗活动,也都是同样的巫师用着同样的巫术,人们也不会称这些巫师为巫医,称这些巫术为医疗活动。
2 神灵主义医学的“绝地天通”模式
神灵主义医学中“绝地天通”模式的源起是上古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绝地天通”,其在古代典籍中的记载见于三处。
《国语·楚语下》载“绝地天通”事件为:“古者民神不杂……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11];《尚书·吕刑》中记载较为简单:“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8]323-328《山海经·大荒西经》则以其一贯的神话色彩描绘“绝地天通”:“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日月山……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12]402
一直以来,“绝地天通”被视为上古时期中国社会与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很多学者也指出,“绝地天通”中所讲重、黎分属神民,是后世神职与民职分流的源头,是一场宗教改革[13]。而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巫师专业分化的过程[14],即从“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的旧秩序,达到“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的新秩序。
虽然“绝地天通”事件本身并未提及医疗内容,但其结果是巫师垄断地位的建立及专业分化的完成。由于巫师占据了垄断的地位,巫术只能由特殊的巫师阶层使用,巫术初步具有了专业的性质;由于专业分化的完成,各种有所区分的职能开始由不同的巫师承担,原本混同一致的巫师职业初步有了分化的倾向。
“绝地天通”发生于颛顼时期,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最早承担医疗职能的巫师见于晚于颛顼的尧时期,《世本·作篇》记载:“巫咸初作医。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15],“巫彭作医”[15],又《说文解字》中释称:“古者巫彭初作医。”[16]
《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将巫彭、巫咸等十位巫师并称,称他们“……从此升降,百药爰在”[12]396,《山海经·海内西经》又将巫彭等六位巫师并称:“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12]301
这些记载表明,在“绝地天通”事件发生的颛顼时期之后,最晚在帝尧时期之前,很可能出现了一批从事专门的医疗活动的巫师。《世本》在记载巫咸的专门职能除了“医”外,还有“筮”和“鼓”[15],《吕氏春秋·勿躬》中也记载:“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17]594-595
可见,在“绝地天通”的巫师专业分化的逻辑下,“医”已经明确地区别于其他巫师的职能,而成为了一项专门的、相对独立的巫术活动。
关于“巫彭”和“巫咸”的职能,《世本》和《山海经》中巫彭、巫咸都称“作医”,巫咸还行使其他职能,《吕氏春秋》称前者作筮,后者作医,这说明当时的巫术虽然出现了专业分化,但其巫师却还不是专业的。各种典籍记载“巫彭”基本仅有“作医”一项,可能其职司较为单一,而“巫咸”的名字却广泛地出现于各类典籍乃至出土的商代的甲骨文中,《山海经》中还有“巫咸国”的记载[12]219。甲骨文的证据显示商代“巫咸”还广泛地参与政治,并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并列于先王受祀”[18]。这位前后出现时间跨度甚广的“巫咸”很可能是当时神巫群体的统称,其工作除医疗外,还有占卜、祭祀、通神等[19]。这些都说明当时有影响力的大巫师,虽说以医疗活动为一项专门的巫术活动,但却不会仅承担单一的医疗职能。

商王虽常为重要人物的疾病而占卜、祈祷,但并没有人会将商王称为巫医。“巫医”应该是由一些等级较低但职能更专门的小巫师来担任。不过,这些巫医还和“作帝尧之医”的巫咸一样,都是服务上层贵族的。而《逸周书·大聚》中则记载了“巫医”在基层社会组织中从事医疗活动:“乡有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22]从服务上层贵族到服务乡里,巫医的普及也不能说不是一种进步。
总的来说,“绝地天通”的医学模式是与“巫医同源”的医学模式相区别的,后者的巫师和巫术并没有独特性,一套占卜、祈祷的手段可以运用在各种场合,疾病的诊疗只是其中一种。而象征着垄断和专业分化的“绝地天通”模式,则是以专门的巫师或巫医从事专门的,区别于其他巫术的诊疗活动,尽管这种活动还是巫术或者以巫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3 “绝地天通”模式的变革趋势
历史上,“绝地天通”和“巫医同源”两种模式长期并存于中国医学的神灵主义时期,因此说“绝地天通”之后,中国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发生了变革,并不是等同于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确切的瞬间——在此之前,巫师、巫术活跃于诊疗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中,而在此之后,特定的巫师或巫医就开始从事专门的医疗活动了,“绝地天通”在医学史上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变革的趋势,它造成了巫师的垄断地位和专业分化,致使神灵主义医学模式的内部形成了一种分化的态势,使得医师和医术有了独立承担医疗活动的机会。一开始这两种模式还是相互补充的,而随着“绝地天通”模式的进一步演进,这个趋势就引向了中国医学的巫医分立。
“绝地天通”的模式具有一种变革的趋势首先是促成了诊疗疾病的专门巫术的产生,促使医术从巫术中分离出来。这些巫术之所以能够区别于“筮”之类的巫术,而作为诊疗的专门手段,一定是具有医疗性质的。实际上,神灵主义时期的医学之所以能够长期指导人类的医学实践,除了因为祈祷等巫术对于自限性疾病具有安慰剂的作用[10],也正是因为这些被区分出来的专门巫术中也蕴含着医术的萌芽。
在一切医术都被笼罩在巫术的氛围下,对于当时的巫医和病人来说,无论疾病痊愈与否,他们总是会采取超自然解释,因为对他们而言,身边的整个世界都被超自然力量笼罩着,神灵主义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然而从实际作用上来讲,从事医疗活动的巫师或者职业巫医虽说会用巫术造成一种神秘的氛围,在真正治疗疾病时还是要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的治疗[20]59。如酒在发明后就是重要的治疗药物,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用药酒和肉滋补病人和老人了[23],《说文解字》称:“醫,治病工也……得酒而使,从酉……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也。”[16]《黄帝内经·汤液醪醴论篇》中也有“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的说法[24]127。此外,大麻、灵芝草也是早期医疗活动中广泛运用的药物。而诸如酒、大麻、灵芝草这些药物,在神灵主义时期,又与巫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巫师服用它们来达到神经失常的状态,以此交通天地、沟通鬼神[25]。
商代甲骨文中也留下了许多治疗疾病的方法,如针刺、艾灸、按摩等[26],出土的药用植物有桃仁、郁李仁、大麻籽、枣核、草木樨等,草木樨能清热解毒,桃仁、郁李仁、大麻籽可润肠通便,大麻籽泡酒还可治骨髓风毒和大风癞疾[27],枣则应是用于治疟的“秉枣”之术[20]59。这些都构成了巫术阴影下早期的医术萌芽。不过,技术是要由人来承载的,没有医师从巫师中的分离,医术不可能自己从巫术中分离,在神灵主义的意识形态塑造下,这些早期医术还是被看作巫术,或者当作巫术来运用,不能成为独立的医术。
“绝地天通”模式的另一个变革趋势,就是医师逐渐从巫师中分离出来。医师从巫师中分离的详细历史过程难以考究,但其逻辑过程却是可以阐明的。巫师作为神灵主义时期的特殊代表,起着“交通鬼神”的中介作用,以神降于身为最高境界,因此神降于身的表现自然不能与正常人的行为举止相同,故巫师往往通过酒、大麻等麻醉性药物达到癫狂的状态以通神明,这使得从事医疗活动的巫师或巫医,难以在交通鬼神的同时运用药物或者技术性的治疗。“绝地天通”使得巫师出现专业区分后,巫教的神事活动中除巫之外,还会增设头脑清醒的神事辅助人员来维持整个神人交通过程的仪式和次序[28]。因此,作为医疗活动的巫术,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有一些辅助人员来进行药物或技术性的治疗,而在他们当中便产生了最初的职业医师。当这些辅助的医疗技术人员独立地采用药物或技术手段治疗疾病有了效果之后,对于疾病痊愈的超自然解释也就越来越无法成立,他们必然从“神灵在世界是设置了疾病和药物并教导我们”[29]的旧观念转向“神农尝百草”这样的由人探索疾病和药物的新的医学观念。
4 巫医分立的最终完成
巫师的辅助人员经过巫术的“祛魅化”后,原先由鬼神致病、沟通神人的超自然观念,转向了自然的观念。医疗技术既然已经具备,疾病的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春秋时期,疾病的解释开始从超自然转向自然的解释。
事实上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已经将自然因素归于致病的原因之一了,商人占卜时经常关注生病时是否下雨[9]18。不过,当时在神灵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作为自然因素的雨被认为是超自然的代理。而当辅助巫师的医疗技术人员,摒祛了巫术的影响后,“雨”就回归到了自然因素的位置,直接地成为了致病原因。《左传》中秦医和总结六种自然致病因素时,“雨”就是其中一种:“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30]1221-1222
《周礼》一书中记载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种专业分科的职业医师,还有“医师”来负责医疗行政管理。其中在说明“疾医”的职务时,也是从自然的角度解释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31]
《左传》中记载的职业医师诊疗案例,除了前述的秦医和以外,还有一位秦医缓,二者都是服务于国公室的医生,受秦公派遣为晋公诊治疾病。很可能当时秦国率先出现了用自然观念解释疾病、运用医术治疗疾病的职业医师,而其他国家尚未像秦国一样完成医师的巫医分化过程。而从《左传》中其他记载来看,较为严重的疾病,还是多以天命、神鬼等异象描述[32],并且往往首先以巫师占卜求因、求治,然后或许才会求医治疗。上述出现职业医师身影的两个医疗案例中即是如此:“晋侯梦大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30]849-850,“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30]1217-1221。
而有的则仅以巫术求因论治,并不寻求医师的帮助。“郑子产聘于晋。晋侯疾,(韩宣子)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30]1289-1290
而《左传》中其他关于重病的记载,也往往都有巫史的身影而不见有医师的作为。一些侧面的例证也可以说明,即使职业的医师已经出现,春秋时期诊疗疾病的首选仍是巫术的占卜,而非医术的治疗,如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曹臣贿赂筮史欺骗得病的晋文公:“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使曰以曹为解。”[30]474
因此,只能说春秋时期是巫医分立的开端,而不是完成,超自然解释和巫师在当时的社会上仍然有广泛的影响。从上述关于医师的记载中也可以发现,尽管当时的医缓和医和对疾病采用了自然的解释,但从结果来看,医师诊疗得出的结果和巫师所说的结果是一样的,也没有展露或阐释医术的作用。于是乎在这两个医疗案例中里,医师的解释反而像是对巫师神秘语言的解释说明,这实际上还是认同了巫术的合理性。从春秋时期的医疗案例中还是可以看出“绝地天通”模式中巫与医互相补充的痕迹。
经过春秋时期的演变,到了战国时期疾病的诊疗活动已经是职业医师的主场,而几乎不见巫师的身影了。《史记·扁鹊列传》中扁鹊的形象是战国时期良医形象的集中投射,西周以来被描绘成治疗者和不死之人的半鸟半人的巫师形象,也转变成了扁鹊这个神医的代名词[9]24。从《扁鹊列传》的内容来看,扁鹊在各个国家都受到了对于其医师身份和医术的高度认可,当时的人们对于疾病也采取了自然的解释:“……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于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33]2145
同样是职业医师,扁鹊相比于春秋时期没有任何展露医术记载的医和、医缓,历史的记录者则细致地描绘其妙手回春的高超诊疗技术。“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適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33]2148
同时,扁鹊开始主动地与巫术撇清关系。当人们称颂他有起死回生之术时,他并不以任何超自然的语言来渲染自己医术的神秘色彩,而是用自然的解释来阐释生老病死。“……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33]2148
他公开地宣称“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33]2149。巫术成为医师所摒弃的内容,说明医师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意识。而主体内容在同时期完成的《黄帝内经》中也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24]113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尽数》称:“今世上卜筮祷词,故疾病愈来。”[17]391
三者所阐述的思想,共同体现了当时职业医师群体对于巫术的主动摒弃,这是春秋时期的职业医师所不具备的,巫医分立最终在这个时期完成了,“绝地天通”模式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