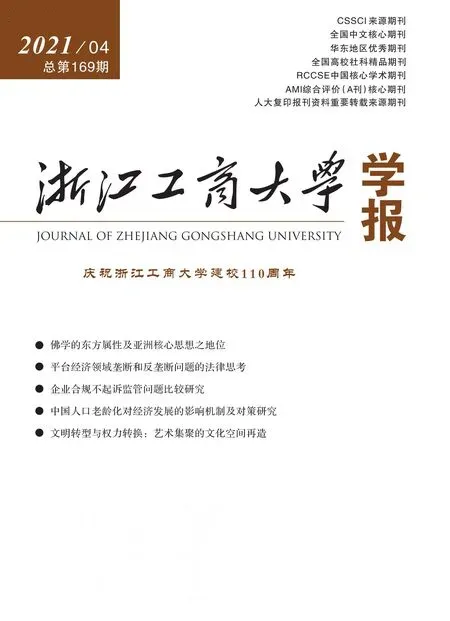文明转型与权力转换: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再造
荣 洁,胡惠林
(1.南京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2.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801;3.上海交通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上海 200240)
一、 作为文化空间的艺术集聚:社会转型中的精神空间
文化空间由自然、精神、社会三重属性的系统性作用而构成,其本质是以人为主体所建构的精神社会性。艺术集聚作为文化空间的一种特殊形态,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相伴生,表征为艺术世界的精神空间建构。
(一) 文化空间的本质:精神社会性
由于文化内涵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基于空间维度的文化空间因此也具有不同视角的概念解读。一方面,文化空间是与生产空间、居住空间相对应的“第三空间”,是人类社会从事文化生产、文化展示与文化消费等一系列文化活动的具象空间。另一方面,文化空间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时所使用的专有名词,用来指代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文化形式和重要形态。上述界定分别基于物质与非物质视角,前者强调文化行为及其活动场域的可视性,后者赋予文化空间以虚拟性和符号性。
事实上,文化空间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并非彼此对立或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联系、融合统一的。物质载体是精神表征的物化形态,精神表征是物质载体的意义升华。在以物化形态为载体的基础上,人文精神、文化表征、文化内涵等要义构成了文化空间的精神本质。其中,“人”是文化空间的纽带和介质,文化空间既被人类建构和塑造,又被人类感知与体验,特定群体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与相应的文化体验和文化归属相呼应,进而赋予文化场所以文化认定和精神交互。这种来自人类精神社会的符号化建构和意义性表达,决定了文化空间的精神社会本质。
更进一步地,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作为文化空间的两个基础性维度,又被纳入社会空间的建构之中,成为社会性空间生产的组成部分。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具有自然、精神、社会三重属性,并据此将空间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这种划分方式与爱德华·W·索雅所提出的物理空间、认知空间和空间性的社会生产[1]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均强调三种空间类型在立体化空间建构中的关联性,以及社会空间对自然空间和精神空间的驱动作用。
概言之,对文化空间的认知既要基于自然、精神、社会三重维度建构系统观,更要从以人为主体的精神社会视角探究其本质。
(二) 艺术集聚:社会转型中的新兴文化空间
本文所研究的艺术集聚是指以美术行业为主体的狭义的艺术生产集聚,具体体现为相关从业者在某个特定区域自发或组织形成的规模性丛集[2]。事实上,艺术集聚这一文化现象古已有之,宋代年画生产、明清地方画派均是传统社会艺术集聚的典型代表。这些文化空间以松散性、地域性、本土化为特点,是古代城市在不断进行自我演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产物,具有典型的农耕文明的文化经济特征。那么,这一古已有之的文化现象,为何在当代获得了画家村、艺术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全新的生命形态并且一跃成为产业转型、城乡发展的内生动力及文化场景?究其根本,当代艺术集聚的生发,并非传统艺术集聚的复现或衍生,而是催化于当代社会转型,与社会转型相同构的文化空间建构。
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和整合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和产业形态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思想解放、制度变革及产业结构调整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弹性与活力,空间资本得以重新配置,从而为艺术集聚奠定了思想基础、体制基础及物质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追求艺术理想的一批前卫艺术家租用闲置民居在北京郊区自发集聚,宣告了画家村这一探索性文化空间的诞生。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下,艺术集聚赋予日趋衰落与闲置的工业空间以新生,由此开拓出城乡并行的空间格局。
在社会转型中孕生的艺术集聚现象,同样也在社会转型中获得了发展的全部合理性。在由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意义已不再仅限于繁冗工作之余的娱乐消遣,而是以文化参与及文化消费的方式逐渐融入大众生活。艺术生产者作为佛罗里达所称的“创意阶层”之一[3],他们所建构的文化空间在注重感性回归与美好生活的后工业社会,逐渐与社会结构和大众生活发生密切关联,从而成为产业转型及生活艺术化的有效路径。正是在物态载体更新、文化意涵演变、社会空间转型的意义上,艺术集聚成为区别于传统艺术集聚的新兴文化空间。
二、 文明关系转型:艺术集聚文化空间再造的精神内核
艺术集聚文化空间再造的精神内核,是社会转型中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发生转变从而推进的文明关系转型与再造。文明关系再造的实质,则充分体现于人与空间的文化关系再造。城市和乡村构成了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单元及文明形态,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依托于城乡而存在,也在城乡文化空间中更迭与转换。艺术集聚的生命形态借助于城市工业遗产及乡村闲置空间得以实现,因而艺术集聚文化空间再造的精神内核也基于城乡二元维度而展开。
(一) 乡村型艺术集聚:前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型
在中国人的精神建构中,乡村承载着最深层次的精神寄托,是数千年来乡土文化得以传承与延续的精神原乡。与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相伴生的乡村衰败,导致乡村的精神生态和精神空间日益遭到解构与毁弃。艺术集聚以艺术介入文化空间的方式,有力地推动了前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前后,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使得原本用于农耕文明生产生活的空间渐趋空置,甚至呈现出空心村景象。乡村型艺术集聚便是以这些乡村闲置房屋或闲置空间为物质载体,赋予农耕文明空间以后工业特征的文化空间再造。与丹尼尔·贝尔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界定,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依次更替的社会发展范式相对照[4],艺术集聚对于乡村文化空间的重塑与再造是跨越式、突变式的。当乡村社会延亘了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后又与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相碰撞时,艺术集聚以空间介入的方式助推乡村文化空间逾越工业社会形态,直接由前工业文明形态向后工业文明形态转型。
乡村型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再造,是由前工业文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向后工业文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文明转型。由农耕文明所建构的乡村文化空间,体现为以农民为主要生产力、以土地关系为主要生产关系的文明关系。在艺术集聚嵌入乡村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文化生产力形态由农民向艺术生产者这一创意阶层转变,生产方式由物质性的农业生产向精神性的艺术生产转化,由此带来的文化生产关系也逐渐摆脱土地的束缚而转向知识、美学、艺术所塑造的新兴文化生产关系。例如,北京宋庄、深圳大芬油画村、观澜版画村、重庆古剑山艺术村、都江堰聚源画家村等乡村型艺术集聚,无论是局部性的房屋租赁再造,还是整体性的空心村改造,均是对村庄原有的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文明再造。伴随着艺术集聚,延续千年的农作习惯和生产方式被迅速改变,收入方式变更又推动了当地农民生活习性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并重塑了原有的空间功能。我们看到,昔日的破败民居,今日的艺术场景、创意空间;昔日的农业生产者,今日的艺术生产者、资本所有者;昔日单一化的农业生产结构,今日复合性、生态型的多元产业链。艺术集聚成为一种文化资源,为原有乡村文化空间注入了后工业文明的文化元素,并以文化动能的形态赋予传统古村落以传续更新、空心村以转型发展的文化再造意涵。
在艺术集聚的变迁进程中,乡村不仅是早期艺术集聚的生发地,也是当前艺术集聚乡村化回流的精神原乡。艺术集聚对乡村文明的文化空间再造是以原有文明形态为基底,前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相互交融的融合性再造。艺术集聚以其独特的文化动力,使乡村的传统性得以延续,现代性得以丰富,由此赋予乡村文明以新的生产力结构。
(二) 城市型艺术集聚: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型
中国城市文明由乡村文明延续发展而来,随后又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衍生出城市精神社会功能的多样化需求,从而使得城市文化空间既建筑于乡村文化空间基础之上,又延展和超越于乡村文化空间[5]。近代以来,城市作为工业文明和工业化进程的核心体现,形成了以工人为主要生产力、以资本关系为主要生产关系的文明关系。
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空间原生功能的退场以及在城市中历史地位的衰退,使城市作为一个精神社会体而发生了巨大变化,所谓“绣带城市”的出现正是这种社会转型的直接产物。艺术集聚对工业文化空间再生进行赋能,其合理性源于对工业文明“缺场”与“在场”这一精神心理的当代呼应。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产业结构转型解构了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及社会层级,也悄然改变了崇尚理性与效用的工业社会内嵌于大众生活方式中的文化价值观。然而,工业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工业时代的文化符号作为一种工业文明的“待在”,赋予人们精神社会层面的场景延伸与情感寄托,并以建筑性历史档案的文化意象获得了文化再造的合法性。
以北京798、上海莫干山M50、重庆坦克库、杭州loft49、成都蓝顶艺术区为代表,艺术集聚对工业文化遗产的空间再造,重构了昔日文化空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史性地转换为后工业时代创意、想象与激情的来源,为文化空间再造提供了文化资源与内生动力。艺术集聚对工业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再造不是从符号本身的内在特征中获取的,而是来源于符号间的对立关系。在艺术介入下,工业文化遗产空间由工业生产空间转变为艺术生产与消费空间;曾经的厂房、仓库、码头转型为开放的、鲜活的公共文化空间、城市文化名片;昔日的物质生产者蜕变为今日的创意者、消费者、观赏者[6]。工业文化遗产在原有空间的价值再造与赋能中得以意义重构,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场域。
(三) 习性促生行为:二元文化空间的互补性建构
由艺术生产的规模性丛集所形成的艺术集聚,作为后工业时代艺术生产与消费行为的聚合体,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资源,赋予乡村文化空间及工业文化空间以精神层面的文明关系再造。在对工业遗产空间与乡村闲置屋舍的艺术介入中,城市工业遗产所代表的复制性、封闭性与程式性,以及乡村闲置空间所表征的传统性、保守性与传承性,统统被后工业时期所崇尚的开放性、个体性、交互性所重构。需要指出的是,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再造并非对原有空间的彻底性解构与颠覆,相反,它在由艺术家所塑造的液态磁场的作用下呈现出多种文明形态相互融合的互构性。
城乡二元文化空间“是一种流动的文化空间,是一种文化互补的空间关系”[7]。对于艺术集聚而言,城乡文化空间的互构性源于艺术家这一特殊群体的习性的形构与再生产。“习性”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基本概念,布氏将习性定义为“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的功能”[8]116-117。换言之,习性是“存在于不同领域的潜在的实践原则”,它既是“一种被结构的结构”,来自外在结构的无意识内化;同时,它又是“一种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不断塑造着行为实践。
一方面,艺术家作为以文化资本为主要权力结构的知识性群体,在自由化的职业特征及创新型的思维模式等方面受到习性的规训,并作为“结构的结构”而发挥着内化于该群体的习性特征。当原有空间的功能衰退引发相应的文化衰退时,艺术家以集聚的方式介入空间,并在习性的作用下着力将价值观、创造力和行动力融入文化场景的营造之中,以充分的文化参与性、文化体验性、文化认同性提升原有空间的文化吸聚力,进而形成由静态到动态、由固态到活态的新兴文化空间,为艺术集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另一方面,习性作为一种触发性、中介性的力量,产生于与客观情景结构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反之又强化与塑造习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集聚促进了城乡二元文化空间再造的互补性建构。在城市型艺术集聚和乡村型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再造中,文明形态转型所建构的文化空间及其客观情境,又进一步形构了艺术家的习性倾向,推进了习性的再生产。一般而言,习性的再生产通过艺术场域中的艺术表征得以实现,例如艺术风格、创作模式的变化等。城市型艺术集聚与乡村型艺术集聚由于融合了不同文明形态而在艺术风格与创作模式方面显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一般而言,前者更强调先锋性和前卫性,而后者更突出在地性和乡土性。这种艺术表达的倾向系统反之重塑了艺术家的习性养成,使之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的行为功能。由于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干预,艺术集聚在物理空间形态上长期处于非稳定状态,这便加速了艺术家在城乡艺术集聚空间之间的流动性。这种长期性的群体性流动构成了一种艺术表达的液态磁场,并在流动中重塑习性,进而促生行为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城乡文化空间再造逐渐呈现出互构态势。乡村型艺术集聚打破了固化的农村文化空间结构,以城市所具有的新锐、先锋、前卫的艺术理念重塑了农村原有的文化生态,使之作为城市文化资源的涵养地而得以空间再生。而城市文化又在乡村的艺术集聚中得到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进而形成一种精神社会层面的城乡文化互补与再造。
总之,艺术集聚文化空间再造的精神内核体现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型,这种转型并非对固有空间的颠覆和消弭,而是在交融与互构的同时,赋予文化空间以更加显著的后工业文明特征,从而实现文化空间的活化与再生产。
三、 “僭越”与“变异”:艺术集聚文化空间再造的权力转换
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再造不仅表征为由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文明形态转型,还体现于艺术场域中的符号权力转换。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在艺术场域中的权力关系转型,使得艺术集聚呈现出文化空间的“僭越”与“变异”。
(一) 文化空间“僭越”:文化资本的能动性实践
所谓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僭越”,指的是前卫性、先锋性、开拓性的文化空间由“地下”到“地上”、由“另类”到“主流”、由“介入”到“确认”的能动性跃升过程,标志着艺术集聚的文化表征由“小众”向“大众”,由“个体”向“社会”的空间转型。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僭越”集中体现于自发形成的原生类艺术区,其实践进程生发于艺术集聚的现当代艺术源流,转型于文化资本与经济场域的资本置换,最终蜕变于文化资本与政治场域的利益共生。
布尔迪厄提出“正统与异端”的冲突,用以指代在争夺文化合法性的场域斗争中文化“掌管者”与文化“创造者”之间的对抗[8]143-144。改革开放后,原有艺术系统的体制变革以及西方当代艺术在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方面的符号语言转变,促进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的身份重构和创作转型。这些处于体制外但仍持有文化资本的艺术家,成为占领新符号的艺术生产者。作为“新知识系统的创造者”,这些前卫艺术家在“正统与异端”的对抗下,不可避免地与主流文化这一“知识的合法化系统的再生产者”发生了冲突。
以中国第一个艺术集聚群落——圆明园画家村为例,集聚者“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自由散漫、野蛮生长的非组织形态,与传统文化空间格格不入的“非主流”艺术,集中表征为“另类”和“叛逆”的“异质性”文化对传统精神社会及主流文化权力的解构,最终引发了系统不兼容的文化排异反应而解体。精神社会层面生态适应性问题的出现,是文化场域中“保守”策略与“颠覆”策略进行权力抗衡的结果。“保守”策略代表着权威、正统,“颠覆”策略意味着异端、叛逆,这两种文化空间在文化聚合力、社会包容度尚处于培养中的社会转型期不期而遇时,权力抗衡乃至排异反应均在所难免。
更重要的,早期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建构一定程度上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符号意涵。冷战后,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愈发具有潜隐性,当西方以对“他者”的想象为预设,以所谓“国际化”标准作为艺术评价指标时,西方对中国艺术区的扶持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渗透的符码[9]。加之西方媒体对画家村的高度关注和报道,西方艺术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力支持,加剧了文化“掌管者”与文化“创造者”之间的权力冲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早期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具有硬性“介入”的特征,反映出多种价值观的磨合与冲撞。
随着文化全球化及产业结构调整,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权力置换,建构出符合时代语境的话语体系。经济场域自身没有符号,需要借助于其他场域的符号以实现权力;而艺术以符号为表征,又具有置换为经济权力以谋求生存发展的物质需求,二者具备相互转换的合理性。这一点在深圳大芬油画村的形成发展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与圆明园画家村几乎同时出现的大芬村,一开始便以“艺术”与“市场”相互融合的艺术产业化模式推进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转换。由于油画产业具有发展经济、解决就业、打造名片的文化经济价值,文化空间再造的过程也因此与社会转型期的在地性文化诉求实现了内在统一。当艺术资本与经济资本在市场规律下相互置换并实现良好的共生价值时,政府作为政治资本的所有者,也开始与艺术资本构建共生关系,并以制度性认定的方式给予其合法性确认。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原创型艺术集聚,如北京79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的文化空间再造。相较于大芬村最初以名画复制为主要生产形态的集聚模式,原创型艺术集聚由于突出的先锋性和前卫性,而在文化“僭越”中表现出更加激烈的权力抗衡。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冲突聚焦于物理空间的规划与再利用,即对空间符号权力的争夺问题。相对于具有统治地位的权力场域,艺术场域在权力斗争中处于“从属的”或“被支配的”的地位,随时面临符号的被重构。而社会权力的强力介入,打破了二者之间强势的对立局面。其中,知识精英和中西方媒体作为社会权力的一部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李向群之于798,栗宪庭之于宋庄,黄永玉之于田子坊,以及中西方媒体将艺术集聚作为文化名片予以广泛宣传,均代表着社会权力对文化权力的肯定及赋能。正是这种社会性的权力赋予,推进了艺术场域的权力转化。于是,权力场域及文化场域从“保守者和挑战者”的尖锐对立中逐渐挣脱而出,在维持艺术场域本身的问题上展现出一体化逻辑,并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新生命形态赋予艺术集聚以制度性、合法化确认。
至此,艺术集聚文化资本的能动性实践,唤起了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的权力关注,并基于权力转换实现了从“介入”到“确认”的文化空间“僭越”,由此获得了文化空间再造的价值意涵。
(二) 文化空间“变异”:文化资本的被动性挤压
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变异”,是指以文化资本为核心要素的艺术场域被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等其他权力资本所侵占、挤压、甚至重构的过程。当前,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变异主要集中在文化业态更为复杂多元的规划类艺术区,是艺术集聚在发展转型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商业化和同质化为表征,反映出权力失衡而导致的艺术生态位的偏移现象。
在布尔迪尔看来,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等权力场域以元场域的形态而存在,更为具体、分化的专业场域则属于一个个区隔化的次场域。元场域与次场域之间既有相对自主性,又具有关联性和同构性。艺术集聚以归属于文化场域的次场域而存在,在转型发展中与元场域之间的同构性不断加强。各种资本间的互利共生一方面为艺术集聚的合法化发展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资本支持;而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对艺术场域的统治性,艺术集聚文化空间逐渐偏离自主性原则,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从而陷入精神失语的“变异”境地。
第一,经济资本挤压下的文化空间商业化。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结合,是精神形态转化为财富之源的特殊存在方式。对艺术集聚而言,物质层面的经济诉求与精神层面的艺术逻辑各具合理性与合法性,前者决定艺术家的生存,后者关乎作品的灵魂。然而,“由于文化和经济的不同社会属性,二者在价值取向上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调和性”[10],这种不可调和性成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相互冲突的根源。经济权力的过度介入极大地消解了文化权力的符号话语权,诸多艺术集聚区转变为文化旅游区、艺术街区等消费场所。例如,798艺术区的文化生态随着经济资本的大量侵入而迅速转向商业化。2004年—2005年,798艺术区的年游客接待量达50万人次,2006年跃升为100万人次,2007年近150万人次,而至2008年,仅奥运会和“十一”黄金周期间,就突破70万人次。(1)沈仲亮:《北京:798艺术区旅游开发再引争议》,载于《中国旅游报》,2009-08-25。这种商业化和低端化的文化空间表征在上海田子坊也表现得极为显著。2015年,田子坊的店铺租金已超过上海新天地,每月高达8万元。高额租金加剧了空间主体的流转速度,艺术集聚的核心在场者由艺术家转变为各类商业店铺。如在田子坊的文化生态结构中,服装店占比22.92%,手工艺品和餐饮业占比均为14.58%,而文化艺术场所占比仅为2.08%。(2)张琰:《他们为什么离开田子坊》,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16-08-25。
如前所述,文化空间是物质载体和精神表征的统一体,物质载体是精神表征的物化形态,精神表征是物质载体的意义升华。在艺术集聚文化业态重构的过程中,物质载体的变迁推进了精神表征的转化,艺术生产的价值意涵逐渐被消费符号所侵蚀、占据甚至消融。从根本上讲,艺术集聚的本质是为艺术家的个性化创作提供空间合法性的艺术生产集聚,具有艺术生产的场域精神。但在经济资本的挤压下,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逐渐疏离了艺术审美的本质属性,消费逻辑取代生产逻辑,从而在商业化的进程中发生了变异性再造。
第二,政治资本挤压下的文化空间同质化。文化资本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常常在政治资本的统治下居于从属地位。当艺术集聚获得了合法性确认之后,便被赋予了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经济转型、产业调整等多重价值形态,这些价值形态为政治资本的累积提供了文化资本转换的新兴路径。于是,在政治资本的推动下,政府通过“收编”与“再造”两种方式对艺术集聚进行规划。一方面,一部分发展成熟的原生类艺术区被政府授牌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实现了由“边缘”到“主流”的身份转型,例如北京798、上海田子坊、深圳大芬村等;另一方面,当艺术集聚的文化资本释放出巨大的权力转换动能时,政府将其视为一种可被“复制”的转型模式,将艺术集聚纳入整体性的空间规划与改造之中。继2006年国家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以来,由政府规划或政府主导的艺术集聚几乎遍布全国。目前,除西藏之外,我国其他省级行政区、直辖市均涌现出艺术集聚区,掀起继工业园区之后的新一轮园区建设热潮。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政治资本对艺术集聚的规划式介入掺杂了政绩优化、经济创收、文化营城等多向度的要素考量,容易导致政治资本对文化资本的权力挤压。其中,同质化是政治资本挤压文化资本最显著的文化空间变异体现。总体来说,艺术集聚文化空间的精神内核表现为以后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多重文明形态的相互交融,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但就个体性的艺术集聚而言,其文化空间又具有鲜明的在地性,因而也就具有了不可复制性。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艺术市场条件、大众消费水平、空间地理区位等要素在影响艺术家集聚空间选择的同时,也作用于艺术家生产创作的文化养成,形构出独特的文化空间。
当前,政治资本在艺术集聚规划中的根本症结在于,对艺术集聚物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混同,换言之,即注重物理空间的模式化再造而忽视文化空间的精神阐发。物理性再造具有可复制的“模式”效应,同时也具有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的合法性;然而,仅仅照搬物理性再造的“复制”模式,缺乏结合文化在地性的个性化表达,便会导致艺术集聚的“千城一面”和内涵失语,仅留存物质外壳却丧失精神内核。当艺术集聚的文化生态被政治资本所重构,则往往容易陷入文化空间同质化的变异性再造之中。
总之,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再造,寓于文明关系转型和权力话语转换之中,前者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驱动,后者由艺术场域中的权力角逐所造就,二者共同构建出艺术聚集文化空间的再造系统。对这一问题的剖析,有助于从精神社会体的更新与再造视角重新审视艺术集聚的现实意义及发展瓶颈,从而进一步赋予其文化价值,激发其文化动力,阐发其文化风貌,塑造其文化正义,最终促进中国艺术集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