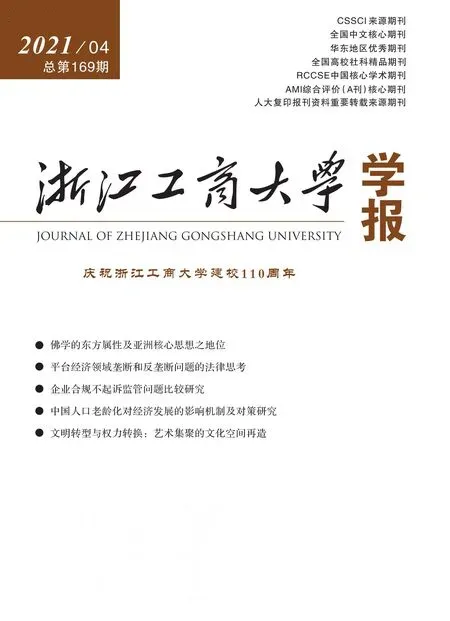犯罪学视角下的矫正社会工作专业性和有效性分析
熊贵彬
(中国政法大学 社会学院, 北京 100088)
一、 问题的提出
专业性和有效性是一个职业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社会工作专业性是指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所应具备的专业素质和专业价值,并运用专业方法提供服务解决社会问题[1]。当前,相较于极力突出的专业性,国内社会工作界似乎有意无意回避了有效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四:其一,在诸多实务领域,专业社会工作的有效性不一定比本土性助人工作更强[2-3];其二,社会工作的有效性难以准确评估,不仅是宏观性的社区工作[4],微观的个案工作同样如此[5],因为很多服务难以随机分组试验,只能进行过程和结果方面的描述性评估;其三,社工学界对社会正义的强调和对工具主义的批判,淡化了对有效性的关注[6];其四,地方政府追求创新,强调在某些公共领域的服务突破,完成相应指标即可,有效性考核成为软性指标。然而,对社会工作有效性的关注甚至质疑自社会工作诞生以来从没有停歇。最著名的莫过于1973年的“费舍尔旋风”(Furor over Fisher),他发现只有少量社工服务满足前后测标准,没有多少服务对象的状况因为社工介入得到改善,甚至有一半情况还更糟[7]。 西方国家随即兴起了一股对社会工作有效性评估的浪潮。当前,我国对社会工作有效性的质疑也开始浮现[8]。而在罪犯矫正领域社会工作有效性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甚至可视为专业性的核心维度。
我国矫正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过程中,主要采取了福利服务模式。矫正社会工作引用最为广泛的是史柏年的界定:“矫正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在矫正体系中的运用。它是指专业人员或志愿人士,在专业价值观指引下,运用专业理论和方法、技术,为罪犯(或具有犯罪危险性的人员)及其家人,在审判、监禁处遇、社会处遇或刑释期间,提供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纠正、信息咨询、就业培训、生活照顾以及社会环境改善等,使罪犯消除犯罪心理结构,修正行为模式,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福利服务。”[9]该界定被社会工作界奉为权威,使得矫正社会工作总体上以一种福利模式得以推展。
然而,20世纪90年代北美兴起的循证矫正运动中,系列研究已经证明纯粹福利服务性质的矫正项目对于罪犯矫正没有什么效果,包括社区治疗服务项目[10]、精神问题干预[11]等领域都一致性地显示出没有减少再犯的效果。而综合运用刑事司法措施和矫正治疗服务的项目都呈现出显著的有效性,无论是在荟萃分析[12]、准试验研究还是相关分析[13]之中。加拿大循证矫正学派专门指出,普通心理辅导对罪犯矫正的效果不明显[14]246-252。我国矫正社会工作一线实务,包括社区矫正和青少年司法等领域,大量借鉴的是普通心理辅导和困难救助方法,体现为明显的福利服务特征。社会工作专业化发端于慈善救助及其方法的职业化和科学化,而矫正领域致力于修正犯罪越轨的思想和行为,单纯的慈善救助思路还难以有效达成该目标。当前亟需在普通社会工作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犯罪学知识和方法,借鉴本土性循证矫正研究成果,不断提升其专业性和有效性。
值得探讨的是,同样关注罪犯矫正的犯罪学在学术发展史上提出了哪些有影响的预防再犯思路?这些犯罪学思潮对西方矫正社工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循证矫正在何种意义上去伪存真、提升矫正领域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矫正社会工作福利模式的核心内涵是什么,面临哪些挑战?我国矫正社工专业性和有效性的本土性循证探索处于什么状态?我国矫正社会工作应该采取何种发展策略?
二、 犯罪学主要流派及其对矫正社会工作的影响
人类社会形成以后,犯罪现象就随之而生,不存在没有犯罪的社会形态[15]。18世纪中叶犯罪学正式诞生以来,逐步形成了众多理论流派,从不同的视角解释犯罪原因,探求预防犯罪/再犯的有效方法,以保卫社会和矫正犯罪人。这些犯罪学思想对不同时代和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措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不同理论流派的创立者及后继者来自不同领域,包括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统计学和地理学等,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分析视角和理论体系。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流派(相近的派别合并)的犯罪原因及预防对策进行简要梳理和归纳,如表1所示。由于某些理论派别内部观点也存在分歧,表格内容只能是粗线条的大致概括。
这些犯罪学思想推动着刑事司法制度和犯罪越轨行为矫正事业的不断发展。古典学派奠定了近代刑法学的基础[16],也推动欧美威慑理念的落实[17]。实证学派则把研究视角由犯罪行为转向犯罪人[18],着重分析犯罪的原因。如菲利认为实证犯罪学是基于犯罪人身体、心理、社会和自然条件的统计分析和经验调查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对于可以治疗恢复犯罪人,广泛采取刑罚替代措施和不定期刑;对于不可治疗对象则采取镇压和隔离措施[19]。 实证学派的治疗恢复理念催生了社区矫正制度[20],注重刑罚效果,落实教育刑和刑罚个别化理念,于是缓刑、假释、少年司法制度等刑事司法措施纷纷登上历史舞台[16]。这些司法制度为矫正社会工作开创了广阔的介入空间。
“二战”后,犯罪学的研究中心由欧洲转移至美国。萨瑟兰和芝加哥学派推动犯罪社会学成为犯罪学的主流范式,突出犯罪的社会原因。克利福德·肖和麦凯20世纪30-50年代发起了著名的芝加哥区域犯罪预防计划,在全市犯罪高发区域建设22个邻里中心,协调教堂、学校、工会等社会资源,举办系列娱乐和培训活动;鼓励刑释人员参加社区活动,并建立其与雇主的联系[21]。20世纪60年代在紧张理论和反贫困运动的共同推动下,美国投入大量资金为贫穷阶层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以期减少犯罪。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克洛沃德和奥林提出的“通过增加机会预防和控制少年犯罪”启动了全美青少年动员计划,重点向青少年帮伙派遣工作人员、开展挑战自我和咖啡馆聚会等活动,并对问题家庭提供咨询和救助[22]。这些措施基本上属于福利服务性质。该时期犯罪社会学同矫正社会工作之间可谓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着美国矫正事业的发展。
犯罪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矫正社会工作实践的蓬勃开展,助长了该领域的一些学者的自满情绪。废除主义学派呼吁废除监狱乃至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用社会机构来代替,将刑事司法权归还社区[23]。社会防卫运动代表人物格拉马蒂卡指出,应废除报应主义刑罚,建立基于犯罪学研究、能够科学调节犯罪人欲望、对其再教育和再社会化的合理社会防卫措施体系[24]。 新社会防卫论的安塞尔淡化了废除刑法的激进思想,认为应将犯罪学和刑法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刑事司法活动受犯罪学的指导;立法、审判和矫正领域工作人员,都应该掌握犯罪学知识以科学地惩罚和矫正犯罪人[25]。这些流派乐观地认为,借助犯罪学研究成果和矫正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犯罪人能够得到有效矫正。当时一些共识也在形成,如矫正专业人员应该具备犯罪学、法学和社会工作的知识和技巧。
三、 犯罪学和矫正社会工作面临的质疑
犯罪学被视为将犯罪作为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探讨犯罪、预防犯罪和矫正规律的社会科学[26]。 但犯罪学流派众多,观点迥异,很多理论在相互批判和争辩中发展起来的,比如社会控制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潜在犯罪人员,遵从是由于各种社会联系的控制结果;而紧张理论和亚文化理论认为,人天生是社会性服从的,犯罪是由于恶劣的社会环境所致[27]。 那么,所有这些理论都是科学的吗,都能有效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吗?加拿大矫正学派批判指出:“犯罪学者对犯罪行为有很多话想说,但他们并没有给出经验上令人满意的解释”[14]36。 一方面,不同理论流派研究视角各异,其解释力往往限于一定的范围,并不能适用所有犯罪现象。另一方面,犯罪学研究方法也受到所在时代的限制。如龙勃罗梭通过颅骨和面相观察、身体测量和尸体解剖等方法即得出犯罪是因为返祖(atavism)和退化所致[28],即生来犯罪人理论(菲利帮助归纳提出);而现代犯罪体质学者发展到通过染色体和脑电波等科技手段进行验证[14]62-69。萨瑟兰最初同一名职业盗窃犯合作完成《职业盗窃犯》即提出不同交往理论[29],而当代犯罪学往往需要长年追踪研究或随机分组试验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有关犯罪原因的争论主要限于学术圈之内,然而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司法矫正实践的政策措施却会引起巨大震荡,甚至是司法气候的巨变。“二战”后由芝加哥学派、紧张理论、亚文化理论、标签理论和社会防卫运动所支撑的矫正社会工作大量参与的矫治恢复运动,在预防犯罪中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1960年—1975年间,美国暴力犯罪比例以三倍的速度激增,达到历史上最快增长速度[30]。紧随社会工作领域的“费舍尔旋风”,1974年罗伯特·马丁森针对“二战”以来的一千多项监狱和社区的恢复矫治项目进行重新检验,发现大部分不符合科学性有效标准,而且“无法得出清晰有效的矫正方法模式”[31],其结论被迅速标签为“什么也没起作用”(nothing works)。威尔逊大力抨击实证学派以来的矫正主义理论,认为虽然众多犯罪学研究解释了犯罪的原因,但其对策却无法落实,如贫穷是犯罪原因之一,但贫穷却长存于社会,犯罪将无法治理。因此,不需要太多探讨犯罪原因,惩罚和监禁即是最好的预防犯罪方法[32]。 由此,美国掀起了猛烈的反矫正运动,倡导复归惩罚和报应主义,史称新古典主义。更大的背景是,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方经济陷入滞胀,新保守主义抬头。决策者迅速制定“强硬”政策,将公共资源从矫正恢复转向监禁,社区矫正也需要严密监管[33]305。矫正社会工作则被批判为对罪犯太过仁慈,营造了一种饶恕文化,不具有专业有效性[34]。由此导致20世纪80年代社工大量撤离该领域,只有1.2%认为自己还在司法矫正领域工作[35]。可见,矫正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是时代留下的课题。
四、 北美循证矫正显示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美国严厉惩罚导向的司法气候,也未能达到有效威慑犯罪的效果,1976—1993年暴力犯罪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33]11。20世纪末美国进入监狱等矫正系统的人数达到1925—1973年平均水平的六倍多,矫正预算也相应增长了六倍[36]。社区矫正中的强化监管、电子监控或“训练营”等中间级惩罚项目,也未能有效降低犯罪率[37]。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促使犯罪学研究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深入探讨犯罪预防和罪犯矫正的有效方法。循证矫正运动应运而生。
循证矫正运动以北美为中心,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两个突出的学派——加拿大学派和马里兰学派。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学派率先提出了著名的“风险、需求、回应性”(RNR)三大原则(1)“风险原则”注重通过有效的评估,将矫正措施和犯罪人员的风险水平相结合,即高风险的矫正对象匹配较为密集的矫正措施,而风险较低的矫正对象则分配较少的介入;“需要原则”是指矫正措施需瞄准罪犯的犯因性需要,促进矫正对象转变;“回应性原则”强调矫正措施要回应案主个别化的性格、能力、学习方式、动机、性别和文化[14]178-182。和犯因性的“八大要素”(Central Eight)——犯罪史、倾向犯罪的态度、不良交往关系、反社会人格、家庭婚姻问题、工作学习状况、药物滥用和休闲娱乐[14]43-46,并基于这些发现相继开发了第三代、第四代犯罪风险评估问卷[14]176-182。马里兰大学对全美500多个犯罪预防项目进行了系统评估,1997年发表著名报告《预防犯罪: 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哪些有希望?》[38]。基于这个报告,美国国家矫正研究所(NIC)与犯罪和司法研究所(CJI)合作推动循证矫正实践,最终归纳出有效干预的八大原则——细致的风险评估、提升内部动机、瞄准介入、开展技巧培训、加大正强化、在原生社区提供持续支持、评估相关实践过程和提供评估反馈[39]。北美循证矫正运动对预防犯罪和罪犯矫正实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采纳循证矫正措施后,暴力犯罪率和财产犯罪率都一致性地明显趋于下降[33]11。加拿大矫正学派发现,全面遵循“RNR”三原则可以在社区矫正领域降低35%的再犯率,高于监所矫正的17%[40]。鉴于明显的矫正效果和专业领域影响,当前北美循证矫正措施已经被国际矫正领域广泛接受和采纳,包括我国香港地区。
仔细分析北美循证矫正提出的系列原则和因素,可以发现很多方面同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具有相通或兼容之处,为什么福利服务性矫正社会工作会失效呢?这里结合我国矫正社工福利服务模式实践进行探讨。
五、 我国矫正社会工作福利模式的内涵和挑战
只有厘清矫正社会工作福利模式的核心内涵和运行逻辑,才能深入理解其有效性面临的困境。在我国中级社工师考试教材中,矫正社会工作被界定为“从本质上讲是在司法体系中的社会福利服务,其服务对象是特殊社会困难群体——罪犯或违法者”[41]。其要义在于将困难群体救助的干预模式运用于违法犯罪人员,具体帮扶内容包括生活照料、经济支持、疾病医治、就学就业指导、心理辅导和家庭关系调适等方面。民政系统倡导的这套矫正社会工作福利服务模式,被上海模式较好地落实了。新世纪我国启动社区矫正之初,面对纷繁的国际经验,福利服务模式成为一种试点进路[42]。上海专门成立社会团体新航服务社,由其组织社工全面负责日常管理和帮扶工作,而司法行政人员仅少量协助[43]。新航服务社不断激励工作人员报考社工师,使其比例达到全国绝无仅有的86%(相较于深圳38.3%、北京9.9%、非一线省市平均5.4%)[44],希望以此提升矫正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实,“据司法部统计,2014年以前几年几乎每年上海模式社区矫正的重犯率都高居榜首”[45]。可见,专业证书并未转化为实际的矫正效果。
实践中,上海模式面临着四大挑战。首先是如何筛选重点介入的矫正对象?社工一般在日常管理中发现存在经济、疾病、就业就学困难的人员,然后协调相关救助措施和福利服务。但循证矫正检验发现贫困和阶层问题并不直接导致犯罪,而是通过更加微观具体的犯因性因素才能起作用,如性格、态度、家庭、交往、娱乐等方面[33]335-338。单纯的生活和工作困难标准就显得太粗犷,未能精准瞄准高风险分子。换言之,困难标准将导致不少再犯高风险分子未被识别而不加干预。其次,救助措施和福利服务能否有效矫正?在很大程度上,福利服务体现为一种微观身体治理技术,在国家代理人和帮教对象之间建立一种“施恩-回报”的感化关系[46]23-30。“施恩”即针对罪错人员也提供公共救助措施并通过社工柔性治理技术尽量解决个人困境,由此在法治之外添加一种道义上的类似福柯式的微观权力[47];“回报”即展现驯服的身体,配合完成司法管理制度,回归社会平均人状态。然而,这种治理术未必总能成功,如马里兰循证矫正学派发现,对26岁以下的矫正对象而言安置工作并不能有效降低再犯,关键在于其能否在就业中建立新的身份认同以及动机和认知的转变[33]106。此外,公共救助还难以避免帮教对象形成福利依赖甚至强行索要[48]。再次,如何应对不服从的案主?诚然,可以采取动机会谈策略同矫正对象有效沟通找到阻碍其服从的原因,并一起想办法克服障碍,进而达成一个可以遵守的矫正计划[49]。然而,总会遇上一些难以沟通的案主,尤其是教育水平不高的对象。有论者指出,对这类人员还需身体治理[46]3-4,通过国家权威代理人的身体在场构成威慑,督促服从[50]。在纯粹福利服务模式中往往缺乏机构权威,工作人员较少控制违规行为,导致矫正对象的一些小错没有被及时纠正,最终犯下严重的错误[51]。还有,在国家技术治理[52]日益深化的时代,如何平衡指标考核和矫正效果?费梅苹[53]和昆士兰大学的李恩深(Enshen Li)[54]分别在上海开展的社区矫正调查都发现,矫正社工大量时间忙于日常管理和目标考核,较少时间开展深入的专业矫正;大部分社工不具备认知行为矫正和家庭治疗技能,主要限于协助申请低保、联系就业和情绪疏导等。最后,如何面对司法系统的质疑?“国内矫正社会工作教科书很少涉及矫正实证研究成果,只是坚持社会工作意识形态(或专业价值伦理),反复言说个别化的助人自助、不批判、无条件接纳、关怀、尊重和支持等专业行话,让保守主义的司法矫正管制人员很难接受。在他们看来,社区服刑人员就是罪犯,怎么能无条件接纳和关怀呢?应该首先是惩罚,其次是改造,最后才是帮扶教育。”[55]法学权威期刊《中国法学》刊文直接将社工倡导的个别化矫治斥为“原教旨主义”,认为社区矫正应该按照“分类监控、规范矫治、正义修复”进行三重机能的先后排序[56]。在这种司法大气候下,上海司法系统最终进行了制度重构。劳教制度废止后,2014年专门设立了区级执行机构——社区矫正中心[57]以弥补监管和惩罚色彩的不足。由此,上海模式可谓被迫走上了福利服务和刑事司法的融合之路。
六、 我国循证矫正的本土化探索
随着循证矫正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我国也开始了本土性循证矫正探索,既有政府推动的司法循证措施,也有学界的循证研究。
地方政府启动的司法循证措施体现了浓厚的政绩创新色彩。2012年司法部时任副部长张苏军带队前往美国考察,然后提出要在罪犯矫正与戒毒领域开展“循证矫正”与“循证戒治”[58]。广州市[59]和苏州市[60]随即在社区矫正领域跟进。他们着眼于引进和运用北美的风险评估工具,将其本土化调整后运用于不同类别的矫正对象。苏州市建立循证社区矫正案例库的设想得到了不少法学学者的认可,包括标准案例库、矫正个案库和矫正专家库[61]。然而由于缺乏扎实的实证研究证据及理论支撑,这些数据库似乎是无本之木。而且,因政绩创新而启动,也因政绩创新而搁置,“我们现在的重心是规范化建设而不是循证矫正”(2018年,访谈其中某市负责人)。
华东理工大学社工团队在南通市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循证社区矫正项目。他们提出“适度循证”概念,致力于探索一种本土性社工专业自主的循证矫正范式,以克服碎片化操作[62]。这种思路仍然停留在矫正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范畴内,总体上并未走出福利服务范式,也未采取量化研究设计,因此其对循证矫正的宣传意义要大于实效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社工团队也开展了系列矫正社会工作循证研究。笔者基于全国十省市社区矫正问卷调查,通过数据检验发现综合了刑事司法和矫正社工两方面力量的深圳模式和当前上海模式的矫正效果优于仅强调刑罚执行的北京模式,而这三大典型模式均优于其他中西部省市的形式化应对模式[63]。此外,笔者还通过逻辑回归检验了西方犯罪学和循证矫正得出的八大要素、综合管理模式和一般紧张理论,基本上在本土层面验证了这些结论[44]。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并未采取循证矫正的最高标准——随机分组实验,也未就具体的干预方法进行检验。郭伟和将布迪厄和布洛维等学者的实践观点引入循证矫正的微观考察,由此将讨论推至一线实务场域。他对经验诠释的犯罪学理论和实证主义的循证矫正都进行了批判反思,认为二者都容易陷入经院学派构筑的理性主义认知行为僵化模式,提倡采取一种“扩展循证矫正模式”[58]。矫正社工需要把实证性知识和实践性策略相结合,既需要熟悉再犯风险的八大要素和RNR干预原则,这样才能建立风险评估框架,发现再犯风险点;也需要对生活实践、生命重要事件和介入时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基于北京的几个详实的社区矫正案例,他具体展示了如何将循证矫正知识“与当事人的生活习性和生活轨迹结合起来,跟随当事人日常生活中不断涌现的压力事件,协助其对自己的行为习性进行反省和自觉,重新选择新的应对模式,逐步改变生活模式,降低再犯风险”[64]。如此,矫正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和专业能力就不能停留在对实证性知识和社工模式套路的机械性掌握上,还必须具备对地方情境的洞察能力,以此协助矫正对象反省和觉识自己在生活处境中形成的“口是行非”的顽固行为习性,进而探索新的亲社会行动策略。
可见,近十年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无论从法学、社会工作还是综合学科视角,都对循证矫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都立足于提升罪错人员思想和行为矫正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政府对政绩创新的追求、法学对案例的偏好、社会工作对专业自主性的渴求,都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体现出不同的行动策略和分析视角,然而从矫正有效性这个终极目的而言,我们应采取一种综合学科视角。毕竟,罪犯矫正是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多学科的视域融合,理论探讨和实践知识、诠释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深入联系,才能推动对矫正社会规律和情境性实务智慧的更深入把握。
七、 结论与讨论
2020年我国《社区矫正法》正式实施,是我国社区矫正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对于矫正社会工作释放出巨大的制度参与空间。该法第11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根据需要,组织具有法律、教育、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知识或者实践经验的社会工作者开展社区矫正相关工作。”该法条显示出对矫正社会工作者综合具备刑事司法、心理教育、帮扶救助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而不是单纯的福利服务。该法出台后,法学界对矫正社工参与社区矫正表达了积极欢迎的态度,但也提出了帮教有效性的期待[65],希望综合推进“外控内矫”[56]。然而,法律话语表达与实践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鸿沟,我们需要“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66],由此建立矫正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矫正社会工作既要借重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和规范性,但更重要的是充分吸收犯罪学经过实证研究和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相较于刑事司法主要关注犯罪、刑罚及其执行的法律规定,犯罪学要向前向后延伸,是探究犯罪原因和犯罪现象规律、有效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的社会科学[16]。犯罪学属于综合性交叉学科,其学术发展史上荟聚了众多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形成大量经典学说;矫正社会工作参与其中讨论相对较晚,但却是最具社会实践应用性的专业和职业。循证矫正以量化统计检验的方式,得出了系列提升专业性和有效性的矫正干预原则和犯因性因素,这些结论也基本上在我国得到了验证。然而,加拿大循证矫正学派早就警示,不可将群集统计层面的量化规律机械套用在个体层面[14]33,情境性实践策略和一线矫正人员的实务经验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或许,这个在循证矫正学说体系中并不太起眼的一个提示,正预示着矫正社会工作专业性和有效性的发展进路。
《社区矫正法》将矫正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主要形式定位为购买服务(第四十条),但更合理的发展策略也许是在体制内设置综合型矫正社工岗位,公开招考专业人员或加强现有工作人员培训。由此使矫正社工兼具监管的权威性和矫正的专业有效性,或与法学背景人员组成工作团队,构成克罗卡斯所提出的综合管理模式。笔者已撰文讨论该模式,此不赘述。
——许春金先生
——张荆先生
——张荆先生
——张黎群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