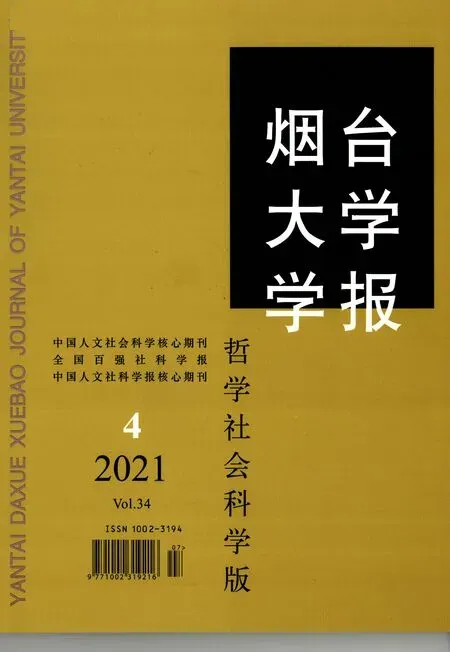皇权授受与政治忌讳
——从王禹偁贬谪事件看宋初政治生态
乐进进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王禹偁曾三遭贬黜,分别被贬商州、滁州、黄州,其原因则扑朔迷离。关于其贬谪事件的始末,学界已有所探究,但大多执着于事件本身,忽视政治生态对贬谪事件的根本性影响。(1)关于王禹偁的贬谪,已有如下主要成果:墨铸在《王禹偁三次谪官缘由》(《文史哲》1984年第5期)中分别就具体情境还原王禹偁三次被贬的缘由。王强《淳化二年王禹偁与道安事件初考》(《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细致分析了道安事件中各人所扮演的角色,把案件的判决归纳为太宗加强集权的表现,并提出这应当是王禹偁被贬的原因。实际上,在王禹偁的贬谪疑云中,潜藏着宋初特有的时代因素。由于史料就此问题的记载含糊不清,必须深入当时的政治生态,追踪王禹偁所处的微妙地位。
一、道安事件与宋初崇佛政策
太宗淳化二年(991),王禹偁初次被贬,《宋史·王禹偁传》对此记载简略:“未几,(王禹偁)判大理寺。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诏勿治。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2)《宋史》卷二百九十三《王禹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28册,第9794页。诸书所载大同小异,以《宋会要辑稿》最为详尽,并言及太宗与断案机构的龃龉处:“大理寺以铉之奸罪无实,刑部详覆,议与大理寺同。尼道安当反坐。帝疑其未实,尽捕三司官吏系狱,而有是命。”(3)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第8册,第4769页。原是太宗派遣大理寺处理这桩案件,当审查机关判定道安以诬告抵罪时,太宗或禁止穷治,或疑其未实,在王禹偁坚请治道安罪时,太宗反倒斩钉截铁地尽行贬黜王禹偁等人。就事件本身而言,王禹偁并无明显过错反惨遭贬黜,给后世留下许多疑团。据王强分析,此次贬谪一是由于王禹偁早先有罪,二是太宗借以整饬司法机构。(4)王强:《淳化二年王禹偁与道安事件初考》,《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整饬司法或可视作王禹偁被贬的间接因素,但王禹偁有罪的说法却不具备说服力,文中也未道出王禹偁所犯何罪,直言敢谏恐怕不能指作罪行。从道安的僧尼身份看,王禹偁被贬根源应当追溯至其排佛态度与太宗崇佛政策之间的强烈对抗。
宋朝太祖、太宗喜读书并重用儒臣治国,推行礼乐文化,但并不独尊儒术,而是推行儒释道兼重的政策。这源于太祖之皇位并不具备正当性,所以需要特定的理论为他进行鼓吹粉饰。佛教为迎合太祖,杜撰出“麻衣和尚谶言”和“定光佛出世谶言”,借以论证太祖黄袍加身的合法性,从而获得宋朝君主的青睐。“麻衣和尚谶言”见于《邵氏闻见录》:
河南节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为枢密使讨之。有麻衣道者,谓赵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气,守正安得久?”未几,城破。……三天子气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艺祖同在军中也。麻衣道者其异人乎?(5)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68-69页。
此段论述象征着太祖即天子位出于上天垂示,非人力所致。“定光佛出世谶言”当时也流传甚广:“有一僧……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6)朱弁:《曲洧旧闻》卷一,孔凡礼点校:《师友谈记 曲洧旧闻 耆旧续闻》,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第85-86页。此则谶言将太祖说成是定光佛的化身,因而要以佛的形式来统治人世。(7)关于支撑宋太祖即位的佛教谶言,以此二则最具代表性,但仍有许多相关的谶言,此处不赘。参见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12-39页。两种谶言都极力将太祖塑造成真命天子的形象,并且深入人心。所以,太祖积极保护和弘扬佛教,正是为他的皇位合法性造势。因此,排斥佛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宋朝统治合法性的否定。
太祖即位始便改善佛教的生存处境,下令“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辛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标点本,第1册,第17页。,又大量新建或重修寺院,如建隆寺、开宝寺等。太祖执政期间,官方主持刊刻《大藏经》,尤为弘扬佛教的表征。其时的李霭事件也是太祖护佛的显证:“河南府进士李霭造《灭邪集》以毁释教,窃藏经以为衾。事闻,上以为非毁圣道,诳惑百姓,敕刺流沙门岛。”(9)释志磐著,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四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点校本,第1020页。李霭仅因言论就被远远流放沙门岛,可见排佛在宋初成为政治忌讳已然确凿无疑。
宋太宗弘扬佛教较之太祖有过之而无不及,先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建成译经院,命高僧译经,又置印经院加以刊刻。太宗甚至自撰《新译三藏圣教序》冠于所刊佛经,褒扬佛教意旨。宋初童人剃度须经过官方考试,太宗则时常特恩允许童人剃度:“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眷言求度之人,颇限有司之制。俾申素愿,式表殊恩。应先系籍童行长发,并特许剃度,今勿以为例。”(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己丑,第1册,第527页。太宗还曾鼓励大臣们研读佛书:“浮屠氏之教有禆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十月甲申,第1册,第554页。有鉴于此,太宗绝不允许有人肆意诋毁佛教,违拗其执政策略,《玉壶清话》载有相关轶事:
开宝塔成,欲撰记。太宗谓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国来,表述本国有金刚坐,乃释迦成道时所踞之坐,求立碑坐侧。朕令苏易简撰文赐之,中有鄙佛为夷人之语,朕甚不喜,词臣中独不见朱昂有讥佛之迹。”因诏公撰之。文既成,敦崇严重,太宗深加叹奖。(12)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二,郑世刚、杨立扬点校:《湘山野录 续录 玉壶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13页。
太宗尤为重视佛教,以至听到对佛教稍带贬义性的称呼即怒形于色。可见排佛的政治忌讳从太祖到太宗一脉相承。据闫孟祥等考证:“宋太宗在世时,已被称其‘前世’在释迦牟尼前得授记弘传佛教。这一说法不仅在当时的佛教中已相当流行,在世俗中也有一定流传。对此,太宗自己也予认可。”(13)闫孟祥、李清章:《宋太宗“受佛记”传说考》,《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二、儒家本位与排佛争端
王禹偁自幼服膺儒家经典,奉圣贤言行为圭臬,如其自述:“予自幼服儒教,味经术,尝不喜法家流,少恩而深刻。……呜呼!古今之不同也如是,遂使圣人之言为空文尔。欲望刑措,其可得乎?”(14)王禹偁:《用刑论》,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百五十五,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标点本,第8册,第39页。其平生志业始终以致君行道自期,因而在商州回顾少时的人生憧憬时,屡次言及“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15)王禹偁:《吾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五十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标点本,第2册,第658页。,而其效法对象显然不离儒家圣贤,所谓“步骤依班马,根源法孔姬”(16)王禹偁:《谪居感事》,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六十四,第2册,第709页。。仅从他早年所存的少部分诗中,便能看出他的胸怀所在,其言“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17)王禹偁:《对酒吟》,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六十九,第2册,第786页。,意即位势得当便能以儒道济世安民。因而他的道终究是儒家仁义之道,将行己有道与治国安邦视为同一轨辙,所以他对权位的追求也不加掩饰:“穷达君虽了,沉沦我亦伤。何当升大用,吾道始辉光。”(18)王禹偁:《寄主客安员外十韵》,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六十三,第2册,第698页。王禹偁出身贫寒,回忆少时生活屡用“乞丐”一词,自小经受的下层生活困苦赋予其浓厚的民本思想。因此,当有蠹虫蚕食国家时,王禹偁不遗余力抨击。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佛教可谓首当其冲。
宋初的政治倾向是崇佛,王禹偁却毫无顾忌地排佛,二者的矛盾正是王禹偁初次谪官的根源。在早年游历生活中,王禹偁并无强烈的排佛意识,担任长洲知县后,他将排佛思想付诸诗歌。其中《酬处才上人》抨击佛教最为淋漓尽致:
我闻三代淳且质,华人熙熙谁信佛。茹蔬剃发在西戎,胡法不敢干华风。周家子孙何不肖,奢淫惛乱隳王道。秦皇汉帝又杂霸,只以威刑取天下。苍生哀苦不自知,从此中国思蛮夷。无端更作金人梦,万里迎来万民重。为君为相犹归依,嗤嗤聋俗谁敢非。若教都似周公时,生民岂肯须披缁。可怜嗷嗷避征役,半入金田不耕织。(19)王禹偁:《酬处才上人》,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六十八,第2册,第781-782页。
全诗叙述佛教本是从蛮夷舶来,若在三代淳质之时完全不可能蓬勃发展。现在却由君相推崇,致使万民景仰,无人敢指出佛教不劳而获、蠹害国家的本质。王禹偁无所顾忌地贬斥佛教,可谓振聋发聩。当他被征召入京,便先后奏上《端拱箴》《三谏书序》《御戎十策》,这三封奏折内均有限制佛教发展的建议。其中尤以《御戎十策》所论鞭辟入里,内中谏云:“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观,劝风俗,务田农,则人力强,而边用实也。若军运劳于外,游惰耗于内,人力日削,边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灾,则寇不在外而在乎内也。”(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太宗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第2册,第674-675页。王禹偁极力抵触佛教特权,由此埋下日后遭受贬黜的祸根。他在《答郑褒书》中回忆初次被贬经历时写道:
天下举人日以文凑吾门,其中杰出群萃者,得富春孙何、济阳丁谓而已。吾尝以其文夸大于宰执公卿间。有业荒而行悖者,既疾孙何、丁谓之才,又忿吾之无曲誉也,聚而造谤焉。以吾平居议论,常道浮图之蠹人者,乃殆为吾《沙汰释氏疏》,盛于髡褐之徒。又云孙何著论以无佛,京城巨僧,侧目尤甚。未几,吾坐事贬官商洛,谤者得志,喉如响而舌益滑也。(21)王禹偁:《答郑褒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百五十,第7册,第393页。
那些业荒行悖的人之所以诽谤得成,全在于他们获得崇佛政治的支持。
太宗既推崇佛教,自不能容许诋毁佛教的言论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就好比当时李蔼著《灭邪论》,不可避免地被太祖流放一样,传为王禹偁所作的《沙汰释氏疏》自然会引致太宗的反感。正因佛教宣扬宋朝皇权正当性,苏易简贬佛为夷已遭到太宗厌恶,排佛是政治忌讳不言而喻,道安事件正好也涉及这种忌讳。与其说王禹偁被贬由道安事件所致,不如视之为导火索更合情理。正如《答郑褒书》中所述,王禹偁自身对于排佛后果亦有清醒认知。太宗虽爱重王禹偁的才华,但在崇佛政策上无丝毫让步。王禹偁竭力排佛,更有作《沙汰释氏疏》之传闻,此时力主治道安罪,太宗为息事宁人、以儆效尤,便将王禹偁等人贬黜出京,确在情理之中。日后太宗把王禹偁从解州召还汴京时,仍对宰相嘱咐道:“禹偁文章,独步当世,然赋性刚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2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太宗淳化四年八月己卯,第2册,第752页。所谓“不能容物”,即不能容忍佛教的存世。王禹偁被贬后只意识到自身生性刚直,却未曾发现已然触犯了宋朝统治者的忌讳,所以在诗文中仍只反省“刚肠”:“归见鳌头如借问,为言枨也减刚肠。”(23)王禹偁:《送江州孙膳部归阙兼寄承旨侍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六十七,第2册,第761页。他于《谢除翰林学士启》中提及“用直道以事君,虽无改变;肆刚肠而疾恶,渐亦销磨”,(24)王禹偁:《谢除翰林学士启》,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百五十一,第7册,第406页。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赋性刚直”,而是触及当时的政治忌讳。道安事件发生时,正处于王禹偁的排佛思想引发热议的时候,太宗想借此申明排佛是不可触碰的政治忌讳,也为给所谓的“巨僧”一个交代,所以径直将王禹偁贬逐商州。由此可见,一旦将此事件置于宋初的政治生态中,王禹偁被贬的疑团纠葛便能迎刃而解。
三、开宝皇后事件与继位疑云
王禹偁的第二次贬谪细节仍旧含混不清,而事件发生时太宗的反应更值得玩味。《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记载:“开宝皇后之丧,群臣不成服,禹偁与宾友言:‘后尝母天下,当遵用旧礼。’或以告,上不悦。甲寅,禹偁坐轻肆,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上谓宰相曰:‘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勗禹偁,令自修饬。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2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七,太宗至道元年五月甲寅,第2册,第813页。王禹偁仅对丧礼仪节发表私见,并非在朝堂上公然谏诤,本不应掀起轩然大波。有人将其语转达给太宗,太宗显然为此勃然大怒,不惜重贬王禹偁,直至太宗逝世仍未将其召回朝廷,这在崇儒右文的宋代无疑极为反常,更遑论太宗对王禹偁赏识有加。之所以会如此,就必须从开宝皇后(即太祖宋皇后)所处的政治地位入手,探讨太宗何以对此事备加关切。开宝皇后实则牵涉到太宗继位的合法性问题,因而太宗对此不容有半分差谬。太祖、太宗间的传位问题,由于史乘不明而众说纷纭。《长编》引述各家笔记的说法,莫衷一是。司马光撰《涑水记闻》详述开宝皇后与太宗间的关系:
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邪?”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26)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标点本,第18-19页。
开宝皇后原先计定太祖之子德芳入继大统,见到当时尚为晋王的太宗不由愕然。事出急促并且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认可太宗即位。在皇位的继承角逐中,可见开宝皇后与太宗势如水火。有这样的历史之背景,太宗对她必然有所顾忌。
另就关涉皇位继承的金匮之盟而言,它本身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可以确定的是,太宗本人必须依赖于金匮之盟的说法,以此建立自己继承皇权的合法性。所以在太宗朝,金匮之盟是朝野上下统一承认的事实,对于任何有关继位合法性问题的议论都属于政治忌讳。关于金匮之盟的记载颇多,虽然有所出入,但盟誓内容大致类似(惟《新录》所载的杜太后遗命说止于太宗,辨析详见下文)。《长编》载金匮之盟为:“始太祖传位于上(太宗),昭宪顾命也。或曰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上复传之廷美,而廷美将复传之德昭。”(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第1册,第501页。如果依据金匮之盟的本意,兄终弟及的观念必须延续下去,并将皇位归还太祖子孙。太宗既要坚守金匮之盟的正当性,又不想把皇位还归太祖子孙,一劳永逸的手段就是铲除既定的皇位继承人,以便自己子孙顺理成章地继位,故而《长编》复载:“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谋。他日,上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于是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2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第1册,第501页。就史乘所载,德昭、德芳、廷美相继离世,均难说是正常现象。而“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之语,正是赵普提醒太宗莫让历史重演,这尤能证实太宗皇位继承正当性的阙失。若依据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的推断,太宗继承皇位纯为弒君逆取,(29)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5-502页。故太宗不仅需要制造金匮之盟的舆论,还必须时刻防范开宝皇后及太祖二子的反扑,令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局面。这就要求大臣们在皇权授受问题上必须立场鲜明,太宗对此的警惕性于德昭事件中显露无疑:
初,武功郡王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或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其事,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谓不可,于是德昭乘间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3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八月甲戌,第1册,第460页。
徳昭作为太祖嫡长子,本应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却只能屈居郡王之位,太宗必然对其满怀戒备。当有人谋立德昭时,即便是无果而终,太宗仍旧耿耿于怀。尤其当德昭涉嫌拉拢人心,为出征将士求赏时,太宗怒不可遏地出面制止,致事态进一步恶化。史载德昭因此事羞赧自尽,关于其死因一向异说并行,但太宗无疑与徳昭之死不能撇清关系。
开宝皇后的处境极为微妙,她虽非皇位继承人,却始终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太宗既剥夺她应得的太后地位,太祖子嗣又都无疾而终。开宝皇后一死,象征着太祖一脉涉及继位的候选人物死亡殆尽,再不能对太宗皇权造成威胁,这就预示着太宗继位问题已画上休止符。太宗当务之急是从朝堂中彻底消除皇位继承事件之影响,稳固自身合法性,群臣不为开宝皇后成服正是他想看到的。同时,太宗反感大臣们向太祖一脉靠拢,也在朝野中逐渐成为共识。王禹偁的私下提议无疑是对当时政治忌讳的公开挑战,试想如果以皇后的规格举行丧礼,难免会相继触发对于开宝皇后所代表的太祖子孙继位问题的探讨。可以想见,太宗无论如何都不愿让此意外情况发生。因此,太宗听到王禹偁私下言论后的勃然大怒纯然出于政治考虑,而非儒家仪节的优劣问题。同时,太宗应当也想通过对王禹偁的贬黜,来明确皇权授受问题是不得触碰的政治忌讳。
四、《太祖实录》事件与《建隆遗事》
王禹偁第三次被贬发生在真宗朝,身为两朝元老,却因含糊的罪名远谪黄州,似超出忍耐极限,他在《出守黄州上史馆相公》诗中质问:“未甘便葬江鱼腹,敢向台阶请罪名。”(31)王禹偁:《出守黄州上史馆相公》,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七十,第2册,第801页。
要探知王禹偁再次被贬的缘由,先须考察他此次被贬之文献记录,《长编》记载:“刑部郎中、知制诰王禹偁预修《太祖实录》,或言禹偁以私意轻重其间,甲寅,落职知黄州。”(3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三,真宗咸平元年十二月甲寅,第2册,第923页。关于此事,当时散布着大量相关轶闻,李焘多已辨证其误。(3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三,真宗咸平元年十二月甲寅,第2册,第923页。可见“以私意轻重其间”意味含混不清,以致激发众人悬想。史籍中并未阐明如何“轻重其间”,因此,必须就《太祖实录》编纂的来龙去脉探讨王禹偁何以触怒真宗。究其本质,王禹偁仍是触及了当时的政治忌讳。《太祖实录》经由四次编修,成书三回。(34)参见谢贵安:《宋实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31页。初始纂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以沈伦监修,后世称所成书作《旧录》或《前录》,此次成书未合圣意:“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多有漏略。”(3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五,太宗淳化五年四月癸未,第2册,第777页。淳化五年(994)太宗下诏重修此书,然无果而终。真宗于咸平元年(998)下令再度编修《太祖实录》,以李沆监修,钱若水等具体编纂,王禹偁参与其中,此回成书即为《新录》。大中祥符九年(1016)真宗又一次诏修《太祖实录》,主要为了弥合与《两朝国史》叙事不合之处。《太祖实录》各本均已亡佚,就《长编》对前后所修实录的引述来看,《新录》对《旧录》多所删订修补,尤其增添了许多有利于太宗继位合法性的记载,如杜太后临终遗命说便由《新录》所增补。(3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第1册,第46-47页。这间接表明了太宗为何汲汲于反复修撰《太祖实录》。换言之,太宗是在为自身继位合法性增强论据,与太宗广集群力修撰宋初大型类书的意图如出一辙。(37)关于太宗修撰宋初四大书的原因,参见巩本栋:《宋初四大书编纂原因和宗旨新勘》,《文艺研究》2016年第4期。那么,所谓“禹偁以私意轻重其间”当是与太宗、真宗的编纂目的相左,因此才会触怒真宗。
《建隆遗事》的作者著录为王禹偁,自南宋以降就不乏学者就此书作者及内容真伪提出异议。李焘曾考辨《建隆遗事》真伪混淆,尤与官修史书龃龉,书中前后矛盾之处多是他人“托名禹偁,窜寄《遗事》中,实非禹偁作也”(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太祖开宝九年十月壬子,第1册,第380页。。此外,晁公武、王明清等人也相继辩驳其然否。(39)晁公武称“世多以其所记为然,恐不足信也”。见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六《建隆遗事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点校本,上册,第262页。王明清则以之与国史所载以及王禹偁生平事迹相悖,认定“其间帅多诬谤之词。……特人托名为之”。见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标点本,第30页。今人顾宏义力主此书为王禹偁所作,并就前人论断逐一罗举。(40)关于《建隆遗事》是否为王禹偁所作的辨析,参见顾宏义:《王禹偁〈建隆遗事〉考——兼论宋初“金匮之盟”的真伪》,《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此书著者实难定论,这里不对王禹偁托名与否进行论证,但就晁公武所说,《建隆遗事》作于淳化年间,(41)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六《太祖实录五十卷》,上册,第226页。然而在王禹偁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均无人辨明其伪,可证此书在当时并未受到质疑。那么,即便《建隆遗事》并非王禹偁所作,至少书中所载事件或言论与王禹偁日常言论乃至政治观点应当极为接近。如同有人伪作《沙汰释氏论》,因为与王禹偁的排佛观点相近,时人均确信为其所撰。《建隆遗事》的情况与此相似,所以王禹偁为此书著者的说法才得以广为流传。
《建隆遗事》已佚,从《长编》及笔记中可辑得数则。其中与太宗继位相关的记载分作两类:一是太宗是否参与陈桥驿事变?二是金匮之盟是否要求太宗日后传位廷美?关于陈桥驿事变,《邵氏闻见录》转引《建隆遗事》曰:
上初自陈桥即帝位,进兵入城。人先报曰:“点检已作天子归矣。”时后寝未兴,闻报,安卧不答,晋王辈皆惊跃奔走出迎。(42)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第65页。
从中可见太宗未随太祖出征,陈桥驿事变实则与太宗毫无瓜葛。然而《长编》言太宗身在陈桥驿军中,先是查知军中异动,复与赵普晓譬诸将,其记载十分详实:“或以黄袍加太祖身,且罗拜庭下称万岁。太祖固拒之,众不可,遂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原注:《旧录》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太祖度不得免,乃揽辔誓诸将。”(4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正月癸卯,第1册,第3页。从李焘自注可知,关于太宗身处陈桥驿中的记载均由《新录》添加,而这直接关乎太宗对于宋朝开国是否起到关键作用。毕竟太宗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说法,可让太祖自愿传位给太宗的舆论更具说服力。但《建隆遗事》明言太宗不在场,那就意味着王禹偁完全有可能熟知此事,以他“刚强”的禀性,应当不会在《新录》中杜撰此类桥段。这就显然触犯了当时的政治忌讳,即上文所谈的皇位继承合法性问题,甚至可能导致重新编修的《太祖实录》背离原定宗旨。如果此推论成立,那么真宗斥逐王禹偁也就合情合理。
金匮之盟本就富有传奇性,《长编》尝引述《建隆遗事》相关记载:
上白太后曰:“臣百年后传位于晋王,令晋王百年后传位于秦王。”后大喜曰:“吾久有此意而不欲言之,吾欲万世之下闻一妇人生三天子,不谓天生孝子成吾之志。”令晋王、秦王起谢之。既而后谓二王曰:“……吾不知秦王百年后将付何人?”秦王曰:“愿立南阳王德昭。”……遂诏陶榖为文。别日,令普告天地宗庙,而以誓书宣付晋王收之。(4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第1册,第501页。
金匮之盟对于真宗实属历史遗留问题,如果按照约定,太宗日后应将皇位传给秦王廷美,嗣后归还太祖之子德昭。果真如此执行,真宗便全然失去继位的合法性。因此新修《太祖实录》也是真宗获得皇位合法性的关键手段。关于金匮之盟,李焘谈及《旧录》无记载,但《新录》却添有杜太后遗命说:“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上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藏其书金匮。”(4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第1册,第46页。本应将皇位归还给太祖子孙的金匮之盟,彻底被《新录》的杜太后遗命说取代。《新录》删除秩序谨严的传位流程,所谓的盟约到太宗戛然而止,政权从太祖一脉彻底转到太宗一脉,真宗也由此获得继位合法性。在太宗朝,廷美、德昭、德芳相继非正常死亡,金匮之盟本身早已失去后半部分的有效性。所以真宗为了自身的皇位正统考虑,最宜沿袭太宗的策略,将金匮之盟事件彻底改造,打消众人对于德昭等人死亡的疑虑。王禹偁作为两朝元老,对金匮之盟的盟约自然十分熟识,《建隆遗事》中的叙述理当与其差相仿佛。因此,在预修《太祖实录》时,王禹偁对大张旗鼓的改动必然有所辩驳,甚至要依照史实秉笔直书。出知黄州后,王禹偁曾在谢表中就此事自我辩解:“自后忝预史臣,同修《实录》,……虽然未经进御,自谓小有可观。忽坐流言,不容绝笔。”(46)王禹偁:《黄州谢上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百四十六,第7册,第318页。所谓“不容绝笔”,当是王禹偁的史笔触及统治者逆鳞。一旦有人将此“私意”转达给真宗,王禹偁的贬逐便势所难免。
总而言之,宋初皇位交接的混沌不明,致使皇权承继者为维护自身合法统治地位实施系列举措以控制舆论。王禹偁再三遭受贬黜,原因看似扑朔迷离,实则均触犯统治者的权位禁忌。儒释道三教并崇是宋初国策,而佛教适时地制造赵宋君权神授的舆论,无疑为宋代政权的合法性建立打下深厚的民间基础,篡位所带来的节义缺失借此得以弥补,因此宋初君权确立势必与排佛主张相对立。太宗继位事件的不正当性,直接促成皇位授受问题的政治忌讳,朝臣必须希旨行事,极尽所能地为太宗的皇权合法性添砖加瓦,堙埋一些不利的历史真相势在必行,而试图秉笔直书无疑会走向皇权的对立面。至真宗朝,真宗必须将前朝遗留的皇权转授链条止于太宗,方能确保自身获取父死子继的皇权合法性。因此,宋初三朝的政治忌讳看似各有侧重,实则均与皇权授受问题密不可分,王禹偁的屡次贬谪恰好折射出宋初政治生态的隐藏法则。由此可知,宋代虽然是一个崇儒右文的王朝,但是宋初的皇权始终以一种警惕的姿态关注着士大夫的言论和行为,这是研究宋初士大夫政治生活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