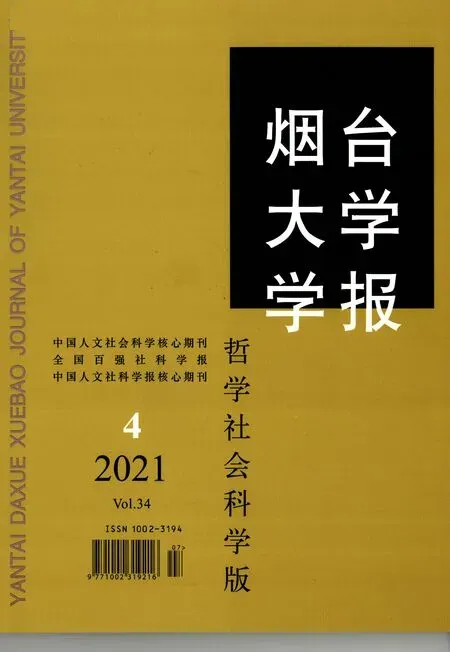清朝皇帝的“元朝观”
邓 涛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元朝和清朝都是兴起于中原之外统一中原和北方游牧区域的大一统王朝,两个王朝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清朝实行满蒙联合,清朝对元朝的认知又多了清代蒙古人这一因素,这为研究清朝皇帝的“元朝观”提供了比较独特的视角。关于清朝皇帝对元朝的看法及其对元朝历史的借鉴,以往有些研究已经涉及,(1)孙静认为,乾隆帝“引用元世祖开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之先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中华正统理论”。见孙静:《“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99页。亦有文章在论及明清两朝帝王庙祭祀时,提到清朝皇帝对元世祖的增祀及对元朝正统地位的确认。见黄爱平:《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邓涛:《明清帝王民族观和历史观的异同——从历代帝王庙帝王祭祀角度出发》,《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但尚无专文论述。通过研究清朝皇帝的“元朝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清朝皇帝对中国古代非汉政权(2)此处的“非汉政权”是指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权及中国古代区域政权。的认识,并从中窥知清朝皇帝的民族观和历史观,进而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过程。
一、清朝统一明朝疆域和蒙古地区
元朝上承宋朝,下启明朝,是继唐朝之后又一个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元朝统一西夏、金朝等地,结束了北方的分裂局面;统一大理和南宋等地,实现了南方的统一,最终实现了南北的统一、中原同北方游牧地带的混一。元明鼎革之后,明朝却未能统一蒙古高原,北元政权在一段时间内同明朝并立,后来,北元政权逐步演变成为明人眼中的鞑靼部。鞑靼部之西为明人眼中的蒙古瓦剌部,瓦剌部是同鞑靼部并立的政治力量。明天启年间,黄金家族嫡系大汗察哈尔“林丹汗士马强盛,横行漠南”(3)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一》,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标点本,第94页。,其试图统一漠南蒙古的举动,引起了部分蒙古封建主的恐慌,进而使得他们选择联合后金以自保。此后,后金率领满蒙联军征讨林丹汗,林丹汗败逃,后金得以控制漠南蒙古大部。崇祯七年(1634),穷途末路的林丹汗病死。次年,苏泰太后携林丹汗子额哲率领余部投降后金,后金以此得到“历代传国玉玺”,并基本统一了漠南蒙古地区。崇祯九年(1636)四月,皇太极接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改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清朝1644年入关之后,采取多种方式先后统一了边疆地区,实现了大一统。到康熙朝中叶,漠北蒙古(喀尔喀)内争,噶尔丹乘机干涉,并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攻入漠北蒙古,漠北蒙古“三部落数十万众瓦解,先后东奔”(4)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二》,第101页。,逃入漠南蒙古。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组织漠南、漠北蒙古在多伦诺尔会盟,决定在漠北蒙古实行盟旗制度,确立了对漠北蒙古的统治。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封青海蒙古诸部首领为亲王、贝勒或贝子,标志着清朝开始正式统治青海蒙古。此外,位于河套以西的阿拉善蒙古亦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正式归附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在漠西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引导下,清军发起了对漠西蒙古的统一战争,达瓦齐战败。此后又发生阿睦尔撒纳反清事件和漠北蒙古的“撤驿之变”,“绰罗斯特、辉特二部及哈萨克先叛,都统和起被诱歼焉。阿逆闻四部构乱,亦自哈萨克归,会诸贼于博罗搭拉河,欲自立为汗,准部复大扰乱”。(5)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第150页。乾隆帝再次调兵遣将,支援新疆清军并平定了叛乱,兵败的阿睦尔撒纳逃至俄国后病死。至此,明朝时的鞑靼和瓦剌故地基本为清朝所统一。
二、清朝确立元朝的正统地位
清朝和元朝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进而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清朝皇帝对元朝正统性的重视和维护,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清朝和元朝皆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认可元朝有助于彰显清朝入主中原的正统性。二是在清代满蒙联合的大背景下,清朝有替清代蒙古人维护元朝正统的义务和必要。三是清朝君臣对中原正统观的认识和继承,如天聪九年(1635),后金降服漠南蒙古察哈尔余部获得了“历代传国玉玺”后,多尔衮认为:“皇上洪福非常,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6)李澍田主编:《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标点本,第494页。清朝在获得此玺之后,亦十分爱惜,正如雍正帝所言:“当日元顺帝将此玺携归沙漠,是以明代求之未获,我太宗文皇帝,天聪九年察哈尔林丹汗之母将此宝进献,至今藏于大内。”(7)《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九,雍正七年十二月丁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册,第206页。清朝对元朝正统及形象的维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帝王庙祭祀体系中恢复元朝之正统地位。清朝入关之后,对元朝正统的确认,首先体现在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之中。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其在帝王庙内祭祀元世祖,都有基于正统性的考虑。明朝祭祀元世祖是彰显对元朝正统性的继承,即“洪武之去辽金而祀元世祖,犹有一统帝系之公”(8)《清朝通典》卷四十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2323页。。清朝在帝王庙内恢复元世祖祭祀,亦有正统性的考量。
历代帝王庙创立于明初,改建于明中叶,清朝承袭了明朝的帝王庙祭祀体系,体现了清朝对中原文化的认可和接纳。虽然宋、金、元等朝代都曾祭祀过中国古代的贤君,但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合祀。小规模的合祀,其范围多限于三皇五帝,祭祀地点多为他们的故乡,祭祀主体是地方官府。洪武朝时,归附明朝的蒙古人答禄与权上疏,建议在京师合祀三皇且由皇帝亲祀。明太祖认可该提议,决定建立帝王庙并扩大祭祀范围,“帝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9)《明史》卷五十《礼四·历代帝王陵庙》,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册,第1292页。按照该条件,洪武十年(1377)入祀帝王庙的古代皇帝或部落首领有太昊伏羲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帝、隋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等十七人,元世祖此时亦入庙受祀。嘉靖朝时,嘉靖帝将历代帝王庙迁至北京。彼时,明蒙关系紧张,漠南蒙古俺答汗曾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率军围困明朝京师(即“庚戌之变”)。由于明蒙双方处于激烈的对峙当中,故明朝君臣迁怒于元朝,将元世祖忽必烈牌位从帝王庙中撤出,“世宗朝大虏频犯内地,上愤怒……帝王庙削元世祖之祀”。(1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四《祀典》,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84页。
清朝在入关之初,便有以中华正统自居的决心和姿态,在帝王庙的祭祀上体现了对正统性的关注。顺治元年(1644)六月,清朝刚刚定鼎北京,即“以故明太祖神牌入历代帝王庙”(11)铁玉钦主编:《清实录教育科学文化史料辑要》,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标点本,第744页。,这一举动向各方传达了明朝已经灭亡的政治意涵,同时也标志着清朝对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的继承,而非废除该祭祀体系。顺治二年,清朝着手恢复元世祖在帝王庙中的地位。当年三月,礼部上奏提到:“当日宋之天下,辽金分统南北之天下也,今帝王庙祀,似不得独遗。”(12)《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三月甲申条,第3册,第130页。清朝在恢复对元世祖祭祀的同时,增加了辽金等非汉政权的皇帝,帝王庙中少数民族属性日益增强。此后康熙至雍正朝时,帝王庙内又新增了北魏等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所建立政权的皇帝,体现了清朝皇帝对中国古代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一视同仁的姿态。
清朝皇帝除了在历代帝王庙内祭祀元世祖,还有“望祭”元帝陵寝之礼。顺治八年(1651),“致祭历代帝王典礼,有望祭元太祖、元世祖陵在宛平县北……”(13)黄彭年:《畿辅通志》卷四《帝制纪·诏谕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标点本,第259页。嘉庆时,望祭元帝陵寝之礼改在清河以北、昌平州以南的宛平县界内进行。
二是辨正统以确立元朝的历史地位。关于唐宋以来的王朝正统,元明清三朝君臣有不同看法。元朝是分修宋、辽、金三史以避免独尊两宋摈斥辽金,而明朝虽尊崇宋朝,但亦在正统上强调对元朝的继承。到了清朝,清朝皇帝不仅需要面对由女真人所建立金朝的正统问题,亦需要面对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元朝的正统问题。
元末明初人杨维桢所著《正统辨》一书认为,元朝继承了宋朝的正统,而非辽金的正统。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发现四库全书馆馆臣在录入该书时,删除了一些原文。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帝针对此事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正统辨》以元继南宋正统的观点是公正的,原因便是南宋虽然称臣于金朝,但其继承了北宋的正统,故辽金不能取代南宋的正统性,“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14)赵之恒等编:《大清十朝圣训》,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标点本,第1332页。乾隆帝认为,虽然辽金统治北方,但正统依然属于两宋,故元朝灭亡南宋,是继承了正统。彼时阁臣删除《正统辨》原文,乾隆帝亦知原因:“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15)赵之恒等编:《大清十朝圣训》,第1332页。部分馆臣认为,金朝和清朝有一定的族源关系,故偏袒金朝,删除《正统辨》原文。在乾隆帝看来,由宋至元为正统,既对元朝的正统性予以确认,亦彰显了宋、元、明、清四朝正统的一脉相承。此后,乾隆帝命四库全书馆馆臣增补了该文。即便是到清后期,清朝皇帝也依然将元朝视为正统,如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道光帝在策试中提到“唐之《律令格式》,宋之《刑统》,元之《至元新格》、《大元通制》,明之《大明律令》,其轻其重,其沿其革……毋有所隐,朕将亲览”(16)王炜编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标点本,第764页。,将唐、宋、元、明视为正统,反映了清朝统治阶级的主流正统观。
三是校核涉及元朝历史的史书。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清朝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既对涉及后金和清朝历史的书籍进行删改,又对辽、金、元三朝史书进行校核。乾隆帝命校核辽、金、元三朝书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满洲人先祖金朝女真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亦是为了给元朝正名,替清代蒙古人维护元朝的形象。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帝下谕,提到《元史》编修存在的问题,“以汉字译蒙古文,间有语音不合处……污蔑蒙古之语,亦不一而足,不可不为之湔雪”。(17)《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五十四,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丙午条,第18册,第300页。乾隆帝命校正和修改《元史》,一方面认为其音译不准,另一方面则是认为文中多有贬低蒙古和元朝之处。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认为《通鉴辑览》中亦有涉及元朝和蒙古的不当用词,“见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尤为鄙陋可笑”,(18)李澍田主编:《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第332页。认为该书对辽、金、元三朝的评论并不公允,在人名翻译上有歧视倾向。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订正《通鉴纲目续编》时,乾隆帝批评了《发明》《广义》二作的“华夷观”,并以编纂《通鉴辑览》为例,提到“司马光、朱子义例森严,亦不过欲辨明正统,未有肆行嫚骂者”(19)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标点本,第1675页。。乾隆帝认为,《发明》《广义》二作对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刻意诋毁,是偏狭之见。清朝皇帝在史书中如此维护元朝的形象,既是为元朝正名,也是在为自己正名。
三、清朝对元朝历史遗产的借鉴
清朝和元朝的创立者都是少数民族,二者在国家治理上面临一些相似的情境,故清朝在治国理政中不时借鉴元朝,如乾隆帝十分重视学习辽、金、元三朝历史,认为“关系前代治乱兴衰之迹”(20)于敏中:《国朝宫史正续编》卷八十九《史学二》,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2512页。。
(一)以元朝的弊政为警示
一是以元朝灭亡警示族人。努尔哈赤十分重视辽、金、元三史的资治作用,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谕诸贝勒:“元顺帝不畏天威,不治国政,疏斥贤能,信任奸慝,致盗贼蜂起,国祚遂亡……今明之君臣,自恃强大,蔑视上帝……”(21)李澍田主编:《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第101页。彼时,努尔哈赤以元朝历史为例,不但是自警自励,而且是告知族人无需畏惧明朝。雍正朝“曾静案”发生之后,针对曾静等将清朝和同为非汉王朝的元朝类比进而加以贬低的言辞,雍正帝批判说:“元自世祖定统之后,继世之君不能振兴国家政事……终元之世,无大有为之君。”(22)《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第49页。雍正帝认为清朝的皇帝勤政爱民、乾纲在握,不可同元朝后期荒废国政的皇帝等而视之。
二是以元朝过于尊崇藏传佛教为戒。“兴黄教以安蒙藏”虽然是清朝的国策之一,但是清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同元朝有不同之处。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曾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23)《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二十七,乾隆五十八年四月辛巳条,第27册,第84页。在乾隆帝看来,清朝对黄教领袖并非滥加封赏,尊崇黄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边疆稳定。元朝时,由于元帝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和优待,造成僧人欺压百姓,“致有詈骂割舌、殴打截手之事”,(24)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2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574页。这使得元朝的宗教政策为后世所诟病。正因如此,乾隆五十年(1785)时,乾隆帝曾要求地方官不得偏袒回护西藏地方派出的贡使,以免“使无知之徒,将以本朝或踵元季尊崇喇嘛之习”(25)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2册),第574页。。
三是以元朝历史警示族人保持民族习俗。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认为《嘉礼考》中关于辽、金、元三朝的衣冠叙述不够清晰,并提到三朝在国初皆能保持民族习俗,但此后统治者“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寖溺,洊及沦胥”(26)李澍田主编:《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第337页。。乾隆帝以辽、金、元三朝历史警示族人保持衣冠风俗,也因此安排人员再修订《嘉礼考》。
(二)以元朝历史反驳“华夷之辩”
雍正朝时,曾静等人持“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27)《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116页。等观点,对少数民族刻意贬低和污蔑,认为元朝等几无可取之处。雍正帝在反驳曾静等人对元朝等非汉王朝的贬低时,一方面承认元朝后期确有弊政,另一方面又认为元朝前期皇帝并非无道,“如元代混一之初,衣冠未改,仍其蒙古旧服,而政治清明,天下乂安……衣冠之无关于礼乐文明、治乱也”。(28)《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153页。雍正帝以元朝历史为例,认为王朝的治乱同族属和衣冠并无关系,而同统治者是否行德政有关。
针对曾静等人贬低元朝的言论,雍正帝反驳到:“元之混一区宇……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29)《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9页。强调元朝曾实现大一统,在政治上也有可取之处,后人完全否认元朝功绩的言论并不公道。雍正帝还以明朝君臣评价元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立经陈纪”(30)《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50页。为例,强调即便是明朝人,也无法漠视元朝皇帝元世祖等人的善政,此亦是表明清朝同样可将国家治理好。
此外,乾隆帝曾就元朝是否为“中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31)赵之恒等编:《大清十朝圣训》,第1332页。在乾隆帝看来,宋朝和元朝虽然并非都是由汉人建立的王朝,但都属于中华正统王朝,认为王朝的正统性与民族无关。
(三)清朝皇帝朝贡观和疆域观中的元朝因素
元朝作为大一统王朝,统一了西域、西藏等地,朝鲜等国亦臣服于元朝,故清朝皇帝在其朝贡观和疆域观中不时借鉴元朝。
清朝入关之后,很快统一了包括陕西、甘肃在内的北方地区,同西域诸部有了直接的联系。西域诸部在得知清朝的声威之后,亦遣使赴北京朝贡。顺治三年(1646)正月,顺治帝召见前来北京朝觐的吐鲁番、哈密卫各贡使,(32)《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三,顺治三年正月己酉条,第3册,第198页。清廷下谕给吐鲁番贡使曰:“尔吐鲁番,原系元朝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受封此地,故明立国,隔绝二百八十余载,今幸而复合,岂非天乎。”(33)新疆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乌鲁木齐:新疆民族研究所,1978年标点本,第11页。在清朝看来,吐鲁番在元朝时即为成吉思汗后裔受封之地,在清初恢复同清朝的朝贡关系,可谓名正言顺之举。
此外,清朝亦借鉴元朝做法以处理同朝鲜的关系。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命人致书朝鲜国王李倧,提及朝鲜对清朝(后金)使臣的“不恭”言行,书信曰:“大元以北夷混一金宋而有天下,明之洪武乃皇觉寺僧而有元之天下,凡此诸国皆尔朝鲜世修职贡者。以此推之,则享有天下,惟有德之故,非世为君长之故也。”(34)云南社科院历史所:《清实录中朝关系史料摘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标点本,第59页。彼时皇太极刚称帝,故将清朝同元朝等作类比。在皇太极看来,元朝能够一统天下是因为其“有德”,“有德”之元朝有入主中原的历史正当性,以此类推,清朝亦有问鼎中原、一统天下的资格,因此,皇太极认为朝鲜向清朝称臣纳贡有史可循、有例可遵。
康熙六十年(1721),诸王、群臣在议请为康熙帝上尊号时说:“三逆背恩,辄党连而蠢动,六师讨罪,遂次第以削平,收元季之流逋,定台湾之岛屿……”(35)齐木德道尔吉编:《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下),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48页。在彼时众人眼中,清朝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元朝的疆域,再次实现了大一统。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在论及“封建制”和“郡县制”时说:“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36)《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三,雍正七年七月丙午条,第8册,第99页。雍正帝认为,元朝虽然有统一北方草原之功,但更认为清朝在疆域的统一上超越了元朝。
(四)以元朝黄金家族身份区隔蒙古
北元黄金家族在经历明初败局、内乱等低谷之后,到明正德初年,达延汗巴图孟克再次统一东蒙古,初步实现忽必烈一支黄金家族的振兴,“并青海及乌斯藏,控弦十余万”。(37)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一》,第94页。明末清初时,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首领大多为黄金家族达延汗后裔,而明代瓦剌即清代漠西蒙古首领多为非黄金家族后裔。从后金统一漠南蒙古开始,到乾隆朝统一漠西蒙古止,清朝统一蒙古诸部前后共经历了一百多年。在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清朝与漠南蒙古实行满蒙联姻,使得该部成为清朝统治全国的重要依托,正如顺治帝所言:“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38)《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三,顺治十三年八月丙子条,第3册,第798页。在满蒙联合的背景下,清朝十分重视对黄金家族嫡系后裔的笼络,如崇德六年(1641),林丹汗子额哲英年病逝,皇太极命人作祭文,并命宗室及大臣亲往祭奠,皇太极在祭文中提到“额哲孔果尔,原系大元之裔、察哈尔汗之子,及归我国,朕甚加优眷,配以公主,为固伦额驸,仍册封为和硕亲王”(39)李澍田主编:《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第2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标点本,第375页。,可见皇太极对黄金家族嫡系后裔的额外重视和关照。
清朝在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除了满蒙联姻之策,亦有分而治之之策。蒙古诸部内部在族源上比满洲人同蒙古人的关系更为亲近,为了淡化蒙古诸部内部的族源认同,清朝在经略北部边疆的过程中经常通过区隔黄金家族与非黄金家族来分化蒙古势力,进而服务于清朝的大一统。清朝在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最大的对手便是漠西蒙古准噶尔部,而该部首领并非黄金家族后裔。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在动议发兵统一漠西蒙古时说:“准噶尔一部落,原系元朝之臣仆……因扰乱元之宗族,离间蒙古……”(40)新疆民族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第545页。在雍正帝看来,漠西蒙古的祖先并非黄金家族后裔,且曾离间蒙古诸部,是元朝统治的不稳定因素,亦暗示了清代漠西蒙古仍是蒙古各部乃至清朝统治的不稳定因素。雍正九年(1731)四月,出兵漠西蒙古的清朝北路军统帅傅尔丹中漠西蒙古之计,为漠西蒙古军所败,仅有两千多人顺利退还科布多城。战后清军无力进攻,只能战略防御。雍正九年九月,雍正帝为鼓舞漠南蒙古诸部协助漠北蒙古反击漠西蒙古,特意指出“喀尔喀之王、台吉,俱系尔等成吉思汗之苗裔,一姓之兄弟也。准噶尔者,自元朝背叛,至今世为尔等仇敌”(41)齐木德道尔吉编:《清朝世宗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标点本,第236页。,希望黄金家族后裔团结一致对抗准噶尔部。雍正九年十一月,雍正帝谕青海蒙古诸部:“准噶尔原系成吉思汗之奴隶,尔等俱系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撒尔之子孙,若以博尔济锦氏诺颜等之先世论之,准噶尔乃尔等之奴隶也。奈何甘心自屈、受制于奴隶乎……朕因准噶尔反间致书,故又谆谆降旨。”(42)何玲编:《青海蒙古史料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283页。雍正帝强调准噶尔部同青海和硕特祖先的地位差异,是为了服务于当时政局,即在清朝处于战略防御的大背景下,希望青海蒙古不要堕入漠西蒙古的反间计之中。乾隆十九年(1754),清廷决定一鼓作气统一漠西蒙古,乾隆帝亦以黄金家族身份区分和排斥漠西蒙古:“准噶尔本元朝臣仆,窜处西北,恃其荒远,凭陵番部。”(43)新疆民族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第1047页。
(五)警惕清代黄金家族后裔的离心倾向
虽然清朝以黄金家族身份区隔蒙古各部,但黄金家族的身份亦给清朝对蒙古的统治带来了隐忧,部分黄金家族后裔特别是黄金家族嫡系——察哈尔部不愿顺从清朝的统治。林丹汗逝后,林丹汗子额哲等投降后金,后金封其为和硕亲王。顺治五年(1648),固伦额驸、亲王额哲去世,阿布鼐袭爵。顺治十六年(1659),阿布鼐“因部人阿济萨持刀行刺,不遵例知会掌扎萨克别旗王、贝勒等,擅自处斩”(44)《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六,顺治十六年五月辛巳条,第3册,第978页,引起清廷不满。康熙朝时,阿布鼐曾多年不朝觐,清朝命其子布尔尼袭和硕亲王爵位,并将阿布鼐囚禁在盛京。康熙十四年(1675),由于清朝调察哈尔部参与镇压三藩之乱,引起布尔尼起兵反清。此后,清朝平定了此乱,布尔尼亦殁于此次战事之中。无论是阿布鼐还是布尔尼,其对清朝的反抗或反叛,很大一部分动机是出于对黄金家族嫡系后裔身份的认知,体现了部分黄金家族后裔对清朝统治的抗拒。清朝亦意识到蒙古诸部黄金家族身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区隔蒙古各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防止该身份成为清朝统一的障碍。漠西蒙古也以黄金家族的身份来挑拨清朝同东部蒙古诸部的关系。雍正九年十月,漠北蒙古赛音诺颜部首领策凌提到,漠西蒙古利用黄金家族身份挑拨漠北蒙古同清朝的关系,漠西蒙古在致书漠北蒙古时说:“今尔等投顺中国,当差纳贡,深为尔等憾之。尔等本清吉斯汗之后裔,并非属人。”(45)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卷二十七,雍正九年十月丁巳条,《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影印本,第443页。此次离间最终并未奏效。但乾隆朝时,漠北蒙古最终还是出现了一次动荡——“撤驿之变”,而此次动荡的一大原因即是个别漠北蒙古贵族对自身黄金家族身份的认知。
“撤驿之变”发生时,正值清朝出兵统一漠西蒙古的关键时刻。漠北蒙古的黄金家族后裔额琳沁多尔济,因监护阿睦尔撒纳不力被乾隆帝处死,漠北蒙古贵族、黄金家族后裔青滚杂卜得知后十分震动,因其亦同阿睦尔撒纳有所联络,担心自己遭受处分,因此煽动漠北蒙古人撤离清朝在漠北蒙古设立的驿站,造成清朝同正在新疆征战的部队联络不畅,新疆局势陷入混乱。此后,“撤驿之变”很快被清朝平定。青滚杂卜在煽动撤驿时声称“元太祖裔,无正法理”(46)昭梿:《啸亭杂录》卷八《超勇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3页。,反映了个别黄金家族后裔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对清朝统治政策的不满及在政治上的离心倾向。正因如此,乾隆帝特下谕批驳青滚杂卜之言:“青滚杂卜乃谓喀尔喀系青吉斯汗后裔,向不治罪,此语舛谬更甚,如朕宗室中有犯刑章者,朕又何尝废法耶。”(47)《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一十七,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己丑条,第15册,第531页。由此可见,乾隆帝对青滚杂卜以黄金家族后裔自居而自认为政治地位特殊的心态明确表达不满。
四、结 语
清朝皇帝对元朝正统的确立、对元朝形象的维护有着多方面缘由。一是清朝(后金)发迹于东北地区,同蒙古诸部有着直接的联系,且通过联姻、征伐等手段,满蒙两大政治势力逐步实现了联合。漠南蒙古各部首领大多为元朝黄金家族后裔,出于对黄金家族后裔的重视和对非汉政权的关注,清朝有意识地维护元朝的正统地位。二是清朝和元朝同样由少数民族建立,后又入主中原成为大一统王朝,二者在面对人口占大多数的汉人时,面临相似的情境,因此,清朝统治者通过维护辽、金、元等朝的形象和元朝的正统,以彰显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现大一统早有先例的历史脉络。三是清朝皇帝具有超越以往帝王格局的民族观和历史观,即清朝皇帝对元朝的尊崇并非仅仅源于现实原因和功利因素,亦源于他们在熟稔中华历史的基础上对非汉政权及汉族政权的公正看法,正如乾隆帝在评论梁、唐、晋、汉、周这五个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时所言:“五十余年,更易数姓,中华统绪,不绝如缕。”(48)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标点本,第1796页。在乾隆帝看来,中国古代诸朝,无论是否是汉人政权,皆是中华统绪的组成部分,亦是中华历史的一部分。
清朝皇帝在了解元朝历史的同时并以之资治。一方面,以元朝灭亡为鉴,警示族人应保持民族风俗,对藏传佛教既利用也限制;另一方面,以元朝历史为佐证,反驳民间的“华夷之辨”思想,并借以处理朝贡等事宜。此外,清朝诸帝在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注意以元朝黄金家族的身份区隔东部蒙古和西部蒙古,分化蒙古诸部的内部认同,以巩固满蒙联姻、扼制蒙古诸部东西联合。
综上所述,从清朝皇帝的“元朝观”以及清朝皇帝对历代少数民族所建立政权的肯定来看,在清朝皇帝眼中,不仅大一统元朝是中华统绪的一部分,辽、金等非汉王朝亦是中华历史的一部分,中原汉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生活的疆域,显示了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