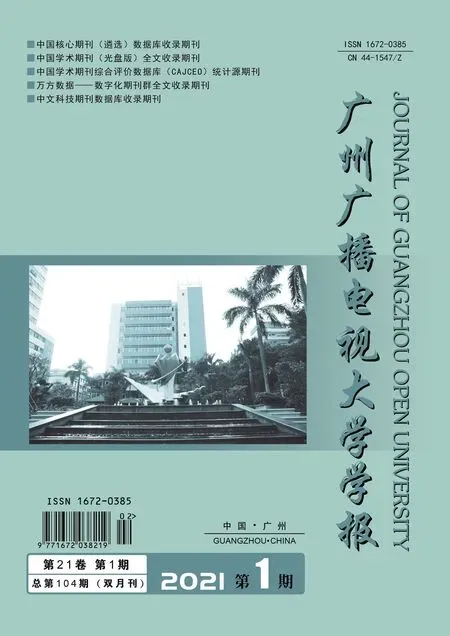关于形声字究竟是“形符表义”还是“声符表义”的考察
张栋鑫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1)
一、形声字的形成与分类
(一)形声字的形成
关于汉字的起源,大约远在战国时期就流行着“仓领造字”的传说,但对形声字是如何形成和分类的,直到近代,文字学史上才对其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比如章太炎、黄侃先生认为形声字是由“初文”“准初文”变易孳乳而来。除此之外,文字学界还有几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如唐兰先生的“合文说”、于省吾先生的“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说、高明先生的“形声源于假借说”等。而关于形声字形成的主流学说,则不得不提到裘锡圭、王凤阳两位先生的相关论述。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的第一章就谈到过形声字的起源问题,他说:“最早的形声字不是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的,而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或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而产生的。”[1]可见裘先生认为在较早的形声字中,形符与声符不是同时产生的。而王凤阳先生在论及形声字形成时,引入了语言中“表达律”和“区别律”的定义。我们可以将其简略转述为:“表达律”是指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要能起到如实记录词形的作用;而“区别律”是指作为词的书面形式的汉字,原则上要求从字形上能体现出词汇的差异,以便不致造成交际中的含糊或混淆[2]。把“区别律”和“表达律”用在形声字形成问题上,我们可以这样描绘形声字的产生过程。首先早期的汉字存有大量的象形字,而象形字的特点在于象物之形,如果不象形或象形得不够准确,就有可能产生误解。但文字毕竟不是图画,不能每一个符号都要去精确描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文字的“表达律”就会促使文字进行简化,使得象形字之后出现了假借字和记号字;但是,人们对有些不十分熟悉的事物费了好大功夫把它记写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又未必能读出来,从字形上也得不到有关提示读音的信息,这样,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必会受到影响,自然无法体现“区别律”这一法则。于是人们在一个不标音的象形字旁边加上一个表示语音的注音符号,其结果不但使原象形字与其它形近字区别开来,而且该字的音读也一目了然,这便是文字的“区别律”在发挥作用。那么在形声字形成过程中,“表达律”与“区别律”所起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根据徐中舒先生在《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的序言中的说法,“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它的产生,是由于象形字笔画简单,在长期使用中容易混淆,所以必须加声符以区别之”[3]。可见形声字的产生更多是因为“区别律”的作用,即“象形字加注音符”,王凤阳先生称作“同形分化形声字”,就形声字形成过程来说,这类形声字是属于早期的形声字,它是为区别字形相似、用法相混的情形下而产生的。
(二)形声字的分类
形声字除了同形分化外又可以细分为:“音同分化形声字”以及“同源分化形声字”。我们上文说到,形声字虽然是文字的“表达律”和“区别律”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是早期形声字主要是由于“区别律”产生的,是为了防止字与字的相混(为了区别一形多用或其它原因而有两种以上读音的字形)而造的区别字。其中“同形分化形声字”,形近致混是其主要原因,包括物形近似和简化混同两种原因,而根据形声字的二重区别法,“形混经常以音别”,所以这类汉字主要是在原字形的基础上加注声符来区别。如“雞(鸡)”和“鳳(凤)”在未加“奚”和“凡”之前容易与“鳥(鸟)”相混,因此加注声符“奚”和“凡”来以此区别。
“音同分化形声字”是指由于假借造成的同音字之间的混淆,根据“音混以义别”的原则,一般是添加范畴符号进行二次分化,使字在二重控制下达到区别的目的。这种形声字是在假借分化基础上形成的形声字,如“父”与“斧”、“因”与“茵”等。最后的“同源分化形声字”,则是因为多义词的分化孳乳而产生的同族词,他们之间多数是同音词,有一些是音近词。同源分化形声字是汉字在母词的字形基础上加范畴符号进行分化,比如“中”与“仲”、“工”与“攻”、“反”与“返”。
这三种类型的形声字根据出现时间的早晚,又可以相对地把同形分化形声字称作“前期形声字”,把同音、同源形声字称作“后期形声字”。我们不难发现后期形声字的主体是字的记音部分,所加的范畴符号只是为了区分同音词的,它已远离了象形字,与所写的词的词义形象脱离了关系,成为符号拼凑的字,可以说是在假借或同源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区别字。而形声字的不同类型又对“形符表义”和“声符表义”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下文我们将对其进行分析。
二、“形符表义”说与“声符表义”说
(一)“形符表义”说的理论基础
在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许慎《说文解字》是如何表述形声的造字法则的:“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江河”二字是由形符“水”和声符“工、可”构成。当人们习惯于把形声字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之后,就产生了对形声字中的形与声的疑问,到底形声字中哪一部分是字的基础?哪一部分主要承担着表意的功能?出于文字有义的观念,在对形声字的早期认识中,人们认为形符是占主导地位的,是意义的主要负荷者,这样就形成了重形符而轻声符的“形符主义”的观念,因此他们也把形符称作“义符”。这个观念统治了文字学发展的千百年。
分析原因,首先可能是上文所说的早期形声字中,即同形分化形声字中,后加的声符主要起到了表音的作用,而该字所记录的词义主要有未加声符之前的字形承担(此时还不是形声字),加注示音符号后,承担词义的这部分字形被看作是形符,因此逐渐有了“形符表义”的观念。第二个原因是自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揭示了汉字“形义统一”的根本属性后,后代小学家们有了本字记录本义的概念。而形声字的形旁有时的确能帮助我们确定本义。例如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里谈到的“理”字,“理”字从“玉”,本义应该是玉的纹理。“理”可以被理解为:按照玉的纹理来剖析它,所以《说文》训“理”为“治玉”。在这里“理”字的形旁“玉”的确起到了揭示部分本义的作用,而声旁“里”是如何示义的,在这里确实是看不到的。不过,随着人们对形声字研究的深入,人们渐渐发现,将形旁的意义跟形声字所代表的词义来进行比对,形旁体现出来的意义大都泛而不切,大多不能在二者之间随便画等号,因此“声符表义”说就开始兴起了。
(二)“声符表义”说的理论基础
那么“声符表义”说到底是怎么产生并发展的呢?首先在一些形声字中,有些字体现出来的词义和该字声符体现出来的词义确实存在着相同、相近或相关的关系,这种现象早在先秦时代就为人们所注意。如《礼记》:“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曰:‘政者,正也。’”[4]这说明,先秦时代人们就知道,一些从某字为声的字,其字义也得之于某字。随着音韵学兴起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形声字“形符表义”的局限性,因此一部分人另辟蹊径,继承了雅学的传统,尤其是刘熙的《释名》的传统,从声音上去探索词义。他们认为词的意义寓于声音,声音才是词义的承载者。反映到形声字当中,就是“声符”是词义的主要承担者。还有一部分人走的更远,选择从词源角度去看,比如章太炎先生的《文始》,黄侃先生的“声音贯穿文字训诂”之说。如果运用他们的主张来看形声字,那么得出的结论应该也是“声符主义”说,而形符只起别义的作用。
此外 “右文说”的出现也大大发展了“声符表义”说,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到:“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践’,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沈括发现了形声字中“其类在左,其义在右”的现象,而对应形声字的结构,“左形右声”又是最常见的形声字结构,将二者对照,因此也就有了“声符表义”的说法,如所举“戋”字,作为不同形声字的声符,都体现出了“小”义。宋末的戴侗著有《六书故》一书,继续发展了这一学说,他首先提出了“六书推类而用之”的方法,就是用同声符的字加以类比的方法,这个方法虽由王氏开其端,但是到了戴氏手里,却更加系统化了。第二,戴氏还以一个词原来的意义为纲,用以解释同声符的形声字所记录的词义,指出了初文和孳生字之间的关系(戴氏当然还不知道用这一类术语),但是这种见解是很了不起的,例如:“昏”字的本义为日色昏暗,因而孳生出“惛”与“睧”(心目之昏)、“婚”(婚娶在昏时)等字。这几个形声字的声符“昏”,既能表音,又有表义的作用,这是戴侗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也是他对“右文说”的一个重要贡献。等“右文说”到了清代小学家手里,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段玉裁、王念孙、阮元、黄承吉等人,都有大量的论述,特别是黄承吉的《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一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右音说”,因为突破了声符字形的限制,而将词义只系于声音,使得“声符表义说”更为绝对化了。黄氏说:“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5]并且他还认为形声字声旁是纲,形旁是目,“其在左之偏旁部分,则即由纲之声义而分为某事某物之目”[6],进一步巩固了声符在形声字的主导地位。
那么“声符表义”说究竟正不正确呢?它的适用范围真的能包括所有形声字吗?作为“右文说”的集大成者的沈兼士先生对“右文说”这一绝对化的说法予以了否定,他说“然形声字不尽属右文,其理至明,其事至显。”[6]原因是因为推崇“右文说”的人看不到声母也可以无义这种现象,因此“一切以右文说之,过犹不及”[7]。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右文说”合理之处,因而提出了利用“右文”探讨语根的设想。沈氏关于“右文说”的见解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其关于并非所有形声字的声符都能表义的论断相当正确,比如上文提到的声符“戋”,也有不表示“小”义的,比如:“践”实则为“履”也。此外,黄侃先生也曾举例加以说明“右文说”的局限,“裸”“踝”“窠”“课”“裹”“颗”等字皆从“果”得声而意义皆不用于“果”,其中意义也并不相通,这正是形声字声符不兼义的典型例子。
而为什么形声字中,有的声符表音兼表义,而有的声符只能表音呢?这就涉及到了“同源词”的概念。词汇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词义的衍生发展,推动汉语不断地构造新词。其结果便是一组组同源词的出现,它们共同构成了“同源词族”。同源词的特点,是彼此在意义上相通,在语音上相同或相近,即所谓的“音近义通”,而记录同源词的字叫做同源字。同源词的特点是“音近义通”,大部分同源字的特点也是字形相似或相近,同时因为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它在汉字中所占的比例从甲骨文时代的20%逐渐增加到金文中的40%多,到《说文解字》中所占比例已达80%,而现代汉字中形声字所占比例则接近90%,因此同源字中也是以形声字为主体的。而新的同源词出现之后,我们要构造记录该同源词的汉字字形时,为了减轻人们记忆汉字字形的负担,客观上就选择了同源字族已经出现过的声符或者是直接是以母字为声符的,所以在同源字族中就大量出现了声符相同的同源字。又因为母字与孳乳分化字二者是同源的,具有音近义通的特点,所以母字所记录的词义在孳乳分化字中也可以体现,又因为二者声符往往相同,因而慢慢也就有了“声中有义”的认识。但同时意味着“声符表义”说是有前提的,形声字声符表义的关键是“字要同源”。这正好与我们上文所说的后期形声字中有一部分形声字类型是同源分化字,且后期形声字占形声字的大多数相对应,因此我们可以说形声字类型中的“同源分化字”为“声符表义”说提供了条件。
三、“形符表义”说重新焕发生机的原因
根据上文,既然对于大多数形声字来说,声符是汉字所记录词义的主要载体,可是为什么传统的“形符表义”说还被有些人所接受呢?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汉字识别中,形旁对字义的提取有重要影响。虽然王凤阳先生在《汉字学》中说“形符除象形字字形混同加声符以区别的早期形声字以外,历来不是词义的承担者。它的作用主要是‘显义’和‘别义’”[8]。如前所述,形旁只是起“别义”的作用,而不起“表义”的作用。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形符看作是词义的范畴符号。比如以“目”为形的字总是和眼睛有关。它们或者与表示眼睛的组织有关,比如“眼”“睛”“睑”“眸”“瞳”“眶”;或者是眼睛流出东西:比如“泪”;或者表示与眼睛有关的状态:“明”“瞎”“眠”;或跟用眼睛的动作有关,比如“瞧”“瞪”“瞅”“瞄”“瞻”“眯”等;或者与眼睛发生间接的关系,比如“眩”“盼”等。虽然上述这些汉字具体所代表的词义不同,但它们表示的范畴义都是相同的,这就形象地反映出了形声字中形符所展示出的“范畴义”,并且在汉字演变过程中,形符的“范畴义”要比声符所体现出的“具体义”稳固得多,当声符发生变化,已经不能直接揭示字义时,形符却往往还能揭示这个汉字的类别或者这个汉字所属的范畴。
此外,“形符表义”说的流行,也跟字典的编纂有关,特别是跟部首检字法密切相关,王凤阳先生在《汉字学》里有过精彩的论述:“形符在造字时代只起区别混淆的作用,可是部首字典通行之后,人们在检字时主要是根据形符进行的,这样一来无形中提高了形符在构字中的地位和作用。”[9]最后,“形符表义”具有一定的心理基础。人脑所具有的联想机制是“形符表义”的心理基础。通过人脑的联想,形符与形声字之间产生了意义联系,如:女,《说文解字》解释为:妇人也。凡从女的字应该都与女性有关,如:娘、妈、姨、妹、姐等都表示女性。作为“形符表义”的心理基础,“联想”使形符的表义具有了概括性的特点。
这样一来,形符和声符的作用在不知道声音揭示词源的后人眼里正好颠倒了位置,好像形符是在表示意义,而声符的作用只限于区别声音了。这种历史的颠倒反映在人的头脑中也就根深蒂固地植下了形符表义、声符表音的观念。
四、小结
可是不论是主张“形符表义”还是“声符表义”,都具有片面性。“形符表义说”对形近分化的字(即早期的形声分化字)来说是正确的,而“声符表义说”对部分同源分化字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们都不能概括全部的形声字。就数量而言,因为形近而分化的汉字发生在整个形声字形成的早期,占形声字的少数,而形声字中由同源分化的汉字处于形声字形成的后期,同源分化形声字数量要大得多,所以“右文说”更接近真理,能解释更多的形声字。只是“右文说”的局限在于把“声符主义”绝对化了,想用以解释全部形声字,结果使它钻入了矛盾丛生、以偏概全的牛角尖,因此我们更容易接受“声近义通”这一折中的说法。
由此可见,历史上关于形声字的“左文说”和“右文说”都是不同时代的人对文字不同感受的产物,人们忘却词源是“形符主义”提出的历史原因;由于古音学研究的深入,人们重新发现词源是“声符主义”提出的历史根据。对形声字的认识就这样走了一条正反不同的曲折之路。而直到王宁先生提出“类义素”与“核义素”的说法,含有词义类别的义素称为“类义素”,大多数是由形声字的形旁表示,含有词义特征的称为“核义素”或“源义素”,大多数由形声字的声旁表示[10]。才使得“形符表义”说与“声符表义”说的分歧得以解决。
最后,我们要着重申明一点:在考察形声字所代表的词义时,不能囿于它自身义符所体现的范畴义,也不能囿于它自身声符所体现的词源意义,而是应该把形声字所承载的词义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考察,这样才能避免像段玉裁先生在说解形声字的时候所犯的“波者,水之皮;坡者,地之皮”那样望文生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