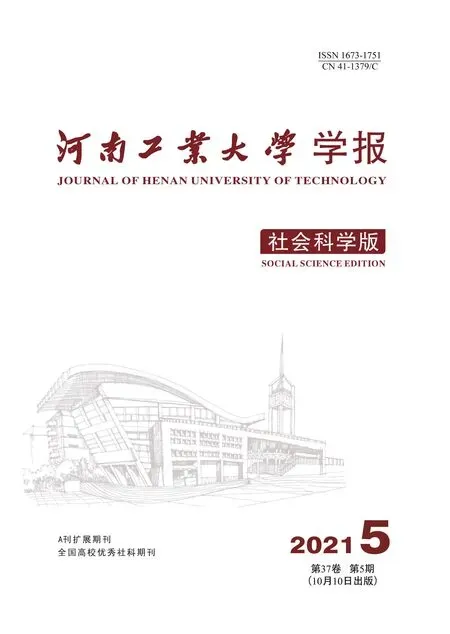由训诂通经义:论乾嘉经学的治经方法
张梦帆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中国传统经学研究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促使有清一代学者一方面全面整理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寻找儒家经典的本意。而要进行这两项工作就必须具备扎实的训诂基础,于是训诂成为通经的必要因素和先决条件。训诂萌芽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在魏晋隋唐五代得到充分发展。宋明时期,受理学的影响,训诂发展迟缓,经典整理工作最多只能占据次要地位。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训诂至清代乾嘉时期逐渐发展成熟,加之清代独特的学术环境和政治引导,训诂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训诂的进步与成熟,带动了考据学的全面发展,以名物训诂为中心的考据之学,成为乾嘉经学的典型特征。
1 “训诂通经”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训诂考据与推阐义理作为研治儒家典籍的两种重要治学方式,在经学发展史上往往表现出此消彼长的特点。自魏晋南北朝“玄学”大行其道后,义理学发展至宋代已经蔚为大观。相比之下,训诂考据虽未停滞,但与东汉古文经大盛时相比,势头明显减弱,元明时期更是呈衰微之势。但是自明中后期开始,尊汉儒、重考据之风渐流于学林,至明末清初渐成气候,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等学者多惩于明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之风,树起了“经学即理学”的大旗。随着清代社会的渐趋安定,文化与经济日益繁荣,宋明以来刊刻的典籍错讹多见与士林对古籍需求日益增长的矛盾急剧激化,对传世古籍进行辨伪、辑轶与校勘等大规模的整理研究,成为客观的需要。加之清廷文教政策的有意引导以及四库馆的建立,乾嘉时期反对宋明“空衍义理”之风愈演愈烈,宗汉尤其是以东汉为宗的学术风气十分浓厚。
东汉治经的典型特征是以古文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与西汉今文家注重家法相承、专习一经与阐释经文的微言大义不同,东汉古文家无师相授,又面临古文难通的困境,故治经多以训诂考证和名物典制为先务,倡导训诂实证、博学贯通和无征不信,注重经文本义的训释,力求恢复经典的本来面貌。因此,东汉古文家多数是训诂大师,如贾逵、许慎、马融、服虔、郑玄等,其所著书如郑玄《毛诗笺》《三礼注》以及许慎《说文解字》等,皆长于名物考辨、训诂考证。东汉以训诂考证、名物典制为首要条件的实证学风满足了乾嘉学者着力改变宋明以来空疏之风的迫切愿望,逐渐成为时人标榜的对象。正如戴震所云:
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于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训、义理而二之,是古训非以明义理,而义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也。[1]册7,2
追求义理要以古经为载体,不能依靠玄想和主观臆断进行推测。但由于今古悬隔,古今语言变化较大,因此要对古经进行解读必须凭借训诂,只有明训诂才能通古经,只有通古经才能领悟经书中圣贤的真实意图。程瑶田亦曰:“今日者人人皆知治经,由人皆知遵守《说文》,所谓‘六书通而经学明’也。”[2]阮元亦云:“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3]53王鸣盛更是直言:“小学宜附经,……然小学却为经之根本,自唐衰下讫明季,经学废坠千余年,无人通经,总为小学坏乱。无小学自然无经学。”[4]钱大昕亦云:“国朝通儒,若顾亭林、陈见桃、阎百诗、惠天牧诸先生,始笃志古学,研覃经训,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谓诂训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5]册9,364-365
在戴震、程瑶田、阮元、王鸣盛、钱大昕等学者的推动下,训诂考证在经学研究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成为治经的必要因素和先决条件。于是,由词通句,由句通文,由文通道逐渐成为乾嘉时期学者“治经达道”的普遍共识。诚如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所言: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1]册6,370-371
古人治经的目的是寻求蕴含于古经中的圣贤之道,而“明道”就必须通晓典籍中的字和词,至于如何通晓儒家经典中的字和词,则需从《说文解字》这类训诂著作开始,进而知其“故训未能尽”,应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才能确定经书中字、词的本意。这是戴震对自己少年求学与早期学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重点强调的“字”和“词”,就是主张从训诂的角度研治经书。又据段玉裁《戴东原年谱》载:“先生十六七以前,凡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诂语之,意每不释。塾师因取近代字书及汉许氏《说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三年尽得其节目。”[1]册6,651戴震正是在厘清《说文》节目、博贯古经的基础上,对文字训诂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并根据自身的训诂实践和研读经书的切身体验总结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经方法。戴震对“训诂通经”的治经方法的总结,显然是继承了东汉古文家以训诂考证为先务、贯通群经的治经传统。
不仅戴震如此,惠栋、钱大昕等学者也是秉持由训诂通经义的治经方法。如惠栋《九经古义述首》曰:“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6]钱大昕《经籍籑诂序》也提到:“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5]册9,366可见,由训诂通经义,由古经通义理,已经成为乾嘉时期普遍的治学方法。
2 解经方法的转变促进经学全面深入的研究
治经的关键在于解经,无论是以义理为中心的宋学,还是以训诂考据为中心的乾嘉经学,均以解经为治经达道的途径。只是宋学对语言文字的依赖性小,而乾嘉经学则以音韵训诂为解经的必要渠道和先决条件。解经方法的转变为乾嘉学者疏通典籍、恢复经书原旨进而追求圣人贤语的真实意义提供了保障,促进了乾嘉经学全面深入的发展。
自清初顾炎武高举“经学即理学”的经学大旗后,学者们研治经书的热情空前高涨,至乾嘉时期,学者们已展开对经学的全面研究。以十三经的注疏为例:乾嘉时期训《诗》之书有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等;说《易》之书有惠栋《周易述》、孙星衍《周易集解》、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和焦循《雕菰楼易学三书》等,释《书》之书有惠栋《古文尚书考》、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以及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释《三礼》之书如秦蕙田《五礼通考》、庄存与《周官记》、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凌廷堪《礼经释例》、张惠言《仪礼图》、杭世骏《续礼记集说》等,注《春秋三传》者如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庄存与《春秋正辞》、孔广森《公羊通义》等。注《论语》《孟子》者,如焦循《论语通释》《孟子正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当然戴震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训释《孟子》,而是表达其哲学观念。疏《尔雅》者,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较具代表性。
乾嘉学者对经典的全面注疏不仅使以往的《三礼》《春秋三传》之学等得以复兴,而且促进了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和研究。在经书研究中,经典意义的疏通历来以字词句的训释为主,相比之下,名物典章制度的研究则薄弱得多。名物典章制度涉及宫室、器物、考工、天文、水地、农业、动物、植物等诸多内容,这些内容所涉范围宽广,对于解经治经同样重要。戴震在论及“经之难明”的诸多问题时,曾从天文地舆、音韵训诂及名物制度等角度阐释了其对解经的重要性:
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1]册6,371
在戴震看来,解经之不易存在许多原因。经典的解读除了对基本字词句的训释,还涉及草木虫鱼、宫室衣物、天文舆地等名物制度的训释。倘若这些知识不通,则无法准确地理解经意。因此,戴震提倡以经书中字词句的训释为基础,兼通旁类。正是在戴震等学者的倡导下,乾嘉时期涌现出大量名物典章制度论著,如为辨释草木鸟兽虫鱼之名,戴震撰《经雅》,程瑶田撰《释草小记》《释虫小记》《九谷考》;为明古代考工,戴震撰《考工记图》,程瑶田撰《考工创物小记》,阮元撰《考工记车制图解》;为考宫室衣物,程瑶田撰《释宫小记》,金鹗撰《楼考》《夹室考》《冕服考》《诸侯祭服考》等;为释天文舆地,王鸣盛撰《说地》,戴震撰《水地记初稿》,程瑶田撰《水地小记》《禹贡三江考》,钱大昕撰《地名考异》,段玉裁作《中水考上》《中水考下》,等等。
乾嘉学者对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扩展了经学的研究范围,而对音韵训诂的精细研究则带动了乾嘉经学的深入发展。乾嘉经学的深入发展主要表现在“求古”和“求真”两方面。“求古”主要指通过音韵训诂掌握经典中字词背后的原始意义,进而恢复儒家典籍原初意义的准确解释。以儒家经典重要名词“理”“仁”和“敬”的训释为例,宋明理学家为表达观点的需要,往往从主观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诠释;而乾嘉学者往往溯本求源,利用训诂、考证对经典中的重要名词概念进行重新分析,力图恢复经书原旨。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对“理”的诠释,阮元《论语论仁论》对“仁”的诠释以及《释敬》一文对“敬”的诠释便是如此。宋明理学强调“理”存于“心”,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则通过训诂、考证将“理”蕴于具体的事物中,对“理”进行重新解读,认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1]册6,151,“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1]册6,158。戴震对“理”的解构打破了“理”的神圣性,肯定了“理”在事物中的客观存在性,有力地抨击了宋明理学“天理具于人心”的理学观。
阮元《论语论仁论》和《释敬》篇对“仁”和“敬”的诠释,同样反映出乾嘉学者追求“复古”的学术目的。《论语论仁论》中,阮元根据“仁”在文献中的记载情况,从词源学角度追溯“仁”的原始义,确立“仁”属于人际交往的范畴。据阮元考证,《尚书》中《虞》《夏》《商》,《诗经》三颂以及《周易》卦爻辞均未曾出现“仁”字。《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宁忍予”中“人”实“仁”字,表示人偶之意。周初已有“仁”义,但无“仁”字,“仁”字在《周官礼》后始造。因此,在“仁”出现之前,“仁”的意义负载于“人”字上。从字源学角度看,“仁”在六书中属会意字。《说文》:“仁,亲也。从人二。”阮元据段玉裁《说文》“仁”注,并征引其他例证,说明“仁”的造词理据:
段若膺大令《注》曰:“见部曰:‘亲者,密至也。’会意。《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大射仪》:‘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于此意相人耦也。’《聘礼》:‘每曲揖。’《注》:‘以人相人耦为敬也。’《公食大夫礼》:‘宾入三揖。’《注》:‘相人耦。’《诗·匪风·笺》云:‘人偶能烹鱼者。人偶能辅周道治民者。’”
……以上诸义,是古所谓人耦,犹言尔我亲爱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3]178-179。
根据“仁”在文献中的记载和对“仁”词源的探求,阮元远承汉儒郑玄注《中庸篇》“仁者,人也”之说,以“相人偶之人”释“仁”,确“仁”字本训,并得出春秋时孔门所谓的“仁”是“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3]176的结论,将“仁”归入人际关系范畴。《释敬》一文,阮元亦从字源学角度对“敬”的造字理据进行训释,又以同声同韵的同源词“警”对“敬”的本义“恒自肃警”“肃警无逸”做出说明,从而反驳以“端坐静观主一之谓”释“敬”的观点[3]1016-1017。“主一之谓敬”[7]是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的观点,二程释“敬”强调内心的专一和无念无想,而阮元通过词源训释更强调“敬”的本义“肃警无逸”。阮元对“敬”本义的探求,说明了《周书·谥法解》“夙夜警戒曰敬”、《易逸象》“乾为敬”、《周书》以“无逸”名篇以及《国语》敬姜之所以为敬的缘由。
乾嘉学者标榜汉学但不局限于“复古”,而是试图通过“复古”达到“求真”的学术目的。所谓“求真”主要指乾嘉学者通过训诂的方法辨识古训、疏明古义,以追求圣人贤语的真实意义。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囿于前人注疏,敢于纠正旧注中不合理的词义训释,是“求真”的重要表现之一。如《礼记·曲礼(上)》“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中“犹与”的训释,唐孔颖达正义曰:“‘定犹与也’者,《说文》云:‘犹,兽名。玃属。’与,亦是兽名,象属。此二兽皆进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谓之‘犹与’。”[8]孔颖达将“犹与”拆分为两个语素“犹”和“与”,认为“犹”和“与”皆是兽名,因二兽进退多疑,故以“犹与”为名。对此,王念孙持否定看法,他在训释《广雅》“踌躇,犹豫也”时,从语音角度将“犹豫”分析为双声连绵词:“此双声之相近者也。‘踌’‘犹’、‘躇’‘豫’为叠韵;‘踌’‘躇’、‘犹’‘豫’为双声。……嫌疑、狐疑、犹豫、蹢躅皆双声字。狐疑与嫌疑一声之转耳。后人误读狐疑二字以为狐性多疑,故曰狐疑。又因《离骚》犹豫、狐疑相对成文,而谓犹是犬名。犬随人行,毎豫在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故曰犹豫。或又谓犹是兽名,每闻人声,即豫上树,久之复下,故曰犹豫。或又以豫字从象,而谓犹、豫倶是多疑之兽。以上诸说,具见于《水经注》《颜氏家训》《礼记正义》及《汉书注》《文选注》《史记索隐》等书。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9]王念孙否定旧注中以犬名或兽名解释“犹”“豫”的说法,认为“犹豫”当为双声词,应根据古音来探求词义,不当拆开而望文生训。依现代语言学观念,王念孙的说法是可靠的,“犹豫”确是一个双声连绵词,本无定字,以声取义,又作“犹移”“犹夷”“犹与”“容与”等,不可拆分训释。又如《孟子·滕文公》篇“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中“养”和“射”的训释,汉赵歧以“养者,养耆老;射者,三耦四矢以达物导气”训释之。王引之则结合古代典章制度,认为赵注是缘辞生训,并非经文本意,不可取。他认为:“养国老于上庠,谓在庠中养老,非谓庠以养老名也。《州长》职云,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谓在序中习射,非谓序以习射名也。……庠序、学校皆为教学而设,养老、习射偶一行之,不得专命名之义。庠训为养,序训为射,皆教导之名,其义本相近也。”[10]与赵歧注相比,王引之以“教”训释“养”和“射”的词义更为合理。又如金鹗《求古录礼说·楼考》篇对《说文解字》以“重屋”训释“楼”本义的说法提出质疑,他通过对“阙”“榭”“隅”等的考证,结合历史文化,提出现在所谓的表示重屋的“楼”始于汉代,许慎以“重屋”训释“楼”的本义是依据汉制,其文曰:“至于今之楼则始于汉。《汉书·郊祀志》云:‘武帝时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上有楼,名曰昆仑。’昆仑三成其楼,亦三重,可知帝作明堂,如带图,而重屋之楼由是以起,殊不知古之明堂实无楼也。许氏《说文》训楼为重屋,但以汉制释之,其亦考之不详矣。”[11]表示“重屋”的“楼”是否起于汉,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金鹗不墨守成规,不为《说文》所束缚的治学理念和质疑精神,却是值得注意的。
3 辩证看待传统训诂的治经方法
中国传统训诂学是治经的重要工具,亦是经学的附庸。经书以文字为载体,解经需要释文义,而疏通文义的关键在于训诂。中国传统训诂学以全面、完整地解经释经为中心,着重词、句、段以及篇章的释义,涌现出以“传”“注”“疏”“笺”等为代表的经学注释书以及以《尔雅》《说文解字》等为代表的训诂专书。经学注释书对解经治经的作用不言而喻。训诂专书作为治经的工具书,对于理解经书文意也有很大的作用。例如作为中国辞书之祖的《尔雅》,虽然以汇总先秦古籍中的古词古义为中心,是一本读经解经的工具书,但在汉代时便被奉为儒家经典。唐文宗开成年间,刻开成石经,更是将其直接列入经部。《尔雅》作为解经的钥匙,被列入十三经是历史的必然,训诂对于解经治经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清代乾嘉经学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与乾嘉时期训诂上追汉唐之求实,近秉宋明之求新,密不可分。这一时期训诂获得高度发展,对中国传统训诂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是中国传统训诂研究的集大成时期。乾嘉学者在训诂研究上获得的成绩,是清代经学在研究虽上承两汉但又能超越两汉的重要原因。
随着封建王朝的结束,中国经学史下限止于近代五四运动[12]37,但学界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却没有结束。当下经典的研究被分划于政治、哲学、文学、历史、语言等诸多学科。无论是哪个领域,我们进行经典研究仍要要重视训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要理解经典原意必须从语言文字出发,哪怕是以义理著称的宋明理学,也要借助语义阐释观点,只是“汉学是借助字义澄清义理,宋学是透过语义构思义理。汉学是对思想源头的挖掘,宋学则是思想景观的构筑”[13]。乾嘉学者从澄清语义的角度寻找蕴含在语言文字中的原始意义,为从历时角度理解更深远的思想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我们今天仍要学习。况且,自汉至清的训诂学家们大多皓首穷经,在解经释经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训诂经验。我们今天进行古经研究,一则不可能再对经典中的字、词、句考究训释一遍,二则前人尤其是清代学者对古经的训释成绩斐然,我们也很难超越,因此古人解经释经的训诂材料仍然值得我们重视,这也是我们尊重民族传统文化、从汉语实际出发研治经典的必要举措。
训诂对于解经治经固然重要,但我们进行经典研究却不是要返回传统的训诂学。一方面,训诂以古代文献的意义解读为中心,侧重于词语、句子的训释,而经学研究除了要理解词语、句子的意义,还要关照文本整体的解读以及作者本身的思想等其他非语言文字的问题。周予同《怎样研究经学》曾指出,汉学古文派经学研究的流弊在于“出发于文字训诂而仍旧归宿于文字训诂。换句话说,他们只懂得经学的外表而还没有把握住经学的核心——除了戴震几个人以外”。[12]127况且,进行经典研究未必需要如清儒那般事事都追求本义,字字都考释得精细,梁启超曾云:“以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痛,结果还是供极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岂非愈尊经而经愈遭殃吗?”[14]另一方面,以释经为主的传统训诂学发展到近现代,在章太炎、黄侃、沈兼士、刘师培等国学大师的推动下,逐步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体系化和理论化逐步增强,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又经过齐佩瑢、陆宗达、周大璞等训诂学家的发展,中国传统训诂学已经成功与现代科学衔接,最终发展成为语言学下的一门独立学科。传统训诂学向现代训诂学的过渡和发展,使得训诂学和经学研究相去甚远。当前训诂学向精细化、系统化和理论化方向发展,着重探讨系统的训诂原理和总结理论性的训诂方法。因此,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不是要回归传统的训诂学,而是要借鉴乾嘉学者治经的思想与方法为今日经典研究服务,促进儒家经典在新时代背景下发生创造性的转化。
综上所述,乾嘉经学“训诂通经”的方法带动了传统小学的全面发展,使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进入鼎盛时期;而传统小学的进步又促进了传统经学的转变和乾嘉经学的纵深发展。总结乾嘉经学的治学方法和研究经验,正视训诂考证在研治经典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非要回归传统的以训诂考据为中心的经学研究,而是当前进行儒家经典研究回望传统的必要条件。乾嘉学者经典研究中的一些学术理念如重视调查研究、反对孤证、强调材料的归纳和总结等,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当前我们进行经典研究除了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学术理论和方法,也要懂得一些基础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识。这不仅有利于对古代典籍尤其是专经的研究,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国经典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