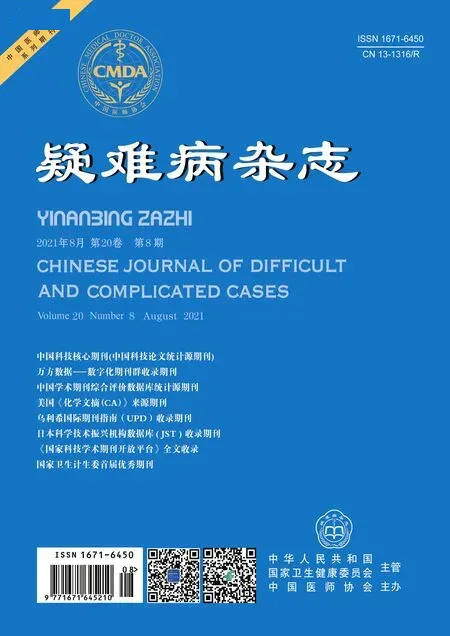肠道菌群与雄激素的相互作用及对冠心病发病的影响研究进展
陶俊,周漫综述 李艳审校
冠心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disease,CAD)是一组由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冠状动脉阻塞,进而导致心肌供血不足的疾病。目前,CAD是人群中发病率和病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1],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有升高趋势。人类肠道菌群是一个复杂的群落,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包括500~1 000种细菌,总重量可达1.0~1.5 kg,包含的细菌数量达到1014个。肠道菌群在消化和代谢、免疫和防御中起到重要作用,不仅使肠道上皮细胞进行信号传导,还能与远端组织器官相互作用[2]。肠道菌群能够影响机体的消化能力,抵御感染和自身免疫疾病的患病风险,其被视为判断机体健康状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肠道菌群构成的改变和菌群失调与冠心病的发生有关。冠心病多见于中老年男性(>45岁)和绝经后女性,提示性激素与CAD的发病密切相关。肠道菌群可影响性激素水平及代谢[3-4],文献报道肠道菌群产生的17β-脱氢酶可催化睾酮代谢为雄烯二酮,表达17β-脱氢酶的菌群主要为分枝杆菌属。且基础研究表明[5],雄激素及其受体可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活性、增强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参与调节脂质在动脉壁的沉积而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从而发挥动脉粥样硬化保护作用。本文主要探讨肠道菌群与雄激素的相互作用及对冠心病发病的影响。
1 冠心病与肠道微生物
1.1 人体肠道菌群特征及性别差异 人体肠道菌群自母体分娩时开始建立。胚胎在母体的子宫内处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通过阴道分娩出生的婴儿肠道定植的细菌是与母体阴道菌群密切相关的种群,以乳杆菌和普雷沃氏菌为主;通过剖宫产出生的婴儿肠道定植的细菌是暴露于环境中皮肤所接触的微生物如葡萄球菌和棒状杆菌[6-7]。1岁之前主要定植双歧杆菌、肠球菌、大肠杆菌/志贺氏菌、链球菌、拟杆菌和罗氏菌等;1~3岁以梭菌属、瘤胃球菌属、韦永氏球菌属为主;3岁以后至成年肠道以拟杆菌、硬壁杆菌为主;65岁以后主要定植变形杆菌、拟杆菌、产碱杆菌等。健康个体的肠道微生物群90%以上是由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组成[8]。
研究报道,在啮齿类动物和人类中,肠道菌群的组成具有性别差异[9-11]。男性肠道菌群的α-多样性较女性更低,这种现象在青中年男性中更为明显[11-12]。肠道菌群的组成在青春期之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在性成熟时两性差异最为明显[4,13]。研究发现,相对于性成熟前后的雄性小鼠而言,性成熟前后雌鼠的肠道菌群差异更小,并且雄鼠去势后其肠道菌群与雌鼠更相似[14]。这表明雄激素与肠道菌群的构成具有某种联系。
1.2 肠道微生物影响机体代谢的方式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的基因总数是人类基因组的100多倍[15]。这数百万亿的菌群所产生的代谢产物,参与了机体多个分子学代谢通路[16]。肠道菌群执行多种功能,并与宿主相互作用,不仅仅局限于食物消化。肠道菌群构成并调节肠道黏膜屏障,控制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协助免疫组织成熟,并预防病原微生物的入侵[17-18]。在生理条件下,肠道菌群会持续刺激免疫系统,这是防御病原体入侵快速、有效的机制[15,18]。肠道上皮屏障由健康多样的肠道微生物群维持,平衡、稳定的细菌组成是维持肠道免疫功能和机体健康的关键[16]。总体而言,微生物群对全身免疫力和代谢具有重要影响,而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群则是影响宿主整体健康的关键因素。
肠道菌群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宿主产生影响。为了与远端器官进行交流,肠道微生物的信号分子首先需要通过肠上皮进行信号的传输。这些信号分子可以是微生物群的结构成分,如脂多糖(LPS)和肽聚糖等,它们可以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RR)与宿主黏膜表面细胞发生相互作用[19-21]。PRR识别并与病原体相关的分子模式(PAMP)结合从而引起宿主的免疫反应[22]。因此,LPS和肽聚糖可以通过与宿主上皮细胞边界和脉管系统内的宿主受体结合进而触发大量下游受体,通过受体的下游信号通路进行信号的传导,特别是在肠壁屏障功能受损的情况下[16]。肠道菌群也可以通过生物活性代谢物,如三甲胺(TMA)/三甲胺N-氧化物(TMAO)、短链脂肪酸(SCFA)及饱和胆汁酸(BAs)等,直接或间接影响远端器官的生理进程[23-26]。某些肠道微生物的生物活性代谢物可与其他内分泌激素,如生长素释放肽、瘦素、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YY肽(PYY)等相互作用,进而影响机体的代谢过程[27-29];有些可通过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从而影响血糖水平等进而导致机体的代谢异常[30]。
1.3 冠心病患者肠道菌群的改变 2012年,Karlsson等[31]应用粪便微生物的宏基因组测序发现,粪便微生物的组成在斑块不稳定的冠心病患者与稳定的患者中发生了变化,斑块不稳定的患者粪便中罗斯伯氏菌属的水平降低。并且冠心病患者肠道菌群基因组中编码肽聚糖合成的基因增多,编码八氢番茄红素脱氢酶的基因减少,这提示冠心病患者的肠道微生物可能通过产生更多的促炎分子来促进炎性反应的发生。2016年,Emoto等[32]发现与健康人相比,冠心病患者肠道细菌中乳酸杆菌目增多,拟杆菌属和普氏菌属下降,厚壁菌门/拟杆菌门的比例上升。2017年,Jie等[33]发现在冠心病患者中,包括大肠杆菌、克雷伯菌和产气肠杆菌在内的肠杆菌科细菌的丰度高于对照组,经常存在于口腔中的细菌(如链球菌、唾液乳杆菌等)的相对丰度也高于健康对照组。
1.4 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对冠心病发生发展的影响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含有细菌DNA,在同一个人的肠道中也存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观察到的细菌分类群[34]。这些观察结果表明,肠道中的微生物可能是斑块中的细菌来源,其可能会影响斑块稳定性和冠心病的发展。
近年来,微生物代谢产物TMA的肝氧化产物TMAO对冠心病发病的促进作用引起了广泛关注。Wang等[35]发现,ApoE(-/-)C57BL/6J小鼠仅在喂食富含胆碱的饮食和具有完整的肠道菌群时才会导致血浆TMAO水平增加,巨噬细胞、泡沫细胞形成增加及主动脉粥样斑块增大。相比之下,无菌小鼠和肠道菌群的短期抗生素抑制了TMAO的生成,后者减少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并且,肠道菌群对胆汁酸及胆固醇的吸收与代谢作用直接影响着血清胆固醇的水平,而胆固醇水平的高低又是影响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36]。其可能是通过产生胆固醇氧化酶、抑制肝脂肪合成酶的活性、影响胆盐的肝肠循环等进而影响胆固醇的代谢,发挥调节血脂的作用[37-38]。
2 雄激素与肠道菌群
2.1 雄激素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睾酮是机体最主要的雄激素,其在睾丸间质合成,在血液中以3种形式存在:游离睾酮(FT),约占2%;与白蛋白结合的睾酮,约占68%,以上2种形式称为有生物活性的睾酮;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HBG)紧密结合的睾酮,占30%。流行病学数据表明,男性冠心病的发生率和睾酮水平呈负相关,且睾丸激素水平低与男性心绞痛患者的冠状动脉疾病有关,这提示生理性雄激素水平可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39]。研究证明,雄激素受体(AR)不但存在于睾丸间质细胞,也分布于主动脉、冠状动脉、心房、心室肌等处[40-41]。并且,研究发现,高剂量睾酮可通过改善内皮功能从而扩张冠状动脉并增加冠状动脉血流对CAD患者起保护作用[42]。RT-PCR技术也已证实,男性巨噬细胞中AR的浓度明显高于女性,这也许是雄激素作用于男性心血管系统的生理基础。
此外研究表明,睾酮水平与载脂蛋白B水平呈负相关[43]。雄激素对冠心病发病的作用途径有很多种,雄激素可通过转化为雌激素及其非基因组作用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同时,睾酮可直接作用于雄激素受体从而起到保护作用。在不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小鼠雄激素水平的情况下,针对特定细胞类型的AR观察到一些有益作用[44]。总之,雄激素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机制尚未完全清楚,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2.2 肠道菌群与雄激素的相互作用 Markle等[4]发现血清睾酮水平在无菌和SPF级小鼠间有差异,Yurkovetskiy等[14]发现丝状细菌的定植会使血清睾酮水平增加,这些研究结果提示肠道微生物可通过某些途径调节血清睾酮水平。关于肠道菌群对雄激素的调节方式,目前尚未完全清楚。研究发现,梭状芽胞杆菌能以糖皮质激素为原料合成雄激素,某些细菌能够产生5α还原酶从而使睾酮转化为活性更高的双氢睾酮,还有一些肠道微生物群调节雄激素水平是通过去葡萄糖醛酸化来释放葡萄糖醛酸缀合物中的游离双氢睾酮[15,45-46]。
雄激素水平会受到肠道菌群的影响,同样宿主体内雄激素也会影响肠道菌群的构成。性腺切除术和激素替代对啮齿类动物的肠道细菌产生了明显影响[9]。在小鼠中,去势后雄性和雌性之间肠道菌群的性别差异减少,这表明性激素对肠道菌群具有调节作用[15]。Moreno-Indias等[47]发现对雌性大鼠从出生当天进行丙酸睾酮(1 250 μg/d)补充后,其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降低,厚壁菌门/拟杆菌比率升高。
3 性激素、肠道菌群及其与冠心病发生发展的联系
冠心病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和雄激素可通过多种途径对冠心病的发病产生影响。
研究证实,宿主雄激素水平可导致肠道菌群的差异,而菌群的改变又会引起代谢的变化[48]。同时,雄激素水平又会抑制肝脏单胺氧化酶的活性,从而抑制TMA向TMAO的转变[49]。而TMAO又是肠道菌群影响冠心病发病的重要代谢产物。雄激素水平也会受到菌群的调节,二者的相互作用对机体疾病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总而言之,机体雄激素水平和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可通过炎性反应、免疫及代谢等多种途径影响冠心病的发病。
4 小 结
肠道菌群、雄激素和疾病的研究方兴未艾,目前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分子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许多未知之处。调控肠道菌群及雄激素水平是否能作为冠心病的潜在治疗靶点,需进一步研究评估,治疗适应证和具体策略也需要进一步论证。随着雄激素、肠道菌群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逐步深入,雄激素及肠道菌群的功能和影响疾病发展的机制也将被人们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