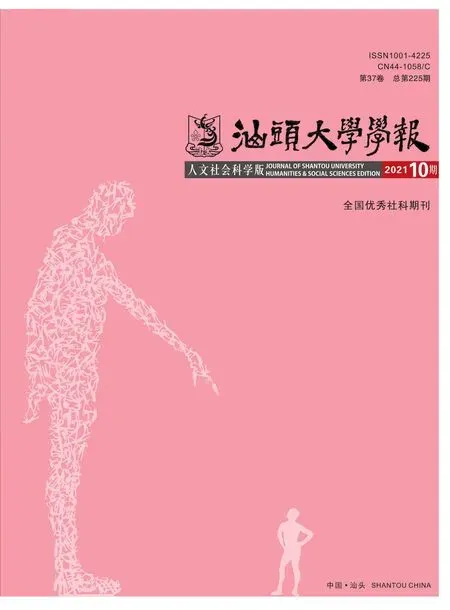人生与世道:嘉道桐城诗人姚柬之及其创作
温世亮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至嘉道朝,感应由盛而衰的时局,一如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所谓“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思为国家致太平”[1],曾盛于明清之际而消弭于清中叶的经世思潮再次兴起。不同于乾嘉时期的诗歌创作,经世思潮或重学问,或重道义,或重性灵,嘉道诗坛的经世之风亦成声势。
姚柬之(1785—1847),字幼榰,号伯山,安徽桐城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先后任河南临漳知县、广东揭阳知县、连州绥猺厅同知,官至贵州大定府知府。姚柬之出生于乾隆末造,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国势渐趋颓靡的嘉道时期度过。同时,姚柬之身为地方官吏,时刻为时政民瘼忧劳,政绩卓著,揭阳知县甚至有“五管贤声第一流”①按:梅曾亮《赠姚伯山》有“五管贤声第一流,头衔新拜主恩忧”句,藉此歌颂其主政揭阳的政绩。见录梅曾亮著,胡晓明、彭国忠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552 页。之誉,厕身《清史稿·循吏传》,堪称嘉道经世士人之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姚柬之出身于桐城麻溪姚氏,曾受知于从祖姚鼐,在诗歌方面亦不乏成就,所作诗既见个性特色,又不乏时代气息,是桐城派晚期的重要作家。正因如此,他在生前便受到张维屏、张际亮、刘开、方东树、姚莹等名流之赞赏,曾燠《题桐城姚伯山柬之燅经堂诗钞即送归里》更是以“今观子作川有源,宗风直溯唐开元”[2]相推许;死后亦不乏褒奖,如《晚晴簃诗汇诗话》称其“诗有雄浑之气,五七言近体尤亮拔不群,寄意深远,一门群从中,与后湘(姚莹)殆如骖靳”[3]。一言以蔽之,在姚氏家族、桐城诗派乃至嘉道诗坛,姚柬之都是值得关注的对象。不过,目前学界对其人其诗的论述几于空白。有鉴于此,本文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诗人的生平境遇,就姚柬之其人、其诗及其诗史意义予以初步讨论。
一、“今古两行泪,乾坤一卷诗”:凄寒的人生心态
姚柬之出身于享誉宇内的文化望族和官宦世家,理应拥有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和仕宦上升空间。然而,一如其《哭阿惪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所云“自我有生来,百事无一欣”[4]卷一,迎接他的却是坎坷曲折的一生。
首先是家难家累频频。据其自传《乐地凡民传》[5]卷六,嘉道时的桐城麻溪姚氏已趋衰落,而柬之出生未三月,即罹失怙之难,自此便与知书达礼的母亲张氏相依为命,在“冬无衾,夏无帐,日一食”的清贫岁月中苦读晨昏,直至成立。而人未及壮,先后有丧母、丧妻之痛;迨及中年,又接连遭受失子之苦。终其一生,凡人世的悲哀痛疾无不备,怎能不凄然于心?也无怪乎他要发出如“既失吾慈亲,又夺余幼冲。我欲乘风去,叩关问穹窿”(《和五月旦日和戴主簿》)[4]卷一这样的凄怨怒诉,指责苍天为事之不公。
其次是仕途偃蹇不达。姚柬之天资聪慧,“四岁能属对,五岁能赋诗”(《乐地凡民传》)[5]卷六,“年十九以冠军补博士弟子员”(《张太宜人六十寿征诗序》)[5]卷六。不过在更高层次的科试中,柬之却屡遭挫折。在如此境况下,饮酒便成为其消解烦忧的最佳选择,即便在殿试前夜亦要痛饮为快。这首题名为《绝酒行》的作品,即其“壬午嘉庆(1822)”“殿试前犹酣饮乃试”的实录,其中有句云:
髯生嗜酒不肯已,犹呼曲生结知己。狂谈之下时作书,往往龙蛇杂蚁蝼。可怜怀抱久不摅,四十昂藏鬓秃矣……[6]
几经落榜后,终于在二十九岁那年成就了柬之的举子梦;又十年,方及进士第。但是,“报国有心悲掣肘,匡时无技且低眉”(《读王阳明瘗旅文有感示诸生》其二)[4]卷七,进士身份并未能真正改变柬之凄恻惨淡的命运。他胸怀大志,然而职小官微,加上耿直的秉性并不为时所容,故时常受到上司的刻意打压,难有权衡大事的机会。为官期间,柬之足迹半天下,为国运奔走四方,疲命于迁谪之途——“之楚、之燕、之晋、之吴、之越,名山大川,江淮河海,无不涉。蛮烟瘴雨,飓风鳄涛,无不耐。猓猡之与居,侏儒之与语,杞菊之为食,又无不处也”(《乐地凡民传》)[5]卷六,只是在受制于人的困境中,即便有天大的本领亦无以施展。志向与现实的反差,势必在诗人的心中激起层层无法平复的涟漪,在衰朽苦痛之余,自将发出“无奈官贫真似水,不能吸水到江南”(《奴归》)[4]卷五、“枉抛心力终何补,坐使萧萧白发生”(《甲午四月初一日发羊城途中登浴日亭寄鹤生》)[4]卷五、“学书学剑两不成,宦海蹉跎已白头”(《答傅青馀孝廉投赠诗即和元韵》)[4]卷五这样的自怜自艾之叹。
他也希望退出官场,归隐林下,却时时虑及沧桑国事,进退难以定夺。不过,终究还是在“负气敢为,大吏寖不悦”[7]的情形下,默念着“浮沉尘网中,一瞬六十秋。既无筮进策,又乏保身谋”(《题扇》)[4]卷二这样的诗句引疾归里,从此开始了他所说的亲近山林而无世俗烦扰的“乐地”生活。只是“请剑除奸前日事,罢官还犊去时恩”(《题姚伯山木叶庵图》其一)[8],清逸的“乐地”生活并未泯灭其心中那颗炽热的报国雄心。
再次则是知音难觅。姚元之为其四十生辰所作的《题红梅》云“千枝破雪独敷荣,不与繁华斗盛名。一种风姿清彻骨,世间惟此足调羹”[6]卷二,将姚柬之比作一枝独秀“清彻骨”的傲雪红梅,评价无疑是准确的。柬之一生坎坷悲戚,但喜言王霸大业,有愤世嫉俗的思想情操,有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亦时常发出刺时忤事之言。在其《伯山文集》中,像《应同》《独断》等关乎政治、漕运、海防等当世事务的篇章,并不鲜见。而在言论尚不自由,士大夫“自屏于政治之外,著书立说,多不涉当世之务”[9]的世风士风面前,这样的为官作风并不容易为人接受,甚至还会受到时人李兆洛《蔬园诗序》所谓的“必迂而摈之,且以为狂怪”[10]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柬之遭此奚落,因恪守经世志向反而被人目为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狂生”,屡见讥于时,即便其友方东树也有过“大言不惭,似李邺侯”(《朝议大夫贵州大定府知府姚君墓志铭》)[11]这样的评价。对此,柬之亦有知己寥寥之叹。其壮年所作的《将进酒》,即是如此心境之反映,诗前小序已说得至为明白:
仆春秋三十有二,以傲见讥于时。而世之好仆之文章者有之,好仆之傲者无有也。阳城张晋题拙集云:“诗有傲骨,笔挟奇气。”奇则仆所不能,傲则仆所不敏也,知音之感不无慨然[4]卷五。
步入晚年后,依然不失被人理解接受的苦恼,《伯山诗集》卷五《赠曾宾谷中丞即题其赏雨茅屋诗后》所云“我生磊落亦如是,负才自觉与人异。词章一事本天来,世俗公卿漫相视。知音自古恒苦少,眼前惟有南丰老。昨者披云见太清,半生慷慨空中埽。呜呼豪杰久消磨,朱门好尚多偏颇。男儿纵有不平气,谁许当筵发浩歌”,其实就是这一心境的自然流露。而《遣闷》所云“惊霜孤雁新依渚,绕树饥鸟旧卜巢。谈笑少年多不识,心情惟有托诗钞”[4]卷五,更是自比“孤雁”“饥鸟”,而“少年多不识”的尴尬,则又是诗人孤寂情怀的最好托化。
面对现实的残酷冷漠,“少小蹉跎老大伤,蟾蜍晓夜促明光。十年意气空湖海,一卷离骚吊楚湘”(《丙子生日有感四首》其一)[4]卷六,于逆境中辗转迁徙的姚柬之,也只好将自己全部的心力倾注到诗歌创作中来,他因此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悲情诗人。不过,内聚着柬之精神意气的诗作,并未能得到全面的保存、流动和传播。虽说在他的生前,友人徐璈便有过“捐赀”为他刊刻诗集的心愿,但终究是无疾而终①笔者按,姚柬之《伯山诗集》卷五《舟中感怀》其九,中有“复闻韩愈欲输金”句,原注:“樗亭欲捐赀刻余诗。”;逝世之后,其子姚世憙抄录存卷欲梓行,大概又是因为资财贫乏,亦未遂;最终赖门人王检心“谨就其家钞”录其“诗若干,分为十卷”,合诗词近一千五百首,方得以行于世,余则“多散失”(王检心《伯山诗集序》)[5]卷首。
“今古两行泪,乾坤一卷诗。”(《题幼榰诗卷》)[12]这是柬之生平知交刘开阅读其诗之后所下的断语。对于柬之这样一个“一身进退都无据,那得心向造物游”(《九日偕友人游古虞书院》)[4]卷七的不平则鸣者而言,刘氏所言无疑是中肯的。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以政治腐化、士习衰朽,以及仕途蹭蹬为背景,《伯山诗集》所透露的类乎融激越、颓唐、迷惘、失落于一体的凄寒怆况的气息亦见浓烈,内中充斥着对个人命运和家国前途的忧虑,成为柬之诗之主旋律。
二、“太息天下事,隐忧如在身”:“伯山诗”之经世表现
张际亮《赠姚伯山柬之大令即送之粤东》中有句云:“词章盖末艺,根本义与仁。处为贞介士,出为经济臣。俯仰千载间,传者惟一真。学道无所得,剽窃皆浮陈。速华实乃堕,流俗不足珍。昔君始释褐,薄宦漳河滨。昨来听父老,去后讴思频。乃知贤母教,为政非因循。以兹溯风雅,若涉知其津。新诗一何高,逸响宛有神。正声郁慷慨,古泽涵渊沦。太息天下事,隐忧如在身。”[13]认为柬之“太息天下事,隐忧如在身”的诗品,源自于其“处为贞介士,出为经济臣”的人品。应该说,这一评价对于解读《伯山诗集》而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柬之少时曾亲炙讲求经济大略的姚骙之门(《与石甫书》)[5]卷五,又深得从祖姚鼐的教益惠泽,更是一个“与民更化”“民服其治”(《清史稿》)的“循吏”,所以崇尚宋学的义理事功之道,便成为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的学术思想的根基所在。如《伯山诗集》卷二《饮酒四首》其二“孔孟不复作,至道那得闻。惟有师我心,先求去扰纷。……汉元牵文义,乱家由太子。贡薛暨匡刘,经生坏国纪。如何圣贤书,乃作富贵饵”,卷四《与光栗原书》“居山泽者,必道德、经济、文章、福泽俱备,始异于村农估客之所为”等,均是重要的佐证。大体而言,这种经世求实的思想反映在诗学上便是对社会功利价值的强调,如《得黄海书却寄以答》“大雅扶轮久不作,输君意气动寥廓。一卷诗成天地秋,中原白日盘鵰鹗”[4]卷五,《赠张宛邻同年》“风雅不再作,苏李开千秋。陈王得风旨,阮籍多离愁。五言盛如斯,匪为章句求。变本自宋人,颜谢导其流。汉道日以微,声病赴节投。岂不极精诣,本意欲矫揉。遂令豪杰士,返始嗟无由”[4]卷二,大抵如此。嘉道时的凋敝四起则为他贯彻自己的诗学理念提供了充分的现实素材,《伯山诗集》也因此有了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
至嘉庆中后期,农民起义、吏治腐败、夷难边患等社会乱象频起,清王朝实际已经进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因此,对底层百姓生活的关注便成为《伯山诗集》的重要内容。作为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生活本来就捉襟见肘,一旦遇到灾年或兵事,其境况就更是苦不堪言了。如此情形在姚柬之的笔下又有如实的反映。卷二《杂诗》其二描绘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及民无所归的惨象,云“大河决豫州,飘没万家室。贫者饥寒哀,富者盖藏失”。卷五《豫州谣》为六首组诗,如诗前小序所谓“古者太史,輶轩采风;今之所职,八股六韵而已。乙亥(1815)之秋,自皖来豫,道路所闻述之为谣,苟有取焉,则彰善瘅恶,亦可补圣化于万一也”,诗人在批判嘉道时期“太史”沉湎于制艺、汲汲于干禄而悖谬于采风以观天下盛衰本质的同时,又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天理教”发生前后的民生。其四《河北民》一首,歌哭百姓受起义军与官军双重屠掠之惨淡,“前邨纷纷呼贼急,后邨攘攘呼贼入。天地黤惨日无光,千门万户皆环泣……贼斫不死官军攫,驱我老弱转沟壑。掳我妻孥恣宴乐,里老吞声不敢云,但嗟不遇杨将军。呜呼,将军奚我后,使我无儿又无妇”;其五《翁无妻》叙述“高禾大芋皆干枯”的灾荒年,饥民不但得不到官府的体恤救济,反而受其变本加厉的盘剥。面对如此境况,他们只好卖衣典食、鬻妻救穷——“夜半虎胥持虎符,搥门大呌来催租”“脱襦换酒衣换菜,虎胥食之追不贷”“夫言鬻汝我不忍,妻言我去君可悯”,这同样是血泪斑斑的现实书写。它如卷三《苦雨》《复雨三首》《晴二首》、卷五《赠李容庵》《书所见》《鱼梁行》等,均为黎庶之苦代言,无不展示民胞物与的哀悯心曲。
柬之诗,不仅聚焦于百姓生活,目光同样触及当时已经糜烂腐朽的官场现实。他在《应同》[5]卷一中指出,在夷氛渐浓的危急时刻,清廷各部门、上下级之间,本应协力同心,方可有效处理纷至沓来的社会问题。但人微言轻的士人,多因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林立的党争而饱尝意志难遂之痛,面对“岛夷肆虐、江介骚然”,只能像圈养于樊笼中被戕杀了性情的仙鹤,除“矫首引吭而唳”“徘徊踯躅,惆怅哀离”(《题周执庵饲鹤图记》)[5]卷六,已别无选择。因此,在他看来自己面对的倒是一个黑白颠倒的宦海。《诗集》卷五《醉时歌》这首为“同岁生袁于谷”而作的七言古诗,先是交代“殷殷如雷,耀耀如雨,索索如树,隆隆如鼓,天示妖祥亦何补”的现实背景,接着借题发挥:
我劝九阍诉忠诚,铜龙詈我为狂生。朝廷衮衮多卿相,尔在荒蛮乘一障。位卑之言不可听,妄将蚁磨测天上。我闻此言泪沾臆,下视九州冥冥黑。天子命我为表率,铜龙叱我为走卒。铜龙铜龙尔形为龙质为铜,风雨暴露不改形,燥湿寒暑不变节。上帝以尔为至精,铸尔作龙守枨闑。尔乃彦圣俾不通,狰狞虎门进谗说。去尔鳞之而刳尔心肺肝,废作云间承露盘。神仙不与尔金丹,化尔为钱品宝货。
尖锐抨击那些独断专横、妄佞阴毒、结党营私、无所作为的官场大佬,寄寓自己对“小人得志,君子道消”现实的怅惘。这与同卷《稚兰同年祷雨立沛甘霖喜而有作》,先以直白的语言描述“做官不肯念民瘼,柄国惟图便己私。所恶坠渊爱加膝,谗谀面谀四面出”的官场丑态后,继以“强将言笑饵贤豪,饿夫不食嗟来食。我生仕宦三十年,百无所恃惟恃天。不合时宜世欲杀,一生惟得穹苍怜”收尾的用意是一致的。而卷八《和平樾峰消寒诗元韵》九首组诗,铺叙面对晚清凋敝衰朽的时局,官员们或不愿作为——“百姓可怜剩皮骨,诸君谁肯奉心肝”,或疲于抵抗——“墨守无人攻有般,猋风掣电势弥漫”,或谋取利禄——“西园钱入即之官,仰屋司农计早殚”,或狡黠庸碌——“如今城社多鼢鼠,不止河沙有射干”,指摘的力度同样尖刻,种种丑陋的吏治形态统摄其中,堪称嘉道官场的现形图。
对鸦片战争前后的文恬武嬉,柬之亦给予尖锐披露,矛头直指那些在国家深处水深火热中却依然蝇营狗苟、荒淫无度而置安危于不顾的统治阶层。《诗集》卷五《闻台湾报捷家弟莹恩赏花翎世职喜而有作却寄石甫》诗,乃因鸦片战争时族弟姚莹驻台湾大胜英国侵略军而作,不仅描述了姚莹“躯干虽小心胆大,驱得鲸鲵上浅濑”的英雄气概,也以主战者的身份辛辣讽刺“何苦低头媚夷鬼”“割地求和起楼台,宁波陆沉乍浦失”的卖国行径,并对“糜烂八都操梃卒,眼前胜负不可知”的现实予以深切忧虑,警醒统治者“小胜尚须防大举,诸君且莫破愁颜”。同卷作于“道光丁未(1847)正月二十八日”的《徐友心通守具舟招余偕退庵司马游灵岩诸胜余腰脚无力不能前往作诗以示退庵》诗,在景崇范仲淹为天下忧的高风后,转笔“武官不肯死疆场,文帅惟知守帷幄”的现实,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而结末“盛衰人事本无常,乐极悲来欲断肠”云云,正是其哀国家之不幸、怒清廷之不争心志的最为直接的表达。
当然,柬之绝非一味地哀悯于社会的衰败、官场的腐烂及时局的不景,他也用诗笔对它们生成的原委予以合理的分析,显示出强烈的社会参与热情。卷二用杜少陵《览元次山舂陵行贼退篇志之》韵而作的《题南山同年黄梅拯溺图》,并未停留于诸如“死者成腐草,生者如晨星”“堂上鬓发白,野外磷火青”此类的百姓困顿生活的正面描写,而是以此为基础引申生发,进而揭示弊病的根源所在——“官无掣肘事,民自尊朝廷。朝廷言治理,州县为长城。州县不敛怨,愚民谁指楹。指楹尚不忍,大厦安能倾”。其实,这与其《书梅伯言记汪刺史事后》所示“官逼民反”思想——“夫民终岁勤动,俯仰不足以事育穷檐陋屋、饥寒交迫,其势不能不为寇。有不为寇者,又迫而必为寇。为寇必死,不为寇亦死,与其束手待死,不如为寇,或幸而不死也。故曰:‘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5]卷六相吻合,站在较为公正的立场看待民反民怨的,而未将犯上作乱之“民”视为寇贼。对于一个封建地主阶层而言,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其“民为邦本”的立场。
“昨日江南卿信到,干戈满眼泪沾衣。”(《答婼话》)[4]卷十作为一个忧心于家国百姓的诗人,对于干戈四起的现实显然是难以接受的。能为民众和社会代言,为国家安危呐喊,这无疑又是柬之苦涩情怀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其诗中最具分量的部分,《伯山诗集》也因此显现清晰的经世面相,它具有的时代认识价值自见分明。明乎此,再回头体会前引张际亮赠诗所谓“太息天下事,隐忧如在身”,其内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自怜豪气三千丈,剩有衰悰满素笺”:现实感应下的审美意蕴
在诗学取向上,姚柬之主张“言之有则”,恪守儒家“美刺”传统,并以学治为一的学术理念运筹诗学,强调情志合一。他在《研雨山房诗钞序》中指出:
诗之作也,其所以导人心之和也乎?人有喜怒哀乐之情,郁焉而未伸,扞格而不达之而为志。歌以永言,夫志者,性情也,《诗》三百篇,诗人性情之流露也,故说诗者,性至焉,情次焉。持其志,无漓其情,言之有则者,斯为美。而才力有丰啬焉,学殖有丰俭焉,而要不失“兴、观、群、怨”之旨[5]卷六。
认为诗是作者内在性情的真实流露,不过“言之有则”,又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有利于世道人心。故对袁枚的性灵说,甚不以为然,称“曩在乾隆、嘉庆间,钱塘袁子才以无则之言倡天下,冠盖之伦,靡然从之,流而为和,怒而为怨,是非不当于人心,粗厉流辟之音作”。而据张维屏《清代诗人谈艺录》记载,对近时黄仲则、朱子颖、张南山、刘孟涂等讲究实学而不事应酬的作者,他却甚为“心折”[14]。
其实,这一观念也贯彻到其创作中。在引疾归里的道光辛丑(1841)年,柬之写有《元夕宴香海棠巢即席留句荷张徐白三君赐和仍用原韵奉答》一首:
潦倒词场四十年,山邱华屋几称先。怀人偶忆欧六一,好句今逢员半千。瘴雨蛮烟写怀抱,镜花水月见心传。自怜豪气三千丈,剩有衰悰满素笺。[4]卷七
显然,这是诗人借诗作不平之鸣的自白语,回首几十年风波不平、堪称潦倒的宦海生涯,心中怎能没有隐痛?而结尾“自怜豪气三千丈,剩有衰悰满素笺”云,则再次向人们证明《伯山诗集》正是诗人哀乐过于人心的产物,饱含着诗人的一往情深。要之,因由现实而生发的情思绵密,确乎成为柬之诗最为突出的艺术形态。至于家难苦累、人事沉浮、时事感伤一类浸润着诗人的血泪辛酸的内容表达,从前文的论述中已足以见出。在此,仅从审美特征这一角度就其诗之现实性做进一步申论。
首先,柬之性情豪爽,嫚志诞言,所为诗表情较为直露,往往给人一种激越奔放、喷薄而出的体会。卷七《连阳江行有作》这首七言律,将自己与刘禹锡、韩愈、苏轼这些曾遭人生困厄的名诗人并论,既表达了自我欣赏这样一层意思,又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个人意愿与现实的乖离,感讽之意极强:
刺连梦得声名早,度岭昌黎性命微。待我后来成鼎足,白头吟望醉望归(原注:“东坡诗有‘头白江南醉司马’,予江南人,故云。”)。
不过,这一特点在他的七言古体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卷五《放歌行》一诗写壮志难遂,时时处处均将情融于笔端。既云“天风吹断银河水,倒灌昆明五百里”的雄奇景观和“我昔骑龙观八荒,手抉浮翳朝天皇”的意气风发,又叙说遭“浮邱拍手訾我狂”屈辱后“有时兴发雷霆吼,少陵谪仙来先后。陈思神力不敢争,退出雄才赠八斗”的愤激落拓神情,想象奇特,由天上而人寰,游走于古今之间,把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事物聚拢一起,为后面“呜呼斯道久沦落,世俗少年喜轻薄。我家惜抱亦孤立,徒有英名动寥廓”情感的进一步抒发张本,与李白诗之想落天外、豪迈张狂,确有几分相似。它如同卷《踏月行》“翻身我欲骑长鲸,携酒如月登帝廷”、《醉时歌》“我生磊落寡俦侣,抉翳而外罕可语”及《醉后放歌别张子佩》“男儿不能马革裹尸疆场死,便合茅蒲袯襫守田里”,或道仕途奔走之艰,或谓知己难觅之苦,或兴失路怅惘之叹,在激越张扬中透露出于现实的体味,与前诗有同工之妙。姚元之谓“伯山亦是今才子,欲学颠狂李谪仙”(《岁暮怀人绝句》其三)[15],由此看来并非虚言。对柬之诗,前人多以“奇”“豪”相称誉,姚莹《哭伯山》称“所著诗文皆有奇气”[16],张维屏跋《伯山诗集》以“豪驱广陵之涛”[4]卷末附录誉,曾燠《题桐城姚伯山柬之燅经堂诗钞即送归里》亦云“浩然高唱落天外,其气千里江全吞”[2],实与其诗依偎融贯现实而富于情感张力,且不加隐饰地宣泄出来的特点相关。至于贬之者,则可能会因此以乖张粗俗相评判,若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便称其“所为诗皆肤廓粗率,仅有腔调,其议论卤莽”[17],盖即缘于此。
其次,《伯山诗集》中尚有不少诗以白描手法来表情达意,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张维屏跋《伯山诗集》所谓“清挹峨嵋之雪”[4]卷末附录之面相。大致又表现为以下几端。一是多将眼前之事与心中之情相勾连,即便是触及景象,也不做刻意的雕琢。卷三《寄桐花阁》:
故乡半轮月,何事到黔阳。照我须眉古,知君心骨凉。添衣清露重。推枕晚花香。相去一万里,空阶自断肠。
此诗抒写浓郁的夫妻相思情,而与诗人流离悲辛、落拓不隅的仕宦际遇似乎又相仿佛,两相穿插。正因如此,虽说是用语简淡而不假修饰,看似日常生活场景的再现,读来却又感人肺腑之深。
二是用典浅切。方东树称柬之“雄文硕学”[11]卷四,不过他并未在用典上炫耀学识,即便用典也是一些浅近通俗的。他喜用王粲、陶潜、嵇康、阮籍、孟郊这类习见的悲戚人事入诗,以寄托自己的满腹辛酸。如卷三《野水》“醉鼓冯暖铗,哀登王粲楼。夜深休画角,鬓短不胜愁”、卷六《和友人述怀原韵四首》“与世无缘奈若何,怜才天上有嫦娥。郁华仙骨同人少,太白诗情谪后多”、卷十《丙申九日将去连山施澄怀仙尉携酒话别即席赋赠》“五日飘蓬亦可哀,重阳不见菊花开。我如彭泽辞官去,君似王宏送酒来”等,像如此用典却不予人陌生感的诗句在《伯山诗集》中,确又是俯拾即是。但是,诗人诸如仕宦升沉、人事消磨之类的苦累,借助它们的运化却得以充分的体现。简言之,用典不仅未使其诗艰涩难读,反而让它有了清新写意的韵味。
三是“和陶诗”的形神兼致。《伯山诗集》卷一存“和陶诗”一百六十余首。大体而言,这些“和陶诗”,其佳处并非因字斟句酌而显示的形似,也不在于那恬淡安闲的色彩,而是王检心序《伯山诗集》所说的“神似”[5]卷首。何以能“神似”,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柬之与陶渊明有着太多的相似遭遇,其诗浸渍了其生命中来自于个人、家庭和国家的酸痛,传达出满贯于心的人生悲情,最终成为其凄寒生活最为集中的投影。如《北风和九日闲居》其一“天风吹湖水,蓦然高如山。升沉固无常,逝者千万年。得势登三天,失路沉九渊。所以古贤人,往往思归田”,看似波澜不惊,但明显是结合自己人生经历与历史时空而给出的理性思考,这无疑最能说尽作者于家国浮沉背景下壮志难遂的一瓣心香。
最后,“伯山诗”有所有景语皆情语的特点。景与情的完美统一,有利于构造意味深长的艺术意境。柬之不仅喜欢将情与事结合起来以强化情感的表现,且喜寄情于景,以凸显其个中情怀。张琦跋《伯山诗集》,称其诗“非复雕青刻翠之技”[4]卷末附录。他笔下的山水景观,并未被给予过多的雕饰,却多见一层浓重的情感色泽。如《弋阳舟中》这首七言绝句,即颇显物我难辨的风神:
夜雨孤篷灯焰青,秋风萧萧水泠泠。金陵北望堪断肠,况复呻吟枕上听[4]卷九。
据作者原注,此诗乃写于“姬患病”“儿新亡”时,诗人之情思,由此可以详见。诗中的景致已经完全为浸淫昼夜而无法消弭的悲情所排遣,无论描绘天雨、行舟,还是书写秋风、江水,均见素淡,不过都因其“断肠”而带上了厚重的人情味。当然,如果说《弋阳舟中》一诗所表现的还只是因接踵而至的家庭变故而引发的哀伤自叹,那么,诸如《伯山诗集》卷八《春泥》“苍雾湿衣春黯淡,黑风吹丝路凄迷”、卷九《将至金陵有怀浦晴田》“菊江枞水两茫茫,回首南云一断肠”、卷十《山行书所见》“纷纷鸥鸟来投渚,孤雁一生飞渡河”等等可以说诗人那种郁于人生凄涩、感于家国破败的凄楚情怀,则显得格外分明,无疑是情景交错、笔致清新的佳句。
凖宜跋《伯山诗集》,有“惊涛怒泷之笔,抑郁不平之气,盖由境遇使然”[4]卷末附录之谓。柬之所为诗,或豪气冲天,或清淡如雪,然“一切景语皆情语”,其诗又多能贴近生平际遇,寄心于言,艺术形式与内在情感相统一,凖宜“境遇”之评,虽说精简,却较为确切地展示了诗人耦合人生经历与历史事实、现实社会的审美情趣。
四、“伯山诗”之诗史意义
“一官万里皆白头,风中飞藿不自由。”[18]这是柬之的同年知交吴振棫《姚伯山同年柬之冷泉图》中的一句,感同身受地描绘了其友人的凄楚人生。如前所论,生活于日趋衰朽凋敝的嘉道之世,生性豪宕却凄怨于人生、仕宦、家国等苦累羁绊的姚柬之,在压抑中确乎用《伯山诗集》寄托了他的全部心魂。大体看来,嘉道时期经世文士那种追求个性的自觉意识与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士人情结在其诗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因此“伯山诗”自有其不可轻忽的诗史意义。
其一,反映了嘉道经世文士的凄苦心态。嘉道时期,政治日益腐化,社会每见凋敝,而随着海外贸易的增多,西方列强的侵犯也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而“无实无用”“唯利是求”的士习,则已然成其大势[19]。在如此时局中,深怀社会担当意识的文士带着明道救世的热情,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趋于高涨,他们胸怀高远,有力挽国家颓废于狂澜的雄心,经世同样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但因掣肘于封建人事之专制或者思想之保守,同时亦如龚自珍《乙酉之际著议第九》所谓“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20],这些经世文士在国家各类事务的处理表决方面所拥有的话语权力却深受束缚。在这样的尴尬处境之中,他们难免要呈现因请缨无门而凄苦失落、压抑无奈的心态,在人事错迕中,也只能诉诸文字予以宣泄。大抵看来,此亦即严迪昌先生所谓,此间“吏治愈趋腐败,人心愈见险恶,才人无所施其志、用其才,类皆以诗为身心所寄、为心血事业的趋势愈见严重”“即使龚自珍的‘箫心剑气’的激荡,也只是痛切地感受自他的前辈的苦郁以及自身的压抑而吹奏出‘万马齐喑’中的一组哀歌”[21],至于龚自珍何以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二百二十)这样的呐喊,若结合当时背景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在这样一个世变趋于急遽的时代,像龚自珍这样的经世人士确又不为少数,他们负重前行,既有求功名以自显的意图,也有为家国浮沉而忧心忡忡,欲挽狂澜于不倒,但又无力为继的窘迫。譬如,与龚自珍同时的桐城派后期诗人方东树,出身儒学世家,深秉经世宏愿,本欲于衰朽的世道中有所作为,却久困于场屋,以幕僚讲习为业以取衣食之资,故今读其诗,往往能从中体会那种感于家国、凄苦无告、志不得伸的复杂心境。如其《幕府》所云“幕府悠优白日残,永怀朝夕送忧端。清霜浅沼层冰薄,粉堞昬鸦暮雨寒。花下图书珠轴贵,戟门风雨酒杯宽。明年又拟栖何处,倚瑟先悲行路难”[11]514,无疑又最能体现其身处如此境况下的个体情怀,沉郁顿挫自成为它的底色。其他如魏源、汤鹏、黄爵滋、姚莹、张际亮、朱琦、贝青乔等名重当下的经世文士,个人的凄苦同样浸渍于他们的歌吟中,终成一时之响。概括而言,这也就是李慈铭《越缦堂诗话》中所说的“亨甫极负时名,诗亦规抚作家,而粗浮浅率,豪无真诣。尔时若汤海秋、朱伯韩、姚石甫、叶润臣所作,大抵相同。时无英雄,遂令此辈掉鞅追逐,声闻过情,良可哂也”[17]1130。
就个体身份而言,柬之是一个频遭家难家累的世家子弟,又属于有抱负、有操守的经世文士,他关注现实民生,批判社会黑暗,有着深厚的家国忧患意识;同时,他还是一个“报国有心悲掣肘”的不遇之士,在其生命历程中,激越的精神与颓唐、迷惘、失落的情绪,始终交织并存。可以说,“伯山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怆况的心绪,或者说凄寒的诗心,与柬之的人生境遇是密切相关的。毋庸置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又代表了嘉道时期那些有见识而想有作为的文士之凄苦无奈的心态。
其二,昭示了桐城派诗学之转向。作为清代重要的文学流派,兴起于清中叶的桐城派不光在古文方面卓有贡献,在诗学上也不乏影响。在诗学方面,受宋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加上身处盛世王朝,以刘大櫆、姚范、姚鼐等人为核心的桐城派诗家,重视“义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多偏重于道德义法的阐扬,在艺术表现方面则以清真雅正为特点,对社会寒凉、现实世态的关注和反映反而有显薄弱,重于“内圣”而弱于“外王”。例如,刘大櫆之诗虽说有“雄豪奥秘”[22]的气度,然于时事的涵容却多有不足;姚范有“凡文字贵持重”[23]之识,所为诗也以“风致清远”[24]见胜;而姚鼐推崇“道与艺合,天与人一”(《敦拙堂诗集序》)[25],与此相应,“诗旨清隽,晚学玉局翁,尤多见道之语”[26]。相较这些前辈诗人之诗,姚柬之的创作固然有其传承的一面,张维屏以“清挹峨嵋之雪”称其诗,大抵即着眼于此;不过,无论从思想内涵还是艺术表现而言,差异也是明显的,不仅人生和世道已成为其书写的重心之一,而且表现了寓含社会情思于豪放的审美姿态,表现了突破流派界限的勇气。当然,以姚柬之为参照,对嘉道桐城派诗人如姚莹、姚元之、方东树、朱琦等经世名士做进一步的考察,同样能从中洞见桐城派诗学前后嬗变的更多史实,藉此而见其嬗变之态势。例如,读姚莹之诗,可时“见忧时之抱”[27];读朱琦之诗,则又可从中体会那“浓厚的诗史特征”[28]。
其三,是晚清经世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感应于时代风云的变幻,“社会参与激情与言关天下社稷的精神,合成了嘉道之际一代士人的文学期待视野”,并终使他们“从拟古复古的泥淖迷雾中走出,而直面社会现实与人生”[29]。他们突破流派界限,以经世为志,以文学为武器,聚合呼应,批判社会黑暗,表达现实关注,经世同样演化为诗坛风潮,朝野共振,所产生的群体效应显于当时,“自来处士横议,不独战国然”,而“道光十五六年后”,“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30]。柬之一生凄楚种身,意志难遂;但他未置身于时局外,一味地作忧生之嗟,世事之忧亦是其生命中的常态,其“伯山诗”亦因此未流于噍杀枯槁,并未步入类乎前朝如明末“竟陵”诗流的深幽孤峭之途。而其中的一些作品不仅在思想上显示出经世风范,在审美表现上亦能铸心魂家国于一炉,或激越奔放,或清新简淡,展露应有的亮点,个性、时代性与艺术性可谓融合无间,内中确乎裹挟着“言关天下社稷”的文学精神,与那种清明广大的“盛世之音”相较,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样的艺术表现虽说仍存儒家“内圣”精神的热度,但显然已不再执拗于文章道德教化功能的创设,也不再拘泥于清俊雍容的儒者气象的形塑,“外王”的气象得以相应凸显。这样的艺术表现也使“伯山诗”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嘉道以返之诗,缺失那种因恪守儒家诗学规范、歌咏王朝太平而呈现的雅正形容,甚至有了“议论鲁莽”而“肤廓粗率”的体态。与此相反,充溢着经世因子的人生情志却显得格外分明,融入时代的印象颇为清晰。
总而言之,“伯山诗”,既是诠释嘉道时期经世文士诗心的重要个案,又是清代桐城诗派乃至于嘉道诗坛创作朝着经世转向的一个重要标识。姚柬之在晚清诗坛的位置毋庸置疑,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诗学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