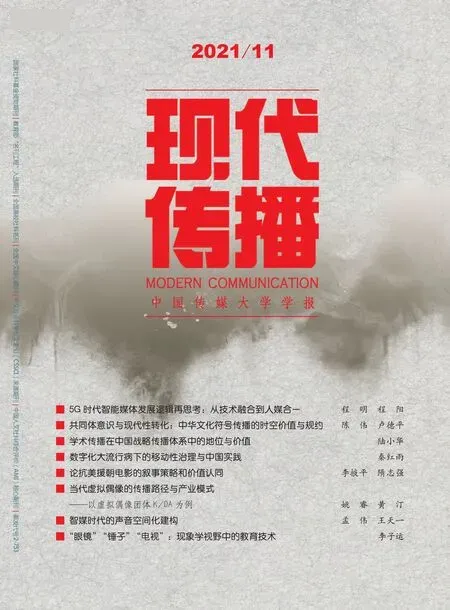论抗美援朝电影的叙事策略和价值认同
■ 李掖平 隋志强
一、引言:问题意识与理论背景
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是我国电影史尤其是战争题材电影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抗美援朝战争至今,以这一题材为叙事主题的电影共计23部,历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高潮和1980年后的低谷,到2020年在后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再现高峰,呈现出一种鲜明的“V”型反转态势。从题材来看,抗美援朝电影虽然多数属于传统革命战争题材,但在70年的时间长河中,单一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伴随着时代与语境的变化生成了丰饶复杂的电影文本,涉及到地面战、空战、雷达战、情报战(谍战)、反特战、后勤补给战、运输战等丰富多样的子题材;从影片类型来看,除传统的战争类型之外,既有反特类型,又有战地爱情类型和较纯粹的战役再现类型,既有宏大叙事的战史类型,也有精准聚焦的小分队作战类型,形成了一种多元化格局;从制作主体来看,虽以传统的国营制片厂制片为主(相对集中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但也有20世纪50年代由多家公私合营和私营公司组建起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制作,改革开放后香港电影人和电影公司的北上制作,以及近年来一些民营企业电影公司的介入和独立制作,代表面较为广泛;从思想导向来看,抗美援朝电影始终与社会发展、时代语境以及观众集体心理需求共律共振,较好地实现了从伦理本位到阶级本位的政治认同(包括阶级对立、民族主义、国族命运、国际主义等),再到向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意识形态责任担当的转型。
面对这一复杂丰富的题材电影谱系,研究者可以选择的研究视角必然是多元的。然而与抗美援朝电影的创作体量、文本的丰富性、文本与时代关系的复杂性相比,有关研究成果却甚少,有许多有意味、有意义的学术课题需要进一步辨析论证。比如,抗美援朝电影表达了怎样的国家属性?其叙事策略的演进呈现出哪些特点?其国族价值认同的重要性何在?对中国战争电影提供了什么镜鉴意义?
一般说来,电影的国家属性及其精神引领作用,都必须经由情感互动的叙事效应方能承载与完成,即让观众在感动、感佩、敬服的情感互动中接受精神引领,实现国家认同(国族价值认同)。从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①这一基础出发,通过情感互动的叙事策略实现价值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国民归属感及为国奉献的心理和行为,是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表现,是国家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②。
抗美援朝电影的国家属性和战争属性,决定了该题材电影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国家形象建构和国家认同机制中,担当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以真实鲜活而又生动深刻的影像方式,艺术化地呈现这场伟大战争历程与情景的抗美援朝电影,较之以往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影片,彰显出其独有的鲜明特征:它同时从国内/国际、当下社会/历史记忆的两个维度上,基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国家认同属性,通过战争集体记忆的书写与想象,询唤、嵌入、重构了新的国族记忆,体现出在证实人民政权的合法性、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以及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有效强化提升了中华民族齐心协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精神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实现广大民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民族形象的国家认同。
二、抗美援朝电影叙事策略的演进
在叙事策略的演进层面,抗美援朝电影体现出从题材叙事到类型叙事的变化。抗美援朝电影的命名来源于多部影片在取材方面的同一性与相似性。从电影类型学的角度,抗美援朝电影绝大多数属于战争类型。中国的类型电影的自觉创作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娱乐片/商业电影的热潮和西方类型电影理论的引入而开始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抗美援朝电影,虽然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类型化元素,但严格说来依旧属于传统的题材叙事,并非真正的类型化影像表达。1992年的《神龙车队》,开始显露出较为鲜明的类型片特征,但直到2016年的《我的战争》,抗美援朝电影的类型化叙事才渐趋成熟。
从1953年《斩断魔爪》到1983年《彩色的夜》,抗美援朝电影的叙事策略主要表现为对单一战争题材的多样化开发。这一时期的抗美援朝电影,虽然都取材于为保家卫国而出兵朝鲜抗击美军的这场战争,但因涉及到丰富复杂而形态多样的不同战役,其题材呈现出多样化趋向。从题材的第一层分类来看,抗美援朝电影分为战争题材、反特题材和后方建设题材,其中讲述战争故事的占比最大,包括《上甘岭》(1956)、《长空比翼》(1958)、《奇袭》(1960)、《烽火列车》(1960)、《英雄坦克手》(1962)、《英雄儿女》(1964)、《打击侵略者》(1965)、《碧海红波》(1975)、《奇袭白虎团》(1972)、《激战无名川》(1975)、《长空雄鹰》(1976)共11部作品;讲述反特故事的有《斩断魔爪》(1954)、《铁道卫士》(1960)、《三八线上》(1960)共3部作品;讲述后方建设故事的最少,只有《慧眼丹心》(1960)1部。
在上述11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故事的影片中,因其战争形态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明显差异,而呈现出子题材(第二层分类)的丰富多样化。从兵种上看,有空战题材,如《长空比翼》和《长空雄鹰》;有坦克战题材,如《英雄坦克手》;有雷达战题材,如《碧海红波》;有侦察作战题材,如《奇袭》《奇袭白虎团》;有交通运输线作战题材,如《烽火列车》《激战无名川》等。而且,这些题材丰富的影片还以区别于以往国内革命战争电影的战斗奇观,如空中作战奇观、坦克作战奇观、雷达侦察奇观、海上作战奇观、游击作战奇观、轰炸与反轰炸的地空战斗奇观、海岛场景奇观等,给观众带来了较强烈的视觉冲击。
在三部讲述反特故事的影片中,也表现出对同一题材进行创新性开发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斩断魔爪》《铁道卫士》和《三八线上》分别表现了后方城市、边境农村和战争前线三种空间内的反特叙事。空间的差异性亦使叙事的行动元产生了较大区别,如《斩断魔爪》是反特题材与工业题材、知识分子题材的结合;《铁道卫士》是反特叙事、抗美援朝叙事和阶级斗争叙事的结合,表现的是乡土空间内以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引领的革命群众(贫下中农和民兵)与地主、反革命分子等阶级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三八线上》则是表现战争僵持阶段中朝军民与美日特务围绕三八线的领土纠纷而展开的反特斗争,具有民族主义叙事特征。正是这种叙事的差异性和丰富性,不断给受众带来新奇的观影感受,较好地满足了受众的期待视野与审美需求。
若以战争类型片的标准予以衡量,这一时期抗美援朝题材电影的战争叙事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如空战电影《长空比翼》虽然通过三场空战构成了故事主体情节和英雄飞行员的个人成长史,在题材上表现出一定的创新性突破,但高潮段落的空战戏并未得到生动逼真的影像呈现,对战斗过程的介绍和战斗结果的宣布,都是通过后方指挥所的即时口头播报间接展现的,使观众对空战场景的观影期待无法实现,进而导致叙事高潮和情感体验高潮的双双落空;再如《英雄坦克手》力图通过坦克外的战斗场景和坦克车内生活场景的双重交织来营造叙事奇观,然而纯粹的坦克作战戏较少,尤其是缺乏敌我双方激烈的坦克对攻场景,严重削弱了在“爽点吸睛”叙事快感引领下而产生的共情律动。更为重要的是,三部反特片在类型叙事层面存在着一个共性问题,即对敌人力量的弱化和对敌人形象的丑化,致使敌我双方高质量的对抗,尤其是智力对抗的紧张与悬疑色彩被冲淡,观众难以体验到玄机重重、惊心动魄的审美快感和叙事认同。这些缺陷不仅影响了抗美援朝电影的叙事效果,甚至引发了此后革命战争电影的一种认同危机,使国内主旋律影片在与境外商业电影和国内娱乐片对观众的争夺中一度处于下风。
1980年代中后期类型电影理论引入国内,引发了以类型化叙事改造传统的革命战争电影的创作热潮,逐渐呈现出从传统的多样化题材叙事,到以满足观众审美期待为诉求的类型叙事的演进轨迹。虽然新时期以来重新讲述抗美援朝故事的电影仅有8部,《神龙车队》(1992)、《铁血大动脉》(1998)、《三八线上的女兵》(2000)、《我的战争》(2016)以及《金刚川》《英雄连》《最可爱的人》(2020)和《长津湖》(2021),但影像表达的创新性拓展与艺术精进却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功融入了以类型叙事重构主旋律电影影像风格的时代潮流,呈现出从类型叙事因素的引入、到标准化类型电影创制、再到实现类型电影叙事中国本土化呈现的三段式发展历程。
《神龙车队》在叙事模式上采用了标准的小分队作战模式,情节的铺衍始终紧扣汽车连的一系列战斗经历,叙事空间从头到尾以汽车行驶为中心,以汽车连十万火急的弹药输送任务、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混乱场景、敌我双方生死博弈的矛盾冲突、车队行进途中不断遭遇的各种险情,形成了单一空间中多样化战斗的影像奇观呈现,小而精的聚焦和一波连着一波的紧张氛围,既巧妙回避了宏大宽泛的战史叙事,又确保了观众情绪的始终在场。按照类型电影的基本套路,片中女记者的采访经历在完成记录报道神龙车队战斗任务的同时,还增添了战地爱情的叙事元素。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在借鉴战争电影类型叙事技巧的同时,有机融合了战争类型、反特类型和公路片类型的多样态叙事特点,有效拓宽了吸引观众观影兴趣的覆盖率,为此后国产革命战争电影的类型化杂糅提供了有益借鉴。
《铁血大动脉》是一部全面反映交通运输线战况的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李奇威将军部署了一整套剿杀战略,对我志愿军公路和铁路运输线展开狂轰滥炸的危机背景之下,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梁军英率领志愿军勇士们,发扬敢打硬仗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在遍布炸弹与地雷的“317”地段抢搭桥梁、抢修铁路、抢运物资,与敌人斗智斗勇生死不惧,建立起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影片将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类型叙事技巧,有机嫁接到宏大叙事的故事主干上,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对主人公梁军英形象的塑造。梁军英的身份是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但影片一开场就是他亲自驾驶列车与敌人军机斗智斗勇的战斗场景,这种行为逻辑虽然与其司令员身份不符,但正是这种传奇色彩特别具有吸引观众的“共情性”。这其实是借鉴了西方战争类型片中个体英雄的塑造方式,以增强观众的情感呼应与认同效果。
《我的战争》则实现了抗美援朝电影在商业大片制作上的突破。从邀请香港类型片导演(彭顺)执导,到全明星演员阵容(刘烨、王珞丹、黄志忠、杨祐宁等),再到引入先进的特效技术和摄影技术(如主观运动长镜头和Gopro拍摄技术),呈现出战争题材商业大片的视听特质。具体到电影叙事层面,抗美援朝题材经过香港类型片导演的改造,标准化的类型叙事特征得以凸显。如对美军强悍战斗力的如实呈现,真实还原了战争的残酷性;如聚焦于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真实处境,回避了恢宏壮观的渲染化战争场景。情节方面,几场相对独立的局部战役,都是按照好莱坞商业电影的特征和观众的观影期待进行剧情和结构设计的。更为创新的是该片采用了战争加爱情的双重叙事策略,对两组男追女式爱情关系以及战争下爱情悲剧的表现更为大胆和直接,有效增强了情绪共振、情感认同的力量。当然,这部影片在类型叙事层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构成情节的几场局部战斗之间,缺少环环相扣的必然联系,致使情节链时陷断裂。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影片以男追女式爱情活动作为贯穿相对独立的多场战斗情节的一条主体线索,然而这种充满巧合、误会甚至具有喜剧效果的爱情戏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战争苦难叙事的悲壮感。
2020年的《金刚川》从战斗形态的递进来看,统一作战的惯常性集体行动,逐渐演化为志愿军个体与美军个体之间的地空对决,个体英雄形象逐渐清晰,广大观众心中渴慕英雄、崇敬英雄的共情体验,被有效引领和汇聚并逐渐进入高潮。从价值观表达层面来看,一方面,影片以志愿军战友之间多重的兄弟情代替了《我的战争》中相对个人化的爱情,生死相托的战友兼兄弟之间的牺牲与复仇构成了强大的叙事动力,更能衬托出战争叙事的残酷与悲壮,更符合真实的战争史实;另一方面,结尾处的反转式叙事技巧更能体现类型叙事与价值观认同相契合的关系,美军用燃烧弹的强力轰炸使大桥化成灰烬,将战场烧成“地狱”,这场围绕金刚川大桥的战斗看似胜败已定,但志愿军硬是以血肉之躯筑起人桥,最终完成了过江作战的任务。正是这种以弱胜强逆转战况的叙事反转,构建起一种酣畅淋漓的审美快感,广大观众被志愿军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和家国情怀所吸引、所打动、所震撼,使影片共情性的情感律动与呼应性的叙事认同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长津湖》则在汲取《我的战争》与《金刚川》的标准化类型叙事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类型叙事的中国化路径,将传统革命战争电影鲜明的民族主义叙事立场、宏大的全景式叙事结构和“沙盘片”式文献记录风格,与商业类型片个体性微观叙事视角、生命伦理情感驱动、战争影像奇观和人道主义价值互融互衬,成功建构起一种商业类型片叙事与新时代主流价值表达有机化合的创新性中国化叙事范式。
三、抗美援朝电影情节模式的多元化探索
在情节模式构建层面,抗美援朝电影主要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铺衍等修辞策略来增强叙事的共情性趣味和意味,以有效提升情绪渲染力和感奋力。这主要表现在抗美援朝电影对“打入”模式(反特片)和小分队作战模式(战争片)的多元化探索。
《斩断魔爪》《铁道卫士》《三八线上》三部反特片的原型故事,其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都是将抗美援朝期间我方对于敌对势力内外勾结行径的怀疑与反击,形象而具体地展示在潜伏特务对新生政权的破坏和军民(警民)合作将其识别并彻底消灭的故事模板中。反特片吸引观众的主要戏码,来自于我方指战员对潜伏特务的识别与消灭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主人公与敌特斗智斗勇;其叙事趣味的精彩之处,是敌我双方人物命运的一波三折和人物情感的起伏跌宕,将诡异的想象、人性的纠结、智慧的较量、吉凶莫测的命运、相互的猜疑与试探、交集的绝望与希望、秘而不宣的残酷厮杀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死博弈等多重元素交织在一起,用悬念引起悬念、以恐怖激起恐怖、从疑局走向疑局,在惊悸、悬疑、传奇、刺激的氛围中,充分展示我方指战员超凡的才华胆识与坚强的不屈意志。
相较之下,《斩断魔爪》和《三八线上》通过弱化敌特力量甚至丑化特务形象的方式,虽然有效凸显了新生政权的伟大、正义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但这种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抗过程几乎毫无悬念,正反人物一出场,我强敌弱的格局就已然奠定,悬疑性、紧张度和揪心效果被严重削弱,正所谓“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致使叙事的趣味性几乎丧失殆尽;而《铁道卫士》则探索运用了“打入”情节模式,以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渲染,获得了悬疑刺激的叙事效果。
“打入”模式在反特片中的故事建构,以“打入”与“反打入”构成基本冲突,既有我方公安或军人为识别和消灭特务而打入敌人内部,亦有敌特打入我方军队或机关中进行潜伏和破坏,敌我双方与忠奸两面既对立又混淆,生存与毁灭、忠诚与背叛、偶然与必然、冒险与刺激、征服与反征服、窥秘与反窥秘、战争局势陡转、政治内幕秘闻、爱恨情仇纠结等内容纵横交错,处处都是陷阱,事事都有玄机,看似不动声色,实则暗潮涌动、万马奔腾。情节推进则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时而一波三折陷入绝境,时而又绝处逢生柳暗花明,有效营造出一种此刻空气高度凝结、下一秒就可能突然爆炸的紧张氛围,牵住观众的眼,抓牢观众的心。影片中的主人公高健,为了弄清敌人的阴谋,冒充已被我方逮捕的特务顾野平,打入敌特内部,一步步探清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并让铁路服务员何兰英充任敌特报务员,掌握了敌人的具体活动计划和全部名单,进而将特务一网打尽。这部影片所探索的“打入”模式,通过英雄人物打入敌人内部的行为,一方面营造出敌我双方相互潜伏、相互防止被识破的叙事紧张感和悬疑性,另一方面成功塑造了一个当时少见的个体式孤胆英雄形象,给观众提供了常规反特片所无法满足的叙事快感,即“打入片在当时找到了一种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上佳方式,其关键在于,既宣传了‘阶级斗争没有熄灭,人民群众要提高警惕’的主流观念,又给个人想象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在想象中容许‘个人奋斗’‘自由选择私人生活方式’等观念在特定条件下暂时存在,从而使个人英雄主义与国家利益得到完美结合”。③
反特片《铁道卫士》所探索的这种“打入”模式,也被一些小分队作战情节模式的抗美援朝战争影片所借鉴,成为其强化叙事趣味共情点和感染力的一大来源。如《奇袭》中志愿军侦察兵小分队,先后化装成美军的巡逻队和李承晚部队伪军伤兵,巧妙通过多道岗哨,打入敌人内部,迅速插至南朝鲜军白虎团团部,趁其开会之际突然开火,击毙白虎团团长,捣毁了该团指挥系统,使部署于周围的南朝鲜军失去指挥,士兵丢弃武器弹药四散奔逃,创造了以超强睿智赢得胜利的战史奇迹;如《英雄坦克手》中志愿军坦克冒充美军坦克,混入敌方部队突袭敌军;《集结号》的抗美援朝段落中,志愿军也是在危难之际急中生智冒充南朝鲜士兵成功闯关,亦是对“打入”情节的复制或致敬。但战争片中的“打入”情节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以智斗形式,为战争片增添了游戏化和浪漫化色彩,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削弱了对抗美援朝战争惨烈性的真实呈现。
小分队作战模式是战争片常见的情节模式,既具有微观叙事的特征,又可以表现双重甚至多重矛盾冲突,一是敌我两方的拼杀博弈即外部矛盾冲突,一是小分队内部成员的差异性及其矛盾冲突。从历时性角度看,抗美援朝战争片中的小分队作战情节模式经历了一个不断拓深创新的构建过程。
在新时期之前抗美援朝电影中的小分队,对外是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战斗集体,对内则是充满战友情谊的“革命家庭”,一般由连长、排长或政委、指导员等人担任爱兵如子并指导战士成长的家长角色。除《英雄坦克手》中的小分队成员之间略有性格、身份的差异之外,其他影片小分队成员间的差异性几乎全部消弭,尤其是对战争的态度都绝对一致,都被塑造成为仿佛生来就渴望打仗并一路英勇无畏的战斗英雄,典型代表就是《上甘岭》中的坑道小分队(八连)。这样的小分队作战模式,由于其内部差异性和矛盾冲突的严重缺失,导致了其戏剧冲突张力的匮乏。
新时期以降,抗美援朝电影中的小分队作战模式,开始在类型电影的启蒙下,大力弥补内部矛盾冲突的缺失,在《神龙车队》《三八线上的女兵》《我的战争》等影片中焕发出生动鲜活的新意与活力。如《神龙车队》中以小分队领袖为代表的个体英雄、国民党降兵为代表的被边缘化的英雄、普通小战士为代表的成长型英雄等组成的英雄群体方阵中的三方参照;如《三八线上的女兵》中以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兵种的各个成员之间,在战争这一极限生存环境下做出不同选择的明显差异互为映衬;《我的战争》和《长津湖》中小分队内部的参差对照则与《神龙车队》相类似,以战斗英雄、老兵与小战士等构成既有矛盾又富有情感的“类家庭”集体关系。这种对小分队成员内部的差异性及其矛盾冲突的呈现,不仅凸显了个体英雄形象的鲜活个性,使广大观众对其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而且因为个体间差异性的存在,使英雄群像洗去了统一的标签化脸谱,其革命情怀通过真实可信的独特人格魅力得以生动诠释和充分敞开,对受众具有更大的激策性和感染力。综上所述,无论是反特片对“打入”模式的探索性建构,还是战争片对小分队作战模式的实践过程,都呈现出一种愈来愈彰显英雄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力量的叙事趋向,从而体现出在集体主义叙事的框架内追求个体价值的创新性表达。而这对引领观众的叙事认同非常重要,因为“在一种集体的氛围中,观众很难对一个抽象的‘集体’产生认同心理,从而容易导致观影过程过于疏离”④。而“打入”模式和成熟的小分队作战模式,由于在集体伦理和国家伦理叙事的缝隙中,既表述了具象的英雄个体面对战争这一生死考验时的内心情感以及信念与抉择,又深入探索了生命个体如何面对死亡这一终极存在命题,这是所有和平时期的观众都能感同身受并能共情呼应,进而实现叙事认同、情感认同、理性认同的根本原因。
四、抗美援朝电影的价值认同路向
如果说,抗美援朝电影建立在情感认同基础之上的叙事认同,成功唤起了广大观众的情感互动,那么在情感互动中,其伦理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等理性指向,方能有效践行于国族民众的行为认同之中。
开抗美援朝电影之先河的《斩断魔爪》以反特叙事,完成了从伦理情感到阶级情感的情感认同和从伦理本位到阶级本位的价值认同的转移。关于伦理本位,梁漱溟从文化、政治、经济等角度全面论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本位特征,他认为:“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何为伦理?伦即伦偶之意,就是说:人与人都在这关系中。……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拟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这种社会可谓伦理本位的社会。”⑤费孝通则以“差序格局”来阐释伦理本位,“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关系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⑥。所以,所谓伦理本位是指伦理关系在人们的各方面社会关系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伦理本体体现出伦理社会的主导原则是情谊而不是法律,而情谊关系是一种具有丰富人情意味的关系。这种人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感情基础而非理性认知。而阶级对立的实质,则是经济利益不同的各对抗阶级或对抗势力之间的斗争,是由人们在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结成的不同关系所决定的,理性认知是其基本支撑。
《斩断魔爪》的特殊之处在于,主人公并不是执行和完成反特任务的公安人员,而是一个被诱惑欺骗而最终醒悟的工程师。通过表现这个旧时代工程师从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情感认同,向工人阶级政治理性认同的逐渐转变,影片提出了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如何由被动地适应到主动“自新”的严肃命题。工程师之所以被骗,是因为国民党特务冒充老友的侄儿,而工程师的醒悟,是在工厂秘书(一个共青团员)和政工干部的帮助下,识破特务的真实身份,完成了知识分子从传统的重“私人情谊”的伦理情感,到“讲政治”和认同工人阶级情感的转变,完成了由伦理本位转向阶级本位的价值认同迁移。
《上甘岭》通过王兰“我的祖国”的歌唱,以抒情蒙太奇方式呈现出一幅祖国河山辽阔壮丽的美好画卷,与上甘岭战役中“失去阵地”“夺回阵地”“固守阵地”和反攻胜利等围绕“阵地”展开的故事情节,共同构成了民族的情感认同和国家的价值认同。《长空比翼》一是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历史逻辑,通过主人公因解放战争中遭遇美机轰炸痛失亲人为复仇而参军,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成为英雄飞行员这一成长过程,完成了对战争正义性即阶级本位下的民族主义表达;二是以伦理情感的认同为中介,通过男女主人公在解放战争中因美机轰炸而离散,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因击败美机而重逢,实现了民族主义认同。《铁道卫士》作为一部反特片,其阶级对立的叙事和阶级情感的动员,较之《斩断魔爪》更为清晰和明确,《斩断魔爪》中的敌人(特务)主要来自于境外派遣和境内的外国教士,而《铁道卫士》的特务则是以境内的阶级敌人为主,如地主、解放前县太爷的女儿、曾在国民党内当过官的车站职员、反动组织“九公道”等与境外敌人(远东情报局)的相互勾结,以形成观众对阶级斗争重要性(阶级对立为主、民族主义为辅)的认同。
抗美援朝电影的国际主义认同策略,也是经由伦理叙事和伦理情感认同方式而实现和升华的。一是以家庭伦理情感表达志愿军战士与朝鲜人民之间的“军民情”,以中朝军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和“鲜血铸成的友谊”,在伦理叙事和伦理情感认同基础之上,实现国际主义的理性价值认同,如抗美援朝电影中常见的阿妈妮角色及其蕴含的“母亲”含义。《奇袭》中朝鲜阿妈妮为掩护救助志愿军战士而牺牲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从而使阿妈妮与志愿军战士形成情感上的母子关系;《烽火列车》朝鲜难民中的阿妈妮被边境上的中国家庭收留后,中国家庭中的儿媳(未婚妻)认阿妈妮为朝鲜妈妈,组成了一个中朝新家庭。由此,母子或母女之间的家庭伦理关系蕴含的情感认同,升华为中朝人民之间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国际主义理性价值认同。
二是以朝鲜百姓家庭的破碎、离散,揭露美国侵略者和南韩军队给朝鲜人民造成的苦难,表现在志愿军帮助下朝鲜家庭的重逢和团圆,歌颂志愿军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以苦难为基调的控诉式伦理叙事,有助于引发国内受众对朝鲜人民悲剧命运的“同情认同”⑦,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性价值认同。如《英雄坦克手》《碧海红波》《长空雄鹰》等,以朝鲜家庭甚至是儿童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建立起了一种同情认同。此外,有的抗美援朝电影还运用了“对立认同”的情感动员策略,即将朝鲜的现实苦难与中国在解放前被侵略的历史苦难进行并置同构,从而产生对共同敌人的仇恨。如《英雄坦克手》开头阿妈妮的家人都死于美军的轰炸,而志愿军的坦克炮长在1947年当工人时被美国水兵打伤过,自己的儿子也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由此生出“帝国主义不消灭,别想过和平日子”的理性认知。同样,《碧海红波》中志愿军小战士的父亲和朝鲜小女孩都是被美军飞机炸死的,由此产生对美军这一共同敌人的仇恨情绪。《三八线上》为了强化对立认同,甚至在抗美援朝题材中塑造了一位狠毒的日本特务角色,他曾是侵华日军中的军官,现在又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将日军这一历史上的敌人塑造为当下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以对立认同实现情感认同和国际主义价值认同。
三是通过确立革命接班人的方式来实现阶级情感认同和阶级本位的价值认同。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英雄儿女》和《打击侵略者》中共同出现的英雄人物与老革命父母的认亲情节。王芳在工人养父的介绍下与革命者生父的相认,身份定位既是工人阶级的女儿又是革命者的女儿,从而确立起一个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形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影片中的认亲情节不仅仅指向了阶级认同,也指涉了国际主义认同。影片通过重新确认老革命的父母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儿女之间的血缘亲情关系,为国内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之间建构了一种历史逻辑,使观众最终认定抗美援朝战争是国内革命战争的某种延续,是阶级对立与国际斗争的结合,是阶级本位下的国际主义精神体现。
这种以伦理叙事和伦理情感认同的方式所实现的价值认同,到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被愈加简单直白的阶级叙事和国际主义标签化叙事所代替。如以对某种革命圣物(道具)的认同代替之前的情感认同,典型案例是《激战无名川》中那把“扳子”,曾经在抗日战场上消灭过日本鬼子的一个装甲营,被尊为革命圣物,又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抢修无名川的重要工具,成为工程兵精神力量的象征物。有的影片甚至直接通过口号式的人物语言来表达国际主义认同,如《碧海红波》中“我们志愿军来到朝鲜,不仅仅是消灭几个美国鬼子,而是要在地球上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度,去建设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长空雄鹰》中“为了天下穷苦人的彻底解放,我们愿把满腔热血撒在蓝天上”等宣誓。
进入新时期之后,抗美援朝电影在价值认同方面逐渐由侧重政治认同向侧重文化认同转变。说到底,民族国家既是“政治—法律”的共同体,更是“历史—文化”的共同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归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文化塑造着国民的特定文化心理,说到底,文化才是民族的“根”和“魂”,国家认同有赖于民众的文化认同即共属一体的文化心理想象⑧。所以,抗美援朝电影根据新时期语境的变化,更重视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来实现国家认同。
与《英雄儿女》《三八线上》《激战无名川》等影片中的战斗英雄,从其父辈老革命者形象和革命圣物所代表的阶级斗争历史中寻求精神资源有所不同,新时期抗美援朝影片中的个体英雄,更注重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寻求精神动力和支撑。如《我的战争》中“老爹”唱着豫剧“穆桂英挂帅”冲上敌阵与敌人决一死战;《金刚川》中“张飞”独自一人面对美军轰炸机时,唱着京剧“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与敌人生死搏斗,为兄弟关磊报仇。在诸如此类的叙事中,影片的叙事文本在角色名字、行为和精神上都与穆桂英、三国英雄等历史文化文本紧密契合为一体。这种文化认同方式,使国家正义和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建立起一种有机链接,较之阶级本位等政治认同,更适合后革命时代的集体意识和观众心理,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和强化了抗美援朝电影的国家认同功能。
注释:
① 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② 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55页。
③ 胡克:《一种反特片模式》,《电影艺术》,1999年第4期,第46页。
④ 龚金平:《在“政治化”与“电影化”之间的艰难抉择——新世纪以来中国战争片的几个新变化》,《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9年第6期,第46页。
⑤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页。
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⑦ 同情认同和对立认同都是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思·伯克提出的内容认同策略之一。其中同情认同指修辞者与受众在态度、思想、价值观等方面相似或相同。对立认同,意为共有反对方而产生的某种凝聚。参见袁影:《肯尼思·伯克的辞格认同观探研》,载胡范铸、林华东主编:《中国修辞》(2014),学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141页。
⑧ 参见吴玉军:《论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