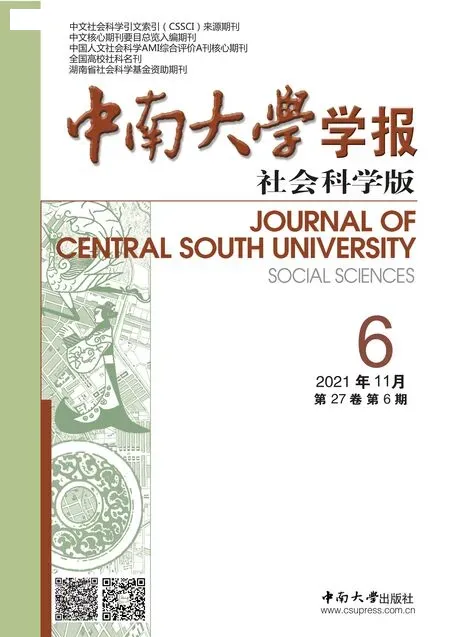王心敬四书学的学术旨趣和义理价值
李敬峰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陕西西安,710119)
明末清初的学术态势由“新安、姚江二派,尚能对垒”[1](482)渐向“学者争以辟陆王为尊朱”[2](95)、“王学为众矢之的”[3](49)转进。在这种学术境遇下,能够毅然以王学自任者,可谓凤毛麟角,而王心敬则是这一孤军薄旅当中的佼佼者。他生于顺治十三年(1656),卒于乾隆三年(1738),字尔缉,号丰川,陕西户县人;年十八,参加岁试,因提学待之无礼,便脱巾帻愤而离开,革去生籍,此后无意功名;年二十五,拜“王学后劲”[3](40)李二曲为师,前后达十余年,学业日粹,声闻日彰,有“天下莫不知丰川”[4](424)之美誉,成为二曲门下最为杰出的弟子。清儒唐鉴说:“关中之学,二曲倡之,丰川继起而振之,与东南学者相应相求,俱不失切近笃实之旨焉。”[5](611)另一儒者孙景烈亦指出:“吾关中自南阿、丰川两先生没后,薪火岌岌不续。”[6](45)由此可见王心敬学术地位之不俗。阁臣朱轼、额伦特、年羹尧、鄂尔泰等迭次举荐于朝,心敬均婉拒不出,但他绝非书斋陋儒,而是极为关心和回应是时愈演愈烈的全国性学术议题——朱、王之争。他沿袭传统学者惯用的方式,即注解四书来表达其理论关怀和现实诉求。在他看来,“四子书虽有朱子《集注》,然亦简约,未尝逐节逐句发挥。初学入门,势不能不资于时下讲义,而讲义却不皆知道之人所为,多是因文衍义,故其意味淡薄,发不尽孔、曾、思、孟原旨”[7](806)。这就是说,朱子注解四书言简意赅,初学者借此难以把握四书要旨,即使那些发挥朱注的讲章亦问题颇多,亦不能抉发原儒精蕴。正是基于这种忧虑,王心敬在应湖北巡抚陈诜之邀赴江汉书院讲学时,专与诸生讲论《四书》。这些讲义后由其长子王功辑录成《江汉书院讲义》,有十卷之多。是书不仅有“皆先儒所未发,人人厌服”[8](3840)之誉,更是清初“尊朱辟王”视域下为数不多的王门四书学注解之作,这两个维度的叠加就使得是书显得颇具学术价值和意义。下面我们就通过王心敬的《江汉书院讲义》这一颇为特殊的个案,兼取心敬其他文集当中关于四书的论述,寻求其四书诠释的义理主旨,探究其如何回应明末清初学界的公共话题“朱、王之争”。同时,也力求透过这一个案来一窥清初阳明心学在全国不同区域的学术样态是否如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同步等质。
一、四书以《大学》为宗
钱穆曾说:“《大学》乃宋明六百年理学家发论依据之中心。”[9](56)此言简明扼要地将《大学》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提揭出来。而这一提揭实则要溯源至朱子,朱子将《大学》在四书中的地位以及四书之间的关系序定得最为清楚,拔擢得亦最高,范导着此后学者对《大学》的认识和定位。朱子说:“《大学》之书,即是圣人做天下根本。”[10](250)“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10](249)朱子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在四书当中,《大学》是纲领,主要讲的是工夫次第,故而在四书当中具有首出的地位。但这“首出”并不是“中心”之意①,只是从为学次序的角度强调它的优先性,以及从功能性的角度凸显它的提纲挈领之意。进一步来讲,朱子认为四书是互补的有机系统,四书因各自特点不同而相应地具有不同的位置。从为学次第的角度讲,朱子设定的是递进之关系;从地位的角度讲,四书是平等并列的。尔后的阳明虽其学问多由《大学》而入,但认为四书是“道同学同”的②。
以朱子、王阳明这两个典范为参照,我们来看一下王心敬在这一问题上的取舍。他沿袭朱子拔擢《大学》的做法,但在具体的缘由和四书关系的设定上则与朱子大相径庭,与阳明亦不相类。王心敬对《大学》的认识是:“《大学》一书,千古圣学之规模局量,千古圣域会归之通衢正路也”[7](692);“《大学》一书,乃吾夫子折中千圣学术以定宗传也”[11](396)。从这些引文中不难看出,王心敬对《大学》的拔擢较之朱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将《大学》提升至“千圣学宗”的境地,也就是学术之宗主的地位,认为《大学》囊括古今学术要旨,奠定古今学术规模,是我们从事孔孟之学必须遵循的范本和规矩,否则就难以登入圣学之堂而落入旁门左道。他更进一步指出:“盖孔子生千圣百王之后,折中千圣百王之道术学术,而融会贯通以示万世也。故学术必衷于孔子,教宗必准乎《大学》,然后范围天地,曲成万物。”[7](617)较之前述,王心敬在此着重强调唯孔子必尊、唯《大学》为宗的必要性。这一方面是对其师李二曲回归原始儒学以救时弊宗旨的承袭,另一方面亦是呼应和融入清初回向原典、回向古代的学术思潮。至此,王心敬已经是史无前例地将《大学》的学术地位推进至无以复加的地位,并将这一主张贯彻到对四书关系的界定上:“《中庸》三十三章,《孟子》七篇,正是《大学》的切注脚”[7](702);“《论语》无一字不表里《大学》……《大学》无一字不会通《论语》”[7](702)。王心敬的意思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大学》一书将圣人之学的宗旨和脉络整全地提揭出来,其他三书《中庸》《孟子》和《论语》不过是各居一偏地对《大学》所昭示的圣学宗旨进行注解而已。这实际上是将《大学》看作其他三书之头脑。王心敬的这种界定与朱子的差异在于:朱子赋予四书不同的学理功能,即“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10](249),这是从为学次第的角度强调了《大学》的首出地位。而王心敬则将《大学》与其他三书看作是整全与一偏的关系,凸显《大学》的宗主和统贯地位。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大学》何以能够统贯三书呢?王心敬在与友人的答问中指出:“千古道脉学脉,只以全体大用,真体实功,一贯不偏为正宗。故举千圣百王之道、《六经》、《四子》之言,无一不会归于此。而惟《大学》一书,则合下包括,更无渗漏。”[7](617)王心敬交代的理由很清楚,那就是六经、四书皆归宗于“全体大用、真体实功”,但只有《大学》完整地涵括这一学术宗旨,不偏不倚,毫无遗漏,其他三书只是“各就其所主明之”[7](746)。因此,《大学》就毫无疑问地具有统摄其他三书的资格,这与朱子之意相差甚大。当然,如此说还流于宽泛,《大学》到底是如何体现王心敬引以为其学术宗旨“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呢?心敬指出:
《大学》明、亲、止善之旨,全体大用,本体工夫,中正圆满,毫无纰漏。学问宗旨至矣尽矣,无以加矣,舍此而标宗立旨,诸儒之胜心也。[7](656)
括之只此“全体大用,真体实工”八字,统之只以明、新、止善三纲。呜呼!《大学》固千圣学宗也。[7](619)
在王心敬看来,《大学》当中的三纲领“明、亲、止善”就是“全体大用、真体实工”,这三句话中正圆满,囊括圣学宗旨,学者只须循此而为,不必另寻它说,否则就是舍大道入小蹊。王心敬这一指陈实际上仍然沿袭了明儒好标宗旨的做法,尤其是从《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中寻一条以之为学术宗旨的做法。演进至王心敬这里,《大学》中能够作为学术宗旨的已经被挖掘殆尽,而王心敬则独辟蹊径,合“三纲领”为一体,将其作为《大学》乃至其本人的学术宗旨。这一方面可从其自述的“我论学宗《大学》明新、止善一贯之宗”[7](898)得到直观的反映,亦可从阮元的“心敬论学以明新止至善为归”[12](210)中得到明确的印证。不唯如此,他甚至指出:“宋、明诸儒之宗无不可用,然究之不外《大学》明、新、止善之旨。”[7](642)那么,何谓“明亲至善”呢?心敬解释道:
人之生也性为主,必明明德,而人之性始尽,《大学》则明明德以止至善之学也;必新民而德之量始满,《大学》则新民以止至善之学也。学而趋会于《大学》之明德,则天德全而会其有极矣。依归于《大学》之新民,则王道备其有极矣。[7](706)
“天德王道”实际上是儒家学派宗旨“内圣外王”的另一视角的表达。王心敬以“天德王道”来解释“明亲至善”,认为只有“明明德”才能最完整地彰显天德,只有“亲民”才能最大程度地昭示王道。也就是说,“明亲至善”就是天德王道达至极致的最好呈现。实际上,王心敬对“天德王道”的推崇是其雅重程颢的一个体现,这可从其注解中高赞程颢“有天德,便可语王道”[13](141)体现出来。要之,王心敬推重《大学》,以其为四书之宗、之首,既不单纯地是朱子为学次序上的优先之意,亦不是阳明的“道同学同”之旨。王心敬以“明亲止善”提领四书,既有对明儒标榜宗旨的沿袭,亦有其本人的创发和超越,显示出其因应时变,抉发四书要旨,重构四书关系以解时弊的学术诉求。
二、会通朱王
“朱、王之争”是明清之际的全国性学术思潮。晚明大儒冯从吾扭转关学旨趣,不仅将关学的主题确立为切入和回应这一全国性议题,更以“会通”而非“尊一辟一”作为回应的基调。后继关学学者延承此旨,清初李二曲以心学为本,兼取朱子,继续回应和强化这一主题,“以致良知为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从视听言动加修。庶内外兼尽,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废。上学下达,一以贯之。故学问两相资则两相成,两相辟则两相病”[14](130)。二曲针对朱子学、阳明心学的各自所长,提出以阳明心学为本体、以程朱理学为工夫的方法,来纠补各自所偏,从而实现相互补救。王心敬接续师说,在解读四书时,不惜笔墨,着意对此问题进行回应。他首先对是时愈演愈烈的门户之争提出自己的看法,“近来学者门户成风,专以口舌议论相尚……如此风尚,甚害学术”[7](473);“门户之争,世儒之隘也;门户之护,世儒之陋也。斯道大公,长短是非自有定理。至当则法,失中则偏。争之固非,护亦未为是也”[7](669)。王心敬“最不喜门户攻击之习”[7](644),故而他对门户之争斥之甚严,认为其妨害学术公正,使人徒耗精力,陷入无谓的口舌之争,于世道无补,于人心无益。在这种学术根底的主导下,他对当时的朱、王之争回应道:
一友问:“今日紫阳、姚江之辨,举世纷纷。平心而论,毕竟其所以优劣者何在?”先生曰:“身立堂上,然后见堂下之得失是非。二先生天上人也,愚昧如余,何能辨之?然窃尝讲读其遗文,穷探其底里。大抵论其立心,皆守先待后之大儒。论其得力,则紫阳学之功勤而密,姚江思之功锐而精。合之皆可入圣;分之各自成家。无紫阳,此道空疏、师心之弊无以救,无姚江,则此道闻见支离之弊无以救也。然学紫阳者,上之固可望于充实光辉,下之亦不失笃学好修之士。学姚江,则得之固可望于明善知性,失且流于专内遗外,甚且流于师心自用。论千古道统,以践履笃实为上;论千古教宗,以流弊轻少为醇,则垂教范世,紫阳固为独优矣。然□此□竟贬姚江为禅宗,而排之不遗余力,亦失三代是非之公耳。”[7](882)
在王心敬看来,朱、王之学各有优长,朱子之学笃实而细密,阳明之学旨远而精深,无论从学于谁,皆有不同之收效。若从垂范后世的角度而言,朱子之学则略胜一筹,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排斥阳明之学,也不意味着王心敬就宗本朱子学。恰恰相反,王心敬亦竭力反驳那种妄议阳明心学的说法:
又有一辈学者,专一贬驳陆王以为近禅。今且无论陆王事功、文章匪禅所有,即其言心性、言立本良知处,禅之说主于离尘超空,以为出世张本,而陆王之旨主于近里务实,以为经世张本。苟有识者参互对质,亦自了然分明,况其宗旨皆渊源于孟子耶,乃忽而不察,但群附而摈之。[7](775)
王心敬的批驳逻辑是这样的:陆王心学源自孟子,而孟子思想纯正无疑,自然陆王心学亦不容质疑。更为重要的是,陆王心学所言的文章、事功皆禅学所无,因此诋毁阳明心学为禅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心敬之论可谓确评。阳明心学在理论形式上确有近禅之处,但无论其内容还是其诉求皆与禅宗有霄壤之别。可以看出,王心敬既不赞成驳朱,亦不赞成辟王,更反对辟王以尊朱,原因在于:“专尊陆王而轻排程朱,是不知工夫外原无本体,不惟不知程朱,并不知陆王;若专尊程朱而轻排陆王,是不知本体外无有工夫,不惟不知陆王,并不知程朱。”[11](360)也就是说,程朱、陆王不能尊其一,废其一,否则是两相不知。既然两者皆不能废弃,那么如何来会通朱、王以消弥他们之间的纷争呢?
王心敬实际上在上述引文中已经表明了他的观点,那就是须从本体、工夫入手来解决这一时代问题。而这一范式并非其独证独创,实则是因循了其师李二曲的“合本体、工夫为一”的范式。他明确指出:“知得本体不离工夫,工夫不离本体,吾辈于程、朱、陆、王正宜兼资,何以爱恶之私轻加排议?……总之,陆王宜补救以平实精密,程朱宜补救以易简疏通。”[7](696)王心敬的意思再清楚不过,那就是陆王之学擅长立本,简易直接,程朱之学优于工夫,切实精密,两者正好相资为用,互相补救。如果说王心敬仅止于此,那不过是拾人牙慧,无甚特色。
王心敬会通朱、王的另一举措就是标举“融以孔孟,准乎《大学》”的学术宗旨。他指出:
今不须论程论朱,较陆较王。只孔孟是吾儒开宗师表,如大家正主,人直奉为正主。程、朱、陆、王则各取其长,融以孔孟,总作分任此家切紧职事之亚旅强以,是为正义。又不须较论“居敬”“存诚”“主静”“穷理”“立大本”“致良知”诸宗主,孰虚孰实,只直以《大学》为功程脉络上可用即用,期于遵守先师已定之宗传,作真学《大学》人,期不负先师真传嫡系是为正分。[7](701-702)
从这段引文中不难看出,王心敬所指的孔就是《大学》所涵具的“全体大用”之旨,而“孟”指的就是:“程朱、陆王不惟相病,正相资也,然终不如以孟子之通通程朱,以孟子之实实陆王,为骨髓通融,元气饱满,不留余毒耳。”[11](389)这就是说孟子所讲的心性本体与工夫之学既可以贯通程朱,亦可以充实陆王。概而言之,王心敬理想的学术形态乃是以孔、曾、思、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它们十分完整地表征了儒家的“全体大用、真体实功”,以它们来矫补、会通程朱、陆王自然再合适不过。心敬这一举措虽然是将程朱、陆王平等对待,但在“近世学者皆讳言陆王”[7](897)的学术境遇下,心敬这种平等视之实则是在提升和拔擢阳明心学,从而与当时清初“由王返朱”的全国性学术思潮拉开距离,呈现出逆潮流而动的学术特质。
三、推重主敬
“主敬”自然是程朱理学的看家工夫,王心敬深受其师李二曲的影响③,对程朱一系的“主敬”工夫青睐有加,将其作为工夫体系中的基础性、根基性范畴看待。他毫不掩饰对“敬”的赞赏和推崇,“千圣万贤发明学术的脉络,总不外一‘敬’字”[7](689),“‘敬’之一字,真合内外,兼精粗,该本末人己,而为圣学成始成终之要义”[7](803)。很明显,王心敬将“敬”视为历代圣贤之学的学术枢纽和脉络,它合内外、兼精粗、该本末、统人己,其地位不可小觑。王心敬对“敬”的定位和拔擢,与程朱之论几乎同出一辙,显示出其对程朱“主敬”学说的服膺和赞赏。这可从其所述的“程朱以居敬穷理立教,自是颠扑不破”[7](656)当中得到直接的印证。
王心敬首先梳理“主敬”工夫的渊源脉络:
“敬”字脉络发源自《帝典》,历禹则祗台,历汤则敬跻,历文武则小心、寅畏、不泄、不忘,迨孔门而脉脉奉为心宗学枢。遂若高曾之规矩,一念一事不容陨越。故程朱表明圣学,遂以居敬穷理示入门要径。然自兹以往,诸儒阐明敬旨愈推愈详。或曰“主一无适”,或曰“常惺惺法”,或曰“其心收拾,不容一物”,至明顾泾阳先生,总而括之曰“不出小心二字”。夫谓“不出‘小心’二字”当矣。[7](690)
王心敬认为“敬”字渊源甚早,早在《尚书》当中就已经出现,后历经先贤弘扬和阐释,逐渐成为儒学的学术枢纽。至程朱则将其提升至为学之要津,尔后诸儒虽不断抉发“敬”的内涵,但尤以顾宪成的“小心”二字解释最为确当。心敬的这种溯源与学术史大致不差,尤其是从尧、舜、禹、汤到程朱、顾宪成对“敬”的不同解释可以看出,“敬”的内涵从最开始的外向性的对象不断地向人的自身、内在转进,尤其是向“心”靠拢。他继续论述道:
心一也,不乱之谓静,不懈之谓敬。[7](712)
心之精神是谓敬。[7](730)
君子之身,天地万物之身也,而统贯者在一心,摄心者在一敬。敬其天地万物之枢纽乎?[7](730)
朱子对“敬”与“心”的关系论述最为详当,他指出,“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10](210)、“敬者一心之主宰”[15](506)、“摄心只是敬”[10](2851),旨在强调“由敬契入,以提撕唤醒心的自存自省”[16](14)。王心敬对“敬”与“心”的把捉基本没有逾越朱子这一规定,意在凸显“敬”在“心”的操存涵养当中的不可替代性。因此,他对顾宪成的以“小心”论“敬”最为赞赏。当然,必须要提及的是,他对“心”与“敬”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亦与其名号有些许联系,他说:“心敬之名,先君所命。余每顾名思义,辄自惕然。先君虽蚤逝,不啻终身耳提而面命。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岂独生育之恩?”[7](662)王心敬并没有简单地把其父赐予的名字当作一个符号,而是身体力行,奉为圭臬。不唯如此,王心敬更加强调“性”与“敬”的关系,他说:
就体统论道论学,则性为道体,敬为学功。就血脉论性论敬,则性即敬体,敬即性功。故舍性而言道者,道非其道;外敬而言学者,学非其学。且即舍性而言敬,是为无米之炊,徒煮空铛;外敬而言性,是为不绁之马,任其奔驰。是则“性”“敬”二字不二视则不得,何者?本体工夫,义原自不同也。不一视又不得,何者?溯其源流本末,实同归而一贯也。然又必有宜知者,道有本原,非可袭取;学有宗要,不容貌求。天命之性,不杂一毫继起之气习者,此乃性之本源,而即道之本源也。存心之敬,一本吾性天之炯照者,此乃敬之宗要,即为学之宗要也。[7](689)
王心敬着重强调了“性”与“敬”的关联,“性”是“敬”的本体,而“敬”则是“性”的工夫。也就是说,他是将“性”与“敬”看作本体与工夫的关系,本体、工夫所具有的那种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模式同样适用于“性”与“敬”。需要注意的是,他特别强调“敬”乃“性”中本有,非从外而得。王心敬的这种界定是朱子所不曾论到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心性原非二物”[7](804)。也就是说,他的思想里融入了阳明心学的元素,将心体与性体等同为一,显示出其调和程朱的学术取向。
而在具体落实“主敬”的工夫时,他提醒学者必须注意两种误区。他指出的第一种误区是:“敬岂是拘苦事?近来一辈学者,每喜舍敬言乐,直是不知敬之真味。然敬原非拘苦事,乐亦岂放诞事?而近来又有一辈学者,往往言敬讳言乐,匪直不知乐,亦直是不知敬耳。”[7](803)王心敬在这段话当中触及的是宋明理学中的核心问题:敬畏与洒落。程颢早就提出“执事须是敬,不可矜持太过”[13](61),要求持敬不能妨碍内心的安乐。而程颐、朱熹则追求“敬畏”的境界,讳言安乐,这就造成二者关系的紧张。后阳明则以“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17](190)对二者进行调和,使其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王心敬既反对“舍敬言乐”,也反对“言敬讳乐”,他认为这二者皆是不知真敬、真乐,正确的方式应该保持两者的“中节”。由此可见,王心敬在这一问题上突显的是阳明心学的学术底蕴。
王心敬提醒学者必须注意的第二种误区是:“为学固以主敬为入门,然须先用明善工夫。明却心之本体,敬之天则,庶几下手时,本体工夫融液浃洽耳。不然徒事主敬,曾无穷理之功,窃恐天则不明,制缚作槁木死灰之心,流于下乘痴禅,终不符主敬真血脉也。”[7](805)王心敬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工夫不能单以主敬为务必,而是必须先明确“心之本体”,主敬工夫才能有个主脑。心敬此意与乃师“识得‘良知’,则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有着落,调理脉息,保养元气,其与治病于标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否则,主敬是谁主敬?穷理是谁穷理?”[14](136)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即“主敬穷理”必须由“良知”“心体”作为头脑,否则“主敬穷理”就会落空,就会茫然无下手处。从王心敬对“主敬”工夫的推崇和阐释来看,他既有对朱子主敬工夫的承袭,亦有对阳明良知本体的采用。换言之,他看重阳明心学的良知所起的头脑性、统领性作用,并以此纠正朱子学的支离之弊;推崇程朱理学的笃实工夫,并以此补阳明心学的空虚不实之病。这就突显了王心敬融会二者的学术取向。
四、王心敬四书学的经学特质
针对晚明以来“离经而讲道”[18](851)所导致的空谈不实、恣意解经和师心自用的不良习气,学者开始积极倡导“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19](193)、“经学即理学”[20](227)、“藏理学于经学”[21](13)等,意在通过“取证于经书”[22](13)的方式来寻求真正的圣人之道。这就在清初形成一股经学复兴的思潮,也就是皮锡瑞所谓的“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23](214)。放置于清初这样的经学脉络中,王心敬四书学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经学特质。
(一)摆落训诂,心解四书
四库馆臣在述及清初学术时说:“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24](132)这一说法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全国性,以王心敬为代表的清初关中学者就游离于这一传统之外。王心敬依然以推阐义理为务,在训解四书时,既不涉名物制度,亦不及字义训诂,直是以开掘经书义理为本。因为在他看来,“解经贵通大义,泥于字句必失正旨也”,[7](390)“读书须知古人命意所在,不可泥文害意”[7](658)。这就是说,读书解经不能泥形逐迹,否则就抓不住圣贤立文之真意。当然,这绝不是说不需要训诂,而是不能本末倒置。他说:“闻见训诂,是借以蓄德明理之事。即以之当学问,而且矜为名高,何异于认张翼门作五凤楼?”[7](771)闻见训诂是为抉发义理服务,绝不能将其当做一门学问,推之过高,终属玩物丧志。那如何算是恰当的读书解经之法呢?心敬指出:“读书却非徒靠训诂,可以明了,要须以反身体验,就正先觉为从入。又必躬行实践,以身证明,然后可以真得诸心。盖四子书与他书不同,原是四圣贤体验心得之言。若行不至,知终不真,故要得理会心得,必以实行为致知第一实法。”[7](629)李二曲曾作《四书反身录》,强调读书贵在验之于心,征之于行。心敬对此赞道:“反身体认之旨,则二曲先生揭之更为明畅。”[7](628)并将其贯彻到对四书的解读上,同样主张读书解经必须反身体验,方能探究到圣人立言之本心。这一主张明显是对关学宗师张载“心解”之法的遥承和落实。
(二)讲义体
讲义体作为一种新的解经体例,兴于宋代,主要是为了适应宋儒义理解经的经学诉求。按照讲授对象的不同,分为经筵讲义、国子学和州学讲义、书院讲义三种[25](63)。前两种讲义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意识形态的味道,主要服务于国家科举考试,而书院讲义则相对自由和灵活,更能彰显学者真实的义理特色和学术旨趣。王心敬的四书注解就是书院讲义的典范,是书采用有问有答的形式,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灵活和自由。一般的章句、集注注经体例往往是在“文本所允许的意义空间之中,阐发自己的理解”[26](57),而讲义体则可以不受一章一句的限制,进行跨章节甚至跨文本的诠释。二是切己和有效。讲义体是传道者与被传道者之间就各自的疑惑、见解进行随问随答的一种形式,往往和讲授双方的生命体验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有鲜活的切己色彩,更可达到治病救人、解惑答疑的目的。也就是所谓的“相见而言,因事发明,则并意思一时传了,书虽言多,其实不尽”[13](26)。
五、结语
回到篇首所预设的问题,从王心敬的四书学所透显的学术旨趣来看,他表面上不持门户,着意会通程朱、陆王,并明确表示自己并非王门中人④,但实则其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阳明心学的理论底色。这既可从同时学者的“原是陆王者”[7](894)、“似得之王阳明”[2](96)的正面评价中得到直接的反映,亦可从张秉直的“尝恨二曲、丰川(王心敬)以陆王之余派煽惑陕右,致令吾乡学者不知程朱的传”[27](4)的反面批评中折射出来。他提出的解决朱王之争的方案,因为与主流的学术格调“由王返朱”格格不入,既没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明显的影响,也未能有效改变阳明心学的颓势,但在相对封闭、远离学术中心的关中地区,则产生了卓绝的影响,这就是前述张秉直所论的“致令吾乡学者不知程朱的传”。换言之,也就是维系了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再来看他所倾力批判的训诂之学,在其去世不久就演进为“乾嘉汉学”,成为一时显学。必须指出的是,正是仰赖于王心敬的这种坚持和努力,“三秦人士不尽汩没于词章记诵者”[28](2),关学并未卷入这一潮流,而是依然保持着独重义理的学术旨趣,以个案的形式佐证了美国学者艾尔曼观察的准确性,那就是乾嘉汉学只是江南一域的学术现象,而非全国性的[29](4-7)。总而言之,王心敬的四书学诠释在清初与那种重视实证的经学诠释的全国性思潮格格不入,与“由王返朱”的学术思潮亦差异甚大,但绝不能以此否定他学术的价值和意义。王心敬的四书学一方面显示出关学特有的保守与开放,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必须注重全国与地域学术间的复杂关系,避免有普遍无特殊、重整体略局部的偏颇,尤其是那种认为阳明心学在清初全国范围内同步等质的观点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注释:
① 厦门大学乐爱国教授对此有详细的辨析。参见:乐爱国.朱子学研究的文本依据:兼评牟宗三所谓“朱子以〈大学〉为中心”.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6):61-66.
② 王阳明说:“自古圣贤因时立教,虽若不同,其用功大指无或少异。……孔子谓‘格致诚正,博文约礼’,曾子谓‘忠恕’,子思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孟子谓‘集义养气,求其放心’,虽若人自为说,有不可强同者,而求其要领归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参见:王阳明.示弟立志说.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59.
③ 李二曲指出:“学固不外乎敬,然敬乃学中一事。”参见:李颙.东林书院会语.张波,点校.李颙集.卷十一.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99.
④ 王心敬自述道:“至于疑我之学是陆王,此则近时学者之习见。”参见:王心敬.姑苏论学.刘宗镐,点校.王心敬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