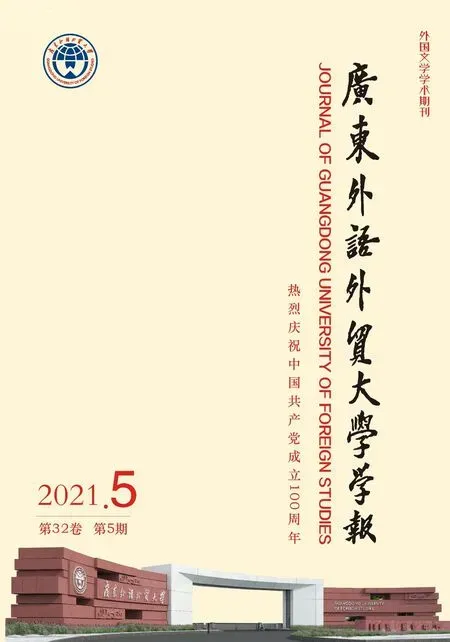西方认知叙事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宋杰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认知科学与叙事学的深度交融,催生了“认知叙事学”这一交叉学科的诞生①,与同一时代发展迅猛的修辞性叙事学和女性主义叙事学并驾齐驱,成为后经典叙事学最为重要的三个分支之一。“认知叙事学”(cognitive narratology)一词最早见于德国叙事学家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发表于《今日诗学》(PoeticsToday)期刊上的“框架、优先选择、解读第三人称叙事:走向认知叙事学”(“Frames, Preferences, and the Reading of Third-Person Narratives: Toward a Cognitive Narratology”,1997)一文中,“认知叙事学”这一概念也正式受到叙事学家的关注。直到2003年,由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主编的《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NarrativeTheoryandtheCognitiveSciences)问世,认知叙事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等用以标志其学科属性的诸多要素才得以渐渐明晰,赫尔曼也由此被视为认知叙事学的领军人物。根据赫尔曼(Herman,2003: 20)的观点,“认知叙事学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它将(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方法与源自认知科学(如心理学、人工智能、心理哲学等)的概念和方法相结合,旨在为从事叙事结构和叙事阐释研究的理论家们所提出的范畴和原则建构一个认知基础”。认知叙事学不同于经典叙事学只重文本的研究特点,也与修辞性叙事学对文本修辞手段和技巧的关注、女性主义叙事学挖掘文本中的性别意蕴不同,着力探讨叙事与思维或心理的关系以及读者的认知过程在叙事理解中的运作方式。这种“关注叙事被感知和被识别时读者的心理过程,而不是语言叙事,尤其是散文叙事的功能分类”(Fludernik & Olson, 2011: 3)的研究方法,决定了认知叙事学的研究基调。通过对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文体学、话语分析、神经科学等学科领域内的资源整合与利用,认知叙事学家将多学科领域内的专业知识用于研究作品的阐释和接受过程,分析文本与读者间的关系,将叙事文本视作读者认知和阅读过程的中间媒介,从而把叙事研究的中心拉回读者本身,不仅体现了较强的跨学科特征,也为当代叙事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
纵观西方认知叙事学研究,大致归为以下三类:第一,各种“世界”理论的涌现。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2018:32)指出,“作品存在就是一个世界”。认知叙事学家利用认知科学的理论资源探索这个世界是如何被建构、如何运转、认知如何在文学世界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等问题。第二,关注真实读者的自然阅读,剖析文学叙事参与者间动态的互动关系。文学叙事交流涉及多个参与者,包括作者、读者、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叙述者、受述者等,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历来就为叙事学家着重关注。认知叙事学家通过读者的心理表征,将叙事交流中的参与者投射到与文本相关的不同阅读位置,并将他们联系起来,形成互动交流。了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认知机制是揭示文学叙事交流活动的必经之路,这也是认知叙事学必须关注个体读者的心理动机、情感反应的重要原因。第三,“认知转向”背景下的情感研究。审美是进行文学阅读的主要动机之一,读者则会在审美过程中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文学阅读的情感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叙事学家的关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文学情感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而且为文学阅读情感体验提供了可行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支持,这也是认知文学研究领域可喜的研究成果和发展方向”(梁福江,2021:78)。因此,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开展对文学的情感研究成为认知叙事学家着力开辟的研究新路径。
世界建构
文学作品从产生一直到为读者品鉴的整个过程涉及多个层面的世界建构,其中有作者在文学创作时建构的世界、叙述者在叙事进程中编织的世界、读者在文学阅读过程中一步步根据文本线索勾勒出的世界。对世界建构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文学创作者的创作意图、作品的叙事结构和技巧、读者对文本解读的方式和机制。“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建构’成为西方人文社科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吸引来自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尚必武,2020:95)。叙事学家也将叙事(包括口头叙事、文字叙事等)视为人们建构世界的重要途径,并致力于探究文学世界建构的叙事方式。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是最早提出“世界建构”这个概念的学者,他在《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WaysofWorldmaking)一书中率先指出世界建构的方式②,为叙事学家研究世界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赫伯特·格拉贝斯(Herbert Grabes)撰文指出世界建构的三种理论模式,分别是“现象学方式、建构主义方式和认知心理学方式”(Grabes, 2010: 47-59)。其中,罗杰·尚克(Roger C. Schank)和罗伯特·阿贝尔森(Robert P. Abelson)通过概念依存理论探究“认知草案”对人类知识结构组织的重要性,是认知心理学用于研究世界建构的成功实践。随着认知科学及相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认知视角下的世界建构研究开始引起叙事学家的关注。认知叙事学中就存在许多用于描写“世界”的概念和理论,例如故事世界(storyworlds)、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文本世界(text worlds)等③。这里的“世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空间,主要指语言或文本的接受者在对话或阅读时建构的心理表征,用以描写对语域文本认知的过程。
故事世界由赫尔曼提出和发展,是其用于研究世界建构方式最重要的观点和方法,成为贯穿其学术研究历程的重要关键词之一。赫尔曼(Herman, 2002: 9)将故事世界定义为“叙事接受者在理解叙事时,被重新定位或作出指示转移的心理模型,即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地点,出于什么原因,同什么人或对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在赫尔曼眼里,故事世界与话语模型这一历来为语言学家所使用的术语多多少少有相似之处。“话语模型可以被定义为心理表征,语言交际者通过心理表征或明或暗地对话语中的情境和事件作出推断”(Herman, 2002: 5)。因此,故事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于理解话语或叙事文本的模型,抑或是称为认知框架,以“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式服务于叙事理解。
在《故事逻辑:叙事的问题与可能性》(StoryLogic:ProblemsandPossibilitiesofNarrative)中,赫尔曼详细探讨了建构故事世界的方式,主要从叙事的微观设计和宏观设计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在微观设计上,赫尔曼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论述:(1)状态、事件和行动:动词在语义层对状态、事件和行动进行编码,不同叙事文类(如史诗、新闻报道、心理小说和鬼故事)在状态、事件和行动上有自身的侧重点,这就是叙事中所谓的“偏好排列”(preference rankings)或“偏好规则”(preference rules);(2)行动表征:通过行为理论学家发展的人类行为模式,来探讨叙事中的行动表征;(3)脚本、序列和故事:借助认知科学中的脚本和图式概念,故事叙述者调动已有的知识表征,尤其是涉及行动和事件的模式化的序列,将行动有组织地、系统地进行叙述;(4)参与者的角色和关系: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和语义学家研究了叙事理解过程中读者、听者和观察者如何对参与者的角色和关系作出推断,发现叙事阐释者将故事世界作了句法分析,认为故事世界由参与者和情境构成;(5)对话和会话风格:故事世界中的参与者通过对话和会话风格完成交流行为,这些行为是叙事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宏观设计上,赫尔曼讨论了以下4个用于建构故事世界的叙事要素:(1)时间性:借鉴“模糊逻辑”的相关研究,赫尔曼提出“多时性”的概念来解释叙事中复杂的“时间倒错”现象,“可以说‘多时性’不仅是故事逻辑中宏观设计的核心因素,还构成了赫尔曼后经典认知叙事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尚广辉,2019:66);(2)空间化:叙事理解需要将故事世界中传达的信息空间化处理或对其进行“认知映射”(cognitively mapping);(3)视角:文本接受者通过叙述者或人物架构的“假定聚焦”(hypothetical focalization)来观察或感知故事世界中的信息④;(4)语境固定:通过叙事话语中的线索,文本接受者在他们所阐释的故事和故事发生的语境之间建立起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语境固定由此具有描述故事与故事阐释者的界面的特征。说到底,语境固定就是旨在说明“故事如何在特定的阐释语境中将自己固定”(Herman, 2002: 337)。
可能世界也是认知叙事学家致力于世界建构的重要维度之一。可能世界这个概念最早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提出,经逻辑语义学家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雅克·欣提卡(Jaakko Hintikka)等人发展为可能世界语义学,形成可能世界理论,最后被文艺学家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Pavel)、卢博米尔·多勒泽尔(Lubomír Doležel)、露丝·罗南(Ruth Ronen)、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等人用于文学研究,以解决文学语言的真值问题、界定文学作品的虚构性、描述虚构世界的内部结构和情节发展。可能世界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现实世界只是众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世界,可能世界是现实世界本可能存在的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世界内的所有事物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文艺理论家借用可能世界理论,把文学叙述作品看作一种由语言建构的特殊的可能世界,提出虚构作品不是现实世界的摹仿或表征,而是现实的一种可能,是具有本体地位的实体,是非真实的可能世界,它与真实世界的关系取决于两者之间的远近距离”(邱蓓,2018:78),可能世界理论为文学研究者探讨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叙事学家,尤其是认知叙事学家推动了可能世界理论的发展,让可能世界理论在叙事的世界建构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瑞安当之无愧是可能世界理论研究领域内最出色的叙事学家之一,她开创性地将人工智能与可能世界理论相结合,用以研究虚构的文学叙事,进一步延伸了叙事研究的跨学科领域。在瑞安(Ryan, 1991: 112-119)看来,虚构世界是由许多文本宇宙构成,文本宇宙包括“真实世界”和“知识世界、知识世界的假设扩展、义务世界、愿望世界、伪装世界、幻想世界”等多个可能世界⑤。瑞安对世界建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借鉴前人对虚构世界的分类基础上⑥,利用人工智能的思想创立了一套叙事嵌构模型,对叙事文本的文类做了更精细的分类。具体而言,瑞安将文本真实世界与真实世界间的可通达关系(accessibility)分为以下9类:属性同一性(identity of properties)、存在物同一性(identity of inventory)、存在物兼容性(compatibility of inventory)、编年兼容性(chronological compatibility)、物理兼容性(physical compatibility)、分类兼容性(taxonomic compatibility)、逻辑兼容性(logical compatibility)、分析兼容性(analytical compatibility)、语言兼容性(linguistic compatibility)(Ryan, 1991: 32-33)。瑞安对世界进行细致的分类,揭示了虚构的叙事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距离和远近关系,为界定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和叙事性、对虚构世界的内部结构和情节发展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也为叙事的世界建构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综合框架。
文学叙事交流
文学叙事交流指的是读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双向互动,历来是叙事学研究的重点。经典叙事学和修辞性叙事学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叙事交流模式进行过深入探讨:经典叙事学研究了其中的叙事结构和叙事语法,修辞性叙事学研究的是文本、读者与作者三者间多层次的交流过程。但是,二者研究的读者都是抽象的、理想化的概念,无法真正考量读者的认知机制、心理动机、情感体验等因素,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学阅读过程的动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尤其是读者的重要地位。而认知叙事学始终强调读者的能动性,关注读者参与文本叙事、建构文本意义的作用,揭示读者阅读活动过程的意义生成机制、背后的认知动力,对经典叙事学和修辞性叙事学在文学叙事交流层面的研究做了补充和延伸。
针对文学叙事交流的研究往往基于文本、读者与作者3个层面,美国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认为叙事交流过程涉及6个参与者: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其中,“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属于文本内部交流成分,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属于文本外参与者”(Chatman, 1978: 151)。叙事交流肇始于真实作者,通过文本信息的单向传递,叙事意义最后被真实读者理解⑦。这一叙事交流模式自创立之初,就广受叙事学界的推崇。但是,该叙事交流模式存在两个局限性:第一,6个叙事交流参与者并未置于同一层面加以对待,过于强调文本内部的交流,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真实读者的参与;第二,叙事呈现出作者到读者的单向流动,读者在这一模式中完全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状态,无法阐释读者与其他叙事参与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此后,众多学者都对查特曼的叙事交流模式作过一定的修正⑧,其中,对认知叙事学家建构叙事交流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与认知叙事学的叙事交流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就是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的读者观。费伦借鉴和发展了彼得·拉比诺维茨(Peter Rabinowitz)的四维度读者观——有血有肉的读者、作者的读者、叙述读者、理想的叙述读者,重点关注有血有肉的读者,认为有血有肉的读者之间在知识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作者的读者和叙述读者的立场⑨。费伦把读者与叙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叙事交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参与,叙事就是读者的动态经验、读者参与的发展进程。
但是,费伦的叙事交流模式依然未跳脱经典叙事学和修辞性叙事学的桎梏,读者依然是抽象概念。有鉴于此,针对文学叙事交流的考察,认知叙事学不仅关注阅读进程中的多层次读者和不同阅读位置的读者在文本内的相互交流,更重要的是,认知叙事学将读者的认知、心理、情感等状态视为影响和决定文学叙事交流是否通达顺畅的重要因素。由保罗·沃斯(Paul Werth)提出和建立、乔安娜·盖文斯(Joanna Gavins)补充和发展的文本世界理论(text world theory)能很好地从认知的角度对文学叙事交流进行解释。文本世界理论“以认知心理学的心理表征和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原则为基础描写人类语言加工过程”(马菊玲,2018:47),其目标是“提供一个语篇框架,研究与情景的、社会的、历史的及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语篇,而这些因素对我们的语言认知起到关键性作用”(Gavins, 2007: 9)。文本世界理论关注语篇交际活动中语篇参与者的知识、经验、动机等认知心理因素,并将语篇交际分为3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层:语篇世界、文本世界、亚世界⑩。根据沃斯的观点,语篇世界是最高的层面,指“言语事件的情景语境”;文本世界指“语篇描述的情景”;亚世界可进一步细分为“指示亚世界、态度亚世界、认识亚世界”(Werth, 1999: 83,87,216-257)。文学叙事交流则在以下2个层面进行:语篇世界和文本世界,前者为叙事交流提供直接语境,后者反映读者对叙事文本的心理表征。
通过文本世界理论,叙事交流过程涉及的参与者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得以明晰: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处于语篇世界中;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分别是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在文本世界的投射体;叙述者是真实作者创造的故事讲述者,受述者是真实读者或隐含读者了解故事内容的中间人,可以说,叙述者和受述者处于文本世界中,架构起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间的桥梁。“叙事交流中的参与者,如作者、读者、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叙述者、受述者等都通过读者的心理表征投射到与文本相关的不同阅读位置,并把他们关联起来形成互动交流,从而产生不同的认知及情感距离”(Chatman, 1978: 71)。阅读活动势必涉及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情感反应等,文本世界理论对阅读过程心理机制的关注和描述有益地弥补了叙事学研究在这一方面的缺憾。认知叙事学家也在文本世界理论的指引下不断挖掘阅读活动的认知机制和情感因素,基于认知视角阐释读者阅读过程的普遍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构,提升了文本性和文本肌理在叙事研究中的地位,进一步彰显了叙事研究的界面性特点。
情感研究
“就文学而言,情感是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渠道,亦是促使读者进行文学阅读的关键因素之一”(黄荷,2020:141)。情感涉及心理和思维,是认知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认知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熊沐清(2019:303)指出,“情感科学与认知科学具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我们可以把‘情感转向’看做‘认知转向’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相关方面,而情感转向引发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是广义的认知文学研究”。纵观认知叙事学领域内针对情感的研究,已逐渐发展得更为系统和全面,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话语体系。
美国叙事学家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Patrick Colm Hogan)是叙事情感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开创了“情感叙事学”(affective narratology)这一建立在认知科学和情感科学基础之上的叙事研究范式。在《情感叙事学:故事的情感结构》(AffectiveNarratology:TheEmotionalStructureofStories)中,霍根开篇就点明了情感与叙事的关系:“人类酷爱情节,这种对情节的酷爱与情节的激情有着密切关系,故事在作者和人物身上体现出情感,也通过故事本身的各种形式在读者或听众那里激发情感”(Hogan, 2011: 1)。他尤其重视故事情节结构与情感系统的关系,在霍根(Hogan, 2011: 158)看来,“具体作品对故事情节的不同安排,以及采用的不同叙事策略,使得故事结构产生差异,从而激发读者对文化历史语境中情感结构特殊性的认识”。故事的情节涉及叙事对时空的组织和建构,霍根的情感叙事学同样关注叙事的时空问题,认为读者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本质上受情感的影响,“叙事时间从根本上说是由情感组织的”(Hogan, 2011: 16),“场所‘存在的’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情感的经验”(Hogan, 2011: 29)。总之,“情感系统为文学题材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原则,就像它们为故事结构和故事的时间成分提供组织原则一样”(Hogan, 2011: 181)。
霍根在伊莲娜·罗施(Eleanor Rosch)原型理论的基础上,以跨文化的视角,从世界不同文化中概括出3种反复出现的普遍叙事原型:浪漫的悲喜剧(romantic tragi-comedy)、英雄的悲喜剧(heroic tragi-comedy)和献祭的悲喜剧(sacrificial tragi-comedy)。“这三种文类占据了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的经典和通俗的叙事”(Hogan, 2003: 185)。霍根认为,“我们不但在确认叙事作品时使用原型,在理解和创造叙事作品时也依赖于原型” (Hogan, 2003: 87)。情感系统为以上3种叙事作品的普遍形式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原则,因为虽然不同地域的人类在情感的体验和认知上存在差异,但是这三种叙事原型都是基于人类普遍的激情原型之上,作者和读者对叙事作品的创作和理解都是激情原型的体现。可以说“典型的叙事作品,包括文学性叙事作品,主要出自原型,显然包括引起激情情境的原型”(Hogan, 2003: 88)。加拿大心理学家凯斯·奥特利(Keith Oatley,1992:201)指出,“当一个人高兴的时候,高兴的记忆就聚集于心中,当一个人悲伤的时候,悲伤的记忆就涌入心里”。对于作者亦是如此,情感体验决定了作者的创作基调,这种情感往往就是激情导致的。不同读者之所以对3种叙事原型能产生情感的共鸣,是因为他们在阅读时产生激情。浪漫的悲喜剧主要讲述情人间的相识、相恋、结合、被迫分离、再结合,对爱情和自由的追求是这一文类的永恒主题;英雄的悲喜剧讲述英雄人物从领袖地位被人篡夺、丧失统治地位,到艰难的斗争和反叛,最后权力得以恢复的人生故事,这一文类通过对背叛、杀戮、死亡等话题的描写,侧面反映了人类自古以来就向往和平和国泰民安;献祭的悲喜剧通常描写的是人类触犯到神灵,因而天降灾害(主要指闹饥荒),人类不得不通过献祭的方式,祈求上天的宽恕,以达成最后的和解,这体现人类对现世安宁的祈求。可以说,这三类作品的主旨均是人物对幸福的追求,虽然对他们而言,幸福的具体内容不一:“献祭的情节涉及食物;英雄的情节涉及王国或民族;浪漫的情节以爱人为对象;三者的原型分别为生理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对象” (Hogan, 2003: 226)。三类作品中都蕴含着人类对幸福的价值取向和永恒追求,极易引发读者的阅读激情和获得读者的青睐,体现了叙事的普遍性,也彰显了认知和心理科学(这里指的是激情理论)对叙事研究,尤其是叙事情感研究的重要性。
“科学和文学理论之间持续不断的渗透在20世纪晚期的文学批评界得到了延续,认知叙事学将阅读理论提高到了理论体系的层面,系统阐释阅读过程中模仿、认同及浸淫等读者反应”(金雯,2015:160)。其中,“移情/共情”(empathy)是重要的叙事情感之一。“移情是一种能力,由于这种能力,人们可以体验他人正在感受(或以往感受)到的感觉、情绪、情感、思想、信念和欲望等,理解他人的行为意图”(Corradini & Antonietti, 2013: 1152)。肖恩·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在“移情、模仿和叙事”(“Empathy, Simulation, and Narrative”)一文中指出,叙事是移情得以发生的条件,并认为,“在他人所处的背景条件下理解他人,即知道了他们的故事,是对他人形成移情态度的基本条件”(Gallagher, 2012: 374)。针对学者在认知叙事学研究中普遍重认知轻情感的现象,苏珊娜·基恩(Suzanne Keen)在“叙事移情理论”(“A Theory of Narrative Empathy”)一文中就指出认知和情感不可分割,“移情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Keen, 2006: 208)。基恩还提出3种类型的叙事移情:读者移情、作者移情和市场移情。读者移情,顾名思义,就是读者对叙事作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作者移情指的是,作者采用一定的叙事策略让读者对作品产生移情效果,因为“很多当代作家认为,通过移情再现,小说可以实现某些事情”(Keen, 2007: 119);市场移情主要考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和图书发行销售对作者叙事移情策略的影响。基恩在另文探讨了叙事移情策略,一反从读者视角切入的做法,另辟蹊径地聚焦作者的叙事移情策略,将作者的移情策略分为三类,即“界域内策略移情、大使级策略移情和散播策略移情”(Keen, 2011: 370-371),以揭示复杂多变的叙事手法是如何引发读者的移情反应,在追求叙事移情策略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探寻叙事移情的普遍规律。
移情能力的发展得益于180万年前人类的“大规模的神经认知进化”(Zunshine, 2006: 7)。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为了在族群部落中生存和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理解他人的行为甚至是心理状态,“心灵阅读”(mind-reading)的能力也逐渐由最初的有意识灌输转变为无意识的运作。阅读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其中也涉及读者“心灵阅读”的认知过程。美国认知叙事学家丽萨·詹塞恩(Lisa Zunshine,2006:4)指出,“小说吸引、戏耍我们心灵阅读的能力,并将这种能力推向可能的极限”,并通过思维理论(Theory of Mind/ToM)建构了她的“心灵阅读”研究范式。思维理论指“关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心灵的科学,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Wilson & Keil, 1999: 838),它和“心灵阅读”都“描述通过思想、情感、信念和欲望解释行为的能力”(Zunshine, 2006: 6)。詹塞恩更是直接将小说比作“一种为了训练读者移情能力而设计的人造认知实验工具”(Zunshine, 2006: 27),因为“我们能够给予由单薄的语言建构的‘人物’以各种思想、情感、欲望的潜能,并且寻找‘线索’,以便我们能够猜到他们的情感,预测他们的行动”(Zunshine, 2006: 10)。其实,“心灵阅读”也得到神经科学的支持,例如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的发现及其相关实证研究佐证了人类可以读懂“他心”(other minds)。“位于大脑皮层,与行动意向、面部识别、体觉加工相关的镜像神经元使得我们不知不觉地抓住他人的意图,了解他人的情绪。由于这些镜像神经元,人类具有了‘读心’能力,即理解他人的意图,产生移情,或感受他人正在产生的体验。这被认为是人类固有的、无意识的、前语言的神经能力”(Pitts-Taylor, 2013: 852-853)。可以说,认知叙事学关于情感的研究已经与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深度交融,足见其浓厚的跨学科特色。
结 语
认知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中的一支主力军,它“试图从新的维度来阐释叙事,打破经典叙事学专注于文本研究的局限,将叙事文本视为读者感知和阅读过程的中间环节,将叙事研究的重心拉回到人本身,更加关注语境和读者,顺应了西方学术发展历程中最新的语境化潮流”(陈礼珍,2020:51)。认知叙事学不但关注作品的阐释和接受过程,而且格外重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认知叙事学注重考察读者的心理表征,认知叙事学家通常称之为世界建构,于是,故事世界、可能世界、文本世界等世界理论被建立,用以深刻阐释读者的认知过程、心理状态和叙事世界中的诸多叙事要素。认知叙事学研究的读者是具有心智功能的真实读者,认知叙事学认为文学叙事交流是语篇多个层面中参与者之间复杂的交流互动,而真实读者的参与是叙事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核心要素,也是语篇意义得以建构的重要保证。此外,认知叙事学尤其关注文学审美的情感体验,力图廓清文学阅读中情感体验发生的基本原则、影响情感效果的相关因素和情感的基本类型,推动了情感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认知叙事学是一门界面特色鲜明的新兴学科,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认知叙事学研究呈现多种理论概念杂糅、多种研究范式并用、多种研究路径交叉的局面,危及这个学科在未来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认知叙事学在之后的发展道路上,应进一步厘清相关术语概念、不同学术流派各自的研究侧重点,注重理论运用和文学批评实践的有机结合,将认知叙事学的理论用于指导叙事文本的解读,以体现认知叙事学的思想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普适性。
注释:
①认知叙事学的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至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罗兰·巴特(Rolland Barthes)对阅读过程中读者的作用与阅读过程的关注,以及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等接受美学研究者对读者反应的研究。
②古德曼在书中明确指出世界建构的5个步骤:组合与分解(composition and decomposition)、强调(weighing)、排序(ordering)、删减和补充(deletion and supplementation)、变形(deformation)。
③针对“文本世界理论”的探讨,详见本文“文学叙事交流”部分。
④关于“假定聚焦”,参见赫尔曼于1994年发表在《叙事》(Narrative)上题为“假定聚焦”(“Hypothetical Focalization”)的论文。
⑤知识世界(knowledge-world)涉及人物的知识、信仰;知识世界的假设扩展(prospective extension of knowledge-worlds)指人物对未来情况的假设;义务世界(obligation-world)指人物根据道德法则应该承担的责任或受到的制约;愿望世界(wish-world)指人物的愿望;伪装世界(pretended worlds)指人物为了欺骗他人而伪造的虚假世界;幻想世界(fantasy-world)由人物的梦想、幻觉和幻想等构成。
⑥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荒诞:一种文学体裁的结构方法》(TheFantastic:AStructuralApproachtoaLiteraryGenre)中,将虚构的叙事世界分为5类:现实世界、奇特世界、奇幻世界、怪诞世界和神奇世界;多琳·迈特尔(Doreen Maitre)在《文学与可能世界》(LiteratureandPossibleWorlds)中,将虚构的叙事世界分为4类:与真实历史事件相关的作品、想象与真实并存的作品、想象与不可能共存的作品、与永不可能实现的事件相关的作品。
⑦具体到文本内部交流,隐含作者以讲述的方式,通过叙述者和受述者向隐含读者传递文本信息。
⑧什洛米斯·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认为叙事交流只涉及真实作者、叙述者、受述者和真实读者,将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排除在叙事交流之外;申丹将6个叙事参与者都纳入叙事文本之内。
⑨理想的叙述读者指的是叙述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完全相信叙述者的所有言辞;叙述读者指的是叙述者为之叙述的想象中的读者,充当叙事世界里的观察者,认为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二者往往难以区分,因此叙事学家们都倾向于略去理想的叙述读者。
⑩由于亚世界是从原来的文本世界中分离出来的,有时依附于文本世界而存在,有时并不附属于文本世界,因此文本世界和亚世界的界限并不明显,概念和性质上存在重叠。于是,盖文斯提出用世界转换和情态世界来代替亚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