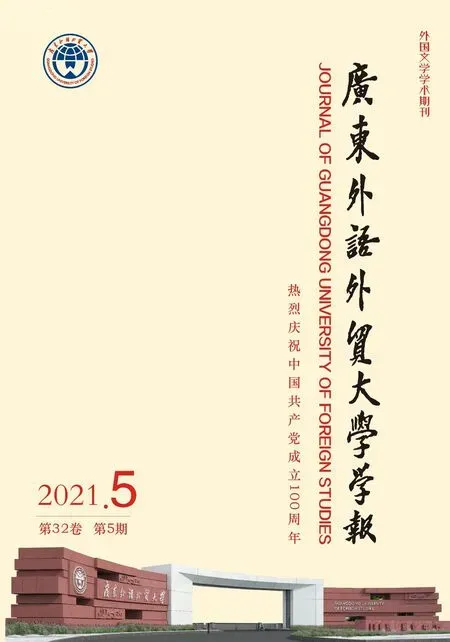18世纪英国旅行文学中的北京: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的逆转
田俊武
引 言
在18世纪之前,英国旅行文学关于北京形象的表征,只有约翰·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而且该书的作者还只是一个“坐在椅子上的旅行家”,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及其首都北京。因此,在旅行文学创作和北京形象表征方面,18世纪之前的英国远远落后于意大利、葡萄牙等其他欧洲国家。但自18世纪以后,情形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一跃成为欧洲的工业和殖民主义强国。出于对华贸易的需要,英国开始接触和了解中国,并由此在英国兴起了一股“中国风”,即研究中国的热潮。在盛赞中国的同时,处于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英国人也敏锐地发现远在东方的中华帝国的腐朽性和停滞性。英国人关于北京形象的乌托邦赞誉和反乌托邦批评,具体表现在约翰·贝尔和丹尼尔·笛福关于北京形象截然相反的表征之中。马戛尔尼使团的北京之行,则将北京作为一个异托邦衰败帝都的形象传播到整个世界。每一次政治旅行和精神旅行,无不是对原有认识的反思和对先前创作的突破(宁慧霞,2016:59)。18世纪英国旅行文学中北京形象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的逆转,正是如此。
英国人关于北京的真实表征:《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记》
约翰·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曾模仿贺拉斯的格言“No man just happens to go to Corinth”开了句玩笑:“It is the lot few to go to Pekin”(Reed,etal., 2007:158)。这句玩笑的意思是,“有幸去过北京的人真是寥寥无几”。的确,在马戛尔尼使团到访北京之前,几乎没有英国人真正到过北京,有据可查并留下关于北京旅行见闻的第一个英国人当属约翰·贝尔。英国当代历史学家詹姆斯·马歇尔指出,“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并非是来到北京或者甚至是描写它的第一批英国公民。这个荣誉应归于一个叫约翰·贝尔的苏格兰人……”(Marshall & Williams,1982:83)。
约翰·贝尔(John Bell,1691-1780)系苏格兰人,曾经到过俄国的圣彼得堡,担任俄国驻波斯大使亚特米·沃林斯基的医生。得知俄国将派使团访华的消息后,贝尔毅然申请随团访华。俄国使团于1720年9月抵达北京,于1721年3月离开,总计在中国停留6个月,其中3个半月住在北京。3个半月的时间使贝尔对北京的方方面面都有系统了解。贝尔的北京游记,比起以前欧洲人所写的游记,更具客观性和真实性。在游记的前言里,贝尔(Bell,1763:xiv-xv)写到:“大体而言,我所呈现给大家的是当时那些值得观看的场景,而没有用旅行者惯常的夸张和捏造事实来美化它们”。在游记中,贝尔对北京的市民、建筑景观等做了详细描述。
城市是由市民构成的。“市民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市民可包含有特殊性质之经济利害关系的各个阶层。因此,市民并非一元的:富裕市民与贫困市民、企业家和手工业者同样可称为市民。其次,就政治意义而言,市民包括享有特定政治权利的所有国民。最后,就身份的意义而言,市民是指官僚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外有财产与有教养的社会阶层,包括企业者、坐食者、有学院教养以及一般文化、有一定阶级生活标准与一定社会威望的人”(韦伯,2004:262)。按照这种分类标准,居住在北京的清政府官员、商人、手工业者、卖艺人、妓女、乞丐等,都属于当时的北京市民。“市民自身特点的普遍存在和行动方式”(格拉夫梅耶夫,2005:8)构成城市的人格。在通往北京的旅行途中以及在北京旅居的岁月中,首先给贝尔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身居北京的清政府官员,包括康熙皇帝、各级大臣以及太监。使团入京后遇到的第一位官员是礼部尚书,他温文尔雅的举止以及对传教士的友好态度,给贝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太监是指中国古代被阉割生殖器、失去性能力并专职伺候皇室人员的男性,他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总体上丑恶和不受欢迎。但是在贝尔的笔下,那些太监不仅心理健康,而且还自制珐琅金表、气枪等礼物送给使团成员。“这个太监是皇帝最喜欢的人。由于他很精通数学和机械知识,他给公使赠送了自制的珐琅金表、气枪”(Bell,1763:15)。在清政府的所有人中,给贝尔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康熙皇帝(1654-1722)。虽然在俄国使团访问北京时康熙已经步入人生暮年,但是他仍然勤于朝政,日理万机。康熙对俄国使团的来访极为重视,曾经亲自接见他们8次,其中3次还是微服私下接见。在接见俄国使团的整个过程中,康熙帝不仅准时到达,而且还善意地要求使团成员不必过于拘泥礼节。对于康熙帝的勤政和亲善,贝尔(Bell,1763:46)做了这样的评价:“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位衰老的君主和蔼可亲之处。虽然他已经在位60年,年龄接近70岁,但是他看起来似乎比他的儿子们还生机勃勃,保持着完整的辨别力和明智的判断力”。
其次,北京的居民、街道、店铺、建筑以及文化娱乐也给贝尔留下深刻印象。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贝尔看见城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走向街头围观他们这些外国人,还有好多妇女躲在自家的窗户后面偷看他们。这一情景让贝尔感觉北京人具有好奇心。当近距离跟北京人谈话的时候,贝尔发现北京人的谈话声音很小,很少具有大声争吵的现象发生。北京的女人也给贝尔留下美好的印象,以至于他在谈论她们的时候按捺不住欣赏的情感:“我要专门谈谈那些女士们,除了相貌的美丽以外她们还具有良好的品质。她们非常爱干净,穿着很端庄。她们的眼睛是黑色的,但是有些小,当她们微笑的时候,就几乎看不见眼睛了。她们的头发乌黑如碳,整洁地挽成辫子,盘在头上,她们还自己在辫子上扎些花,用作装饰”(Bell,1763:106)。关于北京人的总体形象,贝尔评价很高,称他们是“文明好客,对客人和陌生人都非常热情周到。他们的行为习俗非常正常,尊敬长辈,尤其是他们的父母,对各个社会等级的女性也体面对待。这样的行为应该值得学习和称赞”(Bell,1763:103-104)。
凯文·林奇(1990:1)认为,“城市与建筑一样,都是空间结构,但尺度巨大,需要有很长的时间跨度使人们感受。城市设计是与时间有关的艺术,但又难于运用类似音乐那样的时效艺术所具有的能控制的进行序列。因为在不同的时刻,对于不同的人,城市的序列会发生变化,受到干扰,被放弃乃至被切断”。在贝尔看来,北京城很大。他从北门出发,向东走到北门城墙的尽头,然后沿着东门城墙走遍北京城的4个城门,这一旅程花费了他两个半小时。如果骑马将北京城走一遍,至少也得用5个小时。北京的街道宽敞整洁,城墙高大威严。皇帝的金銮殿,是北京城内所有建筑中最大的一个。“大殿占据了很大的地方,四面为高高的砖墙所围。有几排房子供官员和仆人所住,这些房子都非常高大,房顶是黄色的琉璃瓦,在太阳照耀下发出金色的光。大殿的北部是一条河,错落有致,皇家人员经常在这里钓鱼。这条河是人工开掘的,挖出的泥土堆成高高的河岸,站在上面可以观看北京全城以及周边的郊区”(Bell,1763:52)。在北京郊外的所有建筑中,给贝尔印象最深的是长城。“我认为,世界上除了中国人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造出如此巨大的工程。尽管有些王国也可以招募一些工匠造出一些工程,但是如此巨大的工程非聪明、细心、勤俭的中国人莫属,他们能在如此庞杂多元中保持秩序,而且有耐心承受这一巨大工程带来的痛苦。这一巨大的工程,如果不是世界最伟大的,至少也是世界的奇迹之一”(Bell, 1763:90)。
但是,贝尔的北京见闻也并非总是美好的,即使贝尔并没有对这些否面形象进行严词批判。对于北京人吃虱子,贝尔的态度总体上是善意的暗讽:“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我遇到一个老乞丐,从他的破烂的衣服里摸出一些虱子,放到嘴里。这种习俗在这类人身上似乎非常普遍。当中国人跟鞑靼人争吵的时候,鞑靼人作为反击,就称呼中国人为吃虱子的人”(Bell, 1763:48)。对北京人的弃婴现象,贝尔使用了“震惊”和“有违常理”的字眼:“然而,我必须说说一种令人震惊且有违常理的现象,这种现象居然出现在如此管理有序的中国。我指的是把许多刚出生的婴儿抛弃街头”(Bell, 1763:105)。
虚构的游记和关于北京的想象性批评:《鲁滨逊历险记续集》
尽管贝尔的游记被誉为近代英国关于北京形象表征的第一部游记,由于它是在作者出访北京40年后出版的,在时间方面就具有某种程度的滞后性。事实上,若从出版时间考虑,近代英国关于北京形象表征的第一部旅行文学作品应该是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历险记续集》。该书出版于1719年,比贝尔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记》早了40多年。在笛福所生活的时代,英国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正在成长为一个近代化、理性化和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走向对外扩张和殖民的道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昔日在欧洲人心目中作为“帝王之城”“天城”“希望之城”和“圣城”等形象出现的北京,开始成为英国人质疑和批判的靶子。这一批判声音一方面源于英国作为一个西方新兴的、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对昔日的东方帝国的凝视和挑战,另一方面也源于当时欧洲旅行文学中某些对北京的负面描写。例如葡萄牙耶稣会士弗朗西斯克·皮门特尔(Fransisco Pimentel,1629-1675)曾随使团到北京晋见清朝皇帝。在北京羁留3年之后,皮门特尔以愤懑的心情和写实的手法报道了他在北京的旅行见闻,首次以全景式的西方视角将北京描绘成一个寒冷、尘土飞扬、昆虫肆虐、饮食不讲卫生、建筑低矮以及丝毫无法与欧洲的大城市相提并论的负面帝都形象。受欧洲旅行文学中关于中国和北京负面书写的影响,曾经以《鲁宾逊漂流记》而闻名世界的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13),又相继创作出了《鲁滨逊历险记续集》(FartherAdventuresofRobinsonCrusoe, 1719),其中某些章节表现了主人公鲁滨逊在中国北京等地的旅行和见闻。
鲁滨逊在北京旅居4个月,这期间他观看了北京的哪些景致,都干了些什么,书中一概没写。我们看不到鲁滨逊参观游览北京的帝王宫殿,欣赏北京的园林和器物,品尝北京的食品佳肴,观赏北京的戏剧演出。笛福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北京正处于康熙盛世时期,物华天宝,繁荣昌盛,为什么鲁滨逊竟然视而不见?从他关于北京的有限描述看,读者们只知道他在北京期间主要是做生意,临离开前雇佣18匹骆驼来装运货物。即使是关于长城的描写,也是在鲁滨逊一行出北京赴俄国的途中顺便捎带进行的。“两天以后,我们走过了中国的长城,这是阻隔鞑靼人的一种防御建筑,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上”(笛福,1998:557)。这算是鲁滨逊对北京建筑的唯一一次正面描写了。在赞美了几句长城的伟大之后,鲁滨逊马上就以理性乃至功利主义的角度对长城进行吹毛求疵:用9个连的英国坑道兵,不出10天就能整垮这道城墙,或者把它炸得灰飞烟灭。“这道城墙只能抵御鞑靼人,除此之外就一无用处”(笛福,1998:557)。
为什么笛福让鲁滨逊来到了北京却没有描述他在繁华帝都的游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笛福没有到过中国,没有到过北京,因此无法凭想象对北京的建筑、景观、社会习俗、居民形象进行真实的表征。关于这一点,笛福本人也意识到了,因此,在《鲁滨逊历险记续集》中,笛福只能以主人公鲁滨逊的笔记本在旅行途中落水霉烂导致行程资料丢失进行搪塞:“有一回涉水过河时,马一个失足,使我‘离开了那里’……让我落了水。那里的水不深,但我还是弄得浑身湿透。现在我提这件事,是因为这一来,我的笔记本就遭了殃,而那本子上我记着一些应该记住的人名和地名,而事后对那笔记本又没有好好收拾补救,结果那些纸页都霉烂了,弄得上面的字后来都无法辨认了,于是,我也就叫不出这次旅行中到过的一些地方,这实在是我的一大损失”(笛福,1998:550-551)。
那么即使是丢失了在北京游历的资料,为什么笛福又要执意抹黑中国及其帝都北京呢?笛福对中国和北京的恶意批评,甚至连翻译这本书的林纾都看不下去了,他写道:“此书在1765年时所言中国事情,历历如绘。余译至此,愤极,欲岁裂其书,掷去笔砚矣。乃又固告余曰:‘先生勿怒,正不妨一一译之,令我同胞所丑耻,努力于自强,以雪此耻’”(林纾,1960:56)。笛福游记批评中国及帝都北京,顺应了前现代游记文学的创作趋势。苏珊·桑塔格(2004:326)指出,“有关异域的游记总是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其中,“‘我们文明,他们野蛮’,是前现代游记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主题”。因此,笛福在鲁滨逊游记续篇中把中国及帝都北京与英国对立起来进行批判继承了前现代游记文学的主题特征。但是,问题并非这种主题的继承那么简单。笛福在游记续篇中丑化中国及帝都北京,既反映了那个时代英国人关于中国形象集体想象的转向,又反映了笛福本人的思想观。由于在宗教信仰方面反对英国国教,与罗马天主教会形同水火,笛福自然对天主教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及其首都北京的溢美之词具有天然的抵触情绪,故意取其批评中国之语而舍弃其赞美中国之意。作为重商主义的鼓吹者,笛福主张国家的发展和强盛取决于工商业的发展和对外的市场扩张,因此对中国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自然没有好感。
关于北京形象的异托邦表征:马戛尔尼使团游记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1793-1794)是18世纪中英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其访华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英中贸易摩擦、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和挣得“治外法权”。马戛尔尼使团的主要成员有全权特使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3-1806)、副使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1737-1801)、总管约翰·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等共计800余人。为了取悦中国皇帝,使团精心挑选了代表当时英国先进科技水平的礼物600余件,例如榴弹炮、毛瑟枪、望远镜、地球仪等,整整装满了两只船。使团成员于1792年9月26日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出发,于1793年8月5日抵达天津大沽港口,整个旅程花费了9个多月。闻悉英国使团要出访北京的消息后,中国的乾隆皇帝也予以高度重视,像当年的康熙皇帝接待俄国使团那样,责令沿途各地官员予以热情招待。然而,这次精心准备的北京之行并没有达到英国政府预期的目的。从使团成员抵达天津大沽港口那一天起,摩擦就接踵而至,终极原因还在于清政府的妄自尊大和闭关自守方面。中国官员对待英国使团的态度,仍像对待周边藩属国的态度那样,将运送使团成员和礼品的中国帆船插上“英吉利贡船”的旗帜标志,给人一种英国是来向大清王朝进行朝贡的印象,这使得使团特使马戛尔尼非常不悦。后来,围绕着英国使团要不要向乾隆皇帝行三拜九叩之礼的礼仪问题,中英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马戛尔尼认为英国使团向中国皇帝行三拜九叩之礼有辱大英帝国的尊严,反对清朝官员将英国视为藩属国的思想意识,坚持按觐见英国女王的礼节来觐见乾隆皇帝。虽然礼仪之争最终以双方的相互让步达到某种和解,但是在涉及此次出访北京的实质问题时,马戛尔尼使团的谈判使命无功而终。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使团提出的开放通商口岸的要求,责令英国使团马上离开中国。正如该使团的一位随员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佩雷菲特,1993:340)。
马戛尔尼使团的北京之行虽然无功而返,但是使团成员们根据北京之行和见闻而创作的游记文学作品却相当丰富。其中,约翰·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AuthenticAccountofanEmbassyfromtheKingofGreatBritaintotheEmperorofChina, 1797)被认为是此次使团访华的官方版本;约翰·巴罗的《我看乾隆盛世》(TravelinChina,1804),是对北京及中国批评最为严厉的游记之一。这些游记作品从建筑景观、人口风貌、政治宗教等方面对北京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表征。由于马戛尔尼使团是带着怒气返回英国的,他们关于北京的形象就基本是负面的。正如使团特使马戛尔尼在离开中国前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在过去的150 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Tuck,1962:212)。正是基于这种关于中国的总体印象,使团成员们在旅行文学中所表征的北京形象基本上也是没落的,虽然在局部方面他们也赞美北京的某些好的地方。
异托邦的北京首先表现在其建筑景观方面。虽然斯当东一行是英国使团成员,但是在他们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刻起,他们首先也是旅行者,而旅行者的一个显著的身份特征就是将“自我”和异域的“他者”进行区分。就城市建筑景观而言,同一座城市在旅行者和原住民的眼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正如巴柔(2001:121)所言,“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此相比的此在的意识”。在进入北京城之前,使团副使斯当东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据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距离越近,心里越急于想看看它到底什么样子”。穿过北京郊区,斯当东一行终于进到北京城内,看到了最具北京建筑景观标志的城墙。此时的斯当东,对北京城墙的看法还算客观。随着旅行的脚步渐次深入北京的腹地,斯当东(1963:312)开始将北京的建筑景观与欧洲城市进行比较:“初进北京大门,第一个印象是它同欧洲城市相反:这里街道有一百呎宽,但两边房屋绝大部分是平房,欧洲城市街道很窄,但房子很高……北京街道都是土路,需要经常洒水以免尘土飞扬”(斯当东,1963:313)。虽然此时的北京城在斯当东看来在建筑设施方面已经落后于欧洲了,但这还没有过多地影响到他对北京城的总体评价。除了北京的高大城墙和宽敞的街道外,北京的牌楼、黄墙、圆明园别墅等建筑景观都给斯当东留下深刻印象。福柯认为,异托邦最古老的例子就是花园。花园在北京这样一个封建帝都,自然是少不了的存在。在18世纪的北京,最大的花园自然是紫禁城和圆明园了。紫禁城周围虽然是尘土飞扬的鞑靼人生活区,但内部却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仙境。“皇宫之内却似乎是天造地设的另一个天地。里面的山和谷,湖水和河水,断崖和斜坡,这样配合,这样协调,任何一个外来的参观者进到皇宫之后都会自然怀疑到这究竟是一座天造地设的胜景还是人工的创造”(斯当东,1963:397)。
经过北京谈判的失败,使团成员对北京城的总体印象发生了变化。“大家共同感觉是,实际所看到的一切,除了皇宫之外,远没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假如一个中国人观光了英国首都之后做一个公正的判断,他将会认为,无论从商店、桥梁、广场、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国家财富的象征来比较,大不列颠的首都伦敦是超过北京的”(斯当东,1963:317)。斯当东这一关于北京的总体印象,与素有北京形象最严厉批评者的使团总管约翰·巴罗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进入北京伊始,巴罗(2007:69)就对北京的建筑景观予以挑剔性的批判:“这个著名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既不足以勾起巨大的期待,也不能引发深入的了解。接近一个欧洲城市,通常都会有丰富多彩的事物引人注目,如城堡、教堂的尖顶、穹顶、方尖碑以及其他高耸的公共建筑,人们心中自然就会想象它们各自的建筑特点和用途。在北京,连一根高耸于屋宇之上的烟囱都看不见”。
关于北京的建筑景观,还有一处是马戛尔尼使团无法忽视的,那就是位于北京北郊的长城。与以前参观长城的英国人贝尔不同,斯当东一行参观长城的时候,不仅考证了长城的历史,而且还对长城古北口段的城墙厚度、碉楼大小、枪眼尺寸等进行了认真的测量。虽然他们内心也赞叹长城的伟大,但是在主观上却努力贬低它的作用。斯当东认为,任何防线在战争中都不能保证民族的命运,世界上根本没有突不破的防线,长城也不例外。安德逊对长城的贬低比斯当东更为猛烈,认为 “这最为宏大骇人的人类杰作,到头来也必衰颓;自鞑靼与中国合成为一国,在统一的政府统治以后,这城墙就丧失了它的作用……这个由坚毅的劳动所造成的伟大纪念品,依据国策而努力进行的无比的建筑物,它的使命业已终了,无穷尽的颓废从此开始”(安德逊,2001:108)。
继北京的建筑景观之后,北京的市民是马戛尔尼使团第二个最为关注的对象,也是最能反映北京异托邦形象的活的标志。由于马戛尔尼使团是带着外交使命来的,与北京各级官员的接触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总体而言,身居北京的清政府各级官僚,在使馆成员眼中呈现出一种负面的形象。比如中堂大人和珅,在巴罗(2007:280)的笔下就是一个专权贪财的反面角色:“通过隐瞒欺骗,巧取豪夺,暴戾欺压,他为自己积聚了巨额财富,包括金银、珠宝和不动产。人们普遍认为,他获得的财产超过了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的个人”。马戛尔尼(2013:6)认为,“宫廷的特点是表面殷勤和内心猜疑的奇妙结合,讲究礼节实则粗鲁,假谦虚真顽固,朝廷各部莫不如此”。清政府朝廷官员虽然表面上对英国使团成员慷慨有加,但是内心里时刻提防他们。马戛尔尼认为,清政府官员对于英国使团的提防和猜疑既源于他们对于洋人的胆怯、恐惧和偏见,又源于他们的上国心态,认为清政府完美无缺,把前来进行贸易谈判的英国外交使节视为向清政府朝贡的蛮夷之辈。“他们本身已经完美,因此不可能从洋人那里学到什么……一个国家如不进步,必定倒退,最终沦为蛮夷和贫困”(马戛尔尼,2013:11)。
北京各级官员对新生事物和科技知识的蔑视,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们也有同感并予以批判。在马戛尔尼看来,无论是乾隆本人还是他身边的官员,对于西方的机械制造和科技知识缺乏应有的兴趣。“北京的官员对此没有显示出什么兴趣,没有一个人关注水压、光学原理、透视法、电气等,尽管他们中好几个人曾看到排气机、电动机器、望远镜、幻灯、戏箱。总之,可以说前来参观球仪、太阳系仪、气压计和圆明园安装的吊烛灯架的大人们,都漠然视之,好像这些都十分寻常,没有什么稀奇”(马戛尔尼,2013:63)。巴罗(2007:219)也指出,“就是这种荒谬绝伦的自大和对他国的藐视态度,叫这个民族目空一切又冥顽不化。我们的确可以断言,任何外国人带来的东西都别想引起他们的羡慕。无论什么官员来观赏礼品,只要有我们的人在场,他们总是装作漫不经心地一眼带过,仿佛这种东西已司空见惯了”。巴罗认为,北京朝廷的这种傲慢自大和拒绝接受国外的新生事物,对中国的思想和科技进步极其有害。“朝廷傲慢自大,假装对任何新的或外国的东西都不屑一顾,对新的发明创造,不管多么天才奇巧,普遍缺少鼓励,因而及其严重地妨碍了艺术和制造业的进步”(巴罗,2007:221)。清政府官员对西方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熟视无睹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他们对待“君王”号战舰的态度。使团礼品中有一艘“君王”号战舰模型,拥有110个炮位,极具战斗杀伤力。就是这样一种先进武器,乾隆皇帝和宫廷大臣们并不感兴趣。此后, 这件作为礼品的英国兵器被弃置一旁, 无人过问。直到 1860 年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 发现它们仍完好无损地堆在一边, 便又重新运回了伦敦。
使团成员们差不多都听说过北京的弃婴现象。巴罗对北京城的弃婴现象尤其深恶痛绝。通过与负责收容北京弃婴的传教士的谈话,巴罗估算北京城每年的弃婴约有9000个,“每天在北京大约有24个婴儿被扔到那个乱坟岗。那些无辜的小生命还没咽下最后一口气就被无情地宣判了死刑”。据此,巴罗认为“像弃婴这样恐怖的现象,就是在最野蛮的国度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巴罗,2007:125-126)。言下之意,北京就是世界上最残忍、最野蛮的城市。在紫禁城中,太监的存在引起斯当东爵士和巴罗的注意,他们一致对这种非男非女的畸形人的邪恶人性进行了辛辣的批判。斯当东认为,太监“不男不女,男女两性都讨厌和看不起他们,不能生育,不爱怜人,也不受人的爱怜,根本不像是男的……他们在取得主子的欢心之后,逐渐能爬上有权势的地位。这种人一旦得势,他们将以全人类为对象来进行复仇,往往能招致国家灭亡的大灾难”(斯当东,2005:381)。巴罗则对这些皇宫太监各种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们不仅涂脂抹粉,像女人一样搔首弄姿,而且善于在朝臣之间搬弄是非,收受贿赂。更为可恶的是,这些失去性生活能力的太监还包养女人。“中国太监有一种恶癖,使他们有别于他国的同类。不管是抬轿的还是扫地的,或者是可以出入内宫的太监,几乎没有一个不在家里养女人的。那通常都是从穷人家买来的女儿,因而被他们视为奴隶”(巴罗,2007:169)。
对于北京市民的精神和娱乐生活,斯当东和巴罗等人都不看好。斯当东(2005:327)认为,“北京不是一个追求娱乐和享受的地方。欧洲许多繁荣兴盛的大都市同北京情况不一样”。巴罗(2007:163)对北京人的娱乐生活表达了鄙夷态度:“只有不顾事实和失去理智的人,才有可能赞美北京宫廷娱乐的高雅和精致”。在巴罗看来,北京宫廷戏剧讲述的都是远古时期的故事,戏剧对白多为平铺直叙,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即使被奉为经典的《赵氏孤儿》也很粗俗。在对北京宫廷娱乐进行批判的时候,巴罗也不忘赞扬自己祖国的戏剧及其他娱乐活动。“相比之下,英国乡村小镇集会上所演的木偶戏可以被认为是更精致、更有趣和更合理的……在所有其他方面,中国首都的娱乐似乎都不足称道;同样的还有宫廷的那种伪装的严肃庄重和一般民众的文明状态”(巴罗,2007:164)。
结 语
17-18世纪在英国兴起的“中国风”,将遥远的中国重新置于英国的视野之中。在对古老中国文明羡慕的同时,具有启蒙主义理性批判精神的英国人也敏锐地发现中华文明发展的停滞性和腐朽性趋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人开始了与北京的现实交往。这种交往主要体现在约翰·贝尔和马戛尔尼使团对乾隆时代的帝都北京的外交访问。约翰·贝尔随俄国使团访问北京,受到康熙皇帝的盛情款待,因此他在游记中延续了马可·波罗、曼德维尔等中世纪旅行家和传教士那种惯常的对中国及其帝都北京的乌托邦式赞誉,赞扬康熙皇帝及其他官员圣明、北京建筑景观宏大庄重、北京器物众多奢华以及北京民风淳朴等。马戛尔尼使团是受英国女王派遣而正式出访中国的外交使团,旨在与清政府建立商务外交关系。但是因外交礼仪问题,马戛尔尼使团与清政府官员进行一系列冲突,最终无功而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出版了关于中国尤其是其帝都北京的游记。他们关于北京的表征,总体上是异托邦式的,这种异托邦式的表征尤其体现在马戛尔尼的航船比喻方面,既把当时的中国看作一艘破败的航船,又赞叹这艘航船暂时有一个英明的船长在掌舵,还不至于马上要沉船。总之,马戛尔尼使团笔下的北京,就是一个多元对立现象并置的异托邦。至于笛福,他完全没有到过中国,他在《鲁滨逊漂流记续集》中关于北京形象的表征,纯属虚构和贬低,完全出于当时上升的英国资产阶级对古老中华帝国的鄙视和挑战,是将北京作为一个敌托邦来凝视和批判,认为北京的一切都不如伦敦,甚至被当时欧洲人高度赞誉的万里长城,在笛福看来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