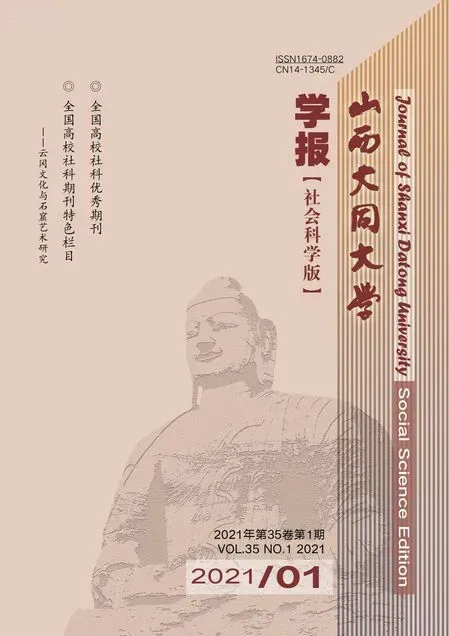乡土性、底层性及边缘性
——关于晋北地区文学的地域性思考
张云丽,李晓璐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地方文学是区域文化的典型文学形态,地方文学的发展直接反映出该地区的文化生态,往往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及文化内涵。“地方文学的文化内涵就在于,一方面它接收着民族文化总特征的影响,体现了文化体系的民族一体性;另一方面,它又是特定区域文化在文学上的反映,是区域文学的一个重要支流,体现了同一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互补性。”[1](P97)地方文学的地域性既受制于整体文学态势的影响,也反映了大区域文化(如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的一般特征,同时还能折射出地方小区域独特的文化个性。山西文学表现出的敦厚朴实、开阔浑厚、务实求真等文学品格,就深深刻上了三晋文化“厚土”般的精神气质。在山西文学内部,又因晋南、晋中、晋东南、晋北地域的巨大差异,又显示出不同的地域性。由于自然、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晋北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于晋南晋中地区,至今仍是经济欠发达的边缘地区,晋北文学的乡土性、底层性等地域文化特征反而被突显出来,也因此具有了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一、乡土性变迁中寄予的作家情感
晋北作为一个区域概念,指称山西北部区域,包括三个地级市——忻州、朔州、大同,地处雁门关一带,有相似的地理气候和物产风物。本文采用“晋北地区文学”指称此地区文学在当代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晋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与很多发达地区相比,受制于地形气候、历史沿革、教育状况等因素,晋北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以农业文化为主体向现代工业科技文化转型的过渡期,晋北文学的地域性因此也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乡土性。
晋北地处黄土高原东北边境,自然环境相对恶劣,高寒凉冷,土地贫瘠,干旱少雨,风、雹、霜等自然灾害频繁,可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限,以土豆、莜麦、玉米、黍子、荞麦等高寒作物为主。正因这特殊的地域特点,晋北地区大多数作家对农村的发展状况、农民的生存境遇都怀有深厚的情结。作家曹乃谦出生于朔州市应县,他最著名的小说以晋北农村“北温窑”为原型,展现20 世纪70 年代晋北农村的生存景观。曹乃谦喜欢这样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之所以关心这些饥渴的农民,是因为我出生在农民的家庭。可以说我是半个农民。最起码我身上留着有农民的血液,脑子里存在着农民的种种意识,行为中有许多农民的习惯。……总之,我是个穿着警服的农民。”[2](P8)作家房光居住在大同市灵丘县,他的小说以自己的家乡为心灵根据地,展现的是20世纪80 年代中期晋北农村封闭落后的风物、人事。王保忠以大同县火山下的村庄黄家洼为原型构筑了一个在城镇化浪潮中快要消失的典型村庄“甘家洼”。王祥夫虽擅长市井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但视线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晋北乡土,他的《上边》《婚宴》《浜下》《归来》等作品恰是由于对“乡土味”的准确把握获得了文坛的认可。
阅读晋北作家创作的乡土小说,常常能感受到一种深沉而忧虑的情感,或内敛克制,或外显勃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万物的深情是他们创作乡土小说的内驱力。房光在《莜麦谣》的后记中表达了自己和晋北山区农村里的山梁河流、黍子莜麦的深情厚谊,“在我看来,老农于温馨夕阳中抚摸庄稼的神情,感人至深。他们在唰唰作响的庄稼地里伫立,或坐在毛茸茸的塄头上,面对炊烟四起的村庄抽烟,心里一定满满当当。”[3](P310)
“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早已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这种理论是从20 世纪40 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经验现实中提炼出来的,指出了几千年来乡村社会的非流动性和封闭性特质,而随着历史的演进,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乡村早已不是全然封闭落后自给自足的社会,“乡村社会的‘乡土本色’逐渐淡去,后乡土性色彩越来越明显,后乡土中国已经来临,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后乡土性的。”[4](P117)
乡村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数晋北乡村人口流动到各个县城、煤矿、市区,甚至三百公里外的北京首都,晋北地区作家笔下的人物也在不同场域流转,城与乡、矿与乡、矿与城之间有文化的承接,也有文化的碰撞,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混杂成一幅幅民间浮世绘,展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阵痛与人性的裂变。
王保忠在2006 年出版的《尘根》中敏锐地把握到了当下农村的变迁,“甘家洼”已经不是沈从文笔下桃花源似的乡村,作品中的乡与城是互相流动的,是变动的,既有城里人来到村里引起村人的艳羡、迷惑、不平,也有村里人进入县城、城市之后的迷茫、困顿、挣扎,这是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念因空间场域的变化而发生的冲撞。《奶香》中木生想要讨好老板,想让刚生了孩子的老婆为老板二奶所生的孩子哺乳,而老婆香妹的奶却说没就没了,面对掌握自己生存命运的有钱人,一家人的惶恐不安、战战兢兢的卑微心理的展示,颇有契诃夫小说的辛酸味道。当然这种卑微心理还并没有完全掩盖乡村夫妻之间的美好情意,这是作家对农民情感的体察和认同。《长城别》“强烈地比照了城里人和乡下人不同的人生状态,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入反思。”[5](P35)城市文化强烈冲击着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
王保忠在2012 年出版的《甘家洼风景》中进一步表现了晋北农村生活变迁带给农民的复杂心理,“甘家洼”的原型是地处大同县火山脚下的村子,只有5 户8 口人,一个正在消失的晋北乡村。“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必然伴随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流动,并最终聚集在城市周围。”[6](P117)在《城市》《宋城泪》《向日葵》中,从甘家洼走出来谋生的村民,成了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服务小妹、蹬三轮车的,建筑工地的工人 ,“无论面对眼前的钢筋水泥丛林还是展望未来命运前景,无助、茫然、困惑,是进城打拼的甘家洼人挣扎于沉沦边缘普遍的精神状态。”[7](P60)
这批60 后和70 后作家时时刻刻关注着农村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熟知晋北农民的生存方式和情感方式,无论他们土生土长,还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这片土地,他们的血脉依然和晋北乡村紧密相联,都对自己的那一小片“约克纳帕塔法”寄予了“针尖上的爱与痛”。[8](P60)
二、观照底层性的日常生活经验
底层写作进入21 世纪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其概念边界、美学价值、与“左翼文学”的勾连、与“纯文学”的争论等,都在文学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论争,形成了一个文学热点,一种强劲的文学潮流。当然,我们也发现晋北作家不约而同地描写底层平民生活模态,并非是追赶潮流,而是一种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
因关隘的阻隔、自然气候的恶劣,贫穷成为笼罩在晋北人心头的巨大阴影,深深影响并制约着他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进而影响到该地区的民情风俗、性格心理等。对生存贫困的书写,对小人物的关注,对底层的书写,成为生活在这个地域的作家的一种宿命。
贫困,扼杀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牵绊着人们追寻幸福的脚步。曹乃谦的温家窑系列似乎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可每一个故事却分明都与贫困有关。贫困不仅蹂躏着温家窑人的肚子,让他们一年到头几乎沾不上什么荤腥,而且贫困造成的食和性的双重匾乏,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道德底线,残酷地剥蚀着人之为人的种种尊严。因为穷,整个村子几年里只有温孩娶了女人;因为穷,黑蛋省下了一千块彩礼钱就得和亲家“朋锅”;因为穷,娶不上媳妇的光棍们困在自己的肉体里,楞二疯了,“羊娃是自个把自个吊在树上给吊死的”。在温家窑的男男女女们眼里,生活就是白天在贫痔的黄土地上“死受”,闲暇时三三五五“窝缩在屹楞下晒暖暖,还不接不续儿地说笑”。[9](P87)曹乃谦笔下的70 年代的晋北乡村底层性的个体生存似乎只剩下了动物性的欲求,由此引发了当时评论家对其描写真实性的质疑。
当然,对贫困生活的书写并不是底层写作的必须要素,文学作品并非是社会学论文,文学作品呈现的底层性应该是对一切有关底层平民生活模态的书写,体现了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生活和公共领域的良知和责任。
在中国文坛上,王祥夫一向被视为底层叙事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草根视阈和底层情怀常被评论家关注。王春林较早认识到王祥夫作品这一特点,“认真地阅读完王祥夫近几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之后,一种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作家对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持久而深入的关怀与表达。”[10](P107)王春林进一步指出作家在“推进了底层叙事的内在化进程”,在克服底层叙事“道德优越性”和“苦难炫耀症”的弊端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11](P52)评论家李云雷直接把自己和王祥夫的访谈文章命名为《底层关怀、艺术传统与新“民族形式”——王祥夫先生访谈》。有论者直接指出,“王祥夫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执著于对卑微人生的关注,其创作维度始终指向草根阶层或小市民阶层,以精湛的艺术表现力展露特有的人性关怀。”[12](P97)在笔者看来,晋北地区作家最可贵的一点便是始终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赋予作品以鲜明的平民视域和民间情感。
三、边缘性写作的拘囿与挣脱
阅读晋北作家的文学创作,常能感到这种基于地域性的本土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出主流文学和传播话语之外的边缘性的文学形态。“边缘”一般相对于“中心”而言,包含着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的考量和定位。从地理气候来看,晋北地区气候条件相对恶劣,群山环绕,天寒地冷,常年干旱少雨,宋元民谣这样写道,“雁门关外野人家,不植桑榆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高寒的地理气候必然影响本土的文化生态。从经济方面来看,晋北地区虽与北京不远,但又隔着八达岭的崇山峻岭,与山西首府太原又隔着雁门关,是一个既想要开放又相对隔绝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从文化方面来看,晋北地区处于晋冀蒙三省交界地带,既有汉民族中原文化的正统性,又有游牧文化的异质性和边缘性。
这种边缘性的文学形态,既来自于作家对自身语言和生存状态所特有的态度和立场,也来自于地域经济文化限制而被边缘化的无奈。曹乃谦完全用本土方言写作其实是一种别出心裁的主动边缘化的策略选择。他对本土方言的坚持显出某种执拗和倔强,面对媒体记者和普通读者质疑“看不懂”,让给某些方言加注释时,他往往拒绝得毫不犹豫。当马悦然给他定位为“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时,曹乃谦不仅是同意的,还应该颇有千里马被伯乐发现的喜悦。用不合于主流语言的纯粹方言写作,恰如沈从文一生自命为“乡下人”——一种对本土性的坚持显露出的某种自豪,实际上是因为这种“乡下人”眼光背后的知识分子身份。这种身份的强调和申明,“更在说明作家性情、人生态度、价值感情、道德倾向等等,他们骄傲于其知识者的农民气质、‘乡下人本色’,”[13](P18)“骄傲的乡下人!这自然只是知识分子的骄傲,与真正的乡下人——农民无干”,[14](P18)也与在泥土中挣命的真正乡下人的文化自卑心理有巨大的反差。
与曹乃谦对这种边缘性的自信不同,更多的作家试图对这种本土性进行突破,他们没有执着地坚持纯粹的方言写作,希望以本土性映射更为普遍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尽可能地摆脱一种地域文化的本土性带给作家的思想束缚。20 世纪90 年代成名的房光在此方面的困扰可能更深刻,“好多年来,我的思绪老在晋北山区一个四周坐满大山的小盆地里游走。那里哪怕极小的一点时令色彩和风物标记也在我的视野之内,我曾为此感到充实,至今已然如故。……一个小盆地形成的隔绝与封闭,具有强硬而又可怕的力量。它在使我与生俱来的局限不断扩大和深入,差不多到了死不悔改的程度。我毫无办法,因为我的目光太软弱,难以穿透根深蒂固的大山。我的风筝,只能在我自己的头顶上空飘飞,虽然我也想让除自己之外尽可能多的人看到我的风筝。”[14](P221)房光深深地感受到大山、盆地对自己创作的拘囿,想要挣脱因地域限制而影响作品传播的焦虑。
对晋北作家地域性书写的考察,在于探讨文学作品地域性、独特性和普适性之间的复杂性关系。在近期《长江文艺》的“自由谈”栏目中,一些年轻的评论家再次对地域性书写重新思考。他们指出一些作家似乎越是突出地域性,他的创作似乎越具有文化根基。金宇澄运用上海方言写作的《繁花》获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一些作家又会因地域性书写陷入画地为牢、老调重弹的创作困境。弋舟指出目前地方性书写的套路化,刘芳坤指出,“异质性写作的关键还在于异质性主体的养成,而先锋性、地域性都是披附在强大主体之上的外衣。”[15]由此想来晋北还有很多基层作家没有走向更宽广的创作领域,部分原因确实在于地域性书写背后缺乏强大创作主体精神的辐射。可见,地域性书写绝不是创作主体的创作目的,而应该借力地域性和“自己胸中那澎湃的拘囿与挣脱之力”,[16]从而走向更宽广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