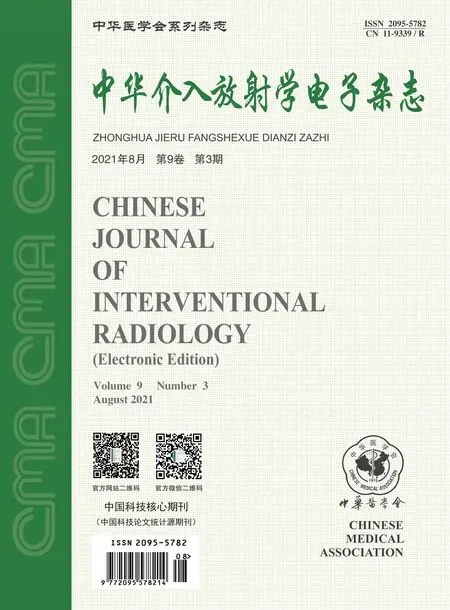外科切除与微波消融对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应用比较
訾洋 韦伟 杨泽军 王曼璐 贾广志 秦孝军 关利君
肺癌是全世界最常见且病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占80%以上[1];因此,非小细胞肺癌的诊疗已受到全世界学者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肺叶切除开始作为非小细胞肺癌的标准术式,同时也将外科切除术视为肺癌治疗的金标准,提高了患者远期生存率。但由于肺癌发病较为隐匿,约有80%的患者确诊时已失去了手术切除的机会[2]。微波消融术(microwave ablation,MWA)的出现,逐渐成为了不能切除或拒绝切除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也因为其适用范围广、预后好、并发症少等特点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而如何选择外科切除术或MWA能为肺癌患者提供更好的预后成为了学者的共同难题。本文对外科切除术与MWA的应用范围及预后进行了综述比较,为未来研究不同类型肺癌的治疗方法提供参考。
一、外科切除与MWA介绍
(一)外科切除
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为外科切除,分为根治性切除和姑息性切除,均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及延长生存期的前提下,尽量根治性切除肿瘤及淋巴结清扫,以减少复发和转移,并缓解肿瘤引起的一系列临床症状。对于一般状况平稳(Karnofsky评分≥ 60)、心肺功能良好、无淋巴结转移(或仅有部分淋巴结转移)及少数伴有肺外转移的肺癌患者均可选择外科切除[3]。对于Ⅰ期、Ⅱ期和部分ⅢA期肺癌,肺叶切除加肺门纵隔淋巴结清扫已成为标准术式,5年平均生存率分别为74%、42.8%和27.3%[4-7]。而部分ⅢB和Ⅳ期肺癌因为常常合并严重的肺外侵犯或转移情况,所以晚期肺癌是否可行切除术争议较大。有学者认为[8],姑息性切除部分肿瘤,可以最大限度保留肺功能,降低肿瘤负荷,减轻肿瘤的毒性反应,消除患者心理负担,也有益于延长生存期。
(二)WMA
大部分肺癌患者因为确诊时已是中晚期而丧失了外科切除的机会,还有部分患者因为心肺功能较差、高血压、糖尿病等原因同样放弃外科切除。尽管这些年放化疗对于这些患者的生存期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但与外科切除相比,放化疗的生存率十分有限,所以总体效果仍然不容乐观。因此,临床上亟需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不仅要比放化疗效果更好,还要更接近切除治疗的效果[9]。MWA的出现与完善,已逐渐成为肺癌非外科切除的有效治疗方法,其主要优势有微创、恢复时间短、患者痛苦较小等。其原理如下[10-11]: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CT、超 声等影像技术引导下,经皮肤将微波消融针穿入肿瘤内,利用微波场使肿瘤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极性分子和钠、钾、氯离子等带电粒子激烈转动和碰撞振动而产生热效应,导致肿瘤组织内的温度在短时间内迅速升高而发生凝固性坏死,以达到治疗效果。对于无淋巴结转移的早期肺癌,MWA后5年生存率与外科切除无统计学差异,并且可以成为老年肺癌患者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之一[9,12]。对于ⅢB期和Ⅳ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有学者认为[13-14]MWA可以有效减轻肿瘤负荷,且与化疗联合,可提高患者的疾病控制率,延长患者生存期。
二、外科切除与WMA比较
(一)不同分期的治疗比较
随着低剂量CT在肺癌筛查中的普遍应用以及影像诊断技术的不断提高,早期肺癌的诊断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对于拒绝切除术或一般状况较差而不能手术切除的患者,MWA具有和外科切除几乎一样的治疗效果。有文献指出[17]MWA与外科切除在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远处转移率等方面无明显差异,且MWA术后出现的并发症要少于肺叶切除。2018年Yao[18]对Ⅰ期患者分别行MWA和外科切除,OS分别为5.97±0.33年(95%CI:5.32,6.62 年),5.81±0.26 年(95%CI:5.31,6.32年),MWA后第1、3、5年生存率分别为100%、92.6%和50.0%,外科切除为100%、90.7%和46.3%,均无统计学意义。2018年Wang[19]回顾性报道,对Ⅰ期肺癌患者分别行MWA和外科切除,中位生存期(median survival time,MST)分别为32.74±0.94(7~36)个月和32.45±0.74(0~36)个月,MWA后1年和2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7.82%、91.30%,外科切除分别为97.65%、90.59%,MWA和外科切除无明显差异,并且行MWA的患者比行外科切除的患者住院时间更短,花费更少。所以,利用MWA治疗早期肺癌患者,不仅可以达到与外科切除一样的根治效果,亦可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治疗费用。
中晚期肺癌是世界各国学者的共同难题,目前并无单一、完美的治疗方法,需要通过多学科联合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部分学者认为对于晚期肺癌患者,外科切除的意义有限;但也有学者认为,外科切除部分瘤灶可减轻肿瘤负荷,并且术前辅助性放化疗可以增加患者完成计划剂量化疗的概率、限制肿瘤细胞微扩散的能力、减小肿瘤最大径而增加可切除性等[20]。2011年Shumway[21]报道,对53例晚期肺癌患者放化疗后行外科切除,1年和2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5%和61.6%,1年和2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67.9%和42.8%,中位PFS为14.6个月,明显高于单纯放化疗组,并且81%的患者病理分期降级。2019年Laura[22]报道,利用放化疗联合外科切除,治疗27例晚期肺癌患者,分析显示OS为75.56个月,第1、3、5年生存率分别为74.1%、57.8%、53.3%。近年来,因为MWA独特的优势,不少学者试图与放化疗等方法联合,提高中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期。2013年高云姝等[23]对58例晚期肺癌患者行MWA联合化疗,结果MST为13.2个月,1年生 存 率 为49.3%。2015年Wei等[24]对39例 晚期肺癌患者行MWA联合化疗,MST达21.3个月(95%CI:17.0~25.4)。2016年何春雷等[25]报道对Ⅲ期周围性肺癌患者行单纯MWA病情控制率为55.43%,MST为27.86个月,行MWA联合放化疗病情控制率为72.82%,MST为32.63个月。由此可见,晚期肺癌的治疗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无论MWA还是外科切除,都需要与其他学科联合,相互合作、相互弥补,共同提高患者的生存期及生存质量。但是,对于晚期肺癌患者究竟选择MWA还是外科切除能获得最大的效益,还需更多研究和探讨。
(二)并发症的比较
外科切除术后并发症包括持续性肺漏气、肺水肿、急性肺损伤、术后感染、血胸、脓胸、血栓形成、肺叶扭转、肺梗死以及心脏疝等。其中肺水肿、急性肺损伤、肺叶扭转、肺梗死及心脏疝等死亡率较高,急性肺损伤死亡率可接近80%,心脏疝虽发生率较低,但死亡率高达40%;持续性肺漏气、术后感染、血胸等虽然相对死亡率不高,但处理相对复杂,必要时需再次手术处理[26]。
MWA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有气胸、胸腔积液、术中出血、术后感染、神经损伤以及支气管胸膜瘘等。其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为气胸和胸腔积液,发生率为30%~53.8%,然而仅有10%的患者需要行胸腔闭式引流[27];对于术中出血的患者,用消融针对出血点行短暂的加热即可止血[17,27-29]。据相关文献记载[29],肺癌MWA后死亡率、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0~5.6%和3.0%~24.5%,必要时须多学科联合治疗。
所以,相对于MWA而言,外科切除术须在术前更加仔细制定手术计划、评估患者状态及预测并发症发生概率。有文献报道,年龄、吸烟、有无合并基础疾病、手术术式、肺功能等因素与术后并发症发生密切相关,术前对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可为顺利渡过围术期和提高手术安全性提供积极的临床指导[30-33]。
(三)肿瘤大小对外科切除及MWA预后的影响
无论对于外科切除还是MWA,肿瘤最大径都影响着复发率。2009年Li等[34]报道,对325例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行外科切除术后,显示肿瘤直径≤2 cm、2 cm<肿瘤直径≤3 cm、3 cm<肿瘤直径≤5 cm、5 cm<肿瘤直径≤7 cm 和肿瘤直径 > 7 cm的患者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75.49%、74.58%、60.87%、55.63% 和46.15%(P=0.025)。2017年刘文科等[35]报道,肿瘤直径 > 20 mm的患者行切除术后PFS明显低于肿瘤直径≤19 mm的患者(P=0.026)。2019年Yun等[36]报道,对1 311例早期肺癌患者行肺癌根治术后,结果显示肿瘤直径<3.55 cm的患者OS为71.72个月,肿瘤直径≥ 3.55 cm的患者OS为56.38个月(P<0.001)。Wolf等[37]在2008年报道,对50例肺部肿瘤患者行MWA,发现最大径> 3 cm的肿瘤更可能复发。Yang等[38]2014年的回顾性研究显示,对47例ⅠA或ⅠB期肺癌患者行MWA,结果发现直径≤3.5 cm的肿瘤生存期长于直径> 3.5 cm的肿瘤。DAS等[15]在2019年研究发现,对于ⅢB、Ⅳ期患者,肿瘤直径≤3 cm的患者,MST为30.0个月,中位PFS为11.0个月。对于肿瘤> 3.0 cm的患者,MST为24.5个月,中位PFS为10.5个月。Zhong等[9]在2017年报道,对113例肺癌患者行MWA,其中2例早期肺癌患者肿瘤进展,且肿瘤最大径均>3 cm,16例晚期患者肿瘤进展或复发,其中13例患者肿瘤最大径> 3 cm。因此,肿瘤最大径对外科切除和MWA的预后都有较大的影响。虽然目前的研究发现早期非小细胞肺癌选择外科切除或MWA的预后无统计学意义,但随着肿瘤最大径的增大,外科切除和MWA的预后是否仍然无统计学意义,还需进一步探讨研究。
(四)肺癌淋巴结转移对外科切除及MWA预后的影响
淋巴结是肺癌的主要转移途径,并且发生淋巴结转移的风险随着肿瘤直径增大而增高[39-41],即使肿瘤直径小于2 cm,也同样有淋巴结转移的风险。尤其对于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 5 ng/mL的肺腺癌,更应注意淋巴结转移。有文献报道,肺癌纵膈淋巴结转移的概率为30%~40%,如纵膈淋巴结转移,则预后较差[36,42]。而MWA目前无法解决淋巴结转移的问题。所以,在MWA前应完善相关检查,确定是否有淋巴结转移,判断其预后。由此可见,对于肿瘤直径较大(尤其> 3 cm的肿瘤)或伴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若符合外科切除的适应证,还应首选外科切除。而对于直径较小的肿瘤选择MWA还是外科切除,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保证患者受益最大化。
(五)肿瘤位置对外科切除及MWA的影响
肿瘤的位置无论对于外科切除还是MWA都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位于肺门附近的中央型肺癌。中央型肺癌是指起源于肺段支气管开口以近,位置靠近肺门的肺癌,约占肺癌总数的60.0%~70.0%[43]。其解剖部位及病理类型的特殊性,大大提高了手术的风险、手术难度及发生并发症的概率[44]。中央型肺癌的治疗主要以外科切除为主,并在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高端、逐渐成熟。从全肺切除发展到现在的袖状肺叶切除,从传统的开胸手术发展到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不仅明显缓解了肺功能的丧失、降低了手术风险及并发症的发生概率,还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提高了术后生存率。2019年Li等[45]统计分析后报道,中央型肺癌行袖状肺叶切除术后,1年、3年、5年的生存率分别为38.00%、27.80%、25.77%。2019年闵伟伟等[46]报道,对早期肺癌患者行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VATS),1年 和2年 无 瘤 生 存 率 分 别 为84.2%、73.7%。2020年Dong等[47]报道,对112例中央型肺癌患者在电视胸腔镜下行支气管袖状切除术,3年OS率估计为 68.8%(95%CI:53.7~83.9),3年 PFS 率估计为60.8%(95%CI:45.1~76.5)。由此可见,对于中央型肺癌,外科切除术的发展已十分成熟及可靠。
然而MWA的疗效虽然明确可靠,但大部分手术来自于周围型肺癌,而中央型肺癌的数据相对较少。中央型肺癌因与心血管、支气管、食管等重要脏器关系密切,不能像外科一样直接观察及分离重要脏器,导致MWA易造成严重并发症或因消融不完全而使肿瘤复发。有学者认为[48],邻近这些重要组织的中央型肺癌,可通过降低消融功率、人工气胸、缩短消融时间、严格把握适应证等方法进行消融。然而也有学者认为[49],若经皮穿刺消融,路径较长,会损伤较大的血管及支气管,可引起大血管出血和支气管胸膜瘘,所以应把中央型肺癌列为经皮穿刺热消融的禁忌证。同时,随着多学科多器械的融合发展,也有支气管镜引导射频消融的报道,以及支气管镜引导的MWA研究[10,50]。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对于中央型肺癌,MWA也可以像外科切除一样成熟可靠。综上所述,目前对于中央型肺癌而言,若有切除手术适应证,还应首选外科切除。
四、总结
肺癌是目前世界上恶性肿瘤病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学者需共同攻克的重点和难点。对于可耐受手术的患者,外科切除依然是首选的治疗方法,尤其对于肿瘤直径较大、有淋巴结转移或中央型肺癌的患者,外科切除癌灶并行淋巴结清扫可大大提高远期生存率。而对于无法进行外科切除或拒绝切除的患者,MWA是一种非常可靠的替代治疗方法,其效果也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肯定。对于晚期肺癌患者,无论外科切除或MWA都无法彻底根除肿瘤细胞,但可以通过联合放疗或化疗等方法延长患者生存期,尤其是合理地使用MWA,可明显减轻肿瘤负荷或解除顽固性疼痛等,提高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另一方面,若早期肺癌患者经影像学及相关检验检查证实无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行MWA的远期效果可与外科切除相媲美。因此,如何抉择外科切除和MWA才能给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带来最大的利益还需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探讨研究。总之,外科切除、MWA或其他治疗手段,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及优势,应相互弥补、取长补短,且无论选择哪种治疗方式,都需要仔细讨论与评估,用最合理的方法提高患者的远期生存率及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