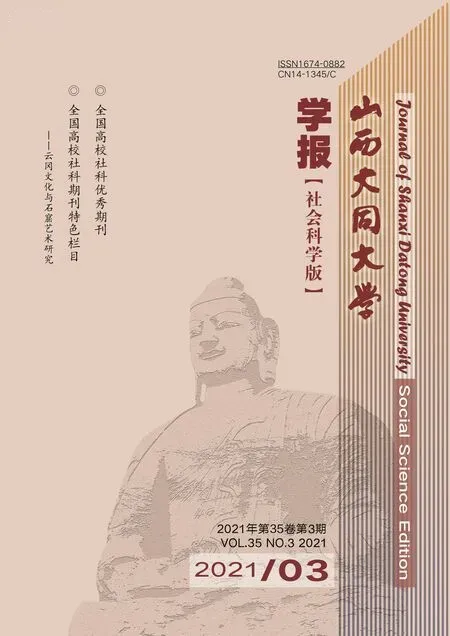论当代女性小说中的“姐妹情谊”书写
——以《弟兄们》和《方舟》为例
杜 越,卢 桢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姐妹情谊”最早发轫于西方文化语境,是一个带有比较浓厚的政治意味的概念,意在通过姐妹联盟的反抗和斗争,终结男权的压迫,争取到平等的自由权利和话语权。“五四”之后,当它作为一个文学命题出现在中国并开始被女性作家们书写时,“姐妹情谊”渐渐剥离了原本的政治属性,变成了一个相对温和的文学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若是将“姐妹情谊”严格地框定在某种“女权主义者”甚至“同性恋者”的范围内,难免有些偏激和狭隘。所以在当代女性文学的诸多作品中,“姐妹情谊”并非是一个很严格的学术性的定义,而是更多体现出一种女性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扶持的情感关系,以及隐藏于其背后的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精神价值的追求。
一、女性书写的传统与演变
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父权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始终是一个被忽略的处于“失语”状态的群体。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脉,在传统儒家文化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里,难以见到女性的踪影;《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更是将女性群体定义在了一个难以相处、不堪重任的桎梏中。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叙事中习惯于表现男性之间的情谊:伯牙子期是知音难觅的至交典范,失去了对方甚至不亚于失去生命;“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家喻户晓,突显出刘备、关羽、张飞之间以性命相托的兄弟情义;“既生瑜,何生亮”是两位身处敌对阵营的英雄对彼此的谋略和智慧的惺惺相惜……几乎每一段典型的男性之间的关系都具有一种超越利益、超越阶级甚至超越生命的高尚性,坚不可摧。但是,反观相关的女性书写,其书写价值与存在意义却始终依附于父权夫权的价值而存在。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她们是妻子,是母亲,是情人,却唯独不是一个单独的、有意识的女性个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女性的身份被深深压制在男性话语权力之下。与此同时,女性之间的情感也被男性话语所压制甚至是扭曲,大部分女性都被描写为互相妒忌、互相排斥、无法共融的形象,甚至为了获得依附于男性的权力而互相伤害。明清时期这种扭曲的风气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一夫多妻的历史背景下,出现更多表现后宫之争、内院之争的内容。例如在小说《金瓶梅》和《红楼梦》中,有很多对女性角色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描写,女性之间互相算计,只为了争夺男性的欢心,维护男性给予自己的有限的权力和资源。无怪乎有学者总结认为,女性的存在就是被限定和要求完成“镜子”的作用,反照出男性的宽阔胸怀和非凡气度——“几千年来妇女都好像用来作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1](P42)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女性书写开始回归正轨。“五四”带来了思想解放的风气,各种西方先进思潮涌入古老的中国,为传统中国社会带来启蒙与改变的契机,其中也包括女性主义与妇女解放的潮流。最初,这种思潮是作为一种政治术语出现在欧美的女性主义运动之中的。当时的妇女们致力于跨越种族限制与阶级限制,团结一致,结成联盟,抵抗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捆绑与压迫。当时西方的女性主义者们将异性婚恋关系当作父权社会掌控女性的主要手段。她们认为,长久以来,通过婚姻这一形式,女性只能被捆绑在自己同男性组建的家庭之中,同时也深深受困于家庭所代表的阶级和种族之中,从而造成女性之间只能分崩离析而无法结成有效联盟的现状,这也是造成所有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因此,“姐妹情谊”号召女性从婚姻与家庭中解脱出来,打破异性恋制度,团结起来共同反抗父权社会,并在这场斗争中为彼此提供物质与精神帮助,互相交流,分享彼此的生命体验,摆脱传统社会认定的女性之间只有嫉妒、攀比、猜忌的怪圈,重新定义被妖魔化了的女性友谊。
在此西方思想解放与启蒙的影响之下,中国社会的女性意识开始苏醒。作为封建传统秩序中受到压迫最多的受害者,女性被推到了“启蒙与解放”的队伍前列。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的女性才拥有了和男性一样接受教育、获得工作的机会,才开始走出封建家庭与封建婚姻的束缚,走入社会,抛头露面。也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这一主题的书写被唤醒。“姐妹情谊”开始以一种正常的面目出现在作家笔下。一批批女性作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捕捉和表达出女性生存真实境况和心理需求,而这种需求一直以来是被男性话语所忽略的。她们第一次展露出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不再是同性之间充满恶意的提防与计较,既有和男性一样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有对自身合理生存状况与自我成长的不断深入思考,当然还有女性细腻的情感体验。五四时期女作家笔下的女性情感关系大致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同窗女友之间真挚的情怀,二是受父权男权伤害的女性之间的彼此抚慰与荫蔽,三是女性之间的同性恋爱。[2](P218)在具体的作品中,这三种情况并非独立出现,而是常常交织在一起。比如庐隐的《海滨故人》就讲述了五位天真烂漫的少女——露莎、玲玉、莲裳、云青、宗莹之间的真挚情感与各自的经历。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之下,她们怀揣理想和憧憬,追求人生与自我的实现,当她们在爱情与社会现实中遇到挫折而陷入苦闷时又相互慰藉。作品深刻表现了五位年轻女性在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的觉醒与追求。人物的不同遭遇和命运,也反映出“五四”一代女性知识青年在社会思潮与自我价值实现中的彷徨。不得不说,这种真实在一定程度上向被歪曲的女性情谊做出了反抗和回应,用自身的经验和创作为“姐妹情谊”正名。
在经历了建国初期与“文革”的暂时断裂之后,这种女性书写的传统在当代文学中重新焕发了生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目光开始再度转向对女性压迫的关注,新的自我意识再次觉醒。一批女性作家开始在作品中反省过去的生存处境与生存方式,建构出更加真实的女性生活图景。“姐妹情谊”这一主题再度出现在文坛上。当然,相比于西方“姐妹情谊”中的激进与反叛,中国的“姐妹情谊”则显得温和很多。自五四时期女性文学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到当代女性作家的积极建构,大部分女性作家都更加愿意选择一种温柔平和的表述方式,她们渴望建立一种姐妹之间无障碍交流、互相关怀的精神乌托邦,以此来暂时逃避不幸的婚姻、残留的封建礼教等因素所造成的不幸命运。因此这一主题更多突显的是全新的思想解放的方式,而非政治化的抗衡。“姐妹”作为一个一直被传统蒙蔽的、突然间又被注意到的概念,唤醒了当代女性对潜藏的自我价值的发掘,在对与自己相似的身体与灵魂的观察和审视中领悟到了一直以来被压抑和否定的体验。
二、当代文学作品对“姐妹情谊”的书写
在当代女性小说中,王安忆的《弟兄们》与张洁的《方舟》是两部非常经典的表现“姐妹情谊”的文本。两位作者对当代女性自我的精神需求与现实困境做出了清醒的体察与深刻的思辨。
王安忆在《弟兄们》中展现了三个与众不同的女性——老大、老二和老三。她们是三个已经走进婚姻的女学生,在各自丈夫的支持下,离开家庭进入大学继续学习。一间学生宿舍让她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三人性情相投,关系亲密,形成了“许多人是走完整整一生也遇不到的这样一次机会”的姐妹乌托邦。在这段关系中,三个人将彼此真实的自我解放了出来,“她们你知我,我知你,互相将各自真实的自己唤醒了。她们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是这样的。”[3](P232)由于远离了现实婚姻生活的困扰,身处在一个相对单纯的校园环境中,三位女性在细致入微的生活与心灵交流中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结,彼此发掘出了自我精神世界的全新领域。她们希望通过彼此的携手,来完成心灵的各种探索与冒险,从而“成为一生中最好的她们,最自由和最觉醒的她们”。
在这一同性相处的过程中,三位女性不仅体验到了全所未有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也使她们与家庭、与男性社会拉开了一段距离,跳脱出了传统男性话语划定的范畴,独立地审视自己的问题与迷茫。在这段安全距离下,纯粹的精神层面的情感交流与自省使她们逐渐窥到了女性自我存在的意义,并为此而感到满足,所以三个人的相互支持和鼓励被形容为“一个自我灭亡和新生的奋搏过程”。三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完全肯定了女性的情感需求,挖掘和表现了女性独特的内心世界,也更加突破了女性对异性亲近的自然本能与对事业追求的社会价值层面。“因为异性间是无可避免地要走入歧途,以情欲克服了思想,以物质性的交流替代了精神的汇合,而肉体最终是要阻隔精神的。所以,同性间的精神对话实际上是唯一的可能。”[3](P261)或许,女性之间这种平等、团结、自由、进取的关系,才是女性作家在“姐妹情谊”这一主题书写下真正应该重视和推崇的。
无独有偶,张洁的《方舟》同样刻画了三位知识女性——荆华、柳泉和梁倩,她们在经历了各自无爱的婚姻与事业的磨难之后,生活在了一起,互相扶持,互相欣赏,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脱离了异性与婚姻关系的辖制,三位女性之间相处交流的融洽与契合使她们意识到“女人和男人的心理是完全不同的,可能他们之间永远不能相互理解,”也明白了“女人,女人,这依旧懦弱的姐妹,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还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靠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实现。”[4](P58)尽管她们想要与异性隔绝,但真正的规避又是不现实的。她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姐妹情谊构成了彼此的动力。她们结成同盟,互相理解,互相扶持,彼此安慰,同心协力地对抗来自男权社会的压力与风雨,争取自身的解放。她们喊出了“为了女人,干杯!”“为了女人已经得到的和尚未得到的权力”“为了女人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为了女人所受过的种种不能言说和可以言说的痛苦”“为了女人已经实现或尚未实现的追求”的口号。她们以鲜明的性别主体意识,通过“姐妹情谊”同盟的构建制造了女性生命的另类“方舟”。
实际上,在女性实现自我解放的道路上,除了外在的阻碍,内在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也深深捆绑着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女性温柔敏感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母性牺牲精神,使她们在屈服传统和追求现代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中苦苦挣扎徘徊。要想保持真实的自我不迷失,或者和男性一样达到同样的成就,往往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倍的努力。因为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下,男性的结婚、生子并不与事业的发展相冲突,男性完全可以很好地兼顾家庭与事业的平衡,而无需付出太多代价,也不必克服来自社会的压力;而女性在自我内在和外界社会的压迫之下,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将觉醒的自我意识掩藏于母性天性的层层束缚之下。在新时期女性小说中,作家试图展现出女性主体的觉醒和自救的努力,尽管很多情况下女性向现实发起的反抗和进攻还稍显天真和脆弱,但无论如何,这种努力实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突破,对于一直以来缺乏女性话语的文学史是一种迟到但不应该缺席的弥补。
著名学者戴锦华曾经比较过不同性别的友谊叙事:“友谊,如果见诸男人,那它不仅是一种莫大的‘自然’,而且无疑是一种高尚的情操。”[5](P5)而女性情谊则完全不同,“作为一种深刻的文化构造和‘常识’性的话语,在女人间有的只是与生俱来的敌意、嫉妒、互虐与猜忌,女人间的情谊只能是一个特定年龄段或者特定情境中的短暂利益结盟,舍此便只有廉价的甜腻、貌合神离、口是心非或虚与委蛇。”[5](P5)令人无奈的是,在文学作品甚至现实生活中,和女性对应的情感总是被无限扩大和神圣化,并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无法替代。比如“母爱”就被描述为一种完美无瑕的、专属于女性的职责,爱情则是单独对女性具有唯一性的浪漫关系,而女性之间的友情却被不断误解和歪曲,渐渐脱离了它真实的面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体现“姐妹情谊”的作品都是有意义的探索。即使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无法避免地会出现许多矛盾和困惑;但无论如何,在这个男性话语主导的世界里,总有人保持着宝贵的自我思考与反省,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便它很微弱很渺小,但毕竟这种发声存在着,并逐渐让人无法忽视。同时也让我们逐渐明白,“姐妹情谊”如同人类任何一种情感一样,是女性之间不可替代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三、“姐妹情谊”的书写意义
当代女性作者对“姐妹情谊”这一主题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完全拒斥男性话语的存在,也并非将“姐妹”完全置于男性的对立面。她们所追求的是结束两性对立、淡化男权话语所引发的对抗和压制。或许“姐妹情谊”的构筑无法成为女性走向觉醒后的最终归宿,历史和现实的强大逻辑也会阻碍对“姐妹情谊”的过分夸大和片面关注,这一叶理想中的“方舟”并非坚不可摧;但是无论如何,这一主题的理论引领和创作实践仍旧为被掩盖了多时的女性话语提供了一个解构和颠覆固有陈旧话语的机会。或许在文学作品的影响下,在文学审美领域之外,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里,也可能出现更多广义上的“姐妹情谊”的实践,让每一位女性都愿意献出一份独属于女性之间的守望与相助的力量。这一切正如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那不勒斯四部曲《离开的,留下的》中写的那样:“女性内心深处的孤独很折磨人,我想,把两个人分开是一种浪费,互相没有参照,没有支撑。”[6](P348)在当代的现实语境中,女性需要对自我以及与他者的关系作出更加清醒的审视与反思,并在彼此“姐妹”间的团结和参照中完成自我的救赎,构建出完善和谐的内在价值体系。
在当代文坛和现实生活中,女性与女性文学仍然面临着种种有形和无形的阻碍和龃龉,但这并不妨碍无数女性写作者与女性文学作品艰辛而执拗的前行步伐。她们的每一场突围都是对千年传统影响下无处不在的男性中心的父权话语场的奋力反抗,都是用自身独特的悲欢书写女性作为个体与历史整体的生命体验。这种努力让女性话语——这一潜行于地表之下的巨大失语群体慢慢地闪出光亮,让她们能够被看见、被听见、被重视,让她们有机会在现实文化语境中不断摸索建构着更多属于“她们”的“姐妹情谊”。
——从群体心理看《弟兄们》中的精神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