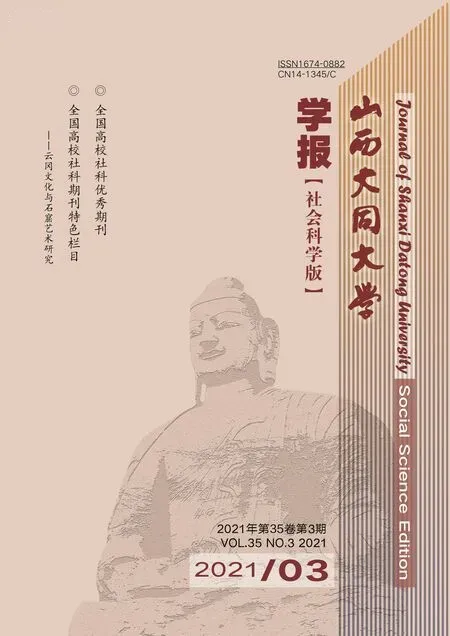分区及治边:刘宋郢州都督区的沿革及政治地理特点
程 刚程 霞
(1.玉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2.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刘宋孝建元年(454),分荆、湘、江、豫四州立郢州,并置郢州都督①以治之。关于此次刘宋设置郢州的举动,学术界严耕望、周品儒、吴成国等人均有论及。严耕望对郢州都督区沿革及其政治地理特点略有论述,周品儒《六朝荆州的发展——以地域政治为中心》虽涉及郢州的政治地理的特点,但因非周氏论证主旨所在,故未深究。吴成国在《刘宋“分荆置郢”与夏口地位的跃升》一文中探讨了郢州都督区治所夏口的政治地位。②相对于上述成果,学术界对郢州都督所辖区域之演变,尤其是其政治地理的特点却未作深入探讨。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刘宋郢州都督区的沿革
刘宋时期,郢州都督区除在孝建元年(454)、二年(455)统辖郢、湘二州外,其他时期其属州仅有郢州一州之地(时有兼统某州之某某郡者),不像其他都督常兼统两三州,或四五州以上。故厘清郢州政区的沿革,大致可知郢州都督统辖区域之伸缩。因之,先述郢州政区沿革如下,据《宋书·州郡志》:“(宋)孝武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立郢州。”[1](P1124)“孝武孝建元年(立安陆郡)……属郢州,后废帝元徽四年(476)度司州。”[1](P1105)又“建宁左县长,孝武大明八年(464)省建宁左郡为县,属西阳。徐志有建宁县,当是此后为郡。”[1](P1128)胡阿祥亦以为:“建宁左郡,先为西阳郡建宁县(元嘉二十年后立),后立为建宁左郡,……大明八年省郡为建宁左县,属西阳郡。”[2](P182)上文所言徐志即徐爰《志》,该著作讫大明(457-464)之末。换言之,孝建元年至大明八年之间,以建宁左县置建宁左郡,大明八年废省。
此外,《宋书·州郡志》载:“徐志有安蛮县,《永初郡国》、《何志》并无,当是何志后所立。寻为郡,(宋)孝武大明八年,省为县,属安陆,(宋)明帝泰始(465-471)初,又立为左郡,宋末又省。”[1](P1105)文中之《何志》,即何天承《志》,该书最迟成于元嘉二十年(443)。故推测孝建元年置安陆郡时,新置安蛮县,寻为郡,大明八年复为安蛮县。另,安蛮郡当先属荆州,孝建元年度属郢州。据此,孝建元年至二年,郢州属郡为十一。但据《宋书·柳远景传》载:“孝建元年正月,……复以(柳远景)为都督……荆州之竟陵随二州诸军事、……雍州刺史。”[1](P1988)又《宋书·刘浑传》曰:“孝建元年,……监……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雍州刺史。”《宋书·刘休茂传》亦载:“大明二年,……都督……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雍州刺史。”[1](P2042-2043)则雍州都督区当常统辖竟陵、随二郡。又《宋书·孝武帝纪》载:“(孝建元年)(454)九月……(以)萧思话为镇西将军、郢州刺史……(孝建二年)(455)秋七月……镇西将军萧思话卒。”
《宋书·萧思话》亦曰:“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萧思话)复都督郢湘二州诸军事、镇西将军、郢州刺史。”[1](P2016)据此,孝建元年至孝建二年,郢州都督所统辖之区域为郢州九郡及湘州十郡。③
孝建二年至泰豫元年(472),郢州都督区域变化较大。具体来说,孔灵符于孝建二年(455)至大明三年(459)任郢州刺史,王玄谟在大明三年至四年(460)续任之。刘袭在泰始二年(466)至三年(467)亦为郢州刺史,然惜史书无载三人为郢州都督事。故欲明了郢州都督区域的变化,必先考辨清三人是否任过都督郢州事。据《宋书·孔灵符传》载:“世祖大明初,(孔灵符)自侍中为辅国将军、郢州刺史。”[1](P1532-1533)严耕望提出:“刺史加将军且加都督(或监、督)者固置府,其仅带将军不加都督(或监、督)者亦置府,惟加都督者又有督府之称,是为异尔。然则刺史之任惟单车不置府,其余加将军者及加将军且加督者均置军府也。[3](P118)故据严氏观点,孔灵符虽有领兵之权,然无都督(或监、督)之职。据此,郢州都督区作为准行政区,在孝建二年至大明三年之间,当被省废。另外,据《宋书·王玄谟传》:王玄谟助孝武帝伐逆后(按:平刘劭之乱),“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后王玄谟又领兵征剿刘义宣、臧质二人反叛,拜豫州刺史,事平“加都督,前将军”。大明元年(457),王玄谟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后又任“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加都督”。[1](P1974-1975)纵观上述,孝武帝时王玄谟均带“加都督”之职。故可断定王玄谟任郢州刺史时,当加都督郢州事。④又据《宋书·刘袭传》:刘袭本任安成太守,因“晋安王(刘)子勋为逆,(刘)袭据郡距之,……太宗嘉之,(泰始二年)以为郢州刺史。”[1](P1567)据严氏观点,刘袭没有带将军号,当为单车刺史。则泰始二年至三年间,郢州都督区当再次被省废。则郢州都督区除孝建二年至大明三年、泰始二年(466)至三年被省废外,在孝建二年至泰豫元年其他时期均被设置。且此期间郢州都督无统辖湘州之记载(详见文末表1)。如上所述,大明八年(464)省废建宁左郡、安蛮左郡。泰始初又复安蛮左郡,宋末省废。则大明三年至八年郢州都督所辖区域仍为郢州九郡。大明八年至泰始元年(465)郢州都督区域所统为郢州七郡。泰始二年至泰豫元年,则为郢州八郡。此外,据《宋书·州郡志》:“前废帝永光元年(465)又度(随郡)属雍(州),明帝泰始五年(469)又还(随郡)属郢(州),改名随阳,后废帝元徽四年(476),度属司州。”泰始元年虽还随郡属郢州,但随郡始终为雍州都督所统辖。换言之,随郡分割或还属郢州皆和其都督区域之伸缩无关。
泰豫元年至升明三年(479)间,郢州都督所辖区域亦有变动。据《宋书·州郡志》载:“后废帝元徽四年度(安陆郡属)司州。”[1](P1105-1106)如上文所及,宋末再次省废安蛮左郡。则泰豫元年至升明三年(479)割郢州安陆郡属司州,并省废安蛮左郡。在此期间虽曾割义阳郡属司州、还西阳郡属豫州,然二郡仍统属于郢州都督。然史书对义阳、西阳二郡割属时间记载前后不一,故考证如下。《宋书·州郡志》曰:“明帝泰始五年,度(南豫州义阳郡属)郢州,后废帝元徽四年(476),属司州。”[1](P1104)但据《宋书·宗室附刘秉传》载:“后废帝即位(472),(刘秉)改都督郢州豫州之西阳司州之义阳二郡诸军事、郢州刺史。”则《宋书·州郡志》元徽四年度义阳郡属司州之说恐误,当以《宋书·宗室附刘秉传》所载为是。此外,《宋书·州郡志》载:“明帝泰始五年,又度(西阳郡)属豫,后又还郢。”[1](P1127)无载西阳郡还属郢州的确切时间。然据《宋书·刘翙传》:“升明元年(477),……(刘翙为)督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郢州刺史。”[1](P2238)文中无载其“督豫州之西阳”事。因郢州都督常统辖西阳郡事,故推测故升明元年当还西阳郡属郢州。但因安蛮左郡省废的确切时间乏考,则泰豫元年至元徽四年,郢州都督所辖区域为郢州八郡或七郡。元徽四年至升明三年,郢州都督当统辖郢州六郡。
二、郢州都督区设置的政治目的及人事任免
刘宋分荆、湘、江、豫四州新置郢州(按:此为郢州都督区所统辖之主要区域)是其重大的政治举措。毋庸赘言,其政治目的就是与荆州都督区相抗衡。后刘休范、刘休祐虽为都督郢州等五州之事,江州刺史。⑤但正如严耕望所说,此二例“非恒制也”。[3](P69)具体而言,郢州的设置是孝武帝为再分荆州方镇实力而作出的抉择。此抉择也为大明三年孝武帝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念[4](P70-85)的实施奠定了较为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有利的军事格局。郢州及都督区的设置如《宋书·何尚之传》载:“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按:即割荆州置郢州、分扬州立东扬州),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1](P1738)此次对政区进行的重新区划,完全是为政治服务,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统治。与此相对的是,此措施根本没有顾及由于过分削弱方镇所带来的恶果。史臣曰:“而建郢分扬,矫枉过直,藩城既剖,盗实人单,阃外之寄,于斯而尽。” 即对刘宋分荆立郢,全然不念及作为“阃外之寄”荆州的政治、军事的作用提出来批评。后唯萧道成蒙“宋文、孝武分割荆州政策之成功”的好处,[5](P204)这当然是后话了。
此外,在孝建元年分荆、湘、江、豫四州立郢州之时,中央朝廷在郢州的首郡选择上,有一番争议。如《宋书·何尚之》云:“江夏王(刘)义恭以为宜在巴陵,(何)尚之议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一郡,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于事为允。上从其议。”[1](P1737-1738)夏口实有控制雍、梁二州,扼制荆州的地理优势。江夏郡本为荆州的东面门户,是其东下的必由之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在郢州都督区的人事任免方面,无论是孝武帝还是明帝,皆委任皇子(常辅之以亲信、能臣)或者忠心朝廷且有政治才干的大臣出任郢州。⑥究其原因,还是在于郢州地理形势的险要,如顾祖禹所说:“盖郢州者所以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者也。自此荆、襄多事,郢州实首当其峰。”[6](P3485)据表1,仅有孔灵符、刘袭二人为无统军权的“单车刺史”。笔者推测孝武帝委任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孔灵符为郢州刺史,当是在无合适人选时,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况孔灵符本人确有才干,堪当郢州刺史之任。⑦刘袭忠心于宋明帝,其任安成太守期间,因抵御“刘子勋之乱”,故“太宗嘉之,以为郢州刺史”。[1](P1467)刘袭由太守直接升任郢州刺史之职,即说明了宋明帝对其宠任的程度。总之,孔灵符、刘袭二人虽无统军权,但皆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所信任和赏识。
表1中,多有皇子任郢州都督者。然而皇子出任时,孝武、明帝皆辅以亲信、干直的能臣,此亦是控制郢州都督区的重要部署。如王奂、柳世隆二人先后出任郢州行事,对中央控制长江中上游的局势,起到了关键作用。后废帝前期,刘休范镇江州,“时夏口缺镇,朝议以居寻阳上流,欲树置腹心,重其兵力”。后废帝最终于元徽元年(473)以皇弟刘燮“为郢州刺史,长史王奂行府州事,配以资力,出镇夏口。虑为(刘)休范所拨留,自太子洑去,不过寻阳”。[1](P2046)此亦是以亲信大臣辅助宗王的明显例证。无需多言,其政治目的是据有长江中上游之险,以防江州胁迫之势也。如元徽二年(474)桂阳王刘休范举兵向京师,刘燮自夏口遣军平定寻阳,刘休范随即败于建康。
三、郢州都督区设置的政治地理效应
如上所及,刘宋时期的郢州及都督区独立于荆州都督区之外。而作为独立存在的郢州及其都督区所形成的政治地理格局,⑧产生出特有的政治地理效应。
首先,孝武帝为达到削强藩、弱荆州的政治地理效应,对郢州都督区的划分可谓费尽心思。如雍、湘二州大部,虽然也是从荆州分割而立,但二州常为荆州都督区所辖(按:除宗王、皇子出任二州刺史外)。郢州则和雍、湘二州不同,即其所属郡县虽也多从荆州割属而来。但郢州及都督区却不为荆州都督区所辖,这其实是孝武帝有意为之的政治策略。后又度湘州巴陵郡属郢州,使得郢州可控带湘州。后梁武帝萧衍亦云:“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7](P4)周品儒认为:“荆南的湘西地区(按:相当于汉时武陵郡的境域)……的入郢,或应当地所拥有的备蛮兵力,可补以郢州抗荆州之不足,这样纺锤状的领土少见于历代。”[8](P102)后世亦承之不改。
其次,郢州都督区范围比较稳定,其都督区包括除竟陵、随(按:后度属司州)二郡之外的郢州所有属郡,并常统辖义阳、西阳(按:后还郢州)二郡。郢州都督区统辖司州之义阳,即担负起治边之责。换言之,维护长江中游边疆地区的稳定亦是郢州及其都督区所要达到的政治地理效应之一。
具体来说,义阳郡为司州之首郡,司州则归都督、监或督郢州都督区的长官所统领,“盖义阳一郡为司州重地,且即为司州刺史治所,郢州都督即统义阳,即无异兼统全司州也。是名异而实亦同。”[3](P71)关于司州的设置,是因为在泰始三年(467),刘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9](P4130)后于泰始五年(469)在义阳郡置司州,⑨该州位于和北魏相对峙的前线,战略地位十分紧要。刘宋政权考虑到单凭司州一州之力无法与北魏相抗衡,故以司州统驭于郢州都督区,为可迅速得到郢州方面的军事和物资援助。即所谓:“(郢州)瞰临沔、汉,应接司部。”[10](P276)后沈攸之即以“监郢州诸军事、郢州刺史。……进监豫州之西阳、司州之义阳二郡军事”的“外蕃”重臣身份和蔡兴宗等“同预顾命”。[1](P1931)元徽初,后废帝以李安民为“督司州军事、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并别敕李安民曰:“九江须防,边备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势,无所致辞也。”[10](P506)也是看到了司、郢二州之间相互倚重的政治地理格局。至萧梁北伐时,梁武帝下诏仍曰:“某勒司郢之师,骁果六万,步出义阳,横轥熊耳。”[11](P233)则司、郢二州唇齿相依,本不可分。
最后,郢州都督区辖有司州,即从地理空间上将荆、雍二州与江州完全隔离了开来。使地处郢州上游之荆、雍二州,无法顺江直达江州,⑩从而避免了二州对下游统治中心扬州的直接威胁,进而达到了当初孝武帝置州于此,以分荆楚之势[10](P276)的政治地理格局。换言之,郢州及其都督区起到了稳定和保护下游建康政治和军事安全的政治地理效应。后齐武帝萧赜更是认识到郢州政治地理的重要性,遽派亲信雍州豪族柳世隆为郢州行事。并最终借郢州之力,破沈攸之的荆州劲旅于郢城下。[10](P446)梁武帝萧衍于雍州举兵,在控制郢州后,才敢顺江而下夺取建康,也是考虑到“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所产生的政治地理效应。
但郢州所起之政治地理效应即有其局限性。当地处郢州下游的江州和荆、雍、湘等三州联成一气时,郢州这种独特的政治地理性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如刘子勋之乱时,邓琬等人迅速控制了江、荆、雍、湘等四州之地,使处于四州中间地带的郢州及都督区仅能被迫胁从。据《宋书·邓琬传》载:“郢州承(刘)子勋初檄,及闻(宋)太宗定大事,即解甲下标。续闻寻阳不息,而(孔)覬有响应,郢府行事录事参军荀卞之大惧,虑为(邓)琬所咎责,即遣……郑宣景率军驰下,并送军粮。”[1](P2134)显而易见,荀卞之是被迫胁从于邓琬等人而举兵从叛的。
结语
刘宋时期,郢州作为一个独立的准行政而存在。这种比较特殊的行政规划,一方面以郢州都督区为独立的中间地带,防范来自上游荆州的潜在威胁,从而保障健康的安全;另一方面,平衡地方势力,起到稳定长江中上游边陲地带的作用。
注释:
①周振鹤认为:“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区,这是以都督为军事长官,统辖数州的军务都理区。都督例兼所驻州的刺史,实际上形成了州以上一级准行政区。”《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1页。
②严耕望《魏晋南朝都督与都督区》,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7本,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1956年;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周品儒:《六朝荆州的发展——以地域政治为中心》,中国台湾私立东海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吴成国:《刘宋“分荆置郢”与夏口地位的跃升》,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③《宋书》卷3《武帝纪》第59页。曰:永初三年,又分荆州十郡还置湘州。《宋书》卷5《文帝纪》第80页、第86页、第101页、第111页。载:元嘉八年,罢湘州还并荆州;元嘉十六年,复分荆州置湘州;元嘉二十九年,罢湘州并荆州,度始兴、临贺、始安三郡属广州;元嘉三十年,以侍中南谯王世子刘恢为湘州刺史。《宋书》卷37《州郡志》第1124、1129页。载:“孝武孝建元年度(随郡)属郢(州)”,“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属湘州”,孝武孝建元年又度巴陵郡属郢州。综上述,永初三年又立湘州,元嘉八年省;元嘉十六年再立,元嘉二十九年又省;元嘉三十年复立。孝建元年当领郡十。十郡当为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营阳、桂阳、始兴、临贺、始安郡。治临湘县。
④《宋书·孝武帝本纪》载:孝建三年秋七月,以前左卫将军王玄谟为郢州刺史。据《宋书·孔灵符传》:孔灵符以辅国将军、郢州刺史。“入为丹阳尹。”《通典》卷37《职官》19宋官品条:“刺史不领兵、郡国太守”。
⑤刘休范任江州刺史时间为470-474年。而刘休祐任职时间史无明文,当在466年任职,寻改任为豫州刺史,王景文续任江州刺史的这一时期。参见《宋书》卷79《刘休范传》,第2045—2046页;《宋书》卷72《刘休祐传》,第1879页;《宋书》卷85《王景文传》,第2179页。万斯同《宋方镇年表》无载刘休祐任江州刺史事,误漏矣(《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
⑥吴成国认为:除沈攸之外的刺史“有的任职时间不长很快调离他职或早死任上,难有作为。”(《刘宋“分荆置郢”与夏口地位的跃升》,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恐有失偏颇,没有深究其中的政治原因与政治地理的作用。
⑦《宋书》卷54《孔季恭附灵符传》曰:“(孔灵符)悫实有才干,不存华饰,每所涖官,政绩修理。”第1534页。
⑧关于政治地理格局的作用,参见程刚:《东晋荆湘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⑨《宋书》卷8《明帝纪》:泰始五年,“以义阳太守吕安国为司州刺史。”第165页;《宋书》卷36《州郡志》载:“(宋)明帝复于南豫州之义阳郡立司州,渐成实土焉。”第1104页。
⑩关于江州的战略地位,参见张承宗:《六朝时期江州的战略地位》,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