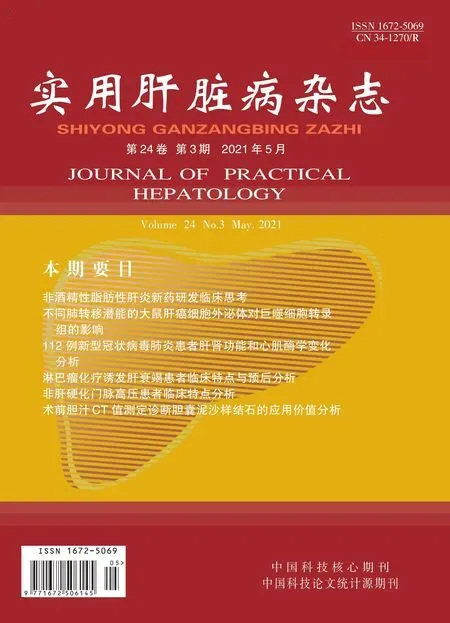重视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特征与预后临床研究*
王梦雨,杨蕊旭,范建高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与胰岛素抵抗和遗传易感密切相关的以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为病理特征的慢性代谢应激性肝脏疾病,疾病谱主要包括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及其相关的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CC)[1]。鉴于绝大多数NAFLD患者是肥胖症、2型糖尿病(T2DM)、代谢综合征累及肝脏的病理学表现,2020年国际专家小组将NAFLD更名为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亚太地区肝病协会、拉丁美洲肝病协会随后正式发布MAFLD诊疗指南,中东和北非肝病专家组、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全球不少专家对NAFLD的更名和新的术语及其工作定义持赞成态度[2-6]。然而,新术语MAFLD的内涵、疾病分型、诊断标准等至今并未得到欧洲肝病学会和美国肝病学会以及国际疾病编码小组等权威机构的认可。
根据MAFLD的新定义,绝大多数NAFLD可以诊断为MAFLD。隐源性NAFLD或瘦人NAFLD可能是MAFLD的早期表现,仅少数可能是肝脏脂肪合成增多的易感基因导致的特殊表型。从流行病学角度,MAFLD群体及其患病率高于NAFLD。不管有无超重和肥胖,MAFLD群体比NAFLD患者群体有更高的T2DM、心血管疾病(CVD)和慢性肾病的发病风险,且有更严重的肝脏炎症损伤和纤维化程度[4-10]。NAFLD/MAFLD现已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慢性肝脏疾病,与失代偿期肝硬化和HCC的高发及其相关病死率增高和肝移植需求增加密切相关[1,8]。为此,当前需要高度关注MAFLD(绝大多数是来自NAFLD的研究资料)的临床特征和自然史,并就此制定相应的筛查、诊疗、随访和管理对策。本文重点分享国际专家小组MAFLD的新定义以及亚太地区肝病协会MAFLD诊疗指南的部分相关内容[3,4]。
1 MAFLD患者肝病负担严重
全球慢性肝病负担数据库显示,2017年全球死于慢性肝病的人数较2012年增加了11.4%,并且死于HCC人数的增长率(16%)高于肝硬化(8.7%)。慢性乙型肝炎(CHB)、慢性丙型肝炎(CHC)、酒精性肝病(ALD)和NASH是肝病死亡排名前四的原因。在肝硬化和HCC死亡患者中,NASH分别占9%和8%,并且NASH是当前肝病死亡增加的主要原因[11]。占全球半数以上人口的亚太地区是肝病的重灾区,2015年全球62.6%肝病死亡和72.7%HCC死亡发生在亚洲,其中以中国最为严重。随着城市化、现代化(久坐和缺乏锻炼)以及饮食结构的西化,接下来的几十年NAFLD的流行及其相关终末期肝病的危害仍将不断加剧[4,8]。当前,NAFLD已累及33%亚洲成人,并且越来越多的ALD和CHB患者并发MAFLD。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亚洲,MAFLD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其疾病负担都已超过其他慢性肝病[4,8,12]。
2 MAFLD的临床与病理学特征
至今鲜见中国和亚洲MAFLD患者真实疾病负担以及种族差异对于肝脂肪变、炎症和纤维化影响的研究报道[2,4,7]。MAFLD患者主要死亡原因是CVD、肝外恶性肿瘤以及肝硬化和HCC。当然,肝硬化和HCC主要发生在NASH患者。全球MAFLD的患病率存在种族差异,拉丁美洲人最高,白种人和亚洲人患病率居中,非洲裔美国人最低。横断面研究显示,亚洲MAFLD患者可能具有更严重的肝组织学损伤。尽管包括韩国、菲律宾、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患者的体质指数(BMI)显著低于其他种族人群,但其肝小叶内炎症和气球样变程度似乎较高加索人、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国人严重。居住在美国的亚洲人比高加索人更容易发生重度肝脂肪变和NASH[2,4,7]。来自英国的一项包括多个种族的大型横断面队列研究显示,血清转氨酶增高的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为亚洲人(孟加拉人18.4%、巴基斯坦人17.6%、印度人14.8%)、高加索人(13.5%),非洲人(11.8%)和加勒比岛居民(10.2%)。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孟加拉种族是MAFLD和血清转氨酶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7]。与白种人相比,亚洲MAFLD患者肝纤维化风险呈增高趋势,而非洲人则呈降低趋势。然而,这些基于肝活检的临床研究结果存在选择偏倚。香港一项基于普通人群的磁共振诊断脂肪肝以及肝脏瞬时弹性检测仪(FIBROSCAN)诊断肝纤维化的研究表明,尽管MAFLD患病率高达25%,但在普通人群中可能存在进展期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比例很低[2,4,7]。
3 MAFLD相关HCC
亚太地区MAFLD相关HCC的报道较北美和西欧地区少见。由于CHB是亚洲人HCC的主要危险因素,MAFLD相关HCC可能被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所隐盖。即使没有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现症/既往感染的血清学证据,隐匿性CHB和CHC仍有可能参与了MAFLD患者HCC的发病[2,4,7]。
在日本,2%以上HCC与MAFLD相关,MAFLD相关HCC患者中位年龄为72岁,男性占62%。一项对6508例日本MAFLD患者的研究发现,在5.6年的中位随访期间HCC发病率为0.043%。基于谷草转氨酶(AST)与血小板比值指数(APRI)诊断的显著肝纤维化的MAFLD患者在随访期间HCC发病率为3.3%(6/184)。韩国一项对329例HCC患者的随访发现,MAFLD相关HCC发病率从2001~2005年的3.8%增高至2006~2010年的12.2%,同期HBV相关HCC则从86.6%降至67.4%。鉴于印度MAFLD和T2DM的流行现状严重,推测印度可能有930000例MAFLD相关HCC[7]。
基于流行病学数据的建模研究显示,2016~2030年间中国MAFLD患者的数量将增加29.1%,MAFLD肝硬化及其病死率将增加1倍以上[2,4,7]。2019~2030年间中国香港和台湾、新加坡、韩国MAFLD患者肝纤维化程度将随年龄增加而加重,并且MAFLD患病率将增加6%~20%,而MAFLD相关肝硬化和HCC发生率则将分别增加65%~100%和65%~85%。一项中位随访3.2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MAFLD相关肝硬化患者HCC累积年发病率为2.6%,这与CHC相关肝硬化患者4%的HCC发病率相近。与CHC肝硬化相关HCC相比,MAFLD相关HCC更常在肿瘤晚期才被发现,并且无肝硬化背景的MAFLD相关HCC患者的生存时间并不优于CHC肝硬化所致的HCC患者。一项来自白种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合并进展期纤维化的MAFLD患者肝硬化失代偿和HCC等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CHC患者,但是两者的总体死亡率相似[2,4,12]。另一项来自白种人的国际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队列研究报道,肝活检证实的瘦人NAFLD与合并超重和肥胖的NAFLD(MAFLD)患者在中位数8年的随访期间肝硬化、HCC、CVD、肝外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以及全因死亡率相似,瘦人NAFLD特别是合并代谢紊乱者同样不是良性疾病,瘦人NAFLD更可能是MAFLD的早期表现或特殊类型[13]。
肥胖、T2DM、代谢功能障碍及其相关脂肪肝是HCC的危险因素,38%以上的MAFLD相关HCC并无肝硬化背景[2,4,7]。鉴于无肝硬化的MAFLD患者群体数量巨大,而其发生HCC的风险相对较低,目前仅建议对MAFLD相关肝硬化患者每隔半年通过超声波等影像学技术和甲胎蛋白筛查HCC。MAFLD相关肝硬化患者的预后与门静脉高压程度和食管胃静脉曲张关系密切,通过瞬时弹性成像技术(FIBROSACN和FIBROTOUCH)评估肝脏硬度值是排除代偿性肝硬化患者并发静脉曲张和HCC的适宜检查技术[7]。肝脏硬度值>15 kPa的MAFLD患者应常规定期筛查HCC,肝脏硬度值>20~25 kpa者还要做胃镜筛查胃食管静脉曲张。对于肝脏硬度值<20 kPa且血小板计数>150×109/L的MAFLD患者,因出现胃食管静脉曲张的概率<5%,可暂不行胃镜检查[7]。
4 MAFLD合并其他肝病患者预后
两种及以上损肝因素并存的肝病患者与单一病因肝病患者相比,理应具有不同的自然转归和治疗应答效果[2,4,7]。并存的MAFLD可能会加快ALD、CHB、CHC患者肝纤维化进程,协同增加肝硬化和HCC发生风险。MAFLD及其基础疾病(肥胖、T2DM、代谢综合征)还增加其它慢性肝病患者代谢和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病风险。此外,即使少量饮酒也会导致合并显著肝纤维化的MAFLD患者肝硬化和HCC风险增高,饮酒还会影响MAFLD患者治疗用药对NASH的改善率。酒精摄入量对ALD和MAFLD等肝病患者肝纤维化的进展速度和预后的影响可能呈剂量依赖关系。此外,饮酒还会通过诱发代谢紊乱增加代谢功能障碍的发病。
肝活检研究证实的CHC患者MAFLD患病率高达38%~76%,后者会促进CHC患者肝纤维化进展、降低对干扰素抗病毒治疗的应答,并增加T2DM和CVD的发病率。另有研究发现,通过直接抗病毒药物治疗或既往干扰素治疗根除HCV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肝脂肪变和肝纤维化,这在基因3型HCV感染的CHC患者中尤为明显。尽管一些研究报道HBV感染与肝细胞脂肪变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但是CHB合并MAFLD群体在急速增多[7,12]。MAFLD可以显著加快CHB患者肝脏病变的进程。泰国的一项研究发现,MAFLD是CHB患者发生显著纤维化和进展期纤维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另一项研究报道,MAFLD导致CHB患者HCC发病风险升高7.3倍。MAFLD是抗病毒药物治疗获得病毒学应答的CHB或CHC患者肝酶持续异常及预后不良的重要原因。
既往,对NAFLD合并其他原因肝病往往仅仅诊断为CHB、CHC或ALD,而NAFLD在肝硬化和HCC发病中的作用因此被低估[2,4,7,12]。即使将有肥胖、T2DM、代谢综合征的隐源性肝硬化都归因为NAFLD,NAFLD相关HCC患病率仍有可能被低估。最近,对一项105例HCC患者的病因分析中,发现29%为隐源性肝硬化,其中仅50%具有与MAFLD一致的肝脏组织学改变或临床特征。日本的一项研究显示,隐源性肝硬化合并MAFLD临床特征的比例高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患者,66%肝脏移植前诊断为隐源性肝硬化的印度患者术后诊断为MAFLD。为此,国际MAFLD更名的专家组以及2020年亚太MAFLD指南建议放弃“隐源性肝硬化”这一术语,规定合并超重/肥胖或T2DM或两种及以上代谢紊乱的肝硬化患者,即使肝脂肪变程度小于5%且无其他明确的损肝因素,也可诊断为MAFLD相关肝硬化[2,4,7]。
综上所述,MAFLD的疾病负担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正在迅速增加,并且亚洲地区MAFLD合并CHB或ALD等双重病因的肝病患者非常普遍。一方面,MAFLD是慢性肝病和HCC日益增加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MAFLD还促进T2DM、CVD、慢性肾病和肝外恶性肿瘤等肝外疾病的发病。肝纤维化是MAFLD患者发生各种并发症的主要决定因素,肝活检仍然是诊断及MAFLD分型的金标准。各种生物标记物和影像学技术可用于且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无创评估肝纤维化。肝硬化患者应考虑监测胃食管静脉曲张和HCC。生活方式干预至今仍然是治疗MAFLD的基石,预计在接下来的10年将有药物被批准用于治疗NASH及其相关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当前,需要建立由多学科医生参与,以MAFLD患者为中心,兼顾防治肥胖、代谢性心血管危险因素以及肝脏炎症损伤和纤维化,合力推进分层全程管理MAFLD的新模式,从而减轻广大MAFLD患者的疾病负担,改善其生活质量,并显著降低代谢性心血管疾病和肝脏疾病的远期不良结局[2,4,7,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