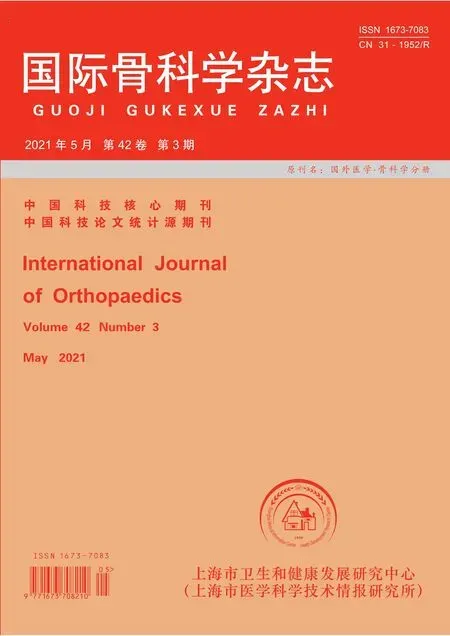掌腱膜挛缩症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张睿 徐佳 王晓昱 康庆林
掌腱膜挛缩症(DD)是以掌、指筋膜纤维组织异常增生为特征,逐步导致掌指关节和指间关节出现不可逆性屈曲畸形的疾病,可严重影响手功能[1]。国外的研究资料显示,DD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可达4%~6%,并具有明显的人种差异[2]。我国至今尚缺少较完整的流行病学研究资料。多年来,由于学者们对DD发病机制认识不足,靶向治疗方案很难得到开发,故DD治疗局限于支具、纤维蛋白酶注射和外科干预等方法,复发率较高[3]。
1 病理生理学
肌成纤维细胞由成纤维细胞分化而来,可合成大量胶原,且其细胞质内含有肌纤维束。在DD病变组织中,收缩的肌成纤维细胞可以通过形成挛缩结节产生纵向回缩力,而沉积的胶原则与结缔组织整合并产生条索,最终造成不可逆的挛缩畸形。
Malsagova等[4]发现,掌指关节周围有一种新的微结构即掌指螺旋片。该结构近端起自腱前带,远端与Cleland韧带和Grayson韧带相延续,螺旋攀附于指掌侧固有神经血管束周围,能够增强神经血管束的稳定性。该结构的发现可以解释骨间肌和蚓状肌参与的DD掌指关节挛缩病例中螺旋条索的来源[5]。
2 遗传学
2.1 遗传特性
DD有一定的遗传倾向。Dibenedetti等[6]对DD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该病具有多种常染色体遗传特性。Larsen等[7]的研究证实,患病亲代的同卵双生子发病率较高,提示遗传因素在DD发病中的重要性。DD常与糖尿病、癫痫等疾病发生于同一个体,这些疾病可由线粒体基因突变引起[8]。Bayat等[9]认为,DD也具有母系遗传特征。然而,目前尚缺乏针对DD的遗传学检测方法。
2.2 基因组学
目前尚未发现DD的单一致病基因,但某些基因突变或表达异常可能与DD发生和发展有关。
编码基因内部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可直接影响蛋白结构或其表达水平。多个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正逐步揭示DD发病的基因组学基础。Dolmans等[10]通过GWAS首次报道,多个Wnt信号转导通路相关基因的SNP位点与DD有关,其中WNT2、WNT4、WNT7B和R-脊椎蛋白(RSPO)2等基因已通过牵连位点间的基因关系分析得到证实。过度激活的Wnt信号转导通路与器官纤维化有关,上述基因的表达产物均可直接或间接参与Wnt信号转导通路,并通过Wnt信号转导通路的依赖或非依赖途径引起组织过度纤维化[11]。Becker等[12]通过全基因组荟萃分析发现,近年来发现的Wnt信号转导通路异常均可导致DD发病。在Dolmans等[10]的GWAS基础上,Ng等[13]将可能的致病基因位点数量扩充至26个并开展更大样本的GWAS,发现这些致病基因位点主要位于Wnt信号转导通路相关基因座内或其附近,再次证实Wnt信号转导通路在DD发病中的重要性。Major等[14]通过表达组学相关研究(TWAS)发现,位于6、11、16和17号染色体的基因区段与DD发病相关,可证实相关基因在DD发病和进展中发挥作用。Jung等[15]通过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GCNA)发现,内质网应激和未折叠蛋白反应相关基因表达在DD病变组织中均有显著改变,并通过多表型回归分析证实锌指蛋白57相关基因在DD发生和发展中与异常蛋白合成、堆积有关。Riester等[16]发现,DD病变组织中与胶原合成相关的微RNA(miRNA)转录显著减少,提示非编码RNA可能调控DD发生,尤其在调控细胞外基质蛋白合成等方面。
尽管学者们对DD的基因组学研究尚不完善,但过度激活或缺乏抑制的Wnt信号转导通路很可能是DD发病的重要环节。针对该信号转导通路相关基因的研究或许有助于开发DD的基因学检测方法和靶向药物。此外,不同学者的研究发现了不同的DD遗传特性。通过检测突变基因的核内(染色体)或核外(线粒体等)位置可对DD进行分型,将有助于DD诊断并予以更有针对性的治疗。
3 细胞信号转导通路
3.1 Wnt/β-catenin信号转导通路
多种Wnt蛋白均可激活相关膜受体,从而抑制糖原合酶激酶-3β对β-连环蛋白(β-catenin)的磷酸化并减少β-catenin降解,使β-catenin能够在核内富集并与T细胞因子或淋巴样增强子结合蛋白结合,从而调控靶基因表达,促进细胞增殖与存活[17]。虽然β-catenin降解还会受到整合素信号转导通路、p53和转化生长因子(TGF)-β等调控,但目前仅报道TGF-β与DD相关[18-20]。
过度激活的Wnt信号转导通路可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导致器官纤维化[11]。DD患者成纤维细胞可大量增殖,多个GWAS亦发现WNT基因的SNP变异。虽然学者们尚未证实能够过度激活Wnt信号转导通路的WNT基因稳定突变,但已发现β-catenin在DD病变组织中表达水平升高[21]。鉴于Wnt信号转导通路异常与DD发生和发展有关,能够促进β-catenin降解或抑制其激活靶基因的相关药物或将成为靶向治疗DD和降低DD复发率的新选择。
3.2 Akt信号转导通路
蛋白组学研究已证实,蛋白激酶B(Akt)信号转导通路在DD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IGF-1R)和erb-b2受体酪氨酸激酶-2是在Akt信号转导通路中被激活的下游信号分子,可通过结合靶基因促进细胞增殖、分化,抑制细胞凋亡。帕金森关联去糖化酶(PARK)7可抑制Akt信号转导通路的抑制物,从而间接激活Akt信号转导通路。Casalini等[22]通过蛋白组学研究证实,具有直接或间接激活Akt信号转导通路作用的IGF-1R、erb-b2受体酪氨酸激酶2和PARK7等均可在DD患者的成纤维细胞中高表达,提示由Akt信号转导通路激活引起的成纤维细胞增殖、肌向分化和细胞骨架重构是导致DD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
不但成纤维细胞的Akt信号转导通路会被异常激活,该通路的上游或下游信号分子也会在DD病变组织内的小血管内皮细胞和汗腺滤泡细胞中过表达[23],并可通过引起局部炎症导致成纤维细胞增殖和分化[24]。
Akt信号转导通路涉及的调控因子较多,细胞功能较广,仅通过抑制Akt活化治疗DD弊大于利,而该通路中引发DD的关键蛋白也尚未确定。因此,对DD患者成纤维细胞、肌成纤维细胞及细胞外环境中转录谱和表达谱的改变进行高通量鉴定可用于寻找Akt信号转导通路的靶向治疗方案。
3.3 Hippo信号转导通路
Yes相关蛋白(YAP)1和带PDZ结构域结合模体的转录共激活子(TAZ)是受Hippo信号转导通路抑制的下游信号分子。当Hippo信号转导通路被抑制时,YAP1/TAZ可被转运至核内与靶基因结合,促进细胞增殖与组织再生。YAP1在DD病变组织中过表达,可促进成纤维细胞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并可通过沉默DD患者肌成纤维细胞的YAP1基因抑制细胞增殖[25]。TAZ可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和收缩,并通过促进分泌促纤维化因子导致组织硬化[17]。然而有研究证实,机械应力下的YAP1/TAZ过表达不完全依赖Hippo信号转导通路的抑制状态,提示YAP1/TAZ可能作为多条信号转导通路的交叉点调控DD发生和发展[26]。因此,寻找YAP1/TAZ的特异性抑制物可以作为研究YAP1/TAZ高表达突变DD患者治疗方案的新思路。
4 细胞外环境
4.1 生长因子
4.1.1 TGF-β
目前认为,TGF-β是DD发病过程中最主要的生长因子。TGF-β可促进成纤维细胞或肌成纤维细胞合成Ⅰ型和Ⅲ型胶原并抑制成纤维细胞凋亡[18],最终导致DD病变组织内胶原大量堆积。因此,抑制TGF-β及其下游通路可以改善DD病变组织内的异常细胞增殖和胶原堆积情况。研究表明,吡非尼酮能够抑制DD病变组织内由TGF-β1诱导的Akt、p38、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RK)和肌动蛋白轻链的磷酸化[20],这些蛋白的磷酸化与成纤维细胞存活、增殖和生长密切相关,提示吡非尼酮可作为TGF-β1的靶向抑制剂阻断DD病变组织异常纤维化。地塞米松也可通过抑制纤维瘤干细胞(FSC)表达TGF-β1减弱下游Smad通路的激活,从而抑制DD病变组织中FSC向肌成纤维细胞分化,故对早期DD有一定的缓解作用[27]。骨化三醇是维生素D的代谢物,有显著抑制胶原合成的作用,而维生素D缺乏与血清TGF-β升高密切相关[28]。维生素D缺乏可通过增加局部TGF-β含量促进DD患者肌成纤维细胞合成胶原,从而导致挛缩[19]。
4.1.2 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可作为成纤维细胞的丝裂原,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和Ⅲ型胶原合成。DD病变组织中成纤维细胞PDGF可过表达,其原因尚不清楚[8]。PDGF过表达可受其他生长因子调控或因相关基因被重复拷贝而产生放大效果,其上游原癌基因沉默同样值得关注。
4.1.3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尽管DD病变组织中存在由血管内皮细胞介导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负反馈调控,但FGF及其受体过表达仍能引起成纤维细胞的异常增殖,进而导致纤维化和结节形成。此外,FGF也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引起局部血流减少,造成缺氧环境,导致氧自由基堆积,引发局部炎症[29]。这与DD病变组织中炎症因子显著增多的事实相吻合[30-31]。
4.2 肿瘤坏死因子
肿瘤坏死因子(TNF)不仅可以通过促进TGF-β表达激活经典Wnt信号转导通路,而且可以通过抑制糖原合成酶激酶(GSK)-3β对β-catenin的磷酸化强化经典Wnt信号转导通路下游靶基因的作用,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并向肌成纤维细胞分化[32]。
DD病变组织肌成纤维细胞的收缩力随重组人TNF水平升高而增强,与收缩力峰值对应的重组人TNF水平与病变组织TNF水平近似,而正常掌腱膜组织内肌成纤维细胞的收缩作用在同样重组人TNF水平下反而受到抑制[30]。该结果提示,病变组织肌成纤维细胞对TNF的敏感性明显增强,故阻断TNF即有可能阻断下游异常信号转导通路。Izadi等[24]发现, DD发病早期掌腱膜组织TNF主要由M2型巨噬细胞表达,外源性TNF可通过特异性结合挛缩结节内基质细胞的TNF受体(TNFR)2促进白细胞介素(IL)-33表达,IL-33反过来又可促进病变组织免疫细胞表达TNF,从而形成正反馈环路。同时,抑制IL-33不仅可以抑制巨噬细胞表达TNF,也可以抑制病变组织中肌成纤维细胞增殖的相关基因,提示抑制IL-33和阻断TNFR2可在TNF异常表达诱导的DD发病中发挥抑制作用。
4.3 基质金属肽酶
基质金属肽酶(MMP)14是DD的另一个高危因素,可激活细胞外基质中的MMP2并使其发挥Ⅳ型胶原酶等作用[13]。敲低MMP14基因可缓解成纤维细胞收缩并减少MMP2激活[33]。MMP14在DD结节中过表达,应用广谱MMP抑制剂的肿瘤患者中亦有出现DD样症状的案例,提示多种MMP参与DD发生和发展。
4.4 整合素
整合素(ITG)α-11在DD病变组织中存在显著的SNP变异[27]。ITGα-11可黏附细胞外基质中的结构蛋白和细胞骨架,从而实现细胞与细胞之间力的传导并调控组织收缩。虽然目前尚无 DD病变组织ITGA11表达情况的相关报道,但该基因在特发性肺纤维化组织中过表达可提示其与多种组织纤维化进展有关[34]。
4.5 免疫反应与炎症
DD与免疫反应和局部炎症有关。DD病变组织内有多种免疫细胞,它们能分泌TNF、IL-6和IL-8等炎症因子并介导局部炎症反应。近期研究已证实,轻微的慢性局部炎症可通过TNF正反馈通路促进肌成纤维细胞增殖和胶原合成[24]。
另有学者认为,DD是一类自身免疫病。活化的T细胞主要位于结节内小血管周围,并可表达一系列限制性T细胞受体,如人类白细胞抗原相关受体等[35]。尽管该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仍可提示一种或多种自身免疫性抗原极有可能作为DD发病早期的始动因素,而自身免疫性抗原暴露常与局部微血管受损有关[31]。尽管如此,相关的自身免疫性抗原尚未得到证实,结节内微血管改变情况也尚不明确。
5 结语
近年来,学者们对DD发生、发展的认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已知的遗传学改变、细胞内信号转导通路异常以及局部免疫反应和炎症反应均不能以“一元论”完美地揭示DD的发病机制。DD的遗传特性也提示,该疾病可能存在多种分型,故其诊治策略应在明确分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未来针对DD发病机制的研究可以围绕新的遗传学改变、重要信号分子和动物模型建立等方面展开,以明确DD发病机制中的重要节点,从而实现针对基因或信号分子的精准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