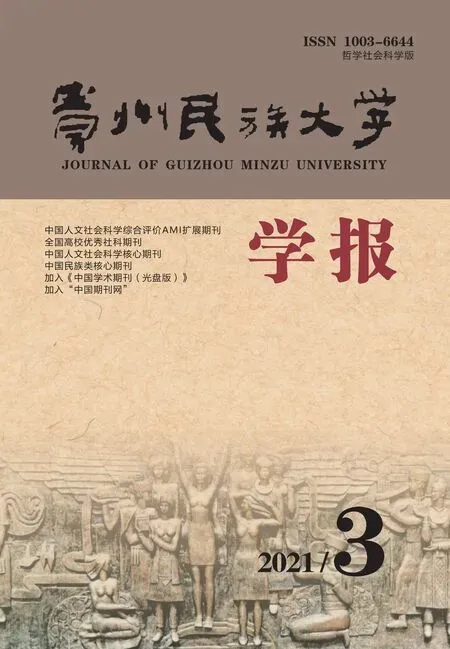重复起诉当事人相同要件研究
——民法典时代既判力扩张理论之探讨
陈 晓 彤
一、引言
“重复”是指同样的事物再次出现,在民事诉讼法语境中,重复起诉指相同的起诉再次被实施。有限的公共资源及尽快解决纠纷从而恢复和平秩序的倾向,决定了司法制度对重复起诉的禁止性态度。《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要求当事人对已有生效裁判、调解书的案件寻求特殊的再审救济,不允许另诉。体现“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禁止重复起诉制度不仅有助于节省法院资源、保障法律关系的安定性,还有利于节约当事人的成本、防止重复诉讼带来的无尽烦扰。但若重复起诉范围的判断不恰当,当事人的程序和实体权利均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因此,界定重复起诉范围的标准至关重要。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颁布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为重复起诉设置了三项构成要件,其中“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为主观要件,“诉讼标的相同”与“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为客观要件。
在前后诉当事人是否相同的理解与适用中,学理上借鉴自大陆法系的既判力扩张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1)① 参见翁晓斌:《我国民事判决既判力的范围研究》,《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张晓茹:《论民事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范围及扩张基础》,《河北法学》2012年第5期;张卫平:《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根据、例外与制度化》,《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万亿:《重复起诉规范要件再解释与裁判标准构造》,《人民司法》2018年第10期。以当事人相同作为重复起诉的主观判断标准,意味着诉讼与裁判的效力原则上具有相对性与封闭性,要求当事人自负其责,同时保护案外人不受当事人之间诉讼或裁判的不利影响,这正是《民法典》确立的意思自治原则在《诉讼法》中的延伸。意思自治原则赋予当事人处分自身私权利的自由,不仅可以拒绝国家的干预,还可以防止其他私权主体的影响。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运行模式与人们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复数的权利、法律关系及法律主体之间往往会形成复杂的网络,互相影响成为法律关系与法律主体的常态,《民法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出来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下,判决的既判力极有可能不得不扩张及于特殊的案外人,否则会导致纠纷解决的结果落空,引起实体法律关系的混乱,这就是既判力扩张理论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自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法典》为既判力扩张理论的中国化提供了契机,即结合实体法与程序法探讨适合中国的既判力扩张制度,从而解决禁止重复起诉的主观范围问题。
鉴于此,本文首先对自大陆法系借鉴而来的既判力扩张理论进行介绍与评析,并结合我国《民法典》中相关规定确定该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应用空间与方式;接着从实体与程序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分析既判力扩张理论在复杂诉讼形态中可能有的体现;最后分析既判力扩张理论与我国案外人申请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等案外人救济机制之间的关系,这同样涉及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交互影响等复杂的理论。将这些问题梳理清楚,不仅仅是研究我国重复起诉当事人相同这一主观要件之必需,还是在《民法典》背景下探讨既判力扩张理论的应有之义。
二、既判力扩张理论在我国《民法典》背景下的应用
既判力扩张理论源自大陆法系,作为既判力相对性原则之例外而存在。①(2)① 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是民事诉讼仅追求纠纷的相对性解决这一特征的体现,即既判力仅在判决当事人之间发生,不及于其他人。参见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07-108页;蒋玮:《大陆法系诉讼系属中重复起诉禁止及经验借鉴》,《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其基本内涵为,基于防止诉权滥用、保障纠纷解决的实效性、实现法的安定性等理念,特定范围内的案外人应如当事人一般承受判决的既判力。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既判力扩张表现在法律规范或判例、通说中具体的案外人类型,每一种类型都彰显一种特定案外人与判决当事人或判决标的之间的特殊关系。我国学者借鉴德国或日本既判力扩张类型,或对两国情形加以整合,界定了承受既判力的案外人范围。这些学说对实务界人士产生了一定影响,并慢慢向司法实践渗透。②(3)② 参见沈德永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第633页。但这些学说及实务界人士所持观点中主张的受既判力扩张所及的案外人类型,未曾与我国《民法典》的原则及具体规范进行对应,实践中由于理解的偏差,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误解与误用。③(4)③ 实践中存在着某种过于宽泛理解诉讼担当的趋势和错误理解当事人继受人的做法,如将保险代位求偿诉讼理解为被保险人求偿诉讼的重复,将责任保险人视为被保险人的继受人,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四终字第00131号民事裁定书;或将同一侵权行为共同实施者作为不同被告的诉讼理解为重复起诉,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6633号民事判决书。为了更精确地划定既判力扩张在我国语境下的界限,有必要具体分析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探讨案外人与前诉当事人或诉讼客体之间存在的关系,从而确定哪些种类的关系允许案外人承受既判力的扩张。值得注意的是,既判力不仅具有消极的遮断后诉(即禁止重复起诉)的作用,还具有积极的拘束力;重复起诉不仅可以发生在判决生效后,还可能发生在诉讼系属之中,④(5)④ 诉讼系属是基于当事人的起诉特定诉讼请求处于法院审判之中的状态,同一个诉讼不应出现两个处于法院审判中的状态,故诉讼系属具有排除效,参见张卫平:《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诉讼系属排除效的主观范围也根据既判力扩张理论来确定,参见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第108页;罗森贝克、施瓦布、哥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717页。借助既判力扩张理论来研究重复起诉的主观范围时应对此保持一定的警惕。
(一)既有既判力扩张理论简介
我国的既判力扩张理论受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影响较大,关于受既判力扩张所及的案外人类型,德国与日本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对我国不同学者的观点也有所影响。
在共性方面,德国与日本均存在以下三种既判力扩张类型:(1)口头辩论终结后当事人的继受人;(2)诉讼担当时的被担当人;(3)家事诉讼判决具有对世效、公司诉讼的某些判决对所有实质上参与法律关系的案外人产生既判力。这些共同类型之外,在德国,既判力还及于(1.a)诉讼系属后口头辩论终结前当事人的权利继受人、(1.b)诉讼系属后从当事人处获得系争标的物直接占有者,此外(4)基于实体依赖关系也存在既判力扩张,如无限公司股东在被要求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时,受公司已获判决中关于公司债务是否成立之判断的拘束,责任保险人可援引被保险人胜诉判决(反之亦然),保证人可援引主债务人胜诉判决等等。日本却不承认基于实体依赖关系的既判力扩张,其既判力还及于(4)诉讼标的物“持有人”,及(5)诉讼脱退人。①(6)① (1.a)与(1.b)是为了表示在德国此两种情形可与(1)归为一大类。参见罗森贝克、施瓦布、哥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175-1180页;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486-490页。
德日的差异对我国学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翁晓斌教授认为当事人继受人应包括诉讼系属后的继受人,请求标的物占有人不限其取得占有的时间,未提及诉讼脱退人与基于实体依赖关系的既判力扩张。②(7)② 参见翁晓斌:《我国民事判决既判力的范围研究》,《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张卫平教授则较为全面地接受了日本的既判力扩张类型,但基于我国《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主张我国对诉讼中权利义务的转移采取了“当事人恒定主义”,故既判力还及于诉讼系属中的受让人。③(8)③ 参见张卫平:《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根据、例外与制度化》,《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张卫平:《诉讼系属中实体变更的程序应对》,《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当事人恒定主义”,是指诉讼中系争的权利义务转让的,不影响原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原当事人事实上为受让人进行了诉讼担当。与此相对是“诉讼承继主义”,是指诉讼中系争的权利义务转让后,原当事人丧失当事人适格,必须更换当事人,否则判决不对受让人产生既判力。仅张晓茹教授在介绍域外既判力扩张类型时提及基于实体依赖关系的既判力扩张。④(9)④ 参见张晓茹:《论民事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范围及扩张基础》,《河北法学》2012年第5期。
域外既判力扩张制度与学说不一定能在我国语境下妥帖地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仅规定了“当事人相同”这一抽象要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在为其编写的解说书中,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对该要件作实质性理解,即诉讼担当人与被担当人同一,当事人继受人、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标的物的人、特定家事或团体法律关系的判决既判力所及的一般第三人均与当事人实质相同。①(10)① 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633-634页。这一对司法解释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在法律效力上或许存疑,但却对司法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②(11)② 该解说书出版发行前,实务中法院很少明确其认为应承受既判力的案外人属于何种类型。该书发行后,裁判文书网上可检索到相当数量的一批案例,法院援用“当事人的继受人”“诉讼担当”等标准考察前后诉当事人是否相同。不过,其在表述的明晰性、准确性及理由方面尚存在较大问题,何谓“诉讼担当”,当事人继受人及直接占有请求标的物者应否满足一定的条件,既判力究竟在哪些情形下及于一般第三人,均存在疑惑,在实务中可能导致重复起诉主观范围过宽或过窄两个极端。
界定属于重复起诉主体的案外人范围时,借鉴域外既判力扩张理论中的案外人类型的确很有助益,但不结合我国的实体法规定加以分析,就不能更贴合本国的实践需要,解决本国的问题。
(二)结合我国民法典对既判力扩张理论进行评析
大陆法系的既判力扩张理论在受既判力扩张所及的案外人类型方面已经取得较大成果,在结合我国《民法典》及相关民事实体法规范进行检视和分析之前,需要先挑出两种不能被涵盖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的案外人类型。第一种案外人类型为日本的诉讼脱退人,诉讼脱退是指,第三人为了主张自己的权利参加诉讼,原一方当事人经对方的同意可退出诉讼,其退出诉讼后,法院对第三人与对方当事人作出的判决对该脱退人也产生既判力及其他效力。③(12)③ 参见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第490页。观之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无诉讼脱退制度,故暂时不需承认此种案外人类型。第二种类型为德国的基于实体依赖关系的既判力扩张,此种既判力扩张与实体法的关联尤为明显,但是此种效力的效果并不禁止后诉,而体现为案外人在后诉中承受前诉判决的积极拘束力。因此,在研究重复起诉当事人相同要件的本文中,限于篇幅不予深入研究。
(1)当事人的继受人
继受包含两种内涵,一为继承,一为受让。《民法典》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自然人依法享有继承权。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通过继承方式取得的权利,与被继承人享有的权利当然具有同一性,相关的法律关系仅仅在主体上发生了变动。关于权利义务的受让,《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规定了债权的转让,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了债务的转让,第五百五十五条规定了合同权利义务的一并转让,符合条件的受让人也应当与转让人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因此,在权利义务的被继承人或转让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已经实施诉讼并得到生效判决之后,如果还允许继承人或受让人以自己并非诉讼当事人为由提起相同的诉讼,意味着法院就同样的权利义务内容进行两次审判,若作出不同的判决就会引起实体法律关系的混乱。因此,有必要承认当事人的继受人受既判力扩张所及。
我国虽无既判力及于继承人(又称概括继受人)的明确规范,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给付判决的执行力及于继承人或权利义务承受者,此种执行力扩张的根据就在于既判力扩张。①(13)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案外人类型上,执行力扩张与既判力扩张存在差异,参见肖建国、刘文勇:《论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及其正当性基础》,《法学论坛》2016年第4期。至于受让人(又称特定继受人),《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诉讼中系争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原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受让人受判决的拘束。该规则背后的法理是“当事人恒定主义”。②(14)② 参见张卫平:《诉讼系属中实体变更的程序应对》,《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系争权利义务转移后,原当事人不再是实体权利义务主体,本不具备继续实施诉讼的当事人适格,应变更当事人,但为了程序的安定性,考虑到权利义务转移是受让人意思自治的结果,且受让人本应注意其受让的标的是否处于诉讼系属之中,法律赋予形式当事人(原权利义务主体)以诉讼实施权,使其对受让人进行“诉讼担当”,即代表受让人实施诉讼,受让人自应为既判力所及。虽然《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未规定诉讼终结后的特定继受,但此类受让人与继承人一样不可能挑战判决的既判力。③(15)③ 实践中法院也采取了此种观点,参见平阳县人民法院(2015)温平民初字第237号民事裁定书,该案中的权利义务转移是一种公法行为(当地国土局没收了原当事人的土地),法院认定前后诉构成重复起诉。德国也认为权利义务的转让包括公法行为,参见罗森贝克、施瓦布、哥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179页。因此,诉讼系属后的特定继受人均属于重复起诉的主观范围。
(2)诉讼担当
诉讼担当是指争议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主体之外的人,基于法律或权利义务主体的授权,作为当事人实施诉讼。①(16)① 参见张晓茹:《再论诉讼担当——以担当人和被担当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关系为视角》,《法学杂志》2012年第2期。前者为法定的诉讼担当,我国《民法典》规定了财产代管人(第四十二条)、遗产管理人(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企业破产法》规定了破产管理人,②(17)② 在我国实践中,有些破产相关诉讼以破产债务人为当事人,以破产管理人为诉讼代理人或代表人,如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4民终193号民事裁定书,这种做法存在一定的问题,参见冀宗儒、钮杨:《破产管理人民实施诉讼地位错位之分析》,《河北法学》2016年第4期。在被宣告失踪人享有的权利义务、遗产或破产财产的归属或分配成为诉讼争议的对象时,尽管财产代管人、遗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本人并不享有争议的权利义务,但基于法律的授权却可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诉讼,获得的判决效果应归属于权利义务的实际享有者,既判力也包括在内,此为法定诉讼担当下的既判力扩张。此外,《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但是该权利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有的学者将债权人代位诉讼也理解为一种法定诉讼担当,并进而将法定诉讼担当区分为共享型(或对抗型)诉讼担当与替代型(吸收型)诉讼担当,前者指担当人与被担当人共享对同一客体的诉讼实施权,后者指仅诉讼担当人享有诉讼实施权。在比较法上,前者不产生既判力扩张,仅后者产生既判力扩张。③(18)③ 参见黄忠顺:《诉讼实施权配置的模式构建》,《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4期。比较法上的资料vgl. Prütting/Gehrlein/Völzmann-Stickelbrock Rn. 39, 转引自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München 2010, S. 234. 高桥宏志:《民事诉讼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第218页。但也有学者认为债权人代位诉讼不构成诉讼担当,此时债权人享有固有的当事人适格,为此债权人获得的判决既判力不扩张及于债务人。④(19)④ 参见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17页。不过,《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十六条规定:“债务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若在《民法典》背景下此种司法实践被延续下来,关于债务人应承受判决何种效力的问题应留待复杂诉讼形态部分去分析。
至于任意的诉讼担当,既然争议的权利义务主体自己授权担当人实施诉讼,类比代理制度,该权利义务主体自然应当受担当人实施诉讼所获判决既判力所及。不过,目前我国关于任意诉讼担当的前提条件和类型还未形成完善的规则。①(20)① 参见肖建国、黄忠顺:《任意诉讼担当的类型化分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在实体法上,专利、商标、著作权的权利人可以授权独占许可使用权人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为维护相关权利而实施诉讼;在诉讼法上,代表人诉讼制度允许人数众多的当事人选择并授权代表人实施诉讼,不过此时授权人并未脱离诉讼故不存在既判力扩张适用的空间。除此以外,权利义务关系主体是否还能选择一定范围内的人员代替自己实施诉讼,应当看该担当人是否对解决该案争议享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3)请求标的物占有人或持有人
前文已述,德国规定诉讼系属后从当事人处获得占有者承受既判力,占有人包括在广义的权利继受人范围内。②(21)② 参见罗森贝克、施瓦布、哥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176页。日本则规定持有人承受既判力扩张,持有人为不论何时仅为当事人而持有之人,其对标的物不具备自己独特的利益。③(22)③ 参见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第489页。在我国,《民法典》第二十章专门规定了占有制度,但似乎并未采纳“持有”这个概念,仅有“仓单持有人”“许可持有人”的用法。就占有而言,不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占有属于次于所有的一种状态,因此将诉讼系属后的占有人类比受让人,符合法律的解释原则。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有关单位或公民持有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票证的应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而交出,这意味着不享有某种法律地位而仅仅为了他人的利益持有财产或财产证明的主体,应当忍受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与其将其理解为既判力扩张,不如仅将其归为执行力扩张的范畴,毕竟此种持有人本来就不具备提起诉讼的利益,不存在重复起诉的可能。
(4)特殊判决的“对世效”
大部分诉讼制度具有“跨实体领域”的特征,统一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实体纠纷,但不同领域的实体法律关系与纠纷特征可能差异甚大,诉讼制度应予以特殊考虑。例如身份关系和公司内部关系,在涉及复数主体时,为方便解决纠纷及确认法律关系,法律允许任一利益相关主体单独起诉,但因为身份和公司法律关系具有特殊性,又有必要对其进行划一性处理,不能允许不同主体实施多个诉讼导致法律关系的混乱,既判力扩张有助于实现这种统一性。
仅有限范围内的法律关系(因涉及公共利益)对这种统一性要求较高,如身份关系(如婚姻、亲子、收养)的确认与形成判决,公司股东会决议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的判决,公司解散诉讼的判决等。①(23)① 大陆法系实体法对此有规定,除身份关系和公司内部关系外,德国还在破产程序、强制执行存在多个债权人时规定,争执债权之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债权人产生拘束力。我国仅在《公司法解释(二)》第6条规定解散公司诉讼的判决约束全体股东。有的学者将此种效力称为对世效,但一般案外人若与争议的权利义务无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实施诉讼的当事人适格,根本无法提起诉讼,即使其应尊重此类判决,也不属于重复起诉主体。②(24)② 德国有学者主张身份事项判决的“对世效”其实是形成权法律后果的体现,而非既判力,Vgl. Calavros, Urteilswirkungen zu Lasten Dritter, 1978, S. 114ff.转引自MüKoZPO/Gottwald, 5. Aufl. 2016, ZPO §325 Rn. 6.
在我国实践中,还有两种案件类型涉及前后诉当事人是否相同的问题。其一,前诉遗漏不可或缺的必要共同诉讼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当事人可申请再审,故学者主张不得另诉,但并非《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适用的对象。③(25)③ 参见王亚新、陈晓彤:《前诉裁判对后诉的影响——<民诉法解释>第93条和第247条解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实践中法院却对此类案件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④(26)④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8100号民事裁定书。不过在效果上一致。其二,前诉原被告仍为后诉原被告,原告或被告一方或两方增加了主体,看起来当事人不再相同,⑤(27)⑤ 有些法院可能因此不认定重复起诉,如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219号民事裁定书。但若新增的原告或被告并非争议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不具备当事人适格,法院仍有可能将后诉视为重复起诉,⑥(28)⑥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2民终3475号民事裁定书。实际上是部分重复起诉、部分不符合起诉条件。
综上所述,基于我国《民法典》及相关实体法规定,受到判决既判力扩张所及的案外人仅为与当事人存在继受关系或代表关系的主体,包括口头辩论终结后当事人的概括继受人、诉讼系属后特定继受人或获得直接占有者、诉讼担当时的被担当人、特定人身关系和公司内部关系的全体参与人。
三、复杂诉讼形态下的重复起诉主体范围
前诉为共同诉讼或者存在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时,判决在共同诉讼人之间、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是否产生既判力,也属于广义上的既判力扩张问题。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将既判力限制在诉讼当事人之间,更具体地说,限制在具有明示的对抗性地位的当事人之间,但在复杂诉讼形态中,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可能并不存在明示的对抗性,此时确定既判力范围尤为困难,关于前后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实践操作也显得比较混乱。遗憾的是,理论研究在此存在较大的“空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共同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均属于诉讼法上的制度,但共同诉讼成立的原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利益均根植于民事实体法律关系,这为本文采取实体与程序相结合的视角探讨既判力扩张理论在复杂诉讼形态下的体现奠定了基础。
(一)共同诉讼中的既判力主观范围
共同诉讼是复杂诉讼形态中的一种典型形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分为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根据实践中的样态学理上又将必要共同诉讼分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与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从意思自治的原则出发,似乎只要作为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参与了诉讼,就将自己置于法院的审判权之下,应当接受判决的既判力。但是共同诉讼既然作为复杂的诉讼形态,其既判力也必然具有特殊性。
案例1:A银行贷款给B公司,C公司及C公司法定代表人D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A以B、C、D为共同被告提起贷款追偿之诉,法院判决B偿还借款利息、C和D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C诉D,以A为第三人,主张D利用其法定代表人身份与A签订保证合同,侵害C公司利益,请求判令D停止侵权、确认保证合同无效。A主张后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认为高管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与担保合同纠纷为不同法律关系,且诉讼主体不同,故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①(29)① 前诉判决为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商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后诉为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32-1号民事裁定书。但法院最终由于公司对现任法定代表人起诉却暂无新的法定代表人,起诉在法律上无法代表公司的真实意思而裁定驳回。
在该案中,若不分阵营、不分角色差异地认为前诉所有当事人承受判决的既判力,就很容易认为后诉当事人与前诉当事人具有同一性,从而适用禁止重复起诉制度。但很明显,在共同诉讼中必须划分阵营来看待既判力主观范围问题。
不同种类的共同诉讼中,当事人的阵营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中,由于所有的当事人都围绕着唯一的不可分割的争议对象实施诉讼,判决在所有当事人之间、任意两个或n个(n小于全部数目)当事人之间均产生既判力,任意两个或n个当事人就相同的争议对象提起后诉都不被允许。在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中,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也认为存在既判力的扩张,前提是对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范围加以严格的限制。在普通共同诉讼中,既然共同诉讼人彼此之间本来就是可分可合,法院也不对争议对象作出合一确定,仅在具有对抗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作出判决,既判力不能及于不存在对抗关系的当事人之间。①(30)① 参见张永泉:《必要共同诉讼类型化及其理论基础》,《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王亚新:《“主体/客体”相互视角下的共同诉讼》,《当代法学》2015年第1期;段文波:《德日必要共同诉讼“合一确定”概念的嬗变与启示》,《现代法学》2016年第2期。
但是问题在于,我国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之间边界十分模糊,什么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合一确定,什么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实质意义上的分别判决,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存在颇多疑问。②(31)② 参见段文波:《德日必要共同诉讼“合一确定”概念的嬗变与启示》,《现代法学》2016年第2期;卢佩:《多数人侵权纠纷之共同诉讼类型研究》,《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罗恬漩:《数人侵权的共同诉讼问题研究》,《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蒲一苇:《诉讼法与实体法交互视域下的必要共同诉讼》,《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任重:《反思民事连带责任的共同诉讼类型——基于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分析框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6期。从实践中来看,要解决共同诉讼的类型及既判力主观范围问题,必须将诉讼法与实体法结合起来。
案例2:交通事故受害人A诉肇事车主B、该车保险公司C,请求损害赔偿。法院认为A应得到赔偿,其主张的鉴定费、拆解费和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范围,故该部分费用由B承担,其他由保险公司C承担。判决生效后,B依据保险合同诉C,请求C赔偿鉴定费、拆解费和停运损失。法院认为前后诉当事人、诉讼标的相同,后诉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判决结果,构成重复起诉。③(32)③ 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2015)农民初字第3832号民事裁定书,类似案件有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5民终388号民事裁定书。
案例3:A诉B、C,请求判令B承担医疗保险费、C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判决支持。B履行判决确认的义务后,起诉C追偿。C抗辩称前诉判决明显错误,自己没有过错不应与B承担连带责任。后诉法院未认定重复起诉,而是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3条认为,已为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C未能推翻,判决支持B的诉讼请求。①(33)①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新中民四终字第492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2与案例3存在较强的相似性,在主体方面均为前诉共同被告(同一阵营)转化为原被告的对立态势(对抗阵营),在客体方面前后诉诉讼请求中要求的权利均不相同,后诉均为追偿诉讼。但案例2法院认为前后诉构成重复起诉,即认定前后诉当事人相同;案例3法院却并不认可重复起诉。究竟是其中一个法院的做法存在问题,还是这两个案件本质上存在差异呢?为解决问题,必须从共同诉讼的类型、前后诉法律关系的关联性出发加以分析。从共同诉讼的类型出发,不论案例2还是案例3,前诉均非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那么它们是否属于法院应当作出合一确定的案件类型,即可以称之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那种案件类型呢?这就必须分析前后诉法律关系的关联性。在案例2中,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请求权与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索赔权之间存在某种“竞合关系”,即其中一个实现了,就会导致另外一个也消灭,因此在前诉法院已经对哪些赔偿项目属于保险公司理赔范围的问题作出判决的情况下,投保人提起后诉要求理赔,确实会影响到前诉判决的效力。而在案例3中,前诉判决仅确定共同被告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二者之间的责任分担并未作出判决,承担了责任的债务人提起追偿之诉是正当的救济途径。换言之,在案例2中,关于加害者的责任与保险公司的责任法院不得不作出合一的确定,而在案例3中法院不必对连带债务人之间的责任分配作出合一的确定。因此,前后诉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的确存在不同。
共同诉讼主体对抗态势的变更还有一种情形,即由于诉讼客体的变更(如原告诉讼请求改变)导致主体的实体法地位发生变化,如下例:
案例4:A诉B公司、C,主张其借款给B公司,B公司以不动产提供抵押,B公司的唯一股东C与B人格混同,故请求判令B公司还款或承担担保责任、判令C承担股东连带责任。法院查明合同实际签订者及收款人均为C,且无B公司公章,判决驳回A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A起诉C和B公司,基于同一份合同,主张借款发生在A、C之间,B提供了抵押担保,请求C偿还借款,B承担担保责任。法院认为前诉主债务人为B公司,后诉主债务人为C,前后诉当事人地位、诉讼标的、诉讼理由均不同,后诉不属于重复起诉。①(34)①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248号民事判决书。
该案当事人前后诉的地位形式上未变,实质上却已不同。A前诉要求C承担股东连带责任,后诉则要求其作为主债务人偿还借款,该请求在前诉中未曾作为诉讼客体由法院加以审理,故不属于重复起诉。②(35)② 该案A对B公司要求承担抵押责任的请求,在前后诉具有一致性,故后诉部分属于重复起诉。
(1)第三人参加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了两种第三人参加诉讼形态,一种是对本诉当事人之间诉讼标的主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另一种是虽不主张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③(36)③ 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在适用中仍存在较多不清晰之处,参见王亚新:《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制度框架与程序操作》,《当代法学》2015年第2期;胡军辉:《论共同诉讼与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的界分》,《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两种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存在较大差异,但《民事诉讼法》授权法院直接判令某些无独三承担责任,在二者之间促成某种转化,故有独三与被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三均具备当事人地位,④(37)④ 无独三被判决承担责任是我国独有的现象,体现了法院超职权主义的特征,引发学者诸多争议,参见蒲一苇:《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判决效力范围》,《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第169页。仅未被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三仍停留在“准当事人”的状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为《民诉法解释》编写的解说书中,认为有独三以独立方式参加诉讼,具有当事人的地位,故受一事不再理的约束;而无独三可区分为独立进行诉讼和辅助当事人诉讼这两种类型,前者实质上具有当事人地位故受一事不再理约束,后者仅具有辅助地位故不属于重复起诉主体。⑤(38)⑤ 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第634页。
案例5:A公司为进口一批大豆,申请B银行开立信用证,A向B出具信托收据约定B享有该批大豆的所有权。因A不支付货款B银行支付了信用证款项。B诉A,根据信用证法律关系与信托收据请求法院确认该批大豆属自己所有。诉讼中,C作为无独三参加诉讼,主张其与A存在货物置换协议,A已将系争大豆置换给了C。法院作出支持B请求的判决。判决生效后,C诉A,以B为第三人,请求确认C为系争大豆的所有权人,B主张后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认为前后诉请求权基础不同,前诉为信用证和信托关系,后诉为货物置换关系,且C在前诉仅为无独三,A在前诉全部承认B主张的事实及诉讼请求,若将后诉视为重复起诉,将剥夺C诉权。①(39)① 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四终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实践中也有将前诉原告诉前诉无独三视为重复起诉的案件,如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99号裁定书,但该案前后诉的主体与客体均不相同,并不属于重复起诉。
该案显示,无独三虽为参加诉讼的“准当事人”,毕竟不是当事人,无法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甚至无法对影响自己法律地位的事项进行充分的争执,若将其视为重复起诉主体,将剥夺其获得司法保障的权利。
若无独三被判决承担责任,就具有了当事人的地位,法院在判断后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时会将其视为前诉当事人,如下例所示:
案例6:A诉B,C为第三人,请求判令B返还其从A处租赁的门面房、占有人C对交还该房屋予以协助,法院判决支持A的诉讼请求。第三人C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C以A为被告提起后诉,请求确认前诉系争房屋为C所有。法院认为,前后诉主体虽不完全一致,但C为前诉第三人且法院判决其承担责任,C在前诉已辩称自己才是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但被法院驳回,后诉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后诉构成重复起诉。②(40)②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9民终31号民事裁定书,前诉为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9民终1671号民事判决书。
本案中,其实A对所谓的“第三人”C提出了诉讼请求(要求其协助返还房屋),C实际上是共同被告,法院判决其承担责任是对A诉讼请求的回应。将实质上的被告称为“第三人”,可能会导致其无法充分攻击防御。此种实践操作意味着,无独三制度尚存在不清晰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
至于有独三,理论上认为其相当于原告,且本诉原被告均为其相对方,故其与原告或被告之一对抗实施后诉时,重复起诉主观要件均得到了满足。但在实践中,有独三提出的诉讼请求有时仅针对本诉被告,未对本诉原告明确提出诉讼请求,法院可能以“法律关系具有相对性”为由,认为前诉客体是原告与被告、有独三与被告之间的关系,后诉客体为有独三与原告之间关系,不构成重复起诉。①(41)①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433号民事判决书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民终472号民事判决书。这意味着我国有独三制度在真正实现“纠纷一次性解决”方面尚存在弱点。更佳的方式是,有独三对被告提出请求的同时,应对本诉原告也提出相应诉讼请求,在此基础上可将有独三与本诉任一方当事人实施的后诉视为重复起诉。
复杂诉讼形态中的当事人理论十分复杂,至今存在诸多争议,其判决的既判力也具有特殊性,对理解既判力扩张理论与重复起诉主观要件提出了独特的挑战。在共同诉讼中,应当结合诉讼法上的共同诉讼类型与实体法上前后诉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之间的关联性,对前后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加以判断;在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有独三与被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三受到判决既判力所及,无独三则应另行享有独立的程序保障机会。
四、既判力扩张理论与案外人特殊救济制度
我国司法实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是倾向于否定既判力相对性的,不仅妨碍了既判力扩张理论的接受,也损害了不少案外人的程序和实体利益。一半是应对此种现实状况,一半是为了更好地为权益受损的人提供程序救济,民事诉讼法中设置了多样化的案外人事后救济机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了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及案外人再审,2012年修改立法时还在第五十六条增设第三人撤销之诉允许本可参加诉讼者在符合条件时撤销他人之间的生效法律文书。一般认为,执行异议主要针对执行程序或执行方法的违法,②(42)② 在我国也可能针对与原裁判有关的实体争议,参见张卫平、任重:《案外第三人权益程序保障体系研究》,《法律科学》2014年第6期。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虽有特殊性,但在程序保障方面与另行起诉没太大差异。案外人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更为特殊,因二者在起诉条件与程序保障上与一般诉讼并不相同,这二项制度的广泛适用(特别是在主体范围上)被认为与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存在矛盾。因为原则上,对既判力扩张所及者才应给予特殊救济,对非既判力扩张所及者给予一般救济(即另行起诉)即可,但《民事诉讼法》对范围较广的案外人适用特殊救济程序,与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有限性存在较大的龃龉。①(43)① 参见张卫平:《第三人撤销判决制度的分析与评估》,《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5期;张卫平:《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与适用》,《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吴泽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适格》,《法学研究》2014年3期。为了在我国语境下澄清既判力主观扩张的范围,有必要考察案外人特殊救济机制与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的关系,主要是回答“可获特殊救济的案外人是否应被禁止另诉”这一问题。
(一)我国案外人特殊救济制度适用的主体范围
与重复起诉相关的特殊案外人事后救济,主要有案外人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相关规范,二者的主体范围需综合考虑再审事由或撤销之诉的要件方可确定。
(1)案外人再审
案外人再审包括执行中与执行程序外两种情形。《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是执行中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案外人认为原裁判错误而进行的再审,此种案外人再审主体为对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且认为原裁判错误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监解释》)第五条规定,案外人对原裁判、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在裁判、调解书生效后2年内,或自知道或应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3个月内申请再审。因此,未在执行中提出异议的再审案外人,为对标的物主张权利、主张利益被损害但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者。
执行中与执行程序外的案外人在申请再审的条件表述上存在差异,虽然都需对执行标的物或裁判调解书标的物主张权利,“认为原裁判错误”与“主张自己利益受损”或许也存在重合或交叉,但执行外的案外人仅能在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时才可申请再审。当然,从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原理出发,不应因为案外人处于执行程序内外而区别对待,采用类推方法,应当认为不论执行程序内外,仅受既判力扩张所及的案外人才能申请再审,从而将案外人再审制度与禁止重复起诉制度协调起来。
但在实践中,不论执行程序内外,法院理解的可以申请再审的案外人范围都远远超出受既判力扩张所及的案外人范围,其对“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理解似乎并不能与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相协调。例如,在一房二卖的情形中,法院在其中一个买受人与出卖人的诉讼中作出调解书,另一个买受人主张权利的,法院认为应对调解书申请再审;①(44)①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终17826号民事裁定书及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内01民终4003号民事裁定书。案外人在另案对调解书中标的物申请财产保全并首先查封,以调解书中确认的抵押债权过高为由申请再审;②(45)②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民申55号民事裁定书,法院最终驳回再审申请,但并非由于因为案外人无权申请,而是因为调解书确定的抵押债权金额合理。甚至,妻子为了避免承担夫妻共同债务,主张丈夫与债权人之间生效调解书中确认的债务不存在,法院认为应对调解书申请再审。③(46)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1年第3辑(总第47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由此可知,法院对案外人再审范围的理解更多地受到实体法律关系关系统一性判断的潜在影响。
(2)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本可作为有独三或无独三的主体,因不能归责于自身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有证据证明生效裁判、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6个月内向作出生效裁判、调解书的法院提起撤销之诉。
第三人撤销之诉起源于法国,被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相继引入。法国第三人撤销之诉源于14世纪教会法,当时民事诉讼中的上诉、异议与再审程序均开始向第三人敞开。由于承认既判力具有相对性,法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既判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其传统理论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理解为专门应对“诉讼欺诈”的权宜之计,仅受诉讼欺诈的案外人可以提起撤销之诉;现代法国为保障公民“接受独立公正审判”的基本人权,扩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范围,凡利益受生效裁判影响的第三人都可提起撤销之诉。④(47)④ 参见巢志雄:《法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研究——兼与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比较》,《现代法学》2013年第2期。在借鉴了法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原告适格问题存在较大争议,有的主张仅受判决效力所及且未被赋予程序参与机会之人可提起撤销之诉,有的则认为不受判决效力所及者并非绝对不能成为适格原告。⑤(48)⑤ 参见刘君博:《台湾地区第三人撤销之诉评述》,《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4期。
我国大陆地区引入第三人撤销之诉后,也成为理论争议最大的问题领域之一,尤其是原告适格问题。①(49)① 参见刘君博:《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问题研究:现行规范真的无法适用吗?》,《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吴泽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适格》,《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王亚新:《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的再考察》,《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张兴美:《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问题研究》,《法学杂志》2016年第6期;刘东:《回归法律文本: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再解释》,《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等。原告适格问题与第三人撤销之诉能否得到切实运用并实现立法机关期望的“遏制虚假诉讼”目标紧密相关。有的学者主张,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存在冲突,在既判力制度下第三人撤销之诉将会受到极大限制甚至成为多余。②(50)② 参见张卫平:《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与适用》,《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有的学者则认为在我国,由于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未完全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可为遭受不利的案外人提供程序保障,还可救济承受判决其他效力(如预决效力)的案外人。③(51)③ 参见廖浩:《第三人撤销诉讼实益研究——以判决效力主观范围为视角》,《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部分学者进而采纳法解释论或体系论思路,或从立法机关遏制虚假诉讼的目的出发,提出原告适格的类型化解释方案。④(52)④ 参见刘君博:《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问题研究:现行规范真的无法适用吗?》,《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吴泽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适格》,《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王亚新:《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的再考察》,《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任重:《回归法的立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体系思考》,《中外法学》2016年第1期。
在我国实践中,与法国相似,一切可能受生效裁判影响(哪怕是《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在另诉中可举证推翻的预决效力)的案外人,都有可能提起撤销之诉并胜诉,最主要的类型为案外人对他人之间生效法律文书中的标的物主张相冲突的权利(包括物权及以获得物权为目的的权利)。⑤(53)⑤ 如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6民终12811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民终569号民事判决书。一般债权人提起的撤销之诉虽可能因其本来无法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不被允许,但偶尔会因涉及虚假诉讼或转移财产而得到法院的许可与支持。⑥(54)⑥ 如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9民终884号民事判决书。因此,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范围远远超过既判力扩张的范围。
(二)可获两种特殊救济的案外人应否被禁止另诉
案外人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二者均为案外人推翻他人之间生效裁判的程序,适格的案外人或第三人均不限于受既判力扩张所及者。因此,二者与禁止重复起诉制度能否协调取决于同一个问题:符合案外人再审或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条件但不受既判力扩张所及的主体若选择另行起诉,法院应否准许?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要考虑案外人独立程序保障权、一般诉讼程序相比再审及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优点,还应注意案外人主张的实体内容是否在他人间生效裁判或调解书中处理过、通过特殊救济机制是否更方便当事人等因素。
我国司法实践对此存在不同的回答,上文提及的案例中就有法院禁止案外人另行起诉而要求其申请再审,但也不乏法院要求或允许案外人另诉的例子。
案例7:A依据《审监解释》第5条向法院申请再审,主张:A、B均为C的子女,某房屋虽登记在B名下但实际上为C所有。B的继承人D、E通过调解书的方式确认二者继承该房屋的份额,A认为该调解书部分内容错误损害其对该房屋的继承权。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登记在B名下,为其合法遗产,D、E的调解书不违反自愿、合法原则。A非本案当事人,如对房屋权属存在争议可另行解决。①(55)①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津01民申153号民事裁定。类似案件有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白中民一终字第181号民事裁定。
案例8:法院对A、B之间借款合同纠纷判决A向B偿还借款并赔偿损失。A、B达成执行和解协议,A将某条生产线整体抵偿给B公司,法院作出执行裁定,A履行完毕。C以A、B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C向A供应机器,A未按约付款,却将包含这些机器的生产线抵偿给B,请求判令A与B返还设备或支付合同欠款及违约金。一、二审法院认为C应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或执行异议之诉,而非另行起诉,裁定驳回起诉。C申请再审,法院认为执行终结后C已无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法院的执行裁定亦非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执行和解协议不能对抗另案诉讼,应进行实体审理。②(56)②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233号民事裁定。
这两个案件不仅说明法院可能允许甚至要求案外人另行起诉,而且显示了案外人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等特殊救济程序的缺陷,二者可能无法充分保护案外人的利益。事实上,这两个案例中案外人主张的权利义务均非前诉裁判、调解书中已经处理的客体,案外人若提起后诉绝非对前诉的重复。何况另诉存在较多益处,一方面另诉对案外人的程序保障较为完备,案外人再审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门槛”均较高,且案外人非前诉当事人,未曾经历过前诉的庭审、庭前准备等重要流程,经常无法主张或证明可能存在的撤销事由,若由于案外人可申请特殊救济就禁止另诉,反而会剥夺案外人的司法救济权;另一方面案外人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往往并不能彻底实现对案外人的救济,原法律文书被撤销后相关主体仍有必要另诉。《审监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案外人非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再审法院仅审理其对原判决提出异议部分的合法性,撤销原判决相关判项的,应告知案外人与原审当事人可以提起新的诉讼解决相关争议。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践中,许多第三人在请求撤销裁判或调解书的同时还提出确权或给付请求,法院却大多只对判决内容进行撤销或变更,极少对其他诉讼请求作出判决,①(57)① 如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06民终1657号民事判决,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提出三项诉讼请求,第一项是撤销他人之间判决若干项,第二项确认原告与被告之一之间的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第三项是确认被告彼此之间的合同无效,法院判决撤销系争判决的判项,但认为第二、三想诉讼请求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解决的事项,因而不属于受案范围,判决驳回。而是要求第三人另诉。学者也认为,考虑到管辖制度与法院负担,此种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②(58)② 参见王亚新:《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的再考察》,《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因此,唯有另诉才能既充分保障案外人权益又有利于最终安排权利义务关系。
案外人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两种特殊救济,虽可向范围较宽的主体开放,但实际上并不能也不应排除其中大部分案外人选择实施的另诉,毕竟案外人的另诉大多不能构成重复起诉。一些案外人或法院倾向于特殊救济机制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方便性,先撤销与案外人的主张或法院后来观点不一致的前诉生效法律文书可直接排除“隐患”。但在根本上真正能够更好保护案外人程序权益、防止程序赘余的做法仍然是另诉。此外,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般仅主人能打扫屋子,案外人不能要求打扫当事人的“屋子”,法院也不应(不考虑当事人意愿)将生效裁判视为其完全负责、完全具有支配力的对象。基于当事人自己事务不受他人随意干涉的原则,当事人(及承受既判力扩张的人)以外的主体本无权推翻他人之间的裁判、调解书,特殊救济机制却赋予其此种权利,因此在具体适用中,必须注意当事人权益与案外人权益之间的平衡。
五、结语
在探讨重复起诉的主观范围及为解决该问题而提出的既判力扩张理论时,不能仅停留在诉讼法的视角上。《民法典》时代的诉讼法研究必须更加关注实体与程序的互动,有了更具体系性的《民法典》以后,诉讼法的研究才能在内容上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与更大的复杂性及深度。具体到既判力的范围上,正是由于实体法上法律关系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存在关联,才有了既判力相对性原则与既判力扩张例外的对立统一。结合《民法典》及其他实体法规范,可知我国重复起诉的当事人相同主观要件应当作如下理解:首先,与当事人存在继受关系或担当等代表关系的案外人也应视为与当事人具有同一性;其次,在复杂诉讼形态中,鉴于当事人之间实体关联的紧密程度、前后诉对抗态势的不同,并不能一概认为前后诉具备当事人相同的条件;最后,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及扩张范围不因特殊的案外人救济机制而轻易动摇,禁止重复起诉制度与案外人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可以在不同的侧面发挥各自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