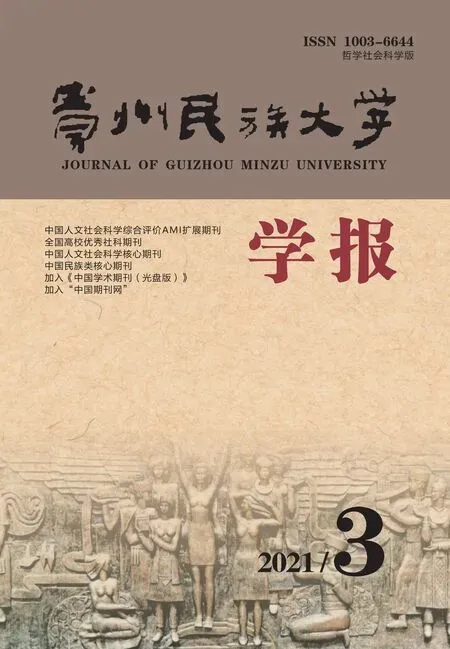明代贵州科举宾兴研究
王 力
“宾兴”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大司徒之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郑玄解释为:“兴,犹举也。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既则献其书于王矣。”①(1)①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4页。说明这是周朝自下而上的举荐人才之法。后世“宾兴”一词的含义慢慢演化,既可直接指代科举制度,有时又是“乡试”的代名词,明清以来则多指地方捐资助考的公益基金。本文的论述也将从公益助考的角度展开。目前国内关于宾兴的研究也多从公益基金角度展开,主要研究者有毛晓阳、杨品优等,既有以全国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也有地域性的个案考察,涉及地域主要有江南、广西、江西、台湾,时间上则以清代为主,少见明代相关研究。而明代贵州科举宾兴至今尚无人关注,本文拟从方志文献入手,探析这一问题。
从毛晓阳的研究来看,明代全国范围内的宾兴资料多见于各种方志之中,留存量亦不算大。①(2)① 毛晓阳:《明代科举宾兴考述》,《井冈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而贵州明代的宾兴资料尤少,可能由几个原因造成:一是在明代十三个省级政区中,贵州建省最晚,纳入科举版图的时间晚,与科举相关的社会活动发展相对缓慢。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才成为省级行政区,而关于其科举的最早信息则出现于明仁宗洪熙元年②(3)② 《宣宗宣德实录》(明仁宗洪熙元年九月)记:“行在礼部奏定科举取士之额。先是,仁宗皇帝以为近年科举太滥,命礼部翰林院定议额数。至是,议奏凡乡试取士,南京国子监及南直隶共八十人……云南交址各十人,贵州所属有愿试者于湖广就试。”,两年后又改试云南③(4)③ 《宣宗宣德实录》卷28:“贵州布政司言:‘普安州儒学生员皆是罗罗、僰人,莫知向学,今选俊秀军士王玺等入学读书以备贡举。’又言:‘前奉礼部文书,本司所辖州郡生徒堪应举者,许于湖广布政司就试,缘去湖广路远,于云南为近,宜就近为便。’上命就试云南”。,直到嘉靖十六年才独立开科乡试,其科举活动的开展可能滞后于其他省份。二是贵州人口偏少,经济开发较晚,或许影响公益事业的发展;三是明代贵州史料存世量不多,现存的明代方志仅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黔记》、嘉靖《普安州志》、嘉靖《思南府志》、万历《铜仁府志》几种,涉及宾兴者仅有嘉靖志、万历志、《黔记》《普安州志》,其中万历志、《黔记》中有些内容与嘉靖志相同或基本相同,应是编修时参考了后者史料,嘉靖《普安州志》中的宾兴资料则是对嘉靖《贵州通志》中“普安州”相关内容的丰富。另有部分清代民国方志回溯地方宾兴历史时的只言片语,如嘉庆《黄平州志》卷五“书院”、《镇宁县志·经制志》之“学制”部分,虽为二手史料,尚可酌情参用。
一、明代贵州宾兴的设立
宾兴的设立在各地均较普遍,代表的是各地官民对文教的重视与支持,是一种主动作为,但明代科举应试者总体经济状况不佳也是一种客观现实。就生员而言,贫困者各地均有,而在晚明更为明显。陈宝良的研究认为晚明生员趋于贫困原因有三:一是廪生数量远少于增广生和附学生;二是徭役过重;三是教官盘剥严重④,(5)④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29页。从侧面印证当时生员贫困的普遍性。
贵州士子的情况相比他省又更显严重。首先是因为贵州地方经济开发较晚。相关记述在明代国史、方志中比比皆是。舒应龙《大木疏》云:“贵州于寰宇最称囗囗荒遐之乡,本省官军俸粮什七仰之邻省,什三取之囗民。”万士和《义仓记》云:“削竹为著,屑木为香,绩丝为网,与夫负米裹盐,搬柴运水,其为利微,为事劳也。贵州以生儒业之,则其地瘠民贫可知已。尽贵之地,山陵材麓居十之七,而军居其三。军户自屯田,官赋外所余无几。”①(6)① 王来贤、许一德纂修:(万历)《贵州通志》卷二十一“艺文志一”,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贵州人口较少,又多卫所,社会经济不发达,常需湖广、四川诸省赈助,贵州不足之钱粮,由湖广之长、衡、郴三府州,四川之重庆、叙州、泸州三府州及乌撒、乌蒙、东川、镇雄等地协济,而各省赈助又常有拖欠,有时拖欠数额颇大。江东之曾查万历十四至二十四年间的拖欠额为“湖广拖欠银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两四钱七分七厘零;四川播州银二万一千二百二十七两九钱;乌撒府拖欠粮六万七千二百七十九石六斗,银三百七十六两七钱;乌蒙府拖欠银一万五千五十四两四钱;东川府拖欠银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两;镇雄府拖欠粮三万六千一十七石。以上两省共拖欠粮一十万三千二百九十六石六斗,银一十二万三千四百四十六两四钱七分七厘”,而其时“查得贵州通省府、卫、县、司、所、站、堡、营、哨文武官、把军兵每年供亿,该粮二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八石零,银八万八千四十两零,此分毫不可缺少者也”②。(7)②江东之:《责成川湖协济疏》,见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九,《经略志一》。江东之征战造成军饷告急,而各省之援助迟迟不到,其乞朝廷责成几省协济的奏疏中语气已颇为峻切,“照得贵州囗囗囗囗,不得不镇以兵威之重;田少山多,不得不望于邻省之济。先因二省解运不前,为之挪借,以待其追补。今则追补不足,年复一年,积虚已极,其在布政司库者,除采木银两之外,仅有五千余两,各有支使项款,十三省之司帑未有如贵州之囗者。贵州素称备薄之省,未有若此时之甚者:计算军饷,将缺一年之额;搜括库藏,再无挪借之金。不但变生肘腋,不能驱饿夫以临戎,即使军狃承平,亦难枵腹以度岁”③(8)③江东之:《责成川湖协济疏》,见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九,《经略志一》。。贵州的经济情况与其土地的缺乏有关,李中清认为“明朝主要依靠土地政策来增加税收”④(9)④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41页。,其据伍丹戈《明代的官田与民田》一文所作的统计表明,在1500年(即弘治十三年)前后贵州的田地数量居全国后列⑤(10)⑤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41页。,税收因此也处于较低水平。地方经济的不足自然影响到广大生员,经济条件不好渐成普遍状态,朝廷曾经多次赈济贫生寒衣。黔士的拮据不仅表现于应考这种花费较多的行为,求学期间的生活也不易应付。万士和任内就深为黔士之贫而震动,据其前引其“削竹为著”等语,可知当时生员常常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谋生计。郭子章任巡抚时贵州贫生众多,其所著《黔草》记各地贫生数就有:贵阳军民府54、宣慰司63、威清卫42、平坝卫33、普定卫50、安庄卫28、安南卫50、普安州13、毕节卫15、乌撒卫30、赤水卫20、龙里卫9、新添卫23、平越卫35、清平卫35、兴隆卫30、都匀府30、镇远府50、石阡府50、思南府50、铜仁府50、思州府50①(11)① 郭子章:《湖广解到饷银赈饥牌》,见《黔草》卷之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5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24页。,总数达820人,而万历四年时贵州乡试的考生数量才仅九百左右②(12)② 《万历四年贵州乡试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10年。,其比例已令人惊异。
其次是赴试距离的遥远。科举考试的地点正常情况下均设于各级行政中心所在地,童试在各府州县治所,乡试在省城,会试在京师。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有不少考生距离考点很远,甚至在乡试时就需远行千里。而对于边远省份的考生而言,会试赴试更是长途漫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福建、广东、贵州、云南几省省城距京师的距离分别为六千一百三十三里③(13)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六、卷一百一、卷一百二十一、卷一百十四。、七千八百三十五里④(14)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六、卷一百一、卷一百二十一、卷一百十四。、七千六百七十里⑤(15)⑤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六、卷一百一、卷一百二十一、卷一百十四。、一万六百四十五里⑥(16)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六、卷一百一、卷一百二十一、卷一百十四。。而在一些文学化的描述中,贵阳与京师的距离则动辄以万里称,贵州举人赴京须经过贵州、湖广、河南、直隶诸省,行旅艰辛,清康熙三十年会试试官之一的顺天府丞兼提督学政王承祐上疏,指出远省士子赴试“驰骋驿路,跋涉间关,经历三月,辛苦备尝,此道路之难也”。除了“每遇公车之年,贫穷居多,艰于资斧,区画借贷,不遗余力”的“在家起行之难”,还有“及其抵京,只身孤影,仆从无人,一切薪水,俱行自给”的“旅寓之难”。他们“拮据奔赴,喘息靡宁,席不暇暖,而场期已及,尚焉能温习揣摩如各近省士子优游暇逸,止专一意读书哉”⑦。(17)⑦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8页。即便是距离相对较近的乡试,对于贵州考生亦有不小的压力。嘉靖十六年前贵州附试云南,士子要长途跋涉,“且以贵州至云南相距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宁等府卫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侵滛,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①(18)① 田秋:《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第308页。贵州山峰林立,道路崎岖,即便在独立开闱后,不少地方的考生乡试亦非易事,明代各府距贵阳最近的有150里,最远的则有770里,西南方向的考生应试要乘船渡盘江,既险且远,自镇远入省城尚属中等距离,但“由镇远至省,跬步皆山,终日行程不过数十里,而舆夫担夫皆劳顿不可支,无平原旷野得以稍舒筯力也”②。(19)② 刘书年:《黔行日记》,出《黔南丛书》别集之《刘贵阳遗稿》,贵阳文通书局。同时,科举又是一种社会化、仪式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行为,对于有相当概率进入官场的考生而言,考试前后还有许多应酬活动需要参加,也要消费一笔钱财。诚如道光《仁怀直隶厅志》所言“且舆夫有费,日食有费,进场笔墨一切又有费”③,(20)③ 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卷五“学校志”之“宾兴田”,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支付能力差的贫寒考生可能因此背负债务,或是难以成行。由于科举中式人数被视为彰显地方文教实力的重要指数,因此地方社会有捐资助考的天然动力。之所以资助者是全体考生而非仅贫士,是因为而若仅仅捐助贫生,则不只有甄别操作的难度,更有悖于地方社会右文兴教的初衷,所以宾兴银两的资助对象必然是全体考生。
二、明代贵州宾兴经费的来源和使用
宾兴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土地和其他各类生产资料产生的租金;二是宾兴银两所产生的利息。前者包括宾兴田外租产生的地租、一些“不系在官屯科数目”的余田地租、牛骡等生产工具的租金等,有些地方会明确划分出宾兴田,也有很多地方由“学田”同时承担助学和助考的任务,宣慰司便有专门的宾兴田,都匀府、黎平府则以“学田”承担此任。后者则直接靠借贷生息。贵州宣慰司的宾兴银来源正是二者兼有,其宾兴田“坐落圣泉水右,大小六十五坵。每年纳米花三十秤,除随田粮米二斗五升,佃户自纳”。而且还有“白银一百两,先巡按御史徐文华给发贵前二卫借与殷实人户,每月每两征息三分,岁该息银三十六两,遇闰多三两,连田租俱给该学岁贡生员,资助赴京路费”①。(21)① 谢东山修,张道等纂:(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志》“附录”, 明嘉靖三十二年刻本。
宾兴田与学田可由官府划拨,也可拨款或集资后进行购买。万历三十一年时,时任贵州巡抚郭子章就曾发银五十两,檄黎平府置学田,其实置这块田地主要目的就是提供宾兴银,因为郭明确提到置田就是“收租备给三年大比应试生员盘缠之费。一分在都莫寨,计二十一丘。除粮差外,年收米花七十七秤零。一分在黄柏坡,计一十七丘。除粮差外,年收米花三十二秤半。”②(22)② 郭子章:《黔记》卷十八《学校志下·黎平府学田》,明万历刻本。都匀府的学田“每年上租谷七十石二斗,内除二十三石三斗完纳本田秋粮差银”,而所剩的四十六石九斗则“给递年贡生盘缠之用”③(23)③ 万历《贵州通志》卷十四《合属志十二》之“学校”,《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明万历刻本第17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00页。,说明其学田也为宾兴而设。
普安州的情况则是“宾兴白银共一百四十两,先该副使毛科、佥事吴倬各发茴银一百两于卫,借与殷实人户,每两每月征息二分,给岁考生员居一等七名以上,并教官每员各月银八钱,为灯油之助。应试生儒各给一两,新科举人各给一十五两,旧举人三两,岁贡生员给二十五两,旧监生给三两,俱于息银内支用。嘉靖间,佥事万敏续发白银二十两,并前生息助用。”④(24)④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志》“附录”。清平卫为“宾兴银六十一两,每岁照例征息,遇有科贡,生员每名给十两,应试生儒每名给一两。今止存本银一十八两收息,岁贡生给五两,应试生各给四钱矣。”普安州除此以外还有“余租银两”,“系先年丈量出余田,不系在官,屯科数目,给与附近军余耕种,总计每年征收白银二十一两,三年共该六十三两,每科举生员一名给银二两,余租不够支销,于牛租银内补数。”⑤(25)⑤嘉靖《普安州志》卷二“食货志”之“惠政”。而在弘治十四年,普安州爆发了米鲁之事,耕牛俱于乱中被抢,为保证农耕的顺利进行,贵州布政司拨银八百两买牛发放给普安各屯,租户多是些未取得正式军籍的“军余”,他们不用将耕牛归还,只需交纳一定的租金,而这些租金最终都归入宾兴经费。“每只每年只收租牛银二钱八分,给与儒学科贡赴京,坐监复班科举盘缠,亦不许别项支销。”⑥(26)⑥嘉靖《普安州志》卷二“食货志”之“惠政”。为便于计算和分发,实物地租最终也要转换成现金,粮米折算成银两。明政府也多次发行钞币,但据谭文熙的研究,明代的钞币始终信用不高,“人民最信得过的还是金银、布帛、粟米”①(27)① 谭文熙:《中国物价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4页。,显然布帛、粟米不利于携带,所以金银才是社会最重要的交换媒介物,宾兴资助多以银两形式出现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宾兴银两有的来自政府划拨,也有的来自民间集资或捐赠,由于资料的缺乏,后者在明代贵州各地的情况难以确知,在现存贵州明代宾兴资料中,除清平卫未加说明,其他宾兴银两均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划拨。政府通过借贷生息以达到增值目的,其银两借与殷实人户,为其提供商贾资金,使其能扩大经营而牟利,最终再回馈于民,其实质类似于今天的贷款行为。强调借与“殷实人户”,正是因为殷实人家即便经营不善,也具备返本还息的经济能力。此类借贷的利率相当高,月息一般在2%-3%之间,因此产生的收益颇丰。以贵州宣慰司为例,其宾兴银本金数量为白银一百两,“每月每两征息三分”,即为月利率3%,每月产生3两银子的利息,则全年总量为普通年份36两,闰年39两。普安州由“副使毛科、佥事吴倬各发茴银一百两于卫”,总数为二百两,月利率2%,则每月产生4两利息,全年总量为普通年份48两,闰年52两。清平卫的本金为六十一两,其利率未予说明,以宣慰司和普安州的利率推算,若以二分算则月息1.22两,全年14.64两,闰年15.86两,以三分算则月息1.83两,全年21.96两,闰年23.79两。
刘秋根的研究表明,明代典当铺的利率低者仅一分或一分五厘,三四分已属重利②(28)② 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宾兴银产生如此高的利率,可能一是有行政权力的介入,二是因为其公益的性质,出于增大收益的考虑,官民双方因此达成共识。
清代宾兴资料中常见官员或士绅个人捐助者,但明代贵州个人捐资情况缺乏文献支撑,尚难确知。但我们可以通过官员置办右文田的行为略作推测。“右文”即崇尚文治,右文田则指资助地方办学的田地,由捐资人购买后赠予地方学校,学校则将所获租金用于办学。许多官员不忍黔士之贫,有能力者纷纷解囊,万士和、冯成能、江东之便是典型代表。万士和于嘉靖间设立义仓以赈助贫士,其《义仓记》自述的“数十石”在郭子章《黔记》中有明确记载“出爰金易粟八十石”,八十石即九千六百斤。此种行为能为当事人带来良好政声,因此会形成传递效应。冯成能于隆庆三年任贵州按察使,在任时深为万士和助学精神感召,拿出薪俸180缗购买两处水田共40亩,一缗是为一千文,180缗即18万文,“每秋成,积贮,视诸生贫乏有差而多寡其数,无改万公之旧,第务增拓之”①。(29)① 郭子章:《黔记》,卷三十九《宦贤列传六》。相比之下,江东之的助学行为涉及范围更广,江于万历二十四年任贵州巡抚,其时,万冯二人之事已广为传颂,江氏为之感佩的同时也对之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已有的七十六分田对于府州司三学贫生颇有助益,应予坚持租贮。但因为设于定番州的广储仓距离省城有四百里之遥,贫生领取救济的费用过高,另外未设义田的州郡生员也不能受益。江氏采取的对策之一是“令州官俟价以粜”②(30)② 郭子章:《黔记》卷十六《学校志上》。,将粮食折价“随价以解”,另一对策是开辟新的资助来源,“且图之会屯中,清出乌当把路之田若干亩,故征巴香备饷,而今无所用之,最号沃畴,岁收米二百石有奇。往输直十六,缗于藩司,而大半肥佃者,余以为屑越甚也。因念贵阳学宫,昔以讲武,今以修文。乌当之田,昔赡戎刚,不若赡文髦。从今卫輣不驰而瑶华耀爽,黔虽凡徼乎,亦知左武矣”。江与应朝卿二人以三百金购田,皆用于资助贫生,受惠者遍及全省。如都匀府右文田有一分七丘,每岁收租达四石二斗;思南府田一分,岁收仓斗谷三十石,用于资助贫生婚丧;石阡府右文田“二分六丘”,其中梭寨田“岁纳谷一十二石六斗五升”,对门河田“岁纳市斗谷八十一斗”③。(31)③ 郭子章:《黔记》卷十七《学校志下》。另一方式是令富户流通粮食,④(32)④ 参江东之《赈谷流通议》,出《瑞阳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89页。江东之身为巡抚,勤于公事,对黔地之苦与黔政之弊均有深刻认识。对于黔民之苦,他常怀悲悯,“余抚黔三月,有青衿子谒余,曰‘岁云晏矣,藿食者忧之。’余惟贫者士之常,而黔士之贫则抚者之辜也,乃出廪余分之,所及无几,且非可继也”⑤。(33)⑤ (明)江东之:《右文田记》,万历《贵州通志》卷二十一,《艺文志一》。黔地本有救荒之赈金,但因办理比较麻烦,很多人疲于应付,宁肯不办,造成有赈与无赈相同的局面。江东之遂与巡按应朝卿一起拿出个人积蓄,并再拨以部分公帑购买肥沃土地赠与饥荒百姓,令其大为感叹的是“诸父老诣庭鸣谢,不曰为黔兴利,而曰为黔除害”,由此深知民生之苦不仅源自物质匮乏,未理顺的官民关系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更老之言也,大都官忧民之饥,民恐官之扰,匪籴斯然,田亦如之。考之农政,耕耘不时必加罚,苗实踰等必加赏。农益田垦,则吏受赏;农损田荒,则吏受罚。寓儆官之法于劝农之中,两台秉持之,两司督校之,郡邑举行唯谨。”①(34)① (明)江东之:《备赈公田铭》,万历《贵州通志》卷二十三,《艺文志三》。非常体恤地提出解决之道。巡抚本就有繁忙的公务,所担职责颇重,“凡徭役、里甲、钱粮、驿传、仓禀、城池、堡隘、兵马军饷及审编大户粮长,民壮快手等项地方之事,俱听巡抚处置。”②(35)② (万历)《明会典》卷211,《都察院》。可为可不为之事江氏皆视为巡抚之责任,并躬行厉为,是传统道德中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品格体现。这些行为与宾兴助考一起,构成了传统社会里延续文教力量的公共行为。
由于贵州和周边诸省之政区犬牙交错,常有邻省附考之事,因此也产生了特殊的宾兴现象。其中湖广的偏桥、镇远、清浪、平溪、五开及四川的永宁宣抚司因离贵州较近,一度或寄学、或附岁科考于黔,嘉靖二十二年时“平溪等五卫军生暨宣抚司民生,称去各该省会险远,比例就近附试,该提学副使蒋信、谢东山先后议呈两院,题奉钦依勘合卫司生儒,俱起贵州应试”③(36)③ 万历《贵州通志》卷十八,《兼制志·学校》,《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明万历刻本第17册,第413页。,虽然考试附于贵州,但“其宾兴银两,仍应办于各该卫司”。这说明宾兴银两的提供其实是生员所在地的责任,而非由考试所属地区负责。
宾兴银两属于公益经费,其来源及支出情况都比较清楚,并非复杂的经济活动。但其运作往往能反映出一方官民对文教的重视程度,因此经费的管理一般都比较严格。严格管理的第一个要求是“专款专用”,这个要求是创办人、管理者及社会各界的共识,一般不准动用本金,款项从利息中支出,本金与利息皆不允许被挪作他用。其次,由于许多地方的宾兴助考与儒学助教的经费来源相同,就要明确规定出二者的使用范围,普安州在弘治、正德年间的款项就分为“激劝”与“宾兴”两种,前者为平时助学,后者为赴考资金,佥事吴倬将总款一百七十五两银子分为两份,激劝本钱为一百两,宾兴本银为七十五两。而在宾兴的七十五两中,又明确规定其中三十两取息给与举人,四十五两取息给与岁贡。二是发放务必及时。到了科考年份,管理者必须及时发放到考生手中,如普安州就明确要求“流水生放,不许停滞,亦不许别项支销,永为定规”。三是专人管理,管理务必公开。吴倬曾将宾兴的相关规定刻碑作记,要求管理者在办理宾兴银管理事务时,要共同出入,公开办理,不许个人私自收放银两,这样就形成了互相监督的管理方式。而对于违规操作产生的资金短缺,将由主管者自行补足。对于承载着地方右文精神的公益助学助考事业,多数地方官及主管者都以比较谨慎负责的态度来面对,如吴倬文所言“诚恐事久弊生,无由稽考,况良法美意,无从垂后,谨勒于石以昭不朽”①。(37)① 嘉靖《普安州志》卷二,《食货志·惠政》,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04册,2014年。严格的管理保证了宾兴经费的良好运转,也使得民间有持续参与的热情。
三、资助对象与额度
宾兴的资助对象主要是参加各级考试的考生,资助金将被用作赴考盘费。上述材料中,受助者有参加会试的新老举人、参加乡试的生儒及即将入国子监读书的岁贡生。
普安州资助对象还包括“凡生员蒙提学道考居七名以前及教官一名”,明代提学道每年都要对所属府州县生员、廪生进行考试以辨优劣,也就是所谓“岁考”,这里所指就是每年的岁考前七名和儒学的教官。由于仅有普安一处有此类记载,而普安州又有特殊背景,“切照贵州一省,极在边荒,苗囗杂处,民不知学。是以各学生徒悉于军士中选补。军士疲惫,为父兄者,多不能自淑子弟,日求衣食,尚有不给,欲其专事文墨,难矣。”②(38)② 嘉靖《普安州志》卷二,《食货志·惠政》。其他州县的情况各一,所以此类人员的受助未必是普遍现象。
人均受助数量上,以岁贡生最多,普安州明确规定为二十五两,几乎是举人赴会试所获的二倍,清平卫岁贡生所获则十倍于应乡试的生员,宣慰司的宾兴银两则全部用于资助岁贡生。比较特殊的是都匀府,在陈尚象《府学学田记略》中提到“以定经费,则举人盘缠二十石,贡生一十五石,而科举者于此酌助焉,贫寒者于此赈恤焉”③。(39)③ 郭子章:《黔记》卷十七《学校志上·都匀府右文田》,明万历刻本。这是明代贵州方志中唯一一则贡生受助额低于举人的记载,总体而言,明代贵州宾兴的最大受益者还是岁贡生。何以宾兴独重岁贡生?这可能与其支出有关。举人入京会试,主要花费除了交通费用,就是考试期间的生活消费,发榜后,中式者很快就有俸禄可以支用,各种社会或个人资助也会纷至沓来,落第者不久也要返乡,总体时间多不超过一年。而岁贡生的花费不仅有赴京旅赀,还有入监读书期间的花费,经费需要可能更高。再者,生员出贡以后往往要发一笔“旗匾银”,上引资料中皆未明言,但若资助经费中已包含此类款项,那么岁贡生所得多于举人就是很有可能的了。
《明会典》卷七十七“贡举”记载弘治十三年时奏准“自十四年为始,各处州学俱四年三贡。其云南四川贵州等处,除军民指挥使司儒学,军民相间,一年一贡。其余土官及都司学,各照先年奏准事例,三年二贡”,而嘉靖二年时又奏准“贵州宣抚司儒学生员一年一贡”。从上列宣慰司的史料看,宾兴捐助由徐文华任巡按御史时始行,徐于正德五年始巡按贵州,《嘉靖通志》则于嘉靖三十二年议修,三十四年修成,这一时间正处于弘治与嘉靖之间,其岁贡生的选拔应是嘉靖二年前三年二贡,之后则一年一贡。从《明会典》的记载看,全国范围内岁贡的人数有每年一人、二年三人、一年二人、三年二人不等,最多者仅一年二人。若以一年二人算,宣慰司岁贡生可平分全部宾兴经费。其宾兴田收入为每年米花三十秤,每秤十五斤,计四百五十斤,粮米二斗五升即二十五升米,明代贵州宣慰司的粮价已难确知,但从田租数量看,折算银两应该不会太多。单就银两算,每名岁贡生也可得到18两银子,闰年则可得到19.5两。嘉靖二年前三年二贡,每三年四名岁贡生可分108或111两银子,平均数已达27两。
岁贡生所获宾兴资助既有地区差异,也有年份差异。宣慰司岁贡生所得为18-27两、普安州为25两,清平卫只有5-10两。清平卫的例子则表明岁贡生所得与宾兴本金的增减紧密相关,其公益金的本金为六十一两,年息为21.96或23.79两,仅够资助两名岁贡生,因为还要支付给应试生儒每名一两,在应试者数量较多的年份,就会出现息金不足的情况,因此就要被迫动用本金,因为没有后续资金的补充,在修志书时本金仅剩十八两,年息仅四两有余,对考生的资助额度也就因此减少了一半。
考生所获资助的购买力如何是另一个需要考查的问题。沈榜曾于万历十八年出任京郊宛平县知县,其所著《宛署杂记》一书记载了许多县署的购买活动,价格记录尤为详细,此书于万历二十一年刻印,与上引贵州宾兴史料产生的年代接近,可为参考。据书中记载,当时大米一斤值钱二厘八毫,猪肉一斤二十厘,棉花一斤六十厘,轿夫一天的工钱六十厘,由一两等于一千厘的标准推算,一两银子可购买大米357斤或猪肉50斤、棉花16.6斤,或可支轿夫16天工钱。以普安州为例,新科举人所获宾兴资助可以购买大米5355斤或猪肉750斤、棉花249斤,可支轿夫240天的工钱,足以解决基本的生活消费。
四、结论
社会对于科举宾兴公益事业多持褒扬态度,嘉靖《普安州志》就将宾兴内容放入“惠政”一节,而此节中除“养济院 在卫城南门内”一句外,全部是宾兴相关内容。并在开篇宣扬“先王之政,莫先于惠,而煦煦之惠,非备政也。是故,惠学校励人才也,惠孤老恤无告也。我国家及诸当道之惠亦周矣。承流宣化,可不加之意乎?”①(40)① 嘉靖《普安州志》卷二“食货志”之“惠政”。
清代史料也可佐证这一认识,以道光《仁怀直隶厅志》为例,仁怀明代隶属四川,清代方归贵州,其“学校志·宾兴田”一节就不无自豪地说“乡试之士,咸取给于,菁莪育材之意,不无小补云”。仁怀离省城较远,科举之年常有考生畏惧路远费钱而辍考,自设立宾兴基金后,“乡试之年,于此取给,会试亦如之。从此多士志切观光,争先恐后,自不难于经费,自不怠于从事。而宪台作育人才之至意,庶可仰副于万一。”②(41)② 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卷五“学校志”之“宾兴田”,道光二十一年刻本。另外,明代贵州诸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中凡有功于宾兴事业者基本都会录之在案,可以看出社会对倡导宾兴之人的敬意。一个较好的例子是上文所提及的吴倬,他于成化十九年任贵州佥事,从嘉靖《贵州通志》的记述来看,其应该是普安州宾兴的首创者。嘉靖《普安州志·宦迹》评其“多方区划,任意儒林,置宾兴而士怀其德”,语气中充满感佩之情,万历《贵州通志》及郭子章《黔记》皆视其“按部见各学廪饩不继,与宾兴士贫不能行者,多方区画,积泉布以置学田”之事为义举,就连其家乡淳安所修光绪《淳安县志》“吴倬传”也将此作为其重要宦迹而旌扬,“贵多军卫,生徒无廪饩,亦无站军额粮。公始为经画,设学田赡师生,及廷对道里费”①(42)① 方象瑛:《廉宪吴倬传》,光绪《淳安县志》卷十四。,可知对此类人物的尊敬乃社会普遍现象。
总体而言,宾兴银两所提供的资助具备社会公益事业的特征,对士子的经济支持也是具体可见的,社会各界的积极评价也为地方文教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资助活动也推动了贵州各民族人才的培养,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