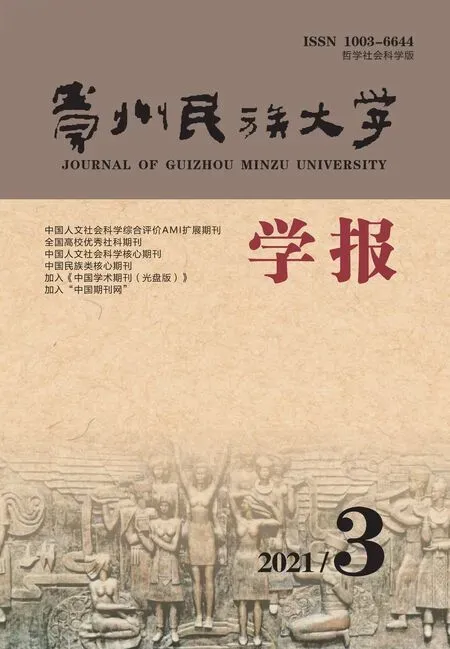“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程序问题
韩 旭
一、引言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结束,取得了预期效果,现已进入常规化阶段。黑恶势力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危害一方,已成为社会的“毒瘤”,确有打击的必要。然而,既往的教训表明:“专项斗争”作为一种专项执法,尤其在“扩大战果”“数字政绩”的影响下,很容易偏离法治的轨道,甚至出现不严格按照正当程序办案的情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实是对黑恶势力的一场“严打”,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才能使“严打”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群众才会真正拥护和支持,受治者也才会心服口服。①(1)①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0,45页。重庆市当年的“扫黑除恶”运动就值得总结。“打黑”行动曾被高度动员,甚至被上升为一种常态的社会治理方式时,原本单纯的执法司法活动日渐趋近于包含非司法活动的内容。单纯的执法司法活动所根据的法律规定和正当程序,在专项斗争中的规范性和引导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此情形下,“打黑”在某些方面突破法律的边界,就成为期望用结果的正当性论证过程合法性的司法模式。这种专项执法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法治权威树立的积极效应,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有可能导致社会治理模式的不稳定。②(2)② 参见邓学平:《警惕运动式执法偏离法治轨道》,《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5月1日第002版。“政策治国是我党治国的重要历史经验,过于强调依照政策办事,就难免导致法律虚无主义。”③(3)③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0,45页。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涉黑涉恶案件陆续进入审查起诉、审判环节时,这一问题更应引起重视。
其实,对这一问题最高司法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伊始即引起重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即要求:“坚持依法办案,坚持法定标准、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加强法律监督,强化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特别强调要“强化程序意识”。虽然“指导意见”未言明程序的内容,但依笔者之见,程序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律师辩护权的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公检法三机关办案模式的适应并真正保障三机关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禁止重复追诉与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和运行问题。上述这些程序问题是防范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制度装置,也是防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偏离法治轨道的重要保障。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于2019年7月20日在成都举行的大检察官研讨班上强调,“在全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决不能前面扫黑除恶,后面再纠偏、再解决申诉问题”。④(4)④ 蒋安杰:《张军亮剑:决不能前面扫黑除恶,后面再纠错、申诉》,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44159032022441583&wfr=spider&for=pc。作为司法机关需要谨防的是:现在轰轰烈烈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年以后我们再去面对信访和申诉的“大潮”,将有限的精力和司法资源配置放在对案件的审查和纠错上。这种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要做到未雨绸缪,防止“扫黑除恶后遗症”的出现。阶段性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虽已结束,但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防止在常态化治理阶段出现越出法治边界的现象,显得很有必要。基于笔者的专业知识,在本文中笔者只打算结合程序法治问题谈谈“扫黑除恶”如何在法治轨道进行。虽然,实体问题对厘清罪与非罪、准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但程序问题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正义”,更容易为社会所感知,也更容易为司法办案人员所忽视,出现“为达目的而不斟酌手段”的情形,因此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拟以律师辩护权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公检法三机关办案模式、禁止重复追诉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构建和运行问题为研究对象,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容易出现的不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意见,从而有利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
二、律师辩护问题
被追诉人有权获得辩护,是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这项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贯彻落实情况稍显不足,主要体现在涉黑涉恶案件办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律师参与度不高、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不足、辩护意见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够等问题,导致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作用难以发挥,辩护制度的作用没有充分彰显,“兼听则明”的制度运转不理想。为此,“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办案机关应当依法保障律师各项诉讼权利,为律师履行辩护代理职责提供便利,防止因妨碍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对案件办理带来影响。”《关于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也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律师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中的执业权利,保证律师依法履行职责。”
根据以往律师办理涉黑涉恶案件的情况可知,专项将开展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地方以“服务中心”“服务大局”为由,要求本地律师承担“协助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义务。否则,律师就会被指责为“不顾大局”。然而,让律师“协助打击犯罪”有两种含义,一是依法协助,二是不依法履行职责协助。后一种情况就会导致要求律师不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与公检法机关相配合,加入“打击犯罪”的行列。一些地方的司法行政机关为了配合地方的“中心工作”或“专项斗争”,明确要求律师在“涉黑”案件辩护活动中“不可纠缠细枝末节”。在此种背景下,有的地方出现了本地律师不敢为本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现象。然而,一味强调律师不纠缠细枝末节必然会影响律师辩护应有的法律品格,使法律之争可能演变为一场行政博弈;一味要求律师“顾全大局”必然会牺牲个体利益,在本该坚持“为案件质量而尽职”的时候却选择放弃;要求律师“不要纠缠细枝末节”必然会使辩护实际效用受限,只要实体正确,程序瑕疵都可以忽略不计;要求律师“协助打击犯罪”在某些情况下必然会使控、辩、审“三方构造”走样,刑事诉讼的运作将更加难以走向现代化。①(5)① 参见韩旭:《刑事诉讼热点问题专题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根据笔者近期调研了解的情况看,律师办理涉黑涉恶案件的执业状况总体上还不能称为已经根本好转。一是有的地方以需要办案机关审批等为由限制律师会见权,以至于律师在侦查期间“难以作为”,这一问题在笔者调研中不是个别现象。二是律师申请取保候审难,一些办案人员担心被指责为“打击不力”,对涉黑涉恶案件的被追诉人不严格掌握羁押的条件,不仔细区分情节差异,均予以羁押,导致有些看守所人满为患。三是法外设置义务,要求律师办理涉黑涉恶案件“报备”。虽然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素质被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反复强调,但在对待律师辩护问题上,一些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培养起来,与法治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权利或者增加公民义务的规定。我国2015年修订后的《立法法》第八十条也作了相应规定:“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然而,据一些律师反映,在涉黑涉恶案件办理中被额外增加了一些义务,例如案件办结后需向律师协会提交书面总结,律师拟作无罪辩护或改变案件定性时,律师事务所要组织集体研究,提出案件处理方案和辩护代理意见。如此一来,律师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不仅工作量增加,而且依法独立辩护受到影响,降低了律师为涉黑涉恶案件辩护的积极性。
律师辩护难问题是刑事诉讼领域的一大“顽疾”①(6)① 2012年刑诉法实施后律师辩护难问题参见韩旭:《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辩护难问题研究》,《法学论坛》2015年第3期。,虽然中央政法各机关单独或者联合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规范性文件,但因这些文件的落实性措施本身不够切实有效,收效甚微。因此,仅靠发文并不足以解决问题,需要采取针对性的综合性措施才有可能,特别重要的是从思维、观念上认识到律师制度、辩护制度存在的价值。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原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撰文指出:“法官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不尊重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工作关系上有无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认真进行深刻反思。要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是人民法院的同盟军,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②(7)② 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第002版。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2015年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指出:“律师依法在诉讼每一个环节上较真、在案件每一个细节上挑毛病,有利于司法人员的认识更符合事情的本来面目。”③(8)③ 孟建柱:《充分发挥律师队伍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人民网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5/0827/c398806-27524695.html。律师的职能就是“较真”“挑毛病”,那种所谓的律师“不要在细枝末节上纠缠”,其实就可能在客观上会削弱律师辩护。只有从思想上认识到律师是防范冤假错案不可替代的一支重要力量,司法人员才会充分信任并自觉运用这支力量。可以说,涉黑涉恶案件中是否重视律师辩护、律师作用发挥如何是检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运行状况的一块“试金石”。针对当前实践中存在的律师辩护权保障不到位的问题,在涉黑涉恶案件中加强辩护权保障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保障律师会见权,尤其是侦查阶段的会见权。虽然这已是一个老话题,但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主要体现在对涉黑涉恶案件的处理中。会见是辩护的起点,如果会见权得不到保障,那么辩护权也将“唇寒齿亡”。各办案机关应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落实律师凭“三证”会见的要求,清理内部的“土政策”,以积极的作为保障律师会见权的落实。二是对涉黑涉恶案件也要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区分犯罪情节和在犯罪中的地位,对律师提出的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被追诉人,仍可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以降低审前羁押率。三是保障涉黑涉恶案件有律师参与。鉴于涉黑涉恶案件的特殊性,为了实现程序和实体公正,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追诉人,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提供法律援助律师为其辩护。四是保障律师的申请权。对于律师申请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予以准许,对于不准许的,应当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五是保障律师在法庭上的诉讼权利。重点保障律师的发问权、辩论权和质证权。作为法官,对控辩双方要做到“平等对待”,不要轻易打断律师的发言,更不能用侮辱性的语言对律师进行人身攻击。近期引起社会热议的广东省某法院刑一庭某法官连续三次打断律师发言,并批评律师道;“你充分不一定能把事情讲清楚,说明你水平不够,抓不住重点,明白不?”该事例即说明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权并未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正如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所言:律师辩护旧的“三难”问题未解决,新的“三难”问题又出现了。六是重视律师辩护意见。无论是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还是发问权、辩论权、质证权的保障,其最终还是服务于提出有理有据的辩护意见,辩护意见被采纳与否是律师价值的重要体现。可以说,裁判文书是法官理性和良知的一面镜子。为此,法官应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尤其是对不采纳律师意见的事项。“两高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恶势力意见》)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恶势力定性提出辩解和辩护意见,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评析回应。”虽然最高司法机关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办理提出类似要求,“举轻以明重”,辩护律师对黑社会定性提出辩护意见的,人民法院更应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评析回应。七是为律师办理涉黑涉恶案件“减负”。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办案机关应当依法保障律师各项诉讼权利,为律师履行辩护代理职责“提供便利”,而不是“增加负担”。对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报备”规定应当予以废除,从而保障律师独立发表辩护意见的权利。当前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积极性并不高,为“黑恶势力”辩护更容易受到消极影响,从鼓励律师积极参与“专项斗争”的角度论,亦应废除上述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规定。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从公安司法机关角度看,应当尊重并保障律师的辩护权,但从律师自身的角度看,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时更应规范执业,尽可能减少执业风险。律师职业要赢得社会的尊重,必须以规范执业为前提。我们不能只一味讲“保障”而忽视了“规范”,两者不可偏废。对此,《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律师违反会见规定的;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煽动、教唆和组织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等,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违反规定披露、散布不公开审理案件的信息、材料,或者本人、其他律师在办案过程中获悉的有关案件重要信息、证据材料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律师辩护、代理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相关办案机关要注意收集固定证据,提出司法建议。”
三、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专项执法更容易出现不重视程序的不规范取证甚至违法取证的情形。①(9)① 参见邓学平:《警惕运动式执法偏离法治轨道》,《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5月1日,第002版。为了将涉黑涉恶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更应重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就笔者长期的观察而言,非法证据排除在普通案件中即难以得到贯彻落实,在涉黑涉恶案件中难度更大。尤其是随着下一阶段以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为对象的“打伞破网”行动的展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状况将检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色”。为此,在实践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职务犯罪案件中应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大多由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在律师尚不能介入调查程序的情况下,权利对权力无法形成制约,调查的正确性主要靠内部自律来保障。例如,《监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问题是,这种“自我排除”如同“自向证明”一样,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显然,仅靠“自我排除”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外部的法律监督。①(10)① 关于监察委员会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在进入刑事诉讼后应否加强司法审查以及能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参见韩旭:《监察委员会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问题》,《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监察调查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的标准应该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衔接。关于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在标准上的衔接问题,参见杨正万:《审判中心背景下监察程序若干问题研究》,《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既然监察委员会调查的案件在进入诉讼后适用《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的规定,那么在理论和制度层面监察委员会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无障碍。但是,在谈及该问题时,有的检察院领导颇感无奈,表示对于监察委员会移送的证据材料只能“照单全收”。理由是除了监察委员会“位高权重”外,在技术操作层面无法对监察委员会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其一,对监察委员会重要取证活动的录音录像,《监察法》规定是“留存备查”而不“随案移送”;其二,参与证据调查的监察人员不像刑诉法上的侦查人员一样“出庭说明情况”。监察委员会作为“政治机关”的定位,其调查取证行为及其后果很难受到司法机关的制约。但是,“政治机关”只要办案,就要遵循办案规律,而办案规律的遵循不仅是事物内在本质使然,而且也是办案机关严格约束权力使然,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应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体工作在监察调查工作上的体现。②(11)② 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要求,请参见杨正万:《习近平法治思想论纲》,《贵州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最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提出坚决防止设定“零延期”“零退查”“零不诉”“零无罪”“零上诉”等不切实际的工作目标,说明这一问题在一些地方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容许这种违背客观规律、不切实际的工作目标存在,那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么根本得不到实施,要么实施会受影响。为了使监察人员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在进入诉讼后能够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使司法审查成为可能,需要明确两点:一是对重要调查取证活动的录音录像,包括对被调查人员的讯问录像不应局限于“留存备查”,而应“随案移送”,辩护律师可以查阅。二是在法庭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调查时,监察人员应当出庭就取证合法性问题“说明情况”,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这应当作为监察人员的一项义务予以明确。其实,当监察人员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其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之前检察院侦查人员的角色。我们不能以监察机关系肩负特殊的反腐败任务为由,令其工作人员不遵守刑事诉讼规则。
(二)“证据合法性法庭调查”应成为常态
审判阶段是非法证据排除的最后阶段,也是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关键阶段。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率低很大程度上与证据合法性法庭调查率低有关系。据有关调研结论显示:2012年刑诉法实施后的一年半时间,某市两级法院一审案件庭审过程中,辩护人和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并明确提供线索的86件,均没有被采纳。①(12)① 参见卞建林、谢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发展——以《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颁布为视角》,《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刑诉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三项规程”中《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以下简称《排非规程》)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可以驳回申请。”无论是“认为可能”还是“有疑问”,都是一种主观性表述,赋予法官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可能存在法官中立性还需要增强。且一旦启动证据合法性的法庭调查程序,势必影响庭审效率,加剧“案多人少”的矛盾。所以很多法官不愿意启动证据合法性法庭调查的程序,如此一来“排非”将遇到更大困难。为了避免涉黑涉恶案件中重蹈非法证据排除率低的覆辙,对法官滥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启动权予以适当限制是必要的。这种限制应当体现在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客观化”上——只要被告方提供的线索或者材料使法官对取证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或者认为非法取证“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即只要被告方能够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等较为明确的线索,所提出的申请客观上具有“可查性”,法院原则上应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以此压缩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②(13)② 参见韩旭:《非法证据排除新规:进步、局限及其适用问题——基于<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正如陈光中教授所言:“对于线索、材料只要比较具体,感觉有一定的真实性,就符合要求了,而不能将线索材料提高到要求提供具体证据的程度。”①(14)① 陈光中:《对<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几点个人理解》,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4期。非法证据排除受程序空间的限制,在侦查阶段难以展开,因此,对于审判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就应该从程序方面推动该规则的落实。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空间分析参见杨正万、王天子:《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研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三)在调查时机选择上应以“先行调查”为原则
我国在非法证据调查时机上经历了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确立的“前置调查”程序、2012年刑诉法司法解释确立的“先行调查”与“随机调查”相结合程序、2017年“两院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确立的“先行调查”为原则、“随机调查”为例外的调查程序。2018年《排非规程》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査的,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一)多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二)其他犯罪事实与被申请排除的证据没有关联的。在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法庭调查程序结束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出示、宣读。” 在调查时机的选择上,应当说最后一种模式兼顾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比较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的目的。“排非”规则解决的是证据能力问题,即是否有资格接受法庭调查而非是作为定案根据的资格,由此决定了“前置调查”“先行调查”的必要性,这也是符合诉讼证明规律的做法。只有非法取证行为能够接受法庭的先行调查,将侦查人员和监察人员的非法取证“成果”排除在法庭之外,并给予负面的消极评价,才能“釜底抽薪”,从根本上遏制其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四)裁判文书应当对辩护方的“排非”意见予以回应
针对过去辩护方提出“排非”申请后,法院“不了了之”的做法,“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并说明理由。”并在第四十条规定了程序性后果,即“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未予审查,并以有关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上述规定有助于提升“排非”申请的审查和证据合法性法庭调查的比率,进而提升非法证据排除率。同时,对法官的恣意能起到较好的制约作用,也体现了对律师辩护权的尊重,有助于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涉黑涉恶案件,社会关注度高,法官更应重视裁判文书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说理。裁判文书是“理”与“力”的结合,只有“有理”才会“有力”。
四、办案模式问题
我国《宪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也作出了类似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分工负责、配合制约”原则既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的宪法原则。然而,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深层次原因。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那样:分析几起冤假错案,我们不难发现,造成冤假错案最关键的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公检法在办案过程中相互遮掩、相互“协调”,最终默契配合出“铁案”。①(15)① 参见彭波:《公检法“默契配合”出冤假错案》,见http://www.sohu.com/a/69866680_365359。“配合有余”的极端表现是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对此,早在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该“意见”第二十三条明确提出:“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各地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模式需要完善,当前模式固然有利于加强对扫黑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但这种办案方式存在联合办案的嫌疑。
“联合办案”其实就是模糊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分工,通常都是由当地领导机关牵头,它固然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发挥集体智慧,但是在职能分工原理指导下的“分工负责、互相制约”原则却难以体现。司法办案是一种“技术活”,不仅需要亲历性,更需要长久的专业训练,非专业人员是难以胜任的。我国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就是为了保障从业人员的专业资质。从以往冤假错案发生的教训看,案件的疑点在“联合办案”中被协调掉了,削弱了后一环节对前一环节的监督制约。
“联合办案”会影响司法改革的成果。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重在解决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问题,确保审判权、检察权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责任制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联合办案”之下,不仅司法责任制难以落实,也不利于审判权、检察权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联合办案”的做法虽然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但是随着程序正义理念的勃兴和司法的文明进步,它的局限性已被充分揭示,其法治精神的体现也不充分。对此,我们应予以高度的警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在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中,公正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不应为了效率而损害公正。“联合办案”的做法不仅于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而且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有消极影响。在当前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
五、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运行问题
涉黑涉恶案件大多是有组织犯罪案件,因此在打击上不能“平均用力”,应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区别对待,“抓大放小”,将打击的锋芒对准“保护伞”“黑社会老大”“恶势力集团头目”。如此,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才能真正推进,案件质量才能有所保障。
(一)用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做好审前分流工作
以审判为中心必须做好审前筛选分流工作,这是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进的前提条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则为审前分流提供了制度基础。从实证调研看,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比例较低,尤其是酌定不起诉的适用受到种种限制,检察官适用酌定不起诉的积极性不高,不起诉制度并未起到审前分流的作用。①(16)① 参见张树壮、周宏强、陈龙:《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运行考量及改良路径——以刑事诉讼法修改后S省酌定不起诉案件为视角》,《法治研究》2019年第1期。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既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不仅使被追诉人背负上沉重的“罪犯标签”,还使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举步维艰。
如果说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由法院主导推进,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则是由检察机关为主导。检察机关应当用好这一制度,做好“繁简分流”工作。对于经过两次退查后证据仍然不足的涉黑涉恶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存疑不起诉”或者“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认罪认罚的犯罪组织成员,可以作出酌定不起诉处理,以体现“从宽”的精神。当然,检察机关正在推行的“捕诉合一”改革,对不起诉比例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依笔者之见,“捕后不诉”对检察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多措并举,促使人证出庭作证
当前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庭审实质化,庭审实质化最主要的是质证实质化,这就要求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实行人证化审理。这是防范冤假错案、保证案件质量的关键。要将涉黑涉恶案件办成经得起时间和法律检验的“铁案”,也必须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促使人证出庭,实现庭审实质化。 而庭审实质化面临的最大障碍即是人证出庭问题。针对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的重点是“保护伞”“黑社会老大”“恶势力集团头目”的刑事政策,应当采取不同措施促使人证出庭。一是为了既准又狠的打击“保护伞”,一方面要通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极鼓励黑恶势力成员检举揭发“保护伞”,并能出庭作证协助指控其犯罪;另一方面办理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监察人员就调查取证的合法性问题出庭“说明情况”。如果辩护方就证据合法性问题提出异议甚至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时,监察人员仍拒不出庭“说明情况”,一则不符合习近平法治思想,二则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难以继续推进。二是为了真正将涉黑涉恶案件办成“铁案”,就要区别对待黑恶势力头目和成员,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对此,《恶势力意见》规定:对于恶势力的纠集者、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以及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共同犯罪中罪责严重的主犯,要正确运用法律规定加大惩处力度,对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坚决判处重刑或死刑。对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罪责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相对不大的,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认罪认罚或者仅参与实施少量的犯罪活动且只起次要、辅助作用,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基于此,有两点可以考虑:其一,将“罪责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相对不大的”黑恶势力成员可以转化为“污点证人”,用来作证指控“黑社会老大”“恶势力头目”的罪行,保证用以定罪的证据确实充分。其二,加强对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保护,解除其作证的后顾之忧。鉴于黑社会性质犯罪大多都是有组织犯罪,加强证人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的保障尤为必要。《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针对涉黑涉恶案件中证人容易遭到打击报复的特点,如何将上述法律规定落到实处,乃当务之急。
(三)严格证明标准,确保案件质量
“扫黑除恶”案件的办理因更强调效率,办案质量需要格外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包括涉黑涉恶案件在内都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案件质量是保障。根据以往冤假错案发生的教训可知,不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搞“疑罪从轻”“疑罪从挂”,是冤错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是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还是不认罪、不认罚的案件,均应坚持法定的证明标准,做到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基于“扫黑除恶”案件的特殊性、打击的必要性,在案件的办理中,至少应坚持“两个基本”: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需要注意的是,证据确实是“质”的要求,证据充分是“量”的要求,两者应当同时具备。“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得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刑诉法规定,在“扫黑除恶”案件中应当得到贯彻执行。
六、重复追诉问题
有律师反映: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存在重复追诉问题,10多年前甚至20年前已经调解结案的,现在又被贴上“黑社会”的标签进行追诉。这从中央政法委近期调研的情况中也可得到印证。中央政法委在《“扫黑除恶”当前需注意6个苗头性问题》中首当其冲提到“随意定性、乱贴标签的问题”和“尺度不一、畸轻畸重的问题”,即由于专项斗争声势浩大,个别地方和部门把专项斗争当成“筐”,搞“搭车执法”,以偏概全,偏离了专项斗争的原旨本意。个别地方和部门办案人员对法律政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欠缺,证据认定标准不一、法律适用不准,出现“拔高”定案问题。①(17)① 参见陈一新:《“扫黑除恶”当前需注意6个苗头性问题》,见http://www.sohu.com/a/314260339_487466。“禁止重复追诉”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所确认。它要求国家在行使刑事追诉权时有义务保持手段的节制,在程序上,国家对同一被追诉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只拥有一个刑事追诉权,只有一次追诉机会。一旦国家行使了这一追诉权,对被追诉人提起了追诉,无论结果如何,则该追诉权即告耗尽,嗣后,不得就同一被追诉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再次追诉,否则,即属刑事追诉权的滥用,将过度侵害被追诉人的权利。同时,也是实现诉讼效益,保持程序经济性的重要途经。②(18)② 参见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9页。显然,对于漏罪、漏犯的立案侦查、补充起诉已经超出了“同一被追诉人的同一犯罪事实”的范畴,不受“禁止重复追诉”原则的约束。问题是,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来临时,少数部门的办案人员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进行追诉,这显然有违“禁止重复追诉”的精神。据悉,有的地方的办案人员为了以“态度积极”的外表示人,主动将案件排查期限延期,上溯至此前的若干年。笔者认为,排查涉黑涉恶案件线索并从中发现“保护伞”确有必要,但是不排除一些地方为“凑数字”“出政绩”而乱贴标签的问题。因此,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一定要警惕“扩大化”的问题。只有严格执法,通过“扫黑除恶”赢得民心的努力才会有保障,才能保证不适得其反。
禁止重复追诉,也被称作“一事不再理”原则,其目的是维护法的安定性和裁判的既判力,进而保障社会关系的安定性,避免公民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只有做到打击与保障并重,才能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偏离法治的轨道。鉴于此,在实践中应当注意:排查涉黑涉恶案件线索应有“度”的把握,不是上溯的期限越长越好。对于已经超过法定追诉时效、没有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证明存在“漏罪”“漏犯”情形的,不得随意“贴标签”进行重复追诉。即便是有新的证据证明过去已经处理过的纠纷存在涉黑涉恶的可能,在对当年的办案人员和部门领导人员追责时也应当慎重,这些人未必都是“保护伞”。
七、结论
“扫黑除恶”既然是一项专项斗争,且有期限的限制,那么就应当更加严格执法标准,更加注重程序法治,保证在实现诉讼效率价值的同时,不留“后遗症”。既然“指导意见”已经强调在“专项斗争”中要“强化程序意识”,那么在“扫黑除恶”中就要培育和树立程序法治的理念。“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①(19)① Justice William O. Douglas Comment in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 V Mcgrath ,See United States Supreme Reports(95 Law.Ed.Oct.1950 Term), 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1951,p,858,转引自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1页。程序具有“作茧自缚”的功能。讲程序就是讲法治,法治是全社会最大的公约数,讲程序可能会降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效率,但是收获的是正义,赢得的是民心,减少的是冤假错案。在传统社会,程序更容易被忽视,程序的价值和程序正义理念也有一个被接受和认识的过程。值得欣慰的是,今非昔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不同于当年的“严打”,程序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办案人员的认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否遵守程序以及遵守的程度如何,是检验我国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试金石”。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特别要关注律师辩护权的尊重和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公检法办案模式的科学化、禁止重复追诉原则的落实、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行等问题。上述这些程序化的指标,既是对前一阶段“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存在问题的反思,也是为期三年的专项斗争结束时少留“后遗症”的重要保障。在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背后,需要我们冷静观察、理性反思,这是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稳致远所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