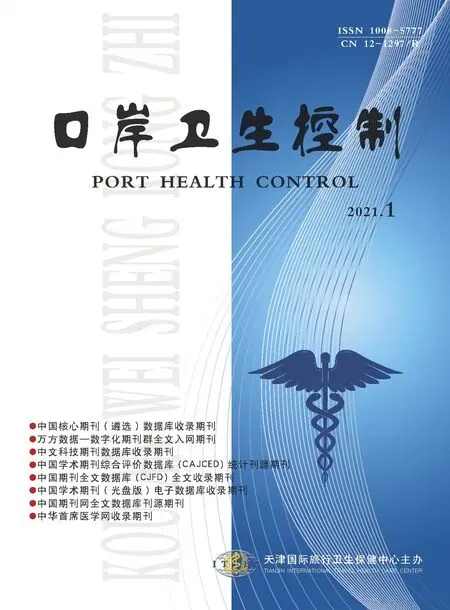国门生物安全
——从火炎防疫、 港口隔离防疫到全球治理
李尉民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北京,100176)
国门,是指国家对出入境的人和物进行管控的场所,也就是口岸[1]。 生物安全,是指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生物技术能够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生物领域具备维护国家安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2]。 生物安全的威胁包括: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传染病、动物疫病、植物有害生物、外来物种入侵,生物资源、遗传修饰生物和人类遗传资源等的非法移动,也就是管制性生物的非法活动。 因此,国门生物安全可以简要地定义为没有管制性生物非法进出口岸的状态。 要达到和维持这样的状态,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和创新[3]。
1 火炎防疫——自动物疫病管控开始起步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者侯客來者,以火炎其衡厄。 炎之可? 當者侯不治騷馬,騷馬蟲皆麗衡厄鞅轅,是以炎之[4]。 ” 这表明,在公元前二百多年之前,秦国就有法律规定,对于其他诸侯国来的客人,都要用火燎烧其马车,防止传入动物疫病,也就是火炎防疫。 此时的秦国已经具有了现代国家的特征[5],可以说火炎防疫是迄今能够确认的最早的国门生物安全管理实践。
然而,在相当长大的历史时期,古代人们的跨境贸易和人员交流频率比较低,规模比较小。 农耕经济社会主要依靠引种等传统生物技术,对危险性生物因子的认知十分有限,火炎防疫这样的管控也就非常少见,而且断断续续,例如,宋神宗时期对从契丹入境的马匹加强检查,严格按照“格式拣选”无病之马[6],终究很难成为长久的制度建设。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国家的形成比较晚。 古希腊是松散的城邦,古罗马没能整合民众,西欧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形成民族国家。 古时的口岸,其主要功能还是边境的军事关卡, 或者仅仅是查验人员凭证、征收税赋等。
2 隔离防疫——传染病防控中走向制度化
2.1 海港隔离防疫与公共卫生
公元前18 世纪,古巴比伦颁布的法律汇编《汉漠拉比法典》中,记载了西亚地区对麻风病患者的处置,麻风患者会被驱逐于市外,并且“永不再知他的居住在何方”[7]。约公元前1250 年,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第三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命令将数万麻风病人从家中带走, 安置在撒哈拉沙漠边缘。 公元前500 年前后成书的《旧约圣经》“利末记”第13 章记载,麻风病人要迁出去“独居营外” ;“列王纪·下”第7 章中, 也有以色列撒玛利亚城禁止麻风病患者在城里生活,而只能集中居住在城外山沟里忍饥挨饿的记载。 古代欧洲的隔离防疫,成效显著。 公元583年,里昂市议会颁布规章,决定由政府建立麻风病院,对患者实施隔离措施[8]。 12、13 世纪麻风病盛行, 欧洲建了许多隔离病院, 13 世纪其数量达1.9万多处,麻风病人随之迅速减少[9]。到14 世纪,强制隔离措施使得欧洲大陆麻风病基本绝迹。
十字军东征后, 地中海再度向西方敞开大口,经贸活动日益频繁。 航海技术进步,海港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欧亚大陆联系越来越紧密,传染病的跨境传播也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14 世纪,来自中亚的黑死病[10-11],1347 至1351 年席卷欧亚大陆及撒哈拉北部的非洲[12-13]。 居住在东西方商贸主要港口——威尼斯的人们认为:往来船只携带的被感染货物可以引起瘟疫,于是将有效控制麻风病等传播的隔离防疫措施,用于防范黑死病,建立了在海港隔离可疑船只、货品和人的制度。 1348 年3 月20 日, 威尼斯共和国组成港口隔离防疫委员会,把守整个地区的海港关卡,可将入境船只、货品和人隔离于环礁湖的小岛上[14-15]。 类似的策略被用于繁忙的地中海港口拉古萨(Ragusa,威尼斯共和国领土)[16]。1377 年,拉古萨通过了一项设置30d 隔离期的法律,被称为Trentino(30d)。 在接下来的80 年里,马赛、比萨和热那亚等也出台了类似法律[17]。 期间, 隔离期从30d 延长到了40d, 从而将名称改为Quarantine(40d),应该译为港口隔离防疫[18]。
随后,西欧许多海港陆续建立起专门的传染病隔离医院,多在城外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或者建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19-20],又逐步创制了由观测站、隔离医院和消毒所组成的抵御传染病的卫生控制系统。 例如,从1493 年开始,从受感染地区来到威尼斯的人,其随身信件在接受检查时,都会用烟熏消毒,钱币则用醋浸泡。 该系统从文艺复兴开始,被人们广泛接受并加以完善。 海港隔离防疫是中世纪西欧社会抗疫的创举,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包括相关的人事部门和资金支持,以及法律效力。
1546 年,意大利医学家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出版《论传染、传染病及其治疗》,提出传染病的三种传播方式,从理论上阐明了港口隔离防疫的有效性。16 世纪西欧港口隔离防疫已经十分普遍,并且出现了《健康证书》,用以证明有关船舶经过的前一港口没有疾病流行。 具有《健康证书》的船舶可以驶进港口,而无须接受隔离[21]。
1580 年,英国开始对来自葡萄牙的商人及货物实施隔离防疫。 1663 年伦敦大瘟疫期间,政府首次颁布法令,对入境船只隔离防疫[22]。17 世纪末,黄热病传入北美殖民地,几乎所有的主要港口都采用隔离防疫。 至18 世纪,北美殖民地都颁布了港口隔离防疫法, 多数港口城市设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18~19 世纪, 英国政府多次颁布法案, 强化隔离防疫。 直到19 世纪中期,英国当局仍会下令将来自疫区的船烧毁或凿沉[23]。
由于实施了严格的海港隔离防疫, 整个18 世纪,不列颠群岛和西欧没有暴发大的瘟疫。 而中东欧则遭受多次瘟疫巨大的破坏,只有哈布斯堡君主制统治的大陆地区例外。 这是因为当局早在17 世纪中叶开始,就将海港隔离防疫法律逐字逐句地应用到了大陆环境,在主要贸易路线过境点设立隔离防疫站。 1739 年,在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之间形成了一条卫生警戒线[24],从多瑙河延伸到巴尔干地区,由军事警察部队负责隔离和净化所有疑似传染病的传播者(人、车辆、货物和动物)。1770 年又总结了诸多皇家法令, 颁布法典:《卫生服务总规范》,违反者最高甚至可能被处以绞刑。 期间,17 世纪40 年代, 哈布斯堡帝国还引入海运健康证书制度,自1768 年与伊斯坦布尔签订双边协议后,又首先使用印刷版健康证书。
美国的港口隔离防疫始于1647 年波士顿条令,瘟疫流行期间所有违令停靠在波士顿港口的船只都会面临100 美金的罚款。 1663 年天花肆虐之际,纽约政府禁止接纳任何来自瘟疫感染区的人进入。 俄国港口隔离防疫始于1654~1665 年瘟疫爆发期间,沙皇政府实施港口隔离防疫猎施,封锁整个莫斯科城,任何试图进入的外来者,都会面临死刑的惩罚。 1840 年代的伊兹梅儿大(Izmail)港口隔离防疫,是俄国最为成功的案例。
黄热病的持续流行, 导致1878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港口隔离防疫法。 1892 年霍乱输人美国,港口隔离防疫法被重新解释,给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1944 年,美国又编纂了公共卫生服务法,联邦政府的港口隔离防疫授权首次被确立。1967 年港口隔离防疫工作转到国家传染病中心,即现在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5]。
19 世纪中后期由于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霍乱成为欧洲国家最大的危害。 1848~1849 年霍乱爆发期间,英国卫生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公然抨击隔离防疫政策,指出环境卫生更为重要[26]。 流行病学之父约翰·斯诺(John Snow)提出霍乱传播理论,英国兴起了公共卫生改革运功。 同时,不同国家港口当局强加的各式各样隔离防疫规则, 给船运、贸易和旅行带来极大不便, 其效果也受到更多质疑,要把船只从其繁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大势所趋。 监测、消毒等措施日益受到重视,医疗卫生的进步终究发挥了主导作用,公共卫生政策、组织、运作程序和技术逐渐完善起来,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隔离防疫在传染病跨境传播控制中的主导地位开始丧失。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细菌学、免疫学和现代药物学的最新进展,应用到有组织的公共卫生领域,使人类首次主动地控制了许多过去一直只能被动无奈受害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等,再加上人权和自由思想横行,隔离防疫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20 世纪后期艾滋病等传染病扩散, 危害全世界。 然而,2003 年SARS、2014 年埃博拉爆发,隔离防疫再次成为最成功的传染病跨境传播管控策略。
港口隔离防疫制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还被应用到了植物保护和兽医领域。例如,1660 年,法国地方政府通过法令,禁止小麦秆锈病菌传入。1866 年,英国签署法令,采用紧急措施,扑杀被进口患牛瘟病种牛传染的全部病牛,后来又制定了《1869 年(动物)传染病法》以控制牛的进口,1907 年发布了《危险性昆虫法,1877》。 美国则是在1875 年制定法律,控制桃树黄化病的传播扩散[27]。
2.2 中国隔离防疫到检疫的发展
据甲骨文和金文考证,公元前1350 年左右,商代建立有传染病人的隔离安置机构[28-29]。 秦还设有疠迁所,隔离收治麻风病人[30]。 7 世纪,唐朝实施行之有效的港口隔离防疫政策,拘留抵达海港的感染瘟疫的水手和外国游客[31]。
明末,占据中国台湾地区的荷兰东印度拓殖公司,1625 年在安平、 红毛等地海港设立隔离防疫机构,对来往船只和人员进行管控,以防止鼠疫传播。这是目前所知海港隔离防疫传人中国最早的记载[32]。明末清初逐渐开始闭关锁国,郑成功实施全面海禁后停办。
清初,天花也就是痘疫流行,满清皇室深受其扰,为此制定了查痘、避痘制度。 康熙年间设立“查痘章京”一职,负责稽查和驱逐出痘的病患[33]。 查痘的对象,还包括出国贸易的人。 俞正燮《癸巳存稿》云:“西洋地气寒,其出洋贸易回国者,官阅其人有痘发, 则俟平复而使之入”, 对出洋返国者加以检查,并对有出痘疑虑者进行隔离[34-35]。康熙采行种痘法,清中叶以后满人渐不以痘为忧,避痘与查痘之事遂渐趋式微。
清代谢清高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之一,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刊行的《海录》中,介绍了海外所见到的海港隔离防疫[36-37]。 19 世纪60 年代,通商口岸海关开始设立海关医务所,聘任关医,负责外籍人员医疗及海港隔离防疫工作[38-39]。 而此时欧洲的海港隔离防疫,已发展成为一套包括隔离、检查、消毒处理等一系列措施的制度,因此中文将其意译为检疫。
鸦片战争前的粤港澳一带,就有西方医师来办医院和传授卫生观念和行为。 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了通商口岸,有一些外国人居住,带来了西方已经实行的公共卫生措施[40]。 因此,中国在创建检疫制度的过程中,一开始就融入了公共卫生的思想。
1872 年2 月9 日,山海新关公布实施《牛庄口港口章程》,对营口(牛庄没沟营)港进口船舶实施检疫做出规定。 1872 年11 月27 日,接到香港行政当局天花疫情来电后, 上海海关派医官登“Enter-Prise”轮进行了检疫。1873 年,为防止印度、泰国、马来半岛等地霍乱传播,7 月21 日、8 月21 日上海、厦门海关分别初拟了检疫章程, 要求登轮查验,还有对染疫船实施薰洗的明确规定[41-44]。 以后各地海关的检疫法规,除了隔离,也有对病人行李实施消毒的要求(如1894 年的汕头)[45]。
20 世纪30 年代初, 民国政府负责卫生检疫的海港检疫管理总处、负责动物检疫的商品检验局和负责植物检疫的农产物检查所相继成立。 原先由外国人把持或地方政府设立的检疫机构,统一归中央政府领导。 检疫的对象也从传染病,扩展到了动物疫病和植物有害生物。
1932 年9 月28 日,民国政府卫生署颁布了《海港检疫章程》, 这是旧中国第一部全国统一的卫生检疫法规。 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实施了卫生检疫、动物检疫和植物检疫的法律法规,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历经多次改革,形成了逐渐成熟的检疫管理制度。
3 生物安全——管制性生物范围不断扩展
进入20 世纪后半页以来, 随着生物技术从传统(细胞或组织水平)到现代(分子水平)的飞跃,除了自然界形成的生物灾害,生物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特别是遗传修饰生物和入侵物种危害生物多样性的风险, 以及前沿生物技术(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的误用、缪用甚至被恐怖组织蓄意滥用的风险,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出现了生物安全的概念。
1993 年新西兰制定世界上第一部 《生物安全法》[46-47]。 2015 年 澳 大 利 亚 颁 布 《生 物 安 全 法》(Biosecurity Act)[48],取代了实施108 年的《港口隔离防疫法》(Quarantine Act), 管理对象包括可能危害人类、动植物和生态环境安全与健康的疫病或有害生物,管理的范围包括可能携带疫病人员、可能携带疫病和有害生物的货物、可能携带疫病和有害生物的运输工具、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等[49]。 这两个国家引领了生物安全管理的新潮流。
2020 年10 月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公布,自2021 年4 月15 日即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起施行。 这部新法律是生物安全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统领性法律,规定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生物安全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为本、风险预防、分类管理、协同配合的原则;针对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安全,生物恐怖袭击和生物武器威胁等生物安全风险做出了管控规定。
港口隔离防疫制度的管控范围一扩再扩,已经演变成为了国门生物安全管理,包括限制无症状的受染嫌疑人或动植物的活动,和(或)将无症状的受染嫌疑人或动植物,及有受染嫌疑的行李、集装箱、交通工具或物品, 与其他人或动植物或物体分开,防止感染或污染人类传染病和动物疫病病原、植物有害生物、食源性病原微生物,入侵物种的播散,以及控制濒危物种、物种资源、人类遗传资源和遗传修饰生物等的非法移动和贸易等。 世界各国大都实施了相关的法律、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并发布了管制性生物名录[50],采取出入境前、中、后三个时段的综合管理措施。
4 国际合作——生物安全国际协议和组织
生物安全威胁具有显著的全球性特征,早在19世纪后半页, 西欧国家就开始了国际合作,20 世纪得到强化, 催生了一系列生物安全国际协议和组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先后签署或加入。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 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通常被称为《日内瓦议定书》是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首个国际公约,1928 年2 月8 日生效。《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通常称为《生物武器公约》(BWC), 1975 年3 月26 日生效[51]。
在英国等召集下,1851 年欧洲国家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公共卫生会议,对各国港口当局采取的隔离防疫进行协调。 由于英国和北欧的卫生改革者,曾认为源自垃圾和下水道秽物的瘴气是致病主因,很多地方一度拆除了隔离防疫设施,前期多次会议无法达成一致。 1860 年后,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提出传染病的根源是病原微生物,开创了医学的细菌学时代,特别是1883 年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发现霍乱病菌,各国对港口隔离防疫才又形成共识,1892 年1 月30 日达成《国际卫生公约》, 后来发展成为《国际卫生条例》(1951 年)。1948 年诞生了世界卫生组织(WHO),是联合国系统国际卫生问题的指导和协调机构[52],在其召开的第58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了新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 (2005)》(IHR2005),2007 年6 月15 日生效,旨在通过缔约方和WHO 之间的合作行动,为从源头上(即在其越境蔓延之前)预防、发现和遏制公共卫生风险提供法律框架,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扰[53]。
1921 年, 法国组织召开国际动物流行病学大会, 并最终促成1924 年建立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54], 主要职能是制定动物及其产品国际贸易中的动物卫生标准和规则。 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于1878 年签署《防止葡萄根瘤蚜措施国际公约》,成为植物保护的第一个国际协定。1951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通过《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1952 年生效, 其目标是建立国际植物卫生措施标准,防止植物有害生物的传入和扩散,保护全球栽培植物和自然植物资源,并使其对国际商品流通和人员流动影响最小化[55]。
鉴于野生动物贸易对濒危与珍稀物种造成的威胁,1972 年6 月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 各国达成共识,促成1973 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诞生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1975 年7 月1 日生效,成为保护野生生物最有效的国际公约[56]。
现代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物种灭绝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地球正处于第六次绝种潮边缘[57],为应对这一挑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8 年开始努力,1992 年达成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CBD),1993 年12 月29 日生效[58-59]。CBD 有两个补充协议:一是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人体健康,而控制和管理生物技术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的 《生物安全议定书》[60],2003 年9 月11 日生效;二是《关于获取遗传资源与公平和公正分享其利用产生的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简称《名古屋议定书》), 2014 年10 月12 日生效[61-62]。
此外,国际上还达成了《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63]、《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64]、《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65]、《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66]等。
5 全球治理——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 世纪90 年代治理理论兴起, 成为各国政府管理变革的普遍趋势。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生物安全这类公共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单纯依靠政府供给出现了困境。 只有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参与、形成凝聚力和协同力,也就是治理,才有可能解决生物安全等问题。 进入21 世纪,全球化明显加快,计算机、通讯、网络和交通技术飞速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虽然反全球化不断,但科技和市场规律推动下,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历史发展趋势。 生物安全问题也日益全球化。 应对生物安全威胁,非经全球治理,绝对不可能奏效。 维护全球生物安全,必然走向全球治理[67]。
5.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指导思想
2013 年3 月23 日, 习近平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68]。 2017 年1 月17 日至18 日,在达沃斯小镇和日内瓦万国宫,习近平对破解“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世界之问的这个中国方案做了详尽的解读,获得全球范围内的积极回应。 2020 年初开始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未平[69],引发全球危机,以沉痛的代价警醒人们,这个世界紧密相连、休戚与共,需要全人类和衷共济,只要有一个国家的疫情尚存, 整个世界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 再次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远意义,这一理念像灯塔一样, 绽放出跨越时空的真理光芒,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指明了确定性的方向,注入了行动的力量,必将成为生物安全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已然存在的事物,更是未来的愿景。 生物安全领域已经形成的一些国际合作机制, 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步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需要的不是破旧立新,而是在已经存在的国际机制的基础上,以改革创新的姿态继往开来,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求同存异地推动其更加完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然选择。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大势所趋[70]。
5.2 主权国家仍是最根本的生物安全屏障
国家是当代最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建制,是国际事务最基本、最主要的行为体,也拥有更多、更强的治理能力和合法性。 人类社会抗击新冠疫情的实践表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告别民族国家只是一个浪漫的幻想,主权国家仍是现今世界最重要的生物安全治理的组织形式。从新冠病毒爆发伊始,世界各国政府都先后启动了防控疫情的各种措施, 对边境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 对这场以前所未有速度传播的瘟疫,国家主权的行使和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全球化时代应对生物安全威胁最根本的力量,独立的民族国家仍然是最根本的生物安全屏障。
5.3 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核心作用不可或缺
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协议,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中一直居于舞台的中央,举足轻重,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硕果累累的成就,是多年国际合作的结晶,是历史给与人类共同的丰厚遗产,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中还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在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各自为政、本国优先干扰甚至瓦解着应对生物安全共同挑战的多边合力, 国际协同防控的迫切性凸显,必须有人类整体利益观。 无论是着眼当前,还是立足长远,应对全球生物安全威胁,进一步强化世界卫生组织等的领导力和权威性刻不容缓。面对命运与共的现实,各国越来越意识到,增强全球生物安全应急管理和风险防范能力、消弭治理赤字时不我待。 作为全球生物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 世界卫生组织等理应得到世界各国更高的重视、更好的配合,从而更好地展现其领导力、发挥其作用。 强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作用,是生物安全全球治理的时代要求。
5.4 隔离防疫是解决生物安全问题的法宝
生物安全管理或治理的精髓是隔离防疫。 隔离防疫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和财富。当今维护生物安全的各种措施都来源于,或者其目标都是隔离防疫。新冠疫情大爆发,隔离防疫被推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度。 中国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的实践[71-72],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和标准,再次证明古老的隔离防疫依然神奇。 隔离防疫是人类战胜瘟疫最有力的武器。即使没有疫苗,如果全世界都能和中国一样,不仅隔离确诊病例,而且隔离其密切接触者,甚至隔离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应隔尽隔,像灭火一样,不留任何火苗、不遗丁点火星,就没有战胜不了的瘟疫。 越南、新西兰等国家比较认真向中国学习,都取得了很好的抗疫效果。 未来对于任何新发传染病等危险性生物因子的威胁,只要采取严格彻底的隔离防疫,就能避免欧美新冠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也只有这样,将来人类才有希望能够真正避免一些灾难电影所描述的病毒等导致世界末日的来临[73]。
5.5 科技是应对生物安全威胁的终极武器
科学技术可以赋能各种生物安全管控措施,是解决生物安全问题的终极武器。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 许多国家利用大数据技术, 有效追踪病例密切接触者,辅以快速检测技术,从而能够及时识别并采取隔离措施,在控制疫情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冠疫苗的成功研制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的[74],已经开始使用,并且成为了不顾风险预警、没有充分尊重科学的一些欧美国家战胜疫情的唯一希望。 虽然非洲猪瘟[75]、新冠疫情爆发,暴露了既往风险评估的一些不足, 但若在予以克服的基础上,开展威胁评估,及时识别危险,开展脆弱性和韧性评估,就能找出防控不足,从而扬长补短[76]。 未来,秉承“同一健康(One Health)”整体理念,推动跨学科合作,将有望能够更加精准地监测、识别、阻止、控制、消除,并及时响应人类、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健康危机,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77]。 此外,宏基因组学检测[78]、区块链,5G 通讯、无人机等新一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也将为生物安全治理提供更坚强的科技支撑。
5.6 全社会参与切实维护好国门生物安全
全球77 亿人口,近些年每年都有12 亿人次跨国旅行。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年国际旅游人数减少约11 亿人次,2021 年以后有望缓慢复苏[79]。 进入新世纪以来,进出口货物、邮寄物和交通工具等数量更是巨大无比, 例如欧盟每分钟就有4.5 千吨商品进出口[80]。 仅靠政府机构应对全球化时代的生物安全威胁这种全球问题, 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生物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共享。 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跨国和全球公司、私人行为体,已经成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中不逊于国家作用的治理主体。 多元治理主体与国家治理主体共同投身生物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坚持知行合一、从我做起,坚持步步为营、久久为功,才能够管控好危险性生物因子,才能够换来全球生物安全,才能够换来青山常存、绿水常在,才能够赢得全球永续发展、开创生态文明新时代。
6 结语
两千多年来,人类为维护国门生物安全,从火炎防疫、港口隔离防疫、检疫管理以及国际合作,走到了全球治理。 新冠疫情这场百年大疫和百年大变局的不期而遇和叠加共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使得世界进入前景晦暗难明的动荡变革期,令全球治理的演进开始进入调整和迭代的新阶段。 未来,病毒还将继续从动物身上溢出,侵染人类,气候变化会使得生物安全威胁更加复杂,各国携手应对,共商、共管、共赢、共享仍然是历史大势。全世界人民都在同一艘船上,纵有风高浪急,只要各方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扬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风帆,通过全球治理,切实维护国门生物安全,人类发展进步的航船必将乘风破浪、不断前行,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