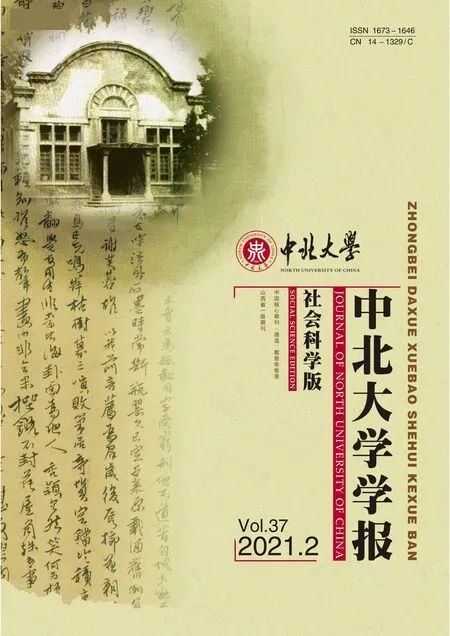视角的不可靠叙述与伦理反思
——以麦克尤恩《星期六》为例
王 悦
(厦门大学 深圳研究院, 广东 深圳 518000)
“视角”(Point of View) 是叙述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从19世纪后半期的福楼拜、 亨利·詹姆斯等人首次在小说创作中探索“有限的观察角度”, 到卢伯克的《小说技巧》和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中开始对叙述视角进行理论阐述, “视角”问题在叙述学中走过了相当长一段时期, 并成为20世纪叙述学中最热门的研究话题。 这一概念在叙述学中有多种不同的表述, 比较常见的如“聚焦” “叙述焦点” “观察点”等。
“视角”作为叙述加工的一种方式, 是叙述者将自我的主体意识局限于某一视角人物的感知范围内, 叙述者去“说”而视角人物在“看”。 这样一种“说”者与“看”者分离的叙述方式, 使得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在视角叙述中被割裂; 因此, 当视角人物由于感知、 判断、 立场等方面的不足或偏见而与隐含作者的规范相悖时, 就产生了视角的不可靠叙述。
自韦恩·布斯提出不可靠叙述的定义以来, 学界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研究长期集中于叙述者本人, 而对于人物的视角所造成的不可靠性关注较少。 事实上, 视角的不可靠叙述由于裹挟了人物的价值判断而使文学作品的现实书写更加立体多元, 不可靠的“看”法两端是主体与客体间的伦理关系, 为什么世界会在人物的审视中变形?扭曲真相的背后是哪些文化价值观的投射?什么样的客体容易成为主体自我欺骗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 不可靠的“看”比可靠的“看”富有更深刻的内涵。 下文就以麦克尤恩的《星期六》为例, 探讨视角的不可靠叙述所引发的伦理反思——从“看”的对象到“看”的主体的内省, 以及由此展开的对文化精神的深入审视。
1 “看”的企图
《星期六》是麦克尤恩创作于2005年的小说, 曾获当年的布克奖提名。 故事仅讲述了主人公贝罗安医生发生于一天中的事件: 凌晨目睹了一场飞机起火的事故、 打球的途中遇到反战大游行、 与街头混混的交通冲撞、 歹徒潜入家中报复及最后的化险为夷等。 全书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进行, 基本上一直跟随贝罗安的固定视角, 展现发生在这个城市和国家的政治局势和生活百态; 同时, 由于贝罗安习惯内省和反思的个性, 我们又总能在他的自我审视中看到对视角本身真实性的怀疑。 于是, 这部主人公的精神游记既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当代文明的简图——囊括了当代西方社会中的许多敏感问题, 又凸显出这种描绘自带的意识形态滤镜——贝罗安作为中产阶级的各种狭隘与偏见, 从而避免了单一的文化论点, 把有关社会伦理的质疑与回答都浓缩进对“看”这一行为的叙述中。
小说开头的第一个场景就是贝罗安在凌晨时分倚在卧室窗前的“看”。 夜半无端醒来的贝罗安, 遥望着窗前广场的月色, 回想近来的工作与家人的境况, 体味着内心思绪的翻涌, 直到一幕奇异的景象映入他的眼帘(或者只是在眼角的余光中意识到了变化):
他没有马上明白过来他看到了什么, 尽管他以为他看到了。 在第一时间, 出于渴望和好奇, 他在行星的范围内进行了推测: 这是一颗在伦敦上空燃烧的流星, 从左向右划过, 靠近地平线, 但比建筑物要高。 不过流星应该是像箭一样飞逝而过, 你只在它们耗完热量之前的一瞬间看得到。 这一个却移动得很缓慢, 甚至很威严。 这时, 他调整了自己的推测范围, 将它扩大到整个太阳系……它是一颗彗星, 有些泛黄, 熟悉的明亮彗核拖着它燃烧的彗尾……他正往床边走, 却听到了一阵低沉的隆隆响声, 像雷声般越来越响, 于是他停下来倾听。 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着火的部位一定是机翼与机身的连接处, 或者是悬挂在机身下面的一个引擎上(1)本文所引《星期六》文字皆出自McEwan, Ian所著Saturday, 2005版本, 引文为作者自译。……[1]12-14
这是一段典型的限定在人物视角中的叙述。 在贝罗安看到空中火焰的短短几秒钟之内, 他两次调整了判断, 叙述者没有直接言明事物原委, 而是让读者跟随贝罗安的视角调整自己的论断: 流星——彗星——飞机坠落, 当事件真相随着贝罗安的推断而渐渐清晰时, 恐怖感也随之逼近了。 它不是远在天边的一场景观, 而是近在咫尺的一场事故。
这一发现迅速改变了贝罗安的观看态度。 他不再以欣赏景观的态度来看眼前的场景, 而是在第一时间内进入一种判断——这是场恐怖袭击。 《星期六》写于2005年, 恐怖活动和反恐斗争是当时全球范围内炙手可热的话题, 麦克尤恩以贝罗安的视角, 表现出恐怖主义对西方人的生活和心理上的重大影响。 然而, 正如上面的引文中显示出来的, 贝罗安视角的局限性使他的判断不一定非常可靠。 “聚焦者的眼光观看什么, 不看什么, 张扬什么, 隐蔽什么, 这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而选择就意味着聚焦者无法排除其中的精神、 心理、 意愿等因素。”[2]108在贝罗安的观察中, 客观的情景已经屈服于内心的需要——“因为就在差不多十八个月前, 大半个地球的人们都不断地从电视上目睹了那些素不相识的受害者飞向死亡的一幕, 从此每当大家看到任何一架喷气式飞机都会产生不祥的联想。 如今人人都有同感, 飞机已不再是往日的形象, 而是成为了潜在的、 在劫难逃的武器。”[1]15
很显然, 到故事发生的时候, “9·11”的阴影还浓重地笼罩在贝罗安等人的心头。 然而, 在他目睹这场飞机事故之前, “9·11”事件对他来说只是一则令人惊骇的新闻——被传播媒介成功地框定在它的体裁范围之内, 这一次却随着他亲眼目睹的飞机事故而具有了不一般的意义——它成功地拉近了他与“恐怖”之间的距离。 无媒介的亲自观看原本应该释放比新闻报道更确切的真实, 却无法撼动贝罗安从“新闻”的视角中看大事件的习惯。 他不自觉地将它设想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 直到后来的新闻播报出来, 说那只是一场发动机起火的事故, 贝罗安才开始反省自己视角的不可靠性——他明明看到了“飞机当时并没冲向任何建筑, 降落的方式是有条不紊的, 其飞行路线是频繁通行的”[1]33, 却选择了忽略。 这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心理呢?
对于这种“过度诠释”, 喜欢内省的贝罗安不能轻易饶恕自己。 他认为自己是“屈从了内心的恐惧”[1]35。 从贝罗安在凌晨醒来开始, 恐惧感就如同一股淡淡的轻烟弥漫在他的视角叙述里, 他不能解释这种感受的来由, 就如同他不能解释自己夜里的突然醒来一样。 这样一种视角叙述细腻而真切地呈现了恐怖主义对西方民众心理的深层影响——它已经进入了大众心理的潜意识领域, 以致于使目击者选择性失明, 无法进行正常的判断。
恐怖事件或者说灾难本身可以转化为一场视觉盛宴, 传播媒体对它的再现对观众而言犹如电影大片。 媒体隔开了它的危险, 而观众则可以在对它的观看中纾解平庸生活所带来的压抑, 获得一种陌生的刺激。 这无疑是一种不可公之于众的隐秘心理, 而麦克尤恩通过贝罗安的视角, 将现代传媒影响下大众心理的暗黑一隅摆上了台面: 人们渴望着爆炸性的新闻, 哪怕是以悲剧的形式——只要自己不是当事人。 在我们对于新闻事件的多方关注中, 我们依然在延续古老的“看客”角色——对社会和民生的关心常常只是一个幌子, 只要不关乎己, 便可心安理得地看下去, 在评论、 谩骂或同情中收获一种对自我生活的满足。
通过这种对“看”的企图的揭示, 麦克尤恩展现出了贝罗安的视角所具有的不可靠性。 有趣的是,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贝罗安本人在自省中完成的。 不可靠的视角与对不可靠视角的揭示并存, 是《星期六》艺术上的一大特点, 反映出这种“不可靠”的背后存在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深层伦理因素。
2 “看”的出发点
在麦克尤恩的小说中, “科学”及其衍生的思想, 与传统的人文观念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常见的主题。 《星期六》的主人公贝罗安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 他与人文工作者在世界观上有本质的不同——贝罗安在人脑中看到的是神经组织, 一切的精神问题都由此而起; 而人文工作者关注的则是头脑中的“思想”, 这在贝罗安看来是一个太抽象而虚幻的事物。 科学与人文的争端在《星期六》的情节中有多处反映: 贝罗安一方面坚持科学主义的信仰, 对文学艺术不屑一顾; 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的文艺观表示怀疑——为什么那么多人崇尚它, 难道自己真的是太肤浅了?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确定, 他尝试着与文艺作品接触,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他有两个以文艺为职业的孩子——诗人女儿黛西和蓝调音乐家儿子西奥。
子女的爱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贝罗安, 尤其是女儿黛西, 她认为她的爸爸的“无知已经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 为了“纠正他的低俗品味和麻木不仁”, 她开始引导他接受文学教育, 并给他列出长长的书单。 贝罗安并不否认自己文学修养的缺乏, 但他觉得自己“所目睹过的死亡、 恐惧、 勇气和苦难已足以超越多部文学作品”。 换言之, 贝罗安对文学的轻视, 是来源于他对文学所构建的虚拟世界的轻视——“他对再造的世界不感兴趣, 他想要的是对世界的解释。 这个时代已经够奇特的了, 为什么还要再编造一个呢?”[1]64-65
这种观点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 关于艺术虚拟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的探讨源远流长, 柏拉图从他的理念世界出发认为诗歌和艺术都是“模仿的模仿” “影子的影子” “与真理隔着两层”[3]399; 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诗歌在虚构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而抛去了偶然性, 所以诗或艺术的真实可以高于生活的真实。[4]81到了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王尔德这里, 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则完全转了一个弯:“不是艺术模仿生活, 而是生活模仿艺术。”[5]143贝罗安的观点是柏拉图式的。 在贝罗安看来, 现实世界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旨归, 文学艺术的存在应该是为了模仿和美化生活, 那么它的价值就是低于现实的, 为什么还会值得当作一项成就去称颂呢?况且, 这种虚拟的模仿和美化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造物主已经非常完美, 我们只需要去解释和探究它的真相即可, 出于这种考虑, 他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尤为反感, 认为它是“想象力贫乏的产物, 是不负责任, 是对现实的困难与奇观的孩子气的逃避, 是对可信的世界的粗劣再现”[1]66。
有意思的是, 麦克尤恩一方面表现出主人公对于虚构的排斥、 对于真实性的信仰, 另一方面, 又通过他的视角, 反映出他眼中所谓真实的不可靠之处, 暴露了人物视角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 例如, 小说中的贝罗安有一辆名贵的奔驰跑车, 他喜欢坐在车里观赏他所在的城市, “享受着车里过滤过的空气和高保真的车内音响带来的完美音乐——舒伯特三重奏使他正在穿越的这条狭窄街道都变得高贵起来”[1]76。 通过“车里过滤过的空气” “高保真的车内音响” 城市里的贫穷、 肮脏、 落后仿佛都消失不见了, 这种逃避真实生活的方式让贝罗安“感到惭愧”, 但是又沉迷其中, 难道不是选择了一种自我对现实的“虚构”?
不止于此, 这种与“真实”生活的疏离更深刻地体现在思想层面。 贝罗安发现, 所谓自由的思想、 独立地观察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愈发困难:
他怀疑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容易上当的傻瓜, 主动而狂热地消费新闻事件、 观点、 推测和一切当局施舍的题材……每日收看新闻节目, 周六下午躺在沙发里看更多的空穴来风的专栏文章, 读长篇大论的实时追踪和后续报道, 看那些读完或证明之前就被忘了的事态预测,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做了就等于说是在参与事件?……他的神经, 像绷紧的琴弦, 顺从地跟着每则新闻的“发布”而震动。 他已丧失自己善于怀疑的习惯, 在针锋相对的观点中变得糊涂, 他的思路不再清晰, 更糟糕的是, 他感觉自己已经不能独立思考问题了。[1]184-185
可以看到, 贝罗安在自己的内省中, 再一次把视角的不可靠性揭示了出来: 当你以为自己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独立观察世界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媒体及其宣传的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你的思考。 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还是被新闻媒介虚构出的世界?当人们的视野随着媒体资讯的发达而空前广阔, 我们的视角也前所未有地充满了不可靠性——媒体在传播新闻的同时, 预设了让我们接受的视角, 要想摆脱它们去独立地思考、 去接触所谓的“真实”, 实属难事。
关于“虚构”在真实世界中的作用, 在小说情节的高潮——贝罗安一家遇到巴克斯特的劫持时得到了最戏剧性的证明: 巴克斯特以贝罗安的妻子罗莎琳为人质, 逼迫他的女儿黛西脱掉衣服, 当大家都一筹莫展时, 歹徒却突然对摆在桌子上的诗集产生了兴趣。 巴克斯特要求黛西读诗给他听, 黛西读的是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 这首广为传唱的诗歌竟引得巴克斯特大为动容, 他说它让他想起了他的家乡, 这种美好的感觉唤起了他对生命的渴望, 他要求贝罗安给他找出医治他的亨廷顿式舞蹈症的资料(之前贝罗安骗他说他手头有医学界对此研究的最新进展), 进而在上楼取那些资料的过程中被贝罗安父子所擒。
诗歌所创造的虚拟世界竟能让一个歹徒向善, 这是贝罗安所无法理解的。 巴克斯特说那首诗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而贝罗安只认为这是巴克斯特的亨廷顿式舞蹈症在作怪, 使得他的“情绪如此脆弱”。 善于内省的文明人贝罗安对于文学的感受力竟然还不如一个街头混混, 这是麦克尤恩设置的一处反讽, 对“真实”的科学主义执着在许多时候并不能使我们走近真实, 因为文艺的“虚构”原本就真实地存在于人性之中。
3 “看”的距离
“看”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意义, 前文已经有所提及。 资讯科技的迅猛发展繁衍了“看”文化, 它一方面使“看”本身具有一种娱乐化的特征, 另一方面, “看”在政治、 经济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关注度”成了现代社会获得名利的一个重要途径, 所谓“眼球经济”就是“看”文化中诞生出来的一个新产物。 但是,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 信息量的空前暴涨在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眼界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个必不可少的问题——人的注意力有限, 面对现代通讯带来的海量信息, 该如何选择?
关于这一点, 《星期六》中的贝罗安也有所体会, 且看他如何甄别和决定自己实施关注的范围:
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变得越来越复杂, 道德同情范围也日益扩大。 不止全世界的人类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狐狸也是, 实验室的老鼠也是, 现在连鱼也是。 贝罗安还是照样的钓鱼和吃鱼, 不过他从来不会把活虾丢进沸水里, 但这不妨碍他在饭店里点一份龙虾。 一直以来, 人类成功主宰世界的秘诀, 就是选择性地实施你的怜悯。 在进行识别时, 只有近在眼前的东西才会对人产生压倒性的影响。 而那些你看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从宁静的马里波恩街看起来世界如此祥和的原因。[1]128
贝罗安的态度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眼不见则心不烦”, 一语道出了“看”在筛选信息中的重要地位: 世界上需要关注的事物太多, 为了既保持良善, 又不妨碍人类“成功主宰世界”, 唯一的方法就是只关注眼前看到的东西, 其他看不到的就权当它不存在。 这一结论的抛出是非常反讽的, 一方面, 人类是出于对生命意识的尊重才改变了从前的人类中心主义, 将鱼虾鸟蟹等都纳入人道同情的范围, 这是所谓文明的发展; 另一方面, 人类也不可能因此放弃了自己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 其他生物对于人类来说既是同情的对象又是索取的对象, 无奈之下只得采取一个标准: 是否在眼前被我看到。 这一掩耳盗铃的做法与人类所宣扬的博爱同情是相悖的。人类对待事物的方式不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 而是由人与事物之间的观看距离所决定, 这从侧面证明了“看”的重要性, 同时说明了它为什么常常不可靠的原因。
小说一开头的飞机着火事故就体现出了“看”的距离在贝罗安心理上的影响。 “他参与了其中”, 这一点是造成贝罗安对事故性质定位错误的重要原因——比在媒体上看新闻更近的观看距离加剧了他的“看”的狂欢企图, 使他在潜意识中希望这是一场如“9·11”般惊天动地的大案。 他此后不断地在电视新闻中搜寻关于这一事件的播报, 又印证了他的这一企图: 在他的感觉中, 自己已不仅仅是一个目击者, 而且是一个参与者, 观看的距离给他造成了错觉, 使他呈现出不可靠的视角。
除此之外, 故事中的星期六这一天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 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大游行。 当伦敦市数十甚至上百万人走上街头游行的同时, 贝罗安却逆向而动, 驾驶着他的名贵跑车像往常一样去与同事打球。 他是倾向于赞成伊拉克战争的, 原因是他由于医生的身份而认识了一位来自伊拉克的教授米瑞·特勒柏, 这位教授向他讲述了他在伊拉克遭到莫名囚禁的悲惨遭遇, 以及那里暗无天日的民众生活。 他认为如果英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能够改变那里的独裁统治的话,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种观看距离的改变无疑是偶然的。 对于大部分英国民众来说, 他们只能通过媒体报道来进行判断; 而贝罗安由于恰巧认识了这一位教授病人, 近距离地了解了一位伊拉克公民眼中的现实, 因而改变了政治态度。 在他看来, 那些走上街头抗议的人们, 只是因为离伊拉克现实真相过远而被头脑中的偏见所煽动——尽管贝罗安自己后来也越来越不确定。 这种观察距离的拉近原本也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如何证明他所看到的就一定是最客观的。
小说中由于观察距离所影响的观念变化, 最集中地体现于巴克斯特闯入贝罗安家的情节中。 故事一开始, 贝罗安就隐隐地感到心中一种不安的悸动, 他无法说明原因, 却一直无法消除。 恐怖和暴力的阴影似乎一直在贝罗安的生活中若隐若现, 从清晨发现的那起飞机着火事故(他想当然地把它看作一场恐怖袭击), 到开车去打球的途中与巴克斯特等人正面发生的肢体冲突, 到耳闻目睹的关于伊战的支持与反对阵营的对峙, 整个世界似乎都不是真正的安宁, 某种令人不安的恐怖埋伏其中。 在他等候飞机事故的报道时、 在他坐在跑车里观赏城市里的一切时、 在他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反战游行的新闻时, 他都在思考着关于“恐怖”的概念——因为与己无关, 他可以在拉远自己与观察对象之间距离的过程中, 耐心地对其进行形而上的思考。 巴克斯特等人的闯入改变了他对恐怖和暴力的理解。 歹徒闯入了他的家, 这一次, 他的视角不由自主地进行了转换: 由于与恐怖分子面对面, “恐怖”对他而言不再是抽象概念, 他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恐怖”对于人们意味着什么。 当巴克斯特用刀子抵住他妻子的脖子, 打断他岳父的鼻梁骨, 并试图奸淫他的女儿时, 贝罗安在一天中不断进行的内省工作终于停止了。 生活的真相似乎在此时才与他无限贴近, 他从“看客”的身份中走出来, 从各种观念的裹挟中分离出来, 所能想到的只是如何击败敌人——令人感到有点讽刺的是, 贝罗安的视角在此刻变得前所未有的可靠。
4 结 语
综上所述, 《星期六》是一部围绕“看”的行为而展开的小说。 “看”的企图、 “看”的立足点与“看”的距离, 从各个层面展现了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个体所处的伦理位置及缠绕在他们身上的文化困境。 就小说而言, 不可靠的叙述视角可以被隐含作者“纠正”[6]194——读者正是以这种方式了解到不可靠性的存在, 它所要反映的并不仅是视角人物在认知、 情感立场上的不可靠, 还通过视角叙述审视“看”的方式本身种种不尽不实之处, 以及导致这些不可靠叙述背后的伦理原因。 呈现与反思、 建构与消解在文本中同时进行, 恐怕只有在不可靠的叙述手法下才能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