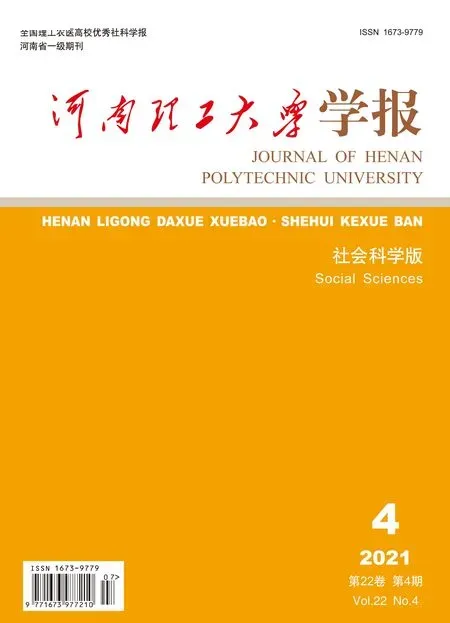论王昌龄悲慨与劲健互渗的诗歌风格
易烨婷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作为唐代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一直被奉为扛起盛唐“风骨”大旗的重要诗人,《河岳英灵集》的作者殷璠对其更是尊崇有加,认为王昌龄处在唐诗走向巅峰的关键时期。目前学界对于王昌龄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但对其诗歌风格的研究,却只是零散地分布在相关著作与论文中。这些论著或认为王昌龄诗歌开盛唐之风、劲健浑厚,或认为王昌龄诗歌继汉魏六朝之气、悲慨哀怨,所论皆有根据,但又都偏执一端①(1)①相关研究参见:魏耕原《王昌龄五古风格与〈诗格〉之关系》(《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2年中国会议),毕士奎《王昌龄诗歌与诗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许娟娟《王昌龄诗歌艺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张左军《王昌龄七言绝句的艺术特色》(《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笔者在细读王昌龄诗歌的基础上,发现王昌龄的诗歌风格虽然会因为题材的不同而呈现出细微差别,但是大部分呈现出一种悲慨与劲健交糅的风格,只不过有的诗歌中悲慨的成分多一点,另外一些诗歌中劲健刚强的作风则占据主导地位,而其最有特色的作品则是将这两种风格完美地融合为一体。根据进一步分析可知,王昌龄是通过抑扬结合的表现技巧、收放自如的场面描写、含而不露的情感表达以及多重架构的意境营造等手法造就这一独特的诗歌风格,而这种诗歌风格的形成,又与时代背景、诗人的生平遭际及其诗歌理论主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悲慨与劲健的诗歌风格的界定
悲慨意为悲伤感慨,有感伤之风;劲健则是刚劲强健,有强劲之格。悲慨、劲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当中,均有详细的阐释。“悲慨”一词最早见于东晋王羲之与殷浩书信中,其原文曰:“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1]2095其始有为家国担忧感伤之意。作为一种诗歌风格,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对“悲慨”的描述如下: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意苦欲死,招憩不来。
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
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露雨荒苔[2]163。
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从字义出发将“悲慨”概括为“悲痛,慨叹”[3]114。笔者以为,所以“慨”者,因是“悲”也。故当先有“悲伤”,挣扎而不能出,而后有“慨叹”。根据司空图的描述,风格悲慨的诗歌应该是起乎比兴、继之呐喊、转而沉吟、归于叹息。起首两句,“大风”卷水,林木皆摧,满是破败之景,令人悲痛。中间八句,则是在起首两句的前提下演化而来的一出悲剧。一“死”一“哀”之间,看透了长命百岁、富可敌国的虚云缥缈,展示了“大道”已倾、“雄才”难为的无奈,突出了“意苦”与“招憩”不得的痛苦,以及“雄才”却“拂剑”于身的悲哀。最后两句,则将两种失意肃杀的自然之景表现出来,令人不胜感慨,顿生无限唏嘘。正如张国庆先生所言,司空图所谓的“悲慨”:“既是一个显示着悲痛感慨(或悲凉慨惋)情调的风格概念,而更是一个近乎‘悲剧’的美学范畴。”[4]417笔者以为,这是一出社会悲剧的全方位展示。通过“大道”(美、善、正)与“大风”(丑、恶、负)的交锋,展现了前者不应有的毁灭与后者的胜利,饱含了作者对前者的深深同情与惋惜和对后者的无限憎恶与无奈,这正是标准的悲剧美学精神的体现。
“悲慨”是《二十四诗品》中比较特殊的一品,无论是从意象表达的激烈,还是从情感喷发的痛切来看,此品当属二十四品中之别调。此品不仅阐述了司空图的风格理论,更是将对现实社会的悲痛、体悟与联想表露于字里行间。通读全品可知,司空图认为的悲慨诗风应该具有慷慨激昂、沉郁悲壮、苍凉沉雄的情感特征,从而达到震耳发聩、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强大艺术感染力。
“劲健”一词出自《后汉书》,其原文为:“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5]2991这里的劲健是形容鲜卑兵力之盛、力量之大。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则曰: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
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
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2]66。
张少康先生从创作风格的角度出发,认为“劲健”,是“一种强劲有力、壮健宏伟的风格”[6]104。乔力先生则说:“劲健,系是对松懈窘迫而言。既指笔力和气势,更总指风格。”[7]44可见,“力”和“气”是劲健诗风最主要的特点。“劲健”一品所述乃是一种强劲有力的诗歌风格。此品以神、气二字贯穿全品。郁沅先生在研究此品时,打破了常规的三段顺序解析法,而是将之分为前后四句、三四句、五至十句三部分来解读②(2)②参见郁沅:《释〈洗练〉与〈劲健〉——〈二十四诗品〉通解例释之四》(《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笔者以为,若从文意解之,当以郁沅先生所分为妙。首先是神气充沛,“神”即内在之思想,“气”即外露之情感,要达到精神与情感的统一,司空图给出的要求是“如空”“如虹”,这里所强调的是精神追求不受任何阻碍,情感表达贯穿全文,并且是一种充沛的、昂扬的、刚健向上的思想情感。其次是云捷风强,捷者速也,强者力也。高谷狭隙之间,风云变幻最是激烈与长久,这里则是指诗歌中透露出来的速度、力量之大与持久。最后是守中存雄,“守中”即是把强劲之力收藏于胸,达到虚静;“存雄”即是指将外在的强劲之力表现出来,以示雄健,这就是司空图所要求的“真气”。可见,这种既要蓄气于胸、又要外露于体的阳刚之气是劲健诗风所必须具备的。
笔者以为,所谓“劲”,体现的是一种力度与气势,且没有衰败之刻;而“健”,体现的则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力,而没有停止之时。总而言之,“劲健”既是一种雄劲刚健的风格,也指内在蕴涵的深厚与强劲。
二、王昌龄诗歌中两种风格的互渗
在论及王昌龄的诗歌风格时,研究者往往是将其与诗歌题材简单对应,如论其边塞诗则曰“劲健”,论其闺怨(包括宫怨)诗和送别诗则曰“悲慨”,而对其诗歌中两种风格的交融互渗则注意不够①(3)①分别参见:张迎胜《王昌龄边塞诗的思想精华与艺术造境》(《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毕士奎《“怨”与“乐”:王昌龄、王建宫女诗情感差异探因》(《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笔者以为王昌龄边塞诗固然以慷慨激昂的风格为主,但亦屡有沉郁寡欢的色彩,而其闺怨诗、送别诗在写得婉转委曲、情深意长的风格里也不乏振起之格调。明陆时雍《诗境总论》论王诗七绝曰:“测之无端,玩之无尽。”[8]388吴乔《围炉诗话》论其五古曰:“或幽秀,或豪迈,或惨侧,或旷达,或刚正,或飘逸,不可物色。”[8]391诚如古人所评价,王昌龄诗歌绝不是单一的风格,而是悲慨与劲健的互渗,是多种风格的杂糅,这才是王昌龄诗歌耐人寻味的地方。
(一)以悲慨为主,悲中有健
以边塞诗为例,王昌龄在传统的羁旅行役题材的基础上加入了个性化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边塞将士丰富的内心世界。如《从军行七首(其一)》: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8]43。
这首诗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代表作,将戍边之苦与闺怨之愁很好地融为一体。 “黄昏”“独”“秋”将出征将士的悲苦、凄楚表现得一览无遗,结尾处落笔在“闺愁”的无可奈何,与前文两相照应。周珽在《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陆时雍的话说:“谓从军者闻羌笛而起金闺之思,非也。盖因边城闻笛,而代为金闺之愁耳。言己之愁已不堪,而闺中之愁将更奈何,亦通。起处壮逸,断句凄楚。”[8]44可见,陆时雍认为此诗虽通篇写愁,却于起句处透出昂扬气势。笔者以为,这是一首将悲慨与劲健完美结合的诗。全诗除首句铺场外,其余三句并及边塞戍守之悲苦,且最后一句更是将无法结束这种生活的无奈尽现眼前,却只能悲叹而已。恰恰是首句的铺场,使得这种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哀怨,显出一种壮美之感。
而迁谪诗《江上闻笛》则抒写的是作为不遇士子的失意愁怀:
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声长楚山外,曲绕胡关深。
相去万馀里,遥传此夜心。寥寥浦溆寒,响尽惟幽林。
不知谁家子,复奏邯郸音。水客皆拥棹,空霜遂盈襟。
羸马望北走,迁人悲越吟。何当边草白,旌节陇城阴[8]113-114。
这首《江上闻笛》是作者开元29年(739)秋在贬谪岭南的途中所作。此时诗人身在“楚山”,心系“胡关”,欲“遥传”此心而不可得的凄惨之情顿生。钟惺评“响尽”一句曰:“五字妙!所谓虚响之意,弦外之音,可想不可说。”[8]114笔者以为,此处的弦外之音,应指身遭贬谪、才不得用的怨愤牢骚 。“邯郸”在河北,而作者当时身处江南,“拥棹”“盈襟”“望北”“迁人”俱是异地思乡之语,诗人对于南贬的悲伤可想而知,最后两句将意境突转,凌宏宪评此句“转得有力”[8]114,悲怨之情一扫而尽。邢昉《唐风定》亦评此句:“边草、陇城入闻笛中,愈见空远。”[8]114笔者以为,此诗本是写贬谪带来的失落之感,通篇凄凉,但是在最后一句一转颓废,透出阳刚之气,一洗俗尘。
《西宫秋怨》是一首宫怨诗:
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
谁问含啼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8]98。
王昌龄进士及第后,任职京师时官至校书郎,这与诗人平生志向相去甚远,故其在京所作诸多宫怨诗,多有暗喻己才不受重用、悲切怨怼之意,这首《西宫秋怨》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芙蓉”指的是荷花,曹植的《芙蓉赋》直言其“览百卉之英茂”[9]179。此处言芙蓉不及“美人妆”,可见美人美艳之极也;其后又以“香”字誉之,极言美人之超凡也。唐汝询《唐诗解》认为此处:“不当以肤浅穿凿,俟妙悟者求诸言外。”[8]99此处不多说,且先看后两句,“谁问”有作“谁分”“却恨”两种版本,此处作“却恨”解诗较为妥当。从“恨”到“含啼”,再到“掩秋扇”,一语三折,画面如在眼前,合前两句读至此,令人顿生怜意。“空悬”句语出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月于洞房。”[10]119杨慎认为“空悬”一句“犹李光弼将郭子仪之师,精神十倍矣”[8]99,此一句,一转前三句造成的悲怨。读至此处,方知唐汝询之意。袁宏道曰:“思而不怨,弃而待用,雄厚之情可想而知。”[8]100此时诗人怀经世之才置身于天子之都,犹如美人在宫,不受宠幸也,却又始终是积极的,等待着明君擢举,这就是此诗悲慨中的劲健之处。
又“万乘旌旗何处在?平台宾客有谁怜”[8]9(《梁苑》),又“追随探灵怪,岂不骄王侯”[8]137(《留别岑参兄弟》),又“身在江海上,云连京国深”[8]158(《别刘谞》),又“谁识马将军,忠贞抱生死”[8]185(《留别武陵袁丞》),又“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8]54(《代扶风主人答》),皆悲怨哀叹中仍有清刚之气。可见在王昌龄以悲慨为主的诗歌中,仍不失劲健的格调。
(二)以劲健为主,健中有悲
王昌龄出生于关中之地,骨子里透着一种北方人的豪情。其劲健诗风在早年便已形成,主要体现在其边塞诗中,如《从军行七首·其六》写道: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
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8]50。
王昌龄此首边塞诗作于入仕之前,充满着对建功立业、封侯拜相的无限向往,故而豪爽俊丽、风骨凛然。“薄汗”“胡瓶”皆西域特产之物,此处指将军坐骑和装扮,碎叶城的月色更衬得将军英姿飒爽。这时皇帝的诏书和宝剑紧急送达,于是马上出发,率领士兵一夜攻取楼兰。这首诗凸显了作者对于唐朝国力的自信和对英雄的仰慕之情,整首诗气势豪壮。但是隐含在字里行间的还有一种欲建功名而不得的郁闷心情,这使得诗人在写作时有意选取了“秋月”这样的意象,秋夜的苍凉将将士的行军之苦不动声色地展现出来。这正是劲健之中又见悲慨之处,也是诗人个人情感的外露之点。
又《变行路难》写道:
向晚横吹悲,风动马嘶合。前驱引旌节,千里阵云匝。
单于下阴山,砂砾空飒飒。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8]33。
《变行路难》出自乐府旧题《行路难》。《乐府诗集》载:“《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8]33王昌龄此首《变行路难》不仅在句式上摆脱了乐府旧题的既定模式,更是一改前者离伤失意的情绪,实是男儿豪言壮语。第二句万马齐鸣,有昂扬之意。其后行军场面之大,又与“马嘶”暗自相合。五六句给出了如此兴师动众的原因,“砾砾空飒飒”足见单于兵力之盛,正是势均力敌,棋逢对手。最后两句点出人物心理,一战封侯是何等的荣耀,亦是多少人心中的梦想,既有此则闺妇何必挂念,然而静思之下,其中似暗含为征妇叹息之意。《诗经·伯兮》曰:“愿言思伯,使我心痗。”[11]84征妇思夫成病,终是徒劳。与征夫的无情相比,征妇的思念甚是可怜。且此诗首句便以一“悲”字定调,使整首诗于振奋之外又含哀伤之情调。
又《城傍曲》写道:
秋风鸣桑条,草白狐兔骄。
邯郸饮来酒未消,城北原平掣皂雕。
射杀空营两腾虎,回身却月佩弓弰[8]16。
笔者认为此诗当是实写。从“邯郸”观之,这首《城傍曲》应是作者游于冀中时所作。唐汝询《唐诗解》以为:“此见城傍猎客而赋其事,言木落草枯,狐兔狡健,猎者乘醉而来,手接皂雕,箭连双虎,向月而归,得意如此。”[8]17此诗用“秋风”“草白”等北方景色烘托气氛,“酒未消”“掣皂雕”写侠士的倜傥风流。“射杀腾虎”足见主人公箭法之精、力量之大。《史记·李将军列传》曾载:“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12]1465李广乃汉时名将,名震边塞,杀一腾虎犹为所伤,而诗中主人公醉酒后仍射杀两虎,其才能不可估量。“回身”“却月”“佩”三个动作行云流水,甚是潇洒。通读全诗,主人公形象饱满,豪情满怀,令人真欲亲眼一见。李梦阳评曰:“悲壮,真盛唐风韵。”[8]17诗人以李广喻己,示己怀安国之才,欲以报国却恨无门,只得以酒为乐。在凸显其壮烈豪迈的同时,又隐含着不遇的悲哀。
又“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8]49(《从军行七首·其五》),又“万里云沙涨,平远冰霰涩”[8]53(《从军行二首·其二》),又“儒有轻王侯,脱略当世务”[8]80(《郑县宿陶太公馆中赠冯六元二》),又“为君百战如过筹,静扫阴山无鸟投”[8]171(《箜篌引》),又“握中铜匕首,粉锉楚山铁”[8]214(《杂兴》),皆豪壮之中暗含哀伤。
(三)悲慨与劲健交糅
除去上述两种诗歌风格外,王昌龄最有特色的诗歌风格,就是能够做到将悲慨与劲健两种风格完美交糅。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王昌龄诗歌“优柔婉丽,意味无穷,风骨内含,精芒外隐,如清庙朱弦,一唱三叹”[8]386,即王昌龄的诗歌并非简单的抒情,而是多种感情的交织,刚健之处暗含悲慨,哀伤之间风骨顿现。如《从军行七首·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8]47。
周珽以为:“上联边塞之景,下联敌忾之词。”[8]48全诗士气极足,同时又将士卒戍守边疆的思乡情绪表露无遗。上联写长云气势之大,直使雪山失色,又将“孤城”与玉门关的距离拉得极长,将空间构建得极为广大,造成威压之感,在气势与力量上达到了一个极限。唐汝询《唐诗解》载:“哥舒翰尝筑城青海,其地与雪山相接,戍者思归,故登城而望玉关,求生入也。”[8]48笔者以为,此语实是将士卒心肝剖开与世人见也。“遥望”二字,将思念的强度无限放大,将士卒的戍守之苦、思乡之念展露于眼前,闻之令人怆然下泪。下联“百战”可见对阵次数之多,“穿金甲”可见战事的激烈,一字一句之间,体现了将士沙场杀敌的英勇无畏和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不破不还”更是国而忘家的牺牲精神的体现。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说:“作豪语看亦可,然作归期无日看,备有意味。”[8]48笔者以为,“不破不还”乃愤激之词,若有机会回来,能不回耶?此乃是久战无功,劲敌未破,悲无还期也。这种悲慨与劲健浑然一体的风格,将王昌龄的思想感情表达得十分透彻。
又《出塞二首·其一》写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8]20。
此诗历来为文论家所争议,有作悲怨解者,亦有作刚健解者。笔者以为,此皆未得其要领,当以二者相互渗透来解此诗更妙。周珽说:“‘秦时明月’,横空盘礴语也,意秦时虽远征尚未设关,但在明月之地,犹有行役之不逾时之意,汉则戍守无有还期矣。”[8]22笔者以为,当以周珽所说极是,方能合第二句之意也。“秦月”“汉关”将秦汉数百年历史在一字一句间述尽,同时作者对于征人的同情也暗含其中。“人未还”是已经死了还是战事未结?其缘由不得而知,但其结果却是“未还”。顾璘《批点唐音》认为此诗:“惨淡可伤。音律虽柔,终是盛唐骨骼。”[8]22“但使”总起末两句,是“不教”的前提。“但使”是为祈使语,实际是“飞将”不在,“胡马”已度,尽显哀伤之意。通读全诗,诗人对于边情危急的担忧、对统治者用人不明的哀怨不言已表,同时又渗透出一种对国家的自信,显示出“飞将”已有的昂扬气势。陆时雍《唐诗镜》以为此诗:“怀古深情,隐隐自负,后二句其意显然可见。”[8]22“龙城飞将”指汉代名将李广,此处作者似有自喻之意,又“不教”句有自负己才之情。
又《九江口作》写道:
漭漭江势阔,雨开浔阳秋。驿门是高岸,望尽黄芦洲。
水与五溪合,心期万里游。明时无弃才,谪去随孤舟。
鸷鸟立寒木,丈夫佩吴钩。何当报君恩,却系单于头[8]161。
胡问涛《王昌龄集编年集注》以为此诗:“贬龙标途中,作于九江。”[8]161此时诗人身遭贬谪、郁郁不得志,心中暗含着朝廷用人不明的恨意,却又无法割舍报效君王的志向与决心。全诗以“漭漭”“雨开”铺开场景,力量十分强大,以后“高岸”“望尽”更是将远景尽收眼底,写九江口之景笔势壮阔。胡注以为“五溪”乃是沅江及其上游之流合称,代指贬地龙标;“万里”本是写贬地,乃万里之外的南蛮之地,却写得刚健向上,毫无怨恨之情。“明时”“谪去”是全诗悲慨的高潮,然而又接以“鸷鸟”“吴钩”入句,以示不与世人(其他被贬官员)一般,以酒、乐自娱,他仍然等着君恩再至,以报知遇之恩。此诗本是被贬发愤之作,然而却透露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息。
又“长风金鼓动,白露铁衣湿”[8]52-53(《从军行二首·其二》),又“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8]51(《从军行二首·其一》),又“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著报君恩”[8]170(《留别司马太守》),又“贤智苟有时,贫贱何所论”[8]181(《咏史》),皆悲慨与劲健浑融一体。
三、悲慨与劲健互渗的诗歌风格在创作中的体现
王昌龄是盛唐大家,其作品尤其是边塞诗皆被视为劲健诗风的代表作,但从前一部分对其不同题材诗歌的分析来看,其边塞诗未必尽是抒发豪情壮志,而往往有深沉的感伤;其他的迁谪、闺怨、赠别等题材的诗歌中也不是一味的悲伤叹息,反而含有一种力求振起、刚健清新之气。这种悲慨与劲健互渗的诗歌风格表现在创作手法上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表现手法,抑扬结合
“抑”者,贬也;“扬”者,褒也。抑扬结合的表现手法主要有先抑后扬、先扬后抑、抑扬并举三种形式,而这三种形式在王昌龄诗歌中都很常见。
首先看王昌龄诗歌《从军行七首·其四》中的诗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8]47此处运用了抑扬并举法,“百战”可见战事是何等的激烈,“穿金甲”则描写了战士是何等的英勇,“不破”“终不还”又需要多大的决心?然而在这决心之后,又暗含着多少无奈?士兵们固守边关既是处于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又往往是无奈之下的军令难违,这中间的种种委屈着实让人生出无限同情。又《出塞二首·其一》写道:“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8]20世人皆以飞将尚在、胡马未度解读此句,殊不知此处作者也是运用了抑扬并举的表现手法。乍一看这是一句男儿的豪迈誓言,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但使”二字却是在感伤“飞将”不在的现实,“不教”二字则是面对“胡马”已度的无奈。又《九江口作》:“何当报君恩,却系单于头。”[8]161此处乃是运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何当”可见“君恩”尚未至,但作者并未从此消沉,而是志在沙场,欲以“系单于头”报“君恩”。这种豪气,非有胆识之人不能为之。
王昌龄诗歌中多次用到抑扬结合的表现手法,除上述所举例证外,如《箜篌引》等,皆有抑扬结合于其间。这种表现手法能够较好地吐露作者的心声,是王昌龄悲慨与劲健互渗的诗歌风格的创作特色之一。
(二)场面描写,收放自如
王昌龄诗作中的场面描写也很有特色。在他笔下,场面描写可大可小,既有整体也有局部,可谓笔随心转,收放自如。
《从军行七首·其四》在空间维度上达到了长广互补。“长云暗雪山”[8]47可见场面极为壮阔,“遥望”则将“孤城”和“玉门关”距离无限拉长;“黄沙”一句则将焦点集中到将士身上,“不破”一句又进一步深入到将士的心理层面。从前两句描写极大的场面到后两句聚焦到个体,一大一小之间,其手段可谓变幻莫测,将边塞的苍凉壮阔与将士的复杂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九江口作》则达到了场面大小的灵活转变。“望尽”一句将诗人眼前之秋景无限放大,“五溪”则超出了视野的范围,指明了诗人的贬谪之地,尽显苍凉之感;后一部分则迅速聚焦于“立寒木”“佩吴钩”等动作上,透露了诗人始终求进的志向。血战沙场时“却系单于头”的战斗场面更是力压贬黜江湖时“谪去随孤舟”的凄凉场景,使得这首贬谪诗,竟透露出昂扬向上之意。
王昌龄是场面描写上的高手,把握甚是得体。除上举诸例外,如《失题·奸雄乃得志》等亦在场面描写上收放自如,并无半点刻意之笔,大小场景的穿插使得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也时而激烈时而纤细,从而造就了悲慨与劲健交融的风格。
(三)情感表达,含而不露
深受儒家诗教影响的王昌龄,推崇“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审美原则,诗歌创作表现出情感表达含而不露的的特点。这种含而不露的创作特点表现为多重情感的表达,而这一表达方式直接促成了他悲慨与劲健互渗的诗歌风格。
《从军行七首·其四》写道:“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8]47“终不还”三字写出了“不能还”的哀怨凄凉,表达上却不失温厚。又“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本意是谴责国家用人不当,导致边地丢失的败局,但用以假设的语气,批评的意思就显得委婉得多。又“何当报君恩,却系单于头”[8]161本写君恩不至,无青云之时,但是却将这种失望之情放在个人壮志的抒发之下来写,所以也并不显得灰暗消极。
世人论王昌龄者,非称其边塞诗刚健大气,则论其贬谪诗哀怨消沉。从上文分析可知,王诗的情感表达模式并非单一直线的,反而呈现出多样性与间接性,具有含而不露的特点,这也是王诗悲慨与劲健互渗的诗歌风格的主要创作特色。
(四)意境营造,多重架构
王昌龄是诗歌“意境”说的最早提出者,其关于“意境”的论述,今见于《文镜秘府论》与《吟窗杂录》中所载之《诗格》。两文虽不尽相同,但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即讲求巧思。空海《文镜秘府论》载:“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8]296追求用尽可能简练的笔墨构造多义性的诗境。王昌龄在诗歌创作中十分讲究意境的营造,尤其擅长一笔两用,以寥寥数句勾勒多重意境。
如《从军行七首·其四》,世人作豪言壮语观者有之,作悲壮看者亦有,陆时雍“测之无端,玩之无尽”即是此说。“青海”“雪山”“孤城”“玉门关”“黄沙”“楼兰”等描述的皆是西北边塞之景物,“暗”“孤”“遥望”等字词皆带有心理层次的意思,这种心与物的融合,使得全诗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对沙场百战的绝望,特别是最后一句连续用两个“不”字表现还家无望。一种则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尤其是最后两句,读后有一种酣畅淋漓的自豪之感。同为边塞名篇的《出塞二首·其一》意境构思亦极巧妙,“龙城飞将”“不教度阴山”皆是豪迈的大手笔,却又渗出对现实的悲伤与无奈。《九江口作》等作皆是如此。王昌龄关于“意境”的理论阐述体现于他的创作中的,除上述诸例外,《长信秋词》《塞下曲》等诗歌,意境都非常丰富,包含了多个层次的理解,这一点无疑也促成了王昌龄悲慨与劲健互渗的诗歌风格。
四、王昌龄诗歌风格的成因
独具的诗歌风格是诗人创作成熟的标志,王昌龄诗歌悲慨与劲健交糅独特风格的出现绝非偶然,这与其个人生平遭际、时代社会背景及诗歌理论主张都有着密切关联。
(一)英雄情结与生平遭际
翻阅新旧《唐书》及时人记载可知,王昌龄是一位豪侠之士,他热衷于功名,对自己的才能非常的自信,英雄情结在其作品中屡屡出现,也是他的作品显得雄劲浑厚的主要原因。如《城傍曲》中有“射杀空营两腾虎,回身却月佩弓弰”[8]16之句,唐汝询认为此句:“箭联双虎,向月而归,得意如此。”[8]17诗人赋予主人公的英雄形象,实是作者心中所向往的。又《少年行》:“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8]18那种慨然赴难、并无半点胆怯的英勇形象就是作者的自我期许。又《出塞二首·其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8]20作者以“龙城飞将”暗喻己才不用,爱国英雄的形象昭然若揭。又“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8]33(《变行路难》),又“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8]50(《从军行·其六》),又“安能召书生,愿得论要害”[8]133(《宿灞上寄侍御屿弟》),又“黄旗一点兵马收,乱杀胡人积如丘”[8]171(《箜篌引》),又“何当报君恩,却系单于头”[8]161(《九江口作》)皆暗含作者的自负。这种英雄情结是王昌龄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时,王昌龄仕途偃蹇,壮志又屡遭摧折。其早年居灞上,常有立功边塞之意。王昌龄曾北游河陇边地,写下大量抒情言志的边塞诗,《出塞二首》《从军行七首》等是此时期的代表作。但世事无常,王昌龄进士及第后,其仕宦生涯与理想愈行愈远。《新唐书·文艺下》载:“昌龄字少伯,江宁人。第进士,补秘书郎。又中宏词,迁汜水尉。不护细行,贬龙标尉。”[13]5780可见,除在京短暂任职外,王昌龄其余时间都是在外放与贬谪中度过的,直至“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13]5780。
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冲击,对王昌龄的诗歌风格影响重大。“暂因问俗到真境,便欲投诚依道源”[8]166等便是其贬谪之时的出世之句,但仍不失“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著报君恩”[8]170的豪情,这也使得王昌龄诗歌无论何时,都不失清刚爽朗的基调。
(二)王昌龄的诗论主张
王昌龄是盛唐诗歌创作大家,也是诗歌理论方面的巨擘。王昌龄的诗歌理论建设是在诗歌创作的基础提炼而来,反过来理论又促进了王诗风格的形成。《唐才子传·王昌龄》载:“有诗集五卷。又述作诗格律、境思、体例共十四篇,为《诗格》一卷,又《诗中密旨》一卷,及《古乐府解题》一卷,今并传。”[14]95今所见《诗格》主要有空海《文镜秘府论》本和蔡传《吟窗杂录》本两种,是为王昌龄诗歌理论精华之所在。
王昌龄的诗论涉及到意境、体例等各方面。关于做诗的意境,他说:“诗不得一向把,须纵横而作……落句须含思,常如未尽。”[8]313这里王昌龄强调了诗歌创作不可偏执于一端,须全方位的建构,另外抒情当含蓄,结尾应有不尽之意。如“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8]20一句,初读之下豪情满怀,但其中暗含对边塞无将悲惨现实的哀伤。又如“谁问含啼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8]98一句,本是写宫廷妃子备受冷遇的无奈,联想此时作者虽任职于长安,然地位卑微与失意的妃子十分相似,有暗喻己不得用之意,同时又表现出一种始终向上之气。关于作诗的体例,王昌龄列举了常用体十四种,以“藏锋体”为第一,其特点是“此不言愁而愁自见也”[8]326。这种写法在王诗中也很常见,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8]47一句,本是写将士沙场破敌的勇气与决心,但“不还”二字又将士卒不能还的忧愁透露出来。又“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著报君恩”[8]170一句,本是写作者欲青云直上、辅佐君王,可现实却是诗人未遭重用,谪居外地,迁客骚人的哀愁见于言外。
此外,王昌龄论诗有三宗旨,其中:“二曰有以。王仲宣《咏史诗》:‘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此一以讥曹公杀戮,一以许曹公。”[8]333这里王昌龄强调作诗须于句中注入其理,以多重立意架构,如“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8]33一句,一是赞将军一战封侯的壮举,一是讽将军对妻子的无情。又“追随探灵怪,岂不骄王侯”[8]137一句,一是言对不受朝廷重用的失落,一是言对世俗功名的不屑。纵观王昌龄诗歌理论,其中不偏执一端、藏情于句、多重立意的理论主张,是促成其悲慨与劲健互渗的诗歌风格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五、结 语
好诗如同七色光,不可能只是单一风格的体现,王昌龄的诗歌就表现出悲慨与劲健互渗的复杂风格。这种风格在诗歌中又有多样化的体现,如表现手法的抑扬结合、场面描写的收放自如、情感表达的含而不露以及意境营造的多重架构。王昌龄所在的时代是唐朝最为鼎盛的时期,诗人们最高的理想便是出将入相,但盛唐似乎并没有给王昌龄这个机会。英雄情结与个人遭际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了王昌龄诗歌的复杂化,而其诗歌理论主张又进一步促成了其悲慨与劲健互渗的诗歌风格的形成。在整个唐朝,与王昌龄生平遭际相似的诗人大有人在,他们在政治上失意后,往往通过诗歌来表达他们的失落,但又不甘放弃心中的理想,期盼君主能够一朝重用自己,因而造就了这种悲慨与劲健互渗的诗歌风格普遍存在于唐朝诗人的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