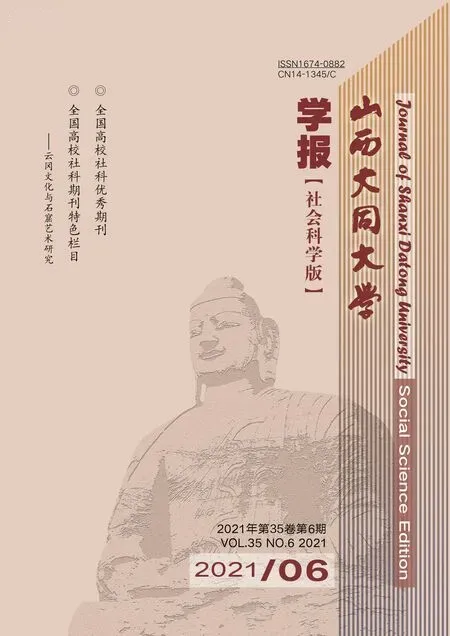新世纪王安忆小说中的现代乡愁书写
王雨晴,郭文元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了便捷和高效的现代化福音,但与此相伴随的也有转型期间的阵痛和失落,并必然承载着乡愁体验。曾经以血缘和地缘维系的乡土情结以及传统落叶归根观念被稀释,甚至受到重创。而以物质、利益和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理念已经昭示中国从传统乡土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知识分子的乡愁意识也从传统对田园生活回望式的怀旧,衍变为工业文明里在回望中批判和审视为主的现代乡愁。王安忆新世纪以来的现代乡愁书写以及对失意个人的描述统摄在现代化建设的框架里,通过空间的嬗变呈现出生态危机、身份认同困境、以及对想象中精神原乡的寻找等问题,展现了王安忆现代乡愁书写的多重意蕴。
一、现代乡愁书写的形成:现代化忧思
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依靠回忆重组的方式“重回”故乡,在充满浓郁地方色彩的表述中展开对故乡的回望和批判,表达了对故乡日趋衰败的慨叹。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所抒发的乡愁相对而言是传统型的怀旧,如博伊姆指出的修复型怀旧,“修复型的怀旧强调‘怀旧’中的‘旧’,提出重建失去的家园和弥补记忆中的空缺”。[1](P46)而新世纪后,现代化的巨轮碾碎了农耕文明的诗情画意,越来越多的离乡者涌入都市淘金。城镇化建设,不仅体现在空间意义上乡村和城镇的杂糅状态,游走在断裂时空下、忧郁混杂的个体也需要被言说。而王安忆的现代乡愁书写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展示生存其间主体的生命样态。这种现代化忧思里包含着生态破坏、技术和景观化的社会中丰富性的丧失,对生活、生命想象性的单一,以及人情的稀释。
传统型乡愁强调对过去的缅怀和家庭伦理上的承担,这种人伦情怀是农耕文明下家本位的典型体现,故乡和过去不仅是物理上亦是精神上的牵绊。现代化的齿轮可能碾压过这片心灵寄居之地,它是前进性和破坏性相统一的存在。上海是王安忆生活的城市,也是现代化建设激烈交锋的轴心点。王安忆在《寻找上海》《天香》中找寻上海的“根”,将上海的文化和地域景观坐实一种切肤之感的都市民间生存,但在追忆后王安忆也陷入了一种怅惘,“再回过头来,又发现上海也不在这城市里。街面上不再有那样丰富的有表情的脸相,它变得单一”。[2](P22)这是激变中带来的粗粝,同一和均质化的建筑削弱和阻挡了感官体验。王安忆的现代化忧思体现在这种表象化和符号化的景观社会造就了繁华的视觉盛宴也导致了精神想象的贫瘠,人们沉溺于也被限制在狭隘的物质世界之中,在此,文学乡愁是一种失落感和某种追忆思绪。这种追忆和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怀旧风潮不同,《长恨歌》里的旧上海风情回应当时在浦东发展下上海被想象为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使当时的上海迫切需要一个繁华的过往来垫底,也使这场追忆和咏叹成为带有强烈目的性的市场化策略。而到了《富萍》中,王安忆将视点移到了上海都市边缘棚户区的移民。当民众重拾辉煌上海的历史文化记忆以完成与都市现代化建设的合奏时,王安忆选择掀开这层华丽的外衣去审视这台现代化机器背后排出的污水、在市区和闸北往来的垃圾船和筑成这些辉煌背后涌入城市离散的移民群体以及其衍生出的朴素温情。诚如王晓明所言“只要王安忆执意远离‘物质主义’和‘强势文化’的笼罩,她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就势必会掠过洋场和西装革履,下落在截然不同的人事和风俗当中”。[3]这种选择的警觉展现的是王安忆面对这些粗粝变化下的时代情绪,并以温和的面貌进行批判和控诉的现代化忧思。所以她着重描述富萍的舅舅孙达亮一家住在垃圾船上的生活,舅舅拉着新鲜的蔬菜进入上海,而返回之后载满了粪。亦或是逼仄低矮的棚户区里各种营生,看似贫瘠的物质生活里也有着充沛的温情和元气。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这个江南小镇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打工者,伴随着国营织绸厂的兴盛、倒闭,这里的生态环境也日益衰败。河里淤塞着垃圾,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华舍镇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过渡环节。环境的污染挤压着人们曾经幻想中诗意的栖居,王安忆思考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陷入了道德伦理的困境。在《众声喧哗》里欧伯伯开了一家纽扣店,每次进货之后都要一粒一粒数清楚放进盒子里,在智能手机和电脑普及的现代化社会中执着地在店里放一部公用电话并每日擦拭,这背后也是自觉的反抗姿态。在效率至上的社会中让生活节奏慢下来,甚至有意用趋于平淡的方式来抵消人内心的焦虑和紧迫感,以寄托其自身的现代化忧思。工业化社会逐渐吞噬传统的风土人情而置换成摩登的现代化建筑。在城镇化建设线性的发展中,工商业社会的发展逻辑倒逼现代乡愁反思这种变化下的粗粝,人伦情怀的某种解体,以及被忽视的离散群体和被稀释的情感纽带。
到了《遍地枭雄》《匿名》中,这种乡愁意识指向了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家园,在想象、虚构和隐喻中拓展了乡愁的表达。“在此,乡愁不仅表现为对‘对象客体’原封不动的复制和再现,其中的乡愁涌现,还取决于观照者或阐释者对对象主体所选择的观察视角和表达方式。”[4]《遍地枭雄》里成长在城乡结合部的韩燕来,成为工厂里流水线上的雇佣工人,遭遇一次次的解雇后选择开出租直到被三王劫持遁入江湖。韩燕来的成长环境隐藏着工业社会发展下的危机,书中开篇描述被水泥建筑日渐包裹而缩小的空地,从杂芜生长的毛豆地到满目疮痍的垃圾,如同林窟曾经也是现代化版图的一块到逐渐被抛弃。这些环境揭示了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也隐喻着生存其间的人可能存在着畸形的成长,和潜隐下被压抑个体的精神危机。王安忆的这些现代化忧思,对家园亦或是心灵精神原乡的思考根植于现代性的两难境地,也是做出介入社会症结的努力。
二、生存空间嬗变下的现代乡愁意识呈现
乡愁与故乡紧密相连,这个空间指涉的是现代乡愁投射的客体,它的具象化或泛指是作家展现乡愁的重要维度。城镇化建设使地方特性受到侵蚀,个体记忆也从整体变得碎片化。故乡的衰颓、多元驳杂的现代景观预示着集体时代的逝去,被切割的个体成为这些转变的主要承载者,背后影射的更是生活在这种现代化激变中人们生存空间的嬗变。文学中的故乡不只局限于来自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这份情感投射也可以在虚拟的仿真语境中获得存在的合理性。“对乡愁的表现与阐释,离不开时代与空间置换的影响。”[5]对于王安忆而言,这份乡愁意识的呈现以文本中人物生存空间的嬗变为表征,由具体的空间形式过渡到对人类本身、本体心灵空间的溯源和皈依,而后者是一种“越轨”的尝试。
王安忆在《寻找上海》《海上繁花梦》中有意追溯上海的发展脉络并为其立传。而当急速的现代化和市场化发展浪潮席卷这座城市,本就缺乏文化根基的都市在巨大的移民流动下也逐渐失去往日的世俗风情,也使得沿此空间地方路径的思考受到阻碍。“王安忆的‘乡愁’因其充溢着反抗现代性的自觉意识,使得她的“乡愁”更像是一种思考的状态。”[4]这种思考,从曾将都市乡愁的表达以具体的上海都市背景为主要参照客体开始转变,人物从弄堂走出来落脚到棚户区、华舍镇、肆意飞扬的江湖和原始神秘的林窟,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思辨过程。
《遍地枭雄》中的江湖和《匿名》中的林窟、藤了根是与都市空间截然相反的存在,它们的虚拟和非限制性能容纳更大的自由。“韩燕来的人性出走意不在善恶意义上的出走,而是在自由生活方式与自由选择意义上的出走。”[6]这种由被迫坠入异度空间的窘境到自愿融入并寻求认同的人物心灵图式在老新身上也有着明显的展现,林窟处在文明的缝隙里,带给老新完全迥乎于都市文明生活的体验。曾经所接受的文明社会里的规训和身上的枷锁被全部抛弃,并在这种失效中重新打开世界,自由中包含着极大的可塑性。王安忆制造出的这两次思想实验也在展示线性进化论的某种“倒退”,无论是布满草莽气息、规则秩序失效的江湖语境,还是让老新重回原始自然状态再次启动认知的林窟,由生存空间翻转进入的思想实验虽具有虚拟性,但这种契机蕴含着自主选择,重新将都市文明中的个体陌生化,在震惊体验中重新审视和寻找自我。老新和韩燕来都是现代化社会的一份子,在后工业社会里承受着都市的异化和心灵的孤独,而江湖和林窟就是为这份被压抑的自由而开放的空间。韩燕来在江湖的自由中得到释放,而老新在全新环境里经历失忆后,“名”与“实”的对应产生错位,随后重新创造联系,实现对事物的崭新认知。这两种都是冒险的自由,漂泊的灵魂在自主选择的精神空间里得到酣畅的释放。“当然,对这种荒野生活的激赏,反观之,就潜藏着对现代性生活的反思。”[7]而这种精神空间的探索是一种现代性的乡愁展现,某种心灵归属的原乡体验,寻求完满的自我和自洽。乡愁主体不再指涉某一类离乡漂泊的游子,更是后工业社会人的普遍心理状态和情感体验。在这种找寻意义感的情感体验中,强烈的主体性在反抗曾经现实世界下命运对个体的控制,其间蕴含着哲理性的思辨和自由英雄式的探险。身处这些崭新空间下的人们,有迁徙到城市的务工者,也有坠入陌生语境下的边缘者,他们从原来熟悉具体的空间中脱域出来,带来了精神上的断裂,而由此产生的虚拟想象基于这个崭新的时空,它充满不确定性,也孕育着新的可能。
全球化的多元和流动成为常态,中国社会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过程不仅缺乏缓慢的预热,同时缺乏稳固的现代理性根基。吉登斯所言的“脱域机制”也成为常态。《一把刀,千个字》里,空间转换到纽约的法拉盛,淮扬菜名师陈诚在纽约看似生活地风生水起,但那些被遮蔽的前尘往事,想要逃避的记忆和内心的愧疚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对于陈诚而言,这不仅来源于母亲的缺位,以及家庭内部沿袭下的创伤体验,更有难以割舍的过去。所以在小说最后陈诚回到上海,走到小时候爷叔带他洗澡的钢厂潸然泪下。“他不敢乱动,也不敢擦拭眼泪,那里面的液体不晓得蓄了多少时日,又是怎样的成分,滚烫的,烧得心痛。”[8](P203)这种乡愁是一种文化归属,是异乡人面对不同文化价值选择后的矛盾和游移,进而追寻安身立命的根本和那些被稀释的记忆。
人物生存空间嬗变指涉着社会的转型,其背后可能隐喻着家园的失守和集体记忆的消散。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离乡远游很多都是偶发性的事件,空间的变化和物理阻隔也是暂时状态。而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这种断裂和失去成为一种不可逆的力量。王安忆的现代乡愁意识在空间嬗变下的表现,展示了对现代化建设下对生态以及人情的破坏,无论是制造出思想实验来寻找抛去外在社会身份修饰下对精神原乡的探索,亦或是在国外远离故乡的阐释,都是在现代性视域下的诉说,而呈现出一种反思的姿态。
三、基于现代乡愁书写上的精神建构
新世纪后的文学乡愁由回望和怀旧的乌托邦回溯,到脱离物理实体牵绊后的精神建构,双重维度使得侧重个人经验表述的乡愁意识开始有一种更为开放式的表现。而从后者衍生的现代乡愁意识更注重反思、批判和哲理思考。“精神生活中的还乡情节并不是期盼回到遥远时空存在中的那个故乡,而是要以此为线索来重塑现代生活中的存在意义。”[9](P159)对王安忆而言,这种乡愁书写在精神上的建构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当下社会中个人生存困境的思考以及与自我认同的呼应。
(一)生存困境思辨与救赎可能 随着消费主义社会的蓬勃兴起,城市成为发展的容器,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屡见不鲜。物欲膨胀、逼仄昂贵的都市空间挤压着被裹挟在现代机器中的人,精神和价值危机成为人新的困境。王安忆在展示当代人的精神危机时,融合了当下发展语境下对精神原乡的希冀。《遍地枭雄》中经历工厂辞退的韩燕来最后开上出租车,王安忆形容其像铁皮甲壳虫一样穿梭在城市,是对卡夫卡《变形记》的致敬。在夜晚中一次次被经历中难以言说的羞耻之事剥夺着他的自尊和纯洁。“似乎,他已经失了贞操,不那么在乎了。这城市的夜晚,就是如此地,一点一点剥夺着人的廉耻。”[10](P51)韩燕来的精神荒原和生存困境在与三王的江湖冒险中得到巨大缓解。规则和秩序之外的逃离让韩燕来充满了无拘束自由的快感,从最初惊恐抗拒到崇拜三王并完全融入其中。这种从现实中的突围是脱离混沌不明的现实状态和嘈杂的世界,虽然这看似无限的自由下隐藏着巨大的破坏性,但破坏未尝不是另一种创造或救赎。而到了《匿名》中,王安忆又通过一起意外的绑架案让主人公老新坠入原始林窟,进而表达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泛化的现代乡愁意识。老新失去和文明社会有关的记忆,在林窟中通过双手在具象的图案和抽象的符号中重新建立起与事物的联系,重新对应“名”和“实”。这是我们祖先在文明之初必经的过程,老新仿佛演示一遍,在退化中伴随着新的进化。王安忆对古老文明和现代社会的乡愁,展现在聚焦被现代社会所忽视的空间和边缘之人,而这个匿名的空间是王安忆要追寻的人类文明之根和乡愁之根。韩燕来和老新开启新世界的过程抵抗着一种现代文明里空虚疲倦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对其本人而言这种救赎重要的是无限的探讨和追寻,一种永远的进行时。
王安忆的现代乡愁意识是一种反思和批判的姿态,对完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评判规则的社会的怀疑,这中间可能有遗漏的人文精神,而后者具有不能与发展并驾齐驱的滞后性。王安忆制造的江湖和林窟满足了韩燕来和老新的都市出逃,去寻找救赎的可能。但这种近似虚拟的想象和异度空间的创作能否承载这份积重难返的乡愁?三王和韩燕来在秩序之外的江湖感受到自由,但触犯了法律的底线,最后遭到逮捕。韩燕来被抓捕回上海,看到自己的村庄被高架劈成两半,也对前方充满未知。老新在最后即将要返回上海的家的前夕却因为溺水而亡,回家成为一个永远延宕和不可能的事情。又或者对韩燕来或老新而言,他们已寻找到精神原乡和归属地,但逮捕和落水又是否意味着精神救赎的失败。如何破解这种精神困境,作者给出一个想象空间但没有确定答案。王安忆将现实生活和精神原乡进行了想象性的弥合,这是现代社会中的乡愁,但这种以“超脱”方式的想象又是否会制造出与现实之间的断裂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二)乡愁意识与自我身份认同的呼应 文学乡愁塑造的乡土或虚构的精神原乡不仅成为现代社会的避难所,更是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维度。“乡愁不再局限于怀念故乡和亲人,它的现代性和身份确认想象更能够引起人们对于生活甚至生命的思考,从而扩充它的文化意义。”[11]斯图亚特·霍尔抛去以往对文化身份研究本质论的探讨,将其看做一个不断进行、建构的过程。这种身份认同和建构在乡愁维度上是一种确认和回归。从追问父系母系家族溯源到《匿名》中老新重塑有关自我的想象,王安忆在现代乡愁中对身份的思考不只是在确认人物回归某种文化或融入想象的共同体中,更有对主体性身份的寻找。《一把刀,千个字》里的海外移民群体以故乡淮扬菜为众人的联接点,家乡的味道承载着共同的记忆和心理体验以实现相互的身份认同。饮食背后是乡愁、漂泊的灵魂和人事变动的惆怅。这种心理安全感以共同的乡愁而产生共情,不只是指涉某一具体地点,更是一种与人的精神和生活状态关联的存在和心理皈依的过程。当人们在现代社会里对身份产生焦虑,在脱域后的新时空里寻找身份归属和想象中的同类社群以换取心灵的慰藉,这份现代乡愁通过寻找和创造新的联接为表征,看似为了唤起和回溯个体曾经的身份,实则更是一份不断进行寻找和建构的过程。
《遍地枭雄》中韩燕来与三王在江湖的冒险中让自我的天性复活,而贯穿其间的更有他对三王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韩燕来从小受到母亲和姐姐过多的庇护而呈现出女性化的特征,父亲的缺位导致他对男性气质的渴望在近乎虚拟的江湖中得到一种合理化的存在。三王的眼界、思考以及做事的魄力给韩燕来带来男性启蒙,这种身份认同加深了团体凝聚力,也让韩燕来的男性气质得到释放和重塑。韩燕来的男性身份在其间得到接受、成长和建构。大王的话语魅惑是助推剂,但行动上的酣畅表达是形塑身份的最直冲击。而《匿名》里老新重新学习语言文字,通过自我主动而能动地载入现代文明的过程就是重新建构自我的过程,主体性的重新认识也随之开始,“我是谁”的哲学命题在空间林窟这个精神之乡中得到重提,将对自我、对世界的原初认知和解释权还给自身,无论是发现和习得新知识还是建立新的联系进行自我身份的认同,这个过程都在一步步靠近对于自我认识和思考的无限可能性。“在这里,王安忆把寻找自我的可能放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加以考量。”[12]无论是韩燕来或是老新,寻找和重建自我,并在身份认同中确证自我的主体性,是对人本身生存困境的思考,也是现代乡愁意识对传统的承接与改造。这份身份寻找预设了一个“丧失”的过程,而从“丧失”到“获得”的即是建构,这种建构不是机械地重复,而是处在不断地认知之中,不断破解新的身份,找寻意义。因为现代乡愁中寻找的身份认同本就存在着未知性和不确定性,避免陷入所谓“终极”答案的陷阱。人物的这种寻找和建构之旅也是王安忆现代乡愁书写的展现,不断产生疑问和惶惑,而生发出新的悟性、理解和冲动,生命的活力和意义即在于此,现代乡愁的过程也没有终结。
现代乡愁意识在当下瞬时和流动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姿态,在回望中更多反思、批判和思考的色彩。卡琳内库斯提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分野,在于强调现代性一维向前发展的启蒙理性与价值迷失、精神世界坍塌溃败的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而后者是现代乡愁着重思考的维度。它包含对传统文化的考量、故乡衰败的境况和个人身份焦虑、精神危机的思索。王安忆从城市书写中将上海视为主体建构的情感投射和参照,到跳出地方路径聚焦现代化语境下的乡愁和生存其间的个体存在状态,包括对现代人“归宿”的思考,是一种视域的扩大,也是自我诗意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