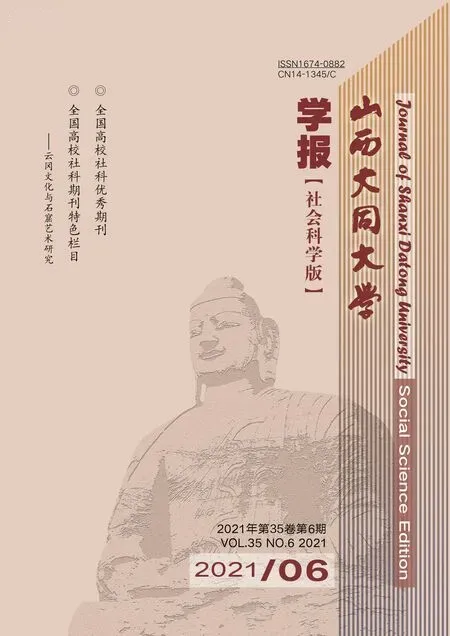“正统之辨”视域下的《魏书》“民族传”叙事与历史文化认同
王宵宵,胡祥琴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2)
西晋短暂统一之后,中国再次分裂,经东晋、十六国后,刘裕、拓跋焘分别建立了政权,形成了南北政权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此时期,南北朝为了维护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采取各种方式争夺“正统”地位。由于北魏是鲜卑族建立,因此使得这一时期的正统之争具有“夷夏之辨”的色彩,也使得“正统之辨”更加复杂化。南朝抓住北魏在民族身份上的劣势,强调夷夏之别。《晋书·石勒载记》载:“自古以来诚无戎人为帝王者”,[1](P2715)南朝始终将北魏视为夷狄,就是为了剥夺其成为“正统”帝王的资格。南北双方利用各种手段争正统,史书就是其中之一。沈约《宋书》直言北魏为“索虏”,充满歧视、贬低的意味,行文之间不断强调北魏政权的残暴无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魏书》创立。魏收将与北魏有关的其它民族政权编入“民族传”,共九卷。民族传记载的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关于十六国政权的记载;第二,关于东晋、南朝的撰述;第三,对边疆其他民族的记述。这样的叙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北魏争正统,从而证明北齐的正统性。
一、“正统之辨”视域下的“民族传”叙事
《魏书》各部分都具有“正统之辨”的色彩,“民族传”也不例外。不论是“民族传”的标目、史论还是具体内容都成为魏收为北朝争正统的工具。《魏书》“民族传”中争正统的方式可谓全面多样。
(一)正统意图明显的各民族列传标目 白寿彝先生认为标目“是在一部书里,按照不同的具体内容分别标出题目来……司马迁的书在他生前虽还没有《史记》的名称,但书中个篇已各有标目了”。[2](P102)史书标目是对内容的反映,如《史记》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等,这些都反映了记述内容的主体,没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魏书》民族列传则不同,有些标目直接反映了对于民族政权的态度。十六国政权的标目大部分不存在表达情感的词汇,只是加上民族名称,如《匈奴刘聪传》《羯胡石勒传》《羌姚苌传》等,也有其它标目,如《賨李雄传》《私署张寔传》,但是情感表达并不激烈。边疆民族的标目与《史记》标目一致,只写民族名称,如《高句丽传》《百济传》《宕昌传》等。
与这两种情况不同,《魏书》中东晋、南朝政权的标目蕴含的感情色彩浓烈许多。魏收直接称东晋的建立者司马叡为“僭晋”,对南朝宋、齐、梁则冠以“岛夷”的称号。这样的标目直接否定了东晋、南朝政权的正统性。“僭”就是超越了本分,使用了本不该使用的名称、仪制,魏收以“僭晋”称东晋,无疑是对东晋正统性的否定。北魏两次议定在五行中的次序,最终确定北魏为“水德”,实际上就是为了说明自身是西晋正统的承接者。正统的继承者只能是一个,既然北魏承继了正统,那么东晋自然就不能是正统了。南朝的政权承接东晋,否定了东晋的正统性,那么南朝政权也不具备正统性。魏收甚至还采用了“岛夷”这一具有贬低性质的词汇。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指出:“岛夷者,以东南际海,土地卑下,谓之岛中也。”[3](P2186)魏收特意突出南朝所处地区的恶劣。标目为“岛夷”极易使人们在没有阅读具体内容之前,就将南朝政权视为偏远地区。偏远地区地区的政权自然不会是正统所在。
(二)正统色彩浓厚的各民族列传内容 民族列传的标目已经体现了魏收对于不同民族政权的态度,在书写各个民族的具体内容时,“争正统”的思想也贯穿其中。现从祖源、地理位置、异象、“春秋笔法”的使用等4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祖源认同与正统传承。对于先祖的追溯意在说明血缘的关系,而血缘往往与正统相联系,有学者认为“政治正统的根本是王位正统,王位正统的保证在于王室血缘的纯正。”[4]因此,北魏追溯自己祖先为黄帝,自己是皇帝的后裔。《魏书·序纪》写道:“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5](P1)由此可见,拓跋氏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与中原民族有着相同的祖先和血缘。这样的描述为“拓跋氏入主中原、占据正统提供了理论依据”。[6]为了突出北魏血缘的纯正性,势必要说明其它民族政权血缘的混杂,甚至要贬低。
魏收记载司马叡是“晋将牛金子也”,[5](P2091)是其母和西晋大将牛金通奸而生,指其“冒姓司马”。这样的说法显然是荒诞无稽的,但是魏收依然采取了这样的叙事。因为这样能直接说明司马叡血统不纯,不配继承西晋的正统地位。对刘裕直接称:“其先不知所出”,[5](P2129)萧道成则是“僭晋时,以武进之东城为兰陵郡县。遂为兰陵人。”[5](P2161)萧衍“亦晋陵武晋楚也。父顺之,萧赜光禄大夫”对于南朝统治者先祖的记载较为笼统,要么不知所出,要么只追溯至父辈。这与《序纪》中对北魏先祖的追溯大相径庭。魏收一边在《序纪》中大力叙述拓跋氏是黄帝后裔,一边贬低、模糊南朝的先祖。两相比较,从而突出北魏血缘的纯正性,进而证明北魏政权的正统性。刘知幾对魏收这种叙事表示强烈的不满,直言“魏收党附北朝,尤苦(污蔑)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可谓助纣为虐,幸人之灾”。[7](P107)刘知幾直接指明魏收贬低南朝政权,是因为其“党附北朝”,要为北朝政权服务,凸显北朝血统的纯正,从而证明北朝的正统地位。
第二,地理优势与正统自信。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它最早发轫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正统理念。”[4]只有占据中原地区的民族才是正统所在,居外的民族是夷狄。这种观念在《魏书》中反映的十分明显。一方面强调北魏“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5](P464)另一方面凸显南朝政权的偏僻、险远,自古就是化外之地。如其载东晋所在之地“春秋时为吴越之地……偏僻一隅,不闻华土”,[5](P2092)战国时“地远恃险,世乱则先叛,世治则后服”。[5](P2093)其地不仅地理位置偏僻,而且此地居民道德品行较差。司马叡因乱世而据有此地。对于南朝宋、齐、梁,虽然没有在内容中特意叙述其地理位置,但是从标目之中已可窥见。“岛夷”也就是说居住在海岛之上的民族,离中原地区就更远了。魏收对其它民族政权地理位置的描述较为客观,一般都表述为去代多少多少里,如“悉居半国……去代一万二千九百七十里。”“渠莎国……去代一万二千九百八十里。”[5](P2264)魏收刻意花费篇幅去叙述东晋的地理环境、位置、风俗等内容,直指南朝为“岛夷”,这样的叙事在地域上将东晋、南朝排除在了华夏之外,变成了夷狄,其建立的政权也就是“闰位”了。
第三,异象宣传与正统争取。魏晋南北朝时期,谶纬十分流行,吕宗力经过系统考察,指出谶纬的历史功用,他认为:“按照谶纬的历史论述,上天依五德相生之顺序,在人间选择天子,轮流坐庄。这些受命于天的代理人,有任期的限制。”[8](P143-153)当代理人转变时,上天会有预兆,《魏书·灵征志》《宋书·符瑞志》《南齐书·祥瑞志》都是专门记载此类现象的篇章。《魏书》“民族传”也记载了部分有关内容。司马叡没有建立东晋之前,想要杀死淳于伯,结果“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径头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5](P2029)行刑者用刀擦柱子,血竟然逆流而上,一直到两丈多才向下流,血流像琴弦一样直。这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上天对于司马叡的警告。司马叡德行有失,才会招致上天的警示。这样的例子在有关十六国政权的记载中比比皆是,如载刘聪时“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达于平阳。肉旁常有哭声,昼夜不止。聪恶之。刘后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须之见在陨肉之旁。”[5](P2046)姚兴时有数万只鸟雀在庙堂的上方打斗,有许多鸟雀死亡,当时有谶言“今雀斗庙上,子孙当有争乱者乎?”又“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得。”[5](P2084)
不论是司马叡还是刘聪等人都有“感生”传说存在,“感生”是祥瑞,是受命于天的征兆。然而,魏收笔下关于他们却只有不详之事,借此说明他们不是受命于天。既然东晋司马叡没有受命于天,那么其后的所有政权也不是天命所在。为什么魏收花了许多笔墨记载十六国政权的灾祸现象呢?北魏想要上承西晋,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就必须要越过、否认在其之前建立的政权,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宣扬自己是西晋的合法继承者。
第四,“春秋笔法”使用中的正统争夺。“春秋笔法”是中国古代书写历史的一种重要形式,通常认为是孔子设立的褒贬标准。其既要求直笔,保证记述史实的真实性,达到“使人之善恶无所隐”的目的,又允许史官用谨慎的文字表达自己的好恶褒贬。文字的使用通常极简,但能表达强烈的情感,所谓“一字之褒,宠踰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9](P7)《魏书》的“民族传”中也有相关内容的体现。有关君主的行动都有特定的字词,如古代帝王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薨”。魏收在记述北魏君主死亡是用“崩”,如“太祖崩”“帝崩于西宫”“肃宗崩”“庄帝崩”等。其它民族政权的君主的死亡多直接用“死”,如司马叡之死为“发病而死”,刘裕直接为“七年(明元帝泰常七年,即422年)五月裕死”,萧道成则是“道成死,子僭立”等。魏收并没有把东晋、南朝君主当作帝王,在魏收眼里他们与其它民族的首领地位别无二致,甚至更为敌视,这样才能凸显北魏帝王的地位。“讨”“伐”“寇”等都是表达战争的词语,但是感情色彩并不相同,“讨”“伐”一般都具有正义性,被讨伐的一方往往是乱臣贼子。刘义符即位之后,北魏太宗遣山阳公奚斤等渡河“南讨”。北魏太祖还曾“南伐”萧衍。总而言之,魏收想要塑造北魏对外战争的合法性,因此多为北朝发动战争寻求合理借口,达到师出有名的目的。如北魏太宗讨伐刘义符,就以其礼敬不足为借口。
除上述内容之外,《魏书》“民族传”将北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定义为朝贡关系,自理行间常见“朝贡”“遣使”“献”等字样,将北魏至于上国的地位。其与其它民族的关系应为众星拱月,其它民族要以它为中心。此外魏收叙事使用西晋、北魏纪年。采取西晋纪年,是因为北魏承认西晋的正统地位。北魏自诩承西晋,承认西晋的正统地位,实际上就是对北魏的正统性的拥护。
(三)正统倾向鲜明的史家传序及论 史论是史家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现象的评论,直接反映了史家的史学思想,周一良先生指出:“纪传体史书仍自有最能体现作者特色的地方,就是序或论部分。”[10](P275)“论”一般以“史臣曰”的形式体现。《魏书·匈奴刘聪传》之前有一千余字的序,每卷之后有“史臣曰”,这些内容都体现了魏收对于其它民族政权的评价。不论是对东晋、十六国政权、南朝政权的评价,还是对其它民族政权的评价,魏收的最终目的都是说明这些民族政权的僭伪性、附属性,只有北魏才是“承天命”的正统所在。
《魏书》“”民族传”的“序”大致可以划分为五层:第一层指出:“夫帝皇者,配德两仪,家有四海,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者也。”[5](P2041)这就直接说明了帝皇仅有一个,而且是德行十分高尚的。第二层主要叙述了汉末以来混乱的政治局面,这些政权“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鼎”。[5](P2042)彼此之间互相攻打吞并,“狼戾未驯”急需一个“成天命”政权来结束这样的局面。第三层重在叙述北魏统治者的才能、功绩和品质。如:“太祖奋风霜于参合,鼓雷电于中山,黄河以北,靡然归顺矣”,世祖“慨然有混一之志。”[5](P2042)第四层说明北魏衰颓的原因及北齐代魏的合理性,特别要指出的是,魏收认为尽管北魏后期出现了一系列动乱、灾祸,魏德有衰,但是“天命未改”,在这种关键时刻,北齐神武帝高欢“屈身宰世,大济横流”,[5](P2043)挽救了危局。第五层说明了撰写“民族传”的原因。魏收称:“自二百许年,僭盗多矣,天道人事,卒有归焉,犹众星环于斗极,百川之赴溟海。今总其僭伪,列于国籍,俾后之好事,知僭盗之终始焉。”[5](P2043)第五层是层层相扣的,首先道明帝皇的唯一性及德行的高尚性,接下来描述乱局中各分裂政权的统治者德行有失,他们的历数、政权合法性都是由自己说出的,并不是真正的“上承天命”。既然他们不是真正的天命所在,那么天命在何处?拓跋魏的统治者德配两仪,令周围政权臣服,自然是真正的天命所在。在魏德有失的关键时刻,高欢力挽狂澜,延续了拓跋魏的天命,将天命过渡到了北齐的头上,达到了力证北齐正统性的目的。最后,再次说明汉末以来有多个僭伪政权,它们犹如众星环绕于斗极,百川终将汇于大海。斗极和大海自然指的是拓跋魏及北齐。写僭伪政权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后世知晓这些政权的始终。
《魏书》“民族传”共九卷(95-103卷),每卷之后都有魏书对于整卷民族政权的评论。魏收对十六国政权、东晋、南朝齐梁政权的评论中心内容基本相同,都意在指出这些民族政权的僭伪性及其危害性。95卷主要记载的是十六国政权,魏收评论刘渊等人“污辱神器,毒螫黎元”“怨积祸盈”,之后发问“天意其俟大人乎?”[5](P2087)“大人”是谁不言而喻。96卷主要记载东晋和成汉,评价主要针对东晋。魏收称:“司马叡之窜江表,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局天蹐地,畏首畏尾,对之李雄,各一方小盗,其孙皓之不若矣。”[5](P2113)在魏收眼里,司马叡并不是君主,地位和成汉李雄一样,甚至比不上孙皓。这无疑是在贬低东晋的地位。97卷记载的主体是桓玄、北燕、南朝宋。魏收评价桓玄、冯跋、刘裕穷凶极恶,是夷人、荆蛮的本性。98卷的民族政权是南朝齐、梁。魏收将齐、梁的争斗比作“蜗牛之战”,萧氏二位是贼寇,在江南窃用帝王的名号,这种情况闻所未闻,比勾践,夫差更为恶劣。99卷记载的是前凉、西秦、南凉等,他们都处在不毛之地,乖张不逊,不自量力,但是彼此之间仍相互争斗,就像“蛇虺相噬”。他们的结局只有被擒获、歼灭。
《魏书》100卷至103卷主要是关于边疆少数民族的记载。魏收的评价相对来讲较为温和,但依然带着歧视贬低的意味,如他称赞高句丽每年朝贡的举措,但是认为其他诸夷碌碌无为,都归附朝贡,难道是“牛马内向,东风入律者也?”[5](P2251)除此之外,魏收还会借评价民族政权之名,行夸耀北魏政权的之实。比如其对西域诸政权的评价,“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羇縻勿绝之道耳”[5](P2281)关于西域的评价史记只有“通魏氏”这一句,其余都在夸赞北魏,称其刚刚平定中原,有一统之心,没有闲暇征伐。深谙羁縻之道,所以西域诸政权才会往来不绝。又如魏收认为北方的民族、高车屡次骚扰大魏,大魏出兵剿灭。虽然北魏发起了战争,但“盖亦急病除恶,事不得已而然也。”[5](P2341)北魏绝不是好战暴虐之徒。
二、正统视阈下《魏书》“民族传”叙事与历史文化认同
《魏书》“民族传”叙事“争正统”的方式多样,这些方式都基于对过往历史文化的认同。汪高鑫先生认为:“历史文化认同是一个广义概念,主要包括对于治统、道统、制度、血缘等的认同。”[11](P219)《魏书》“民族传”叙事主要是对血缘、地域、民族、治统以及道统的认同。
第一,血缘认同。在南北朝“民族传”中,沈约、萧子显、魏收不约而同地对南、北朝的血缘做了描述。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对立政权血缘的不正,但是始终没有把对方排斥一统的范围之外。沈约追溯拓跋氏的先祖是李陵,而不是魏收上溯的黄帝之子昌意。沈约、萧子显自认为南朝政权是礼仪文化之帮,自然懂得血缘在正统传承之中的重要性。魏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魏收载司马叡是牛金之子,不是“宣帝(司马懿)曾孙”。[1](P143)与沈约、魏收相比,萧子显的记载较为客观,其记述:“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12](P983)此种说法看似把拓跋氏排除在了汉族之外,但是“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13](P2879)夏后氏的先祖也是黄帝,而且夏后氏的曾大父是昌意。如此看来,南、北朝都是黄帝的后裔。早在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就已经构建了一个华夷共祖的认同体系,《史记》关于五帝与民族祖源的记载,可以说是“源出于一、纵横叠加”,这个源就是黄帝。这个体系不但被华夏族认同,也逐渐为夷狄族认同。[14]十六国政权皆将自己的先祖追溯至黄帝即是力证。因此,魏收利用血缘为北朝“争正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地域认同。《春秋》载“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但有着尊王攘夷的色彩,而且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在先秦时期,将占据中原的政权视为正统的观念就已经存在。[15]这一中原正统观影响了十六国政权。石勒占据洛阳和长安,建立后赵,仍觉得自己不是正统,他的臣僚建言:“魏(曹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陛下旣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1](P2753)十六国时期已经接受了这一正统观念。北朝时期更是如此,因此,魏收才会在“民族传”中不惜笔墨地记载南朝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斥其为僭伪、岛夷。与此同时,魏收还在《魏书》中强调中原正统观。《魏书·礼志四》载:“帝王之作,百代可知,运代相承,书传可验……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5](P2744)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嘎仙洞石壁上的祝文也有相似的记载:“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16]孝文帝重议五德次序时,群臣对两种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时都提到了中原正统论。高闾主张承前秦为土德,依据的是“石承晋为水德,以燕承石为木德,以秦承燕为火德,大魏次秦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征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征。”[5](P2747)李彪认为北魏应该承西晋为正统,因为“魏、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5](P2747)虽然李彪反对高闾的主张,但是并没有否定中原正统观。这无疑是对中原正统观的坚持和发挥。南朝自然也懂得中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其确实偏居一隅。这样的事实是南朝不愿意面对却又不得不接受的,因此,他们要采取措施弥补这样的缺憾。汪高鑫认为东晋、南朝实行的乔治州郡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之上是对中原正统观的坚持,通过这样的方式表明南朝依然是“中原”正统所在。[6]
第三,民族认同。南北朝时期正统之争的最大特点就是夷夏之辨。南、北朝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将对立政权视为僭伪、夷。沈约、萧子显将北魏称为“索虏”“魏虏”,突出北魏政权的民族身份,十分强调拓跋族与匈奴的关系。北朝却极力避免其与匈奴之间的联系,尽管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北魏经过长期的汉化,再加上其占领了嵩洛之地,北朝不再认为自身是边疆的民族,而是具有礼仪文化的华夏族。因此,北朝有底气指责南朝政权为“岛夷”。这与十六国政权相比有了极大的转变。尽管十六国政权一直在为政权的合法性努力,但是始终缺乏自信。有学者认为北朝修史的过程是修掉拓跋族夷狄身份,建立华夏身份的过程。[17]南朝政权深知自己在夷夏身份上所占据的优势,因此在“民族传”中也不断凸显这一优势。《南齐书》载北魏孝文帝曾言“江南多好臣”[12](P992)萧子显借孝文帝之口夸赞南朝是人才聚集之地。南朝政权深知夷夏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差异,而不仅仅是血缘。所以才会在“民族传”中记载北朝失礼之处,与魏收笔下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此。南朝这样的处理方式刻意忽视了夷夏之间的转变,这在《宋书·索虏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相比《宋书》,《南齐书》记载了北魏汉化的部分内容,承认了北朝向华夏族转变的过程。
第四,治统认同。《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称:“所谓治统认同,即对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连续性的认同,反映的是一种政权连续性的认同,反映的是一种政治的继承性。”[11](P219)魏收都在“民族传”中利用了天人相应说、五德终始说,这实际上就是为了说明其所属政权与前代政权的密切关系。北魏经孝文帝重新议定历运之后,就极力说明自身与西晋的联系,撇清其与十六国政权的关系。因此,魏收将十六国的部分政权列入“民族传”,并通过谶纬等内容说明十六国政权的僭越性、非法性。北魏作为成天应运的政权自然不能承继十六国,而应该上承同样是天命所归的西晋。这也说明了北朝争取对于西晋的承认。北朝将先祖追溯至黄帝也是对这一继承性的认同。总之,无论出于自愿,还是巩固统治的客观需要,北朝都将自身置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统绪之中。也就是说,北朝不仅承认这样的继承性,而且参与到了政治承继的过程之中。
第五,道统认同。有学者认为道统认同就是对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及其传承的认同[18]不论南北都十分注重“正统”的地位,这也直接导致了南北朝正史“民族传”中“争正统”的现象。对“正统”的争夺首先建立在认同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北朝不认同这一说法,大可以避而不谈,绝不会产生争正统的现象。正统论本身就源于儒家思想文化。欧阳修提出:“《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19](P34)即《公羊传》是正统论的起源。饶宗颐从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正统之论起源于《春秋》,指出:“治史之务,原本《春秋》,以事系年,主宾昈分,而正统之论遂起。”[20](P1)不论是《春秋》还是《公羊传》都是儒家经典。正统论蕴含在这些经典之中。北朝对正统的争夺,“虽是对天子或霸主地位的争夺,却又是对华夏文化的归属。其文化上的价值选择是站到华夏正统文化的旗帜之下,进而成为它的合法主宰。是归属它,而不是毁灭它。”[21]北魏不仅将自己归属于华夏正统文化之下,更成为华夏文化的捍卫者、传承者。
结语
南北朝时期政权对立,民族关系复杂,正闰难分,这一局面使南北政权陷入正统之争中,直接影响了《魏书》“民族传”的叙事。《魏书》“民族传”标目、具体内容、史论都体现了争正统的思想。通过在具体内容书写中追祖溯源、强调中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记载异象、使用春秋笔法等叙事方式,贬低南朝,突出北魏在争正统中的优势。这样的叙事方式隐含着对历史文化的认同。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增进民族感情,更有利于各民族从心理上、情感上互相认同和接受。同时,这样的叙事方式也为各民族接受、学习儒家文化提供了心理支持,从而使夷夏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弭,为隋唐大一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