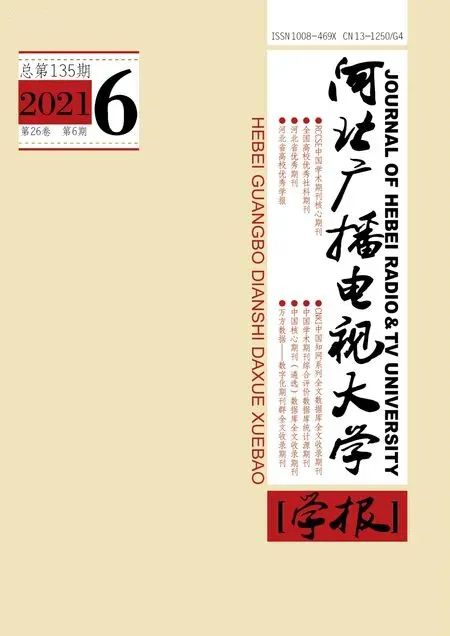霍夫曼《金罐》中的空间交融
——论“花园仙境”的诗化功能
井源浩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金罐》是E.T.A.霍夫曼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于1814年首次问世,副标题为“一则现代童话”,收录于《仿卡洛风格的幻想作品》中。故事讲述了大学生安泽穆斯的奇特经历。在现实社会中他生性天真、行为古怪并处处碰壁,但借助其童稚般的诗意心灵,他接触到与现实交融碰撞的魔幻空间,并在林德霍斯特馆长和其待嫁之女塞佩蒂娜的帮助下,通过在馆长神奇的温室花园里描摹自然文字,不断克服来自尘世内心和外界黑暗巫术的诱惑与阻碍,最终成为真正的浪漫诗人,去往“诗的国度”。学界对该篇小说的文学样式及其“二元性”总体创作特色的分析已颇为透彻,对其中体现的艺术幻想也有详细的研究。[1]把作品主题阐释为主人公安泽穆斯通过经历诱惑与磨难,不断完善自身,完成浪漫诗化的过程已成定见。[2]但小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仙园奇遇,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主人公在此奇丽空间的抄写员经历本是他蜕变的关键点。可以说,如果没有仙园的奇遇和引渡功能,主人公无法前往诗意的亚特兰蒂斯。因此,本文结合空间诗学理论,分析花园仙境所象征的灵性自然空间如何对主人公的童稚心灵空间施加影响,令其在此体悟自然,描摹自然,最终成为真正的浪漫诗人。
一、童稚的心灵空间:感知奇异世界的主体
同自己的好友沙米索所塑造的倒霉蛋彼得·施莱米尔一样,霍夫曼笔下的大学生安泽穆斯同样不通世故,行为笨拙,且时运不济,他会“在光滑的地板上失足跌倒”“碰坏瓶瓶罐罐”“走起路来活像个旅鼠直来直去”[3](P239)。但这种和当时德累斯顿上流社会颇为异质的天真与举止,正是安泽穆斯“童稚般的诗人气质”[3](P239)的外化表现,并借此使主人公拥有了联结世俗之外奇妙事物的通路。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谈到神话与遗弃的孤儿时认为,虽然孩子处于一种本质的孤独状态,但是无论如何,他在最初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人类家庭中的孤儿,神明家庭中的宠儿,这就是这神话成分的两极”。[4](P174)对自然神秘事物的感知力以及尚未世俗化的心灵共同构建了主人公童稚的诗性心灵空间。在此空间中安泽穆斯自然地接受了不断涌现的奇异事件,而该空间正是融入自然、联结神秘空间的必要前提。此论断在文本中有诸多细节佐证:在横渡易北河的游船上,众人看到的是烟火在水面上的反照,大学生瞥见的却是小蛇的金光,听到水中小金蛇的呼唤,便要跳下水去[3](P196);在林德霍斯特馆长讲述完童话故事般的家族传说后,其他听众对此一笑置之,而安泽穆斯“却产生一种阴森之感”[3](P204);文书为安泽穆斯介绍工作时,将馆长的生活环境描述为“偏僻的旧房子”[3](P198),而在安泽穆斯眼中却是“花园仙境”[3](P222);在林德霍斯特从指间迸出火星为赫尔波兰特文书点烟时,文书只道“您看他玩的这化学戏法”,而安泽穆斯却不无惊悸地想到了蝾螈[3](P240)。与童稚心灵,即诗性的心灵空间辩证对立的,是仙园展现出的浪漫世界:神奇的棕榈树、会说话的小鸟、罕见的古籍、神秘的蓝色书屋。在此,自然的灵性空间进驻主人公的心灵世界,令他突然能看懂自然神秘复杂的文字,甚至通过黄金与宝石映射出自己诗化的内心;而当主人公被女巫魔镜所蛊惑、逐步堕落回现实、沉沦功名利禄、再度来到馆长的庭院后:一切神奇不复存在,他的耳朵再也听不懂鸟语,眼睛再也看不到奇异的棕榈树,再也无法抄写文卷上的神秘文字,并最终犯下大错被困于水晶瓶中。但与安泽穆斯所辩证联结的神秘自然空间自古一直存在,却未曾有人获悉其中的奥秘。在世俗视角下,这个充满灵性的空间仅是一个鸟语花香的温室,而只有在拥有诗性心灵空间的主人公眼中,它的灵性才得以感悟。这两类空间的共鸣,共同构成一种崭新的认知维度,同时也使空间的跨界与融合成为可能。因此小说中致力追寻的童稚诗性特质,正是联通两个世界共同的前提,也是实现空间融合的必要一环。这正是“童年时期的存在将真实与想象互相联结,而在此他以完全的想象体验现实的形象”[4](P139)。但这种空间的联系又是极不稳定的,当童稚心灵走向世俗而不再追求更高级的理念和诗化时,该联系便会断裂;只有当主人公悔改,并克服自身的弱点(即打破女巫的镜子)才可能再次建立两个空间的联系并实现融合。
二、灵性的自然空间:花园仙境的诗意体验
文本中,作者大量着墨于安泽穆斯做抄写员的工作地点——林德霍斯特馆长的温室花园。在德累斯顿市下的水泥建筑中,如此一个散发魔力而变幻莫测的花园无疑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广阔而神秘的自然空间。在这一点上,巴什拉叙述了其与心灵空间的关系:“广阔性就在我们心中。它关系到一种存在的膨胀,它受到生活的抑制和谨慎态度的阻碍,但它在孤独中恢复。一旦我们静止不动,我们置身别处;我们在一个广阔的世界中梦想。广阔性是静止的人的运动。广阔性是安静梦想的动力特征之一。”[5](P237)于此,对该空间的感悟可分为三阶段:自然感知阶段、自我审视阶段和文字教化阶段。
自然感知阶段始于安泽穆斯来到庭院大门前,这是一种无意识的知觉体验。庭院大门在空间上起到分割世俗与灵性自然空间的作用,主人公只有借助馆长的药水消除女巫的诅咒才得以入内,进入一个自然的幻境中。馆长的房屋虽然外表不起眼,但门内外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而幻境与现实恰是借助这道门实现越界与融合。[6](P61)进入大门并穿过甬道后,一个“长满奇花异草的,有着奇特树木的美丽温室”[3](P221)、一个主人公可以与鸟类自由对话的奇幻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此空间中最显眼的是“一棵棵高大的、形成穹隆的棕榈树”[3](P222),文本中正是这些棕榈在安泽穆斯将墨水滴到珍贵的手稿原件上时变成条条巨蟒。综合上述的“鸟”“蛇”以及“树木”等元素,不难看出小说中采取了宇宙之树的神话原型:他象征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也被视作链接天堂、人间和地狱三界的轴线;在许多文化中,宇宙之树的树干顶端栖息着作为神之信使的鸟类;树干有大蛇缠绕其上,象征着大地和自然的无尽创造力。而宇宙之树在另一方面也象征着人类克服天性中的缺点,并获得精神的启示。[7](P97)
在感受灵性的自然空间时,主人公的自我审视阶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贯穿于文本中。体现之一为:通过这样一个以宇宙之树为中心的自然灵性空间,安泽穆斯克服了自身的缺陷(人间),打破了巫婆的诅咒(地狱),最终成为真正的浪漫诗人,前往诗的国度“亚特兰蒂斯”(天堂)。另一处体现便是花园中央反映出安泽穆斯和塞佩蒂娜第一次相见场景的金罐,其映象联系着馆长为吸引安泽穆斯到此工作而拿出的绿宝石镜子,镜面上显示出了三条小金蛇的影像。作为映象载体原料的黄金和绿宝石本身是自然矿物宝石,因而具有与自然本体的连通性,其反映的幻境给人以明亮而高贵的感觉。由其反射出的跟大自然完全和谐一致的奇异国度带领安泽穆斯从世俗走向诗意和精神的世界。与天然黄金宝石形成对照的是女巫魔镜,它由人工的方法拼凑而成,映照世俗欲望以引诱安泽穆斯堕落。[6](P61)说明只有真正的自然之物,才能产生对诗意国度的反映,形成自然灵性空间。
最后,作者将蓝色藏书室描写为安泽穆斯的工作地点,在此开始了主人公的文字教化阶段。安泽穆斯能够前往蓝色藏书室工作的前提条件是,能证实他具有“按照我(林德霍斯特)的愿望和要求完成分配给您(安泽穆斯)的工作的能力”[3](P223)。蓝色藏书室象征着无限与神圣,因此记载馆长家族传说的珍贵手稿原件正是保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使棕榈树上的翡翠叶子产生笔画和繁杂文字;在该空间中也具有平静、反省与智慧的神秘力量[7](P97),安泽穆斯便是在这里强化了对自然的感受力,在梦境中与塞佩蒂娜相遇,听她讲述家族故事,进入语言构建的诗的世界。诗意的自然与梦想空间赋予我们一个“非我”,即诗化了的“我”,正是这“非我”赐予主人公体验到生存世界的信心。在荒凉而毫无温情色彩的现实世界里,这种非现实机制对童稚般的诗人气质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事实上,霍夫曼对馆长花园的指称词语已明示其功用:它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暖房(Gewächshaus),更是“醉人的仙园”(berauschender Feengarten)。也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灵性空间下,林德霍斯特的考验和教化悄然发生,大学生安泽穆斯凭其纯粹之心和良善之性,成为花园仙境合格的抄写员。
三、心灵空间与自然空间的融合:浪漫诗化之果
塞佩蒂娜为主人公带来的梦中世界标志着内心空间的无限性,空间的诗学特征正是在于赋予我们寻求梦想空间的幸福。巴什拉认为,从几何学来看,内与外的辩证法依赖于一种强烈的几何主义,它把边界变成了壁垒。而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确定不变的直观,召唤起我们内心经验的细微之处,在内心与自然空间的张力中进行内与外的双重辩证互动,以寻求一种平衡的融合。[5](P297)上述空间的融合经历了忠实描摹自然和通过梦境感受事物这两个过程。
忠实描摹自然的核心是对浪漫诗人进行后天培养,即对自然的感悟与模仿。文本中处于现实空间的角色对自然手稿敬而远之,神秘文字于其视角下只是“不属于已知任何语言的奇特符号书写的手稿”[3](P199)。而安泽穆斯却凭借童稚心灵,对这些古文字有着天然的、特殊的亲近。在此前提下,主人公以梦境与自然感悟为途径,成功地实现了两个空间的融合并逐步成为真正的浪漫诗人,而在该过程中,安泽穆斯对象形文字手稿抄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泽穆斯视角下,象形文字古文手稿书写于棕榈树的翡翠绿叶上,笔画曲折,状如植物、苔藓和动物;而当主人公堕入世俗后,这些文字展现出来的却是“繁杂古怪、纵横交错的笔画……似乎像一面布满彩色纹理的大理石板或者是一块长着斑斑青苔的石头”[3](P246)。象形文字作为最早的文字符号系统,体现的是事物最本质的样子,是对自然事物的直接描写;而之后产生的字母文字则是抽象符号,这样的语符所指只是抽象而非自然事物。字母文字虽利于表情传意,但却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安泽穆斯没有抄写、描绘象形文字,而是通过对自然灵性空间的感受完成了工作,这也从侧面表明象形文字以及阿拉贝斯克不是“不可画的艺术”,而是“真正的画作”[8](P55)。树叶上的象形文字如同叶脉纹理,是文字的最自然状态,也是自然本身对其秘密的记录。这种自然界的文字既表现了世界的创造力,同样也具有创造世界的能力,基于此,浪漫诗将语言和象形文字作为非物质的原料来构建世界,构成了“自然文字=自然事物”的直接联系。因此仅仅是一个错误的书写就会颠覆世界,在林德霍斯特对主人公的警告中也得到印证。[8](P49-51)从初期的“笔画不圆润”到后来的“得心应手”,安泽穆斯本体内在的美学意义在感受自然的过程中得到了提升,通过这样的“后天的培养”,他理解了自然之声和创作的先声,最终写出了诗意的文字笔画[8](P37),成为真正的浪漫诗人。
对自然的感悟描摹是实现空间融合的第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在作者笔下皆发生在梦境中:安泽穆斯在塞佩蒂娜的帮助和引导下,亲身感悟了诗性王国,游历了史前的亚特兰蒂斯,并在梦醒回归现实后发现,那些深奥的手稿抄件已自然天成。由此可见梦境对于空间融合的催化作用。
自诺瓦利斯起,德国浪漫派便十分重视梦境。诺瓦利斯认为,“梦常常意味深远,具有预见性,因为它是自然灵魂发展的产物,且以联系为基础。”[9]梦的真正目的在于揭示梦与文学的共性,发觉梦对个体的意义,以使梦与联想引导下的文学服务于对个体内心的探索。[10]在理性主义世界观中,梦具有“非理性”的面孔,主人公在梦中的自我感觉表明,个体在做梦时与清醒时一样,都能通过感觉来体验自我,甚至有时候梦中的自我感比清醒时更为强烈。在主人公的梦境中,安泽穆斯的理性达到了最低点,但对于自然与神秘事物的认知能力却达到了顶峰。在梦中,绿蛇化身为清醒状态下不可见的婀娜少女,并引导主人公进入诗的国度,亲身在史前亚特兰蒂斯的空间中感受了万物之间存在的“神圣和谐的奥秘”[3](P263)。这恰似浪漫派人类学的观点。按照其设想,在人清醒时,负责意识感知思维的大脑系统和无意识精神活动的精神系统间毫无瓜葛,而梦则好比一个媒介,在其间架起了沟通桥梁,在梦中,人的无意识上升为意识。[11]通过器具以及其他媒介无法实现对自然奥秘的理解,而对自然的直接感悟才是唯一的途径,借此才能够了解自然真实的原貌,实现两个空间的融合,这是诗人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四、结语
霍夫曼在《金罐》中构建的空间不仅是文本背景,也是带领读者走入浪漫诗化世界的心灵与自然空间。作家本人虽怀抱诗心文才,然受制于社会现实因素,受困于德累斯顿的隆隆炮火,终未能抵达传说中的诗意王国。不过,他在小说中创造了一处神奇的花园,让同样具有艺术家心灵的主人公得以隔离尘世,接受自然净化以及教化,最终实现了抵达亚特兰蒂斯的理想。小说结尾的叙述者脱离前十一章的叙述框架,跳入故事同林德霍斯特进行对话,对整部“现代童话”进行反思,并对现实空间展开批判。实际上,艺术家独特的心灵空间与外部现实空间的冲突是霍夫曼诸多小说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是《沙人》的主人公还是音乐家的代表克莱斯勒,最终都在现实空间中惨淡收场。而《金罐》中的大学生作为唯一的幸运儿得偿所愿,委实仰仗作家特意为他建造出的这所神奇的“花园仙境”,这正是在俗世中修行的艺术家们可遇不可求的自我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