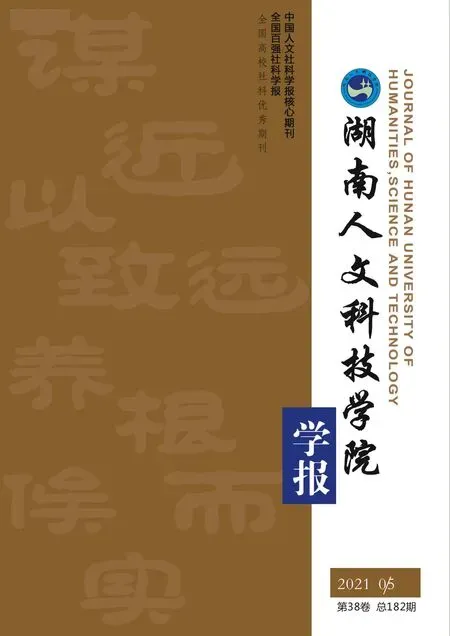农民主体性视角下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进路
——基于湖南湘西州18个脱贫村的实证调查与分析
胡伟强,郑 熠
(1.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乡村有乾坤,事关天下事。当前,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确保如期全面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脱贫地区要从集中力量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在此背景下,该如何抓紧谋划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呢?本文通过对湖南湘西州18个脱贫村的实证调查,从农民主体性视角,探析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逻辑旨归、现实问题与推进理路。
一、问题的提出
从政策演进之维看,农民主体性视角下实现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是顶层设计的战略呼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打赢脱贫攻坚战专题会议、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和外出调研考察等多个重要场合均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1],“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等纲领性文件以及2019年、2020年、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统筹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再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但总体来看这项工作还处在“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结合实际先做起来,为面上积累经验”[3]的阶段,尚未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和规划。
从地方实践之维看,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促进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具有现实紧迫性。虽然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平稳过渡和有效衔接已在最高决策层的顶层设计上形成共识,也尽管脱贫攻坚在产业扶贫、人才扶贫、文化扶贫、生态扶贫、组织建设等方面为乡村实施“五大振兴”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与借鉴,但遗憾的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中央高层的强烈呼唤与基层现实境况中的虚与委蛇形成较大的反差。笔者在湘西州一些贫困村调研时发现,由于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二者在主体维度、时间维度、目标维度等层面具有异质性,再加之脱贫攻坚严格的考核评价机制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压力型体制,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出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张皮”运作的现象。在村域实践中,一些党员干部对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认识不到位,对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衔接与融合发展思路还不够清晰和成熟。事实上,不少地方政府在制定统筹推进乡村脱贫与振兴的具体措施时,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
从已有研究之维来看,探讨农民主体性视角下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亦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学界已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但仍存在着研究的整体情况还比较薄弱、学术研究和实践创新之间尚未有效关联和贯通穿透、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亟需优化与拓展等问题。综上所述,从农民主体性视角下深入研究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相关论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时代意义和现实针对性。本文立足于田野调查事实,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范式,深入分析农民主体性视角下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逻辑脉络,客观剖析两大战略有效衔接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现实表征及成因机理,以探讨和找寻可能的接续理路。
二、农民主体性视角下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证成
(一)农民主体性视角下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逻辑
人之存在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属性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主体性就蕴含着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创造性等基本特征[4]。那么,农民主体性就可以界定为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所具有的主导权、参与权、表达权等,主要体现为农民的经济主体性、社会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等[5]。从理论探源上讲,在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诠释。也可以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坚持农民主体性地位的理论来源。这就需要深刻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丰富内容和科学内涵:作为发展思想的“以人民为中心”,意指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价值遵循的“以人民为中心”,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作为行动宣言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奋斗目标,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农民主体性视角下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历史逻辑
1.从传统乡村建设的历史启示来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将自己的学术理想经世致用于乡村建设中,开启了一场传统中国乡村建设的“理想国”构建实验。但是,这些传统乡村建设的实验运动收效甚微,有的甚至走向失败,试图通过振兴凋敝的乡村来改变当时中国的落后面貌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以“梁漱溟的困惑”为例,梁漱溟本人也坦言:“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6]449。究竟缘何会造成如此困局?梁漱溟分析认为是“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未能与乡村打成一片”,反而,“我们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的道路……这样,则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他们是被改造的,我们要改造他们”[6]450。综上分析,传统乡村建设运动收效甚微、未获成功的历史启示在于:建设和振兴乡村必须以乡村的利益为出发点,代表农民的要求和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农民内源力量,让农民群众都自觉行动起来。
2.从百年党建的历史昭示来看
1944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雄辩地指出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讲政策、脱离群众,且“久已失掉民心”[7]。毛泽东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号召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牢记历史经验的启示,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事实上,始终密切联系群众、自觉贯彻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建党百年以来的宝贵历史经验。百年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三)农民主体性视角下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价值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全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根本目的的逻辑旨归和价值所在,这在客观上要求必须尊重和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从价值哲学视野看,“农民主体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均内蕴着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人民共享的价值目标、人民满意的价值准则,这三个维度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价值体系,构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内核。同时,我们还必须深刻认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农民主体性”的重要意义。农民不仅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创造主体,而且还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价值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农民主体性”对于新时代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整合作用、价值激励作用和价值规范作用,有利于凝聚共谋振兴的磅礴力量,有利于激发基层乡村干部的激情斗志,有利于塑造良好的乡风民俗。具体来说,农民主体性视角下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包括如下价值判断:一方面,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勠力实现人民共享;另一方面,要永葆“最大政治优势”就必须明确“人心就是力量”,就必须坚持人民评判的标准。因此,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必须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
三、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的表征及成因
上面的分析表明了农民主体性视角下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应然性和逻辑必然性,但要明晰两大战略有效衔接中农民主体性建设的实际境况,还必须基于实践的实然性,深入地做进一步的农村调查,去把脉思考、对症下药。2020年7月—9月,我们对湖南湘西州的18个脱贫村进行了较为扎实的田野调查,并根据实地调查形成的田野经验和访谈情况、文本资料等,分析和阐释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现实表征及成因机理。
(一)“三农”政策的内卷
农民主体性缺失的一个重要现实表征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实施和衔接过程中“三农”政策的内卷化。“内卷化”指为了有限的资源展开非理性的内部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无助于促进社会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黄宗智将小农经济中出现的“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现象称为“内卷化”或“过密化”,即“没有发展的增长”[8]。杜赞奇提出了“政权内卷化”的概念,意在强调“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9]。“三农”政策“内卷化”的关键机理在于:虽然出台的支农惠农富农的“三农”政策越来越多,并且与之相配套的投入“三农”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但一些地方的“三农”工作的成效却没有成比例增长。相反,因为出台的三农政策太多,一些基层干部的主要精力用于应对上级政策的布署及检查,开始慢慢脱离农民群众,并导致形式主义抬头。
从笔者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基层治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形式主义与“三农”政策内卷化的问题。特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伴随着国家资源和财力的大规模下乡,为防止扶贫和乡村建设资源的滥用,国家制定了相配套的规则制度和督查机制,这在规制基层权力的同时,也导致了农村基层疲于奔命、办事留痕、目标偏移等问题。农村基层组织忙于应对上级的检查,无法抽出更多的时间深入群众,基层工作中过程代替结果、形式代替内容、表面工作代替实质工作的现象较为突出,并最终使得基层治理陷入空转和内卷[10]。湖南某高校的驻Z村扶贫工作队G队长向笔者坦言:
“现在的村干部确实辛苦,工作也不好干,上级派下来的事很多,管的又很严,有的老乡的思想工作又很难做……我们工作队驻村扶贫快3年了,每天的工作都很饱和……扶贫手册、贫困户档案、工作台账等等,都必须按上级的指示和要求去做好以备随时检查用……每年搞(扶贫)省检、州检,还有(扶贫)‘回头看’的时候,大家是真心的累,没日没夜地走访贫困户,然后核实和准备各种表格材料……”。(访谈记录:GFA20200706①)
W村一名村民小组长的话印证了上述说法:
“这几年上边儿的会议和文件特别多。有时候L支书没时间,就喊我代他去镇上(开会)……好些个文件带回来后都要村里照着去办,上边儿有人会来检查的……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村部楼里每天都热闹得很……我们又不拿国家工资,家里负担都要靠出去做工赚点钱用,哪有那么多时间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有的事L支书打电话说了,随便应付一下算了……嘿嘿,确实存在有些老百姓说的‘热热闹闹走过场,扎扎实实搞形式’问题”。(访谈记录:LMX20200703)
在K村,一位村民也向笔者吐露心声:
“村里的干部,不管他是支书、村主任,还是外来的扶贫队的干部,那都忙得很……(有时候)上面有人来检查的时候,他们(扶贫队的驻村干部)就会到那些娭毑嗲嗲屋里打个转……基本天天能看见他们开个车子往镇上跑……那他们主要还是听上面的,上面让做啥就做啥嘛”。(访谈记录:CTX20200709)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三农”政策内卷化和形式主义抬头?这其中有压力型体制、“顶格管理”等行政技术层面的原因,但其背后更为隐秘和复杂的深层次原因是:在包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内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农民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内源性动力匮乏,致使各项“三农”政策和措施“剃头挑子一头热”,正如斯科特在剖析“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原因时所指出的“国家的视角”[11]。简单化、极端现代化、急于改善以及市场化等逻辑理路,以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代替公众的参与和反馈,没有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必然会导致“三农”政策内卷化和形式主义抬头。故此,“十四五”时期,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就必须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从“国家的视角”回归“农民的视角”,调动农民积极性,激发农民内生动力。
(二)“精神贫困”的凸显
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另一个现实表征是一些贫困群体或边缘贫困户的“精神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并且成为其致富奔小康的关键阻力。这里的“精神贫困”主要是指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准则、生活态度等精神世界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通常表现为脱贫致富的主动性低、依赖性强,“等、靠、要”思想严重。Z村村主任的看法形象地说明了上述的“精神贫困”问题:
“一些上了年纪的嗲嗲娭毑硬是把我们的扶贫当作是天上掉馅饼。在他们的意识里,如果他们没吃没喝、没地方住,政府就要按时给他们发钱,扶贫队就要给他们修房子住,这是共产党干部的分内之事……还有的甚至天天打牌,好逸恶劳,你急他不急,上动下不动,他们主要觉得反正有人给兜底……吃、喝、住、行总是有人管的,不用自己发愁……”。(访谈记录:LW20200702)
笔者调研发现,与自然地理或先天禀赋低劣等客观条件所造成的空间贫困和物质贫困相比,根植于贫困群体自身的文化贫困、知识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等层面的精神贫困则更为严峻,更具危害性,正是政治、社会、文化和心理等主观层面的贫困才是使之陷入“贫困陷阱”的深层次因素。笔者在S村调研遭遇到戏剧性的一幕,颇值得反思。
贫困户L:你是新来的干部吗?
笔者:呃,老乡,我是……
贫困户L摊开手笑着说:你是干部你要给我捐钱啊,呵呵……(访谈记录:LXL20200708)
一位省派驻村扶贫干部也向我们抱怨说:
“在贫困户眼里,我们扶贫队就是‘无限责任公司’,什么都要包……你给他(指个别贫困户)配发了猪仔鸡苗,他还得要你把饲料也给他搞好,这样子怎么行呢……怎么说呢,有些个人就是死死地赖着你,自己不想事也不愿干事……眼睛只是盯着农商银行那个折子上国家每个月给他们补贴的钱,该得的都得了没……”(访谈记录:GFX20200723)
笔者也注意到,一些报道中出现过个别地方的个别贫困户将用来发展产业扶贫的粮种或畜禽苗种直接吃掉等极端案例,也有“争当贫困户”的咄咄怪事。虽然脱贫攻坚以来“扶智”“扶志”的扶贫实践从未间断,但“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精神贫困问题仍然存在。如果在未来五年两大战略有效衔接过渡期内的精神贫困不根除,那么解决相对贫困的物质帮扶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压力就会增大,不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作为内源动力、价值依归和脱贫助推器的农民主体性的丧失、进而诱发农民的“精神贫困”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从权利视角分析。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不足”[12]13。在我国的改革发展中,贫困地区和农民的权利、机会和能力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一些地方可能被排除在优质资源配置和优先发展机遇之外。第二,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舒尔茨将贫困的根源归结于人力资本的质量不高[13]。换言之,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富的关键,为此,必须要加大教育投入以提高人口质量,但这恰恰是贫困地区和人口所不足的。第三,从制度视角分析。缪尔达尔通过制度方法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认为“要提高穷苦群众可悲的社会水平,需要进行激进的制度改革”[14]。从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国家区域发展的优先次序、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非均衡发展战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虽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但也是造成农村农民贫困发生和存续的重要制度诱因。
四、农民主体性视角下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进路
(一)保障农民社会主体性
农民的社会主体性是指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角色。保障农民社会主体性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核心在于把属于农民依法享有的权利还给农民,并保障农民在村庄社会事务中依法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得到落实和维护。通过赋权来改善困难群体生活境况的观点最早由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森考察了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贫困、饥荒以及不平等问题,得出造成贫困的原因是权利的丧失和被剥夺,森所说的权利主要是指资格和能力以及自由[12]。这对2020年后我国的贫困治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显然也具有很强的参照性、解释力和启发性。当前,保障农民社会主体性,就应当保障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就应当按照“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新要求,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加强农村群众自治建设,探索基层协商民主路径,健全村民监督机制,确保群众知情权和决策权。
(二)增强农民经济主体性
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是指农民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地位。增强农民的经济主体性,其基本的出发点在于“增能”。森最早提出了能力贫困理论,他认为贫困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15]。从我国波澜壮阔的反贫困实践来看,特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实施以来,贫困是一个包含多种内容的概念,不仅是指贫困人口的低收入和低消费,而且还意味着缺少机会和缺乏能力。故此,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十四五”脱贫之日起设立的五年过渡期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紧紧围绕“赋权增能”来增强农民经济主体性,激发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内生动力。为此,必须着眼于提高农民的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继续深化扶贫与扶智的融合实践,强化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制定可持续的农业产业发展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农民长效增收机制。
(三)培育农民文化主体性
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是指农民在农业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文化主动与创造[16]。培育农民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要义在于激活乡村和农民自身的价值,让农民从精神上和心理上焕发生机,充满斗志。刘易斯首先提出了“文化贫困”概念,其意在强调形成于贫困环境中的心理定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等形塑着贫困人口的生活并加剧了贫困[17]。这一理论表明,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当着眼于农民文化建设现状,紧紧围绕农民群众的需求,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促进2020年后的长效治贫机制向更加注重和突出扶智扶志与精神文明建设转变,切实使农民群众的志向立起来、主人翁意识确立起来。此外,还应当破除城市中心主义价值取向,摒弃盲目追求现代化的发展理念,用生态文明的思维重新审视乡村,发掘乡村自身的内在价值功能,重视乡村特有文化在教化群众中的作用,对乡村的村落庭院、民俗文化、乡规民约、德孝家风、民间文艺等的生产价值、生态价值、教化功能进行现代化的创造性转换,以传承优秀的乡土文化来滋养民心。
注释:
①访谈记录的编码规则:访谈对象姓名的汉语拼音首字母+访谈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