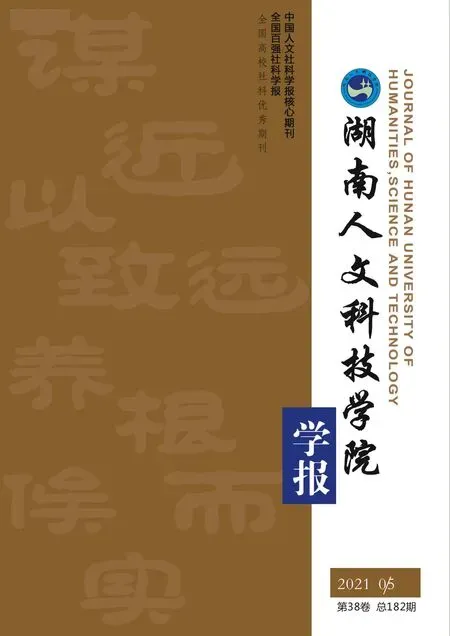边缘人物的关怀:湘籍女作家对俄苏文学的主题借鉴及差异书写
年 颖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人文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410205)
文学始终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融入转型和动荡时代形形色色的阶级纷纷进入作家的视野,进而衡量着作家的人文态度和价值尺度。事实上,能够经久传世的作家和作品对人数庞大的底层民众总是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关注“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也是俄国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一般而言,“小人物”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不属于统治者和权贵阶层,而是指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的、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破产的农民、劳力、小职员、流浪汉、小市民、小官吏、小知识分子等”平民阶层[1],这是19世纪俄罗斯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和变迁的历史语境下的一个典型缩影。同样处于社会裂变中的现当代湘籍女作家,学习俄苏现实主义作家对边缘人物的塑造,通过对小人物的性格特点、心理动态、行为方式、生活境况的独特言说,从多个层面表现感知时代、探求人性、寻找生命出口的主题,赋予这群边缘人、多余人以更多的社会价值、文化蕴含乃至政治意义。当然在借鉴同时,湘籍女作家也能结合本土社会境况作出一些差异化的改变,进而凸显本土创作关注边缘人物、同情下层民众的别样趣味和独特题旨。
一、“边缘人”的社会画卷与人道精神
自19世纪普希金的《驿站长》出现维林这一人物形象以来,“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成为了俄苏文学中的特有传统,俄国文学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更深深影响了湘籍女作家的创作。鲁迅将这种影响比之为“不亚于古人发现了火”,因为从俄国文学那里,中国读者“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那里,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辛酸的挣扎”[2],同时也激发了中国作家对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强烈内心共鸣和对强权者的憎恶。小人物的本质特点就是社会边缘性,这类人群表面上可能焕发出一丝新时代文化气息,然而无可避免的是“他们自身又受到了传统旧时代思想的深远影响”[3],面向新时代时又无不带有旧时代的痕迹。最早将“多余人”一词从俄国引入的是瞿秋白,他的《赤都心史》(1921)中就有“中国之‘多余人’”一节,这一节的开头醒目地引述了俄国“多余人”罗亭致娜达丽娅的一封感叹自己虽有良好禀赋但却一事无成的信。
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俄苏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其紧密联系社会现实,表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等特征,充分凸现了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关爱之情。高尔基在文学创作中大量书写了对社会底层人民痛苦生活的体验,展现他对“边缘人”的深刻了解,这些都成为他创作历程中永不枯竭的艺术魅力。如其代表作《切尔卡什》《游街》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残暴,重点描写了小市民的空虚与无聊,从而表达出底层人民的痛苦与不满,高尔基的《在底层》展现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底层人物的生活悲剧,并且探寻了他们的出路,在此基础上体现了对社会底层人物的肯定与尊重,凸现了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受此类作品的影响,湘籍女作家陈衡哲彻底否定了卑弱顺从的传统女性意识,其作品常常流露出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她坚持为无数不能自己发声的“被侮辱者”代言。她时常控诉这“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4]。
丁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和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将为人生、为社会苦难谋求纾解之路作为自己的写作理想,从个体的寂寞,转向“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很想做些事,却找不到机会”,最终将文学的目的认定为“提起了笔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5]。丁玲在自己的创作中尝试展现女性痛苦而无望的境地,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和《新的信念》中两个被侵略者凌辱的女性形象——贞贞和陈老太婆。小说中的贞贞命运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索尼娅,但是命运比索尼娅更加不幸。贞贞在民族战争中失身于敌人后不见容于自己的同胞,“连我也当着不是同类的人的样子看待了”,被“当一个外路人”。丁玲笔下贞贞是圣洁的化身,是“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的人”“人也不就是爹娘的,或自己的”。如果说莎菲是一个觉醒后找不到出路的女性形象,那么贞贞的形象就更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也显得更有光彩。那些“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女性遭遇也正是自身性别无法逾越的鸿沟,遭遇不幸后女性对世界、对人生的态度,也反映出了女性作家对自身困境的反抗与挣扎。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画卷离不开底层人物的社会呈现,离不开“边缘人”的生活。尤其是在1930年代陷入民族生存绝境的时刻,在各个阶层中受到压迫最深的就是广大底层妇女,主要包括妓女、女工、妾室、女仆等。湘籍女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会从社会底层的妇女视角入手,深入地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和人生价值等问题。袁昌英在创作三幕剧《孔雀东南飞》中,就将视野转向封建家庭中身为子媳者的痛苦,意识到女子处于另一种身份的不幸,而《人之道》中被遗弃的妻子王妈到处寻夫却阴差阳错来到丈夫新建的家庭里做了女佣等。除此之外,白薇在《打出幽灵塔》中塑造了一群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主要包括深受欺凌与摧残的妾、女仆等不同身份的角色,她们长期以来受到了作为封建家长、性暴君的“父”的镇压与奴役。在作品的最后,这些“边缘人”集体反抗,努力创造了一个“我们的世界”[6]。
中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都较为关注一些被欺凌、被压榨或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这些人物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客观现实,突出创作的主旨。这种创作对象的选取也映衬出俄苏与湘籍女作家在精神上的互通,展现了文学作品的批判精神、人道主义关怀。
二、裂变时代的文化缩影与反叛姿态
19世纪的俄罗斯,经历着从农奴经济向商品经济裂变的艰难过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小人物无疑是处于这粗粝车轮生死边缘的人群。无可阻挡的是,必然有一些底层的弱者会被时代淘汰,或者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处于尴尬而悲苦的境地。普希金《驿站长》中的维林,他的一生遵循俄罗斯体制的既有陈旧模式,循规蹈矩,本份老实直至女儿被拐走,也默默忍受,毫无反抗,最终抑郁而死。他终身的处事信条就是息事宁人、委曲求全,他无法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新的生活观念,也看不到资本主义萌芽在俄罗斯大地上破土而出。他代表着巨变时代一大群逃避现实、麻木不仁的俄罗斯小人物的社会心态。
封建社会的瓦解既造就了普希金笔下维林式的逃避者,也造就了契诃夫笔下尼古拉式的庸俗者,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索尼娅式的受害者,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不屈的反抗者。屠格涅夫在创作小说《前夜》时,俄国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步入了第二个阶段,传统的农奴制经济正在急剧瓦解。叶琳娜就在“新生活”来临的过程中表露了她的渴望。在爱情与婚姻上,叶琳娜选择了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英沙罗夫,因为担心父母不允许,叶琳娜选择自作主张、私定终身,展现了自己的决心与勇气。虽然后来丈夫不幸英年早逝,但是叶琳娜却没有被现实所击垮,而是选择加入到保加利耶人民的革命事业之中,为这份事业付出自己的青春与汗水。
在中国现当代湘籍女作家开展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边缘人物的反叛精神在作品中也有着较为突出的展现,湘籍女作家塑造了多个不同的“走出去”的女性形象。谢冰莹的一生是逃奔的一生,其人生选择、文学创作都是向封建制度宣战,展现出她强大的战斗精神与叛逆精神。每当遇到绝望与打击时,谢冰莹就会常常鼓励安慰自己,作为一位富有战斗激情的青春女性,“不断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视野、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7]在她本人的《自传》中,谢冰莹就曾讲述过青春的叛逆经历。比如反对裹足、为争取上学权利绝食、四次为包办婚姻奔逃;在参加革命斗争之后,谢冰莹北上南下,东转西突,鲜明地展现了其奋战的叛逆精神。谢冰莹之所以产生这种强烈的叛逆精神,不仅是因为受到俄苏文学以及现实社会的影响,更是为她对人生理想永恒追求的信念所驱使。她在第二次到日本求学时,看到一名遭受毒打却意志坚强的韩国革命志士后,充分感受到他为自由、解放而斗争到底的精神。《在日本狱中》她诅咒军警毫无人性,赞扬韩国志士是为所有人谋解放的革命志士:“你们为什么丝毫同情心也没有,居然还忍心毒打他,你们难道是狼心狗肺,凉血动物吗?”[8]在后期的文学创作中,谢冰莹也始终坚持这种叛逆以及敢于追求自由的精神意志。
边缘人物的反叛精神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更为丰富充实的精神力量,体现每个人物角色的自我意识,也为作品注入具有生命力的灵魂。俄苏文学与现当代湘籍女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都有着较为强烈的反叛精神与价值观念,这种精神价值的融入让这些文学作品熠熠生辉,映衬出作者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反叛精神直接指向病态的社会,让读者能够对社会现实有着更为全面的思考,而反叛下催生的新人物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感召性。
三、个体的精神困境与集体斗争的出路
对于处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来说,如何从边缘的困境中走出来,也是俄苏作家与现当代湘籍女作家思考的问题。不论向内的个体承担,还是向外的社会突围,实际上就是文学家在刻画小人物形象时两种不一样的精神抉择,这也会影响到作品中小人物的命运走向和作品最终的风格风貌。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思想有过这样震耳发聩的描述,他认为俄罗斯是两极化的民族,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与自由放任,另一方面又是专制主义与国家至上主义;一方面是善良、柔顺和人道,另一方面又呈现为倾向暴力残忍;一方面追求永恒真理,另一方面又信守宗教仪式;一方面充满着民族主义、救世主义和全人类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个人意识。俄罗斯“是对立面的融合——在他们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9]。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俄罗斯人本身在民族性格上就有着较为突出的悖论,在国家现状的分析上包含了极度的不满与深沉的爱国主义。
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部分俄苏作家也从家国视野的角度入手,将这种对国家现状的思考与集体主义精神结合于一体,突破俄罗斯传统民族思想中个人主义、个体价值的局限。列夫·托尔斯泰就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的创作中展现了自己的冷静思考。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最终走向了悲剧,托尔斯泰并没有局限于男女爱情的角度,而是从整个黑暗罪恶的社会入手,将安娜与渥伦斯基爱情悲剧的结果归结为俄罗斯封建社会体制,将个人命运的演绎与国家、社会的危机融合在一起,不仅使整篇小说的高度得到提升,还体现出作者对于社会、国家走向的关注与思考。
文学中的集体主义突破个人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在文学创作中注重群体的价值,关注人格与社会的关系,强调社会价值的实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理念,被涂抹上浓厚的现代政治革命色彩。湘籍女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由于受到精神思想的发展变化与外界多元因素的影响,她们在小说话语方式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最初对个人意识的关注逐渐转向以集体主义精神为依托的创作。
丁玲在早期文学创作中关注女性的欲望、精神心理、人际关系与社会出路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然后走向“过渡期的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纠结”,经历延安时期以后,又转向“中后期集体主义的高扬”[10]。从早期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就可以看出丁玲站在个人与女性的角度,表达自己的迷失与焦灼、幻想与痛苦,凸显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在过渡时期,丁玲的政治意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女性意识出现弱化的状况。在这一阶段,丁玲尝试从民族、阶级解放的视角出发,加强对社会中女性问题的关注程度。在《韦护》《一九三O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中,丁玲选择以“革命+恋爱”式为题材,写出自己对女性解放的思考。
在中后期创作中,丁玲接受了革命理念,加入革命文学的创作道路。正如蒋光慈在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中提到,当前时代的重音在于集体主义,通过革命实践,集体主义的萌芽渐渐产生,“由个人主义趋向集体主义……算是已经发展到了极度。”他还断言,个人主义必将走上绝路,“无政府式的个人主义只是混乱,争夺,不平等,无秩序,残忍,兽性的行为”,这是难以为继的,而“出路只有向着有组织的集体主义走去”[11]。在这一阶段,丁玲创作了《田家冲》《一天》《水》等作品,也创作出长篇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这部小说中,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命运架构,丁玲都是基于党的政策思想、政治态度、阶级成分来进行分门别类、加工构造的。作品淡化了“五四”时期的个性化色彩,塑造出多位承载政治使命和符号的文学角色,一定程度上造成丁玲文学创作中“自我”的迷失。除了丁玲,杨沫在创作《青春之歌》等文学作品中也融入了强烈的集体主义思想。《青春之歌》是一部探索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道路的长篇小说,它以林道静的生活轨迹为主线,揭示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思想得到全面升华。他们突破了个人主义的局限,加入到集体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完成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阶级解放集体斗争的实践参与,最终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现当代湘籍女作家先后站在家国、集体的立场,对文章的主旨内容进行全面的升华,将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与国家的、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从精神内涵的角度来看,俄苏文学与现当代湘籍女作家都呈现出较为浓厚的集体主义诉求,他们都将民众的生活、国家的发展与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忏悔精神,将民众的痛苦与自己的情感紧紧相连,展现出了博大的民族精神与情感,“在揭露社会的不公平、同情下层人民的不幸的同时,又在着力挖掘普通人的人性美,展示他们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追求”[12]。这一精神主旨的设定,为大时代的小人物寻求个体生命价值指出光明的方向,这种文学创作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更强,顺应了1930年代革命文学转向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