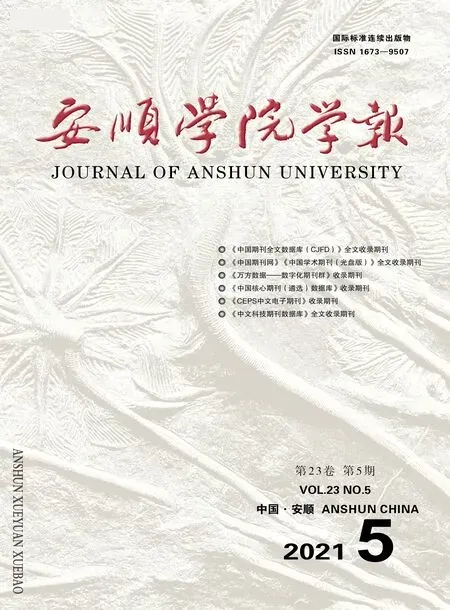“红色经典”叙事话语初探
刘晓华
(《贵阳学院学报》编辑部,贵州 贵阳550005)
“红色经典”叙事,一般泛指以中国革命历史为题材、在中国拥有大量受众的文艺作品。它既包括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红色苏维埃政权”“红色革命根据地”“红军”等的书写,也包括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更特指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中大量出现的革命历史小说。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每逢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庆祝节点,“红色经典”叙事都会持续绽放光彩,并带动不同时期的“红色热潮”。“红色经典”叙事话语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它与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左翼文学的“革命话语”是一脉相承的,也接续中国传统文学“诗言志,文载道”的根脉。因此,“红色经典”叙事话语是可以成功复制的,尽管有类型化的倾向,但它的叙事颇有特色,既暗含传统叙事的“中国风”,又具有吸纳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开放性。因其承载着无数国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侵略与压迫、实现国家富强不惜一切付诸努力与牺牲的民族精神,能够唤起全体国民的红色记忆,赓续红色血脉,让一代代国民沉浸在叙事中,持续发挥着文学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而备受中国读者喜爱。
被称为“经典”的红色叙事作品,全方位展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工人罢工斗争、学生学潮运动、农村轰轰烈烈地反对各种苛捐杂税斗争到土地革命、游击战场和正面战场的战斗场景以及城市地下斗争的残酷性,等等,均为读者提供了史诗般的阅读盛宴。在叙事视角上多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全景展示革命斗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残酷性,也有意识地采用适当的艺术形式配合政治宣传和主流思想,其内在的叙事动机都是以历史来论证现实,强调“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认知[1]。基于此,“红色经典”叙事的主客体便有了某种规定性,只是会随着现实革命斗争的变化与需要而做出微调。
一、“红色经典”叙事主体姿态的变迁
叙事作品从来不是历史的实录,叙事主体不但要讲“故事”,还要在故事中勾勒理想,而将叙事客体与理想联系在一起,不断刻画“时代新人”是“红色经典”叙事一条看不见的主线。早期启蒙叙事希望达到的理想是“人得活得像个人”,无产阶级革命叙事表达的理想是“人人都活成了人”,而到了工农兵叙事表达的理想是“人人都活成了不平凡的人”。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经典”叙事,将这些理想付诸现实,叙事客体已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巨大变化,而叙事主体也悄然由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变为身处其间的亲历者。这种叙事主体叙事姿态的变迁,见证着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共同铸就了主客体的身份认同和家国认同。同时跨越时空,引发不同时代、不同阶层身份的接受者的共情。
(一)启蒙者姿态——俯视
启蒙者叙事主体对底层民众的态度无疑是悲悯的,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们同情底层民众,对加之于广大民众身上的非人待遇积极鼓呼呐喊,希望民众们早日觉醒,奋起斗争,获得精神和肉体的解放与自由。实现此理想,唯有“革命”。然而如何“革命”?就连鲁迅也含糊其辞:“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2]他们也唯有在黑暗中不断探索,处处碰壁,后来,才逐渐清醒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完成只能依靠底层民众自己,开展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唯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底层民众精神与肉体的解放和自由。
(二)旁观者姿态——平视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叙事”已经正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正面阐释与宣传。在《八月的乡村》中,叙事主体借人物之口指出:“革命就是把从祖先就欺负我们的那些臭虫们,全杀了;把现在东三省的日本兵全赶跑,剩下田地我们自己种。我们不再纳粮,纳租,养活那些白吃白喝的臭虫,懂了吗?比方没革命以前,富人们有三个五个十个八个老婆,你现在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起一个老婆呢;革命以后,一个钱不花,你就可以有个老婆!自己有地,不再给别人种了。懂了吗?这就是革命!”[3]用直白的语言讲述革命的道理,叙事主体已经从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精英立场,转变为脚踏实地站在底层民众中间进行理想宣传。这种宣传并不宏大,完全是从底层民众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相信底层民众蕴藏的巨大能量,通过激发他们的热情和创造性,最终达成无产阶段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亲历者姿态——仰视
“红色经典”叙事的叙事主体大多数都是一些革命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如罗广斌就是白公馆的幸存者之一。还有的人在战争年代大都有过担任随军记者或宣传干事的经历,如欧阳山、杜鹏程、刘知侠、吴强、曲波、杨沫、李英儒等,也都算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或亲历者)。他们在谈到作品创作时,使用最多的话语是:“这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杨沫);“《苦菜花》这本书,就是以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为基础写成的”(冯德英);“书中所有的战斗场面都是实有其事的”(刘知侠)。以这种身份进行述史,无疑会对接受者产生无可辩驳的说服力。“真实”成为红色经典叙事能够成为“经典”的独特标签,同时,作为亲历者的叙事主体,他们对乡亲、战友、英雄几乎无一例外地衷心赞美和讴歌。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是现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值得仰视和赞颂的。
叙事主体叙事姿态的变迁,其成因受着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想等因素影响,有些时候固然是顺势而为或不得已而为之,也造成了作品艺术质量的良莠不齐,但故事中塑造的“时代新人”形象都已随着作品的经典化而广为人知,并持续不断地发挥着“艺术感染人、教育人”的作用,这一点足以弥补“瑕不掩瑜”的遗憾了。
二、“红色经典”叙事客体 “时代新人”形象的变迁
红色叙事主体不断调整叙事姿态,以革命为意义元点,对革命历史进行文本化的阐释,生发出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朋友与敌人等看似简单的二元对立,通过对叙事客体不同时代 “时代新人”形象的刻画,深刻揭示了人、家、国的内在联系。
(一)萌发出自我意识的“时代新人”
打造“新人”,改造国民性,是启蒙者叙事主体的时代使命,他们的笔下虽然更多的是麻木、愚昧的阿Q、闰土、祥林嫂及看客们,但已然也有了主动出击、开始把握话语权的庄爱姑们(鲁迅《离婚》)。这类时代新人形象并不多见,甚至或许只是寄托创作者对底层妇女解放理想期许的幻景,但毕竟现实中还有“刘和珍君”这样的“真猛士”。底层民众的革命力量已经进入革命家、政治家以及文学家的视野,他们必将带来“庶民的胜利”。因为,“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4],底层民众才能摆脱悲苦命运,实现真正的解放。
(二)有了革命理想的“时代新人”
到了“左翼叙事”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革命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时代新人”已经主动将追求“个人的解放”与追求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结合起来。“丰收成灾”主题揭示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底层民众的疯狂掠夺,觉醒了的底层民众认清了造成他们贫困落后的根源,开始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抗和斗争的洪流中。在斗争中他们变得有勇有谋,贡献了无数充满“中国智慧”的奇思妙想,这支撑着他们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而有了革命理想的“时代新人”,如小二黑、小芹(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王贵(李季《王贵与李香香》)、赵玉山、郭全海(周立波《暴风骤雨》)等,已经不仅仅是“时代新人”,还成了“生活的主人”。因为有“新政权”做坚实可靠的保障,这些“时代新人”展现了更加乐观、自信和充分的自主意识。他们积极参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团结一致向前进的英雄群体。
(三)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时代新人”
共和国建立初期大量涌现的“红色经典”叙事,成为和平时期出生、成长的“时代新人”塑形的典范,也呼应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亟待建立新的国民精神的诉求。不难想象,经历了血与火考验的林道静(《青春之歌》)、雷石柱、刘洪、芳林嫂(《铁道游击队》)、周炳(《三家巷》)们,终于迎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们在参加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时该是怎样地全情投入;也不难想象,他们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出怎样优秀的后代。这些后代应该是纯粹、透明、乐观、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新人”,延续到艺术作品中有像梁生宝(柳青《创业史》)这样为集体无私奉献的先进人物,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有像欧阳海这样默默无闻的生产劳动者,他们都是高扬起继承先辈光荣传统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时代新人”的变化,生动体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给个人带来的深刻变革。“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种“旧”与“新”的对比,在实质内涵上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新人”是深刻觉醒、具有明确自我意识、充分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新型国家的拓荒人、主人和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这种深刻变革将个人的成长、生存与家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必定焕发永续的生机与活力。
三、 “红色经典”叙事话语的教育价值
“所有写作都具有指涉物、意义和价值。要想削去或取代它们最终总是不可能的。”[5]“红色经典”叙事的指涉物明确,即那段峥嵘岁月中可歌可泣的人与事,讲述过去的故事总归有它的意义和价值,至于其教育价值能否实现,关键要看讲故事的方式方法是否得当。从“红色经典”叙事话语的叙事技巧来看,它既有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传统的反拨,两相结合,在艺术水准上未见得都能称得上是上乘之作,但在传播中让接受者于潜移默化中受到教益是毋庸置疑的。
(一) 对传统的继承——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讲故事
1.对传统潜结构的继承。传统潜结构包含了丰富的“集体无意识”,《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这类作品就包含了比较丰富的传统结构要素,《红旗谱》包含的是朱冯两家“家族恩仇录”原型故事,《青春之歌》包含的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故事原型,《林海雪原》包含的是“绿林传奇”故事原型。从接受心理的角度看,这类含有“传统的集体无意识”的作品都具有牢固的潜伏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在结构、语言、人物的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能接近民族风格,因此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2.“大团圆”式结尾
“红色经典”所讲的故事是千差万别的,但结尾的方式却几乎一致,都是“大团圆”式结尾。例如:《红日》《红岩》《保卫延安》《红旗谱》等作品的结局部分,无论是对环境的浓墨重彩的渲染,还是对人物群像的描绘,以及刚刚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或对走向新的胜利的展望,都符合接受者的传统期待视野——历经磨难,终于迎来光明或胜利(或圆满)。如果将这种“大团圆”式结尾与故事的悲惨开头进行比较,接受者很容易得出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青年人应倍加珍惜胜利成果的结论。
(二)对传统的反拨——时间美学号召人们向前看
主要体现在“红色经典”叙事革命性/现代性的“线性叙事时间”与传统的“循环时间观”的鲜明区别上。在中国的古老哲学中,时间是一个无限长度的混沌概念,老子说:“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间是一个近乎无限重复的轮回,体现在叙事上就是“由聚到散,由分到合,由盛而衰”反复循环的“圆形”结构。而红色叙事引入的是革命进化论和历史阶段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中国革命”纳入“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6]。这样的“线性时间观”体现在叙事中就是“党自从诞生以来┅┅领导我们在各个时期贯彻了阶级斗争,领导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7]。线性的时间美学号召人们向前看,未来肯定会更好,这对于今天进入新时代的青年人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结 语
“红色经典”叙事虽是特指,但由于每一个时代都不乏红色素材,而且它的话语体系是可复制的,因此,每一个时代都可以生产自己的“红色经典”。文艺工作者们应具有将“红色经典”持续讲下去的自觉,而广大受众也必将在品尝这道独特的“红色”盛宴中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