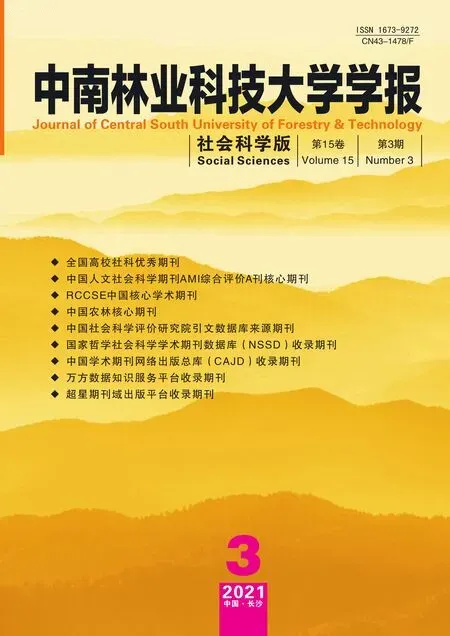场景视域下文化旅游社区模式构建
——以阿那亚文旅社区为例
陈舒萍
(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精神生活的需求随之提高,文化旅游成为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重要消费方式。在西方语境下,旅游与文化相互依存[1],文化的概念不断延伸,越来越与日常生活靠近,文化旅游的意涵也在不断发展,从“对他人的历史遗产的参观”[2],到“以文化事件为前提的移动”[3],再到对文化、艺术、创意产业以及特殊生活形态的参观。中国文化旅游融合的研究随着中国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文化旅游部的组建而不断深入,从文化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4]以旅游文化的形式成为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特性,将文化作为旅游发展的灵魂[5],发展到在产业融合的语境下,对文化旅游的发展动力及对策[6]、融合路径[7]、产业边界与互动等问题的探讨。旅游业的发展也催生了旅游社区构建[8]、社区参与[9]、社区赋权[10]等问题的讨论。当前对文化旅游及其社区的讨论多集中在旅游对社区带来的影响、社区如何赋权、增权与参与的问题中。社区是文化旅游的重要载体,不同的在地文化赋予了文化旅游社区不同发展模式。
一、文化旅游社区的发展模式
不同于依托自然资源开发的旅游景区,文化旅游依托于人文资源、历史文化遗产,在地文化、风俗历史、民族气质构成的文化氛围是消费者产生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基础。在地的人,由人产生的文化、历史、风俗,由人与文化塑造的建筑等物质遗产共同组成了人文类旅游资源。居民与生活环境的互动赋予区域活力,构建区域的文化价值,因此人文类旅游资源往往以文旅社区的形式呈现。
基于不同的文化资源类型、社区开发形式、居民参与情况,文化旅游社区大体分为三种发展模式:艺术介入实现乡村创生、历史遗产支撑文旅开发、新兴社区构建在地文化。
(一)艺术介入实现乡村创生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出现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人口大量外迁、文化日渐流逝等问题,激发乡村活力、实现乡村振兴成为近年来的重要议题。除结合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产业特色等区位因素发展乡村经济外,通过旅游业的介入实现乡村创生是实现乡村人、自然、经济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地方创生是乡村社区营造、乡村振兴、城乡统筹的理念和实践[11]。在外部力量的干预下,尤其是与旅游业的结合中,乡村富有特色的人文历史、工艺传承、地理风貌、生产方式等区域资源实现创意再生,为乡村注入活力,实现地方创生,文化与经济有机发展。
艺术介入是乡村与旅游结合最主要的途径。艺术作为能反映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成为连结乡村的人、文化与景色的纽带。艺术介入往往以地景艺术为媒介,利用乡村资源,如废弃的民宅、老旧的设施等,融入农耕、养殖等在地产业,通过艺术家与村民的共同创作,实现资源活化,将在地文化融入艺术作品中,并在文化旅游中实现经济联动。艺术介入乡村创生的文旅社区可以促进居民的广泛参与,激发居民对在地社区的认同感与价值感。在地文化通过艺术作品实现可视化与再创造,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乡村发展要求,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紧密结合[12],是可持续性的文化旅游社区构建模式。
利用艺术介入实现乡村振兴的实践在世界各国的乡村推行,其中最突出的案例为日本“大地艺术祭——越后妻有艺术三年展”。大地艺术祭从策划之初就贯彻“社区参与”的理念,由当地居民协助艺术家进行创作,居民的公众参与形式可以应用到其他文化空间的开发构造中[13]。艺术家从远到而来的客人逐渐转变为融入乡村生活的“村民”,创作的艺术作品以村民的生活为基础,村民产生共鸣的同时,在艺术表达生活的形式中获得新的体验与认知。艺术作品基本涵盖了当代艺术最为完善的样式[14],使观众对文化产生可视感与融入感,在欣赏作品、与作品的互动中融入乡村生活。居民在创作活动的参与中激发了对在地文化的自我认同感,随着大地艺术祭活动的开展,当地整体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提升,进一步提高居民的认同感与满足感。大地艺术祭的相关艺术作品与在地资源紧密联系,活动结束后仍保留在原地,持续吸引文化旅游的客源。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形成了以艺术创作、展览为核心的产业链,随着活动影响力的增强和艺术消费市场的扩大,艺术介入为乡村带来了稳步提升的收入和与文化旅游业相关的多点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可达性较强的乡村地区也有依托艺术介入实现乡村创生的案例,如凤凰艺术年展、许村国际艺术节等,形成了以艺术家、居民为主体的文化旅游社区,通过文化旅游业带动了当地经济增长,但艺术介入的在地性、与当地文化的融合程度、居民的参与程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历史遗产支撑文旅开发
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空间的转型已成为必然。以当地历史文化为核心资源,以历史建筑为依托,以特有的社区文化作为历史记忆构建历史文化社区,发展文化旅游业,成为保护与开发历史文化区的重要方式。随着政策制度的完善,我国当前构建起历史文化名城与村镇、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建筑等从宏观到微观的保护体系,在以文化遗产资源为依托的文旅社区中,以历史文化街区为主要形态。历史文化街区包含了历史城区、历史地段等内在含义[15]。
城市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地方的集体记忆,组成具有观赏价值的景观,消费者参与这类型的文化旅游实际上是主动识别、参与创造集体记忆的过程[16]。当游客将历史文化街区的日常生活当成景观凝视时,凝视的其实是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居民生活日常[17]。当地居民在历史文化街区中的生活,包含了居民对社区的地方认同[18],对消费者而言构成了具有原真性的文化场景,赋予消费者最真实、最具地方特色的旅游体验。居民在文旅社区生活的惯常,成为消费者文旅体验的非惯常,居民的生活习惯、饮食特征、特色产业、经商模式等习以为常的事物正是消费者旅游体验最重要的部分。当文化旅游活动嵌入到文旅社区中,进而居民形成与消费者互动的新的行为惯常,在交互与融合中产生新的生活方式,为消费者带来新的旅游体验。居民在历史文化空间中的活动,增强了历史文化资源的续存能力和生命力。除人的活动之外,在地的空间与文化设施,如传承百年的店铺、历史久远的雕塑共同构成地方空间的历史文化,为消费者提供历史文化街区氛围与时间的感知、对独特社区精神的认同。因此对于以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的文旅社区而言,居民的生活、历史的沉淀以及居民与环境形成的集体记忆是消费者获得旅游体验的关键。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浪潮扩张迅猛,文旅社区中承载文化记忆的物质与非物质形态受到了冲击,被千篇一律的现代文明逐步侵蚀。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历史文化街区在深入开发中使历史文化景观失去了地方性特质,如丽江古城、凤凰古城等文旅社区,街道成为公共交通通道与购物街,沿街的门店失去原有的生活气息,转变成面向游客的商铺[19],社区中的原住民大量迁出,游客难以从居民的生活景观中获得当地历史文化的原真性体验,历史文化街区失去了原有的特性。文旅社区的商业化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由此造成的历史文化的流逝与缺失却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对以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的文化旅游社区在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界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在地居民日常生活与旅游活动的矛盾与融合、消费者的在地体验与消费刺激等方面的平衡是以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的文旅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新兴社区构建在地文化
在以乡村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为核心开发的文化旅游社区外,在没有当地文化为支撑的前提下,出现了文化旅游社区的新模式。依托新建立的社区与新成立的社群形成新的在地文化,引入文化旅游设施,从无到有构建新兴文旅社区。新兴文旅社区以北京古北水镇、河北阿那亚等社区为代表。
新兴文旅社区实际上构建起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空间,文化旅游的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消费者的旅游实践共同作用于文化场域中,参与文化场域的共创[20]。乡村、历史文化街区中居民对地方文化的依恋,将转化成消费者对文旅社区原真性的体验。对于新兴文旅社区而言,往往缺少具有历史支撑的在地文化,文化的构建依托于建筑、文化设施等外部条件,并由新进入的居民在社区营造中共同创造。依托于外部并不断更新的社区文化构建模式反过来影响旅游空间的实践。当消费者进入文旅社区时,旅游凝视与经营者的生产经营产生互动,成为社区内部人员与外部来访者之间的信息传递渠道,并在活动交互中潜移默化地传达认知与情感。新兴文旅社区的文化既由新居民及其社区活动构建,社区文化场域又与旅游消费紧密联系,消费者的偏好、导向将影响文旅社区的发展方向,文旅社区为居民与消费者提供了互相审视、判断、模仿的空间,共同构建起激发居民认同感、消费者消费意愿与共鸣的社区文化。
不同于其他文旅社区对旅游参与较低的诉求,新兴文旅社区的社区参与程度较高,开发商、商户、居民可以共同参与到文旅社区的建设中。以古北水镇为例,尽管小镇的建设依托于袁家村,但随文旅空间建立的社区生活覆盖了原有的生活模式,引进的商户、开发商等逐步融入社区中,成为新村民参与社区的建设。古北水镇成立了油坊、豆腐坊、醪糟坊等8 个作坊合作社,引进了各具特长的手艺人,既作为商户代表,引领了旅游空间生产经营方向,同时作为文旅社区中的特色产业,参与到旅游空间的建设中。多方的共同参与构建起新的物质空间,创造了新的收益方式,构建了新的社区社会关系[21]。在新兴文旅社区中,社区不再处于弱势地位,主动将旅游作为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在旅游开发中有更多的选择权与控制权[22],社区与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站在同一战线。
二、文化实体空间下的场景理论
当人们产生文化旅游的行为时,实际上是将个人情感投射到文化空间中,并为审美产生的快感消费。随着消费升级、文化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人们对文旅社区所能提供的美学价值与愉悦体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求端的刺激为目的地文旅社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影响并重塑了文旅社区原有的生活形态、地域文化,促使文旅社区转变开发、经营模式,也催生出依托于新的人文地标、在地文化的文旅社区的出现。场景理论将不同形式的消费与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特质、生活方式与美学特征结合起来,并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通过场景理论对文旅社区进行分析,为文旅社区的构建与发展提出可供参考的路径。
在文化空间中,个体的行为是对文化与价值观的诉求。文化空间不是场所、地点等单一物理概念,而是包含了人、场所、活动三要素、并且要素相互联系的“场景”。“场景”来源于电影,原有的概念包括了空间、设施道具、演员、服化道以及影片传递给公众的氛围与信息,因此“场景”意味着包含了各个元素,其中各个元素相互联系,共同表达,传递信息与思想。
特里·克拉克将场景应用到城市生活中,认为城市中生活娱乐设施的组合构成场景[23]。在地文化、价值观蕴含在城市生活娱乐设施的构成和分布中,也就是蕴含在城市的建筑、社区和活动中,并形成抽象的符号和信息传递给不同人群[24]。场景符号能够被人们识别、区分,影响个体行为[25]。场景强调了人们在物理空间中的美学体验和人们在其中的消费实践,本质是作为由文化、价值观形成外化符号的社会空间以及影响个体行为的社会事实,也反映、塑造人们在文化空间中的行为。目前场景理论被应用于部分文化空间场景构建的分析中,如图书馆[26]、特色小镇[27]、城市街区[28]、文化产业园区[29]等,强调场景综合了文化空间特定的功能,将凝结的文化要素展示出来,场景理论为文化空间传达特定的文化内涵、刺激消费提供了可供发展的路径。
文化旅游社区凝结了在地文化,文化符号依托于建筑、文化设施构成可视化形象,在文化空间中开展的社区活动彰显鲜明的文化特征,构建起为游客传递文化氛围的场景。文化旅游社区通过强化场景特征,突出社区的在地文化,增强文化被消费者的理解与接纳程度,丰富消费者的文化体验。因此场景理论为文化旅游社区文化空间的建设与价值生成搭建了分析框架,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三个维度是场景分析评价的重要维度。
真实性指向的是人们在场景中形成的对地域、民族、国家等所在团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对于文化旅游社区而言,真实性就是构建或传承独一无二的在地文化。在地文化往往通过可视化的文化符号呈现,以特色建筑、文化设施等实体为依托,形成地域文化的象征与标识,引发社区居民的共鸣和消费者的认同,并时刻强化对在地文化的认同归属感[30]。
戏剧性指向的是场景通过活动互动实现文化精神的表达和对美的认识。对于文化旅游社区而言,戏剧性就是让文化空间、文化设施在活动中产生文化意义。文化设施为在地文化提供了静态依托,活动成为文化空间中的动态符号,赋予空间美学意味。消费者在活动交互中深化对在地文化内涵的理解,更好地感知场景内的文化符号,提升消费意愿。社区居民在活动中增强了对参与文旅社区构建与发展的主动性。
合法性指向的是对场景文化本身的判断与认同。对于文化旅游社区而言,合法性就是通过合适的方式,促使居民和消费者更加认同并信服社区的在地文化是得到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承认和支持的。居民在文旅社区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游客在体验中对文旅社区建设的见证、居民与游客的交流,都能增强居民与游客对合法性的认同。
三、场景理论下文旅社区构建
位于河北省秦皇岛的阿那亚社区是新兴文化旅游社区的代表,从2017年转型起,通过构建新的标识系统、精神与艺术建筑和住宅,举办艺术类、生活类活动,传递社区精神与社区文化,成为吸引游客、新住民的重要旅游目的地。阿那亚依托南戴河构建独特的海洋文化,吸引了亲水偏好的消费者,不可否认自然资源在其中的影响作用。纵观南戴河沿岸,保利观潮的住宅均价为13 000 元/m2,保利和堂别墅均价为27 500 元/m2,而阿那亚文旅社区的住宅均价为30 000 元/m2,远高于其他依托海洋资源开发的楼盘,因此在同样自然资源的条件下,通过场景营造、文化塑造,依托于在地文化构建的文旅社区在居民、消费者的影响力更大。
(一)以建筑IP、文化设施明确真实性环境
阿那亚作为新兴的文化旅游社区,在文旅社区的场景中通过建筑IP、生活文化设施的构建,营造独一无二的在地文化,赋予社区明确的文化真实性,连接当地居民与外来文旅消费者。
场景中独具特色的建筑确定了文旅社区的精神文化特质。阿那亚邀请国内外知名建筑师为园区内不同功能的建筑操刀,如邀请董功设计孤独图书馆、阿那亚礼堂,李虎设计沙丘美术馆,徐甜甜设计海边剧场,张轲设计观鸟屋等。尽管建筑之间的主体功能与设计思路不同,但无论是与海相连的图书馆,还是形如沙丘的美术馆,都在传递人、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理念,探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不同形态的建筑在场景中共同构筑了“海边共同体”的社区理念,以建筑IP 为标识传递出“共生”“共享”的社区文化,于居民和消费者而言,随视觉体验直接感受到社区明确的文化真实性。
社区内的公共建筑包含了社区的责任,应该与社区生活相融合。建筑IP 除原有的图书馆、美术馆、剧院等使用功能外,还具备了审美功能,更发挥着社区内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以海边剧场为例,其外观是棱角分明的混凝土多边形,不同纹理的混凝土又区隔出不同大小的独立空间,丰富了外观层次,增强视觉冲击,建筑物在整体静态的基础上增添了动感,为观者带来视觉的美感,产生美学直觉。多元的空间设计使得海边剧院不仅符合建筑美学,更体现了生活美学。建筑中心是环形剧场,既满足了剧院演出的功能,同时还作为社区居民、消费者聚集活动的场所,共享艺术空间与生活空间,满足多元的审美体验。建筑IP 将美的体验与公共生活结合,构建起以美为元素的真实的在地文化。
建筑IP 成为文旅社区宣传的名片,文化精神的标识。孤独图书馆、阿那亚礼堂、沙丘美术馆因其出色的外观与室内设计,成为“网红”建筑,是消费者争相“打卡”的胜地,文旅社区也将建筑作为重点推广的对象,制作系列宣传品,打造建筑IP。建筑IP 成为场景的人文地标,是消费者认知中代表文旅社区的符号,更是地域文化的可视化表现。如孤独图书馆,无论是独自伫立在空旷的沙滩上产生的静谧而美好的氛围,还是作为社区公共空间承载艺术活动传递的与社区相融的生活美学,于消费者而言都代表了阿那亚的气质。消费者会将美学体验延伸到整个文旅社区中,在感官、情感和精神三个层面获得场景体验。孤独图书馆以小见大地展示了文旅社区在地文化的真实性,作为文旅资源吸引文化旅游也是“图书馆+旅游”的重要实践[31]。建筑IP 成为游客了解文旅社区的重要窗口,游客对文旅社区在地文化的理解在从建筑IP 产生审美体验中逐步深化。
文化设施构成半公共的文化空间,为艺术与文化的展示、社群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对于新兴文旅社区而言,日常所接触到的文化设施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文化设施的形态、是否具有美感不仅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感与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更是塑造了社区文化。
在场景理论下,场景代表了一个有价值观维度的消费场所,其中消费是指能够给人们带来内心愉悦体验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消费行为,如欣赏音乐、品尝美食等[32]。场景的外在形式包含了城市生活中休闲娱乐设施,如咖啡馆、体育场所、餐馆等。人们在场景中的活动与消费,实际上是通过生活活动来获得社会身份的认同,通过审美体验获得情感的表达。阿那亚文旅社区邀请建筑师设计独特的文化设施,董功设计了海边咖啡厅,俞挺设计了儿童餐厅,张利设计了青少年营地。文化设施满足了居民与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尤其符合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一方面通过内饰设计、通感等手段制造气氛美学,给居民和消费者真实的场景体验,另一方面在居民与文化设施的相互影响下,作为生活场景为社区居民提供归属感,赋予社区文化价值观内涵,由此构建社区独一无二的在地文化。
文化设施除本身的作用外,更是社区内的公共空间,连接生活与情感。社区内的公共空间成为泛文化设施,是生活美学的直接体现。咖啡馆、青少年营地等文化设施强调去边界化,社区、居民与消费者有更多可使用的场景和可发挥的空间。社区内的青少年营地是社区内举办青少年活动的重要场所,在确定的空间之外建造了许多“不确定”的“冗余”空间[33],为建筑的多元使用提供了机会,不仅能满足体量较大、群组较多的大型活动需求,也满足较为安静、群体较小的私人交流活动的需要。以海边咖啡厅为代表的泛文化设施在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更是社区中带有互动与交往功能的社交空间。文旅社区中的文化设施与公共空间相互交融,分布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共同构建起居民与消费者感知美学的场域。居民与消费者通过现场体验的方式感受文化空间的气氛,在人与物、人与文化空间中形成在场性经验[34],也就是文旅社区中无形感知到的文化精神特质和无意识的审美感知,从而产生直觉和由欲望转化而来的活动与舒适物,构建起在地文化的真实性。
基于广泛的文化设施与公共空间所构成的场域,居民与游客在无形中感知社区在地文化的真实性,由此人与文旅社区之间形成特殊的依赖关系,既是居民对所在场所的依赖,也是游客对休闲旅游目的地的依赖。居民与游客在对泛文化设施的感知中形成了与社区文化相契合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从而产生与之连结的实践与情感,是对新兴文旅社区在地文化真实性的认同。
(二)艺术介入、生活创新还原戏剧性活动
通过艺术介入,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设施在活动交互中产生文化意义,阿那亚社区通过戏剧、音乐等多种艺术形态的引入,使社区中的咖啡厅、餐厅、居民生活中心等文化生活设施富有文化意义,还原场景的戏剧性。
阿那亚从2017年转型至今,每年举办了上百场文化艺术活动,通过活动留住居民、吸引消费者。以季节为主题,举办了春日艺术季、夏日运动季、秋日生活季、冬日读书季;发挥建筑IP的功能性,以文化设施为依托,举办“孤独图书馆驻馆计划”,邀请艺术家、作家驻扎阿那亚,体验生活并进行创作;以业主为活动举办主体,利用业主资源,排演话剧、音乐剧并举办阿那亚戏剧节,开设乐器夏令营与讲座;发挥社区组织能力,举办多种艺术形式的主题活动,如音乐节、喜剧之夜、文学节等。通过活动的举办,将艺术变成社区生活的日常,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用活动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往文旅社区体验生活。
基于艺术的介入,生活创新成为社区文化的重要内涵,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还原了在地文化,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景观。艺术与生活在多元活动中融合,放大了社区生活的特色。与居民生活方式相结合的单体活动,如红酒马拉松、风筝冲浪节、沙滩音乐节,随着活动数量与体量的增大演变成阿那亚年年举办的“生活节”。于社区居民而言,随着城市财富的积累,在对生活方式的反思中,形成了对多元文化培植的需求,在中产群体情怀的推动下,促使了以资源和闲暇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出现。消费者通过参与生活节,融入社区生活,一定程度上产生对文旅社区生活方式的向往,增强对休闲旅游目的地的场所依恋。活动还原了文旅场景下在地文化的戏剧性,在增强体验感的同时提升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艺术活动依托建筑IP、文化设施举办,使得文化空间的场景体验具有多元戏剧性。无论是由社区管理者组织举办的大型活动,还是由社区居民以社群为基础自发举办的小型讲座、分享,主办场所涵盖了建筑IP、文化设施、公共区域等文旅社区的各个空间,静态的文化设施在动态的活动交互中产生文化意义,构成环境、空间、居民和消费者之间的情感交互。于消费者而言,艺术介入、生活创新的活动需要消费者审美、在场体验的真实参与,深化了消费者对文旅社区文化内涵的理解。文化活动成为场景中流动而变化的文化符号,让消费者更容易地捕捉与感知。
文化艺术活动还原文旅社区场景戏剧性,更传递出社区的精神内涵,吸引更多艺术家驻扎。阿那亚文旅社区的居民中有不少艺术家,如小提琴家高露、古琴演奏家李凤云、设计师蒋友柏等,当艺术家配合社区参与活动或自发组织社区艺术活动时,会邀请艺术界中的同行作为嘉宾参与。许多艺术家在活动的参与过程中,被由人与文化空间形成的互动与社区精神特质所吸引,从被邀请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进而变成了社区的居民业主,再一次发挥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在社区举办相关活动。相关的艺术活动又给活动参与者传递精神,构建起活动、环境、人之间的联结,形成良性循环,在地艺术家随艺术活动的增加而增加。艺术活动赋予文化设施文化意义,为参与者、消费者提供不同的审美体验,在场景中展示社区的文化与精神,以此吸引更多人融入社区。
社区艺术活动不仅在社区内的艺术空间呈现,更是走出社区,通过艺术活动传递社区文化,将社区外的文化场所变成连结社区与其他消费者的空间。社区居民每年自发排演话剧,不仅实现了在社区推广戏剧艺术,还将社区艺术搬上社区外更专业的舞台。如2016年排演的音乐剧《朝九晚五》,在社区内进行排练,并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2017年举办阿那亚戏剧节,50 余位居民走上戏剧舞台,排演的戏剧《雷雨》《小安妮》《恋爱的犀牛》,在阿那亚蜂巢剧场与北京天桥剧场共同上演。艺术活动在外展演既是对社区居民自主、自觉、自发参与的艺术活动质量的肯定,更是通过艺术活动将文化空间拓展到社区外,在非社区的空间中创建新的场景。艺术活动成为社区外文化空间建立气氛美学的媒介,消费者在文旅社区外也能体验文旅社区的文化,从而建立并深化场所依赖,促使消费者产生前往游览、重游的动机,并提高为文旅社区付出更多金钱与时间的可能性。
(三)居民参与、游客背书回归合法性认同
文化场景下,不仅通过文化设施、活动等构建符合期望的文化空间,更需要在互动中提高消费者的积极性,并让消费者相信在场景中所感受的文化具备合理性和可传承性。阿那亚社区通过活动互动构建起阿那亚的社区文化,其文化活动除了艺术工作者的投入,更鼓励居民参与。居民在活动中相信场景中的价值观是得到传统的支持的。居民的参与对消费者而言构成社区文化合法性的背书,增强消费者对社区文化的认同。
居民在文旅社区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主导地位有利于让消费者在与当地社群的交流中形成对在地文化合法性的认同。阿那亚社区的艺术活动、生活节日邀请社区居民参与筹办,担任主要演职人员,如年度大戏由阿那亚居民自导自演,小型演唱会、音乐节邀请社区居民担任主唱。居民身体力行地参与为消费者带来在地文化的认可,说服消费者相信在活动中所感受到的精神特质、在文化设施中感受到的文化氛围是得到社会承认的。除参与活动外,阿那亚的大量活动由社区居民自主发起,活动与理念在居民业主的共同认同下逐步发展为文旅社区的大型活动。如社区内足球爱好者自发组成社群开展活动,从2017年第一场沙滩比赛开始,吸引其他业主居民参与活动中或自发成为活动志愿者,逐渐发展成社区生活活动的代表“足球嘉年华”。2020年疫情前,阿那亚社区平均2 ~3 天将举办一场活动,大部分由社区居民主导发起、居民与消费者共同参与。社区居民对活动的主导事实上是文旅社区的开放商让渡了部分社区营造的权利[35],社区居民增加了对社区活动的决策权,减少了居民对社区发展无权的无助感,发挥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居民在活动的参与、组织中增强对社区文化的认同,从而加强与消费者交流的主动性。于消费者而言,在文化活动中感受到居民对社区生活、社区文化的认可,见证与了解社区文化,增强对在地文化合法性的认同。
社区通过艺术文化活动提高消费者参与的积极性,游客对活动的高参与度反过来为居民形成文化背书,促使社区居民更加认可随社区构建起的在地文化,刺激居民对文化展示的主观能动性。阿那亚社区的不少居民是由消费者转化而来的。以游客的身份参加社区活动,体验社区文化,被社区精神特质与文化所吸引,进而融入社区,成为社区居民。游客到居民的转化,对原有的在地居民而言,是外界对文旅社区的认同,增强居民对社区在地文化合法性的认同。对消费者而言,游客到居民的转变,实际上是既往消费者结合自身的文化体验对文旅产品的反馈,转变消费者身份融入社区是对文旅社区文化较高的评价,更是融入场景中对消费者行为满意度的展示。消费者更容易理解这部分居民的思想转变,在惯性认知中形成对社区文化、居民社群的整体印象与普遍认可,提高消费者对文旅社区场景的认同,近一步强化场景下文旅社区文化的合理性,实现文化旅游产品的有效传播。
新兴文旅社区中,人与人的社群交流取代了冷漠的邻里关系,居民对文旅社区的运营、治理有较大的话语权。在阿那亚社区发展初期,随着阿那亚宣传效果渐有成效,社区文化的吸引力愈发增强,文旅社区中的游客逐渐增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游客与居民对公共资源的争夺。区别于其他旅游社区居民话语权小、牺牲社区利益满足旅游需求的情况,阿那亚文旅社区由居民与开发商共同治理。居民与开发商在协商谈判中明确多方职责与义务,居民牵头草拟社区公约,并由开发商最终落地实施。社区公约包括了《阿那亚业主公约》《阿那亚访客守则》《阿那亚民宿公约》,将文旅社区中因游客迅速增加而野蛮生长的现象进行规范管理,解决了因社区住宅销售太快而导致的社区价值观稀释、配套服务捉襟见肘的问题。
不同于有历史积淀的习俗传统,新兴文旅社区由居民选择、展示社区生活的面貌,并由居民从无到有地在文旅社区场景下建立在地文化。阿那亚构建起社群文化,居民自发按照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成立社群,由社群主导阿那亚生活与艺术的主体活动。居民重视社区营造,在不同的活动现场,都有阿那亚的居民自发成为志愿者,为社区服务,形成互帮互联的文旅社区价值观。在阿那亚文旅社区中,开辟了占地面积只有32 m2的“深夜食堂”作为居民情感交流的空间,居民可以通过社群认领经营权,与亲朋友邻组队完成一日的经营。导演孟京辉、陈明昊,跨界设计师蒋友柏,艺术家朱英豪都曾以社区居民的身份担任过主厨。社区居民的高度参与是文旅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社群的运营、居民的管理也证明“海边的情感共同体”这一从无到有的文旅社区文化是得到现实社会承认、支持的。
四、结论与建议
新兴文旅社区将从无到有构建在地文化作为重要资源,将社区生活与居民社群作为消费者体验社区原真性生活的重要依托,对真实性的明确、戏剧性的还原和合法性的认同为新兴文旅社区的发展、既有文旅社区的转变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首先,通过静态的场所塑造社区形象,明确场景文化真实性。文旅社区可以依托于已有的建筑历史遗迹、乡村房屋再建或从无到有构建反映在地文化特色的建筑,并将单体建筑或建筑群打造成建筑IP。建筑IP 将成为文旅社区内重要的文化标识,将场景中的文化、价值观转化成可视的实体传递给消费者。文化设施可以成为展示、体验在地文化的特定场所。文旅社区中的咖啡厅、餐厅等文化设施以及社区中的公共空间蕴含了文旅社区的精神价值,消费者可以在感官、审美的多重在场体验中明确社区文化的真实性,如消费者在新兴文旅社区的餐馆中能体会到睦邻精神的社区生活美学,在历史文化景区的咖啡厅中能体会到历史的积淀等。文化设施中蕴含的内涵将吸引对文化本身感兴趣的消费者,为场景释放更多能量。
其次,通过动态的活动实现场景互动,还原场景文化戏剧性。动态的活动赋予社区空间文化意义,成为联结文化空间与居民、消费者的重要媒介。文旅社区可以通过举办与社区文化相符的艺术类、生活类、体验类活动,吸引消费者的参与,消费者得以在活动体验中感受在地文化,增强消费者的地方依恋,提升消费者的付费意愿。文化设施在举办文化活动时,已不仅仅具备其本身的功能,如咖啡厅不仅是消费者饱腹的场所,更是吸引消费者的场景,具备了休闲娱乐功能,成为消费者与居民进行互动、情感交流、信息交换的重要场所。
最后,通过社区参与者构建在地文化,增强场景文化合法性。居民及社区的高度参与是文旅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当前我国文旅社区中居民的参与薄弱,社区的话语权较小。因此文旅社区可以鼓励居民主动参与社区营造,创造文化交流的机会,提升居民的参与度,如通过社群构建与活动支持,激发居民参与、组织社区活动的动力。一方面居民的认可证明了场景中在地文化的合法性,是受到了社会的承认与支持的,另一方面在居民参与中增进社会交往,基于友邻互助形成相互信任的社区社会资本[36]。同时,文旅社区的开发商或政府应该构建起与社区居民顺畅沟通的渠道,让渡部分权力,提高社区居民的话语权,重视居民在文旅社区中的合法权益,既保证社区生活的原真性,又增强居民对文旅场景中在地文化的认同,从而在交流与互动中促进消费者对在地文化合法性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