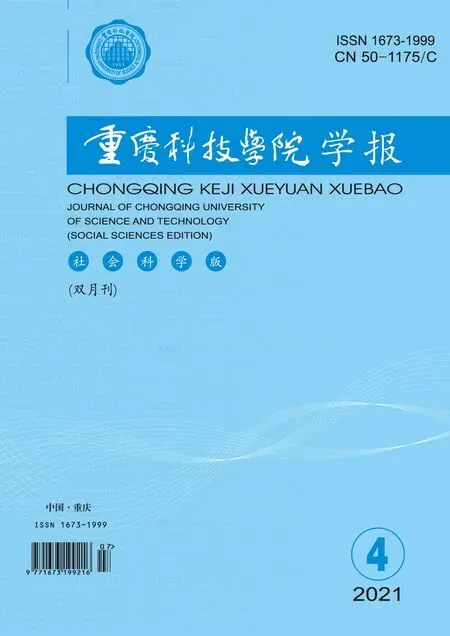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的镜像叙事与身份认同
兰立亮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个人的体验》是大江健三郎1964年继短篇小说《空中的怪物阿归》之后,于同年发表的第二部以残疾儿出生为题材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幻想去非洲旅行的日本青年鸟,得知刚出生的儿子脑部异常之后选择了逃避现实,去旧情人火见子家中寻求精神慰藉。二人原本打算委托私人医生杀死婴儿后赴非洲旅行,但鸟却在最后关头选择了回归家庭与残疾儿共同生活。与前作《空中的怪物阿归》不同,在这部作品中,大江不再强调孤立的个体面对现实世界时所感受到的人生荒谬感,开始反思和批判那种绝对个人主义心态,尝试将个体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进而使个人体验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
在接受尾崎真理子的采访中,大江阐释了自己对“个人体验”的理解,认为“历史中会出现只有作为个人才能体验到的完全孤立的体验”,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便是“尝试以一种完全特殊的形式将可能是普遍的体验作为紧贴个人的内容再一次重新审视”[1]。小说通过主人公鸟的个人经历,生动地表达了战后个人身份认同这一主题,而这一主题的达成,与作家在空间设置、人物塑造上的匠心密不可分。
一、自我欺瞒的空间:“非洲”与“多元宇宙”
小说开头描写了主人公鸟凝视非洲地图的情景。鸟眼中的非洲大陆,像一个低眉垂首的男人的头盖骨,显示人口分布的微缩图则像“刚刚开始腐烂的人头”,交通微缩图则像是“一个剥掉皮肤、露出了全部毛细血管的受伤的头颅”[2]2-3,给人一种血腥、残暴的印象。地图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鸟内心的焦虑不安和暴力冲动。
在小说发表的1964年这一时间点前后,非洲正值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先后有3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取得重大胜利,是对帝国主义在非洲殖民统治的沉重打击,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3]整个非洲因旧政治体制解体而孕育着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世界也因美苏如火如荼的核军备竞赛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岸信介政府1960年与美国修订了日美安全条约,进一步将日本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鸟所感受到的非洲这一场所唤起的“血淋淋”的印象,与当时暴力遍布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如同受伤的头颅般的非洲地图预示着之后鸟的孩子出生时脑部异常。在此意义上,脑有残疾的婴儿的诞生又可以视为时代的隐喻。小说一开始就利用头盖骨这一意象,将个体的不幸与世界危机笼罩的时代状况紧紧联系在一起。对鸟来说,非洲成了摆脱阴郁、封闭的日常生活,追求自我身份认同的新天地,是鸟通过在非日常生活中历练自己来寻找自我的一条重要途径。
可以说,鸟这一形象和大江《迟到的青年》(1960)中描绘的那种因战争结束而无法成为战斗英雄的日本青年一脉相承。这类青年从小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幻想着有一天能走上战场杀敌报国,但却因战争结束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而产生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残疾儿的出生更是彻底打破了鸟通过非洲冒险实现自我个性发展的幻想,使他认识到非洲探险只是自己逃避现实的借口而已,当下的自己是深陷自我欺瞒之中的“卑鄙的类型”[2]122。
但非洲对火见子来说,并不是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冒险之旅,而是改变自己生存现状的一丝希望。火见子在丈夫死后将自己封闭起来,白天总是躺在阴暗的卧室里睡觉。火见子的房间“是封闭内心、隔绝外在联系的象征”[4]。空间的封闭性象征着火见子封闭的精神状态,随着鸟带着非洲地图和非洲作家阿摩斯·图图欧拉的小说来到此处,这一空间的封闭性就开始被打破,二人的生活都因此发生了变化。鸟对非洲的热情转移到同火见子的性爱上,放弃了自己形而上的追求,“就连看看非洲地图,读读非洲人的小说也没了兴趣”[2]143。与之相反,火见子开始对非洲地图和非洲作家的小说产生了兴趣,并着手计划卖掉房子去非洲。可以说,她开始尝试摆脱丈夫自杀的阴影,走出封闭的小屋去追求新生。当火见子告诉鸟这一计划时,鸟朝思暮想的非洲变成了荒凉的唤不起热情的非洲,觉得自己“就像一匹野猪捉不住一匹愚蠢的地鼠,茫然地站在撒哈拉大沙漠上发呆”[2]172。也就是说,鸟脑海中幻想的非洲荒凉的场景与火见子所说的多元宇宙具有共同之处,均可以视为逃避现实的幻想空间或者说与现实相应的另一种可能性。
围绕着一个人,恰恰像离开树干的枝叶一样,跳跃着各种各样的宇宙呀。我丈夫自杀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宇宙细胞分裂。我一方面留在了死去的丈夫的宇宙里,而另一方面呢,在丈夫仍然活着的宇宙里,另一个我仍在和他一起生活着呢[2]56-57。
从以上火见子的解释来看,多元宇宙是一个多样的可能世界。美国学者埃弗雷特(Hugh Everett)在1957年提出了多世界理论,认为量子测量过程中所有可能态共存且具有同等的实在性,每种可能性都会在一个个不同的宇宙中得以实现。“经过反复曲折的发展,以埃弗雷特的相对态解释为原型的多世界解释目前已经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合理性,且在经验和理性对话的平台上为量子力学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5]的确,多世界解释(多元宇宙或平行世界)这一观点虽然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但其解释的合理性同样也为作家、艺术家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撑。火见子在丈夫自杀之时感受到“宇宙细胞分裂”这一情节设置,很明显受到了多世界解释这一科学话语的影响。鸟将其视为火见子“为了不把死看成是绝对无可挽回的东西而设计的心理骗术”[2]58。大江借人物之口将多元宇宙这一概念引入文本,既展现了人物自我欺瞒的生存状态,也呈现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原则,即关于火见子和鸟的叙事构成了一种平行对照关系。鸟在半梦半醒中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与火见子自杀的丈夫的重合这一场景很好地体现了大江在情节设置上的匠心。
在刚入睡时浅淡的梦境里,鸟把死去的青年和自己视为一体。他意识清醒的部分,感觉得到火见子轻轻在自己身上擦汗的手,而在梦里,他则断定,火见子给那青年净身的手在自己的身上轻轻移动——我就是那死去的青年[2]109。
一般认为,梦境是独立于现实的可能世界。在以上引文中,现实和梦境不断重合,交替往复,令做梦人真假难辨。可以说,通过将自己和火见子自杀的丈夫一体化,鸟同时体验了两个不同的宇宙。鸟在梦境之中的存在与客观现实世界并非毫无关联,“可能世界理论虽然预设了现实世界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世界就是单一而稳定的。对德勒兹而言,虚拟世界(指记忆、梦境等而不是技术上的)同现实世界一样是真实的,但并非所有的虚拟都能成为现实。虚拟之所以是真实的,是因为虚拟能够对现实产生影响。这就为各种世界之间建立一种替代性关系提供了基础”[6]。在此意义上,梦境这一可能世界必然会对鸟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产生影响,梦境和现实正如以上引文中鸟的感受所体现的那样,正处于一种相互抗争的混沌之中。
多元宇宙这一精神空间设置本身就体现了大江探索现代个体存在的创作动机。在存在主义哲学中,选择本身被视为问题,选择是自由的且无处不在。如果从时间维度来看这一存在主义认识的话,可以说人的选择具有未来指向性。多元宇宙学说则与之相反,将过去的选择以及未被选中的另一种可能性推向了前景。即便如此,多元宇宙中也必然存在着伴随着选择而来的责任问题。鸟最终选择了承担家庭责任,放弃了非洲幻想。在作出这一抉择之时,鸟脑海中浮现出杀死了婴儿的自己和火见子在去非洲的船上“用力地眺望着诱惑的地狱”[2]199的情景,再次提及了鸟的非洲幻想和火见子的多元宇宙。不难看出,鸟已经接受了火见子的多元宇宙观点,闭上眼睛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宇宙中的自己。鸟选定了与残疾儿共同生活这一点已确信无疑,但心中并没有彻底摆脱未被选择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影响,认识到另一种选择是“诱惑的地狱”,并开始反思自己内心曾经存在的人性之恶。
石桥纪俊分析了火见子名字的出典与《风土记》的关系,认为这一人名代表着“在混沌与秩序或者说生和重生之间展开的神话符号”。同时,阿摩斯·图图欧拉的小说《我在幽鬼森林里的生活》所描绘的主人公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但却有惊无险的幽鬼森林世界与火见子的多元世界想法相似,“对火见子而言,与鸟同居,一方面是陪鸟度过等候婴儿死去消息的一段艰难时光,实际情况却是‘火见子’在阅读鸟带来的阿摩斯·图图欧拉小说的过程中沉醉于小说中的一段时间。在这一过程中,非洲对‘火见子’来说,是以将‘多元宇宙’和神话源头合一的越界性的新的场所出现的”[7]。在小说结尾,火见子和鸟最终交换了二人拥有的精神空间——火见子毅然卖掉房子去了孕育着精神救赎可能的非洲,将自己在封闭小屋里思考的多元宇宙留在了鸟的心中。在此,非洲和多元宇宙随着男女主人公的人生选择属性发生了变化,非洲成了火见子精神救赎的空间,多元宇宙成了鸟反思自我的参照。《个人的体验》关于鸟和火见子的叙事呈现出平行的镜像式结构,也预示着两人无法结合的爱情悲剧。
二、动物比喻、镜像与身份认同
除了利用“非洲”这一地理空间和“多元宇宙”这一精神空间表现人物的性格发展之外,《个人的体验》还利用大量的比喻表现人物的生存状态。利泽行夫指出,《个人的体验》这样的作品“几乎每一页都存在着人物根据时间不同成为不同动物(有时候是虫子)的意象”[8]。的确,对小说中比喻进行梳理不难发现,文中大量的动物比喻喻体自成体系,构成了神秘的“非洲动物园”。比如,鸟看到的书店工作人员“手指像缠绕在灌木丛里的变色蜥蜴的四肢一样粗鄙”[2]3;医院院长“胸部像骆驼背一样须毛浓密”[2]22等。鸟眼中呈现的动物比喻匠心独运,充分体现了非洲幻想在其现实生活中的投射。大江之所以选用非洲动物为喻体,是基于对主人公非洲冒险与现实考验相似性的认识,充分展现鸟犹如通过仪礼般的现实考验。大量的动物比喻体现了大江对自然生命形态的回溯,蕴含着强烈的主体反思意味。通过以不同动物为源域,大江映射了鸟的生存境遇及其尚未体验的非洲世界。动物比喻随着人物的性格发展富于变化,不仅生动形象地强化了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也是呈现主人公身份认同过程的重要手段。小说大多数情况下多用处于弱势的小动物、海洋生物、虫子来形容鸟,鸟这一绰号本身就是关于其容貌、性格的隐喻,体现了他消极的边缘生存状态,但当他积极面对生存困境时,其形象又被比喻为勇猛的动物。如在反抗不良青年的围堵时“对着年轻人的腹部牛似地冲撞过去”[2]16-17;在接到医院通知婴儿异常的电话时鸟骑上自行车,“像一匹发怒的烈马,蹄下砂土翻腾,从树篱间穿过,奔向柏油马路”[2]20。透过动物与人类世界的比喻映射,大江生动描绘了小人物现实存在的荒诞感,凸显了现代社会中小人物的滑稽生存图景,充分体现了现代个体闭塞生活状态下的精神面貌。与动物比喻对人物性格发展的镜像表达一道,小说还借助具体的镜中场景塑造人物。镜子以及具有投射和映照功能的物体如眼睛多次出现在情节发展之中,构成了一系列镜子意象组合,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意蕴。
他看到了宽大而暗淡的玻璃窗里映现出来的自己,看到了正以短跑运动员的速度衰老下去的自己……他这副鸟样子会延续多久呢?他是那种从15岁到60岁都容颜不变、身姿不改的人吗?倘若如此,那么,现在鸟从装饰橱窗玻璃看到的,就是凝缩了整个生涯的自己[2]5。
在此,橱窗玻璃所映照的鸟的映像寓意深刻,在小说主题生成中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拉康认为,镜像是指6个月至18个月的儿童能够逐渐在镜中辨认出自己的身体形象,进而将自己的真实身体和镜中自我相互认同,完成自我同一性和整体性的身份认同过程。鸟借助橱窗玻璃看到自己的形象后,觉得自己从15岁至20岁一直没有变化,甚至觉得一生都没有获得自我成长,进而产生了自我反思。也就是说,橱窗玻璃(镜子)犹如一个呈现前世今生的魔镜,凝缩了鸟一成不变的性格规定性。鸟意识到镜前的自我明显与镜中形象的割裂而产生自我嫌恶,势必会尝试自我重塑。“照镜子时并不是自己注视自己,而是镜子在注视你,将它的法则强加于你,作为规范工具衡量人对上流社会的风尚法典的遵从程度。对自身映像即人的可见的外在体现——我可见故我在——的意识,自我意识起初是与之同时产生的。身份的确定要通过外形、角色、认同,决定着主体地位的建立。”[9]对鸟来说,照镜子是个体自我意识产生和决定身份认同的有意识的行为。镜像仅仅是一个通过想象叠加构建而成的虚假自我,是可以改变的自我。去见岳父之前,鸟在理发店的镜子中仔细观察了伪装的自己。
在镜子里,他看到自己刮过的脸宛如正午的海滨那样阳光灿烂。与昨天晚上在书店装饰橱窗里看到的肖像相比,这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鸟。鸟想,去见岳父之前,先来理发店,还是对了。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2]39。
小说的镜子意象充分体现了鸟对自己的认知:镜前的自我与镜中形象无法统一,也就是说,鸟犹如绰号所昭示的那样仍处于自我尚未确立的镜像阶段。镜像阶段是一个自我欺瞒的瞬间,是一个由虚幻影像、镜像引起的迷恋过程。人经过镜像阶段确立了自我,但这一自我确立的过程仍存在着自我欺瞒的成分。镜前的鸟是一个身份认同出现问题的青年,大量的镜中映像呈现了鸟寻找身份认同的精神之旅。在鸟通过玻璃、镜子或他人眼睛窥视到的各种自我映像中,存在着自我迷恋、自我嫌恶、自我反思以及自我重塑的欲望。
在去医院看望婴儿时,鸟从挂在门口柱子上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自我封闭式昏暗的眼睛”“一副色情狂模样”[2]86,再次确认了内心“自我封闭”的一面并对此深感厌恶。也就是说,鸟一直生活在与他人关系的隔绝之中。“色情狂模样”体现了鸟一开始与火见子的关系纯粹出于性本能。在火见子看来,鸟与她大学时代的初次性爱就是“强奸”[2]61,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鸟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自我执著之人。
拉康指出,匮乏的出现、对匮乏的想象性否认和欲望的产生是形成“镜像阶段”的前提。小说自始至终没有提及鸟的母亲,可以说母亲的缺席伴随着鸟的成长过程。或许大江有意这样设置,为鸟人格的发展和当下自欺人格的形成埋下伏笔。鸟6岁时向父亲提出了自我存在之问:“爸爸,出生前的一百年,我在什么地方?死后一百年,我又在什么地方?爸爸,死了以后,我会变成什么呢”[2]137,却遭到父亲的一顿暴打而忘记了死之恐怖。在父亲这一镜像强行介入下,鸟的主体性被阉割,从而将父亲作为自己的认同对象。如果根据小说的出版时间1964年11月和鸟的年龄27岁、苏联核试验等时代符号来推算的话,鸟应该出生在1937年左右,6岁时应为1943年前后,正值二战进入日本军队节节败退的后期阶段。书中提到的鸟的父亲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人使用过的手枪自杀这一信息本身就具有象征意味。拉康认为,个人主体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可分为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3个层面。现实界是指婴儿无法区分自己与满足自己需求的客体的阶段;想象界是指婴儿镜像阶段具有“想象的自我”,但尚不具有构建真正主体能力的层面;象征界则是想象的主体向真实主体过渡的阶段,“进入象征界从标志主体的演化跃入了一个转折点。象征界的代表是父亲:有鉴于象征界存在于主体之前,主体还未出生就已落到符号的支配之下,而成为自己的名字和自己家族的姓的拥有者,象征界势所必然便同父亲联系起来”[10]。在小说中,母亲的缺席使鸟自然将与自己最亲近的父亲视为镜像。父亲是一个专制的暴君式家长,鸟的主体在其影响下开始变异,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形成了投射着暴君式父亲影像的镜像。鸟陷入我是他者这一状况之中,主体被外部镜像异化而无法走出自我执著的怪圈。
在镜像阶段中,主体在后期还会陷入对自己镜像的迷恋状态。鸟在镜像阶段中已发展为自恋的状态,他“渴望独自一人达到高潮”[2]106,一直处在将他者的存在置于身后的“自体爱”状态中。也就是说,鸟迷恋的是在他内心深深刻有父亲镜像的自己,他自恋着变异后的自我,试图以父亲式的暴力控制火见子。然而,在火见子具有牺牲精神的性爱感召下,鸟开始包容他者,重视与他者的关联,进而从自我欺瞒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主体的成长。在和火见子这一他者逐渐深入的交流中,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变化。
鸟的主体因被父亲这一他者阉割而无法获得主体性,加上战争结束失去了在战场上实现自我的机会,从而生活在自己构筑的想象界中。通过与火见子真心的交流,鸟开始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一反思本身标志着其身份认同的达成。鸟发现在婴儿出生之前曾和他斗殴的那帮人并没有认出他,从而意识到已经改头换面的自己。同时,“你变了,你和你那有点孩子气的外号鸟已经不相称了”[2]200,岳父这一对鸟的肯定和赞许,也意味着他最终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
鸟等着围着婴儿热心地边走边谈的女人们跟上来,他朝妻子怀抱着的儿子的脸望去,鸟想在婴儿的瞳孔里看到映照在上面的自己的面影。婴儿的瞳孔澄清的深灰色镜面上,映现出了鸟的影子。可是婴儿的瞳孔太微细了,鸟无法细微地辨识自己的新面容。回到家后,我要先照照镜子,鸟想[2]200。
在此,希望在新的他者(婴儿)眼中看到全新自我的那种喜悦暗示着其身份认同之旅告一段落。运用镜像理论对鸟的心路历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个人的体验》就是一部描写鸟这样一个具有生物特征的自然人如何获得个人身份认同的故事。换句话说,是讲述日本战后一代青年如何认识“我”这一概念、如何建构自我这样一个带有强烈伦理色彩的故事。作为一种给予主体定位的象征物,小说中的比喻和镜像描写映照出鸟艰难的自我追寻之路。小说的镜像叙事反映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变化,极大地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对小说主题建构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三、从逃避现实到回归家庭的伦理叙事
在这部小说中,鸟和火见子都是具有严重精神创伤的人物。鸟一直对生活不满,又因孩子天生残疾备受打击;火见子因丈夫自杀一蹶不振。团野光晴指出:“透过火见子的经历可以看到,都市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暴力造就了她成为娼妇的悲剧过程,她丈夫自杀不用说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11]在此意义上,团野光晴将火见子对鸟的性安慰视为一种自我精神救赎。不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火见子这一人物形象似乎更能体现大江在人物塑造上的匠心。聂珍钊指出,斯芬克斯因子是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的有机组合,人性因子体现在人的理性意志层面,兽性因子则来自人的动物性本能,兽性因子的极度膨胀会导致人陷入伦理混乱甚至走向毁灭[12]。火见子很难说是妓女,因为火见子在二人交往中并未对鸟提出物质或金钱上的要求。从男女关系角度来看,火见子颠覆了传统社会中男性拯救女性的传统模式,客观上发挥了对鸟进行精神拯救的作用。但是,火见子为了达到和鸟一起去非洲的目的试图设法杀死婴儿,这一行为本身体现了她身上兽性因子的爆发和失控。在火见子身上,兽性因子的失控还表现为其放纵情欲导致了家庭危机和丈夫自杀,她也因此一直生活在对丈夫之死的内疚之中,生活在“多元宇宙”这一自我欺瞒的想象中。
萨特指出,自我欺瞒(自欺)是一种被规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人的实在是根本的,而同时又像意识一样不是把它的否定引向外部,而是把它转向自身。这态度在我们看来就应该是自欺”[13]。鸟和火见子均利用自欺来逃避现实,逃避自己的价值选择和道德责任。鸟遭受父亲暴力的童年经历早已使他学会了放弃自我,以自欺的态度逃避现实。在鸟最终决定接受残疾儿,受到岳父称赞时,鸟“像是压掉怨气似的”说道:“可在现实生活中生活,最终只能被正统的生存方式所强制的。即使想落入欺瞒的圈套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又只能拒绝它。就是那样吧”[2]199。不难看出,鸟对选择回归家庭这一正统生活仍心有不甘。“我们从主人公的语调中感受不到穿越黑暗的长长隧道后终于走在开阔的蓝天之下的那种明朗的肯定感和解放感,一种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感觉反倒更为强烈一些。我们不应将它与好莱坞戏剧式的喜剧结局等同。”[14]虽然大江对鸟回归正常的家庭伦理持肯定态度,但同时也为暴露这一道德表象背后存在的人性固有的复杂性留有一丝余地。
在与火见子分手之际,鸟发现自己爱上了火见子,认为“如此和自己能合得来的外人,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再遇到吧”[2]159。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描写了爱之价值的重新审视和个人自我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鸟非常清楚自己不具有火见子那种自我牺牲式的爱;火见子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预见到了鸟最终会回归家庭这一结局。将鸟的经历放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这一人格结构论中来看的话,小说的主要故事脉络就是主人公带有本能倾向的本我与拥有批判和道德功能的超我相互博弈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爱情与责任的博弈,鸟勇于承担家庭责任的选择意味着超我战胜了本我,也意味着个体的精神成长和身份认同的达成。
高桥由贵认为:“小说结尾决定避开‘欺瞒’的鸟的位相并不能直接作为‘成长’‘变化’来接受。毋宁说,他置火见子的哭泣于不顾,只回应了婴儿的声音。”[15]小说中另一人物菊比古批评鸟和7年前没有变化。眼前对火见子的哭声充耳不闻的鸟,与之前置弱者菊比古的哭声于不顾而固执于自我行动的鸟毫无二致。毋宁说《个人的体验》存在着拒绝单一解释的复杂结构。但不管怎样,在选择悖论面前,鸟最终选择回归家庭,正是因为这一伦理抉择体现了小人物身上那光彩夺目的人道主义光辉。火见子认为植物似的婴儿“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个毫无意义的存在”[2]197,让婴儿死去才是为了孩子,而鸟选择接受孩子的动机“只是不想做一个兜圈子逃避责任的男人”[2]197。也就是说,大江将一个人道主义的道德悖论摆在了读者面前,体现不同个体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在此意义上,桑原丈和认为鸟的决定“依旧是一种利己主义的继续”[16]。小说中,火见子的个人体验隐蔽在鸟的性格发展这一显性情节发展之后,成为与这一情节平行且贯穿整个小说的一股反讽性叙事暗流。讲述火见子个人体验的隐性叙事进程与讲述鸟个人经历的显性叙事一道,深化了小说主题,体现了大江对人道主义和身份认同问题的多元思考。
一般说来,自由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我行我素,其实现与他者息息相关,表现出一种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乐观向上的生命延伸。鸟在选择与残疾儿共生的同时,也最终获得了人格和道德的完整性,实现了自我身份认同。一般说来,强调个人自由选择很容易构成对他者利益的伤害而产生矛盾冲突,进而导致个人身份认同的实现往往带上了一种利己主义色彩。《个人的体验》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伦理属性,正因为没有陷入人道主义最终获胜的俗套结局之中,从而为小说阐释留下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进而使这部作品成为超越单纯的道德批判而获得了某种人性高度。
四、结语
《个人的体验》可以说是描写鸟这一“反英雄”人物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伦理叙事,其中蕴含着大江小说创作中后期的两大主题——与残疾儿(弱者)共同生活这一人性主题和“核时代人的生存”这一社会性主题的萌芽。鸟这一视点人物体现了作家试图像鸟类那样站在高处俯瞰小人物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立场。大江不仅将对个体生命的观照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而且还将其与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体验上升到社会普遍层面成为可能。通过对小人物纯粹个人体验的文学书写,大江表达了对现代个体生存悖论的深切关注以及对时代危机和充满暴力的现实世界的忧虑。小说的镜像叙事呈现了与现实空间对应的个体带有自我欺瞒色彩的精神空间,生动地描绘了主人公试图摆脱自我欺瞒,勇于面对现实的身份认同之旅,小说的空间设置、动物比喻和镜像书写高度契合了个体身份认同这一主题。无论是小说形式实验还是主题表达,《个人的体验》在大江文学创作中均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