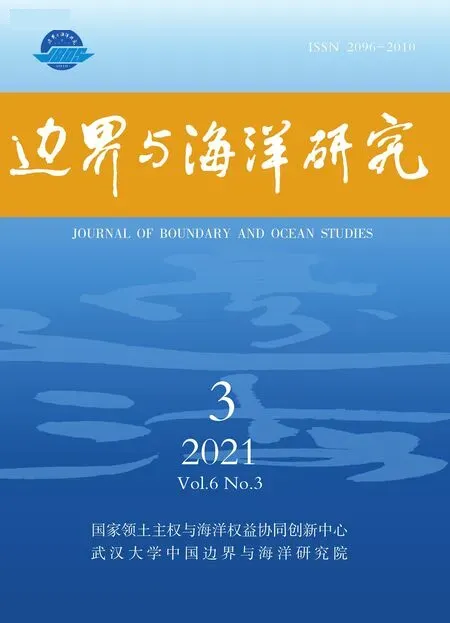英加澳新共同体:“后脱欧时代”英国的新选择?*
胡 杰
随着英国与欧盟在2020年12月24日正式达成贸易协定,历时四年多、曲折坎坷的“脱欧”进程终于划上了句号。关于“脱欧”的影响,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硕果累累,但鲜有人关注“脱欧”与“英加澳新共同体”(CANZUK)的关系。①目前,除“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的发起者和支持者的著述外,国内外学界鲜见结合“脱欧”背景专门探讨这一倡议的研究成果。少数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盎格鲁文化圈”和英联邦展开,它们对“英加澳新共同体”的考察通常停留在简单介绍层面,缺少有深度的系统分析,一般对其可行性持否定态度。“英加澳新共同体”的支持者往往又夸大了这一倡议的价值,他们更多是描绘了蓝图但未能提出有操作性的具体方案,其著述的宣传意义大于研究意义,如James C.Bennett,A Time for Audacity:How Brexit Has Created the CANZUK Option,Washington D.C.:Pole to Pole Publishing,2016等。邓肯·贝尔是近年来少有的关注“英加澳新共同体”的严肃学者,其观点颇具代表性。贝尔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这一倡议的来龙去脉,但对其基础的分析不够充分,对该倡议“重温旧梦”的定性略显武断。See Duncan Bell,“The Anglosphere:New Enthusiasm for an Old Dream”,Prospect,January 19,2017;Duncan Bell and Srdjan Vucetic,“Brexit,CANZUK,and the Legacy of Empire”,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1,No.2,2019,pp.367-382.“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起初反响并不热烈,但2016年的“脱欧”公投带动了该倡议的热度持续上升。“英加澳新共同体”的主旨是在英国(UK)、加拿大(CA)、澳大利亚(A)、新西兰(NZ)四个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国家间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特别是促成商品、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甚至是实现四个国家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跨洲际的联邦实体。①Duncan Bell and Srdjan Vucetic,“Brexit,CANZUK,and the Legacy of Empire”,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1,No.2,2019,p.368.这里的“共同体”指的是英加澳新四国间高度整合、统一协调的合作关系。当前,“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的目标是促使四国建立以商品、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联盟,而长远目标则是构筑政治联盟和防务联盟,甚至向缔造具有实体性质的邦联或联邦方向发展。在摆脱了欧盟制度和规则的束缚后,英国可以变得更加开放和全球化,②Adam Hug et al.(eds.),Finding Britain's Role in a Changing World:Building a Values-based Foreign Policy,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20,p.7.可以更方便地与在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经济模式、文化传统上相近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展深度合作。换言之,“脱欧”赋予了长期被冷遇的“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获得持续关注的契机。
一、“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历史与基础
(一)“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的由来
“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实际上是对“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概念的具体化和机制化方案。“盎格鲁文化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大体上可以认为是传统英式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社会文化等获得延续或传承的区域,基本上涵盖了今天的英联邦国家和地区。狭义的“盎格鲁文化圈”一般指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及其后裔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集合,通常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直到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这一倡议才逐步进入公众视野。2016年6月24日,即“脱欧”公投次日,美国企业家和作家詹姆斯·贝内特在《今日美国》专栏文章中率先提到“英加澳新共同体”,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主流媒体上。贝内特同时提出了建立“英加澳新联盟”(CANZUK Union)的主张,他笔下的“英加澳新联盟”是一个足以取代欧盟的政治邦联,而不仅仅只是促进四个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之间的全方位联系。③James C.Bennett,“Brexit Boosts‘CANZUK’Replacement for European Union:Column”,USA Today,June 24,2016,https://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columnist/2016/06/24/brexit-boosts-canzuk-replacement-european-union-column/86347818/,visited on 4 February 2021.2016年6月和8月,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利里科也分别在英国《泰晤士报》和加拿大《金融邮报》上撰文,提出英加澳新四个文化和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应组成一个“紧密的地缘政治联盟”,以增强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④Duncan Bell and Srdjan Vucetic,“Brexit,CANZUK,and the Legacy of Empire”,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1,No.2,2019,p.370.英国保守派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更指出,“脱欧”公投为构建一个以自由贸易、人员自由流动、集体防务及有限但高效的邦联政治结构为标志的新联盟奠定了基础,而“英加澳新共同体”则可成为继欧洲大陆和美国之后的西方文明的第三大支柱。①Duncan Bell,“The Anglosphere:New Enthusiasm for an Old Dream”,Prospect,January 19,2017,https://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anglosphere-old-dream-brexit-role-in-the-world,visited on 31 July 2020.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盎格鲁文化圈”的倡导者就一再强调英语国家在机制和特征上拥有欧洲和亚洲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宣扬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②Ben Wellings and Helen Baxendale,“Euroscepticism and the Anglosphere:Traditions and Dilemmas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Nationalism”,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October,2014,p.7.1999年12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英语人民协会(English-speaking Union)的演讲中概括了她所认为的英语民族的共同点和特征,即尊重人权、宗教宽容、恪守民主和建立代议制政府、捍卫和推广法治。她还提议建立一个英语民族组成的新联盟,将他们珍视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以促进和平与繁荣。③Margaret Thatcher,“The Language of Liberty:The Inauguration of The Thatcher Lecture Series”,December 7,1999,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8386,visited on 3 February 2021.
目前,在“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中,形成了三个最有代表性的组织,即“英加澳新共同体国际”(CANZUK International)、“英加澳新共同体运动”(CANZUK Campaign)、“英加澳新共同体联合阵线”(CANZUK Uniting)。“英加澳新共同体国际”于2017年1月建立,其前身是“英联邦自由流动组织”(Commonwealth Freedom of Movement Organization),创始人是温哥华的律师助理詹姆斯·斯金纳。2015年,斯金纳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倡议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实行人员自由流动的请愿书,参考的范本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的塔斯马尼亚协定(Trans-Tasman Travel Arrangement,TTTA)。截至2018年年中,这份请愿书已获得25万人的签名支持。同时,“英加澳新共同体国际”还主张四国缔结全面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并建立更为紧密的情报、防务和外交合作关系,扩大四国公民在“英加澳新共同体”国家内的权利。2020年10月,“英加澳新共同体国际”又向英国议会提交了关于在四国间实现人员和贸易自由流通的请愿书,主张英国在“脱欧”后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相互开放移民和贸易的正式协定,超过1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由此获得了等待英国政府官方回复的机会。④“CANZUK Petition to Receive UK Government Response”,CANZUK International,December 7,2020,https://www.canzukinternational.com/2020/12/canzuk-petition-to-receive-uk-government-response.html,visited on7 January 2021.
“英加澳新共同体运动”建立于2016年7月,总部设在爱丁堡。这一组织主张英加澳新四国在贸易、人员流动、信托、外交、安全、科研和主权等七个领域加强合作。其中,贸易合作可以“澳新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R)为范本,促进人员自由流动则可参考澳新塔斯马尼亚协定(TTTA),外交合作则可借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柏林创建“使馆联合体”,以及英国和加拿大共享在巴格达、蒙特雷、太子港的外交设施的模式。
“英加澳新共同体联合阵线”成立于2016年,其主要参与者和成员除前文提及的詹姆斯·贝内特等人外,还包括加拿大专栏作家康拉德·布莱克、英国历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加拿大政治顾问迈克尔·博纳、美国艺术评论家和社会时评家罗杰·金伯尔等。
除上述三个民间组织外,也有一批政界人士对“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表现出支持或赞赏态度,主要代表有加拿大在野党政治家安德鲁·希尔及其影子外交部长伊琳·奥图尔,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阿博特及澳大利亚前驻英高级专员亚历山大·唐纳等,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也对这一倡议颇有兴趣。①Duncan Bell and Srdjan Vucetic,“Brexit,CANZUK,and the Legacy of Empire”,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21,No.2,2019,pp.371-373;https://www.canzuk.co.uk/,visited on 27 January 2021.
一言概之,“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以贸易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为其核心主张,并着眼于将四国的合作扩大到外交、防务和安全等层面。也有学者建议,构建“英加澳新共同体”可从五个方面入手:第一,实现贸易和人员的自由流通;第二,建立统一外交;第三,开展深度军事合作,联合采购装备;第四,建立印太联合舰队;第五,订立正式的防务互助协定。②Bob Seely,“Proposals for CANZUK”,The British Interest,July 13,2019,https://britishinterest.org/proposals-for-canzuk/,visited on 30 November 2020.
(二)构建“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基础
1.历史和文化基础
“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倡议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同历史上的帝国联邦运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倡议提出在英国这个母国和殖民地之间建立更为正式的宪政联系。帝国意识的觉醒、移居殖民地的人数爆炸性增长,以及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加剧的不安全感,让这一提议在19世纪70—80年代再度得到热议。③DavidKerstein,“Greater Britai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 Victorian Idea,1865-1939”,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9,pp.129-130.“不列颠民族主义”(Britannic nationalism)构成了移民殖民地同英国结成一体的思想纽带。④John Darwin,The Empire Projec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1830-197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47.19世纪下半叶,面对外部强国的竞争和英帝国内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建立“更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的构想应运而生,其中最有代表的思想家首推迪尔克、弗鲁德和西利。
1868年,查尔斯·迪尔克出版了《更大的不列颠》一书,他因此而名声大噪。迪尔克认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白人移民殖民地肩负着传播最先进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重任,英国应该与其白人移民殖民地结成统一体,由此英国才能告别狭隘的英格兰主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⑤See C.W.Dilke,Greater Britain,London:Macmillan&Co.,Limited,1868.1871年,詹姆斯·弗鲁德首次提出可通过“帝国联邦”方案来构建“更大的不列颠”。⑥Daniel Deudney,“Greater Britain or Greater Synthesis?Seeley,Mackinder,and Wells on Britain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Er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No.2(April 2001),p.193.1885年,他通过《大洋国》一书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其“帝国联邦”方案,即“大洋国”(Oceana)是由共同血缘、利益和荣耀连接起来的联邦,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帝国。①See James Anthony Froude,Oceana or England and Her Colonies,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886.1883年,牛津大学教授约翰·西利出版了经典名作《英格兰的扩张》。他在书中表达了对帝国联邦论的支持,强调殖民地是英格兰本土的延伸,英国应通过将殖民地联合起来的方式来直面大国竞争。②See Sir 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Two Courses of Lectures,London:Macmillan&Co.,Limited,1905.
迪尔克、弗鲁德和西利都主张英国与殖民地的联合,他们观点的主要差别在于联合的方式。迪尔克笔下的“更大的不列颠”是一个由盎格鲁—萨克逊人主导的“种族帝国”,他倾向于“伦敦统治英帝国”。弗鲁德和西利则认为,殖民地特别是白人移民殖民地应该与英国本土保持联合和协作的关系,双方在共同的法律、文化和利益的联结下组成帝国联邦。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帝国联邦运动,代表性方案主要有三种,即议会制的帝国联邦、以“咨询议会”为中心的帝国联邦和以“联邦议会”为中心的帝国联邦。③张红:《英帝国史》第六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5—186页。1884年成立的“帝国联邦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网罗了一批政界精英和社会名流,他们积极宣传帝国联邦,并促成了第一次殖民地会议的召开。以推进关税改革著称的约瑟夫·张伯伦更是将帝国联邦的构想付诸实践,他主张在帝国内建立关税同盟,鼓吹通过推行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来建立联邦制帝国。不过,他的帝国联合计划遭到英国议会体制和殖民地形成新的民族认同等因素的掣肘,最终以失败告终。
当然,构建“更大的不列颠”也面临诸多反对声音,特别是以曼彻斯特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强烈反对建立统一的帝国,他们高举自由贸易和道德的大旗,强调英国与殖民地“自由和自愿”的联系。格莱斯顿执政时大力推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主张建立以感情、文化、贸易为纽带的“无形帝国”。而以迪斯累利为代表的保守党人则抨击自由党的帝国政策是分离主义,要求建立正式的“有形帝国”。值得注意的是,“无形帝国”和“有形帝国”之间并无不可跨越的鸿沟。19世纪80年代以后,在列强竞争日趋白热化、殖民扩张浪潮盛行的年代,自由党和保守党都开始追求“有形帝国”。在布尔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都得到其帝国成员的鼎力相助,这一方面增进了各自治领与英国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各自治领民族主义的发展,助长了它们的独立倾向。可以说,战争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加强帝国团结的同时也助推了各自治领的分离主义情绪,而后者是建立“有形帝国”的所有方案最终化为泡影的最关键因素。
2.政治和安全基础
构建“英加澳新共同体”的政治与安全基础,主要来源于“脱欧”后的英国希望借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地理优势和安全网络资源,提升自己的全球影响力,特别是增强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印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影响力,以及“盎格鲁文化圈”现有的双边和多边防务与安全合作机制。
首先,英加澳新有着悠久的开展防务与安全合作的历史。从布尔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倾其全力支持英国。二战结束后,随着印度独立,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英国的贡献得到进一步凸显。在战后的对日占领行动中,由于印度撤军,澳大利亚成为英联邦占领军的绝对主力。①Tim Hewish,“The Commonwealth's Call to Duty:Advancing Modern Commonwealth Defence Connections”,Commonwealth Exchange,2018,p.13.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305fde9e4b09fae2c90af6b/t/5511f96de4b01cde388ce089/1427241325819/Defence+Report+-+FINAL.pdf,visited on 29 October 2020.
其次,在“脱欧”背景下,英国致力于以印太为重点推进防务外交,更需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鼎力支持。在印太地区,为实践“全球英国”构想,英国愈发倚重澳新两国,特别是澳大利亚。近年来,英澳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如火如荼,双方在英国对澳出售26型护卫舰、两国舰艇联合巡航南海、澳大利亚为英国在太平洋地区部署航母提供支持等问题上一拍即合。英加澳新加强在自由流通、自由贸易、统一外交、军事合作和国防装备采购、建立印太联合舰队、宇航空间、构建共同防御体系等方面的合作,也是大势所趋。②Bob Seely MP and James Rogers,Global Britain:A Twenty-First Century Vision,London:The Henry Jackson,2019,pp.30-31.在“英加澳新共同体”框架下,四国可深化现已存在的军官交流和联合训练等项目,同时在军备采购、征兵、核合作等领域保持更为密切的沟通和协作。③“CANZUK Defence Alliance:Start Small,Think Big”,CANZUK Campaign,http://www.canzuk.org/canzuk_defence_alliance_start_small_think_big.php,visited on 28 January 2021.此外,五国防务组织(FPDA)也是英国深化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防务与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无论是“全球英国”构想还是未来英国的印太战略,都会将印太地区的英联邦国家作为其重要支撑点。为此,英国将持续推动英联邦提升对海洋安全等议题的关注度。④Veerle Nouwens,“Re-Examining the UK's Priorit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RUSI Commentary,March 17,2020.
最后,“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契合英国日益重视价值观外交的政策取向。“英加澳新共同体”以传统英式的自由贸易、普通法体系、议会民主制、精英教育、基督新教等为主要标志,表现出颇为浓厚的“盎格鲁—萨克逊主义”甚至“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英国在整个“脱欧”大戏开启之后,在外交叙事和政策实践中愈加重视意识形态的“站队”,反复强调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system)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或明或暗地指责、批评中俄推行“专制主义”“修正主义”“军国主义”政策,这是英国着眼于“后脱欧时代”开展价值观外交的表现。未来的英国外交在坚持一贯的务实原则的同时,会较以往更加看重意识形态的作用,高调推进价值观外交,以便为英国充分发挥其“软实力”优势创造有利条件。有学者也指出,在“脱欧”后英国更需要重视价值观和文化影响力的作用,寻求构建新的联盟关系,而这种新型联盟关系将高举以人权、法治、和平、安全、自由贸易等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大旗,而英国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获得塑造21世纪国际秩序的话语权。①Adam Hug,et al.(eds.),Finding Britain's Role in a Changing World:Building a Values-based Foreign Policy,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20,p.20.从目前的表现看,英国正着眼于与拜登政府合作推进针对中国等国的“民主攻势”,修复被特朗普撕裂的英美盟友关系,并在推进民主外交的议题上寻求获得英联邦国家的支持与合作。②Jonas Parello-Plesner,“How the UK Becomes a Global Force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in Adam Hug(ed.),Finding Britain'sRole in a Changing World:Projecting the UK's Values Abroad,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20,pp.24-25.
3.经济和贸易基础
相较于历史和文化基础、政治和安全基础,“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的经济和贸易基础是比较薄弱的,这源于无论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在英国的外贸总额中的比重都太低。单纯的“英加澳新贸易集团”不足以弥补英国因为“脱欧”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英国对三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不到3%。③Andrew Gamble,“The Brexit Negotiations and the Anglosphere”,The Political Quarterly,2021,p.3.英国也并未寄希望于通过深化同英联邦国家的经贸联系来弥补“脱欧”后的损失,更不可能将英联邦作为欧盟市场的替代选项。④Rishi Gulati,“Global Britain?Replacing the EU with the Commonwealth is fanciful”,LSE,June 18,2019,https://blogs.lse.ac.uk/brexit/2019/06/18/global-britain-replacing-the-eu-with-enhanced-cooperation-at-the-commonwealth-is-not-aviable-option/,visited on 5 August 2020.
同样地,英国也不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可预见的将来,尽管英国脱离了欧盟,但欧洲依然是英国贸易和投资最为重要的市场,美国、中国、印度、日本等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也远远超过加澳新三国。不过,对“脱欧”后的英国而言,构建一个更为机制化的英加澳新自贸区仍然是颇有吸引力的。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反全球化倾向,特别是种种“退群”行为,使得英加澳新与美国的贸易面临显著的不确定性,这也构成了四国结成更为稳定的贸易集团的动力。当然,这种贸易集团的构想并非以损害或削弱英加澳新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关系为前提,而是旨在为四国的贸易,特别是英国在“后脱欧时代”的贸易政策提供一种新的选择。更何况,“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倡议者们相信,英国在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对欧贸易翻番的事实证明,英加澳新结成贸易集团将带来彼此间贸易额的显著增长。⑤“Lilico:In What Areas Might the CANZUK Countries Work Together?”,CANZUK Uniting,https://www.canzuk.co.uk/single-post/2017/03/08/lilico-in-what-areas-might-the-canzuk-countries-work-together,visited on 4 February 2021.
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来说,构建“英加澳新共同体”可密切它们与英国的贸易往来,特别是有利于它们对英国的出口。⑥Adil Cader,“The Australian Case for Closer CANZUK Ties Post Brexit”,OXPOL,September 3,2019,https://blog.politics.ox.ac.uk/the-australian-case-for-closer-canzuk-ties-post-brexit/,visited on 10 August 2020.澳大利亚前总理阿博特就指出,“脱欧”使得英国可以摆脱来自布鲁塞尔的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束缚,促进“后脱欧时代”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商品、服务、人员等的自由流动。⑦RebeccaAdler-Nissen,Charlotte Galpin,and Ben Rosamond,“Performing Brexit:How a Post-Brexit World Is Imagined Outside the United Kingdom”,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3),2017,pp.584-585.英国也有意将扩大与英联邦国家的经贸往来,作为“后脱欧时代”贸易安排的优先考虑。①Kai Oppermann,Ryan Beasley and Juliet Kaarbo,“Brit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Brexit:Losing Europe and Finding a Role”,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4(2),2020,p.143.在英国的自贸协定谈判路线图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被置于重要地位。2020年6月29日至7月10日,英国与澳大利亚就两国签署关于自由贸易、人员流通和市场准入方面的协议进行了首轮谈判。②James Skinner,“Free Movement&Trade Talks Between Australia&UK‘Productive'”,CANZUK International,July 15,2020,https://www.canzukinternational.com/2020/07/visa-free-mobility-trade-talks-between-australia-uk-productive.html,visitedon 31 July 2020.2020年7月,英国与新西兰开始自贸协定谈判。2020年11月21日,英国与加拿大达成过渡协议,双方同意在2021年开启谈判,以争取达成一项新的、专门的英加贸易协定。英加协议也使得英国在过渡期内仍将享受加拿大—欧盟自贸区的待遇。③“UK Secures Vital Rollover Trade Deal with Canada and Agrees to Start Negotiating More Advanced Deal Next Year”,HM Government,November 21,2020,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ecures-vital-rollover-trade-deal-with-canadaand-agrees-to-start-negotiating-more-advanced-deal-next-year,visited on 30 November 2020.
2021年2月1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一意向此前已获得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支持。如果英国获准加入CPTPP,届时英加澳新将同为CPTPP成员,它们组成的统一战线将有力地增强英国在这一全球性自贸区中的话语权,并借助CPTPP扩大英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二、“英加澳新共同体”获得的机遇
(一)“脱欧”导致英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契合了“脱欧”背景下英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为英国加强与英联邦各国的经贸联系,甚至将英联邦重建成历史上的经济和政治集团提供了可能性,即“2.0版大英帝国”。④Rebecca Adler-Nissen,Charlotte Galpin and Ben Rosamond,“Performing Brexit:How a Post-Brexit World is Imagined outsidethe United Kingdom”,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3),2017,p.584.而“脱欧”本身就赋予了构建“2.0版大英帝国”的机会,这是一种帝国情怀的体现,甚至“全球英国”构想就是重建帝国迷梦的表现,当然这种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思维也必须面对众多反对声音。⑤Oliver Turner,“Global Britain and the Narrative of Empire”,The Political Quarterly,Vol.90,No.4,2019,pp.727-728.“后脱欧时代”英国种族主义深植的土壤,突出地表现为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英国的结构性衰落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边缘化地位,是“英国性”政治所处的背景。⑥SatnamVirdee and Brendan McGeever,“Racism,Crisis,Brexit”,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41,No.10,2017,p.1810.统计数据显示,有50%的英国人将自己视为英联邦公民,其中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二的多数高度认同自己的英联邦公民身份,有53%的英国白人将自己视为英联邦的一部分,保守党党员对英联邦的认同度要远远高于工党党员。①E.Elliott and S.Gaston,Behind Global Britain:Public Opinion on the UK's Role in the World,London: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2019,pp.16-17.此外,英国智库的民调显示,对英国在英联邦中保持领导地位重要性的认同(31%),要明显高于对英国在欧盟中保持领导地位重要性的认同(24%)。②Edward Elliott and Sophia Gaston,“Behind Global Britain:Public Opinion on the UK'S Role in the World”,Working Paper 2019,p.4,https://henryjacksonsociety.org/wp-content/uploads/2019/04/Behind-Global-Britain-Public-Opinion-on-the-UKs-Role-in-the-World.pdf,visited on 16 January 2021.
尽管“日不落帝国”早已分崩离析,但昔日辉煌的历史依然能激起英国本土的爱国主义热情,使英伦三岛迸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这种为昔日帝国感到荣耀和自豪的历史情结在现代英国面临的每个重大关头都体现得淋漓尽致。③Nadine Elsayed,“Make Great Britain Great Again:Populism and Nationalism in Brexit”,Perspectives on Business and Economics,Vol.36,No.3,2018,p.95.“脱欧”正是英国在21世纪面临的首个重大关头,“英加澳新共同体”即为英国人历史情结和民族自豪感的又一次集中体现。不仅“英加澳新共同体”如此,英国官方提出的“全球英国”构想同样带有浓厚的怀旧主义色彩和帝国情结。④AlecLlywelyn Frost,“Examining the Validity of a‘Global Britain'and Its Ties with the Commonwealth”,E-International Relations,July 29,2019,https://www.e-ir.info/2019/07/29/examining-the-validity-of-a-global-britain-and-its-ties-with-thecommonwealth/,visited on 5 August 2020.这两者在迎合伴随着“脱欧”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
(二)加澳新需在美国之外寻找更多选择
二战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对外关系上“疏英亲美”的倾向日趋明显,尤其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将英国排除在外,同美国建立了澳新美同盟(ANZUS)。澳新美同盟既是美国“岛链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澳新对外关系的基石。同样地,作为美国最重要的邻国,加拿大在经济、防务等领域也格外倚重美国。不过,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政府任内中美冲突的加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意在对外关系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将“重启”同英国的传统关系作为新的选择。
“脱欧”凸显了英国的中等国家(middle power)身份。英国以这种身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展开合作,有助于四方形成平等关系,也更能安抚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排除“抱团取暖”的阻力。这在当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同中国的关系面临严重波折的情况下,更能引起两国的共鸣。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也需要重新评估澳新美同盟,避免被卷入中美冲突中,⑤Louis Devine,“Australia Should Re-imagine Its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May 7,2020,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australia-should-re-imagine-its-alliance-with-the-united-states/,visited on 31 December 2020.它需要在对外关系上寻找更多的选择方案,而一个回归传统、进军印太的英国无疑是澳大利亚难以拒绝的。在经济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第一”政策导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难以为继。这对澳大利亚而言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必须拓展贸易网络,而不能只是寻求同英国签署简单的双边自贸协定。①Andrew Lilico and Tim Andrews,“It's Time for CANZUK”,Spectator Australia,1 December 2016,https://spectator.com.au/2016/12/canzuk/,visited on 4 February 2021.
香港实施国安法和华为风波出现后,“五眼联盟”(Five Eyes)在协调西方国家反对中国的立场上颇为活跃,这也使得“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似乎不再只是帝国迷梦的写照,而具有了“应景”的政治意义和可行性,即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要建立针对中俄的所谓“反威权主义联盟”。②Ben Judah,“Facing Trump,Putin,and Xi,London Needs Old Allies for New Ideas”,Foreign Policy,June 30,2020,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30/hong-kong-uk-trump-canada-australia-alliance/,visited on 10 August 2020.这种“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团结”固然主要是美国主导的结果,但离不开英国的支持和配合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追随。在这其中,作为前殖民宗主国,英国将加澳新凝聚起来的作用不可小觑。也有保守派人士指出,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拥有坚实的联合基础,“英加澳新共同体”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盎格鲁—萨克逊超级大国”。在欧盟无意遏制中国的情况下,“英加澳新共同体”可以成为美国在21世纪对抗中国的得力盟友。③Andrew Roberts,“It's Time to Revive the Anglosphere”,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8,2020,https://www.wsj.com/articles/its-time-to-revive-the-anglosphere-11596859260?mod=e2tw,visited on 10 August 2020.
(三)可借力“全球英国”获得政策支持
如果说“英加澳新共同体”还只是民间倡议的话,那么“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则已是官方构想,尽管英国尚未系统阐明“全球英国”的内涵,也未出台具体政策,但“全球英国”的主旨是英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全球国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其重点指向是印太地区,这一点已毋庸置疑。要推进“全球英国”构想,英国就必须充分利用大英帝国留下的丰厚殖民遗产,特别是要借助“盎格鲁—萨克逊兄弟”的支持。因此,构建“英加澳新共同体”符合落实“全球英国”构想的目标,它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推进“全球英国”构想的五大战略优先选项之一。④James Rogers,“How to Deliver‘Global Britain':Five Strategic Priorities for Britain's New Government”,The British Interest,July 25,2019,https://britishinterest.org/how-to-deliver-global-britain-five-strategic-priorities-for-britains-new-government/,visited on 30November 2020.反过来,“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也有望获得“全球英国”的政策支持。即便无法构建一个类似“帝国联邦”的“英加澳新共同体”,也会促进英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更深度的融合。
在现实政治中,英国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一直主张英国应与“盎格鲁—萨克逊兄弟”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他在外交大臣任上就一再表明推进“全球英国”构想的决心。2019年12月,约翰逊当选英国首相后,也公开支持英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现自由贸易和人员互通。⑤韩剑:《“全球英国”理念下的英国自贸协定谈判及中英FTA前景展望》,《国际贸易》2020年第5期,第63页。
在经贸层面,“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的核心主张是实现四国之间商品、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提升四国间的经贸合作水平。构建“英加澳新共同体”有助于英国开拓欧洲以外的市场,特别是印太市场,这同“全球英国”展望的大力发展与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的目标是一致的。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硬实力”不足的英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重视发挥自身“软实力”的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抱团发声”,共同维护英国反复强调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也是“全球英国”构想的重要目标之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指的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由历史上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和现实中的“美利坚治下的和平”所维系的。①Oliver Turner,“Global Britain and the Narrative of Empire”,The Political Quarterly,Vol.90,No.4,2019,p.730.构建“英加澳新共同体”有助于扩大英国在外交事务、国际条约和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巩固英国在国际法的解释和运用上的优势地位,充分发挥英语媒体强大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②Robin Niblett,Global Britain,Global Broker:A Blueprint for the UK's Future International Role,London: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21,p.17.顺应了英国决心通过重振英联邦来实现“全球英国”的思路。③House of Common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Global Britain and the 2018 Commonwealth Summit,London:House of Common,2018,pp.8-9.
三、“英加澳新共同体”面临的阻力
尽管“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具有一定的基础,也因为英国“脱欧”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它所面临的阻力更大,这决定了这一构想在短期内无法实现。
首先,“英加澳新共同体”的保守性、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与“全球英国”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原则存在矛盾,其浓厚的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色彩一定程度上会损害英国的国际形象。“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强调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性,在意识形态上偏向保守,特别是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种族优越感,其本质上是“五眼联盟”的继续,而且会以同西方价值观迥异的中俄为假想敌,采取更为直接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述和政策取向,助推英国的价值观外交。可以说,“英加澳新共同体”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集合体,是所谓“抵制强权政治”的共同价值观伙伴的联盟。④Andrew Hastie,“What Is to Be Done?”,in Andrew Foxall and John Hemmings(eds.),The Art of Deceit:How China and Russia UseSharp Power to Subvert the West,London: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2019,p.41.
“英加澳新共同体”不仅树立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还将印度、新加坡、南非等非白人的英联邦国家排除在外,体现出“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倾向,这不利于英国处理与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关系,⑤Andrew Mycock and Ben Wellings,“The Anglosphere:Past,Present and Future”,British Academy Review,Autumn 2017,p.44.难免会引发英联邦内部的矛盾。“脱欧”后,英联邦在英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但很多英联邦国家对英国欲借英联邦巩固其国际地位的热忱反应冷淡,也相当反感和警惕英国的新殖民主义倾向,质疑所谓的“2.0版大英帝国”。⑥Kai Oppermann,Ryan Beasley,and Juliet Kaarbo,“Brit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Brexit:Losing Europe and Finding a Role”,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20,Vol.34(2),p.143.一些英联邦国家领导人甚至怀疑英国谋求利用签署自贸协定来重演历史上英帝国剥削其殖民地的一幕,“全球英国”构想同样也被类比为“2.0版大英帝国”。①AndrewMycock and Ben Wellings,“The Anglosphere:Past,Present and Future”,British Academy Review,Autumn 2017,p.44.
即便同为“白人俱乐部”,“英加澳新共同体”的支持者也借“脱欧”一再强调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与欧陆思想的差异。激进的“盎格鲁文化圈”支持者甚至将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视为巨大的错误及抛弃英语民族的背叛行为,直接将“盎格鲁文化圈”同欧洲的制度对立起来。②Duncan Bell and Srdjan Vucetic,“Brexit,CANZUK,and the Legacy of Empire”,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1,No.2,2019,p.369.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对“盎格鲁文化圈”的机制化方案,“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与“全球英国”构想所提出的更开放、更包容、更全球化的原则背道而驰,英国不是更为国际化,而是更为内敛、保守、封闭。
其次,英国与加澳新不同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加澳新不愿削弱与欧盟的经贸关系,让建立“英加澳新共同体”缺乏足够的共同利益基础。“英加澳新共同体”更多是以血缘、情感、历史和文化等为纽带,而非以现实的利益为最坚实的基础,这一方面给“英加澳新共同体”贴上了理想主义标签,另一方面也使得其在凝聚力和组织性上面临较大的困难。
尽管欢迎与英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不赞同英国“脱欧”。“脱欧”使得英国拥有了完全的贸易政策自主权,“全球英国”的重要指向是将英国建设成为一个全球贸易型国家,但英国的这一雄心壮志受到包括加澳新在内的英国主要伙伴的质疑,它们普遍将自己同欧盟的贸易关系置于对英国的贸易之上。③Kai Oppermann,Ryan Beasley,and Juliet Kaarbo,“Brit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Brexit:Losing Europe and Finding a Role”,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20,Vol.34(2),pp.138-139.例如,澳大利亚就认识到,尽管“脱欧”使得大打历史情怀牌的“英加澳新共同体”和“盎格鲁文化圈”的热度持续上升,但不能以此来处理同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实用主义导向才最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换言之,在澳英和澳欧关系上,澳大利亚不能为了发展同一方的关系而牺牲同另一方的关系。④Laura Allison-Reumann,“After Brexit:Australia's Relations with the EU and the UK”,Global Affairs,Vol.5,NOS.4-5,2019,pp.567-568.不仅如此,广大的英联邦国家也避免将自己定位为欧盟的竞争者。对于它们而言,英国在吸引力上不及美国、中国和欧盟这样体量大得多的经济体。⑤Oliver Turner,“Global Britain and the Narrative of Empire”,The Political Quarterly,Vol.90,No.4,2019,p.731.英联邦秘书长帕特里夏·苏格兰就强调,英联邦是欧盟的伙伴而非竞争对手。⑥RebeccaAdler-Nissen,Charlotte Galpin,and Ben Rosamond,“Performing Brexit:How a Post-Brexit World Is Imagined Outside the United Kingdom”,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3),2017,p.580.
在防务与安全层面,英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同的战略重心也会影响“英加澳新共同体”的统一性,特别是尽管“脱欧”后的英国会将更多资源和注意力向印太倾斜,但欧洲和大西洋才始终是英国牢不可破的战略重点,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地缘战略核心区。①James Rogers,Core Assumptions and British Strategic Policy:Towards the Next Foreign,Security and Defence Review,London: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2020,pp.18-19.同样地,加拿大的战略重心也在大西洋而非太平洋,这与身处印太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迥然不同的。在澳新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天平中,美国甚至日本的分量都要远胜于英国。美国是加澳新最重要的盟友,这一点不会因为英国“脱欧”而发生改变。②DuncanBell,“The Anglosphere:New Enthusiasm for an Old Dream”,Prospect,January 19,2017,https://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anglosphere-old-dream-brexit-role-in-the-world,visited on 31 July 2020.
“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津津乐道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共同血缘、历史和文化纽带,也面临着族群结构改变带来的巨大冲击。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内都有以华裔为代表的大量非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移民,加拿大境内还有法国移民占主导的魁北克省,他们视自己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或新西兰人,而非盎格鲁—萨克逊人。经济联系的变化也削弱了传统的白人族群对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身份的认同。例如,澳大利亚就意识到,虽然英国依然被澳大利亚人视为仅次于新西兰的挚友,但二战后澳大利亚与亚洲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大量亚洲移民的涌入及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的历史,都显著淡化了澳大利亚人对英国作为故土的情感。简言之,构建“英加澳新共同体”必须正视四国利益取向的显著差异性,必须在四国间营造强有力的共同利益纽带,而不能只是单纯地回顾历史和传统。③Adam Hug,“Introduction:Partnerships for the Future of UK Foreign Policy”,in Adam Hug,ed.,Finding Britain's Role in a Changing World:Partnerships for the Future of UK Foreign Policy,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20,p.13.
最后,英国尚未厘清“后脱欧时代”对外关系的思路,突出表现就是迄今仍未对“全球英国”构想的具体内容予以明确阐释,这决定了“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发展前景存在诸多变数。
在对外政策上,英国在“脱欧”后的自我定位尚不明晰,它所畅想的全球贸易国家、大国、美国的忠实盟友、欧盟的地区伙伴和英联邦领导者等角色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国际社会对此也充满疑虑,这些都会促使英国在“脱欧”后可能不是走向更开放而是更孤立。④Kai Oppermann,Ryan Beasley and Juliet Kaarbo,“Brit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Brexit:Losing Europe and Finding a Role”,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4(2),2020,p.135.例如,促使英国“脱欧”的一大动力是收紧移民政策,提高移民门槛,避免现行欧盟框架下的无限制移民,转而从英联邦国家引入更多高技术移民。⑤James McBride,“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Brexit and the Future of‘Global Britain'”,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rch 5,2020,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ommonwealth-nations-brexit-and-future-global-britain,visited on 4 August 2020.然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英联邦国家要求英国放宽移民政策,特别是印度希望英国为印度公民提供更多前往英国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这与英国控制移民的政策相矛盾。⑥RebeccaAdler-Nissen,Charlotte Galpin,and Ben Rosamond,“Performing Brexit:How a Post-Brexit World Is Imagined Outside the United Kingdom”,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3),2017,pp.580-581.此外,伴随着“脱欧”,英国建立由盎格鲁—萨克逊白人组成的自由经济区的政策取向符合英联邦中少数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但此举很难取悦英联邦中的诸多欠发达国家,它们将欧盟作为其产品进入英国市场的捷径,“脱欧”会让其对欧和对英贸易蒙上阴影。①Rebecca Adler-Nissen,Charlotte Galpin,and Ben Rosamond,“Performing Brexit:How a Post-Brexit World Is Imagined Outside the United Kingdom”,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3),2017,p.585.“英加澳新共同体”在经济上就是想象中的英联邦自贸区的“盎格鲁—萨克逊化”,它难免会触动其他欠发达的英联邦国家的利益,影响英联邦的团结。
除受到英国对外关系思路不明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的挑战外,“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本身也还需进一步凝练方向、细化方案。目前,关于“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虽有不少宏观阐述,但缺少具体和可操作性的方案,这一倡议仍主要停留在利用网站和社交媒体进行宣传的层面,未能争取到强有力、明确的政治支持,也难以说服公众。在叙事上,“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的相关分析和解释都浮于表面,不够深入和有吸引力。此外,尽管“英加澳新共同体”的支持者都强调这一倡议的创新性,宣传其并非简单地“复兴大英帝国”,但一直无法对“英加澳新共同体”的新意予以有力的说明。无论如何包装和解释,“英加澳新共同体”都难以摆脱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等“历史负担”。
四、总论
“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同历史上的帝国联邦运动一样,是在英国面临重大危机或挑战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如果说“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最早出现的20世纪60年代,英国是在非殖民化运动的浪潮下不断收缩、逐渐由“全球主义”退回到“欧洲主义”的话,那么这一倡议再度受到关注的2016年则是英国“脱欧”大幕开启的一年。英国告别欧盟国家身份后将何去何从?如果不愿就此“荷兰化”的话,英国将通过什么路径重新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全球性强国?对此,“全球英国”构想提出了宏大美好但不甚清晰的展望,而“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则给出了相对明确的思路,即以贸易和人员的自由流通为抓手,促进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深度融合,进而将一体化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外交、防务、安全等领域。在逻辑关系上,我们可以将“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看作落实“全球英国”构想的一个具体方案,加澳新在不同程度上也可将推进“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作为搭上“全球英国”构想的顺风车、实现各自利益的可行路径。虽然“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倡议者一直讳言帝国,以避免引起外界的反感,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终极目标是组建事实上的“盎格鲁—萨克逊联邦”,这无疑是历史上帝国联邦构想的翻版。
目前看来,“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还是一个抽象、理想化的构想,它受制于各种障碍、阻挠和挑战,距离实现憧憬中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倡议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在“后脱欧时代”,以英联邦为依托,特别是通过全面深化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前自治领的合作来推进“全球英国”构想无疑是英国的必然选择。“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倡议者也深知建立“2.0版大英帝国”是不切实际的,也会引起诸多非议,因此将这一倡议的主基调确定为“合作”而非“联合”,①“Lilico:What Other Countries Might Eventually Join CANZUK?”,CANZUK Uniting,https://www.canzuk.co.uk/singlepost/2017/03/10/Lilico-What-other-countries-might-eventually-join-CANZUK,visited on 4 February 2021.而且反复强调英加澳新四国在感情、血缘、文化上的相通性,其主张近似19世纪自由党的“无形帝国”构想,这是一种现实的考虑。尽管在短期内,英加澳新的合作是松散、碎片化和框架性的,合作的方向、领域和程度未来究竟如何发展也有待观察,我们更不能就此断言英加澳新已踏上了建立联邦制国家的道路,但无可置疑的是,在前景不明的“后脱欧时代”,“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为英国巩固全球性大国地位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思路,它在未来很长时间都会是对英国颇具吸引力的选项。
就国际影响而言,“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是典型的西方价值观和利益导向,这一倡议若能逐步付诸实践,将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竞争渐趋激烈的今天,不可避免地使英加澳新四国更深度地介入印太事务,这在助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同时,也会加剧印太地区的大国博弈甚至对抗,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另一方面,“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始终带有浓厚的“盎格鲁—萨克逊集团”色彩,这种排他性的“小圈子主义”同全球化的发展潮流背道而驰,难免会给世界多边主义进程带来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