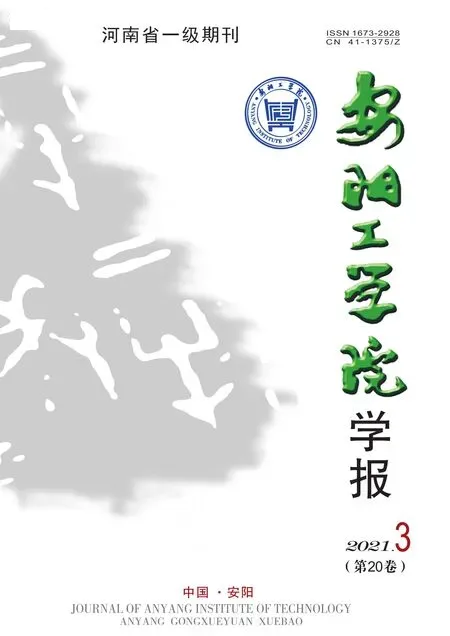新业态背景下劳动者权益的保障
薛 韵
(四川工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成都 611730)
在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新经济、新业态等不断涌现,社会就业环境、劳动就业方式、劳动者权益保障方式等发生了深刻变化。2017年国务院发布就业创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新经济、新产业发展,建立适应新经济和新产业的企业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所以应当从新经济、新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劳动者权益保护所产生的新变化、遭遇的新挑战。
一、新业态催生新的劳动就业形态
在经济新常态下落后产能、过剩产能等逐步被淘汰,新产能、新业态等不断涌现,各种新型劳动就业关系不断出现,这些新型劳动就业关系往往以“互联网+”为依托,成为释放新产能、发展新经济、激发新消费的重要方式。
(一)新业态创造许多崭新的工作岗位
从宏观背景看,中国正处于经济深度转型期,钢铁、煤炭、化工等传统行业日渐式微,互联网、人工智能、生产服务业等新经济蓬勃发展,这种经济深度转型必然带来社会就业、工作岗位、就业方式的深度变革。新业态、新经济和新就业的背后,是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要素智能化、数字化和信息化,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多种分工体系相互协作、多种就业方式相互结合的新局面。随着网络平台和网上消费的广泛普及,劳动就业呈现出去雇主化和平台化的发展趋势,如共享经济、创客经济、自由职业者等新就业模式越来越多,快递员、网络主播、外卖员、网店店主等新就业方式和工作岗位不断涌现。此外,网店卖家、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都成为新业态下比较典型的职业,这些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往往工作场地不固定、收入不稳定、自由度较高,给传统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许多新挑战。在经济新常态下产生的新工作岗位不仅涉及互联网行业,还涉及社会服务、家政服务、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如创业咨询师、形象设计师、珠宝首饰评估师、景观设计师、宠物健康护理员、数字视频合成师等。
(二)新职业带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
从总体上看新业态使劳动就业呈现出形式灵活化、工作碎片化、组织方式去中心化等新特征,对传统的雇主组织劳动生产、固定工作场地上班的劳动就业构成较大挑战。以某网约车平台为例,它最初只是为了方便人们出行而开发出租车服务平台,此后逐步将业务拓展到私家车领域,从而为私家车业主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某外卖平台是以在线外卖订餐、送餐为主要业务的平台,为社会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帮助无数外卖小哥实现了人生理想。大量就业人口涌向互联网、电商、生态旅游、共享经济等,也使社会就业方式变得更加灵活,加之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让隐性就业、隐性失业等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些不仅给失业就业统计带来巨大挑战,也给市场监管、社保体系等带来许多新问题。显然,在新经济、新业态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劳动关系范畴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并且给新业态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许多新挑战。
二、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发展状况
在经济新业态下就业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灵活就业、自主择业等成为崭新的就业形态,这些为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新业态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仍不够完善,面临劳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社会保障体系落后、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
(一)劳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监管难度比较大
在人力资源市场上,雇主想要获取雇员充分的工作信息,但是求职者无法将所有信息完全呈现给雇主,很容易带来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与雇员都要进行逆向选择,然后两者之间会形成较为稳定的劳务关系,这些也是开展劳动监管的重要基础。但是在新业态和新经济下,劳动就业方式越来越复杂,市场监管难度不断增加。从总体上看,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劳务关系较为稳定,劳动监管也比较容易,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比较简单。但是在“互联网+”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市场信息获取及传播越来越便捷,人力资源市场的中间环节不断减少,劳动者择业就业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多,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增加了劳动保障的监管难度。如在互联网环境中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店卖家、网络主播等,他们与平台之间是松散的劳务关系,往往是按照任务量结算费用,这些增加了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监管难度。此外,新经济和新业态往往有较大的虚拟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劳动就业中的“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高技术含量和高工资待遇的岗位、低技术含量和低工资待遇的岗位不断增多,中间岗位数量逐渐减少,劳动力市场上“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这些都给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二)就业方式不确定性强,法律法规不健全
新经济、新业态的出现并未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就业方式和就业形态,比如传统劳动力市场上的季节工、临时工等灵活就业者,与新业态下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网络主播等就有许多相似之处,这项职业多是技术含量低、非全日制的,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劳动权利常常遭到雇主或平台的侵犯。在传统劳动环境中,季节工、临时工等常遭到雇主的刁难,工资收入无保障;在新经济业态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常遭到公司或平台的刁难,劳动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此外,快递员、送外卖等职业收入水平较低,收入不稳定性强,职业发展空间比较小,从业者多是受教育程度低、劳动技能缺失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多生活于社会底层,多是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没有覆盖的对象,其劳动者权益往往难以得到充分保护。许多新就业形式中,劳动标准、劳动合同等比较少,在发生了劳资纠纷时往往无法依靠法律法规解决,导致劳动纠纷、矛盾冲突等时有发生,这些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许多隐患[1]。
(三)劳动关系更加灵活,劳动保障制度落后
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新业态、新经济等不断涌现,这些对企业用工制度、市场监管机制和劳动就业制度等带来较大挑战,并因此带来许多矛盾冲突。在服务业发展中仍面临许多行业垄断、部门垄断问题,导致民营资本、中小企业等无法进入相关领域,并因此带来劳动就业需求与行业岗位供给不匹配问题。此外,在新经济、新业态下,就业方式和就业形态等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但是政府的监管理念、方法和政策等不能适应这些新变化。比如有些劳动者要求在正常工作之外有偿加班,有些劳动者希望从事无拘无束的自由工作,但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导致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保护无法可依。再如有关部门对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外卖员等新职业的劳动权益保障立法较为滞后,在行政执法中常面临无法可依、法律漏洞多等问题,这些也给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新挑战。
三、创新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
新业态和新经济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也给市场行为监管和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带来新挑战。所以要正视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建构与新经济、新业态相适应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
(一)推动劳动者权益保护立法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方式等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出现了许多快递员、网络主播、外卖员、网店店主等新职业,这些给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诸多法律挑战,为此,应当转变劳动者权益保障理念,从新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的现状出发,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立法工作,建立与新经济、新业态相适应的劳动者权益法律保护体系[2]。首先,要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提高法律对新劳动关系、就业方式的适应性和规范性。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工资支付暂行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规范,将新劳动关系、新就业方式等纳入法律规范的规制范围之内,有效解决新业态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的法律问题。要将共享经济、网络经济等模式下的劳动关系纳入法律范围,提供便于双方执行的法律标准、政策规范等,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其次,应当加强新劳动关系的立法工作,完善劳动监察的配套政策和行政法规,建立与新经济、新业态、新岗位等相适应的劳动监管机制。要健全劳动监察制度、劳动纠纷仲裁机制等,充分保障新经济下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的劳动权益。
(二)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如失业保险统筹层次较低,失业金领取比较困难,许多灵活就业人员无失业保险等。医疗保险制度、工伤制度、养老制度等也面临着与失业保险制度相似的问题。所以应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广覆盖、低保障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将新业态下的新型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范围。完善网店店主、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职业的社保、医保、养老等制度,为新经济下的自由职业者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还应当将“平台+个人”的劳动关系纳入劳动监管范围,保护不同阶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新业态下的劳动者能够获得法律庇护。比如应当明确平台型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中的具体责任,完善网络平台和新从业人员之间的劳务关系、法律关系等,为新业态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提供法律依据。此外,政府还应当大力支持商业保险体系建设,支持劳动者购买商业性质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为劳动者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劳动关系越来越复杂,新业态中就业者的工伤保险、养老保险等复杂多样,面对复杂多变的劳务关系,政府应当大力支持商业保险体系建设,鼓励高收入的自由职业者参与商业保险,以商业化的方式保障劳动者权益。
(三)不断完善劳动监管模式
新业态的增长速度和复杂程度远超社会预期,新就业模式、新劳动关系等重构了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调整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建立与新经济、新业态相适应的劳动监管模式。应当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劳动监测体系,通过数据分析、人工算法等分析新业态下劳动者就业规律和趋势,为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建设提供决策参考;还可以利用对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建立劳动信用平台,加大对劳动就业领域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比如网约车司机、网店卖家、外卖员等从业者的工作数据在网络平台上都有记录,这些为行政部门的劳动监察提供了充分的数据支持,所以有关部门应当大力挖掘网络数据信息,建立劳动监察的云监督平台,为劳动执法、劳务纠纷仲裁等提供法律依据。此外,政府应当加大劳动督查、劳动执法的力度,严厉查处各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切实保障新业态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整治执法部门的不举报不查处、劳动执法不作为等问题,建立劳动执法问责制;应当加强劳动仲裁、劳资纠纷调处等工作,切实保护新业态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3]。
(四)建立多元劳动服务体系
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保护,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力量、司法力量等,还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体、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应当提高全社会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意识,引导企业和劳动者自觉遵守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还应当发挥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网络舆论的监督作用,促使劳资双方自觉尊重法律法规。应当发挥微信、抖音、微博等自媒体在劳动者权益保障中的积极作用,以自媒体平台宣传劳动权益保障法律法规,提高新业态从业者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等[4]。要发挥工会在新业态下的劳动者权益保护职能,将工会组织打造成维护和谐劳动关系的工作主线,最大限度地将新业态下的劳动者纳入工会组织,以工会组织为新业态劳动者维权,将各种社会不和谐、不安全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应当积极探索新经济、新业态下的工会组织建设,推动工会组织网络化、平台化建设,将新经济从业者、自由职业者等纳入工会体系之中,充分发挥工会在新经济、新业态中的劳动者维权功能[5]。
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保护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和新事物,也是保护新型劳动关系和劳动者权益的重要内容。所以应当高度重视新业态下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完善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及监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