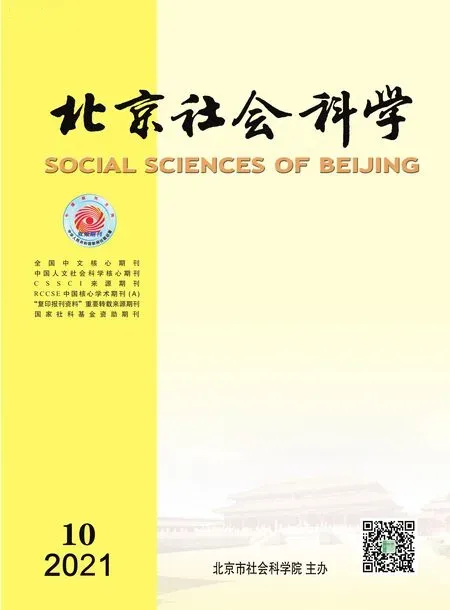论王绩文学史地位的升格及价值建构
龚 艳
一、引言
王绩以《野望》一诗千古留名,王夫之赞曰:“天成风韵,不容浅人窃之。”[1]闻一多称该诗“不愧是初唐的第一首好诗”。[2]王绩是初唐的重要诗人,现在看来似无疑义。然而,王绩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认同。两《唐书》将王绩列入《隐逸传》,便是明证。这种局面直至高棅的《唐诗品汇》选录王绩诗才被打破。其后,“诗必盛唐”的诗学观及建设“新文学”的思潮共同完成了对王绩诗学价值的建构,王绩的文学史地位遂得以确立下来。这背后传达的,是一个诗人的价值始终与时代意识相维系,诗人只有符合时代的需要才能被文学史接纳,而文学史也在主动建构出一个符合时代意识的诗人。以王绩为个案,可以审视其他作家在文学史上的接受问题,亦能窥见作家与文学史之间进行的双向互动。这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文学史、作家、作品这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
二、隐节既高:王绩隐士人格的凸显与诗学价值的掩弊
王绩诗在唐代并没有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唐代文人欣赏的是王绩作为隐士的精神志趣。王绩的诗作由其友人吕才蒐辑成编,并为之作序。吕才在序传中娓娓叙述王绩的仕隐经历以及“纵意琴酒”的风流韵事,对其诗文只字未评。时隔百余年,陆淳阅览王绩的文集后,为突出王绩“乐天之君子”的形象而将文集里的“有为之词”大幅删减。二者皆为王绩的文集作序传,却不关注其诗文,不是很可怪吗?这说明,他们对隐士王绩的认可远大于对诗人王绩的认可。这种认识在唐代其他文人身上亦能得到证明,审察唐人称引王绩的诗文,可见唐人对王绩的接受多集中在隐士形象的层面,如白居易赞赏王绩的隐行,其《九日醉吟》云:“无过学王绩,唯以醉为乡。”[3]柳宗元向往王绩的东皋之隐,其《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云:“四支反田亩,释志东皋耕。”[4]刘禹锡在《王公神道碑》中评价王绩:“议者谓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间,君子称之,虽四夷亦闻其名字。”[5]刘禹锡之言充分证实了王绩在两百年间都以高尚的隐士闻名。《旧唐书》将王绩列入《隐逸传》,是对王绩隐士身份的盖棺定论。王绩的隐士身份在历史定格的背后,显示的是唐代主流文人群体对王绩诗的轻忽。由此可以说,在唐代文人眼中,王绩的身份主要是一位隐士,而不是诗人。
到了宋代,王绩的隐士形象进一步向士人群体渗透,而其诗的价值仍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随着意识形态领域内儒释道三教的融合,隐逸成为宋代时代精神中被普遍推崇的价值观念之一。王绩的隐士形象引起宋人的普遍注意,其中的代表便是苏轼。他在诗作中多次称赏王绩的隐逸之行,甚至将其与陶渊明并举,如其诗《和陶归园田居》云:“斜川追渊明,东皋友王绩。”[6]苏轼不仅欣赏陶渊明的隐者高行,对陶渊明的诗作亦不遗余力地赞美。苏轼虽欣赏王绩,却未逸出隐逸的范畴,如“且向东皋伴王绩,未遑南越吊终军”[7](《会饮有美堂答周开祖湖上见寄》),“谏苑君方续承业,醉乡我欲访无功”[8](《次韵朱光庭初夏》)。苏轼在《书东皋子传后》中盛赞王绩的风雅逸趣,对其诗文不置可否。从此可以看出,苏轼主要接受的是王绩作为隐士的一面,而非其诗作所具有的审美内涵。苏轼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宋代主流文人群体对王绩诗的态度,翻检宋人述及王绩的话语,王绩大多是以隐士的面貌而出现,王禹偁云:“伯伦酒德,披文见意。王绩醉乡,含章遁世。”[9](《著作佐郎赠国子博士鞠君墓碣铭》)刘克庄:“王绩何曾醉?刘蕡本不风。”[10](《再和四首》)我们看到,宋人对王绩的接受仍停留于隐士形象的层面,这背后体现的是宋人对王绩诗作本体价值的忽视。
概而言之,王绩在唐宋时期以隐名显世,其诗名不显。唐宋文人虽然在诗文中流露出对王绩的欣赏,但立足点在隐逸的范畴之内。陶渊明最初亦被视作隐士,至其诗获得广泛认同后,诗人便成为他的第一属性。王绩亦如此,其诗学价值未获得唐宋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隐士便是他的第一身份。至其诗学价值逐渐得到认可后,王绩的隐士身份遂开始受到质疑,如四库馆臣云:“《新唐书》列之于《隐逸传》,所未喻也。”[11]在后来的文学史中,王绩亦被当作初唐的重要诗人进行书写。王绩的隐士形象被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其实就是王绩的诗学价值被发现与构建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依靠学术思潮的加持来完成。
三、肇启盛唐:“诗必盛唐”的学术思潮与王绩诗学价值的构建
南宋严羽提出以盛唐诗为宗的理论主张,再经由明代复古思潮的推动,盛唐诗逐步成为诗学领域的典范,如宇文所安所言:“以盛唐诗为正统的观念时不时受到谨慎地限定或激烈地反对,但它始终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其他见解都围绕着它做文章。”[12]诚然,在盛唐诗成为诗学领域的权威后,之后的诗学主张或是“诗必盛唐”的理论产物,或是对此的延伸与反拨,基本都是“围绕着它做文章”。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明清文人挖掘出王绩诗与盛唐诗的诗学共性,视其为盛唐之音的先声,带来王绩在文学史上的关键转变。
高棅《唐诗品汇》选录王绩诗若干,将其列于“正始”,是王绩进入诗学批评领域的关键。《唐诗品汇》之前的唐诗选本甚少选王绩诗。可见的如元代杨士宏《唐音》选录了一首王绩诗,并归于“遗响”。较之于《唐音》,王绩在《唐诗品汇》中的诗学地位有了明显提升。《唐诗品汇》五言古诗类选王绩《古意》《田家》,五言绝句类选王绩《过酒家二首》,五言律诗类选王绩《野望》,五言排律类选王绩《赠学仙者》。从数量而言,王绩诗一共入选六首;从诗体上说,所选诗涉及王绩所作五古、五绝、五律、五排;从定位上而论,所选王绩诗全部归于“正始”之列。由此可见,高棅已经开始重视王绩的诗学价值。
王绩诗之所以得到高棅的重视,是因为高棅具有建立在诗歌本体价值上的发展意识。高棅并不是孤立地看待唐诗发展的各个阶段,而是着重于把握唐诗各个阶段之间的纵向联系。因此,初唐诗作为盛唐诗发展的起始阶段也具有了关键意义。我们看到,高棅在杨士宏《唐音》的基础上有意加大了初唐诗在唐诗史上的权重。首先,《唐音》的“始音”部分仅选王、杨、卢、骆四家诗,而高棅增录了大量初唐诗人;其次,高棅将“始音”之名易为“正始”,“正”字之冠显示出高棅对初唐诗格走向盛唐正格的肯定。[13]王绩诗作为初唐风格的组成部分受到高棅的重视在情理之中,但更重要的是,王绩诗与盛唐诗具有某些诗学共性。从高棅选录的王绩诗可见出,高棅正是发现了王绩诗具有与盛唐诗相似的诗体特征,才有意识地突出了王绩的诗学地位。如高棅所选《野望》一诗,已初具唐律的诗体特征,可视作“唐代五律的开新之作”;[14]《过酒家》一诗“浑是上继嗣宗、渊明,下启王维、李白的”。[15]由此见出,选录王绩诗是高棅建立以盛唐诗为中心的唐诗发展体系的结果。高棅选录王绩诗的意义之一在于将其引入诗学批评领域。《唐诗品汇》在后世基本成为士人必读的唐诗选本,如胡应麟云:“至明高廷礼《品汇》而始备,《正声》而始精,习唐诗者必熟二书,始无他歧之惑。”[16]自《唐诗品汇》出,明代几部重要的唐诗选本如《唐诗选》《唐诗归》《唐诗镜》皆收录王绩诗作,使得王绩在诗学领域的地位日益稳固。意义之二在于高棅将王绩置入唐诗发展史上的“正始”之位,奠定了后人构建王绩诗学价值的基础。后人延续了高棅的诗学逻辑,在诗律和诗风上发现王绩诗对盛唐诗的贡献,从而完成其诗学价值的建构。
杨慎将律诗上溯至王绩,指出其诗乃“沈、宋之先鞭”,“诗律又盛”成为明清文人肯定王绩诗学价值的重要方面。前人往往将律诗的成型归功于沈、宋,杨慎则认为王绩在沈、宋之前已开唐律之先声。杨慎明确指出王绩在律诗上的肇启之功,其评曰:“王无功,隋人,入唐,隐节既高,诗律又盛,盖王、杨、卢、骆之滥觞,陈、杜、沈、宋之先鞭也。”[17]杨慎所谓的“陈、杜、沈、宋之先鞭”,正是着眼于王绩在律诗发展进程中起到的承启作用。首先从七律来讲,王绩的《北山》已基本符合七言律的诗体特征,该诗云:“旧知山里绝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时返,仲叔长游遂不来。幽兰独夜清琴曲,桂树凌云浊酒杯。槁项同枯木,丹心等死灰。”[18]前六句在属对上基本符合七言律的要求,只不过后两句杂以五言。杨慎将此诗视为“七言律之滥觞”,确为中的之论。其后的学者亦认识到这一点,王夫之直言“七言律诗应当以此为祖”:“如此首前四句,句里字外俱有引曳骞飞之势,不似盛唐后人促促作辕下驹也。故七言律诗亦当以此为祖,乃得不堕李颀、许浑一派恶诗中。”[19]赵翼亦认为该诗:“皆七言属对,绝似七律,惟篇末杂以五言二句耳。”[20]再者,王绩的《野望》一诗几乎已是成熟的五言律诗,被普遍视为唐代五言律诗的开山之作。旧题李攀龙《唐诗选》承继《唐诗品汇》而来,[21]不过在《唐诗品汇》的基础上做了一番严格筛选。其结果是王绩的《野望》不仅被保留,且位于五言律诗开卷第一首,紧邻其后的是杨炯、王勃、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等人。《野望》的诗体价值亦得到清人的肯认:王夫之《唐诗评选》五言律诗选录《野望》并评之“天成风韵,不容浅人窃之”,[22]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认为《野望》“五言律,前此失严者多,应以此章为首”,[23]姚鼐《今体诗钞》亦列《野望》为五言今体诗开卷第一首。由此可以看出,王绩的“诗律又盛”获得了明清文人的普遍认同。杨慎通过建立王绩与沈、宋的诗学线索,打通了王绩诗与盛唐诗的联系,从而将王绩在唐诗发展历程中的位置具体化。王绩肇启唐律,促进律诗在沈、宋等人手中定型,最终迎来盛唐诗的高潮,这便是王绩诗学价值得以生成的理论逻辑。
何良俊则指出王绩诗呈现出劲挺、真率的面貌,直与盛唐诗的气息相通。其《四友斋丛说》对王绩诗如此评价:
唐时隐逸诗人,当推王无功、陆鲁望为第一。盖当武德之初,犹有陈、隋遗习,而无功能尽洗铅华,独存体质,且嗜酒诞放,脱落世事,故于性情最近。今观其诗,近而不浅,质而不俗,殊有魏、晋之风。[24]
何良俊以“尽洗铅华”评价王绩诗,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王绩诗摆脱辞藻的浮华,具有“质而不俗”的诗歌风貌。唐初诗坛弥漫着堆砌辞藻之风,如闻一多先生言:“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辞藻的时期……连诗的制造也是应属于那个范围里的。”[25]王绩却挣脱时习,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子,其《九月九日赠崔使君善为》一诗:“映岩千段发,临浦万株开。香气徒盈把,无人送酒来。”[26]语言素朴自然、清新明快,而韵味自显,甚至“有点盛唐山水诗的气味”。[27]黄汝亨览其诗文后,曰:“吾辈净眼读一过,甚为爽然胜读《鵩鸟赋》远矣。”[28]曹荃读其诗,亦觉“如吸风饮露,疏快宜人”。[28]所谓的“爽然”“疏快”正是王绩诗质朴无华的体现,而这种艺术特质直接与之后的审美风尚相接。“四杰”与陈子昂等人在创作中扫除雕琢风气,而回归内容的充实便是印证。二是王绩诗抒发真情、兴寄深远,呈现出遒劲的诗歌风貌。这一点可以参考何良俊对王绩的另一段论述:
唐初虽相沿陈隋委靡之习,然自是不同,如王无功《古意》、李伯药《郢城怀古》之作,尚在陈子昂之前,然其力已自劲挺。盖当兴王之代,则振迅激昂,气机已动,虽诸公亦不自知也。孰谓文章不关于气运哉?唐人诗如王无功《山中言志》……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真率?若后人,便有许多缘饰。[29]
首先,何良俊以“劲挺”“激昂”“真率”等词语来评价王绩诗,表明王绩诗的风貌已经超越了初唐而与盛唐诗的气息相通。再者,所谓的“尚在陈子昂之前”,则点明了王绩的诗学史意义。陈子昂提出的兴寄与风骨,为盛唐诗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而王绩诗在此之前就已隐含兴寄与风骨的创作特征,如高出《黄刻东皋子集序》认为其诗“喻旨目前,高寄象外,闲适自得,兴远理微”,[30]《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其诗“《石竹咏》《赠薛收诗》,皆风骨遒上”。[31]如果我们认同陈子昂是促进盛唐诗到来的关键人物,那么“王绩—陈子昂—盛唐诗”的逻辑关系就可以打通,王绩对盛唐诗的肇启之功也可以落实。只要盛唐诗的核心地位存在,这种逻辑关系便能够成立。如清人吴乔言:“王绩《野望》诗,陈拾遗之前旌也。”[32]《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古意》六首,亦陈、张感遇之先导。”[33]皆通过构建王绩与陈子昂的承接关系,来确立王绩的诗学价值。由此可见,王绩的诗学价值取决于其诗对盛唐诗的先导作用,而王绩的诗学地位则是由他在盛唐诗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具体位置来明确的。
王绩从隐士形象到作为肇启盛唐之音的关键诗人为世人肯定,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转变正传达出主流学术思潮对作家价值的融入与建构。明清文人对王绩诗学价值的构建主要沿着两条线索:第一是发掘王绩诗对肇启盛唐诗所起的作用,这体现在王绩诗在诗体和风貌上促进了盛唐诗的形成;第二是通过串联王绩诗与盛唐诗的诗学线索将其在诗学史上的位置具体化,这体现在王绩扬沈、宋之先鞭,启陈子昂之滥觞。总之,王绩诗的价值是依靠其诗与盛唐诗的诗学共性来获得。四库馆臣云:“(王绩诗)能涤初唐俳偶板滞之习,置之开元、天宝间弗能别也。”[34]这是官方在以盛唐诗作为审美参照的前提下,对王绩诗给予的高度肯定。可以说,明清文人在“诗必盛唐”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下,以盛唐诗的价值标准对王绩的诗学价值进行了建构,从而使得王绩完成了其文学史地位的关键转变。
四、反抗宫体:建设“新文学”与王绩文学史地位的奠定
明清文人将王绩诗引入诗学批评领域,明确其对盛唐诗所做的贡献,无疑促进了王绩文学史地位的提高。然而,王绩在初唐诗坛的重要性并没有体现在早期的文学史书写中。早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作对王绩的着墨皆极其有限,对其人其诗皆不作过多评价。兹举王梦曾《中国文学史》(1914)为例,他专设一节探讨古今体诗格之成立,论及除王绩以外的多位初唐诗人,将唐代诗格之始成归于“四杰,陈、杜、沈、宋整齐之功也”。[35]这说明在早期文学史家的眼中,王绩的诗学地位尚不足以在文学史中留下重要笔墨。客观而言,王绩的文学史地位虽有所提高,但其对盛唐诗的贡献始终难与陈、杜、沈、宋等人比并。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是王绩在文学史发展历程中的又一转捩点。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将王绩作为初唐的重点诗人进行论述,将其视为七世纪中出现的“三五个白话大诗人”之一,大大提升了王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改变了此前文学史著作中突出书写“四杰”的模式,将“四杰”作为“王绩”的附论。可见,王绩在文学史中由之前的一笔带过转变为专门的论述,由初唐无足轻重的诗人一跃变为最值得书写的诗人之一。胡适云:“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不过是酒徒与自命为隐逸之士的诗而已。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36]显然,胡适不认同以盛唐诗为标准的价值观念。那么,胡适是如何对王绩的诗学价值进行重建的呢?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白话”作为文学史书写的核心内容和价值标准,试图冲破传统的文学史观以建立新的文学观念,是王绩诗完成价值重构的关键。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的文学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与挑战,“整理国故”“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几乎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胡适开创性地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理论主张,成为王绩诗进行价值重判的契机。首先,胡适以“白话”作为文学史书写的核心内容,意味着评定作家的价值标准发生了根本变化。胡适所谓的“白话”指的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不加粉饰的话”以及“明白晓畅的话”。[37]从这样的价值标准出发,王绩就不再是盛唐之音的肇启者,而是陶渊明的继承者,因此被视为文学史上的“白话大诗人”之一。其次,在文化运动的时代语境下,胡适认为王绩诗具有反抗宫体的精神内涵,这与倡导革命的胡适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白话文学史》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文学史本身,其牵系的是作者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抗以及追求进步的革命意识。[38]胡适所构建的白话文学是为了与“传统的死文学”相对立,宫体诗作为“死文学”阵营的一员必然成为胡适的革命对象。因此,胡适不会建构王绩诗与盛唐诗的联系,而是将王绩上溯至陶渊明,寻求二者在反抗宫体上的一致性。审视胡适对王绩的评价,他将王绩视作陶渊明的同盟,如王绩“有点像陶潜,他的诗也有点像陶潜”,[39]他的诗“似是从陶潜出来的,也富有嘲讽的意味”。[40]陶潜是胡适最推崇的诗人之一,其原因在于陶潜的诗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如胡适所云:“陶潜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一切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气都扫除的干干净净。”[41]王绩在宫体笼罩的诗坛独树一帜,所谓的“有点像陶潜”指的是王绩诗与陶渊明诗共有的革命意味,传达的正是胡适对王绩反抗宫体的革命精神的肯定。由此观之,无论是从王绩诗的白话特点而言,还是就王绩反抗宫体传统的进步意义而言,胡适将王绩提升至文学史上的显要位置都具有必然性。在建设新文学的语境下,这是符合时代需要的结果。因此,王绩被视为陶渊明在初唐的继承者,成为文学史上必不可少的诗人之一。
无论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还是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都深深影响了其后文学史的写作。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传统文学史观逐步被取代,胡适及其《白话文学史》所代表的文学进化观念为文学史家普遍认同。余冠英先生在论及文学革命后文学史的写作通例时断言:“以影响重大论自然该首推胡适之白话文学史,这本书表现文学革命以后的新观念并指出中国文学史上的主要通例,实为划时代的著作。”[42]胡适创建的文学史书写范式以及倡导的文学观念对文学史的写作格局都造成了重大影响。经过胡适对王绩诗学价值的建构以及对其革命精神的凸显,之后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肯定了王绩在初唐诗坛的重要性,尤其强调王绩在反抗宫体上具有的进步意义。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1931)认为王绩“因崇拜阮陶而使他的作风超脱齐梁而复于魏、晋”;[4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认为王绩对诗坛的重大贡献是在梁、陈风格笼罩之时以澹远纠正浓艳,并赞赏王绩其人“行事甚类陶渊明”;[44]谭正璧《新编中国文学史》(1936)则云王绩诗“甚者或可比拟陶渊明”;[45]陈子展《唐代文学史》(1944)认为“王绩的人格和诗格都深受陶潜的影响”,其诗能突破“当时体”的桎梏。[46]可见,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们基本延续了胡适的思路,将王绩视作陶渊明的继承者,大力赞扬王绩对当时诗坛的反抗。其中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专列一节论述“王绩与王梵志”,对王绩的书写最为典型:
他的作品在当日的诗坛,却又是最革命的了。如果在潘岳陆机以后,觉得陶潜作品出现的可贵,那末在齐梁陈隋的宫体诗以后,有王绩的作品,也是一样的可贵。在艺术的价值上,王绩虽比不上陶潜,然在其作品的情调与对当日的诗风的反抗,却是一致的。在这一点,王绩在初唐诗坛的地位,是存在着不可摇动的重要性……他却完全洗尽了宫体诗的脂粉气息,充分地表现了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这些诗是陶渊明的承继者,也就是王维、孟浩然作品的先声。如《野望》一首,完全是唐律的格调,比起徐陵、庾信们的诗篇来,不要说内容是全异其趣,就是在声律体裁方面,也更为进步更为成熟了。[47]
刘大杰认为王绩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时风进行了“反抗”和“革命”,因而其地位在初唐诗坛具有“不可摇动”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刘大杰还指出了王绩诗上承陶渊明,下启王、孟一派,在诗史上具有嗣晋开唐的重要意义。这一见解融摄了明清以来学者们对王绩的认识,体现出更为通达和进步的理论意识。经过胡适及之后的文学史家对王绩诗学价值的建构与阐释,王绩基本奠定了其在初唐诗坛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
强调王绩对宫体诗的反抗,并突出其文学史地位,是时代主流文化思潮下文学史写作的必然选择。胡适将王绩溯源至陶渊明,对其反抗宫体传统的诗学价值进行挖掘与构建,实则是建设“新文学”的策略之一。当时学界的主流思潮是建设“新文学”,打破传统的文学观念,作为“死”的、“僵硬”的宫体诗必然成为革除的对象。王绩的白话诗作为宫体诗的对立面,不仅符合“新文学”的审美标准,而且具有反抗传统的精神内核。因此,强调王绩的诗学价值就是彰显“新文学”的价值,亦是强调文学革命的进步意义。与其说是他们选择了王绩,倒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王绩。可以说,王绩文学史地位的升格是学者们以新理念重写文学史的结果,亦是合乎时代意识以及顺应文学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结语
一个作家的价值由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构成,这两者并不处于完全一致的价值系统。王绩的文学价值是有限的,相比起陶渊明和盛唐诸人,王绩并没有为诗歌的艺术世界增添多少创新的内容,这也是其诗在唐宋时期未获得认可的主要原因。就文学史价值而言,他为扫除宫体诗的障碍做出了贡献,又在诗体未纯之时开盛唐先声,其价值不言而喻。明代以后文人正是从文学史的视角审视王绩的诗学意义,从而完成其诗学价值的建构。
王绩的诗学价值是顺应学术思潮的发展和适应时代的思想需要被构建而出的。王绩诗的文本内容是恒定的,而其是否具有价值就在于能否与时代的价值观念相融合。王绩起初诗名不显,原因在于其诗不符合唐宋诗学的主流价值标准。在“诗必盛唐”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明清文人以盛唐诗的价值标准审视王绩诗,发现并建构出王绩诗肇启盛唐之音的诗学价值。当文学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意识时,王绩又成为“新文学”的代表并被融入反抗宫体的革命内涵。王绩诗学价值被构建的过程,其实就是后人不断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注入其中的过程。从此可以看到,文学史具有能动性,会主动吸收和容纳符合文学史发展规律的因素,同时亦会摒弃没有融入于文学史发展历程的作品。到底是作家和作品构成了文学史的内容,还是文学史发明和构建了作家及作品,这其中主客关系的互动和转化值得我们反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