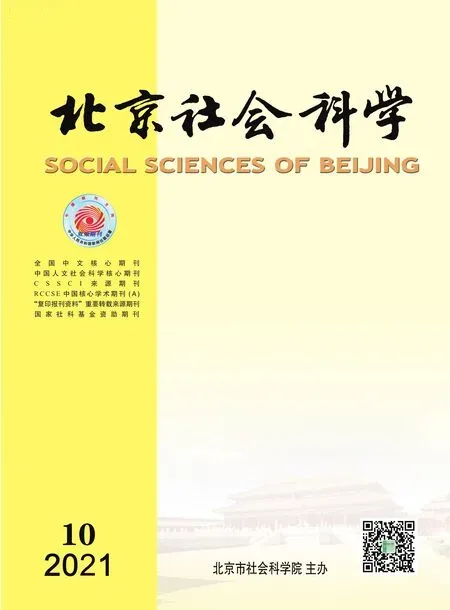重读《钟鼓楼》:时空装置、空间焦虑及伦理困境
刘军茹
一、引言
《钟鼓楼》原载于《当代》1984年第5期、第6期,是刘心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与“新时期”初期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等中短篇小说相比,有着刘心武作品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但也明显表现出焦点下移而更具日常性和京味儿特色。
小说聚焦北京某胡同四合院里的一场普通婚礼以及院内9户人家的日常生活,正是对“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活”的呈现,洪子诚归之为“寻根小说”类别,[1]也有人归之为“京味文学”范畴。[2]但《钟鼓楼》显然不具有《爸爸爸》(韩少功)、《异乡异闻》(郑万隆)、《小鲍庄》(王安忆)等重铸并反思传统文化的“寻根”意味,也没有邓友梅、冯骥才、林斤澜等作品浓郁的民间“市井”腔。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学者小说”,[3]具有“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学特征,[4]“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发生史”。[5]据此,有学者指出,正是1980年代各种批评声音之间的撕扯所带来的定位模糊,使得《钟鼓楼》未成为当时文学潮流中的一个典型性存在。[6]笔者认为,“定位模糊”恰恰反映了刘心武对被预设、被定义的单一主流文学思潮的有意突破,而之后刘心武对韩少功“寻根宣言”[7]的敏锐反应和匡正也体现了其新的创作理念:“我主张将少功所提到的纵向历史追索和横向的时代概括起来,将外来文化中的优良因素同本民族地域的初始文化、民间非规范文化中的精华合起来熔铸成一种合金文学。”[8]刘心武作为最早“预示新时期文学春潮”,“始终追随历史前进的脚步,并一直站在历史的潮头”的一面镜子,[5]此时没有继续紧跟波澜壮阔的“寻根”文学主潮,而是强调古与今、中与外的“纵横熔铸”即“合金”。这种转向是偶然还是必然?随着我们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及其作品的再回顾,也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刘心武打磨近两年的这部长篇处女作,与他几个月后力推的“合金”文学理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为什么《钟鼓楼》未成为文学潮流中的一个典型性存在?
二、时空装置:钟鼓楼、四合院、日历、钟表等
事实上,《钟鼓楼》甫一发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结构形式。刘心武称之为“花瓣式”或“剥橘式”,即从一个花心出发,花瓣朝各个方向张开,一层又一层,或剥开橘皮,又一瓣瓣地将橘肉加以解剖。[9]30多个人物的悲欢离合、矛盾激荡都集中压缩在一个相对静态的时空——12个小时、一个四合院,这样的时空架构,对于一部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在1980年代的文学界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细读则发现,作者一瓣瓣剥开的其实是不同人物纵向的成长轨迹,并涉及钟鼓楼、什刹海、地安门大街、胡同、四合院等北京古城的特有空间。其中“钟鼓楼”和“四合院”两个关键性的时空装置最为突出,既是结构也是象征,更体现了刘心武所倡导的“合金”文学的特质。
钟鼓楼,曾是古都中轴线最北端的最高建筑,也是中国古代的报时工具。到了1980年代即新时期,其空间位置意义和报时功能虽然有所消减或中断,但按照阿斯曼对记忆地点的划分,钟鼓楼属于“纪念之地”,仍然保留着与过往生活相关联的历史痕迹。[10]小说不仅冠以“钟鼓楼”之名,把“钟鼓楼一带”设置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空间,而且开篇的“楔子”——钟鼓楼银锭桥畔之美少年抱打不平,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惩恶扬善的民间传奇。于是,小说在重建历史归属的寓言性想象中,开启/见证了100年后钟鼓楼下一个个普通百姓的当代四合院故事——“时间流到了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在钟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中,有个四合院;四合院中有个薛大娘……”
四合院,作为“家庭之地”“代际之地”,[11]寄寓着平凡琐碎的日常烟火。刘心武刻意把“四合院”独立出来,作为“本书的一个大主角”,并如导游般推开院门、移步换景地步步深入,使我们了解到:这个四合院里,除了里院张局长家有单用的自来水管,其他人家则合用一个公共水龙头。“回水”就成为他们所特有的一种用水方式。接下来,作者又一一介绍了薛家婚宴中迎亲、帮厨、喝喜酒等传统习俗,既显示了雅俗共存的民间喜庆活动的代际相传,又呈现出1980年代初人们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京剧演员澹台智珠的剧团因财政压力而明争暗抢,张奇林所领导的局级机关因分房换房陷入财务纠纷,诗歌刊物编辑韩一潭则被各种人情世故蹂躏捶打,还有厨师、工人、个体户等底层市民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同时,作者还多次指出这个“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所特有的文化内涵。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中的“大主角”四合院与“书名”钟鼓楼一样,都成为打通时空记忆、联系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合金”装置。同时,小说的第一章也以薛大娘站在“四合院”门口仰望“钟鼓楼”结束: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
薛大娘抬头仰望着这溶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着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着。
此时,古老的钟鼓楼已经不再鸣响、记忆时间,但依然可以通过“剪影”显示对空间的掌控,依然“俯视着”陈旧的四合院和喜迎崭新一天的薛大娘们。因为钟鼓楼和四合院所铭记的历史已经溶入他们的生活和灵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几代人的经验感知、文化记忆。正如费孝通所说:“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12]沃尔什也说:“历史思维是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而有赖于记忆。”[13]某种意义上,钟鼓楼和四合院就是这种特殊的时空记忆装置,唤醒我们被时间所遗忘的历史和命运,空间铭刻着流动的时间,时间则沉淀为历史的空间。由此,刘心武在小说扉页写道:“谨将此作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
此外,小说中还有两个动态性小装置日历和钟表,也多次出现,且时隐时现、首尾呼应。小说第一章“卯”是这样开始的:“薛大娘洗漱完,用发散着香胰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文字下面则附上了一页阴阳历并行的日历图。民国时期虽然曾经强制改用阳历,但因为阴历的岁时节气与百姓日常民俗活动密切相关,所以民间一直保持着阴阳历并行的习惯。[14]1980年代钟鼓楼下的四合院里薛家人办喜事,也是参照了传统的民间阴历习俗。而薛大娘如此郑重地撕开日历,一上来就散发着一股雄赳赳向前挺进的芬芳诱人的生活气息。同时,日历除了可以标识婚嫁祭祀、节气节令等,对于家境贫寒、勤奋好学的荀磊来说,这一本本用过的旧日历就是其知识启蒙的“老师”。文化荒漠时代的上进少年,恰如石缝中的小草一样顽强地吮吸着所能获得的每一滴营养,此时的日历,无疑还有着撒播知识、传承文化的作用。
如果说日历更多寄寓、保持着人们对传统的依恋,那么钟表则是现代化所强调的效率、前进的象征。新娘子潘秀娅痴迷镀金的瑞士雷达小坤表,张局长不仅要求全家人的手表精准,而且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校对单位所有人的钟表。“时代进步了,人们不再依赖钟鼓楼报时,即便公共计时器遍布每一个路口,人们也还是要拥有自己独享的计时器。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钟,几乎每一个成人都有表,而且有的家庭不止有一座钟,有的成人不止有一块表——随着普及型的廉价电子表上市,儿童们也开始拥有表了。”相比钟鼓楼上曾经气势恢宏的击鼓撞钟,薛大娘在卯时破晓撕下一页旧日历的计时习惯,以及陪伴海奶奶几十年却早已停摆的檀木老式挂钟,院里的年轻人显然更喜欢精确度高且外表光鲜的电子表。或者说,1980年代四合院里的每个家庭、成人乃至儿童都被拧在了更普遍、更现代的电子表所匡正的时间观念里。
日历是慢的钟表,钟表则是快的日历,日历以“天”为单位记录整体性的宏观时空,钟表则以“时分秒”细分和刻录更精准的微观时空。类似这样的承载着特定时空记忆的小装置,比如邮票、相册、书信等,也都巧妙地出现在小说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总而言之,无论是钟鼓楼、四合院两个位置固定的静态性大装置,还是钟表、日历等不断向前的动态性小装置,前者贯穿全篇,后者如草蛇灰线,拽之皆通体俱动。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思想文化界蓬勃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大讨论”中,刘心武的首部长篇小说有意识地设置了钟鼓楼、四合院、钟表、日历等几个时空叙事装置,试图呈现出一个时间与空间、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合金”的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社会生态景观。
三、四合院及其空间焦虑
确然,刘心武与编辑孟伟哉的通信也是这样表述的:“在这部作品中,我主要是企图给读者提供一幅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社会生态群落图,或者叫作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社会生态景观。”[9]小说发表不久的1985年3月,《当代》杂志社举行了《钟鼓楼》座谈会,会上部分学者并没有把《钟鼓楼》列入京味小说,认为其所蕴含的哲理性不是京味。[15]这里的所谓“京味”哲理,可以理解为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再建构。贺桂梅对这一时期北京书写/京味小说进行了概括,即总体上建构了古都的想象形态以及即将消逝,有着一种文化挽歌式的回望和认同,并逐渐转换为一种深切的感同身受的同情。[16]重读《钟鼓楼》则发现,小说虽然不乏钟鼓楼、四合院等极具历史意蕴的叙事装置,但相比同时期的《烟壶》(邓友梅)、《辘轳把胡同9号》(陈建功)、《安乐居》(汪曾祺),似乎并无过多关注古都的传统民风器物,更没有挽歌式的怀旧情绪。换句话说,《钟鼓楼》的传统“京味”其实并不突出,突出的反而是身处其中的四合院居民当下的生存状态及其感受。生活世界本身是一个直觉的、个人的、可经验的领域,即梅洛-庞蒂的“被感知的世界”,而个体对特定生活世界及其空间关系的敏锐感知,恰恰是某种存在性不安的体现,于是空间叙事逐渐成为现代人焦虑感的表达元素。因为“空间始终处于等待的状态,等待被占有,等待被填充。……面对空间,人类总是难以抑制自我介入和征服的欲望”。[17]福柯则明确指出:“不管怎样,我认为造成目前的焦虑的原因,更多地是与空间有关,而不是与时间有关。”[18]《钟鼓楼》突出的时间和空间意识,尤其是围绕四合院内部和外部的空间叙事,在1980年代的北京书写中确乎比较突出。
四合院,顾名思义是由四组房屋以方形组合而成,各家各户相互独立而又可隔窗而谈,甚或推门而进。“这种建筑空间和民风民俗所构筑的人际关系,带有类似于传统乡村的特点,因人伦亲情、邻里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于现代大都市的疏离关系的紧密关联。”[16]所以薛家老二娶亲这样的大事,邻居们会送上贺礼,也会代表男方家长帮忙迎亲、摆宴。列斐伏尔说:“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是一种社会的产物。”[19]即空间关系体现社会关系。《钟鼓楼》所描述的1980年代的这个四合院,表面看似乎已经被改造成一个逐渐抹去阶级差别的城市平民大杂院,但其固有的空间布局还是显示出某种阶层关系。比如,高大宽敞的三间大北房是张局长家,出身底层的薛家和荀家则住在偏院,老实木讷的编辑韩一潭夫妇偏居于院内“死角”,各家各户因住房紧张而私搭乱建的“小厨房”则参差错落地不断冒出。这样的居住格局,这样的或明或暗地抢占公共空间,已表明四合院这个貌似和谐安稳的“都市里的乡村”,其内部基于现代阶层关系的某种存在性不安正悄然暗涌。
与独门独户的乡村院落不同,四合院内部的院落属于各家共同使用的半公开空间。从社会学上看,这种互动互应的类似舞台的建筑布局,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了戈夫曼所定义的前台表演的属性——“当个体在他人面前呈现自己时,他的表演总是倾向于迎合并体现那些在社会中得到正式承认的价值。”[20]或者说,四合院里人们的言行举止会下意识地趋向一种标准和仪式,于是隆重热闹的婚礼仪式直接被推到了“被看”的前台。薛家婚礼从早晨到黄昏,从大院门口到里院,各色人等次第登场、聚集,呈现出一个标准的现代婚礼景观。然而,人们在摒弃或隐瞒某些与标准不一致的行为时,“经常会发现自己陷入了表达与行动对峙的困境之中”[21]。比如,薛大娘虽然忌讳不是“全可人”的詹丽颖去迎亲,但碍于情面无法拒绝,于是整个婚礼都很郁闷;小莲蓬一早生病,薛家大儿媳孟昭英却忙前忙后而无暇照顾女儿;梁福民夫妇平日里很是节俭,此时却让孩子衣着光鲜到院中心吃进口香蕉。置身四合院这一视觉性空间及全程被注目的婚礼,人们在他人的目光和期待中表现自我,或忧心忡忡,或紧张不安,或沉溺自满。被压抑的情绪集中爆发体现在未申之时的“回水风波”和“丢表事件”。作者借詹丽颖的快人快语表明:“嵇志满可怜,慕樱孤单,薛家失窃,新娘子委屈,韩一潭优柔寡断,澹台智珠力不从心。”总之,表面上看起来热闹风光的婚礼场面,实际每个人都在极力掩饰着内心深处的焦虑和惶恐。鲍勒诺夫说:“居住是与任何别的活动不同的一种活动,它是人的一种规定性,人在这种规定性中实现他的真正的本质。”[22]海德格尔也说“空间决不是人的对立面”,相反“人的存在基于栖居”。[23]婚宴中处处感到掣肘的四合院居民们的自我压抑、自我否定式的“表演”,似乎预示了四合院已经不再是给予人们庇佑的传统院落和使人获得身心自由的栖居之地。
无疑,四合院的内部空间是整部小说的聚焦之地,但作者还通过穿插与跳跃把人物推向了更广阔的外部空间。为了演出顺利而往返于电话亭电梯间的澹台智珠,不断出入邮电大楼寻找珍贵邮票以便接近“目标”的慕樱,为了买到处理名牌家电而跑遍全市卖场的新郎新娘,坐着小汽车、飞机争分夺秒谈工作的张局长。“空间在所有维度上都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的转变必须通过一种新的社会空间关系的自觉创造来推进。”[24]电话亭、电梯、邮电大楼、小汽车、飞机这些依靠现代技术创造出的新空间散发的现代之气使古老的四合院暗淡,使城市生活变得便利、高效、绚丽的同时并没有消除人们的焦虑和不安,反而加速通向一个看与被看的“梦幻世界”。自从薛纪跃和潘秀娅的约会内容变成去王府井大街“看表”,闪闪发光的瑞士小坤表就开始不断地在潘秀娅的想象和梦境中出现;登龙有术、四处拉关系的“客厅作家”龙点睛“望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暗暗发誓:“在人生的战场上,抓紧一切机会不放。”这些渴望“不仅是他们想要什么和可以买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什么和因此需要什么”[25]。文坛地位对于龙点睛,就像小坤表对于潘秀娅,他们都被越来越炫目的物质和名誉占有和征服。此外,小说还写到16岁的中学生姚向东如何从“后进生”滑向“小流氓”——最初就是“厕所中递来的一支烟、溜冰场上的一次蓄意冲撞、游泳池畔的借用‘鸭蹼’”:“结识小流氓,原是容易的事。公共厕所、溜冰场、游泳池、邮局门口倒换邮票的人群,足球场入口外等候退票的人从……都是小流氓们经常麕集出没的所在。”这里,溜冰场等四合院之外的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俨然隐藏着某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和恐惧。而随着天色晦暗,“(鼓楼)渐渐成为一个巨大剪影”,偷了手表的姚向东很是忐忑懵懂——“一会儿朝南边疯走,一会儿又穿过马路、朝北边行……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此外,小说还精心插入了乡村姑娘郭杏儿来四合院认亲的一段空间叙事。她下了火车,穿过新奇而神秘的地下通道,看到了装有日本精工表的灯光广告箱,感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城里味儿”。接着又走马观花地看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故宫等建筑景观,而景观只是被用作拍照的背景。这些瞬间性的视觉行为,以及身体在“城市文本”中的流动,是最直接地介入空间的方式,是“一种城市经历的基本形式”,一种言语行为和空间表述。[26]当然,郭杏儿最渴望参观的还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她兴致勃勃地走到了王府井,无限激动地走进了百货大楼,她一口气登上了三楼,还下意识地在三楼那儿跺了跺光亮如镜的水磨石地板,内心里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此时,郭杏儿与城市姑娘潘秀娅一样,都满足于“一个具有无尽可能性的世界”,[27]而王府井则与本雅明的拱廊街一样,都成为被凝视、被消费的对象,成为对城市空间景观和现代性本身的幻象,暂时创造了一种不太真实的城市生活体验和氛围。所以,当郭杏儿真实地走进钟鼓楼附近的那条胡同,走进满是高高低低小厨房的四合院,走进空间和走向都很“差劲”的荀大爷家里时,惶惑之余内心竟浮上一种自豪感。但接续就是与谈吐洋气的城里人冯婉姝的短暂冲突,于是郭杏儿“进京的兴奋感突然消失了。她发痴地想念起娘和枣儿来”。至此,这部分就以一个乡村外来者的行走、观看,并对照现代宏大的城市空间,重新审视了四合院内部空间的独特性,以及开始被现代性焦虑和梦幻欲望所挤抑、所改变的四合院生态景观的日渐衰微。
梅洛—庞蒂认为“一切感觉都是空间的”,同时“主体是时间的”,“时间是生命的方向”。[28]也就是说,生活世界/空间是由一个个具体而偶在的生命组成。身陷现代景观迷雾中的四合院居民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所组成的“可能性世界”,显然越来越焦虑、惶恐。我们不禁要问,铭刻着历史记忆的四合院将何去何从?是进一步加大现代化的空间改造,还是像张局长那样搬到规划整齐却彼此疏离的单元楼房,或者像郭杏儿回到阡陌交错的乡村?四合院是否也会像钟鼓楼逐渐成为“纪念之地”而被现代的日历、电子钟表所取代?四合院居民们的将来和命运又该如何选择?“时代弄潮儿”刘心武,这一次给四合院这个传统的“家庭之地”及其居住者选择了怎样的位置和方向?
四、从“启蒙”转向“承认”中的伦理困境
毋庸置疑,“新时期”初期刘心武率先以“拯救者”“班主任”的姿态浮出历史地表,开启了一条基于现代启蒙话语的叙事之路。但是七年后的《钟鼓楼》,同样面对一个问题少年,刘心武则不再指点迷津、举旗呐喊,不再是“救救孩子”式的激情教导,而是客观冷静地一瓣瓣地剥开其成长的家庭环境。姚向东的父母都在机关工作,对于青春期孩子的顽劣却只会用训斥和暴力解决。偷表后的少年一路徘徊,“想到母亲的吆喝、斥骂,父亲的巴掌、鞋底,他真想就在外头过夜”。小说还对照性地设置了几个同样来自社会底层家庭但秉性气质、人生之路截然不同的年轻人。路喜纯的母亲曾经是妓女,父亲是妓院里的杂工,他少年时父母双亡,自此更加自强自立,苦练做菜基本功,希望成为一名掌勺大厨;卢宝桑的爷爷和父亲都曾靠行乞为生,他长大后一直游手好闲,像个小混混一样到处蹭吃蹭喝;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荀磊,从小爱读书,自学外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外事部门录取。作者纵横交织地勾画出几个年轻人的成长轨迹,他们或消极沉沦,或努力上进,但都不再归于社会和他者,而是以各自家庭为中心向内审视,审视每一个独立个体的成熟与成长。或者说,刘心武从“班主任”式的他者启蒙转向了自我启蒙。“家庭之地”是我们的历史记忆之源,但个体成长更需要内在精神的觉醒和自我意志的追寻。
澹台智珠和慕樱两个中年女性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历程。重登舞台的澹台智珠在事业上风生水起,但与保守的丈夫之间的矛盾则日益加剧,为了父母和孩子,她隐忍负重、勤劳持家,经常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慕樱则三段婚恋都很主动,甚至为了个人幸福不惜抛家弃子。表面上看,澹台智珠代表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女性,慕樱则是义无反顾地追求自我幸福的新女性;前者为了家庭而忽视自我,后者则以他人的名誉为人生目标。慕樱对几段情感的占有乃至全然否定,是对自我生命的否定和逃避。
冯婉姝和郭杏儿两个有追求、有个性的女青年不仅是情敌关系,某种程度上还是城乡冲突的代表。面对冯婉姝的热情招待,郭杏儿觉得酒心巧克力又苦又辣,咖啡难喝又恶心,还有怪怪的荤饸烙、难听的德彪西曲子、太软的沙发床垫、闻不惯的花露水等,她都觉得“不舒坦”。“每一种外部知觉直接就是我的身体的某种知觉”“当我们在以这种方式重新与身体和世界建立联系时,我们将重新发现我们自己。”[29]易言之“感觉是构成自我的重要因素”[30]。显然,冯婉姝和郭杏儿两个自我意识突出的女性都有着丰富敏锐的感知。作者无意评判城乡两种感知的高低,而是客观呈现出两个人的真实差异。但是,当冯婉姝滔滔不绝地向郭杏儿输出知识,时不时地问道“懂吗”,“能理解吗”时,乡村姑娘则变得烦躁、愕然,“心底里却泛起了一种古老的、难以抑制的对占有知识优势的城里人的一种厌恶……乃至于仇恨”。
余英时曾说中国是一种内倾文化,“中国人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也就是说,中国人一方面强调个人的价值自觉,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伦秩序。[31]可见,中国人的自我追寻并不悬空孤立,而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存在。但是,对现代化的热切渴望以及西方现代思潮的激荡澎湃,使得新时期文学在主体性旌扬中,往往忽视了差异性他者的存在,尤其是低位者、漂泊者、异己者。[32]或者说,新时期的很多小说在理性编织的现实政治、公共空间等同一性叙事中,并没有过多地表现出叙述他人故事的热情。但《钟鼓楼》的落脚点不再是宏大主题、时代英雄,其所呈现的“社会生态群落图”给予了众多差异者尤其是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修鞋匠、厨师、售货员、卡车司机、园林工人、个体户——更多的话语权,其中自然也包括来自传统乡村的当代年轻人。这似乎也暗合了作者几个月后提出的“合金”文学理念:“文学本应是多元的,即使有的‘元’相比之下显得辉煌深邃,也不应由此而取消他元的存在,甚而也不必由此而贬低他元的价值。”[8]
所以,郭杏儿对冯婉姝的“厌恶”和“仇恨”将如何发展,作者没有也无意交代;就像我们同样不知道四处彳亍的姚向东,是把手表还给了薛家还是扔进了什刹海,不愿回家的他又去哪里熬过寒夜?望着宣传画上“为了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几个大字苦笑的澹台智珠,其举步维艰的京剧演出是否能正常进行?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而澹台智珠与慕樱一前一后相遇在邮电大厦的电梯里,也只是相互揣度地擦身而过。面对同一时空下的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等各种矛盾对立,刘心武不仅没有给出明确的是非判断,反而在小说结尾直接把问题抛给了读者:
我们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这天所认识的这些人物,将怎样继续生活下去?我们对他们的分析、预测和评价,将被时间所确认,还是将被时间所否定?
薛纪跃和潘秀娅能否和谐相处、得到幸福?薛大娘和她的两个儿媳……是否仍将不断地爆发出微妙的矛盾冲突?杏儿将怎样向母亲和枣儿交待首都之行,并将怀着怎样的情绪回忆这一段遭遇?张奇林夫妇搬入新居后,是否能保持同原来那些“小市民”们的联系?慕樱的爱情观和道德观,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是将遭到大多数人唾弃,还是将被大多数人宽容乃至接受?……龙点睛一定会“有志者事竟成”吗?姚向东究竟是及时地被挽救过来,还是竟从此沉沦?小莲蓬、小竹这些孩子长大了,将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
看来,这一切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
此时,没有了“班主任”的热烈激昂、“哥哥”的爱憎分明,也没有了“如意”的深情悲愤,而是不无冷峻平和地指出“这一切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意味着刘心武进入了创作的“冷静期”。对此,刘再复说:“如果他的‘如意’——他昂扬的充满着爱的人道主义之歌能被批评家们所理解,他是会继续他的昂扬的,而不会这么快地就背起着一个蜗牛似的冷峻的外壳。”[5]这种委婉说法似乎暗指当时刘心武以《如意》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创作所遭遇的冷遇和批判,也侧面表明作者给“钟鼓楼”戴上这层冷峻的外壳未必是自愿,而是作家后退、收敛的“彷徨”之作、积淀之作。或许,也正是从一路“呐喊”到短暂“彷徨”,客观上促使刘心武从炽热激昂中退出,开始静心思考,开始有意从“同一”转向“多元”,从“单质”转向“合金”。
抑或说,刘心武开始从“启蒙”转向“承认”——既承认海奶奶对老式挂钟的执念,也尊重潘秀娅基于外在审美需求的小坤表情结;既抬头仰望钟鼓楼的巍峨肃穆,也俯身溶入四合院的人间烟火。即承认每一个具体的差异性他者的存在。所以,四合院故事的结尾,爱慕虚荣的潘秀娅并没有因为糟糕的婚宴而赌气回娘家;粗蛮豪横的卢宝桑也会把自己最珍爱的打火机送给别人;姚向东这个混乱制造者,内心却是极其恐慌和痛苦的;马上搬离四合院的大学生张秀藻,也为自己不曾主动接近邻居们而内疚;对待家庭婚姻大相径庭的澹台智珠与慕樱,电梯上彼此“腹诽”一两分钟后继续前行,因为“她们有着各自的生活轨迹,有着各自的心绪与期待”。这种基于“多元”的“承认”更体现在工人家庭出身的荀磊这个主要人物身上。荀磊不仅有自尊自爱、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同时主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但已经不是“班主任”“哥哥”等“卡里斯马”式的强势启蒙者,也不像张秀藻那样“远离粗鄙庸俗的一群”而高高在上。四合院土生土长的荀磊,情感更趋内敛含蓄,不仅能够倾听冯婉姝和郭杏儿之间的城乡矛盾,也能在邻居窘迫之时伸出援手、解围济困。这里的问题是,荀磊最后通过自己出钱出力而佯装手表“失而复得”所达成的谅解和宽容,果真能够弥合薛家婆媳、妯娌之间的罅隙吗?果真能够缓解四合院居民们日益突出的矛盾和焦虑吗?
实际上,荀磊、澹台智珠、韩一潭等人的宽容克己,始终没有摆脱费孝通所定义的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之道德伦理。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以父子、夫妇、朋友、集体或四合院等某个私人关系的名义,要求他人付出、牺牲,因此这种人伦秩序中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和”往往是不稳定的。澹台智珠的迁就表面使丈夫回心转意了,但这是否从根本上促发了他自身的成长,或只是他酒后一时的冲动?老好人韩一潭的忍让是否能够填平龙点睛无尽的欲望之壑?而被大家原谅的卢宝桑是否还会不劳而获地海吃足撮?面对婚宴残局和媳妇的委屈、烦怨,匆忙赶回家的薛家老大也只是嗫嚅:“别这样,别……凡事想开点,都能闹清楚的……一家子人,还是要谅解着点,要团结……”但显然,他已经感觉到被公婆欺骗、忽视的孟昭英“更委屈更烦怨了”。克己式的宽容/承认不仅没有让自我身心舒展,也未必能激励他人健康成长,彼此反而像是被或隐或现的夹子夹住/扭曲了身体。“承认”,不是我们赐予别人的恩惠,而是内在发生的,必须以“本真性理想”为基础,即自我和他者都保持各自的独特性。“我们给以承认的是这个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认同,是他们与所有其他人相区别的独特性。正是这种独特性被一种占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而这种同化是扼杀本真性理想的罪魁祸首。”[33]换句话说,多数人的“同化”对少数人的“本真性”其实是一种扼杀,是以某种无形的压迫把自我和他者都囚禁在虚假的存在之中。缺失自我、否定自我的宽容,是一种虚假的、扭曲的承认,又怎能达至真正的平等与和谐?
毋庸置疑,20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北京某四合院,其内部和外部的社会生态景观日益绚丽、复杂、现代,但是也不可避免地趋向“同一”和“单质”,如何保持自我与差异性他者之间的平等与和谐?当时刘心武所给出的“古今中外纵横熔铸”的“合金”理论,亦即“承认”策略,是否是一条理想路径?易言之,现代社会转型期我们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当时的四合院居民和中国故事讲述者都需要真诚面对的一个社会性的伦理问题。对此,当代文学批评家周展安指出,《钟鼓楼》“既反映了刘心武在创作上题材越来越开阔、越来越伸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倾向,也提示了整个时代的转向……”[34]不过遗憾的是,刘心武的这种日常性叙事倾向或者说真诚“提示”,在当时的创作实践和批评语境中都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
五、余论
37年后重读《钟鼓楼》,我们亦能感觉到作者的这份真诚,不被认可却依然前行的真诚,彷徨困惑但仍然求变的勇气。此外,开篇的楔子、类似章回体的结构、适当的北京俚语等传统的形式技巧,以及现代的时空意识,如今读来,依然能感受到作者的匠心独运。但同样不可否认,也正是刘心武这种古今浮掠、纵横兼顾的“合金”创作理念,某种程度上使人物的内心世界无法深入展开。比如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冯婉姝和郭杏儿、澹台智珠和慕樱、路喜纯与卢宝桑等,最终还是没有突破扁平化、标签化的窠臼,对人物焦虑冲突背后的沧桑与疼痛及文化价值层面的伦理困境都缺乏更本质的挖掘与反思。而接下来,《钟鼓楼》以及刘心武的这种市民日常生活的叙事倾向所显示出的从“单质文学”向“合金文学”,从“同一”话语向“多元”话语,从“启蒙”向“承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便很快淹没在被异域文化、现代性思潮所强势推动/裹挟的寻根和先锋叙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