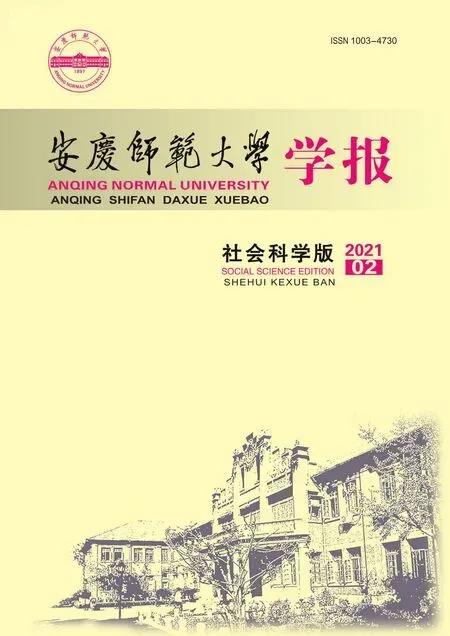16世纪英国农民的土地诉求:凯特起义《请愿书》解读
吉 喆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16世纪是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英国经历了一场以圈地运动为表现形式的土地产权变革运动。土地产权的变革使一些小农失去了土地,因此成为农民起义的主力。1549 年的凯特起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爆发的。凯特起义席卷了诺福克地区,同时也波及萨福克、剑桥、林肯部分地区,其主要形式是反对圈地[1]。在诺里奇东北部的莫斯霍尔德驻军期间,凯特起义者起草了一份《请愿书》,由凯特、诺里奇市长以及诺福克33个百户区的24名代表签名,呈递给国王。《请愿书》列出了29 条要求,以土地问题为中心,在陈述圈地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客观上也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诉求。
长期以来,凯特起义一直颇受学界关注。国外学界对凯特起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侧重于对起义过程的梳理,主要论著如弗雷德里克·威廉·罗素的Kett’s Rebellion in Norfolk(London:Longman,1856),路易莎·马里昂·凯特和乔治·凯特的The Ketts of Norfolk,a Yeoman Family(London:Mitchell Hughes and Clarke, 1921),宾多夫的Ket’s Rebellion 1549(London:Historical Asso‐ciation,1949),比尔的London and the Rebellions of 1548-1549(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12,No.1Nov.1972)和康沃尔的Revolt of the Peasantry 1549(London:Routledge&K.Paul,1977)。其二,强调凯特起义是1549年广泛流行的影响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的骚乱的一部分,代表性论著有麦卡洛克 的Kett’sRebelllion in Context(Past and Present,No.84,1979)和琼斯的Commotion Time:The Eng‐lish Risings of 1549(University of Warwick Ph.D.,2003)。其三,从政治与宗教角度研究凯特起义,阐释了凯特起义、大众政治以及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沙干的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伍德的The 1549 Rebellions and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其四,从经济角度解读凯特起义,认为经济问题是凯特起义者抱怨的核心问题,以简·怀特的Lords and Tenants in Kett’s Rebellion 1549(Past and Present,Vol.207,No.1,May 2010)为代表。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凯特起义,如刘博的《1549年凯特起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虽然国内外学界对于凯特起义的研究有一定的积累,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尤其是对凯特起义《请愿书》中所反映的农民土地诉求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凯特起义《请愿书》进行解读,剖析16世纪英国农民真实的土地诉求,以此管窥英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土地产权变革及其对农民的影响。
一、富裕农民的土地诉求:保护有益的圈地
凯特起义《请愿书》的第一条就提到圈地:“由于种植番红花的花费较大,现存的种植番红花的圈地可以保留,但从此之后不再允许新的圈地。”[2]48一个以反对圈地运动开始的起义,却首先提出要求政府在某些条件下保护圈地,看上去令人相当费解。实际上,这一要求代表了富裕农民的利益,需要在富裕农民也进行圈地的背景下理解。
在凯特起义的参与者中,不乏一些富裕农民。以凯特兄弟为例,关于凯特兄弟的身份,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弗雷德里克·威廉·罗素认为凯特兄弟是“皮匠和屠夫”[2]30;托尼认为凯特除了是一名皮匠之外还拥有大量土地,是富裕的中产阶层[3]326;路易莎·马里昂·凯特和乔治·凯特认为凯特兄弟是拥有一定土地的富裕自由持有农,即约曼[4];简·怀特认为罗伯特·凯特是来自怀门德姆(Wymond‐ham)的小庄园主,他的弟弟威廉·凯特是来自同一个镇的屠夫[5]22。虽然学者们对凯特兄弟的身份各持己见,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凯特兄弟是拥有土地的富裕阶层。
除了凯特兄弟之外,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百户区代表中也有一些富裕农民。米特福德百户区(Mitford)的代表威廉·豪利(William Howlyng)出身于什普海姆(Shipdham)庄园的富裕家庭。北厄平海姆(NorthErpingham)百户区的代表威廉·道蒂(William Doughty)是南来普斯(Southreppes)庄园的庄头[5]22。亨斯特德(Henstead)百户区的代表威廉·莫(WilliamMowe)在小弗雷明汉(Little Framingham)庄园持有41 英亩土地。耶尔弗顿(Yelverton)的约翰·里奇·波因特(John Riches al.Poynter)在小弗雷明汉庄园持有45英亩土地[5]23‐24。艾尔舍姆(Aylsham)的约翰·威思(John Wythe)曾持有艾尔舍姆、布利克林(Blickling)和霍文厄姆(Hevingham)三个庄园的土地,很可能是伯威克堂(Bolwick Hall)庄园土地的承租人。史密斯顿(Smithdon)百户区的金码头(Docking)庄园的乔治·霍顿(George Houghton)属于“约曼和乡绅之间”的阶层。他的父亲罗杰(Roger)是1545年案件的被告,因为他违反了1534 的《限制羊群数量法令》,在金码头、弗利特查姆(Flitcham)和安默(An‐mer)庄园饲养了大量羊群[5]25。此外,还有一些屠夫,例如布林福特(Billingford)庄园的约翰·迪克斯(JohnDix)。屠夫是典型的富人,许多屠夫同时也是牧场主。还有一些乡村精英,例如埃尔默顿(Aylmerton)的劳伦斯·道蒂(Laurence Doughtye),南来普斯的约翰·珀迪(John Purdy),耶尔弗顿的约翰·里奇·波因特,这些人都至少持有40英亩公簿持有地,这一土地持有规模在东诺福克地区是相当引人注意的[5]39。
富裕农民的圈地诉求与诺福克的农业结构有关。诺福克和萨福克的一半土地包含了两个轻质土地带,在16世纪用于种植谷物和养羊,羊粪提供了土壤自然形态中所没有的肥力,给谷物的高产提供了可能。广义上说,这两个养羊-谷物地区首先包括沿着萨福克海岸从南部的界标点(Landgu‐rad Point)到北部的洛斯托夫特(Lowestoft)以及桑德林斯(Sandlings),其次是一个更大的地区包括西萨福克的北半部、北诺福克海岸以及除了与林肯郡和剑桥郡交界的沼泽地以外的整个西诺福克[6]50‐51。养羊-谷物地区实行敞田制。在敞田制下,农民的土地以分散的条田形式持有。从开始耕种直到收获的这段时间内,条田是属于农民“占有”的,条田上收获的农作物也归农民个人所有。然而,在收获之后和播种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农民的条田要对村庄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开放,供其牲畜放牧。这样一来造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私权共享现象:虽然农民拥有对条田的实际占有权,但使用权却是公共的[7]。此外,敞田制下农民缺乏自主决定土地用途的权利,利用土地的权利给谁,应当怎样利用土地,都要由村庄共同体做出统一的安排,使得每个农户对土地的自由使用受到了限制,他们不能自主决定哪块地耕种,哪块地休耕,什么时候播种,种植哪种作物。在这种体制下,个体农民的任何生产活动都要与村庄共同体保持高度一致,制约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16 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土地被极大商品化,具有市场价值。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需要为更多的人提供粮食,农产品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在这个寸土寸金的时代,诺福克的富裕农民渴望通过圈地打破敞田制的束缚,面向市场生产,从土地上获得更大的利润。
此外,诺福克地区还存在一种封建特权——领地积肥权(rightoffoldage),又被称为“羊栏受制义务”,它要求佃户必须将他的羊圈牧于其领主羊栏内以供应粪肥,而不得私自设置羊栏放牧[8]563。如果佃农因领地积肥权而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放牧,他会本能地合并和围圈土地用于耕种谷物和放牧牲畜,以此来给自己的庄稼提供肥料[6]51。因此,摆脱领地积肥权的制约也是诺福克富裕农民的圈地动机。
与产权模糊的敞田制相比,圈地促进了土地产权的明晰,使农民获得了自主经营权,同时也摆脱了领地积肥权的制约。《请愿书》第一条请求种植番红花的圈地被保留。番红花种植业是诺福克重要的地方产业,是精纺毛纱的制造所必需的[9]。圈地培育番红花能获得更多收益,因此参与起义的富裕农民要求保留这些圈地。由此可见,作为凯特起义的重要参与者,富裕农民并不反对这一时期的土地产权变革。他们要求建立明晰的土地产权,保护有益于自身利益的圈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反对圈地为目标的凯特起义却首先提出要求保护圈地。
二、下层农民的土地诉求:要求合理的地租
要求合理的地租和入地费是起义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在《请愿书》中多次出现:《请愿书》第5 条:“我们恳求:苇地和草地,应按照亨利七世在位第一年的价格出租。”[2]49《请愿书》第6条:“我们恳求:一切向国王陛下交纳自由租或他种地租的泽地租户,应仍按照亨利七世在位第一年的标准交付。”[2]49《请愿书》第14 条:“领主对公簿持有地所征收的不合理的地租应以亨利七世在位第一年的标准征收,在佃农去世之后,领主对土地的新获得者应征收合理的入地费。”[2]51
要求合理的地租和入地费反映了参与凯特起义的另一个重要阶层——无地和少地的下层农民的利益。在请愿书签字的24名百户区代表中也有一些下层农民,例如哈平(Happing)百户区代表托马斯·克劳克(Thomas Clock)是来自帕尔海(Sea Palling)庄园的农夫,塔沃汉(Taverham)百户区代表威廉·皮特斯(William Peters)是一个木匠[5]22。此外,简·怀特研究了庄园档案中所记载的46个起义者所持有的公簿持有地的规模,其中,25人是土地小于10英亩的小土地持有者,他们中的18人土地持有规模小于5 英亩[5]23。更有甚者,仅持有一英亩习惯土地,例如辛多维斯顿(Hindolveston)庄园的约翰·尼古拉斯(John Necolls)[5]23。这些参与起义的下层农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要求领主征收合理的地租和入地费。
地租和入地费是16世纪英格兰农民普遍抱怨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是由圈地引起的。圈地之前英格兰土地大多是习惯保有,其中公簿持有农占大多数,可以为期数代或数年占有土地。他们的地租通常包括两部分,一大笔入地费以及金额相对较少的地租。入地费是对公簿持有地的新获得者征收的,在习惯保有下,入地费和地租通常是固定的,并且具有法律保障不能改变。16 世纪农产品价格的飞涨使领主意识到要应付通货膨胀必须打破原来的习惯保有,缩短租期,征收高额地租和入地费,以此来增加土地收入。习惯保有的废除与契约租地的建立是通过圈地实现的。当公簿持有农租约到期时,领主与他们重新商议地租,向他们收取能够反映土地的市场价值的竞争性地租。这种地租比较高,公簿持有农往往因负担不起而不能继续承租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领主就把土地以契约租地的形式租给富裕的农场主。习惯保有的废除与契约租地的建立是圈地造成的变化,以竞争性地租为特征的契约租地在通货膨胀的年代更受领主欢迎[10]。
凯特请愿书中关于地租和入地费的要求,是对当时英国社会一种普遍抱怨的呼应。高额地租和入地费使一些贫苦小农无法续约,导致失地者数量越来越多,引起了英国社会的普遍关注。当时的道德家们严厉谴责领主征收高额地租和入地费,菲茨赫伯特(Fitzherbert)在其《调查》一书中写道:“我代表上帝劝告领主们不要提高佃农的地租或者让他们缴纳一大笔入地费,不要敲诈勒索佃农。”[3]148休·拉提默(Hugh Latimer)在1549 年的祈祷中说:“地主,地租提高者,你们每年收入太多了。过去地租是每年20或40英镑,现在是50甚至100 英镑一年。”[11]参与凯特起义的下层农民对地租和入地费问题的强烈呼吁,希望引起国王重视,能够解决这一在英格兰各地普遍存在并对下层农民伤害颇深的问题。
三、全体农民的共同诉求:公地使用权
对公地使用权的诉求是起义者众多诉求中最关键的一个,在《请愿书》中多次出现,如《请愿书》第3条:“我们恳求:任何庄园领主不得和平民共同享用公地”[2]49;《请愿书》第11条:“我们恳求:所有自由持有农和公簿持有农都可以利用公地并从公地获得收益,而领主则不能利用公地并从公地上获得收益”[2]50;《请愿书》第29条:“我们恳求:任何贵族、骑士和乡绅,如果他们一年的土地收入超过40英镑的话,不得在公地上饲养牛羊,除非是为了自己家庭食用。”[2]56
公地,即Common Land,就是每个教区那些终年处于休闲状态中的敞地,因其大多处于未开垦的状态,也可被称为荒地[12]117。公地是敞田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每年条田收获之后和播种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条田作为放牧地区对村庄共同体所有成员开放,供其牲畜放牧。从每年的2月份到8月份,当春季作物生长时,条田不再开放,整个村庄的牲畜要被饲养在公地上。公地还被领主用于商业性质的牲畜饲养。坎贝尔和欧文顿的研究显示,自14 世纪以来领主和佃农对牲畜饲养的兴趣显著提高[5]42。随着15世纪、16世纪人口的持续增长,土地变得越来越紧缺,可耕地在开垦荒地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直到公地缩小到不能放牧村民的所有牲畜。这样一来,公地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领主和农民竞相争夺的对象。
公地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无主的土地,在原则上,它属于领主所有,人们有时把它称为领主的荒地[12]118。1066 年诺曼征服后,征服者威廉将英格兰村社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居民一起以保有制的形式封赐给各级领主。封建保有制将村舍居民变成了土地保有人,而庄园领主取代了原来的村庄共同体成为土地的主人。于是“庄园内无主性财产被初步认定归领主享有,领主不仅是庄园居民的领主,也是庄园土地的领主”[13]。
尽管公地名义上是领主所有的,但拥有公地权利(Common Rights)的农民可以合法使用公地。根据公地权利的渊源,公地权利又分为公地附属权(Common Appendant)、公地从属权(Common Appurtenant)和公地独权(Commoningross)。在英格兰最初的庄园里,每一块保有地都附带有一定的使用庄园荒地的权利。这种权利使土地保有者能够在荒地上放牧一定数量的牲畜,并且能够从荒地上采集泥煤作为燃料,还可以砍伐木料用于维修篱笆和房屋。这种权利附属于占有的土地,可以说是土地保有的一部分。这就是公地附属权的最初形式[14]221。公地附属权在1290年《买地法》之前就已存在的古老庄园里普遍适用,是自由佃户拥有的权利,因此也被视为自由保有权的基本元素。自由佃户能够凭借公地附属权在荒地上饲养用于农耕的牲畜[15]8‐9。依此权利放牧牲畜的数量由惯例确定;若无惯例,则限于荒地产草量所能供养牲畜的数量[8]259。与之相比,公地从属权起源于领主的赠予证书,适用于1290 年《买地法》之后的庄园里的自由保有,但这种权利进一步扩展,还包括被给予赠予证书的庄园里的公簿持有农或其他人。所放牧的牲畜不仅是农耕所必需的,还扩展至羊、猪、山羊甚至鹅。依照公地从属权放牧牲畜的数量或限于荒地产草量所能供养牲畜的数量,或是一个固定的数量[15]10。当公地从属权所能放牧牲畜的数量是一个固定值时,这种权利可以与土地或房屋分离,由此形成公地独权。例如,北安普敦郡提顿村一位名叫托马斯·斯瑞斯的织工把他的房子留给他的一个儿子,而把能够放牧两头奶牛的公地权利留给另一个儿子[16]。在这个案例中,后者拥有的就是公地独权。因此,拥有公地附属权、公地从属权和公地独权的农民可以合法使用公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居住在公地附近的穷人开始依据“默许和习惯”使用公地。这些人既包括茅舍农、雇工、手工业者和小零售商,还包括从外地迁来的移民和擅自占用公地者(squatters)。他们依据宽容的庄园习惯把茅舍建在公地上并利用公地上的自然资源生活,不仅可以在公地上放牧,而且可以利用公地上的灌木、森林、林下植被和沙石来修葺房屋、修建栅栏以及充当做饭和取暖用的燃料。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公地上捕鱼、打猎和采摘野果[17]。然而,他们对公地的使用是一种“默许”而非法律规定的权利[14]222。在公地充足的时期,领主往往默许这种“白搭车”①“白搭车”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个专门术语,意指在产权制度不明确的条件下没有付出劳动就无偿取得劳动报酬的行动。行为。因此,这些依据“默许和习惯”使用公地的贫穷小农认为自己是公地合情合理的使用者。
领主和农民从各自的土地权利出发,都认为自己对公地拥有一定的土地权利,导致公地的产权归属非常不明晰。领主十分渴望明确公地的产权归属,通过圈地的方式把农民排斥在公地的使用权限之外。早在13 世纪,就有领主圈占公地的记载。1235年《默顿法令》(Statute of Merton)是有关领主圈占公地的最早记录,该法令“允许庄园领主在荒地上给佃农保留充足的牧场之后圈占剩余土地”[18]。随着16世纪物价飞涨,饲养牲畜的利润显著增加时,土地变得不容易获得,领主也加快了圈占公地的进程。他们用篱笆和栅栏把公地围起来,剥夺了农民对公地的使用权。根据星室法庭所记载的1509 至1558 年间诺福克和萨福克的25个圈地案例显示,领主对公地的圈占引发了农民的愤怒[5]43。农民为了夺回公地使用权,与领主就公地展开争夺,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和纠纷。
早在1513 年,艾尔舍姆的领主埃德蒙·威思(Edmund Wythe)曾被指控非法圈占了黑文汉庄园的公地,引发了农民骚乱。1549年6月,阿特尔伯勒(Attleborough)、埃克尔斯(Eccles)以及威尔比(Wilby)庄园的农民们拆毁了威尔比庄园领主约翰·格林(John Green)在公地上树立的圈地篱笆,这一事件成为凯特起义的导火索[19]。此后,推倒领主的圈地篱笆更是常见的现象,例如,赫瑟西特(Hethersett)庄园领主约翰·弗劳尔迪(John Flow‐erdew)以及莫利(Morley)庄园领主哈巴特(Mr Hobart)的篱笆都被推倒[2]25,27。除此之外,在诺福克的庄园法庭和季审法庭案卷中也记载了农民和领主之间因争夺公地产生的纠纷。西蒙·森道尔(SimonSendall)作为在凯特起义请愿书签名的德普沃德(Depwade)百户区代表,他曾在丰塞特(Forncett)庄园的沃克顿(Wacton)和其他人一起在一块公地上犁了一道沟,目的是把这块公地与领主斯特拉顿·圣玛丽(Stratton’St Mary)的公地分开。在庄园法庭上他被罚款20 先令,因为他参与了公地纠纷[5]18‐19。
领主圈占公地遭到农民的一致反对。对于拥有公地权利的农民而言,领主不顾他们的土地权利把他们排斥在公地的使用权限之外,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对于依据“默许和习惯”使用公地的贫穷小农而言,领主圈占公地剥夺了他们的公地使用权,使他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利用公地上的自然资源生活,只能被迫离开土地。因此,他们联合起来在《请愿书》的第3条和第11条要求禁止领主使用公地。即便是禁止不了,也要对领主在公地上饲养牛羊的条件进行限制。随着15 世纪、16 世纪土地越来越紧缺,许多人开始在公地上过度放牧,尤其是有较大牲畜饲养能力的领主。因此,《请愿书》第29条要求土地年收入超过40英镑者不得在公地上饲养牛羊,以此防止他们故意过度放牧。
综上所述,公地不仅是依据“默许和习惯”使用公地的贫穷小农维持生活的重要保障,也是拥有公地权利的农民放牧牲畜所必需的。正是因为公地和农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当领主圈占公地使农民不能再像往常一样利用公地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抵制。“要求公地使用权”的条款在《请愿书》中多次出现,反映了公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意义。
四、结 论
在凯特起义的《请愿书》中,关于圈地、地租以及公地使用权的有关条款占了最多的比重,显然也是和起草者们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请愿书的起草者可以明显的分为两个阶层——富裕农民和下层农民。对于富裕农民来说,他们要求建立明晰的土地产权,保护有益于自身利益的圈地;对于下层农民来说,他们要求维护习惯保有,对其征收合理的地租和入地费,从而保护自己免受资本主义农业的攻击。公地使用权关系到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当领主圈占公地使农民不能再像往常一样利用公地时,富裕农民和下层农民联合起来对抗领主,与其争夺公地使用权。可见,凯特起义《请愿书》反映了16世纪英国不同阶层农民的地权诉求,有助于更加客观地认识社会转型时期英国的土地产权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