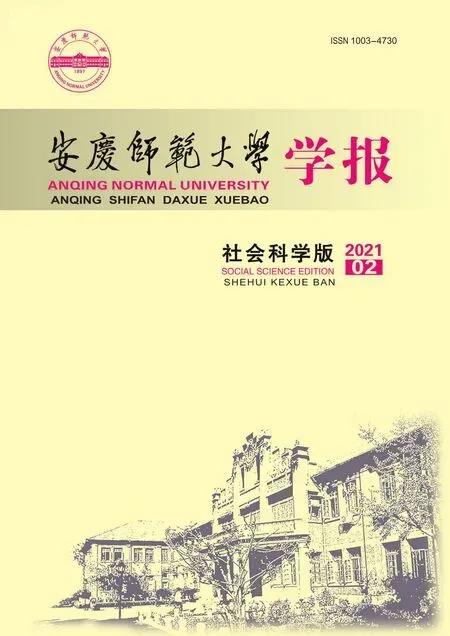论姚莹的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戴 赟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039)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又自号幸翁,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大师姚鼐的侄孙,也是著名的“姚门四杰”之一。嘉庆十三年(1808 年)中进士,自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开始任职,曾在福建、台湾、江苏等地做官。姚莹做官清廉富有政绩,在闽经常受上司嘉奖,声名鹊起。在任台湾兵备道期间,曾率领台湾军民抵抗英军的侵略。近年来,学界对姚莹的研究成果颇多,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其生平与交游、爱国思想与抗英保台、哲学及文学、经世思想及边疆史等方面[1]。关于姚莹的经世致用思想,有学者认为以姚莹为主的青年经世派在桐城兴起,并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对清中叶学风转变起到积极作用[2]。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姚莹的经世思想进行一些补充研究。姚莹的经世思想不仅体现在文章著述方面,也体现在对家族的认识和中外攻防等方面。在文章著述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济时致用的目的;在家国关系上,主张家运与国运同一,家运建立在国运之上,主张从正史中建构家族祖先,家国一体;在中外关系方面,主张中华与外国在国势上已经逆转,特别重视“夷情”和防务。
一
嘉道年间,政治腐败,时弊丛生,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此种社会现实也深深地刺激了桐城派的文论思想,姚莹作为桐城派的传人,为桐城派的文风注入了经世致用的新鲜血液,从而促进了桐城派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桐城派的文风历来讲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姚莹对桐城派文风做了整体性的继承以外,还对当世文人士大夫提出了远远超出文风的“体用”观。嘉庆十六年(1811 年),姚莹在给自己的至交好友吴岳卿书信中就曾提到:“身心之正明其体,伦品之济达其用。总之,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3]120
姚莹所阐述的“四端”,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嘉庆十四年(1809 年),姚莹接受了两广总督百龄的聘请[4]44。在任职期间,亲眼目睹了海盗肆虐百姓,英人横行侵略。此种社会现实也让他将学问与实践相联系,提出了“经济”之说,所谓“经济”就是经世致用之意。
所谓“多闻”,顾名思义即是见识广博之意。姚莹将“多闻”代替桐城派文论中的“考据”,是蕴含了他对现实思考的深意。乾嘉汉学曾盛极一时,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大都穷经皓首,埋头于故纸堆中。此种学问与社会现实联系甚少,而当时晚清社会所处的环境是,列强环伺,大有侵并中国之心。“多闻”也是对只知学习儒家经典而不关心社会实情的一种批判。姚莹说:“取先儒删弃蹖驳不经之说,搜而出之以为异宝,炫博矜奇,毫发无益实用。末学空疏为所摇惑,群而趋之,咸以身心性命之说为迂疏。”[3]24据此,姚莹认为这种学问只是“末学空疏”,而对现实生活“毫发无益实用”。不仅如此,姚莹的“多闻”还与自身实践相结合,他一直强调要关注外国的国情,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他自己所言:“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愤败至此耳。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聩聩从事而不败者也。”[3]273“多闻”这一点也是与他的经世思想相联系的。
所谓“文章”,即是写作之事。古人云“文以载道”,文章大体上都寄托了作者的思想与精神。姚莹认为文章是继承了先贤们的思想,其主要用途是要立足于实践之中,姚莹在自己的文章中将“道”的思想一以贯之,但最终的创作主旨思想寄托在“功”上。“道足以继先哲,功足以被来兹,若此者已不必传,天下传以被来兹”[3]38。正是坚持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文章才具有非凡之功。文章不仅培育价值观,引导着价值取向,维护着伦理纲常,“夫文者,将以明天地之心,阐事物之理,君臣待之以定,父子赖之以亲,夫妇朋友赖之以叙其情而正其义”[3]124;文章还要具有现实关怀,要关心世风时情,“文章之大者,发明道义,陈列事情,动关乎人心风俗之盛衰。”[3]112
清朝的科举制是以八股文章取士,而八股文章向来为后世所诟病,由于八股文章框架太严,往往束缚思想。姚莹所提倡的四点要端,具有对八股取士的批评意味,认为科举制是“猥俗浅陋”的末流。“后世学术纷裂,纯杂多门,然一艺之成,咸足通显当时,称名后世,未有猥俗浅陋如近日科举之学者也。”[3]120姚莹认为学者学习古人,不能从现实出发,是误国误人之举。他说:“古之学者不徒读书,日用事物出入周旋之地皆所切究,其读书者,将以正其身心济其伦品而已。”[3]120从这一段话也可了解到姚莹对于盲目的学古持鄙夷的态度,主张得其精髓。姚莹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一方面是因为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文章束缚太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八股文章不能从实际出发,解决现实问题。
乾嘉时期汉学风靡一时,姚莹对于汉学家舍本逐末的治学之道,认为是枉费精神,并且认为他们毕生从事的文字训诂等工作,其实不过是治学的入门。与此同时,他也批评宋学家们崇尚空疏的习气。他认为“文章一道”,如果不能与实际相结合,经世致用都是无用之言。这一说法也是针对当时中国晚清内外交困的社会情形而提出的。当面临社会危机之时,学术界需要提出解决危机之道。文风与经世思想是相互影响的,姚莹对以前的治学之道的否定,为清代中后期的治学提供了方向与动力。
姚莹在其著作上也体现了他对经世致用的理解。他的著作包括《康 纪行》《东槎纪略》《识小录》《寸光阴》等,《康 纪行》一书是姚莹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体现姚莹经世思想的代表作,从中不难看出姚莹的行文特点。他提倡“沉郁顿挫之妙”而反对“浮率平直之病”[5]。此书是姚莹被贬官西藏后,为了解决藏僧纠纷,以其出使途中的札记汇编而成。该书全面介绍了西藏的风俗地貌,以及关于西藏周边的尼泊尔、印度等情况。而这本书的出版目的,也是出于对现实情况的考虑,“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3]280。他对英国和俄国在印度之间的武装斗争十分关注,认为“俄罗斯之垂涎印度,亦犹英吉利之垂涎前后藏也”[6]519。他对于英俄两国各自争夺殖民地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可以利用两国的矛盾而达到“制驭”的方针,这对当时内忧外患的晚清社会来说,可以缓和一下来自外部的压力。由此可见姚莹面对实际情况,不单单是叙述以成作,而更重要的是实现“事功”,谋求独立富强以驭外强。《康 纪行》这一著作可以看成是和魏源《海国图志》在同一时代经世致用文人的良苦之作。它们最为突出的一点,都是希望国人能够了解外国,破除狭隘的“天下”思想,从而真正地知道“万国”的局面,揭露外国列强的“亡我中华之心”。他对祖国边疆的考察,对夷事夷情的关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著作,是他济时致用文风的重要体现。
总之,文章一道,文道合一,讲求文章著述的经世致用,是姚莹一以贯之的理念。姚莹在著述方面的现实追求,也反映在家谱的编修以及对家国关系的认识方面。
二
在传统社会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儒士的理想和最高追求。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血缘文化,家族这样的血缘组织比较发达。齐家收族的意思是使家族成员能够齐心协力、和睦共处、共同发展。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编修家谱,尤其是宋以后家族组织庶民化、世俗化之后,家谱的教化功能凸显。编修家谱可以用来约束和管理族人,实现推行教化、稳定家族和社会的功能。嘉道以降,世风日下,社会矛盾和家族内部矛盾也在加剧,这个时候编修家谱的现实意义就更为重要。姚莹本着经世致用的思想,对于家谱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并将家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进行了关联,放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
姚莹在家谱编修方面,坚持家谱与国史是有紧密关联的,这一方面表现在祖先世系的建构上,要以正史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进行详实的考证,实事求是,建构祖先世系;另一方面,同样要依据正史,去除家谱中虚构、攀附、妄冒的祖先,还历史以真实。
姚莹所在的桐城姚氏家族在第五次编修族谱时,编者曾将稿本寄给姚莹,姚莹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和主张。他认为修谱时应该“爰据历朝传表,编其世系,寄存族中备考”[3]158。这是对于世系的处理办法。家谱编纂中最难的可能就是世系的建构。因为如果没有及时记录,高祖以上的祖先实际上很有可能被遗忘,更遑论多少代之前的先祖了,更是难以接续。这是每一个家族长时间不修谱就会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姚莹采取的办法就是,广泛考察正史中关于姚氏历代先人的记载,拟清世系,辨认与本族的关系,从而与家谱所编写的内容相印证。他通过详细考证,指出了本族所修宗谱的错误。他特别强调正史资料对家族世系的意义,反对妄附世系,“人莫不有祖,诬之不可,无其事而为说,犹之夫之诬也。伯昂云遍考传表,何以有此失?良有惑于赣州旧谱一言,又不知会稽族谱之无据,辄喜而依附之耳。乌知正史具在,考之固未详乎!此莹所不得辨者也。”[3]161原先修谱之人正是由于不认真查阅史籍,而且轻信旧谱的一家之言,不知道旧谱并没有实据,只是旧谱怎么说他就怎么记,才有这样的失误。并且他批评修谱的姚元之:“伯昂不能援正史以纠其妄,乃反援之以紊吾宗。”
姚莹不仅指出了自己族人原先修谱的错误之处,而且他在修谱时也贯彻了他的一贯原则和方法。即“窃本诸家乘,上求国史,旁采各省郡州县志,及贤士大夫之文,搜辑所闻,编为《麻溪姚氏先德传》。”[3]287姚莹广泛的搜集资料,并且与正史相互考证,务实不务虚。
姚莹不仅给自己本族的族谱中提出要注重实际,不务虚言,而且给别族修谱序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例如《桐城破冈胡氏宗谱》中,胡氏族人将自己的迁桐世系定于“安定”。姚莹认为桐城破冈胡氏宗谱中对于迁桐胡氏来源记载有误,并且将迁桐胡氏定于“安定”之地提出疑问。“稍有疑似,子皆阙之,谱其所可知,阙其所不可知。然而犹系于安定者,何哉?”[3]289姚莹认为宗谱中缺失的地方,就应该存疑,不应该不加分别地都收纳。并且他进一步指出胡氏族人修谱时可能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即“岂不以凌氏《万姓统谱》总系胡于安定乎,抑未察凌氏之疏乎?”[3]290正是因为胡氏宗族修谱时没有考察明代万历年间凌迪知所编著《万姓统谱》的疏忽而照抄错误之处。从这儿可以看出,姚莹贵疑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
对于桐城破冈胡氏的世系问题,姚莹也给出了他自己的解决办法。他认为:“然则今兹之谱宜将何系?曰:系之以桐城破冈,则不必远望,而前后乎安定之望……不定所望而望自存,犹愈乎自紊其系也。”[3]291将世系定于桐城破冈,不必攀附其他的地方,将来桐城破冈就成了以后考察的世系所在,如果定于存疑的地方,也会紊乱自己的世系,得不偿失。
在给桐城桂溪项氏作谱序时,姚莹显示出了他的家国同运的经世理念。“呜呼,士大夫家族盛衰,岂不视国运哉!”[3]292他认为一个家族的繁盛与国运是紧密关联的。姚莹的视野不是关注一家的繁荣衰败,而是立足于整个国家进行考察,这跟当时的时局氛围以及经世致用的理念是一致的。并且他讥讽世俗之人道:“每怪世人言,受国恩者必尝为显宦,否则群笑之以为侈妄。曾不思身享太平,得鼓腹于陇亩以繁衍子孙者,伊谁之力?”[3]293
姚莹还注重家族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例如他在《宗谱见存人数记》中就曾说到:“岂族之盛衰又不计以众寡计耶?夫众寡之数存乎天者也,若贤知之事,则人皆可勉。凡吾宗人惟尽其所当为者,以求合于天焉,庶几延世之道乎。”[3]385从中可看出,姚莹从人口数量论及人口质量,认为人口的数量是由上天决定的,但是人口的质量“贤知”是人力可为的,应当尽力去做。这也体现了姚莹的“事功”思想,注重实际生活。
姚莹跳出小我、小家、小族,明确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安居乐业、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撑力量、保障力量来自于国家。从这个意义上,家族不能独立存在,家族与国家是同一个命运,是命运共同体。有了国运,才有家运,家运之盛是由于国运之盛,国运衰落自然家运衰落。在姚莹的思想中,有一种超乎个人与家族的国家理念,以国家太平、人民幸福为主旨,具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
姚莹这种家国同运的经世理念,既有对传统收族理念的继承,也有对其发展和补充。姚莹对家国关系是以国家为基础的,其经世致用思想还反映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
三
姚莹为官从政最能体现他经世思想的地方,即是他对“夷情”非常关注。面对外夷,姚莹的防范之心始终贯穿于他的思想之中。他身具忧患意识,从实情出发,讲求利功。同当时的经世派人物一样,他认为了解“夷情”是非常有必要的,如同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早年间他便说:“天下之道,守在四夷,岂可茫然存而不论乎?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6]2这种对“夷情”的关注也是始于在广州做幕僚期间,当时他与总督松筠交好,从而获得了一些中外信息和域外知识,开拓了眼界,从此开始留心并研究域外和边疆情事[4]52。
姚莹在广东任职期间就对晚清社会内忧外患的局面非常担忧,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不能将国内治理平定,肯定会引起外夷的窥伺之心。在《上座师赵分巡书》中就曾说道:“夫极众力未集之时,不设策诛戢之……且夫粤地内有瑶黎杂处,外有蕃夷往来,我之虚实,彼皆知之,今吾官军骄至不能戢定内贼,不虑有启彼之戎心乎。”[3]45姚莹不仅是对夷情的关注,更加注重国家社会内部的稳定。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姚莹赴闽从政,起先由于闽地民风剽悍难以治理,后来他因地制宜推行相应的政策,使地方得到大治。“俗强悍好斗,盗贼滋多,莹治之严。太宜人戒之曰:古者循吏治术不同,固当因地制宜。”[3]95姚莹在闽地才干突出,被闵浙总督董教增器重,尝称其为“闽吏第一”。随后不久,便升任台湾任职。
姚莹在广东做幕僚期间对于“外夷”非常敏感,他在台湾任职时也有所体现。道光四年(1824年)八月,他曾对夷船滞留鸡笼港贩卖鸦片事情,写信给台湾道孔昭虔,指出要阻止其在台湾的活动,警惕其对台湾的窥伺之心。“夷情叵测,始意不过图售鸦片。……及往来台湾,海道既熟,又见我海防之疏……能保无他日之忧耶?……又畏夷船高大,不敢驱逐。”[3]64由此可见,姚莹确实眼光长远深思熟虑,认为图谋鸦片利益是小侵吞之心为大,而且提出了对海防的担忧之情。
姚莹在台湾任职时的经历,使他具有了初步的海防思想。由于他积极了解夷情,为随后保台抗英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夏,姚莹在台加强战备,获得了“鸡笼战役”的大胜。“夷五犯台湾,不得一利,两击走,一潜遁,两破其舟,擒其众而斩之。”[3]267这次胜利发生在鸦片战争期间,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说击溃了外国的进攻,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此次胜利波云诡谲,朝廷有人参奏姚莹,认为他有“贪杀冒功”之嫌。不久后姚莹虽胜而获罪,这沉重打击了他对朝廷当局的信心,更使他对于国家的前途未来深感茫然。这一点可以在姚莹与好友的通信中略知一二,他感叹道:“举世获罪,独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镇道受赏,督抚无功,又有以小加大之嫌。况以英夷之强黠,不能得志于台湾,更为肤诉之辞。”[3]266此等言论虽然有牢骚之处,但更表现出其满腔的爱国之情与经世之思。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姚莹被贬于四川,并没有就此沉沦,在给光律原的信中说到:“弟不自揣,妄意济世利人……生平多历崎岖,惟气未衰耳。”[3]267如此情况下,姚莹仍怀经世之志,希望还能够济世利人。当时有些官员闭目塞听不留心海外之事,姚莹对此尖锐地批评道:“古今异势,非可拘谈。……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6]358由此可见,即使被贬偏地,姚莹一直都在关注“夷情”,并说“外夷”都“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有一丝悲凉也有一丝无奈的意味。
在姚莹看来,中华“茫昧自安”,曾经的国势已不再;外夷“勤求世务”,国势蒸蒸日上。时异世殊,华夷异势,他为国运所深忧,正因为如此,他极为重视对国外情报的收集工作,极为重视防务,因为他知道,衰弱的中国正在成为西方列强的口中肥肉,他也只能鼓与呼,并尽己所能,鞠躬尽瘁而已了。
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想是在中国社会即将转型时期出现的。这一经世思想风潮的出现是有其大的时代背景,一方面,社会内部矛盾重重,这一环境促使姚莹用经世思想谋求救世之方,另一方面,西学东渐让姚莹眼界大开,丰富了自身的思想资源,不再束缚于迂阔之习,而是“留心经世学,遇事激昂奋发,锐欲有所为”[7],关注现实社会的问题,提出解决之道。
姚莹的文章著述既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又关注现实,讲求济时致用,注重事功。姚莹主张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相同的,他在祖先建构方面也是以正史人物为依归,实际上是其家族属于国家、家国同运理念的另一种阐释。姚莹在从政方面,深刻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与外国在国势上已经发生了逆转,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当中,因此他尤其重视国家治理和“夷情”防务。总之,姚莹通达世务,关心国计民生,其经世思想一以贯之于修齐治平的每个阶段。姚莹的经世思想虽然没有突破传统经世之学的窠臼,但他已然是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