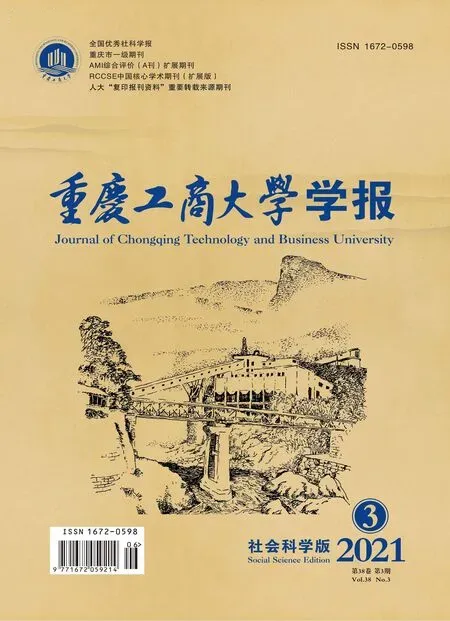《周易》易简原则与苏轼的处世哲学*
徐建芳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一直以来,人们在探究苏轼潇洒自在的原因时,大都认为是受了佛、道思想的影响。[1]毋庸讳言,佛、道思想在帮助苏轼超越现实拘囚中的确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终生研治《周易》且有解易专著《东坡易传》传世的苏轼,不可能不受到《周易》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正如耿亮之先生所说,“东坡人格的文化底蕴正是《东坡易传》中的易学思想和哲学智慧”[2]。余敦康先生说:“苏轼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写了《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著名的经学著作。……如果不了解他的易学,便无从了解他的文学,也难以了解他的为人。”[3]基于此,本文拟从《周易》易简原则角度探讨苏轼之所以那么潇洒自在的哲学思想根源。
一
“易简”是《周易》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而且是《周易》三大原则“变易”、“不易”、“易简”中唯一直接被《易传》明确描述出来的原则(“变易”与“不易”都是后人根据《易经》的哲学思想概括出来的),在《周易》哲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像陆九渊所说,“圣人赞《易》,却只是个‘简易’字道了”[4]。
在《易传》中,直接提到“易简”的共有四处,这四处都是用来描述生成其他六十二卦的父母卦——乾、坤两卦的德性及乾、坤具备易简之德的巨大功用。具体如下:(一)乾、坤的德性就是“易简”:“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5]296是说,乾的特征,坚确刚健而以平易显示于人;坤的特征,隤弱柔顺而以简约显示于人。韩康伯注曰:“确,刚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恒一其德,物由以成,故简易也。”[5]296(二)乾、坤的易简之德达到了“至德”的境界:“夫乾,……夫坤,……易简之善配至德。”[5]273是说,乾、坤的平易简约之美善原理可以配合至高的道德。(三)乾、坤具备易简之德就可以洞知险阻之所在:“夫乾,……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德行恒简以知阻。”[5]320是说,乾的德性恒久平易而能知晓艰险所在,坤的德性恒久简约而能知晓阻难所在。(四)乾、坤具备易简之德就可以洞晓天下万物之理,可以成就可久、可大的德业,可以在天地之间确立自己的位置: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5]259-260
是说,乾以平易为人所知,坤以简约见其功能;平易就容易使人明了,简约就容易使人顺从;容易明了则有人亲附,容易顺从则可建功绩;有人亲附就能长久,可建功绩就能弘大;可长久是贤人的美德,可弘大是贤人的事业;通过易简的方法,就可以穷尽天下之理;能够掌握天下之理,就可以参天地之所宜而于其中确立自己合适的位置。
由上可见,象征天、地的乾、坤两卦的德性就是易简,具备易简之德就能洞知险阻之所在、洞晓天下万物之理、成就可久可大的德业、确立自己合适的位置。而根据《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6]的创作目的,推究天、地的规律是为了明白人生所应该遵循的规律,因为作为天地间一份子的人类必须遵循天、地规律;那么,人类理所当然应该效法象征天、地的乾、坤两卦的易简之德。
二
终生研《易》的苏轼对《周易》所论述的易简原则的重要性及其功用深所认同。如其《东坡易传》曰:“易简者,无不知也。”[7]144“已险而能知险,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尝有也。夫险阻在躬,则天下莫不备之;天下莫不备之,则其所备者众矣。又何暇知人哉?是故处下以倾高则高者毕赴,用晦以求明则明者必见,易简以观险阻,则险阻无隐情矣。”[7]144在苏轼看来,秉守易简原则,则可无所不知,尤其是能洞察险阻隐情。可见,苏轼对易简原则在人们认知活动、立身处世等中的功用充分肯定。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苏轼在思考如何贯彻实践易简原则时,体悟到了奉行易简原则的必备心理机制——“无心”。这可说是苏轼对《周易》易简原则的创造性阐发。如其《东坡易传》解《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曰:“乾无心于知之故易,坤无心于作之故简。易故无所不知,简故无所不能。”[7]121乾之所以能“易”,坤之所以能“简”,是因为它们都以“无心”的态度行事。易言之,“无心”是易简的先决条件。又如其释《系辞下》“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说:“刚而无心者,其徳易,其形确然。柔而无心者,其徳简,其形隤然。论此者明八卦皆以徳发于中而形著于外也。”[7]136因为乾、坤内在有“无心”之德,所以外在才有简易、纯粹之表现形态。苏轼甚至认为,“无心”是专一、有信、易知、易从、万物“尽其天理”、圣人“备位于其中”等的必备前提。如其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曰:
易简者,一之谓也。凡有心者,虽欲一不可得也,不一则无信矣;夫无信者,岂不难知难从哉!乾坤惟无心故一,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从之也不难。[7]121
意思是:易简就是专一不杂。凡有心机的人,虽欲专一也不可得;不专一就无信用,无信用则令人难知难从。乾坤只因无心所以能专一,专一所以有信用,有信用所以外物容易认知它、跟从它。又如其解“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曰:
夫无心而一,一而信,则物莫不得尽其天理以生、以死。故生者不德,死者不怨,无怨无德,则圣人者岂不备位于其中哉?吾一有心于其间,则物有侥幸、夭枉不尽其理者矣。侥幸者德之,夭枉者怨之,德怨交至,则吾任重矣。虽欲备位,可得乎?[7]121
意思是:无心则专一,专一则守信,万物则能顺其天理而生、而死。因此,生者不必认为自己的“生”是圣人的恩惠,而对圣人感恩戴德;死者不必认为自己的“死”是圣人的残害,而对圣人心生怨恨;既不遭报怨也不受感戴,则圣人就能在天地之间确立其合适的位置了。假如圣人一有心于万物的自然运行,则万物就会有侥幸、夭枉不能尽行其天理者。侥幸者感恩圣人,夭枉者怨恨圣人;德怨交至,则圣人的责任就重了。即使想确立其合适的位置,岂可得乎?可见,“无心”的确是圣人及天下万物尽其性命之理、确立其合适位置的先决条件。
基于以上认识,苏轼特别推崇“无心”这一处世之道,在著作中屡屡提及。如《东坡易传》释《易·中孚·彖》:“以‘巽’行‘兑’,乘天下之至顺而行于人之所说,必无心者也。”[7]112《杜纯可刑部员外郎》:“以不忍之心,行无心之法,则予汝嘉。”[8]1112《郊祀庆成诗》:“无心斯格物,克己自消兵。”[9]1828等等。其中最集中地阐述他这一“无心”、“无思”处世态度的莫过于《思堂记》:
建安章质夫,筑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将朝夕于是,凡吾之所为,必思而后行,子为我记之。”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少时遇隐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与欲,若是均乎?”曰:“甚于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隐者指之曰:“是有蚁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蚁漏者。”思虑之贼人也,微而无间。隐者之言,有会于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乐,不可名也。虚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易》曰无思也,无为也。我愿学焉。[8]363
章质夫筑堂命名为“思”,本是为了警戒自己做事应深思熟虑,不可草率行事。但苏轼丝毫不顾及朋友的心意,而大发其“无思”之论:“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因为苏轼认为:(一)当事情未发生时思虑,则事情未必按照预虑的发生;当事情已经发生再思虑,则于事无补;所以终生“不知所思”。(二)情动于衷而发于言,不吐不快;因此,宁可一吐为快,也不愿憋在心里使自己不畅快。(三)君子对于善、恶,应该像“好好色”“恶恶臭”一样直情而动,哪里还需要思虑、计较其美恶而避就之呢?若临事而为利害思虑计较,则必不能成事。(四)人生的穷达得丧、死生祸福早已由命运决定,个人的思虑谋划根本无济于事。(五)思虑对人的贼害尽管微小但从无间隙,比欲望对人的戕害更严重。(六)“不思”有不可名状的快乐。因此,苏轼宁愿学习《周易》所倡导的“无思”、“无为”处世之道,也不愿用心思虑。此文写于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43岁,已过不惑之年。这应该不是他的一时兴到之言,而是他处世态度的真实流露。这从苏轼其他诗文中也可得到印证,如《密州通判厅题名记》:
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疎,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以此尤不可与深中而多数者处。君既故人,而简易疎达,表里洞然,余固甚乐之。[8]376
因不暇思虑对象之亲疏远近、品行邪正,有言则发、言无不尽地“输写腑脏”;结果轻则因自己的疏略而引起人的怨咎,重则被那些“深中而多数者”深文周纳;因此苏轼最喜欢那些“简易疏达,表里洞然”的人。又如《李仲蒙哀词》:“中心乐易,气淑均兮。内外纯一,言可信兮。……浑朴简易,弃弗申兮。往者不还,我思君兮。”[8]1964李仲蒙最令苏轼怀念的就是他秉性乐易、内外纯一、言行可信、浑朴简易。
正因崇尚“无心”、“简易”的处世态度,所以苏轼向来反对处世中使用机巧、智谋。如其《寄题清溪寺》:“口舌安足恃,韩非死说难。自知不可用,鬼谷乃真奸。遗书今未亡,小数不足观。秦仪固新学,见利不知患……君看巧更穷,不若愚自安。”[9]50首句以韩非为例,“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9]50,说明口舌之智不足依恃。接着批评鬼谷子明知智谋不可用,却仍把那些不足观的“小数”传给苏秦、张仪,使二人皆因智巧而不得其死。因此,苏轼认为智巧反而更易使人走向绝境,不如简易朴实反倒能使人获得平安。又如其《再用前韵寄莘老》:“君不见夷甫开三窟,不如长康号痴绝。痴人自得终天年,智士死智罪莫雪。”[9]377“夷甫”指王衍,“长康”指顾恺之。据《晋书》载:“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10]卷四三,p1237-1238“初,恺之在桓温府,常云:‘恺之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耳。’故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10]卷九二,p2406王衍不以经国为念,用尽心智为自己营造“三窟”,结果国破家亡身死;而顾恺之虽然看起来痴呆愚鲁,却能够终其天年。正所谓“聪明之不可恃也”[8]31!以此,苏轼主张:“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8]1363智术对人才来说并非第一位要素,识见气度才是首要的。
三
因为推崇“无心”“简易”的处世态度,所以在人际交往上,苏轼强调首先应该“诚”,应“不拒不援”“得其诚同”。如《东坡易传》解同人卦彖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曰:
“野”者,无求之地也。立于无求之地,则凡从我者,皆诚同也。彼非诚同,而能从我于野哉!“同人”而不得其诚同,可谓“同人”乎?故天与人同,物之能同于天者盖寡矣。天非求同于物、非求不同于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诚同,而可以“涉川”也。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其诚同,与之居安则合,与之涉川则溃矣。涉川而不溃者,诚同也。[7]27
同人卦是讲和同于人的,而卦辞却只说“同人于野,亨”,难道在其他场所与人和同就不亨通了吗?在苏轼看来,野外是无所求之地,自己立于无所求之地,则凡是跟从我的,皆是真心诚意与我和同;若不是真心诚意,岂能跟从我到一无所求的野外!就像天本与人和同,但万物能同于天者却很少。天既不求同于物,也不求不同于物;只是立于上面,天下之能同者自至,不能同者不至;“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这样就能得到真心诚意与己和同的人,就可以同舟共济、共涉患难。若不得其真心诚意和同,则与之居于安稳环境则合同,与之涉越险难则必溃散。只有那些涉越险难时仍不溃散的,才是“诚同”。这段释文可说是苏轼交往原则的理论表白:真心诚意待人,不以任何外在利害为交往条件。愿意来与我交往者不是我拉拢的,不愿意来与我交往者不是我拒绝的,“不拒不援”“得其诚同”。
当苏轼把这一原则落实于具体的人际交往中时,便更明确地提出了“至诚相与,简易平实,不为虚文”的交往准则:
蒋侍郎堂家藏杨文公与王魏公一帖,……其略云:昨夜有进士蒋堂携所作文来,极可喜,不敢不布闻。谨封拜呈。
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观此帖,不特见文公好贤乐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补于公者,亦固多矣。片纸折封,尤见前人至诚相与,简易平实,不为虚文。安得复有隐情不尽不得已而苟从者。皆可为后法也。[8]2550
杨文公夜里发现一个人才,早晨立即写了张帖子把他推荐给宰相王魏公。一则可见杨文公是一位好贤乐士而非嫉贤妒能的君子,一则可以想见他平日对王魏公的治国安邦肯定也提供了不少补益。由这“片纸折封”就可见出前人那种“至诚相与,简易平实,不为虚文”的高风亮节。哪里还会像后人那样发现人才时尽力隐瞒遮蔽、迫不得已时才苟且行事呢?苏轼对此帖特加题跋的目的就是希望后人效法杨、王二公之间这种交往态度。“精神还仗精神觅”![11]苏轼平日若没有这样的交往心态,岂能从别人的“片纸折封”里面感悟到这种交往态度!
苏轼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他在自己的人际交往中就切实奉守了这种交往原则:苏轼向来不喜欢与人虚情假意地客套应酬,总是迫不得已才与人应和。如其《答舒尧文二首》之一:
轼天资懒慢,自少年筋力有余时,已不喜应接人事。其于酬酢往反,盖尝和矣,而未尝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谓和者,又不能给,虽知其势必为人所怪怒,但弛废之心,不能自克。闻足下之贤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远,加之往来者,具道足下,虽未相识,而相与之意甚厚。亦欲作一书相闻,然操笔复止者数矣。因与贾君饮,出足下送行一绝句,其语有见及者,醉中率尔和答,醒后不复记忆其中道何等语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语,惘然如梦中事,愧赧不已。[8]1670
这里虽然字面上说自己“自少年筋力有余时,已不喜应接人事。其于酬酢往反,盖尝和矣,而未尝敢倡”,是因为“天资懒慢”所致;其实更深层的心理原因应该是他所奉守的交往准则“至诚相与,简易平实,不为虚文”使然。因此,尽管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他都应该给舒尧文写封书简一通相交之意,但几次三番都拿起笔又放下了。若不是看到舒尧文给别人的送行诗里提到自己,才于醉中率然作诗和答;苏轼大概绝不会先给舒尧文通信。这种交往态度在苏轼是一以贯之的,又如《与蒲诚之六首》之一:“闻轩马已至多时,而性懒作书,不因使赍手教来,虽有倾渴之心,终不能致一字左右也。”[8]1817《谢吕龙图三首》之三曰:“某久以局事汩没,殊不获觏止。窃惟应得疏绝之罪于左右,不意宽仁含垢,察其俗状之常情,恕其简略之小过,光降书辞,曲加劳问,拜贶之际,益增厚颜。旦夕诣宾次。”[8]1824与上文所述如出一辙。可见,不管是对陌生人,还是对朝中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苏轼都始终秉持着至诚相与、简易疏略的交往态度。
四
“易简”原则贯彻于苏轼衣食住行中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衣食住行上简略草率,从不讲究身份地位。如《北窗炙輠录》载:“东坡性简率,平生衣服饮食皆草草。……观其岸巾,止用一麻绳约发耳。又,筑新堤时,坡日往视之,一日饥,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贮其陈仓米一器尽之。大抵平生简率,类如此。”[12]文中所记乃苏轼任杭州知州时的事。作为一州最高首长的苏轼“止用一麻绳约发”,丝毫不介意吃百姓的“陈仓米”,东坡的简率草略的确名副其实!这一点从苏轼的自述中也可得到证实,如苏轼给王定国的信中说:“书意欲一相见,固鄙怀至愿,但不如彼此省事之为愈也……某其余坦然无疑,鸡猪鱼蒜,遇着便吃,生病老死,符到便奉行,此法差似简要也。”[8]1528王定国是苏轼患难与共的朋友,曾在“乌台诗案”中受苏轼牵累而被贬蛮荒多年。王定国致书苏轼想见一面,这也是苏轼的至愿;但生性简略的苏轼认为不如不见彼此更省事。至于自己的日常饮食则从不挑三拣四,“遇着便吃”,生病老死,顺其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苏轼平日养成了这种简率的生活方式,所以才使他能够坦然应对被贬蛮荒、流放海外的恶劣生活环境。如他初贬黄州时给朋友写信说:“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8]1412被贬惠州时给朋友信中说:“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8]1864-1865《老学庵笔记》还曾记载这样一则轶事:“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13]“黄门公”指苏辙。文中所记乃苏轼晚年被贬海南,苏辙被贬雷州,他们在前往贬所途中相遇后所发生的事。面对难以下咽的粗恶食物,当苏辙还在对食而叹时,苏轼已经一扫而空,“大笑而起”。若不是早已习惯了这种简易草略的生活方式,当被贬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8]1628的儋耳时,苏轼岂能应对裕如、安然无恙地度过那九死一生的贬谪岁月?
另一方面表现为生活节俭。如《鸡肋集》叙述苏轼为人:“刚洁寡欲,奉己至俭菲。”[14]我们从苏轼的下列文中也可证明这一点: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乂挑取一块,即藏去乂,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8]1536
知治行窘用不易。仆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悭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侪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又《诗》云:“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8]1499
……此外又有一事,须少俭啬,勿轻用钱物。一是远地,恐万一阙乏不继。一是灾难中节用自贬,亦消厄致福之一端。[8]1514
这三则材料均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时。第一则材料大概是秦观来信中为苏轼被贬黄州没有了经济收入,而为他的生计担忧,所以苏轼不无自嘲地详细告诉他自己的“痛自节俭”之法。向来给我们以豪爽不拘、自由潇洒印象的苏学士,如今竟然为了节省开支而精打细算;这判若两人的形象实在令人忍俊不禁,但又为他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坚强勇气油然生出钦佩之情。与历来那些中道败落,却不敢正视现实,仍要装体面、摆阔气的虚荣、软弱文人相比,苏轼的俭素难道不更值得我们景仰吗?难道不是另一种潇洒吗?当然,苏轼的节俭绝不同于常人的斤斤计较,只是比往日更节制一些而已。正如后文所说“吾侪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他在体验另一种生活滋味呢!否则,他就不可能轻松地宽慰秦观说:到积蓄用完时,肯定有别的办法,水到渠成,不必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被贬中的苏轼何其潇洒自在!后两则材料都是规劝朋友们应加节俭的。苏轼认为,人应克制对口体之欲的追求,多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尤其是遭难中,节俭自贬一则可以防止“阙乏不继”,一则可以“消厄致福”。这均可说是苏轼处贬经验的自我写照!
综上所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在《周易》易简原则启示下,苏轼养成了无心的处世态度、至诚简易的交往原则、简率草略的生活习惯,从而使他能够毫无机心、任情率性、随遇而安地应对人生中的一切境遇,展现出潇洒自在的精神风貌。通过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使人们对《周易》的人生智慧及苏轼的思想根源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与了解,而且对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崇尚机谋、人际复杂、奢靡浪费等不良风气也可起到警醒、针砭作用;简易朴实的生活也许更能让人们获得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