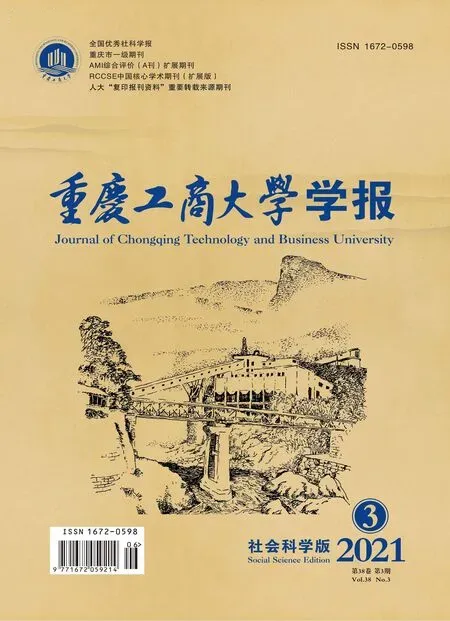慢直播的互动仪式建构与融合传播*
王建华,宋亭芳
(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024)
2020年伊始,一场来势汹涌的“新型冠状病毒”最早在武汉被发现,并在短时间内蔓延至湖北以及全国,引起了大范围的社会性恐慌。目前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这有赖于我国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同样得益于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表现。主流媒体在此次疫情的危机传播中不仅起到信息沟通作用,而且发挥着重要的情感疏导作用,尤其是主流媒体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一系列融合传播举措。
央视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于2019年9月上线的视频平台,拥有5G、4K、AI、VR等技术支撑。2020年1月到7月,央视频上线的《疫情24小时》栏目分别推出《与疫情赛跑——全景见证武汉火神山医院崛起》《近景直击武汉雷神山医院》和《云守望:见证此刻春暖花开》等系列直播,对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工地,武汉长江大桥、洪山广场等地标性建筑进行固定机位直播。截至2020年2月4日,1月27日上线的医院建设系列慢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超过1亿;截至2020年7月28日,2月16日上线的“云守望”系列慢直播累计观看人数突破1.6亿。[1]除《疫情24小时》外,央视频还推出《江城武汉,人间烟火》等慢直播节目。与常见的真人秀直播、游戏直播等模式不同,慢直播具有播放时间长、画面不加修饰、无剪辑、无主持等特点,略显单调。然而,央视频的疫情慢直播却是主流媒体融合传播中的一次成功范例,并表现为一种情感传播模式,在抗击疫情中起到积极心理干预作用。
本文从互动仪式理论出发,以央视频为例,对新媒体疫情慢直播中互动仪式的形成与传播效果进行分析,以期为主流媒体的融合传播提供启示。
一、慢直播互动仪式的建构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指出,互动仪式的形成包含四个条件:(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2)对局外人设定了限制。(3)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且互相传达、各自明确关注焦点。(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慢直播通过虚拟的身体共在,共同的关注对象以及情绪、情感基础,建构互动仪式。
(一)互动情境的建立
“人们的一切互动都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之中,其中至少包含由两个人组成的际遇。”[2]互动仪式的启动首先在于互动情境的创立,慢直播为受众搭建了际遇的平台。直播间设置了仪式准入的门槛,观众进入直播间,便进入一个互动的场所,加入“云监工”或“云守望”的队伍中,没有进入直播间的用户则被排除在互动仪式之外。尽管互动仪式理论强调两人或两人以上的身体在场,但是慢直播作为观众之间社交互动的场域,其创造的互动情境以虚拟在场代替亲身在场。央视频的慢直播界面上半部分是实时输送的视频画面,下半部分是观众可以即时互动的评论区。虚拟在场同样使观众之间彼此影响,产生有节奏的连带活动,例如频频出现的“武汉加油”,整齐的国旗应援,甚至有观众跟单叫外卖。
慢直播是对事件发生过程原始、共时的记录,直播的排演、表演成分几乎为零,这恰好符合新闻真实性、时效性的价值特征。同时,慢直播是相对于快直播而言的概念,全天候24小时的播出时长以及VR技术的加持,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虚拟的沉浸感与临场感。2020年4月8日,武汉正式解除离汉通道管制,央视频连续28小时直播武汉开城,将镜头对准汉口火车站、黄鹤楼附近铁路、江汉关等交通要塞,以及黄鹤楼、武汉长江大桥、光谷体育馆等地标建筑。观众在《云守望大武汉》的直播间实现群体聚集,随时参与、实时见证武汉开城仪式。慢直播的即时性、在场性为观众加入“云守望”的互动仪式提供便利。
以往的电视直播或移动直播都会安排主持人或主人公的阐释部分,慢直播却将直播内容的解释权力完全移交给受众,创造了自主的传播情境,传者和受者的关系模式不再是“我说你听”。疫情中隔离的生活状态造就了大量“闲疯帝”,即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网友,主持人、表演者的缺位反而激发了“闲疯帝”们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二)共同的关注焦点
人们加入互动仪式的初衷是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面对世界变动时能够及时做出正确决策。新冠疫情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加剧了人们对确定性信息的需求程度,尤其是关于疫情态势与抗疫进程的信息。央视频通过对网民关心的新闻现场进行长时间的慢直播,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满足网民对舆论监督的需求。例如,医院建设是防疫工程中最直接、有效的举措,也是大量网民密切关注的焦点话题。火神山、雷神山分别于2020年1月23日和1月25日投入建设,是武汉在疫情暴发初期效仿非典“小汤山”模式快速建造的应急医院,而央视频在2020年1月27日便对医院施工现场进行实时直播。此外,物资援助也是疫情期间人们关注的焦点。2020年1月底,武汉红十字会在物资分配中出现严重失职问题,造成医护人员物资短缺,社会信誉大大降低。2月初,杭州等地的地方媒体便在央视频上直播红十字会的物资转运过程,消除人们对当地红十字会的疑虑。此外,直播间还包括“疫情数据”“预防知识”“最新动态”“疫情寻人”等板块,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焦点话题资源。
参与互动仪式的各方拥有共同的话题焦点,这是彼此相互关注、互动交流并形成情感连带的基础。互动仪式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伴随着焦点的转移或焦点的再生。在医院系列直播中,随着慢直播时长的增加以及围观人数的上涨,直播画面中施工设备等具体物件成为人们共同关注和讨论的对象。观众将高层吊车称为“送高宗”,将蓝色挖掘机称为“蓝忘机”,将白色板房称为“白居易”,将火神山摄像头前的三颗桂树称为“吴三桂”。这些共同的关注对象增加了直播观众的群体谈资,围绕这些符号进行的互动行为强化了观众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
(三)情绪与情感基础
人们共享情绪与情感体验是互动仪式形成的条件之一。“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着民众的生命健康和日常生活,并让民众情绪产生一种‘疫情焦虑’。‘疫情焦虑’是对未来发展‘不确定性’、主体自由‘受限性’以及生命存在‘虚无性’产生的心理反应。”[3]在疫情暴发期,新增病例数与死亡病例数持续攀升。孤独、恐慌甚至愤怒是观众的主要情绪,他们对慢直播的围观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缓解、宣泄负面情绪的目的。一方面,慢直播通过对世界另一个角落真实、共时的再现,通过千万直播观众的在线社交,发挥情感陪伴的作用,改变人们孤独、焦虑的心理状态。“无聊又睡不着看直播造医院”便是医院建设直播期间观众发起的重要微博话题。其二,物资援助、医院建设是有效抗击疫情的基础措施,央视频通过对救援行动不加解释、不加剪辑的原生态直播,让人们第一时间了解抗疫的进度并持续增加对国家抗疫力量的信心,从而消解其恐慌甚至愤怒的情绪。此外,民族自信与家国情怀是慢直播互动仪式得以形成的深层次情感基础。不论是“基建狂魔”“与疫情赛跑”还是春暖花开的江城山河,都巩固着观众对于民族、国家的信心。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强调仪式准入规则,即仪式对局外人设置限制,参与仪式的人互相知道对方的身份。但是在移动互联时代,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陌生化、匿名化的在线交互情境中,加入仪式的人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就公开性的慢直播而言,仪式的严格准入一定程度上让位于群体成员共同的情感基础。慢直播汇聚了大量具有相同情绪和情感体验的人群,并成为疫情期间人们情感投射的窗口,共同的情感需求成为人们加入同一互动仪式的动力。
二、慢直播互动仪式的融合传播效果
依赖于受众疫情期间特殊的情绪状态以及长期积累的家国情感,慢直播通过建立互动情境、提供关注焦点,从而启动对抗击疫情产生积极效果的互动仪式。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4]慢直播的互动仪式起到共享信仰与维系群体的传播效果。
(一)身份认同与群体道德感
参与疫情慢直播互动仪式的人群有着共同的关注对象、共同的情感体验,通过“天涯共此时”的在线交流,逐渐形成一个想象共同体,并在持续的情感交流与文化共享中,加深集体认同。
“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联结,仪式是一种相互专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身份的符号。”[5]例如,武汉开城直播中,面对黄鹤楼附近铁路恢复运转的画面,观众化身为“云列车长”,在评论区播报列车运行状况,并与其他“云列车长”进行工作互动。在医院建设系列直播中,观众则自命为“云监工”或“包工头”。
“云列车长”将观众置于亲身参与武汉解封开城的情景中。而“云监工”“包工头”之类的词汇为观众赋予监督者的身份,并隐喻着个体对防疫工程的社会责任感。观众的身份自豪不仅来自群体的文化共享以及团结一致,更来自主流媒体对其虚拟身份、虚拟地位的背书,“云监工”等身份诞生不久后便获得了《主播说联播》等主流媒体的纷纷报道,包括央视频的认证。此外,观众在直播间通过日常的仪式互动维持着对“云监工”等身份符号的认同,例如将自己观看直播的行为描述为“打卡”“上班”“换班”“轮班”,并且完成清点挖掘机数量、清点工人数量等日常任务。通过一再重复日常仪式,人们对群体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得到稳固维系。
不管是“云监工”还是“云列车长”,背后都是对抗疫群体这一身份的认同,他们在见证、监督、守望等一系列行动中,获得身份认同感。慢直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远程参与抗疫的平台,直播间的观众通过留言、互动来证明自己也是抗疫行动中的一份子。在身份认同基础之上,观众进一步培养起自身的群体团结意识与群体道德感,这体现为维护群体价值观念,尤其是赞叹“中国速度”和表达抗疫自信,“加油”“致敬”“守护”“战胜”也成为评论区的热词。
(二)符号资本的创造与共享
机位固定、无主持、无剪辑的慢直播激发了受众的生产力,参与式文化获得发挥空间。在特殊的疫情时期,观众自发的符号创造与消费行为起到心理代偿作用。喻国明认为:“即使网民在这个空间(网络空间)里‘吐口水’、‘撒野’甚至‘低俗’一下,这也是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所应该容忍的。须知,虚拟空间的发泄性代偿总比现实的社会冲突代价低得多。”[6]尽管观众的符号创造与共享具有娱乐性、游戏性成分,但是其对情绪宣泄、情绪疏导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在医院建设系列慢直播中,随着身份认同的建构,“云监工”逐渐形成具有群体标志性的符号,包括为自己、为直播画面中的机械设施命名。观众对机械设备的命名有多种机制,一类是具有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特色,将历史名人的光环迁移到这些虚拟偶像身上,如××帝、××宗,其中蕴含着一种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另一类是孩童化、二次元化的命名,如小××、××酱,为这些虚拟偶像披上一层幼小可爱、需要保护的色彩。命名实现了虚拟偶像的人格化和性格化,通过命名行为,观众寄托着自己对国家防疫力量的信心与希望。
除此之外,“云监工”围绕已有的文本符号、仪式符号等进行持续不断的消费和再生产。为机械设施命名最终演化为将机械设施拟人化为偶像人物,并将围绕真实偶像与追星行为而诞生的饭圈逻辑、饭圈话语迁移到这些虚拟偶像身上。“云监工”以“妈妈爱你”“守护全世界最好的××”“挖掘机天团出道”等饭圈惯用话术来表达自己与虚拟偶像之间的亲密关系及其对虚拟偶像的支持。此外,他们还会以简短而重复的口号和色彩鲜艳的图标在微博新闻下宣传这些虚拟偶像,如“工地最靓小叉车”“可可爱爱呕泥酱”,通过这些符号的创造与共享,疫情中的负面情绪得到有效疏导。
这些群体符号在慢直播情境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参与者通过对这些符号的领悟理解、消费和再生产,进行群体区隔。虽然慢直播为所有网友敞开大门,但是要真正融入受众群体及其对话流程中,后来者必须对群体文化符号、仪式等有一定了解,群体成员也在符号资本的积累过程中,不断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向心力。
(三)情感能量的回报
“高度的情感能量是一种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与热情的感受。它是个人所拥有的大量涂尔干所言的对于群体的仪式团结。”[7]互动仪式如同一个市场,人们加入互动仪式主要是为了寻求情感能量回报的最大化。在慢直播互动仪式中,情感能量是人们观看并参与讨论的主要驱动力。
观众获得的情感能量回报首先源于慢直播的情感抚慰作用。央视频的疫情慢直播在题材选择上多有考究,一类是灾难救援型,聚焦于天河机场的人员、物资驰援,方舱医院的抢建;另一类是景观、景色直播,车水马龙的洪山广场、闭馆后静悄悄的方舱医院、繁华的汉口会展中心等风景得以呈现。前者发生在疫情暴发期,防疫工作以初步遏制疫情发展势头为主,积极的救援行动象征着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为观众创造出喜悦、自豪的感受,有效地缓解恐慌、焦虑的心理。而后者多见于复工复产期,疫情得到一定控制,防控逐步常态化。一如往常、巍然屹立的地标建筑,春暖花开、车来人往的街景,构成恬静美好的视频画面,为人们恢复生产增添信心与希望。“现在的武汉多美”“武汉明天更好”等话语常见于评论区。慢直播承载着人们对疫情风暴的集体记忆,并通过对新旧武汉的展示将伤痛转化为对美好未来的希冀。
其次,观众通过虚拟在场实现对话、交友,在彼此的互动过程中获得情感能量。慢直播为疫情中焦虑而孤独的观众带来陪伴式的社交体验,并将其对疫情严峻态势的注意力转移到积极抗疫上来,起到建设性传播的作用。此外,观众不断协商出新的群体互动仪式,积极情绪通过群体感染不断扩散,战胜疫情成为群体共识。例如,在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直播中,“云监工”们每当直播间人数突破千万时要“合影”,每逢整点集体“刷国旗”。新的群体互动仪式又进一步增强了“云监工”群体的凝聚力,群体成员不仅有了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感,而且抗疫信心在互动狂欢中得以强化。这种情感能量回报成为观众持续参与观看慢直播,并进行符号创造的动力源泉,也为早日战胜疫情提供帮助。
三、慢直播互动仪式融合传播的启示
情感能量与符号资本是互动仪式的主要市场资源,人们以获取最大限度的情感能量和符号资本为目的,选择加入某一互动仪式。疫情慢直播成功建构了受众间的互动仪式,其主要传播特征表现为以情感传播为核心以及受众自发创造和共享符号资本,这对主流媒体的融合传播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尤其当面临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
(一)情感传播模式的形成
情感是互动仪式作用机制中的核心要素,人们在具体的互动传播情境中吸收情感能量,以抵抗社会压力。从互动仪式的启动到其产生传播效果,慢直播无不体现出情感传播的底色,以情感唤醒、情感抚慰、情感共振为传播的着力点。在疫情暴发初期,央视频慢直播激起人们对“中国速度”和战胜疫情的信心,起到情感唤醒的作用;同时,慢直播以陪伴式的社交方式纾解隔离生活中人们产生的孤独和恐慌,起到情感抚慰作用。慢直播提供了受众之间情感共振的场域,虚拟在场的观众建构起身份认同,并通过符号共享实现娱乐体验,强化群体团结感与防疫信心。此外,受众对慢直播的自发宣传不仅为慢直播以及央视频带来流量,也让战胜疫情的积极情绪得以向外扩散,形成互动仪式链。
“‘情感’不仅是个体体验的产物,而且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事实’。”[8]慢直播在此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期建构起人们积极的情感,表现出建设性新闻的特征。建设性新闻强调新闻应当具有解决社会问题、传递积极情绪的价值。媒体不仅要完成信息传播的任务,更应该承担起情感关怀的职责。有研究对2019年12月11日至2020年2月12日“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相关的微博文本分析发现,“消极情绪文本占63.5%,积极情绪文本占36.5%”[9],消极情绪成为疫情暴发期网民的主导情绪。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期,人们出于安全考虑,倾向于关注负面信息,风险可能被放大,媒体需要发挥其积极心理干预的作用,搭建起情感宣泄和情感抚慰的平台。
从央视频疫情期间成功的情感传播模式中可以发现,主流媒体情感传播功能的实现一方面在于对受众心理的把握,受众心理状态决定其特定的情感需求和信息需求;另一方面在于激发受众参与感和生产力,这依赖于技术赋权,主流媒体通过不断创新新媒体产品形态和叙事方式来拉近自身与普通受众之间的距离。
(二)融合文化与融合传播
央视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新媒体环境下融合传播的一次创新,《疫情24小时》上线仅两天,“央视频App在苹果市场总榜排名达到第10位,娱乐类排名飙升到第2位,远超腾讯、爱奇艺、优酷等视频客户端的排名。”[10]这不仅得益于5G等新兴技术的赋能,更有赖于饭圈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在慢直播中,受众创造和共享符号资本的行为其实是饭圈文化中粉丝行为的迁移,他们将饭圈文化与主流文化进行拼贴、杂糅,让疫情慢直播扩散到广大的年轻群体中。
尤其在医院建设系列直播中,工地的机械设备不仅被拟人化,而且被作为虚拟偶像。在饭圈文化的助推之下,慢直播的传播效应延续到微博等其他社交平台上。“云监工”为工地的机械设备取名并开设微博超级话题,形成再生产与再消费的循环。同时,微博与央视频对受众的这些自发行为也给予及时、充分的反馈与迎合。例如,微博超级话题专门建立“云监工”板块;央视频在《疫情24小时》直播界面下增加“助力榜”板块,网友可以为自己支持的虚拟偶像打榜助力。由此,央视频通过对饭圈文化的兼纳,展现出亲民化的传播姿态,增强了年轻群体对主流媒体和主流文化的认同感。
媒介融合不仅包括渠道、内容、组织等层面的融合,更涉及文化融合的层面。主流媒体融合传播的过程,也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融合的过程,即主流媒体不断收编、吸纳青年网民的话语、行动方式的过程。从“香港修例风波”中饭圈女孩的“出征”开始,“阿中哥哥”(饭圈对中国的称呼)等饭圈话语被主流媒体认可,主流文化与饭圈文化的融合不断加深。慢直播之所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不仅是受众自发传播、生产的结果,更有赖于主流媒体及时的回应、认证、再度传播。粉丝在对主流媒体所创作的文本进行盗猎,争夺对文本意义的控制权、解释权,主流媒体同样也对粉丝文本进行盗猎,将粉丝话语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当中。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过度的消费与娱乐会消解人们对严肃议题的理性思考,以及对风险的感知。主流媒体的融合传播要把握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平衡,尤其是涉及灾难事件。例如,主流媒体不仅对医院建设进行远景慢直播,同样也对慢直播背后的建筑工人给予大量报道,避免使观众陷入追逐虚拟偶像的在线狂欢中,而漠视疫情的现实性和残酷性。
四、结语
不管是早已流行的游戏直播、真人秀直播还是2019年蓬勃兴盛的电商直播,传播者既是传受关系中的强势方,也是传播内容的主体。而慢直播将视野转向宏大的户外场景,传播者不再作为内容元素现身或现声。慢直播的传播效果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自发形成的群体以及群体的生产力,通过对受众参与式文化的激发和兼纳,主流媒体融合传播效果的实现有了新的可能性。此外,慢直播改变了传统网络直播的叙事节奏,固定镜头、原景、原声的实时记录表现出舒缓、真实的表达风格。慢节奏的内容呈现与受众的互动仪式共同起到情感疗愈作用,尤其在特殊的危机事件中。
疫情期间央视频的慢直播创造了一段难得的集体记忆。随着疫情防控逐步常态化,人们的生活步入正轨,共同关注的焦点消失,情绪基础发生变化,互动仪式难以启动,疫情系列慢直播的传播效果逐渐式微。但是,慢直播在其他特殊景观或特殊事件传播中依然被广泛应用。央视频的“关键汛期”系列节目对气象云图变化、鄱阳湖、三峡大坝等进行24小时慢直播,观众可以实时监测长江水位;“珠峰十二时辰”系列慢直播则以一个VR视角和三个固定视角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极地体验。除情感慰藉外,慢直播还可以起到及时传递信息、极端景致可视化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