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长命百岁
葵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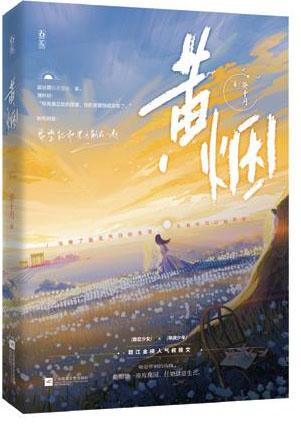
太婆生于民国,我看过她年轻时的相片,穿着旗袍,很是明媚。太婆一共有两段婚姻,我见过的太公便是太婆改嫁后的先生。
我不懂那个年代的爱情,自然也无法体会太公之于太婆,太婆之于太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但在他们身上,我头一次感受到了“白头偕老”这四个字的分量。
太公年轻时在邮电局工作,退休以后买了张麻将桌,天天让太婆出去帮他张罗麻友。他们的老年生活简单又惬意。
别家老头、老太拎个篮子步行去镇上买菜的时候,太婆搬个小板凳坐在太公的电动小三轮上。太公的小三轮特别小,小到只能装下外婆和菜。
后来太公病了,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邻里街坊总拿这事儿调侃太婆:“别人都说打麻将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结果呢,你家老头子不还是痴呆了?”
太婆也不生气,只是笑笑:“那是因为他打麻将不爱动脑。”
不知是不是因為我常年在外,总觉得太公生病以后,太婆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变。每次回去还是能见到太公骑小三轮,太婆一脸享受地坐在后面。不管家人怎么劝阻都没用,只要太公骑,太婆就一定坐。
我依稀记得太公去世那天,太婆一个人默默地走在最前头,反复地说:“能活到九十多也够了,走吧走吧,我也快来了。”
太公走后没多久,太婆把麻将机卖了,门前的空地变成了菜园子。太婆每天不是浇水种菜就是坐在门头剪纸。
今年四月初,九十六岁的太婆摔了一跤,吓得我们这些小辈连夜赶回去。那天晚上,病房里挤满了人,好多张嘴一起嘀咕,吵得我脑袋疼。
我和表妹站最离门最近的位置,远远地望向她。
几个月前还犟坐在麻将桌上的老太太,此刻躺在病床上一言不发,头顶稀松的白发胡乱地缠在一起,宽大的蓝色病号服能装下两个她。
我迟钝地意识到,她已经很老了,也终于明白那群人在忧虑什么。
幸好没什么大碍,医生也说:“老太太命大,没骨折,回家休养几天就好了。”
这件事之后,太婆被山里的姨婆接走了。
我们再见面已是七月末。
老人家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手里摇的还是多年前我送给她的那把蒲扇。蒲扇中间破了个洞,被太婆用旧布补上了。
我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太婆握着我的手,轻轻地给我扇风。老人家年纪大了,说话不像以前那么有劲,她问我现在去哪儿工作了,累不累。
我说不累,都挺好的。
所有小辈里,太婆最疼我,总担心我身体不好,过得不好。
听到我这么说,她欣慰地抚着我的手背,连声说道:“那就好,那就好。”
阳光透过窗子落在她长满老年斑的手臂上,我抬眸看了一眼太婆。那双眼睛早已没有了神韵,松弛的皮肤堆起道道褶皱,整个人像后山上晒脆的树枝,轻轻一折就会断。
我鼻头一酸,不敢再看她。
那日我没办法久留,临别时余光瞥见太婆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从裤兜里翻出几张五十块钱的纸币,还跟以前一样,用一片窄窄的红纸在纸币腰上封一圈。
“拿着!”
我说我已经会挣钱了,以后就不收红包了。
说来有些羞愧,小时候喜欢黏着太婆,纯粹是因为我的过年红包比其他孩子大一倍。
我常常想,或许真的存在某种隐秘的东西,将我和太婆联系在一起,所以即使隔了四代,我们仍然相爱相惜。
小镇的清凉山风吹起太婆的银发和轻薄的衣角,脚步虚浮的太婆立在古树下,一遍又一遍地说:“我跟你们走。”
她想回到和太公共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可那边没人能照料她,所以我没办法带她走。
我只能对着上天祈愿:希望她长命百岁,希望我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她还可以给我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