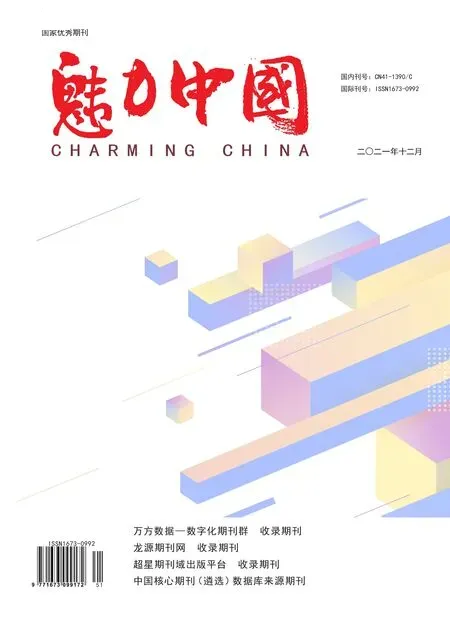另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读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
陶永杰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一、“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永恒的文学论题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超越我们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怎么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1]其实,畅想与追求更好的“人的范式”、想象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乃至于将文明发展的意义更多地寄托在新的人的高贵素质,而不是物质成就上,这种文化心态并非西方所独有。而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文学作品因其长期以来作为社会心理-文化的叙事性文本,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时代里人们集中讨论重大思想事件的载体。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历史上,大致从梁启超起,关于新人、新的生活和新的文化的讨论就成为晚清巨变以来,追寻中国道路的一代代知识分子讨论的重要议题。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对理想的人和理想的生活的种种想象和争议,也是自五四以来就有的一条贯穿始终的辅助线。而对这一问题提出、改写和回答,总是和时代的转变、文化范式的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1918 年,鲁迅先生以一篇《狂人日记》宣告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创生。其在里面就大声呼叫“救救孩子”,直斥旧中国礼法体系对人的窒息,并全力对新生的一代作为突破力量的可能予以关注和呐喊。
建国后,一方面有《创业史》里的“梁生宝”这种浪漫而气势磅礴的新人典型的产生和确立,而另一边像是《我们夫妇之间》、《千万不要忘记》等文本内部,却透露着坚持革命理想和新兴的生活趣味可能带来的新一代人“脱域”危险间的巨大矛盾[2]。“文革”后,国家经历了又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文化和价值随之巨变。因此新时期文学里的典型文本《班主任》,就敏锐地再一次提出了文革后新人的培养和教育问题。
来自北京的70 后作家石一枫在2014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3]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一经典问题的再一次改写和回应。围绕着主角“陈金芳”的兴衰故事,小说给我们留下的问题依然可以概括为: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和理想的生活?
二、“活出个人样来”和主角“陈金芳”的人生悲剧
《世间已无陈金芳》叙述的是一个不甚复杂却颇为曲折的故事。作家石一枫在小说里借助一个北京土著和犬儒式的中年人物“我”的视角,叙述出来自底层的“失败青年”“陈金芳”的人生故事。“陈金芳”原本是90 年代从湖南老家来到北京的一个土丫头。因为和“我”是同一所学校,她寄居的姐夫家和我家也是同一个大院,所以,“我”不得不亲眼目睹了她大部分的人生经历。
“我”是在学校里认识“陈金芳”这个从乡下转学来的土学生的。最初,“陈金芳”因为她的土味而根本没被学生们注意,可后来,她渐渐打扮起自己来,但因为经济条件不足和审美信息上的闭塞,她的新打扮非但没有让自己洋气起来,拉近和城市同学的距离,反而迅速遭到同学们的集体排斥。而她却很有些高雅品味,很喜欢听“我”拉的小提琴,是我为数不多的“知音”,所以和“我”有了一点若有若无的联系。
后来,陈金芳家里遭遇变故,无法再负担她在北京的学业,于是想让她退学回乡。一向唯唯诺诺的“陈金芳”这次却坚决留在北京,并不惜和姐夫一家闹翻,大打出手。她被赶了出来后,先是混迹在各个流氓团伙中,后来又和流氓头子“豁子”姘居,开起了服装店。等到十几年后,当“我”再遇到她时,“陈金芳”已经变成了“陈予倩”,成了文化投资领域里呼风唤雨的贵妇人。最后,经过“我”在中间牵线,“陈金芳”加入了“B 哥”的一场投机生意,而随后这场投机的失败彻底把她打回原形。她的发家秘密也最终暴露出来:原来她是靠引诱乡亲们非法集资才撑起了表面烈火烹油的生活,而骗局破产后,等待她的是难以偿还的巨额债务和法律的惩处。
在小说的结尾处,当自杀未遂的“陈金芳”被送上警车时,她这样向我解释自己不断折腾的人生“她突然欠起身来,直勾勾地盯着我。说:‘我只是想活得有点人儿样’。”[4]
纵观“陈金芳”的一生,对“人儿样”的执着追求的确是推动她每一次人生转折的重要心理动因。“陈金芳”执着地模仿城里人的穿衣打扮,反映的不只是一个青春少女的爱美心理和对成人世界的追求,而且也是对突破自己的阶层的巨大决心。而这立即遭到了“我们”的排斥,因为,“对于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5]
小说里的“陈金芳”是一个怎么都不能安分的人,对“人儿样”生活的追求之执着和野心勃勃,令人想起了当年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但不同的是,《人生》中的那种隐隐地代表了不同生活模式之间的争锋的城乡对立没有了,当今的城市文化已经足够强大,回到乡村不再能够成为城市生活之外的另一种有力的选择。所以,70 年代以后出生的“陈金芳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回乡生活,她们心中的“人儿样”的生活只能与城市联系在一起。
其实,这种生活理想不仅仅是“陈金芳”个人的发明,它本就是90 年代以来逐渐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人生逻辑。有学者认为,80 年代后期,传统的意识形态开始衰弱,进入90 年代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逐渐发展起来。
“……关于人的定义,不再像以往那样认为“人应该活得像雷锋一样”,而认为人是首先要满足眼前物质利益的生物;关于过去40 年的历史,是用崇高理想来压抑人的起码物质需求的历史;关于当代社会的认识,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现代化要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通过平等竞争来进行,只要这个基本方向不变,现在我们担心的问题都会解决。”[6]
关于理想的人生和生活方式,新的意识形态绘制了一幅“成功人士”的美妙肖像:“它通常是男性、中年、肚子微凸、衣冠笔挺。他很有钱,开着簇新的宝马车去自己的办公室;他也可能在美国留过学,养成了西式的习惯,在怀揣即将与外商签订的合同、匆匆跨出家门之前,不会忘记与美丽的太太吻别……”[7]这些成功人士富足、高雅、文明又自信,经常出现在高档轿车发售的广告和楼盘的宣传画里,向全社会宣示的新的一种生活的理想。
但正如王晓明形容的那样,这副“成功人士”的素描画毕竟只是“半张脸的神话”,在它从不示人的另外半张脸上,说不定隐藏着不能说清的财富的来源;他光鲜衣着背后的是90 年代逐渐拉大的阶层差距,社会价值体系里狂热的金钱崇拜和对人的单向度化处理。
三、另一种生活何以可能
“成功人士”是90 年代新意识形态的一个准确的塑像,一种饶有意味的症候。而巧妙的是,在小说里,“陈金芳”也是在90 年代从湖南来到北京,并由此开始了她不安分地对“人儿样”的追求。虽然小说中没有明确描写这种新意识形态对“陈金芳”的影响和她接受的过程,但她所渴求的“人儿样”里面,当年“成功人士”的半张脸清晰可见。
90 年代以来新的意识形态所描绘的理想生活模式仿佛有意地回避着不同生活方式后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难以逾越的阶层差距,而着重标榜着所谓高雅趣味的区隔,穷与富在一定程度上被俗和雅所掩盖。新富人们想要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是高雅、文明、敬畏未知又善良和有人情味。小说里,富起来后的“陈金芳”努力地要跨进文化界,在音乐会上大喊“bravo!”,投资画家的欧洲画展,也正是对这种高雅的生活趣味的模仿。
而社会文化学家布迪厄认为,所谓高雅的趣味本就不存在,一个社会的合法趣味总是领导阶级的趣味,它总是会扮演成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公正的趣味,而现实中这不过是这些特定阶层的趣味而已。结合中国大陆90 年代以来的社会情况,可以说,塑造与信仰着这些生活趣味的阶层就是那些数量庞大的“小资们”。“小资”式的生活理想其实在“文革”后期就已经萌芽,比如北岛写的《波动》里的主人公“肖凌”和“杨汛”,就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文学文本里的第一代小资的代表。而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当年只存在与北岛这些少部分精英知识分子想象中的,代表着现代化、西方文明和另一种世界图景的小资理想,现在已经十分强大,并且配合着消费时代的经济文化逻辑,成功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普遍趣味。正如李陀在《波动》的新版序中所预言的,无论承不承认,今天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在小资们手上,是这群人在规定着总体的审美价值、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8]小资的生活趣味给资本市场披上高雅的面纱,资本市场借助这种生活趣味,迅速将其转化成消费欲望,并由此组织生产,完成经济循环。
但这些生活趣味离不开大量的财富支持,当然也离不开并不那么高雅的剥夺和欺诈逻辑。小说中,“陈金芳”为了维持这种“人儿样”的生活,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把全部资金投入到一个投机项目里,最后,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可是,也不应该过分苛求“陈金芳”们对这种新意识形态没有足够的辨析力,没能建构自己的独立意识,因为实际上,从来没人也没有哪种力量向她展示过另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的存在可能,所以,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其他选择可言。虽然,90 年代后期,有一些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过堪称犀利的分析和批判,但在无时无刻不被广告、传媒、不被资本化的力比多包裹的生活世界里,这些话语显得过分渺茫和无力。
对今天而言,描述市场时代的失败者的伤情故事已经不算鲜见,诸如“寒门难出贵子”、“阶层固化”等话语,也早就充斥在一些自媒体和营销号上,成为他们涨粉的语言套路。而石一枫的这部《世间已无陈金芳》的新颖之处或许不在于写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的故事,向社会重复着对阶层阻隔和底层青年成功之难的控诉[9],而是重新复活了葛兰西的语境,再次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某个特定的“陈金芳”的失败或者成功,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偶然,但是,重要的在于,在今天还能不能有一种别样的生活理想,一种新的值得过的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