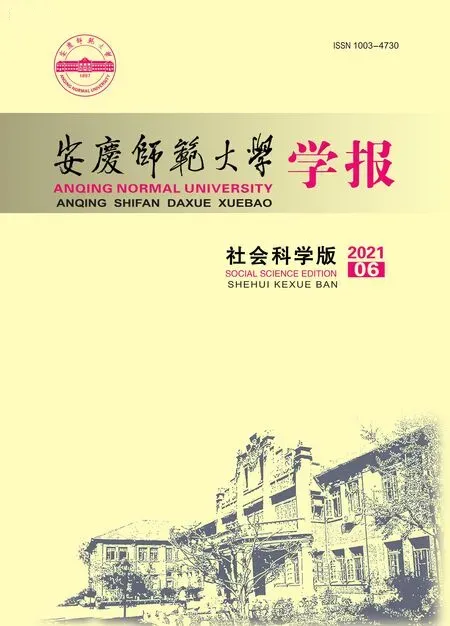李宗棠对日本国民性的认知述论
郑素燕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246011)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通过学习西方,迅速成为强国。而同一时期的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逐步沦为受列强侵凌的半殖民地。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提出向日本学习的主张。正如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在《文明及其内涵》中所说:“中国的失败成为中国文明的低谷;日本通过学习西方而成为一个新晋的文明之国和帝国主义强国,如今它扮演起了文明导师的角色。”[1]113为了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文人去日本考察游历,李宗棠正是这一时期赴日考察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宗棠(1870—1923),字柏荫,一字隐伯,别号江南吏隐,千仓旧主,安徽阜阳永兴集(今颍上县新集镇)人。“作为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日外交舞台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李宗棠生逢其时,当之无愧地承担了省际间开创中日邦交的先行者。”[2]从1901年到1908年,李宗棠曾九渡日本,考察学务、警务、矿务,商办游学,劝募皖赈等,均留下详细的日记,这些日记合编为《东游纪念》九册。除了《东游纪念》外,李宗棠还写了多首东游诗,收录在《千仓诗史初编》里。在这些著作中,李宗棠对日本国民性进行了评判。日本国民性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尚会鹏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以社会人类学的基本理念为学术核心,采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旨在阐明中日两大民族深层的文化特征[3]。李文的《日本国民心理嬗变的原理与趋向》,认为日本国民心理富于变化,与日本民族特有的哲学传统和审美习惯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性[4]。尚会鹏、张建立、游国龙等的著作《日本人与日本国——心理文化学范式下的考察》,梳理了“日本人论”的学术脉络,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对日本人及日本国进行了分析[5]。但学术界对晚清皖籍学人对日本国民性的认知鲜有研究。本文拟以李宗棠的《东游纪念》及东游诗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对日本国民性的认知,了解晚清皖籍学人对日本的探索,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他们自我文化反思、寻求救国真理的历程。
一、友善、忠君、勤劳
清末中国人游历日本时,“接待方大多态度诚恳,彬彬有礼,有问必答,甚至为中国发展新兵新政积极出谋献策”[6]。因此,他们对日本国民的印象比较好,评价普遍比较高。他们认为日本国民待人真诚友善,如刘学洵评古河铜矿局总办藤陆三郎:“论矿物甚详,人极诚恳。”[7]程淯评东京府学务课长涩谷元良:“涩谷君浑厚和平,于学事不厌缕告,并作绍介通函,以便各校参观。又作函于留冈君处,俾往观家庭学校,意殊可感也。”[8]58他们称赞日本国民忠君爱国:“自将佐以及兵卒皆曾受国民教育,人人富忠君爱国之思想耳。”[9]他们赞赏日本国民谦和有礼,如严修笔下的汽车乘务员“极谦和殷恳”[10]95,旅馆女服务员“皆恂谨”[10]157;程淯笔下的火车乘客“均不妄谈笑,虑扰他客也”[8]19。李宗棠对日本国民亦赞赏有加,认为他们热情友善、忠君爱国、勤劳善良。
(一)热情友善
日本人的热情友善给李宗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第一次东渡日本时,在中国的日本友人写了四十多封信,带投东京、横滨、神户、长崎、大浦、名古屋、大阪等处,托人关照于他,日本总领事小田切君也帮他与日本外务省打招呼,“情谊谆谆,令人可感”[11]3。在日本考察期间,李宗棠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款待。如首次赴日参观学校,外务省专派翻译官堺隅三吉陪同,并表示李宗棠在考察期间可“随时随地开支公费”,“各处参观,均已预备供张”,李宗棠再三婉辞,不容推让,他对此感慨道:“其郑重邦交如此,令人可感。”[11]22参观麴町区大手町二丁目三番地印刷局时,局长得能通昌不仅率同各部部长佐田清次等,“引观官报编辑所庶务课、会计课、调查课、雕刻课、颜料室及印刷各机器工厂”[11]32,还专门为他演示救火法,“此法不轻试演,是乃局长格外优待之意”,并提供他从东京来往的车费,“情谊肫挚,殊可感篆”[11]34。参观陆军户山学校时,田中大尉“已在彼处等候”,守门兵“举枪致敬”,校方专门安排演习巡览[11]76-77。参观铜山矿业时,副所长井上公二专门派人在铁道旁迎候,行至驻所,副所长暨各职员“鹄立门外,延入客室”,并对李宗棠热情款待,“主人先让入浴,浴罢更衣赴宴。西餐盛色,劝酒尤殷。”在住宿上也是招待周全,“派有专员茂野留宿,招待一切。……室内陈设雅洁,预备周全,衣服被褥,均系绸制,极绵软且适体,与我国被服无异,真有宾至如归之乐。”[11]560
除了政府官员,日本普通国民对李宗棠的招待亦十分热情友好。他初到东京,住在旅馆,不能适应日本席地坐卧的习俗,旅馆主人便“殷勤款接,特置桌椅于室中”[11]9。去横滨拜访原富太郎,原富太郎“款以茶点,并拟定期邀饮”,李宗棠赞其为“滨中绅士”,“诗酒自娱,素好风雅,且喜与华人游,接待颇觉殷勤。”[11]54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多次与李宗棠谈论女子教育,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昌兴女学,还陪同他参观了女子工艺学校及实践学校,并送他绸织、纸织、通草花等礼物[12]36。长冈护美子爵多次邀请李宗棠到其爵邸饮酒畅谈,“特设盛馔,座无他客,款待意颇殷勤。”[11]57李宗棠也数次赠诗于长冈护美,其中一首《长冈子爵招饮即席赋赠》:“与君初握手,如见平生亲。今朝共谈笑,美酒涤风尘。座上无二客,惟有主与宾。主人山海量,客亦江湖身。主醉客复饮,忘却忆鲈莼。”[12]20体现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李宗棠离开时,经常有日本友人送行。如光绪壬寅年正月二十八日(1902年3月7日),李宗棠离开新桥时,送之者众,“近卫公爵握谈,东邦之友送行者二十余人,姓名不及详载。”[11]105光绪癸卯年秋八月二十日(1903年10月10日),李宗棠离开东京时,诸多日本友人赠送礼物以送别,“神户外务大臣小村,遣秘书官吉田来,送天鹅绒织画轴等物以赠别。长冈子爵、张景韩观察皆来寓。小林、岩村、末吉、平岩诸君持赠书籍、皮包、漆盘等物。”到火车站送行的人则更多,“送行者五六百人,途为之塞。”[11]228光绪戊申年二月初五日(1908年3月7日),李宗棠乘铁道马车离开铜山矿业所,“井上、高桥、木部、浅野、籐林、樱井、川地、西牧诸君送别,情意殷殷。”[11]567
日本人的热情友善,使李宗棠深受感动,《东游纪念》中经常出现“令人可感”一语,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邦交友谊两相亲,视我非同陌上人。蔼蔼旭旂迎道路,琅琅木铎见精神。连朝辛苦勤王事,一片真诚爱善邻。恍接平生诗酒伴,偏教耳目者番新。”[12]22足见他对日本国民热情好客、真诚友善态度的赞叹。
(二)忠君爱国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人的“忠”是这样解释的:“对天皇、法律、日本国家的责任。”[13]106李宗棠对日本人的忠君爱国感受颇深,在《东游纪念》里多次提到。
1904年,李宗棠前往日本商办游学事宜,此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他在日本街头多次目睹日本民众为庆祝日本战胜而举行的祝捷会,李宗棠一方面感到屈辱,但另一方面,日本人的忠诚爱国又让他感到羡慕:“自旅顺第一次报捷后,东京已屡次举行祝捷会。其极盛时,持灯人约三四万,扶老携幼,举国若狂。……近因极东屡获胜仗,祝捷会乃益多,几于无日无之。是固国民真正团体,其忠爱之至诚,实出于自然流露,殊令人艳羡不置。”[11]239
李宗棠对日本民众送军队出征的场景也作了详细描述:
此车装兵三千,皆陆军。沿途经过各乡村,男女老幼争相趋送。或执旗,或执灯。道旁高张大帜,有书“恭送某人出征”者;有书“敬送出征军”者。书某人即系本村之人,书出征军统指大众而言。又有大书“犒军祝捷”等字样者。更有一般男女小学生,由教师率领,排班鹄立左右,或唱得胜歌,或唱祝捷词,从容奏曲,颂祷凯旋。临开车时,或免冠,或摇巾,或举伞,或举手。灯旗灿然,狂呼万岁。彻夜间,络绎不绝。其停车场,皆树有木牌,上书“军用饮料,麦汤接待”等字,任人自取[11]245。
李宗棠不禁感慨道:“噫!所谓国民真正团体,今于日本见之矣!”[11]246
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13]114。李宗棠记载了日本天皇御幸横滨时,国民对天皇的追捧:“四旁行人均各肃立,相距不过四五丈,脱帽高举,大呼万岁,人声鼎沸,如雷震耳。是日,由东京至横滨,绵亘二百余里(以华里计),红男绿女,充塞道路,约略计之,近百万人。有自长崎来观,有自北海道来观者,附近各处来观者尤众。”[11]328
(三)勤劳善良
李宗棠最欣赏日本人的勤劳品格。他在日本考察矿务时发现,日本矿场的雇佣劳役之法,和我国内地没有什么差别,但日本矿夫能吃苦耐劳,比我国民要强数倍,“但矿夫之性格,其诚实者实能胜我百倍。彼投身于矿场,若将誓以终老,绝无偷惰情弊”[11]531。日本矿夫为何能如此勤劳?李宗棠通过考察得知,日本的矿山公司为让矿夫安心工作,“为幼儿设保育所,人皆无内顾忧。矿山多设此所,如铜矿则每矿山必设一学堂,更必设一医院,以普教育而保生命云”[11]530。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制度下,“矿夫请原家室偕来,男女自食其力,各勤工作。”[11]530除了矿夫能辛勤工作以外,很多在国外游学习成专门者,也愿意躬身技术,不计较报酬,“高桥即精究电学者,游学习成专门,归来竟见实施。俸给并不甚丰,责任固觉颇重,但名誉上占优势,故尔乐从。”[11]560李宗棠由此对中国重官贱商的传统进行了反思:“我国重官贱商,无怪游学虽众,莫不以禄位为目的;次则举人、进士,亦足称荣。未闻有从事工场、躬亲技业之人,良可叹也!”[11]560
善良亦是李宗棠对大部分日本人的印象。光绪三十二年(1906),淮河下游地区发生重大水灾。同年十一月,李宗棠奉两江总督端方、安徽巡抚恩铭之派前往日本、朝鲜劝募皖北义赈。在日本,李宗棠积极劝募,得到了不少日本商人友人的支持,“同孚泰劝募日本人零捐一千五六百元。又有银行物产各会社允为合筹十万元”[11]520,但安徽巡抚恩铭来电表明不愿接受洋赈,李宗棠无奈,只得将“其已交来之五万八千元”按户退还,但零捐户数太多,“断无退理”[11]524。虽然最后大额捐款并没有收,但日本人的慷慨善良在李宗棠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歧视国人、嗜利狡诈
李宗棠虽然对日本国民的诸多方面赞赏有加,但他亦认识到了日本国民的劣根性,并加以批评。
(一)歧视国人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再败于西方列强,甲午战争又败于日本,清政府的软弱和无能暴露无遗。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胜,民族优越意识高涨,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开始急剧转变,“由原来对中国的崇拜逐渐转变成了对中国的蔑视”[14]。布鲁斯·马兹利什从“种族主义”的角度分析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日本人对附着于欧洲文明之上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十分敏感,他们付出巨大努力来反驳日本种族低人一等的观点。……然后,日本人又开始轻视其他‘种族’,认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其他‘种族’都是劣等种族。”[1]110-111日本人的歧视,使一些赴日的清政府官员不得不穿西装来避免歧视,程淯在游记中说:“余遂偕立侯至洋服店,定购西式衣裤。盖自长崎至此,途中日童之呼腔腔薄支者,随处而有,不得不暂易服装,以免歧视。”[8]26李宗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歧视。
光绪甲辰年七月二十五日(1904年9月4日),李宗棠在街头被日本儿童讥讪:“各报馆宣布国家公报‘占领辽阳’。高树牌竿,大书特书,商民人等,争购旂灯。入晚,则街市间遍燃电光,非常热闹。余著华装观场,遇幼童数十人,狂呼‘锵锵钵子’,并言‘辽阳为我日本人占领了’。种种讥讪,令人忍辱难受。余回寓换着西装,仍往观场。竟无复识余为支那人矣。奇哉!可叹!”[11]245面对此种屈辱,李宗棠作七律一首:“满城风雨竞相夸,老幼扶携笑语哗。旅顺辽阳同奏凯,不知战地是谁家?”[12]47以此来表达他在异国他乡身心受辱的沉痛感受。
日本儿童都如此歧视中国人,更不用说成年人了。李宗棠第九次赴日,在投宿博多高岛屋宾馆时,便遭到了店主人的刁难。进门时,因为李宗棠穿着西装,说日语,店主人以为他是日本人,所以“颇具礼貌”,但填完投宿人名簿后,见其职业栏内写的是“清国游历官”,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彼遂渐露慢容,询问来历极详,并言支那人到境,例须立刻报知警察,语中似有讥刺。”[11]528李宗棠怒斥店主:“复正告以外交,警察无论对待何国,若误用强横手段,岂独自失文明,且必遭意外之不测。我固深知贵国警察办法,虽北海道极野蛮地,亦曾亲往视察,近来民情驯顺,旅馆人甚敬余,余尝佩服贵国人多受良善教育。又告以历年足迹几遍日本,今获承教,实增阅历。”[11]528
(二)嗜利狡诈
虽然李宗棠认为大部分日本人是善良的,但他也碰到了一些嗜利狡诈的商人,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东京吉沼店店员铃木,“为人狡诈,不可与交。前有南洋某官,被骗千余金。”[11]217。另有长崎港一回漕店,“店中小楼数椽,尘埃满室,款待亦不周全。运金、食料种种奇昂,颇有欺诳外人之意。”[11]353
李宗棠还记录了他去正金银行取船票时的一件事:“午前,至正金银行取船票。知西村旅馆从中作弊。此间客店代购船票,向有扣头,与上海情形仿佛。该店因余已托正金银行代购,始而央托,继而倔强,非获此利不肯甘心。”[11]231他在场看着这种情形,感叹嗜利小人可恶亦可笑。李宗棠对大阪商人的印象也不好,他说:“市廛购物,价值无定。外人交易,往往受其欺蒙。不如东京远矣。”[11]109
三、自我文化反思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学者认为:“认识他者,能够帮助认识自我、反省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他者,也就成了认识自我,在认识他者的过程中,能够达到更准确、更全面认识自我的目的,从而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发展。”[15]李宗棠通过日本这一他者,重新审视自我,对“他者”与“自我”之间做出比较,并对自我文化进行反思。
(一)对自我文化形象的反思
李宗棠在日本考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注意观察日本的国民性,并时时与中国相比较,通过日本这个他者,来进行自我文化形象的反思。在目睹日本人为庆祝日俄战争的胜利而举办的各种祝捷会时,李宗棠虽然会感到屈辱,但仍会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赞赏日本人的团体精神,感叹中国没有这种真正的国民团体。在称赞日本游学归来者躬亲技术、不计较报酬时,叹息中国虽游学者众,但都以禄位为目的,少有投身实业者。在受到日本人轻慢时,哀叹我国游历官员素质良莠不齐,致使落人笑柄:“然亦可见我国游历官品类不齐,近年种种笑柄,屡见报端,致贻羞及全体,真可浩叹!”[11]528在考察日本警务时,发现日本警察素质总体较高,“多系高等小学以上中学毕业资格”[12]39,他们审犯人时,“或独诉,或对质,绝不加以恫愒之状”[11]147,对待被抓到的小贼,也只正言劝责,毫无厉色。而中国吏卒多不认字且态度蛮横,与日本警察相比素质差距甚大,对此,李宗棠愤然道:“吏卒识丁无几辈,痴聋荷甲吓愚民。从今休咎凭谁任,莫笑区区独卧薪。”[12]44-45
在与日本国民的对比中,李宗棠发现中国国民的种种缺点:没有团体意识、素质低、自私自利、缺乏公德观念。他在《示以劝晋人游学书》中还提到了中国国民的另外两个缺点:“知守旧不知更新,求近功而无远志也。”[11]307即指中国人守旧,没有创新精神,急功近利。大部分赴日考察的官员会将日本的政治、经济、教育等与中国进行对比,从中看出中国落后的原因,探求解决的方案,但很少有人会反思中国的国民性。李宗棠的文化反思在当时是比较独特的,但与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的论述相比,他的认识则不够系统深刻。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品格的四大缺点: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强调要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改造[16]。李宗棠只指出了中国国民的一些缺点,并没有去深入思考如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二)主张改变自我文化形象
旅人在观看他人之际,同时也会成为他者的观看对象,从他者的反应中,提供了旅人重新审视自我形象的机会。李宗棠在日本时,一开始并没有穿西装,他仍穿华装,维持中国儒者的形象,但屡遭嘲讽。一次是在日本街头,被日本儿童讥讪,一次是被法国少妇嘲讽:“遥望中间座,皆短衣秃头,西人固居多数,东人亦复不少,却无著和服者。而惟我长袍大袖拖辫者,叨陪末座,深觉赧然。法国少妇,举止轻佻,常操英语(毘克台而)、德语(史玩訾)嘲讽之,令人难堪。”[11]349面对他者的嘲讽,李宗棠主张削发、着洋装,改变自我文化形象:
无论国势之弱,人格之低,我国人亦何至为列邦所不齿?殊不知非然也,实厌恶一辫之臭味耳。今余着洋装、覆假发,莫辨揶揄,昂然入座,竟得列为上宾,是即左证。设我国剃发之令一变而为削发之令,万国从同,断无虑此[11]350。
这种自我文化形象的改变,从深层次意义上说,反映了李宗棠的自我文化反思和向日本借鉴的心理,正如他自己所说:“惜当道诸巨公,不能微服远游,略尝忍辱滋味,奏请宸断,效明治之维新。”[11]350
李宗棠对日本国民性的认知,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基本上还是局限于表象的观察,尚未真正认识到军国主义对日本国民性的毒害,没有深刻认识到日本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
(三)对中国教育的反思及贡献
李宗棠在去日本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中日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国需要向西方和日本学习,他说:“怪哉蕞尔国,一跃登文明。呜呼我神州,滓秽乎太清。礼失当求野,物蔽始知盲。远参乎西域,近法乎东瀛。”[12]15在日本考察过程中,李宗棠不断反思日强中弱的原因,探索中国富强的途径。他认识到日本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的振兴:“观于维新以后之政略,而知其强盛所由来。当必自振兴教育始,其次则便利交通最关紧要。”[11]42在李宗棠看来,日本人重视教育,连马夫、车夫都“人人识字”[11]10,而我国教育落后,存在诸多问题:“我国学堂,教授诚不如人,管理亦未合法。是固办学通弊,岂仅江皖为然?”[11]118为了改变中国教育落后的局面,李宗棠做了一个总体规划:“果欲救正其弊,非先造就师范生不可。俟师范众多时,务须广设小学。能从乡学入手,最中肯綮。三五年后,教育自然普及。彼时再筹增设中学堂、专门学堂。俾获循序渐进,免致躐等。”[11]118李宗棠的总体教育规划及他撰写的《考察日本学校记》和《考察学务日记》,“对张之洞普及义务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直接影响到‘癸卯学制’的制订者”[17]。
除了对中国总体教育有影响外,李宗棠对地方教育的贡献则更大。他在山西为官三年,选派、护送首批山西留学生赴日,为山西的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晋省本极闭塞,经宗棠规划,文化进步一日千里,至今以自治模范称于全国,所出英才如阎锡山、崔延献、赵戴文等,皆所造就。”[18]李宗棠还于1909年在南京创设千仓师范学校,鼓励毕业生去其家乡颍上任教。同时在颍上推广乡学,创办了八所千仓义塾,“丙午设第一塾,丁未设第二塾,均在永兴集;王尹庄设第三塾,洄溜集设第四塾,梓树庄设第五塾,姜口集设第六塾,刘家集设第七塾,八里垛设第八塾,均在辛亥年”[19],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